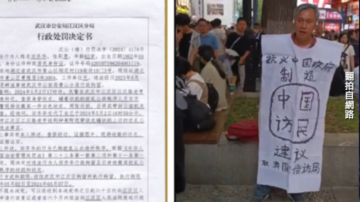【新唐人2007年1月12日訊】熱點互動直播(118)也談《民主是個好東西》:在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
主持人: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直播節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最近中國俞可平發表了一篇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起了海內外的關注。
那麼民主是不是一個好東西?對中國人民來說它需不需要?在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我想這是很多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那麼今天我們就請兩位嘉賓和大家一起進行探討,如果您對民主有疑惑或者您所聽到的朋友,或者其他的人對民主有一些資詢的話,歡迎來電話,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請兩位嘉賓來為您回答,也歡迎您參與我們的討論。
今天是熱線直播,我們的熱線電話號碼是646-519-2879。中國大陸的觀眾朋友也可以打我們的免費電話號碼:179710-8996008663。我再說一遍中國大陸的免費號碼是:179710-8996008663。那現在向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兩位來賓。這位是《北京之春》雜誌的總編胡平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胡平: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那麼這一位是著名的時事評論家陳破空先生,陳先生您好。
陳破空: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我想二位都看了俞可平先生的這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那我想有些觀眾朋友可能還不太了解這篇文章,可不可以先請陳先生先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介紹一下這篇文章?
陳破空:好的。這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一個叫俞可平的人在國內寫的。文字不多,發表在《北京日報》,是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在《北京日報》刊出之後呢,又在別的一些重要的中共黨政的報紙上刊登出來,像《人民網》,或者是一些別的重要的報紙、重要的刊物轉載,紛紛轉載,那麼激起了不小的風潮。
這篇文章主要是,就是首先它承認「民主是一個好東西」,而且承認民主制度是人類實行制度,最好的制度,同時說呢人們即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沒有民主也是人格不完善,這些都是積極的一些語言。
但這篇文章到後面呢,又回到說就是現有的中共的語言體系。它說到中國實現民主不能照搬外國的模式、甚麼要社會主義特色等等,又回到了老的一套,那麼這一正一反就激起了思索和討論。
主持人:那胡先生也看過了這篇文章,您能不能跟我們談一下您看過這篇文章之後對甚麼地方印象比較深?
胡平:我認為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重視,主要還是它發表在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上,就像剛才破空剛剛也談到的,還被一些官方的媒體所轉載,所以人們就懷疑這當中是不是有某種別的背景。
因為在今天,不要說海外的中國人,包括國內的人,不要說異議人士,就包括學院派的這些學者,那麼在談民主方面,談得更清晰、更透澈的是大有人在。就此而言,俞可平先生這篇文章並不算特別的突出。他突出之點呢就是人們懷疑這個是不是有別的背景?是不是表明上面有甚麼意思?所以有人把它稱為是胡錦濤的幕僚、是胡錦濤的文膽等等等等,所以它也可能是從這樣來的。
那我們現在評一下這個文章,我讀這個文章也是著眼於它這種特殊的身份。那就像剛才破空也已經談到了,它這個文章主要優點就在於肯定民主是個好東西,肯定民主。它也指出民主好東西呢,是對國家、對民族而言,不是說對某個個人而言。
而尤其它強調了對那些以個人利益為重的這些官員來說那民主就不是個好東西,是個麻煩東西、是個壞東西。因為你要靠選舉嘛,你就可能選不上等等等等。這也揭露了一些人抵制民主、反對民主,那他們是出自於他們自己個人的私利。
另外他也談到民主就是迄今為止人類設計的發明的最好的制度,儘管它有這樣的那樣的缺陷和不足,那麼這些也對中共當局過去那麼多年來散佈對有關種種對民主不好的那些謬論呢,多多少少是一個駁斥。
可是呢它有它的問題,那就是它留下了幾個尾巴。比如說一談民主,就又談到甚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啦、不要照搬外國模式啦、那麼這就使它原來的積極意義給沖淡了,就變得官方可以利用。
另外它也談到建設中國民主需要客觀的經濟文化社會條件,如果這個條件不具備,那麼實踐民主就會帶來災難。這個也跟中共一貫講的,中國現在還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也等於是在替這種錯誤觀點背書。
當然這個問題,就是不管他正面意思和它反面意思,說得都不是特別明晰,所以從這個講,你也不好特別去批評他。就是認為他在替這個共產黨欺騙世人,你也不能這麼說。但也正因為它不是說得那麼清晰,所以這種話呢也可以在官方的報紙上談出來。
因為比如說最簡單嘛,它談到民主有種種好處,而對甚麼是民主?我們要的甚麼是民主、而我們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它又有那些具體的內涵?你把這些問題說清楚了,我想恐怕它的正面意義就更大了。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是在這個文章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不足。
主持人:那剛才胡先生談到,就是民主其實現在在中國還是非常敏感的字眼。比如說你要是上網的話,打「民主」兩個字的話,可能真的海外有關民主的網站都上不去,可是這篇文章的話,居然能夠在機關報上發表。那就有人有很多的猜測,比如說剛才胡先生說的一項,那您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俞可平這個人?
陳破空:俞可平是一個政治學博士,它現在的職務是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同時兼任了很多大學的教授或是客座教授,四十多歲還算比較年輕,最重要的他是胡錦濤的智囊,所以他的身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因為如果說這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一個普通的人,而一個普通的人寫這篇東西可能不會引起人的注意,但是呢要就上上下下反革命,要嘛就完全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那麼中國有一句古話說「人微而言輕」,反過來說,「人顯而言重」。
正因為他的身份很特別,那麼使人們對此有所猜測,說是不是有來路啊?有來頭有背景?由於這種種的猜測,加重了這篇文章的神祕性,所以說他是這麼一個背景。
主持人:那現在有很多人認為這一篇文章也許是胡錦濤這邊的投石問路,那有人認為是,比如說《文匯報》最近說這是海內跟海外的一些人們的過份的解讀,還有人認為這是放煙霧彈,也就是共產黨的又一個救命稻草。那我想問一下胡先生,您認為為甚麼在這個時候會出它這樣一篇文章呢?
胡平:實際上這篇文章是發表在十月下旬,也就是說離現在都快三個月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那麼大的影響。那可見文章的觀點本身在目前中國也不是那麼突出,因為在那個時候發表這個文章並沒有覺得有特別深厚的其他的背景。
那麼當然最近,現在就是炒得比較熱,我想這裡的原因呢有些情況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是特別清楚。不過一般的推論,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至少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解釋的理由。
比如說,你說現在接著要開十七大,那中共高層免不了就會有權利鬥爭,而在這種鬥爭中間呢,那麼唱一唱民主的調子,總是能夠比較能夠爭取得人心的。另外呢我們也知道過去的這一年多,中共當局,胡溫在這個壓制自由民主方面那還是像過去一樣,而且有些事情還做得很惡劣。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引起外界的很多批評。
那登這篇文章就會使很多人產生一種想法,覺得人家這最高層還是有想有民主的這個願望,所以哪怕說得含糊其詞,就讓人們對他們平白無故的添了好感,這個是當局經常會這麼做的。它說得含含糊糊的對不對,讓人覺得,人家說不定也還要的意思,也不是那麼壞嘛對不對?這個也是一條。
再加上離奧運會的舉行也就只有一年多了,那麼為了奧運的問題,因為當初中共為了申辦奧運,曾經做出了改善中國人權的這麼一個承諾,那麼現在國際社會在這方面呢非常的關注。你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唱一唱民主方面的這樣一個調子,那顯然對這個形象,而且雖然就是那麼大的事情,但是把它炒得這麼熱,引起外界都很關注這個問題,那總是…。
一般對這篇文章的解讀,無論如何,總是解讀得結果總是對中共的形象要稍微有利一點嘛,因為它畢竟不是一篇壞文章嘛,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都是可以考慮,都是可以考慮它的一個背景的背景。
主持人:我們的熱線號碼是646-519-2879,那中國大陸的觀眾朋友也可以打我們的免費號碼179-710-899-600-8663,那今天我們的話題是「也談民主是個好東西」。
所以如果您要有在對中國是不是實現民主這方面有什麼疑問的話,或者您所聽到其他人有任何疑問的話,都歡迎您打電話來提問;如果您有什麼想法,也歡迎您和大家分享。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陳先生您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文章,它對海內外的華人朋友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破空:首先這個民主本身就是個好東西,本身就是一個人類經過這麼數百年、數千年的進化和演變之後,得來的一個迄今為止最認同和最完美、最普及的一個優秀的制度。這個本來是一個常識,不是一個有待發掘的真理,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2/3以上的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民主制度、享受了民主的好處。
俞可平這篇文章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好像在中國激起了石破天驚的感覺,那只能說明反襯了中國這個社會的病態和扭曲,又把常識歪曲了半個多世紀;現在一下子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好像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話,其實這句話就是一個常識,只是反映了一個常識。
這裡面有幾點我們可以透視一下。首先一個,過去我們對共產黨抱了很多希望,當共產黨說什麼的時候,所以我們現在要看它做什麼。
因為在所謂的解放前的四、五十年代,共產黨就高唱民主,三、四十年代,跟國民黨政權就爭民主、爭自由,什麼反飢餓、反獨裁、反內戰,真的結果是它上台之後就說「我們就是要獨裁」。
毛澤東親口講「我就是要獨裁」,什麼「親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就是要獨裁」。那就是說他是公開騙了人,而且自己承認是「陽謀」,這個就是一個謹防再次欺騙。
甚至於在五十年代的時候,毛澤東又搞了一個「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叫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結果說是要「引蛇出洞」,所以這大概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我想今天中共不至於走到毛澤東那種玩大「陽謀」的情況,但是這個是個極端的例子,這些歷史教訓都要讓我們警覺:就說,說什麼不重要,關鍵看你做什麼?現在中共越來越會說話了,大家都知道,越來越善表達了。
主持人:會包裝了。
陳破空:對,會包裝了。但是究竟離行動還有多遠,這是個疑問;你可以今天說這個話,明天說那個話,但是這個都是口頭上的東西、都是言詞上的東西。所以我想綜合這幾方面來看,這是一些負面的因素,我們要警惕的東西。
正面來說,它有幾種可能性。第一種就是說中共這制度是壞的,中共這個黨的主體是壞的,毫無疑問。但是其中有一些人不排除還有一些良知、還有一些人性,還想做一點好事。那麼利用一點機會,發出一點聲音,來推進一些事情,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包括有一些人覺得公開的做不到,通過一些他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角度散放說出來。
同時我們也看到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我們要注意的就說,中共壟斷的不僅是國家權力、國家資源,也壟斷了話語權。談民主的時候,如果別人談,比如說胡先生來談,那就把你當成反革命、顛覆政府,把你當作敵對份子;一旦它談,沒事兒。
所以這是一種霸佔,它不僅霸佔國家資源、國家權力,它霸佔話語權;也就是說我就是要搞民主,也要把你們這些人排除在外、把這反對派排除在外。我不搞民主是我的事,搞民主也是我的事,它要霸佔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要看正面,一種霸權嘴臉的同時,中共在想彌補一些它的東西,想它已經知道它犯了深重的罪孽,它就是來彌補的時候,我也不需要別人來給我提,也不要別人來糾正,我自己去糾正一些東西。然後把糾正好的東西來掩蓋過去的東西,說成是成績,那就繼續當「偉、光、正」,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應該比較注意的。胡平:我接著你剛才提的那個問題。「民主」這個詞,現在在中國、在網上幾乎成為敏感詞了。當然有時候在有些網站上,「中國政府」這個詞都是敏感詞;有時候「江澤民」都是敏感詞。
一方面這些詞中共經常正面的用它,包括「民主」,「民主」這個詞,你看中共從建黨一直用到今天,它的文件裡也是層出不窮、沒斷過。而且有時候它甚至比民主國家還更愛標榜它是民主,它認為它是最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別人都是假民主。
但是這麼多年下來,人們逐漸認識到共產黨所標榜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你那個才是假東西,西方這種民主才是真的民主。因此共產黨就面臨這麼一個為難,它所定義的「民主」,它仍然需要,雖然那是一套謊言。
但是它知道很多人現在談「民主」談的已經不是它那個「民主」,而是真真正正的民主了,所以它就要擋那個真民主。因此「民主」這個詞在它那兒…就像「江澤民」、像「中國政府」,它怎麼稱為敏感詞呢?因為它知道別人一談這個,多半是在罵它,所以乾脆都給拿出去再說,所以現在就成為這麼一個狀況。
俞可平這篇文章我覺得有一個弱點,它對於什麼是民主,沒有給出特別明確的解釋,而這也是中國目前比較忌諱的一點。如果你這一點不是談的很清楚,你光談民主怎麼好怎麼好也一樣,因為共產黨在它的辭彙裡,民主原來也是一個正面的詞,所以這就容易混淆。
當然,從俞可平的文章中的很多觀念來看,其實他還是懂民主的,但談的並不是很清楚。比如說,現在共產黨也談民主,它還出過關於人權民主這方面的白皮書,它強調要共產黨來領導。但我們知道「民主」的意思就是最高權力是要靠競爭、要輪換的,所以有民主就意味著不可能有哪個當然的黨來領導,就好比體育比賽不會有當然的冠軍一樣。
這一點本來是民主的最基本涵義,你把這個涵義一旦突出、明確的表達了,那意思就是說你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是絕對的,不能是當然的,不能寫在憲法裡頭的。如果他這麼一說,而共產黨還敢登出來,那我們可以認為那是一個很可觀的變化。而顯然他這文章儘管對民主是什麼也說了很正確的話,但是他沒有用最清楚的語言把民主是什麼,把最本質的方面明確的表達出來。
主持人:您說到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真正的民主到底是什麼?中共所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又是什麼?就是這個概念我們要分清楚之後才好討論。好,現在我們接下一位紐約劉先生的電話,劉先生請講。
劉先生: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你好!
陳先生、胡先生你們好!我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所謂的「五星紅旗下長大的」。我想問一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領導時的民主,跟日本人打中國時的民主有哪個不同?以前有個「右派」的跟我說過,毛澤東統治的時候比日本人還狠。
其實日本人有沒有民主,我不是那個時代出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日本人有自由,應該有民主的定理灌輸到那裡去。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教授,被趕到鄉下牛棚去做什麼改造,走都不能走,你說有沒有民主?到底是日本人那個時期好,還是毛澤東領導的時期好?我就不明白,所以問問陳博士跟胡先生,我就講這樣多了。
主持人:好,謝謝劉先生。那可不可以請陳先生先回答一下?
陳破空:劉先生,首先謝謝你,我不是博士,不用叫我陳博士了。我想說一下,你是把兩個最惡的東西來對比,這個對比很有意義。日本鬼子侵華,欺負我們中國同胞,欺壓我們中國人,這是一個悪;同時中共專政暴政,欺負中國人,又是一種悪。這兩悪相比,中共之悪大於日本之惡。
這很簡單,因為日本人欺負中國人、打中國人,那是另一個民族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戕害和欺負;中共自己號稱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是自己的所謂黨,自己的人,至少它裡面的人是中國人構成的,所以它來欺負自己的同胞,比外族人欺負自己的同胞來得更狠、來得更猛而且更兇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想中共當然是更惡。
舉個簡單例子:當日本鬼子跟中國軍人作戰的時侯,如果中國軍人英勇作戰最後壯烈犧牲,日本人還表示敬意,軍人對軍人的敬意,還脫帽、還鞠躬、還要隆重的安葬這個中國軍人。
但是共產黨跟國民黨軍人打戰,它是完全無情的,是斬盡殺絕的。它可以用千人火炮對人口密集的錦州城轟擊,不管居民的死活;它可以把長春城團團圍住,圍住幾個月讓長春沒有糧,二十多萬人餓死。所以這是非常殘酷的,而且對方越是英勇的抵抗,它越是把對方徹底的打垮、打死而且毫不留情,也毫無尊重可言,而且它的對手是自己的同胞。
我們看到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國會紀念南北戰爭的時候,他們把北方將軍和南方將軍的銅像放在一起,雖然他們有內戰,但是美國人認為大家都是同胞,都要互相尊重,誰勝誰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是將軍。
但中共這些信念完全沒有,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講,中共當然比日本人更壞。更不用說日本人打中國人,那是一種戰爭的手段,是戰爭時期日本人屠殺中國人。那麼中共不是通過戰爭,它是和平時期,所謂的和平建國,它仍然繼續大規模的屠殺中國人,而且是幾千萬、幾千萬的屠殺,所以這個數量跟日本屠殺中國人的數量是不能對比的。
再一個情況下,不管是日本鬼子來中國或者中共在中國統治,中國人都沒有民主可言,但是比兇殘、比兇惡,中共是更勝於日本鬼子。
主持人:那胡先生有什麼要講嗎?
胡平:他都談了。
主持人:那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我們知道,現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實行民主制度,那麼對大多數人來說,民主到底是甚麼概念?民主要有甚麼樣的特點和因素才能認為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胡平:關於民主,現在一般人大多用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定義,他的定義我這本書裡也都談到過。這定義就是:「民主就是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利。」
因為現在的社會中,由於規模大、人口多,所以很多事情不可能採取直接民主,就是所有的事情大家一起投票來決定,不可能這樣子。所以在今天這個時候講主權在民,他主要體現在人民選出政府,不同的人宣揚他們的主張來競爭人民的選票,獲得選票之後,就代表人民進行統治,然後有一種定期的改選。
在民主國家中,他也提到很根本的東西,首先提到人民的基本人權、基本自由。比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就是很根本的東西,人們一定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尤其是能表達自己不同於政府的意見。
另外在這種社會中,人們一定要有結社的自由,包括組織反對黨的自由;還有這種社會中它有定期的改選,這種改選一定是開放式的,所以就絕不存在哪一個黨壟斷政治權力,把自己認為是當然的執政黨,這就絕對站不住了。
另外還有權力的分立。因為不管怎麼說,掌握權力的人都傾向於濫用權力,只有造成權力之間的平衡,才能使得哪一方面都不能濫用。當他在濫用權力的時候,會遇到來自另外權力的抵制,這樣就造成權力的平衡,而這些東西就是構成民主制度的要件。如果拿這個觀點來看,那就知道今天的中國大陸離這個還非常遙遠。
主持人:那我們現在又有一位觀眾朋友在線上,我們接一下紐約何先生的電話,何先生請講。
何先生:兩位嘉賓好。
胡平:何先生您好。
何先生:今天討論這個民主問題,我想在上個世紀提的這個好東西還要討論討論。今天這個討論,我覺得作這個文章的太幼稚了。今天我報上看了,布什在流淚;去年報上看到了胡錦濤也流淚,登的這篇東西就沒有好下場,在中國裡流淚都沒有民主還有什麼民主?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討論的,好,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何先生。那我想問一下陳先生,何先生的這種想法,可能不只他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他反映人們甚麼樣的心情?
陳破空:沒錯!何先生說得很對,現在討論民主是不是好東西顯得非常幼稚、可笑。雖然近代民主制度好像誕生於西方,但是早在東方就有它發源的源頭。像中國古代大賢孟子說過一句話:「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原始的民主思想。就說主權在民,老百姓是最重要的,要由老百姓來決定。
孔子也主張如果一個暴君不仁的話,民眾是有權利起來推翻他的。所以這個民主思想在很古老的時候就有了。包括唐朝的時侯,唐太宗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也是當時一個很了不起的民主思想。還有一個文官武將的標準說「武死戰、文死諫」,都是講文官要進諫,要給皇帝說真話,哪怕皇帝把你處死,哪怕你撞階而死,你都應該要講真話。
所以今天中共這個集團跟古人都不能相比,沒有一個文官會撞階而死,最了不起的就是彭德懷說了一點話,被毛澤東打入死牢,而且還要不斷的要寫檢查,還要繼續反省自己。沒有人願意為進言而獻出生命,所以說在這個時候中共已經把社會的進步力,落差到最低點,讓文明在中國落差到非常倒退的地步。
因為時間是有成本的,錢放在那裡有利息,沒有利息的話,通貨膨脹會把它抵消掉。同樣的,時間跟政治也有因素,你如果不隨著時間進步,你落在時間後面的話,那你這不算是進步,你連古代都不如。所以在這個時候來討論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確是很荒唐。但這就是中國的大悲劇,這是個非常荒唐和可笑的時代!
主持人:所以我想,我們之所以討論這個話題也是因為很多人覺得中國是應該有民主,所以我們拿出來討論。剛才我們談到了大多數國家對民主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我們看到俞可平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說「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那您覺得他所說的民主和普遍普世對民主的認識有甚麼不同呢?
胡平:問題就在這裡,在中共那裡,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從來都是一個空洞的詞,它從來沒有在這個詞裡加進具體的內容。有時候它又說這個民主不是甚麼,當然也從來不會說它是甚麼。如果它不是甚麼,那你要說反對黨那個東西不能有,對不對?你要說三權分立,那也不能有?
所以我就講了,中國設了社會民主這麼一個框框,你可以看到這裡頭真正的言論自由是沒有的,多黨制是沒有的,權力的分立制衡是沒有的,那到時候還有甚麼呢?你就甚麼都沒有了,所以它也成了這麼一個障眼法。
我為甚麼對這種說法特別反感呢?因為它就是一個空洞的詞,它以此做為理由,說我們不要西方式的民主,而把民主的普世價值,一些最基本的原則通通給拋棄掉了。
所以這裡頭你要談民主,那麼你看,去年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國際會議上大講民主,一口氣講了十幾個民主。那麼這又多個問題了,你講的民主到底是甚麼?他的具體內涵是那些?包括哪些內容?不包括哪些內容?所以這點我覺得是個關鍵的問題。
而現在中共之所以避諱談民主,因為它知道它過去那套謊言,對民主詞意的篡改,在大多人心目中早就已經破了產,所以它以後就乾脆不談。而它每次談的時候都迴避,就包括這篇文章也沒有確切的談論民主的定義,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一定要更密切的關注。主持人:那我們現在又有觀眾朋友在線上等候,我們接一下洛杉磯丁先生的電話,丁先生請講。
丁先生:安娜主播您好,兩位特別來賓晚上好。現在紐約這邊已晚了,各位精神可嘉。我就講一下民主,當年四人幫時代壓榨自由民主而且草菅人命,這當然是很不對。可看我們處在地美國,美國的法律規定不能打小孩,父母不得不把小孩寵壞,將來長大了,你看這小孩變成像當年中國的紅衛兵一樣殺父母的案子很多,這也不太對。
我覺得緬甸的那個翁山蘇姬實在是一個女英雄很不容易,已經差不多有60出頭了吧,所以說把她關押在監牢裡面,那個獨裁男性政府怎麼把一個英勇的女性關在監牢裡面,實在也是很不人道的,翁山蘇姬是個自由民主偉大的領袖,將來會名垂青史。不管她帶領的群眾將來會不會在緬甸掌權,她都已經將來一定會永垂不朽、萬古流芳。
那麼我覺得好像就是歐美各國的泛民主,歐洲還好,歐洲的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打小孩。我在德國當美國空軍的時候,在法蘭克福跟同事在街上走,常常看到那個德國的媽媽打她們的小孩,不過那裡的小孩很多都是從越南、柬埔寨那邊領養過來的,白人也有,他們自己的也有,不乖就動手打,警察也不會去干涉他們,所以說德國人教育小孩比美國人成功,跟我們中國人差不多。而且他們德國的民主絕對不會妨礙對下一代的教育,他們的子女對他們的父母都會很孝順,不亞於中國人…。
主持人:丁先生,你可不可以長話短說,談一下就是你對民主的看法?
丁先生:好。這個民主要適中,不能太過自由、也不能壓榨也好、打壓也好透不過氣來,就好像是完全沒有人道也不行,好謝謝三位。
主持人:謝謝。
陳破空:丁先生,一口氣提了很多問題。我想講一下這個「專制跟民主」它的義意其實很單純。現在在中共語言體系之下,影響了一些人,老是談的民主有西方的或是東方的,什麼西方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或者是還有專制的、有東方專制、西方專制。
我想「專制」的意義很單純,就是「獨斷獨行」,就是鎮壓和壓制異己。「民主」的意義也很單純,就是民眾當家做主。
就是要有公民對權力構成監督,所以它不存在東方或西方的問題,民主即可以在西方實現、也可在東方實現、即可以在美國實現,也可以在日本、韓國、台灣等地實現。同樣的道理,甚至在宗教文化背景沒有不同的地方,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可以同時實現。所以說民主跟專制的它的本義本來是很單純的,沒有什麼區別的。
至於丁先生講的民主能不能太過的問題,剛才舉個例子恰恰證明,舉了一個德國的例子和美國的例子,打小孩的事情,我想這個美國非常注重人權、說不主張打小孩,那麼德國我不太了解,如果是說你的情況那正好印證了這個現實,所以德國不如美國,你看德國挑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兩次敗北,而且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
那麼美國給人類的和平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保護,應該說兩次的世界大戰都是在美國的領導的盟軍戰勝了這個獨裁和極權勢力,戰勝了德國。所以這恰恰說明美國是人類的一個積極的和正確的方向的代表;而德國特別是以前的法西斯德國是人類陰暗的代表。
所以今天的美國是一個環球的一個大國,影響所致遍佈全球,而德國的影響是沒有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如果舉美國和德國的例子,我想應該說尊重人性,這個講人道的美國更佔上風,這也是人類的一個方向。
所以說美國不存說民主太過或泛民主而不好的問題。而且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每一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一半以上是美國人,而這個獎不是在美國評的,是在瑞典或瑞士評的,而不是說一半以上是德國人,所以這個例子也證明美國的教育對孩子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希望丁先生可以再進一步思索一下,謝謝。
胡平:嚴格說來,剛才丁先生談的問題跟民主不民主,不太相干
主持人:對。剛剛我沒有太明白他想要講什麼?
胡平:打孩子、不孩子這個和民主、不民主都不太相干,
主持人:而且可能還有一些文化的習慣?
胡平:它是另外的問題,那他怎麼評價那另當別論,但它不涉及是否泛民主的問題,那麼當然這位丁先生說,這個民主也不能搞得太過,這種說法由於我們缺少一個很具體的一個案例,這也很難說誰過誰沒有過。
不過今天中國而言我想顯然還不存在「過不過的問題」,而是它根本就有沒有的問題。那麼你也可以想像即便中國明天實現了民主,它只好在一段時期之內都它還不太可能出現「太過的問題」,所以我們更關心的就是要讓民主的一些基本的因素,能夠在中國早日實現。
主持人:我看到這個俞可平這篇文章,他談到了就是說,也像剛才丁先生說的很有相似之處,比如這個民主要過了、要適度、要是一個…,我不記得他具體的原話怎麼說了,就是說要有一個精確的制度的設計等等,技巧方面的東西,那你覺得在中國,現在真正的民主是這個問題嗎?陳先生。
陳破空:當然不是,因為這個俞可平這篇文章只有短短的幾百字,那麼他這個正面的意思不用再講了,是有很多了。但另一方面來講他又講到負面的時候,講這個民主說也可能是引發政局的不穏定,所以可能是很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甚至說增大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等等,那他恰恰這個話就反而說反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中共實行專制的時候,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比如說它對付「法輪功」就調動無數的人力、物力、財力。它還用這個有網特、有網警,有這個特務跟蹤,光對一個高智晟就有幾百人的去對付,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
它又在全世界派出特務、派出間諜,到美國去刺探、去監控異議人士,監控法輪功學員、到澳洲去、到加拿大去,所以這個成本非常高,就為了維護它的專制所付出的成本我們看不見,但是這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而且它還有建立監獄、還有建立警察、還有搞祕密審判、還有不斷地轉換車輛交通工具,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那麼實現民主這些東西都可以省的,都不存這些成本了,都不需要誰去跟蹤誰、誰去監視誰,事實上那是很小的,無關國家的安全的事情是不需要做的。所以說成本增高是不存在的。
另外來說,事情變更複雜也是不存在的,因為如果民主要做像三峽大壩這種事情,通過民主的程序,公開的聽證會,科學的決策反而能降低成本,甚至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但是你在專制的條件下,盲目的拍腦袋,拍腦袋的是一個殘廢、是一個智障,它就拍了,結果就建了,成本就非常的高,說不定有一天要炸掉。
你看最近廣州就把一個天河體育館給炸掉了,那我記得我在87年剛到廣州的時候,廣州人也是以天河體育館為自豪的,覺得是一個不得了的工程。認為是當時是不得了的,現在把它給炸掉了。所以在國內有很多豆腐渣工程,這究竟是成本高、還是成本低呢?所以它在舉民主負面的東西時,恰恰舉的是專制的負面。
但也許是這個俞可平先生不得不說這句話,以便文章能夠出籠或者通過,所以也許是言不由衷的,是安慰。事實上他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專制的保守集團。
因為前不久中共的黨校,中央黨校做了一個調查,百分之六十的中共官員對政改不感興趣,它反而對維護社會穩定感興趣,而對政治改革感興趣只佔百分之八,這就說明中共官僚集團已經墮落成一個最守舊的集團。
另外,最近中共在培訓所謂「縣官」,招集了5,300名,分批的縣官在中央黨校培訓,縣委書記、縣長跟著培訓。培訓本身就是證明你縣官不合格,因為在民族條件下選舉出來的官員是經過千挑百選出來,你一上來就賣命的奉獻幹活了還要培訓你才能上任。
主持人:要有這個能力去做。
陳破空:現在還培訓縣官,就說明縣官就不合格,而且它們培訓發現,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概念和政策完全不懂,這說明這些都是不合格嗎?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成本是非常的高昂,而中共的這個集團是非常的守舊,在這種情況下像俞可平這些如果有好意、有好心的話,他去說服這些人的確是難度很高的。
主持人:那好。我們有幾個觀察朋友在線上等候,我們先接一下加拿大的賈女士,賈女士請講。
賈女士:主持人,你好 。
賈女士:我想借對貴臺的機會,想給我中國的執政者說幾句話好嗎?
主持人:好,請講。
賈女士:我是一個中國人,非常希望我們的祖國繁榮富強、人人都能過上平等自由的生活,可是從中國走到國外,我們現在在所謂民主社會,我們深深感到我們中國跟國外的社會方面,方方面面不一樣。
那麼中國的統治階級就說制度和能影響制度的社會主義應該能夠看到,他們最多的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西方來,送到美國、加拿大,那就說明他們也知道這個好,所以我就希望你們能夠知道什麼好,我們要面對好的一面是因為我就希望你們能夠知道什麼好,面對好的一面,放棄大家都不太歡迎的這個不好的制度,讓我們的民主倒是走上真正的繁榮富強,這樣你們這種人也好去面對我們的祖宗;也好去面對我們的後代,對你們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對吧?
大多數一直是為大多數人的謀利益,因為共產黨都少數人謀利,這種世界上什麼是惡?在我們的理解為大多數人是善,因為就有人為什麼不抓住這個機會,為人民、為國家、為自己後代做個好事呢?也為你自己做點好事,我真的衷心希望你們能夠面對這個歷史背景、面對這個現實問題和這種的和目前這種人類共同來為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的中華老百姓千千萬萬的數十億中國老百姓做出善事吧!
主持人:謝謝賈女士,我想你這個誠懇講話,它們都會能看得到、也能知道,那現在我們在接一下加拿大的陳先生的電話,陳先生您請講。
陳先生:你們好,兩位嘉賓你們好,我有個個人的問題問你們兩個個人的問題,在你們有生之年以你們剛才所講的基本民主定義,你們兩個會認為,在你們兩個有生之年能不能見到中國實現?
主持人:好,謝謝陳先生。那我們現在再接下一位觀眾是洛杉磯的周先生,周先生您請講。
周先生:您好,我是在洛杉磯,我現在需要講一下,在美國這邊空談民主非常容易對不對,我不知道你們到中國以後,你們離開中國已經有多久了,我是剛從中國過來,中國的情況你們可能也大概知道一點,貧富差距那麼懸殊、國土幅遠那麼遼闊、人和人之間的差別那麼大,意見那麼多,實行民主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現在從我自己看來,大多數老百姓關心的還不是這個空洞的民主,還是怎麼把自己的生活搞上去,還是怎麼把社會、把這個環境問題解決掉。
所以我想,跟美國這邊談民主,肯定很容易,談民主的定義也很容易,談民主的理論也很容易,談民主的前景也很容易,現在中國最主要的問題還是解決經濟的問題,實行民主是一定要有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基礎,需要有人民很高的素質才能實現,你們也知道台灣這個民主就是我們的一個鏡子,好吧,我大概就說這個,謝謝你們。
主持人:那可不可以請陳先生對剛才幾位觀眾朋友的問題來回答一下。
陳破空:謝謝剛才幾位觀眾的指教,問題提得非常好。我想首先回答洛杉磯周先生的問題,周先生說在美國空談民主很容易,的確在中國很不容易,因為如果你不是胡錦濤的智囊,你在中國談民主可能會坐牢,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講到中國不具備實現民主的條件,講了兩點,其中第二點說貧富差距那麼大、幅員那麼大。首先貧富差距就是因為不民主造成的,在專制的條件下,越靠近權力的人越富有;越遠離權力的人越貧窮,這就是貧富差距的來源。但是一旦民主實現了,權力受到監督不能通過權力支付了,那這種貧富差距當然就會消除,所以這是反過來思考的。
另外你說國家大、幅員遼闊,我想現在世界上有一百零二個民主國家,從來沒有因為國家小和人口稀薄才能實現民主,這些民主國家中,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既有人口稠密,也有人口不稠密的。所以人口多少、國家大小從沒有構成一個民主的條件或者障礙。
另外,你再提到說中國老百姓現在更加關心的是經濟和生活,這個當然是一個方面,但這只是表面的。因為老百姓沒有表達權的時候,你不知道他真實的民意,你看到的是一個虛假的民意,你看到的是中國老百姓在受到約束條件下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沒有辦法的選擇。
他不能在政治上有所選擇,不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不能夠自由的寫自己的作品,他當然只能夠選擇追求錢這麼一條可以選擇的路。但是你一旦開放報禁,開放黨禁,讓老百姓來自由選擇的時候,那時候你周先生聽到真正的民意是什麼?老百姓真的不關心政治只關心經濟嗎?不關心自己的權利只關心生活嗎?我想你現在被虛假的民意所誤導,這是一點。
另外剛才佛羅裡達州的劉先生提到,說PBS的節目,提到人大代表,提到監督政府的事情。我想如果我們記憶力不壞的話,早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或者趙紫陽主政的時代,就有人大代表講出了更加進步的話,說黨政要分開,人大絕不當橡皮圖章,要取得真正的監督功能,所以跟那個時代相比,現在再說這話,我想這不是一個進步,也不是一個變化,只是一個重覆或者是一個恢復。
中國的確在變,因為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中共也不由自主的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與其說中共在變,不如說中國在變;與其說中國在變,不如說世界在變。世界的變動,潮流浩浩蕩蕩、瞬息萬變,引導了中國的變動。而中國的變動引導了中共的變動,所以中共所謂的變化永遠落在民意之後、落在時代之後。它是一個被動的變化,而這個世界、這個中國的變化,民眾的變化卻是一個主動的變化,你要看到這種區別。
另外再一個就是加拿大的陳先生說的個人問題,我們認為有生之年,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我們絕對有信心的說,在我們有生之年,我們一定能看到中國實現民主,因為中國不可能自外於人類文明,謝謝。
主持人:謝謝,那再請胡平先生說一下,剛才還有洛杉磯的周先生,他談到說民主是需要人民的高質素,台灣就是一個鏡子,那我不知道他是一個肯定的意義,還是一個否定的意義,我想你能不能就這個也來回答一下?
胡平:我想剛剛談中國還不具備這樣那樣的條件,人民素質不高,因此還不能民主。這種說法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和民主相對的是甚麼東西?如果不是民主那又是甚麼?所以我老講民主和專制的最大區別就是民主是數人頭,專制是砍人頭。你說不要民主那你就主張砍人頭,很簡單,你就主張捉人、主張殺人。
因為中國人素質還低、還窮,所以統治者就應該去殺人,應該在天安門開槍,應該迫害法輪功,應該迫害議異人士,應該讓有錢人去巧取豪奪?如果你說我不是那個意思,好,那就需要民主。因為人們天生是對各種事情會有不同看法的,所以大家意見是不一致的。
要怎麼樣解決這種不一致?那只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就是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利,就是數人頭,誰得了多數人的支持,誰就能夠執行他的主張,於此同時要保護少數人的的權利;另外一種辦法,那就仗著你有勢力、仗著你有槍桿子,對不同的聲音加以鎮壓。
所以當你說中國現在還不要民主的時候,那你其實就是在說中國現在要專制,而甚麼叫要專制?專制的意思就是要迫害、就是要鎮壓,所以我老講專制這個東西是從來不吃素的,它每天都要吃人肉、喝人血的。只要它有一天它不吃人肉、不喝人血,它就死掉了嘛!
所以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專制和民主的區別,我覺得那就非常清楚了。就像台灣,僅管你對台灣的民主有這樣那樣的批評,但是你單單看,在台灣已經實現了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這一點,就憑這一點,那它就比專制好一萬倍。所以這是問題的一個觀點,這也是俞可平的那篇文章沒有把這點談得特別透徹的。
陳破空:我想補充胡先生的話。說人口素質低是對中國人民的歧視和對中國人民的污辱。我們看香港,香港應該素質不低了吧?經濟發達、文化發達、具國際都市的地位、大都市的地位,而且在硬件上、經濟上、科技上都居領先地位,但是中共還是說它條件不成熟。
可見並不是因為香港人素質不好,也不是因為中國人素質不好,而是中共或者中共的那些官僚根本就不願意實現民主,它願意維持它的獨裁,維持它的既得利益,所以這跟人口素質好與不好沒有關係。
胡平:另外再多談一點素質問題,什麼中產階級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你看蘇聯、東歐的變化就看得很清楚,包括蒙古也在十幾年前就完成民主的轉型。而當蒙古完成民主轉型的時候,當阿爾巴尼亞這些國家作民主轉型的時候,他們的經濟改革當時和中國比,還沒有中國走得遠,他們既沒有自由市場,更談不上中產階級,但是他們同樣完成了民主的轉型。所以這些東西,中產階級、什麼自由市場啊,它都不是實現民主的必要條件。
主持人:我想可能有人會挑戰你這個說法。那你看,東歐或者蘇聯他們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都是…比如說經濟都很困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等等。那你怎麼解釋這種現象呢?
陳破空:那個時候是暫時的,只是在蘇聯解體的頭兩、三年出現了困難,貨架空空,但是即便是俄羅斯那樣的貨架空空也沒有餓死一個人。但是中國呢,中共在和平建政的時候餓死了至少三千多萬人,三千八百萬人,而那個時候的情況並不是很差。我就說過這跟產婦生孩子會有陣痛,陣痛之後是新生命的誕生;同樣的,新舊制度的轉換也是會有陣痛的。
但是今天我們看,今天的俄羅斯是崛起的大國之一,國民經濟是欣欣向榮的,國際地位是日益增高的。今天的東歐有波、捷、匈三國,叫做「東歐三小龍」,波蘭、捷克、匈牙利經濟是快速成長的,這跟共產主義時代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所以今天的短暫陣痛是恰恰相反,它的經濟融入了國際軌道快速發展,跟中國人民得到的、被中共歪曲的信息是不一樣的。
主持人:好,那我們現在再接兩位觀眾朋友的電話,下面請伊利諾依州的吳女士,吳女士您請講。
吳女士:主持人好!特別嘉賓好!我看了這個關於民主的問題,我想請問兩位嘉賓,關於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我想我們在民主社會中生活,那他的文章裡頭提出來的民主跟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民主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胡錦濤在陳良宇的案子出來的時期,他同意顧問團的人說出這種民主的概念來,我請問在你們專家分析上來說,他的目的是什麼?還有作為胡錦濤來說,他現在在中共專制的情況下提出這種民主,能夠走多遠?而且這種改革的民主能夠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麼樣真正的結果和改變?這是我的問題,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那我們現在再接一下紐約一位女士的電話,您請講。
某女士:新唐人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評論員、各位觀眾你們好!我講三個意見。第一個意見我認為呢,中國大陸根本不可能有民主,它說的民主只是假民主,這是欺騙老百姓跟欺騙國際社會的一個更糟糕的手段。
第二個,我認為中共不可能改變了,沒有得變的,如果它會變,豬都爬上樹了!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它現在全世界去騙,中共是全世界的大騙子,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你像高智晟的家屬,他的太太跟小孩子是不懂事的,為什麼要控制小孩子,不給他自由?他的太太,你中共不是講個人做事個人當嗎?他太太跟小孩跟高智晟,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人嘛!那中共只會說、會騙人,自己又做不到,講到做不到!
中共自己本身說什麼都是假的,只有一樣是真的,只有假的東西是真的。你說它還有什麼可變?只有一個,如果它真是要變的話,共產被中共控制這點可能很快就變。第三個就是,我們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中共以最快速度垮台;第二條是如果中共不垮台,整個世界完蛋了。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現在已在這種非常緊急的狀態下,我們不要被中共表面的東西騙倒了!
主持人:好,謝謝,謝謝這位女士。那可不可以請陳先生回答這兩位觀眾朋友所說的、問的問題?
陳破空:剛才吳女士說俞可平提到的民主跟我們現實生活所見證的民主有什麼本質的區別?當然有些本質的區別。因為他作為一個中共的御用文人,作為胡錦濤的智囊,在他提出民主的時候,是有他的框架的,是有他的思維框架的,所以這個是我們應該看到。
但是,我們如果從消極的一面看,那麼那是個煙幕彈,是個厚黑學,是只說不練。因為我們上共產黨的當,上了很多,就算它是真的,我們也寧願抱著不相信的態度。在它還沒有採取行動之前,我們抱著不相信的態度來看待會比較謹慎一些,少上點當、少受點騙。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中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不是黑幕一塊,畢竟還是有些人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想法,那麼通過一些渠道、一些事情、一些自己所處的位置來做一些積極的事情,這種可能性也不會排除。
我是希望胡、溫他們現在黨政軍大權在握,又面臨十七大的人事更弦,面臨奧運會的舉辦,國內外的壓力,希望他們抓住這些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能夠做一些積極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事情,我想這樣會有一些功德。如果僅僅放一些煙幕彈出來哄一哄、騙一騙,應付一下局面,我想最後的結局跟江澤民他們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主持人:那胡先生呢?
胡平:我想說的就是,不論中共的報刊發表這麼一篇文章有什麼意圖,民主是個好東西,這並不是因為它是俞可平說的,而是我們自己這麼認為的。我們要民主,那當然不取決於中共是否有兌現民主的誠意。
所以無論他講這種話是出於什麼樣的背景,對我們來說,我們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去爭取民主的實現。而事實上,即便中共上層有實現民主的願望,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它也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好,謝謝二位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也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打電話參與和您的收看。那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您還有更多的想法,歡迎您寫電子郵件到我們的信箱,feeback@ntdtv.com,感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主持人: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直播節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最近中國俞可平發表了一篇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起了海內外的關注。
那麼民主是不是一個好東西?對中國人民來說它需不需要?在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我想這是很多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那麼今天我們就請兩位嘉賓和大家一起進行探討,如果您對民主有疑惑或者您所聽到的朋友,或者其他的人對民主有一些資詢的話,歡迎來電話,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請兩位嘉賓來為您回答,也歡迎您參與我們的討論。
今天是熱線直播,我們的熱線電話號碼是646-519-2879。中國大陸的觀眾朋友也可以打我們的免費電話號碼:179710-8996008663。我再說一遍中國大陸的免費號碼是:179710-8996008663。那現在向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兩位來賓。這位是《北京之春》雜誌的總編胡平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胡平: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那麼這一位是著名的時事評論家陳破空先生,陳先生您好。
陳破空: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我想二位都看了俞可平先生的這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那我想有些觀眾朋友可能還不太了解這篇文章,可不可以先請陳先生先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介紹一下這篇文章?
陳破空:好的。這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一個叫俞可平的人在國內寫的。文字不多,發表在《北京日報》,是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在《北京日報》刊出之後呢,又在別的一些重要的中共黨政的報紙上刊登出來,像《人民網》,或者是一些別的重要的報紙、重要的刊物轉載,紛紛轉載,那麼激起了不小的風潮。
這篇文章主要是,就是首先它承認「民主是一個好東西」,而且承認民主制度是人類實行制度,最好的制度,同時說呢人們即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沒有民主也是人格不完善,這些都是積極的一些語言。
但這篇文章到後面呢,又回到說就是現有的中共的語言體系。它說到中國實現民主不能照搬外國的模式、甚麼要社會主義特色等等,又回到了老的一套,那麼這一正一反就激起了思索和討論。
主持人:那胡先生也看過了這篇文章,您能不能跟我們談一下您看過這篇文章之後對甚麼地方印象比較深?
胡平:我認為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重視,主要還是它發表在中共北京市委的機關報上,就像剛才破空剛剛也談到的,還被一些官方的媒體所轉載,所以人們就懷疑這當中是不是有某種別的背景。
因為在今天,不要說海外的中國人,包括國內的人,不要說異議人士,就包括學院派的這些學者,那麼在談民主方面,談得更清晰、更透澈的是大有人在。就此而言,俞可平先生這篇文章並不算特別的突出。他突出之點呢就是人們懷疑這個是不是有別的背景?是不是表明上面有甚麼意思?所以有人把它稱為是胡錦濤的幕僚、是胡錦濤的文膽等等等等,所以它也可能是從這樣來的。
那我們現在評一下這個文章,我讀這個文章也是著眼於它這種特殊的身份。那就像剛才破空也已經談到了,它這個文章主要優點就在於肯定民主是個好東西,肯定民主。它也指出民主好東西呢,是對國家、對民族而言,不是說對某個個人而言。
而尤其它強調了對那些以個人利益為重的這些官員來說那民主就不是個好東西,是個麻煩東西、是個壞東西。因為你要靠選舉嘛,你就可能選不上等等等等。這也揭露了一些人抵制民主、反對民主,那他們是出自於他們自己個人的私利。
另外他也談到民主就是迄今為止人類設計的發明的最好的制度,儘管它有這樣的那樣的缺陷和不足,那麼這些也對中共當局過去那麼多年來散佈對有關種種對民主不好的那些謬論呢,多多少少是一個駁斥。
可是呢它有它的問題,那就是它留下了幾個尾巴。比如說一談民主,就又談到甚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啦、不要照搬外國模式啦、那麼這就使它原來的積極意義給沖淡了,就變得官方可以利用。
另外它也談到建設中國民主需要客觀的經濟文化社會條件,如果這個條件不具備,那麼實踐民主就會帶來災難。這個也跟中共一貫講的,中國現在還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也等於是在替這種錯誤觀點背書。
當然這個問題,就是不管他正面意思和它反面意思,說得都不是特別明晰,所以從這個講,你也不好特別去批評他。就是認為他在替這個共產黨欺騙世人,你也不能這麼說。但也正因為它不是說得那麼清晰,所以這種話呢也可以在官方的報紙上談出來。
因為比如說最簡單嘛,它談到民主有種種好處,而對甚麼是民主?我們要的甚麼是民主、而我們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它又有那些具體的內涵?你把這些問題說清楚了,我想恐怕它的正面意義就更大了。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是在這個文章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不足。
主持人:那剛才胡先生談到,就是民主其實現在在中國還是非常敏感的字眼。比如說你要是上網的話,打「民主」兩個字的話,可能真的海外有關民主的網站都上不去,可是這篇文章的話,居然能夠在機關報上發表。那就有人有很多的猜測,比如說剛才胡先生說的一項,那您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俞可平這個人?
陳破空:俞可平是一個政治學博士,它現在的職務是中央編譯局的副局長,同時兼任了很多大學的教授或是客座教授,四十多歲還算比較年輕,最重要的他是胡錦濤的智囊,所以他的身份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因為如果說這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一個普通的人,而一個普通的人寫這篇東西可能不會引起人的注意,但是呢要就上上下下反革命,要嘛就完全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那麼中國有一句古話說「人微而言輕」,反過來說,「人顯而言重」。
正因為他的身份很特別,那麼使人們對此有所猜測,說是不是有來路啊?有來頭有背景?由於這種種的猜測,加重了這篇文章的神祕性,所以說他是這麼一個背景。
主持人:那現在有很多人認為這一篇文章也許是胡錦濤這邊的投石問路,那有人認為是,比如說《文匯報》最近說這是海內跟海外的一些人們的過份的解讀,還有人認為這是放煙霧彈,也就是共產黨的又一個救命稻草。那我想問一下胡先生,您認為為甚麼在這個時候會出它這樣一篇文章呢?
胡平:實際上這篇文章是發表在十月下旬,也就是說離現在都快三個月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那麼大的影響。那可見文章的觀點本身在目前中國也不是那麼突出,因為在那個時候發表這個文章並沒有覺得有特別深厚的其他的背景。
那麼當然最近,現在就是炒得比較熱,我想這裡的原因呢有些情況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是特別清楚。不過一般的推論,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至少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解釋的理由。
比如說,你說現在接著要開十七大,那中共高層免不了就會有權利鬥爭,而在這種鬥爭中間呢,那麼唱一唱民主的調子,總是能夠比較能夠爭取得人心的。另外呢我們也知道過去的這一年多,中共當局,胡溫在這個壓制自由民主方面那還是像過去一樣,而且有些事情還做得很惡劣。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引起外界的很多批評。
那登這篇文章就會使很多人產生一種想法,覺得人家這最高層還是有想有民主的這個願望,所以哪怕說得含糊其詞,就讓人們對他們平白無故的添了好感,這個是當局經常會這麼做的。它說得含含糊糊的對不對,讓人覺得,人家說不定也還要的意思,也不是那麼壞嘛對不對?這個也是一條。
再加上離奧運會的舉行也就只有一年多了,那麼為了奧運的問題,因為當初中共為了申辦奧運,曾經做出了改善中國人權的這麼一個承諾,那麼現在國際社會在這方面呢非常的關注。你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唱一唱民主方面的這樣一個調子,那顯然對這個形象,而且雖然就是那麼大的事情,但是把它炒得這麼熱,引起外界都很關注這個問題,那總是…。
一般對這篇文章的解讀,無論如何,總是解讀得結果總是對中共的形象要稍微有利一點嘛,因為它畢竟不是一篇壞文章嘛,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都是可以考慮,都是可以考慮它的一個背景的背景。
主持人:我們的熱線號碼是646-519-2879,那中國大陸的觀眾朋友也可以打我們的免費號碼179-710-899-600-8663,那今天我們的話題是「也談民主是個好東西」。
所以如果您要有在對中國是不是實現民主這方面有什麼疑問的話,或者您所聽到其他人有任何疑問的話,都歡迎您打電話來提問;如果您有什麼想法,也歡迎您和大家分享。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陳先生您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文章,它對海內外的華人朋友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破空:首先這個民主本身就是個好東西,本身就是一個人類經過這麼數百年、數千年的進化和演變之後,得來的一個迄今為止最認同和最完美、最普及的一個優秀的制度。這個本來是一個常識,不是一個有待發掘的真理,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2/3以上的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民主制度、享受了民主的好處。
俞可平這篇文章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好像在中國激起了石破天驚的感覺,那只能說明反襯了中國這個社會的病態和扭曲,又把常識歪曲了半個多世紀;現在一下子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好像是很了不起的一句話,其實這句話就是一個常識,只是反映了一個常識。
這裡面有幾點我們可以透視一下。首先一個,過去我們對共產黨抱了很多希望,當共產黨說什麼的時候,所以我們現在要看它做什麼。
因為在所謂的解放前的四、五十年代,共產黨就高唱民主,三、四十年代,跟國民黨政權就爭民主、爭自由,什麼反飢餓、反獨裁、反內戰,真的結果是它上台之後就說「我們就是要獨裁」。
毛澤東親口講「我就是要獨裁」,什麼「親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就是要獨裁」。那就是說他是公開騙了人,而且自己承認是「陽謀」,這個就是一個謹防再次欺騙。
甚至於在五十年代的時候,毛澤東又搞了一個「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叫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結果說是要「引蛇出洞」,所以這大概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我想今天中共不至於走到毛澤東那種玩大「陽謀」的情況,但是這個是個極端的例子,這些歷史教訓都要讓我們警覺:就說,說什麼不重要,關鍵看你做什麼?現在中共越來越會說話了,大家都知道,越來越善表達了。
主持人:會包裝了。
陳破空:對,會包裝了。但是究竟離行動還有多遠,這是個疑問;你可以今天說這個話,明天說那個話,但是這個都是口頭上的東西、都是言詞上的東西。所以我想綜合這幾方面來看,這是一些負面的因素,我們要警惕的東西。
正面來說,它有幾種可能性。第一種就是說中共這制度是壞的,中共這個黨的主體是壞的,毫無疑問。但是其中有一些人不排除還有一些良知、還有一些人性,還想做一點好事。那麼利用一點機會,發出一點聲音,來推進一些事情,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包括有一些人覺得公開的做不到,通過一些他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角度散放說出來。
同時我們也看到這裡還有一個問題我們要注意的就說,中共壟斷的不僅是國家權力、國家資源,也壟斷了話語權。談民主的時候,如果別人談,比如說胡先生來談,那就把你當成反革命、顛覆政府,把你當作敵對份子;一旦它談,沒事兒。
所以這是一種霸佔,它不僅霸佔國家資源、國家權力,它霸佔話語權;也就是說我就是要搞民主,也要把你們這些人排除在外、把這反對派排除在外。我不搞民主是我的事,搞民主也是我的事,它要霸佔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我們要看正面,一種霸權嘴臉的同時,中共在想彌補一些它的東西,想它已經知道它犯了深重的罪孽,它就是來彌補的時候,我也不需要別人來給我提,也不要別人來糾正,我自己去糾正一些東西。然後把糾正好的東西來掩蓋過去的東西,說成是成績,那就繼續當「偉、光、正」,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應該比較注意的。胡平:我接著你剛才提的那個問題。「民主」這個詞,現在在中國、在網上幾乎成為敏感詞了。當然有時候在有些網站上,「中國政府」這個詞都是敏感詞;有時候「江澤民」都是敏感詞。
一方面這些詞中共經常正面的用它,包括「民主」,「民主」這個詞,你看中共從建黨一直用到今天,它的文件裡也是層出不窮、沒斷過。而且有時候它甚至比民主國家還更愛標榜它是民主,它認為它是最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別人都是假民主。
但是這麼多年下來,人們逐漸認識到共產黨所標榜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你那個才是假東西,西方這種民主才是真的民主。因此共產黨就面臨這麼一個為難,它所定義的「民主」,它仍然需要,雖然那是一套謊言。
但是它知道很多人現在談「民主」談的已經不是它那個「民主」,而是真真正正的民主了,所以它就要擋那個真民主。因此「民主」這個詞在它那兒…就像「江澤民」、像「中國政府」,它怎麼稱為敏感詞呢?因為它知道別人一談這個,多半是在罵它,所以乾脆都給拿出去再說,所以現在就成為這麼一個狀況。
俞可平這篇文章我覺得有一個弱點,它對於什麼是民主,沒有給出特別明確的解釋,而這也是中國目前比較忌諱的一點。如果你這一點不是談的很清楚,你光談民主怎麼好怎麼好也一樣,因為共產黨在它的辭彙裡,民主原來也是一個正面的詞,所以這就容易混淆。
當然,從俞可平的文章中的很多觀念來看,其實他還是懂民主的,但談的並不是很清楚。比如說,現在共產黨也談民主,它還出過關於人權民主這方面的白皮書,它強調要共產黨來領導。但我們知道「民主」的意思就是最高權力是要靠競爭、要輪換的,所以有民主就意味著不可能有哪個當然的黨來領導,就好比體育比賽不會有當然的冠軍一樣。
這一點本來是民主的最基本涵義,你把這個涵義一旦突出、明確的表達了,那意思就是說你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是絕對的,不能是當然的,不能寫在憲法裡頭的。如果他這麼一說,而共產黨還敢登出來,那我們可以認為那是一個很可觀的變化。而顯然他這文章儘管對民主是什麼也說了很正確的話,但是他沒有用最清楚的語言把民主是什麼,把最本質的方面明確的表達出來。
主持人:您說到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真正的民主到底是什麼?中共所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又是什麼?就是這個概念我們要分清楚之後才好討論。好,現在我們接下一位紐約劉先生的電話,劉先生請講。
劉先生: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你好!
陳先生、胡先生你們好!我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所謂的「五星紅旗下長大的」。我想問一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領導時的民主,跟日本人打中國時的民主有哪個不同?以前有個「右派」的跟我說過,毛澤東統治的時候比日本人還狠。
其實日本人有沒有民主,我不是那個時代出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日本人有自由,應該有民主的定理灌輸到那裡去。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教授,被趕到鄉下牛棚去做什麼改造,走都不能走,你說有沒有民主?到底是日本人那個時期好,還是毛澤東領導的時期好?我就不明白,所以問問陳博士跟胡先生,我就講這樣多了。
主持人:好,謝謝劉先生。那可不可以請陳先生先回答一下?
陳破空:劉先生,首先謝謝你,我不是博士,不用叫我陳博士了。我想說一下,你是把兩個最惡的東西來對比,這個對比很有意義。日本鬼子侵華,欺負我們中國同胞,欺壓我們中國人,這是一個悪;同時中共專政暴政,欺負中國人,又是一種悪。這兩悪相比,中共之悪大於日本之惡。
這很簡單,因為日本人欺負中國人、打中國人,那是另一個民族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戕害和欺負;中共自己號稱是中國人民自己的政權,是自己的所謂黨,自己的人,至少它裡面的人是中國人構成的,所以它來欺負自己的同胞,比外族人欺負自己的同胞來得更狠、來得更猛而且更兇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想中共當然是更惡。
舉個簡單例子:當日本鬼子跟中國軍人作戰的時侯,如果中國軍人英勇作戰最後壯烈犧牲,日本人還表示敬意,軍人對軍人的敬意,還脫帽、還鞠躬、還要隆重的安葬這個中國軍人。
但是共產黨跟國民黨軍人打戰,它是完全無情的,是斬盡殺絕的。它可以用千人火炮對人口密集的錦州城轟擊,不管居民的死活;它可以把長春城團團圍住,圍住幾個月讓長春沒有糧,二十多萬人餓死。所以這是非常殘酷的,而且對方越是英勇的抵抗,它越是把對方徹底的打垮、打死而且毫不留情,也毫無尊重可言,而且它的對手是自己的同胞。
我們看到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國會紀念南北戰爭的時候,他們把北方將軍和南方將軍的銅像放在一起,雖然他們有內戰,但是美國人認為大家都是同胞,都要互相尊重,誰勝誰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是將軍。
但中共這些信念完全沒有,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講,中共當然比日本人更壞。更不用說日本人打中國人,那是一種戰爭的手段,是戰爭時期日本人屠殺中國人。那麼中共不是通過戰爭,它是和平時期,所謂的和平建國,它仍然繼續大規模的屠殺中國人,而且是幾千萬、幾千萬的屠殺,所以這個數量跟日本屠殺中國人的數量是不能對比的。
再一個情況下,不管是日本鬼子來中國或者中共在中國統治,中國人都沒有民主可言,但是比兇殘、比兇惡,中共是更勝於日本鬼子。
主持人:那胡先生有什麼要講嗎?
胡平:他都談了。
主持人:那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我們知道,現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實行民主制度,那麼對大多數人來說,民主到底是甚麼概念?民主要有甚麼樣的特點和因素才能認為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胡平:關於民主,現在一般人大多用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定義,他的定義我這本書裡也都談到過。這定義就是:「民主就是為達到政治決定的一種制度上的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競取人民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利。」
因為現在的社會中,由於規模大、人口多,所以很多事情不可能採取直接民主,就是所有的事情大家一起投票來決定,不可能這樣子。所以在今天這個時候講主權在民,他主要體現在人民選出政府,不同的人宣揚他們的主張來競爭人民的選票,獲得選票之後,就代表人民進行統治,然後有一種定期的改選。
在民主國家中,他也提到很根本的東西,首先提到人民的基本人權、基本自由。比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就是很根本的東西,人們一定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尤其是能表達自己不同於政府的意見。
另外在這種社會中,人們一定要有結社的自由,包括組織反對黨的自由;還有這種社會中它有定期的改選,這種改選一定是開放式的,所以就絕不存在哪一個黨壟斷政治權力,把自己認為是當然的執政黨,這就絕對站不住了。
另外還有權力的分立。因為不管怎麼說,掌握權力的人都傾向於濫用權力,只有造成權力之間的平衡,才能使得哪一方面都不能濫用。當他在濫用權力的時候,會遇到來自另外權力的抵制,這樣就造成權力的平衡,而這些東西就是構成民主制度的要件。如果拿這個觀點來看,那就知道今天的中國大陸離這個還非常遙遠。
主持人:那我們現在又有一位觀眾朋友在線上,我們接一下紐約何先生的電話,何先生請講。
何先生:兩位嘉賓好。
胡平:何先生您好。
何先生:今天討論這個民主問題,我想在上個世紀提的這個好東西還要討論討論。今天這個討論,我覺得作這個文章的太幼稚了。今天我報上看了,布什在流淚;去年報上看到了胡錦濤也流淚,登的這篇東西就沒有好下場,在中國裡流淚都沒有民主還有什麼民主?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討論的,好,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何先生。那我想問一下陳先生,何先生的這種想法,可能不只他一個人有這樣的想法,他反映人們甚麼樣的心情?
陳破空:沒錯!何先生說得很對,現在討論民主是不是好東西顯得非常幼稚、可笑。雖然近代民主制度好像誕生於西方,但是早在東方就有它發源的源頭。像中國古代大賢孟子說過一句話:「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原始的民主思想。就說主權在民,老百姓是最重要的,要由老百姓來決定。
孔子也主張如果一個暴君不仁的話,民眾是有權利起來推翻他的。所以這個民主思想在很古老的時候就有了。包括唐朝的時侯,唐太宗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也是當時一個很了不起的民主思想。還有一個文官武將的標準說「武死戰、文死諫」,都是講文官要進諫,要給皇帝說真話,哪怕皇帝把你處死,哪怕你撞階而死,你都應該要講真話。
所以今天中共這個集團跟古人都不能相比,沒有一個文官會撞階而死,最了不起的就是彭德懷說了一點話,被毛澤東打入死牢,而且還要不斷的要寫檢查,還要繼續反省自己。沒有人願意為進言而獻出生命,所以說在這個時候中共已經把社會的進步力,落差到最低點,讓文明在中國落差到非常倒退的地步。
因為時間是有成本的,錢放在那裡有利息,沒有利息的話,通貨膨脹會把它抵消掉。同樣的,時間跟政治也有因素,你如果不隨著時間進步,你落在時間後面的話,那你這不算是進步,你連古代都不如。所以在這個時候來討論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確是很荒唐。但這就是中國的大悲劇,這是個非常荒唐和可笑的時代!
主持人:所以我想,我們之所以討論這個話題也是因為很多人覺得中國是應該有民主,所以我們拿出來討論。剛才我們談到了大多數國家對民主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我們看到俞可平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說「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那您覺得他所說的民主和普遍普世對民主的認識有甚麼不同呢?
胡平:問題就在這裡,在中共那裡,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從來都是一個空洞的詞,它從來沒有在這個詞裡加進具體的內容。有時候它又說這個民主不是甚麼,當然也從來不會說它是甚麼。如果它不是甚麼,那你要說反對黨那個東西不能有,對不對?你要說三權分立,那也不能有?
所以我就講了,中國設了社會民主這麼一個框框,你可以看到這裡頭真正的言論自由是沒有的,多黨制是沒有的,權力的分立制衡是沒有的,那到時候還有甚麼呢?你就甚麼都沒有了,所以它也成了這麼一個障眼法。
我為甚麼對這種說法特別反感呢?因為它就是一個空洞的詞,它以此做為理由,說我們不要西方式的民主,而把民主的普世價值,一些最基本的原則通通給拋棄掉了。
所以這裡頭你要談民主,那麼你看,去年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國際會議上大講民主,一口氣講了十幾個民主。那麼這又多個問題了,你講的民主到底是甚麼?他的具體內涵是那些?包括哪些內容?不包括哪些內容?所以這點我覺得是個關鍵的問題。
而現在中共之所以避諱談民主,因為它知道它過去那套謊言,對民主詞意的篡改,在大多人心目中早就已經破了產,所以它以後就乾脆不談。而它每次談的時候都迴避,就包括這篇文章也沒有確切的談論民主的定義,所以我們在這一點上一定要更密切的關注。主持人:那我們現在又有觀眾朋友在線上等候,我們接一下洛杉磯丁先生的電話,丁先生請講。
丁先生:安娜主播您好,兩位特別來賓晚上好。現在紐約這邊已晚了,各位精神可嘉。我就講一下民主,當年四人幫時代壓榨自由民主而且草菅人命,這當然是很不對。可看我們處在地美國,美國的法律規定不能打小孩,父母不得不把小孩寵壞,將來長大了,你看這小孩變成像當年中國的紅衛兵一樣殺父母的案子很多,這也不太對。
我覺得緬甸的那個翁山蘇姬實在是一個女英雄很不容易,已經差不多有60出頭了吧,所以說把她關押在監牢裡面,那個獨裁男性政府怎麼把一個英勇的女性關在監牢裡面,實在也是很不人道的,翁山蘇姬是個自由民主偉大的領袖,將來會名垂青史。不管她帶領的群眾將來會不會在緬甸掌權,她都已經將來一定會永垂不朽、萬古流芳。
那麼我覺得好像就是歐美各國的泛民主,歐洲還好,歐洲的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打小孩。我在德國當美國空軍的時候,在法蘭克福跟同事在街上走,常常看到那個德國的媽媽打她們的小孩,不過那裡的小孩很多都是從越南、柬埔寨那邊領養過來的,白人也有,他們自己的也有,不乖就動手打,警察也不會去干涉他們,所以說德國人教育小孩比美國人成功,跟我們中國人差不多。而且他們德國的民主絕對不會妨礙對下一代的教育,他們的子女對他們的父母都會很孝順,不亞於中國人…。
主持人:丁先生,你可不可以長話短說,談一下就是你對民主的看法?
丁先生:好。這個民主要適中,不能太過自由、也不能壓榨也好、打壓也好透不過氣來,就好像是完全沒有人道也不行,好謝謝三位。
主持人:謝謝。
陳破空:丁先生,一口氣提了很多問題。我想講一下這個「專制跟民主」它的義意其實很單純。現在在中共語言體系之下,影響了一些人,老是談的民主有西方的或是東方的,什麼西方的民主不適合中國或者是還有專制的、有東方專制、西方專制。
我想「專制」的意義很單純,就是「獨斷獨行」,就是鎮壓和壓制異己。「民主」的意義也很單純,就是民眾當家做主。
就是要有公民對權力構成監督,所以它不存在東方或西方的問題,民主即可以在西方實現、也可在東方實現、即可以在美國實現,也可以在日本、韓國、台灣等地實現。同樣的道理,甚至在宗教文化背景沒有不同的地方,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可以同時實現。所以說民主跟專制的它的本義本來是很單純的,沒有什麼區別的。
至於丁先生講的民主能不能太過的問題,剛才舉個例子恰恰證明,舉了一個德國的例子和美國的例子,打小孩的事情,我想這個美國非常注重人權、說不主張打小孩,那麼德國我不太了解,如果是說你的情況那正好印證了這個現實,所以德國不如美國,你看德國挑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兩次敗北,而且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
那麼美國給人類的和平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保護,應該說兩次的世界大戰都是在美國的領導的盟軍戰勝了這個獨裁和極權勢力,戰勝了德國。所以這恰恰說明美國是人類的一個積極的和正確的方向的代表;而德國特別是以前的法西斯德國是人類陰暗的代表。
所以今天的美國是一個環球的一個大國,影響所致遍佈全球,而德國的影響是沒有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如果舉美國和德國的例子,我想應該說尊重人性,這個講人道的美國更佔上風,這也是人類的一個方向。
所以說美國不存說民主太過或泛民主而不好的問題。而且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每一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一半以上是美國人,而這個獎不是在美國評的,是在瑞典或瑞士評的,而不是說一半以上是德國人,所以這個例子也證明美國的教育對孩子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希望丁先生可以再進一步思索一下,謝謝。
胡平:嚴格說來,剛才丁先生談的問題跟民主不民主,不太相干
主持人:對。剛剛我沒有太明白他想要講什麼?
胡平:打孩子、不孩子這個和民主、不民主都不太相干,
主持人:而且可能還有一些文化的習慣?
胡平:它是另外的問題,那他怎麼評價那另當別論,但它不涉及是否泛民主的問題,那麼當然這位丁先生說,這個民主也不能搞得太過,這種說法由於我們缺少一個很具體的一個案例,這也很難說誰過誰沒有過。
不過今天中國而言我想顯然還不存在「過不過的問題」,而是它根本就有沒有的問題。那麼你也可以想像即便中國明天實現了民主,它只好在一段時期之內都它還不太可能出現「太過的問題」,所以我們更關心的就是要讓民主的一些基本的因素,能夠在中國早日實現。
主持人:我看到這個俞可平這篇文章,他談到了就是說,也像剛才丁先生說的很有相似之處,比如這個民主要過了、要適度、要是一個…,我不記得他具體的原話怎麼說了,就是說要有一個精確的制度的設計等等,技巧方面的東西,那你覺得在中國,現在真正的民主是這個問題嗎?陳先生。
陳破空:當然不是,因為這個俞可平這篇文章只有短短的幾百字,那麼他這個正面的意思不用再講了,是有很多了。但另一方面來講他又講到負面的時候,講這個民主說也可能是引發政局的不穏定,所以可能是很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甚至說增大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等等,那他恰恰這個話就反而說反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中共實行專制的時候,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比如說它對付「法輪功」就調動無數的人力、物力、財力。它還用這個有網特、有網警,有這個特務跟蹤,光對一個高智晟就有幾百人的去對付,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
它又在全世界派出特務、派出間諜,到美國去刺探、去監控異議人士,監控法輪功學員、到澳洲去、到加拿大去,所以這個成本非常高,就為了維護它的專制所付出的成本我們看不見,但是這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而且它還有建立監獄、還有建立警察、還有搞祕密審判、還有不斷地轉換車輛交通工具,這個成本是非常高的。那麼實現民主這些東西都可以省的,都不存這些成本了,都不需要誰去跟蹤誰、誰去監視誰,事實上那是很小的,無關國家的安全的事情是不需要做的。所以說成本增高是不存在的。
另外來說,事情變更複雜也是不存在的,因為如果民主要做像三峽大壩這種事情,通過民主的程序,公開的聽證會,科學的決策反而能降低成本,甚至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但是你在專制的條件下,盲目的拍腦袋,拍腦袋的是一個殘廢、是一個智障,它就拍了,結果就建了,成本就非常的高,說不定有一天要炸掉。
你看最近廣州就把一個天河體育館給炸掉了,那我記得我在87年剛到廣州的時候,廣州人也是以天河體育館為自豪的,覺得是一個不得了的工程。認為是當時是不得了的,現在把它給炸掉了。所以在國內有很多豆腐渣工程,這究竟是成本高、還是成本低呢?所以它在舉民主負面的東西時,恰恰舉的是專制的負面。
但也許是這個俞可平先生不得不說這句話,以便文章能夠出籠或者通過,所以也許是言不由衷的,是安慰。事實上他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專制的保守集團。
因為前不久中共的黨校,中央黨校做了一個調查,百分之六十的中共官員對政改不感興趣,它反而對維護社會穩定感興趣,而對政治改革感興趣只佔百分之八,這就說明中共官僚集團已經墮落成一個最守舊的集團。
另外,最近中共在培訓所謂「縣官」,招集了5,300名,分批的縣官在中央黨校培訓,縣委書記、縣長跟著培訓。培訓本身就是證明你縣官不合格,因為在民族條件下選舉出來的官員是經過千挑百選出來,你一上來就賣命的奉獻幹活了還要培訓你才能上任。
主持人:要有這個能力去做。
陳破空:現在還培訓縣官,就說明縣官就不合格,而且它們培訓發現,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概念和政策完全不懂,這說明這些都是不合格嗎?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成本是非常的高昂,而中共的這個集團是非常的守舊,在這種情況下像俞可平這些如果有好意、有好心的話,他去說服這些人的確是難度很高的。
主持人:那好。我們有幾個觀察朋友在線上等候,我們先接一下加拿大的賈女士,賈女士請講。
賈女士:主持人,你好 。
賈女士:我想借對貴臺的機會,想給我中國的執政者說幾句話好嗎?
主持人:好,請講。
賈女士:我是一個中國人,非常希望我們的祖國繁榮富強、人人都能過上平等自由的生活,可是從中國走到國外,我們現在在所謂民主社會,我們深深感到我們中國跟國外的社會方面,方方面面不一樣。
那麼中國的統治階級就說制度和能影響制度的社會主義應該能夠看到,他們最多的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西方來,送到美國、加拿大,那就說明他們也知道這個好,所以我就希望你們能夠知道什麼好,我們要面對好的一面是因為我就希望你們能夠知道什麼好,面對好的一面,放棄大家都不太歡迎的這個不好的制度,讓我們的民主倒是走上真正的繁榮富強,這樣你們這種人也好去面對我們的祖宗;也好去面對我們的後代,對你們自己也有個好的交代,對吧?
大多數一直是為大多數人的謀利益,因為共產黨都少數人謀利,這種世界上什麼是惡?在我們的理解為大多數人是善,因為就有人為什麼不抓住這個機會,為人民、為國家、為自己後代做個好事呢?也為你自己做點好事,我真的衷心希望你們能夠面對這個歷史背景、面對這個現實問題和這種的和目前這種人類共同來為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的中華老百姓千千萬萬的數十億中國老百姓做出善事吧!
主持人:謝謝賈女士,我想你這個誠懇講話,它們都會能看得到、也能知道,那現在我們在接一下加拿大的陳先生的電話,陳先生您請講。
陳先生:你們好,兩位嘉賓你們好,我有個個人的問題問你們兩個個人的問題,在你們有生之年以你們剛才所講的基本民主定義,你們兩個會認為,在你們兩個有生之年能不能見到中國實現?
主持人:好,謝謝陳先生。那我們現在再接下一位觀眾是洛杉磯的周先生,周先生您請講。
周先生:您好,我是在洛杉磯,我現在需要講一下,在美國這邊空談民主非常容易對不對,我不知道你們到中國以後,你們離開中國已經有多久了,我是剛從中國過來,中國的情況你們可能也大概知道一點,貧富差距那麼懸殊、國土幅遠那麼遼闊、人和人之間的差別那麼大,意見那麼多,實行民主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現在從我自己看來,大多數老百姓關心的還不是這個空洞的民主,還是怎麼把自己的生活搞上去,還是怎麼把社會、把這個環境問題解決掉。
所以我想,跟美國這邊談民主,肯定很容易,談民主的定義也很容易,談民主的理論也很容易,談民主的前景也很容易,現在中國最主要的問題還是解決經濟的問題,實行民主是一定要有廣泛的中產階級的基礎,需要有人民很高的素質才能實現,你們也知道台灣這個民主就是我們的一個鏡子,好吧,我大概就說這個,謝謝你們。
主持人:那可不可以請陳先生對剛才幾位觀眾朋友的問題來回答一下。
陳破空:謝謝剛才幾位觀眾的指教,問題提得非常好。我想首先回答洛杉磯周先生的問題,周先生說在美國空談民主很容易,的確在中國很不容易,因為如果你不是胡錦濤的智囊,你在中國談民主可能會坐牢,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講到中國不具備實現民主的條件,講了兩點,其中第二點說貧富差距那麼大、幅員那麼大。首先貧富差距就是因為不民主造成的,在專制的條件下,越靠近權力的人越富有;越遠離權力的人越貧窮,這就是貧富差距的來源。但是一旦民主實現了,權力受到監督不能通過權力支付了,那這種貧富差距當然就會消除,所以這是反過來思考的。
另外你說國家大、幅員遼闊,我想現在世界上有一百零二個民主國家,從來沒有因為國家小和人口稀薄才能實現民主,這些民主國家中,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既有人口稠密,也有人口不稠密的。所以人口多少、國家大小從沒有構成一個民主的條件或者障礙。
另外,你再提到說中國老百姓現在更加關心的是經濟和生活,這個當然是一個方面,但這只是表面的。因為老百姓沒有表達權的時候,你不知道他真實的民意,你看到的是一個虛假的民意,你看到的是中國老百姓在受到約束條件下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沒有辦法的選擇。
他不能在政治上有所選擇,不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不能夠自由的寫自己的作品,他當然只能夠選擇追求錢這麼一條可以選擇的路。但是你一旦開放報禁,開放黨禁,讓老百姓來自由選擇的時候,那時候你周先生聽到真正的民意是什麼?老百姓真的不關心政治只關心經濟嗎?不關心自己的權利只關心生活嗎?我想你現在被虛假的民意所誤導,這是一點。
另外剛才佛羅裡達州的劉先生提到,說PBS的節目,提到人大代表,提到監督政府的事情。我想如果我們記憶力不壞的話,早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或者趙紫陽主政的時代,就有人大代表講出了更加進步的話,說黨政要分開,人大絕不當橡皮圖章,要取得真正的監督功能,所以跟那個時代相比,現在再說這話,我想這不是一個進步,也不是一個變化,只是一個重覆或者是一個恢復。
中國的確在變,因為世界在變、中國在變,中共也不由自主的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與其說中共在變,不如說中國在變;與其說中國在變,不如說世界在變。世界的變動,潮流浩浩蕩蕩、瞬息萬變,引導了中國的變動。而中國的變動引導了中共的變動,所以中共所謂的變化永遠落在民意之後、落在時代之後。它是一個被動的變化,而這個世界、這個中國的變化,民眾的變化卻是一個主動的變化,你要看到這種區別。
另外再一個就是加拿大的陳先生說的個人問題,我們認為有生之年,中國能不能實現民主?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我們絕對有信心的說,在我們有生之年,我們一定能看到中國實現民主,因為中國不可能自外於人類文明,謝謝。
主持人:謝謝,那再請胡平先生說一下,剛才還有洛杉磯的周先生,他談到說民主是需要人民的高質素,台灣就是一個鏡子,那我不知道他是一個肯定的意義,還是一個否定的意義,我想你能不能就這個也來回答一下?
胡平:我想剛剛談中國還不具備這樣那樣的條件,人民素質不高,因此還不能民主。這種說法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和民主相對的是甚麼東西?如果不是民主那又是甚麼?所以我老講民主和專制的最大區別就是民主是數人頭,專制是砍人頭。你說不要民主那你就主張砍人頭,很簡單,你就主張捉人、主張殺人。
因為中國人素質還低、還窮,所以統治者就應該去殺人,應該在天安門開槍,應該迫害法輪功,應該迫害議異人士,應該讓有錢人去巧取豪奪?如果你說我不是那個意思,好,那就需要民主。因為人們天生是對各種事情會有不同看法的,所以大家意見是不一致的。
要怎麼樣解決這種不一致?那只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就是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利,就是數人頭,誰得了多數人的支持,誰就能夠執行他的主張,於此同時要保護少數人的的權利;另外一種辦法,那就仗著你有勢力、仗著你有槍桿子,對不同的聲音加以鎮壓。
所以當你說中國現在還不要民主的時候,那你其實就是在說中國現在要專制,而甚麼叫要專制?專制的意思就是要迫害、就是要鎮壓,所以我老講專制這個東西是從來不吃素的,它每天都要吃人肉、喝人血的。只要它有一天它不吃人肉、不喝人血,它就死掉了嘛!
所以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專制和民主的區別,我覺得那就非常清楚了。就像台灣,僅管你對台灣的民主有這樣那樣的批評,但是你單單看,在台灣已經實現了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這一點,就憑這一點,那它就比專制好一萬倍。所以這是問題的一個觀點,這也是俞可平的那篇文章沒有把這點談得特別透徹的。
陳破空:我想補充胡先生的話。說人口素質低是對中國人民的歧視和對中國人民的污辱。我們看香港,香港應該素質不低了吧?經濟發達、文化發達、具國際都市的地位、大都市的地位,而且在硬件上、經濟上、科技上都居領先地位,但是中共還是說它條件不成熟。
可見並不是因為香港人素質不好,也不是因為中國人素質不好,而是中共或者中共的那些官僚根本就不願意實現民主,它願意維持它的獨裁,維持它的既得利益,所以這跟人口素質好與不好沒有關係。
胡平:另外再多談一點素質問題,什麼中產階級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你看蘇聯、東歐的變化就看得很清楚,包括蒙古也在十幾年前就完成民主的轉型。而當蒙古完成民主轉型的時候,當阿爾巴尼亞這些國家作民主轉型的時候,他們的經濟改革當時和中國比,還沒有中國走得遠,他們既沒有自由市場,更談不上中產階級,但是他們同樣完成了民主的轉型。所以這些東西,中產階級、什麼自由市場啊,它都不是實現民主的必要條件。
主持人:我想可能有人會挑戰你這個說法。那你看,東歐或者蘇聯他們在民主轉型之後,國家都是…比如說經濟都很困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等等等等。那你怎麼解釋這種現象呢?
陳破空:那個時候是暫時的,只是在蘇聯解體的頭兩、三年出現了困難,貨架空空,但是即便是俄羅斯那樣的貨架空空也沒有餓死一個人。但是中國呢,中共在和平建政的時候餓死了至少三千多萬人,三千八百萬人,而那個時候的情況並不是很差。我就說過這跟產婦生孩子會有陣痛,陣痛之後是新生命的誕生;同樣的,新舊制度的轉換也是會有陣痛的。
但是今天我們看,今天的俄羅斯是崛起的大國之一,國民經濟是欣欣向榮的,國際地位是日益增高的。今天的東歐有波、捷、匈三國,叫做「東歐三小龍」,波蘭、捷克、匈牙利經濟是快速成長的,這跟共產主義時代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所以今天的短暫陣痛是恰恰相反,它的經濟融入了國際軌道快速發展,跟中國人民得到的、被中共歪曲的信息是不一樣的。
主持人:好,那我們現在再接兩位觀眾朋友的電話,下面請伊利諾依州的吳女士,吳女士您請講。
吳女士:主持人好!特別嘉賓好!我看了這個關於民主的問題,我想請問兩位嘉賓,關於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我想我們在民主社會中生活,那他的文章裡頭提出來的民主跟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民主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胡錦濤在陳良宇的案子出來的時期,他同意顧問團的人說出這種民主的概念來,我請問在你們專家分析上來說,他的目的是什麼?還有作為胡錦濤來說,他現在在中共專制的情況下提出這種民主,能夠走多遠?而且這種改革的民主能夠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麼樣真正的結果和改變?這是我的問題,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那我們現在再接一下紐約一位女士的電話,您請講。
某女士:新唐人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評論員、各位觀眾你們好!我講三個意見。第一個意見我認為呢,中國大陸根本不可能有民主,它說的民主只是假民主,這是欺騙老百姓跟欺騙國際社會的一個更糟糕的手段。
第二個,我認為中共不可能改變了,沒有得變的,如果它會變,豬都爬上樹了!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它現在全世界去騙,中共是全世界的大騙子,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你像高智晟的家屬,他的太太跟小孩子是不懂事的,為什麼要控制小孩子,不給他自由?他的太太,你中共不是講個人做事個人當嗎?他太太跟小孩跟高智晟,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人嘛!那中共只會說、會騙人,自己又做不到,講到做不到!
中共自己本身說什麼都是假的,只有一樣是真的,只有假的東西是真的。你說它還有什麼可變?只有一個,如果它真是要變的話,共產被中共控制這點可能很快就變。第三個就是,我們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中共以最快速度垮台;第二條是如果中共不垮台,整個世界完蛋了。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現在已在這種非常緊急的狀態下,我們不要被中共表面的東西騙倒了!
主持人:好,謝謝,謝謝這位女士。那可不可以請陳先生回答這兩位觀眾朋友所說的、問的問題?
陳破空:剛才吳女士說俞可平提到的民主跟我們現實生活所見證的民主有什麼本質的區別?當然有些本質的區別。因為他作為一個中共的御用文人,作為胡錦濤的智囊,在他提出民主的時候,是有他的框架的,是有他的思維框架的,所以這個是我們應該看到。
但是,我們如果從消極的一面看,那麼那是個煙幕彈,是個厚黑學,是只說不練。因為我們上共產黨的當,上了很多,就算它是真的,我們也寧願抱著不相信的態度。在它還沒有採取行動之前,我們抱著不相信的態度來看待會比較謹慎一些,少上點當、少受點騙。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中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不是黑幕一塊,畢竟還是有些人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想法,那麼通過一些渠道、一些事情、一些自己所處的位置來做一些積極的事情,這種可能性也不會排除。
我是希望胡、溫他們現在黨政軍大權在握,又面臨十七大的人事更弦,面臨奧運會的舉辦,國內外的壓力,希望他們抓住這些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能夠做一些積極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事情,我想這樣會有一些功德。如果僅僅放一些煙幕彈出來哄一哄、騙一騙,應付一下局面,我想最後的結局跟江澤民他們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主持人:那胡先生呢?
胡平:我想說的就是,不論中共的報刊發表這麼一篇文章有什麼意圖,民主是個好東西,這並不是因為它是俞可平說的,而是我們自己這麼認為的。我們要民主,那當然不取決於中共是否有兌現民主的誠意。
所以無論他講這種話是出於什麼樣的背景,對我們來說,我們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去爭取民主的實現。而事實上,即便中共上層有實現民主的願望,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它也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好,謝謝二位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也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打電話參與和您的收看。那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您還有更多的想法,歡迎您寫電子郵件到我們的信箱,feeback@ntdtv.com,感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