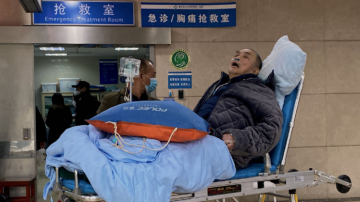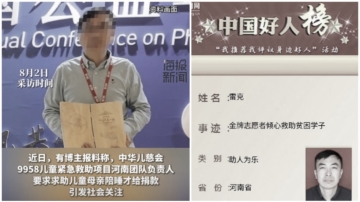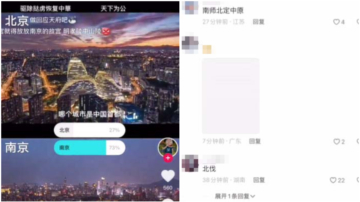【新唐人記者林丹綜合報道】中國政府再次由於懼怕異議人士的不同聲音,拒絕給獨立中文筆會前祕書長,現居瑞典的張鈺博士延長護照。
十一月十九號,星期三,獨立中文筆會前祕書長,居住在瑞典的張鈺博士也接到駐瑞典的中國使館的通知,拒絕給他延長護照。有關這個事件的情況,記者采訪了張鈺博士,他向自由亞洲記者天溢介紹說:(錄音)“上個月我去換護照了,我的護照是明年二月到期,大概需要三周。所以昨天我就去了使館,他說根據外交部方面的指示,不能給我換護照。我問,為什麼?他說,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我說,我知道我沒有做什麼壞事。你必須告訴我!他說根據外交部領事司的批復,說是我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不予換照。”
對此,張鈺博士要求他們具體講明是根據什麼法律,(錄音)“他們說,你自己去查,我就說有幾百條法律,我自己如何去查。他就說,反正是根據法律。我說,恐怕是沒有這條法律吧!外交部外事司也沒有權力決定一個人的罪名。這罪名是司法部門決定的。你們憑什麼?他說,你要有意見可以向外交部領事司去投訴。你跟我們說也沒有用,我們是執行命令的。”
為此,張鈺博士退一步要求他們給予一個書面答復,(錄音)“他說,我們這麼多人在這兒,我們還會騙你!我說,要是按照你的道理,法庭法官說,當着那麼多人宣判了,那人家就不出判決書了!哪有這個道理!我正式申請,你正式答復卻是口頭的。他說,我們就是口頭的,我們作為外事機構是有權力給成文的東西,也可以給不成文的東西。我說,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有義務為我服務。他沒話說,然後就說,反正你不管怎麼說,你的事,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張鈺(右),萬之,齊思盈2005年11月在紐約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新聞自由獎發獎晚會上
對此,張鈺博士聯系到最近包括多位德國漢學家在內的四十九人維護中國政府的公開信說,(錄音)“我就想起來了,四十九人寫的回信說,我們在爭論中國政府是個流氓政府,還是值得信任的伙伴。這整個是個流氓無賴嗎!”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政府感到已經難以像以前那樣保持國內統治的的穩定,因此對於海外的異議人士采取吊銷護照,對於國內的異議人士采取驅逐出國的做法。最近幾年,這種做法沒有因為國內所謂經濟形勢的好轉而有所緩和,反而更加擴大。
【附錄 】給胡錦濤主席的申訴信
胡錦濤主席:
我歡迎您到瑞典訪問,不僅是因為您可以向瑞典的先進社會制度學習,而且還因為您所提倡的“和諧社會”可能有希望改正貴黨政府處理本案所犯的錯誤,包括非法剝奪我入境祖國的中國公民權利。
我估計您沒有收到我在今年四月給溫家寶總理信的副本(如下所示),我是通過電郵請貴州省的國安部門轉交的,因為當我妻子在今年初帶着幾個小孩回國探望她父母時,這個部門的人員就多次傳訊她,詢問有關我的情況,到她回瑞典後也未放松。我還未收到溫總理那方面的答復,只聽說國安又驚擾了我在國內更多的親屬。事實上,他們至少在一年前就開始這麼做了,只是在我被拒絕入境前沒讓我們夫妻知道而已。
由於國內有關當局至今未答復我的問題,我不得不利用您來訪的機會向您提出申訴,希望您所關注的“和諧社會”能具有現實意義,也包括同是中國公民的我本人及親屬,希望您在百忙之中責成有關部門:
1)讓警察停止驚擾我的家庭成員和親戚——因為他們與我的言行毫無關系,甚至都不曾聽說我的近況,所以無論警方用什麼罪名來對付我,也沒有任何理由株連他們。
2)敦促處理此案的部門盡快改正錯誤,尊重我回國和探母的基本權利。
望您或貴黨政府早日給我一個答復。預祝你訪瑞及提倡全民和諧社會的成功。
張鈺
2007年6月4日

獨立中文筆會原祕書長張鈺博士
就在北京西站被拒入境事給溫家寶總理的信
溫家寶總理:您好!
我是旅居瑞典的中國公民,現因今年2月7日下午在北京鐵路西客站入境被拒事,不得已向您投訴。
2007年2月7日下午4點35分,我所乘的T98次京港直通快車在晚點一個多小時後到達北京西客站;大約剛過5點,我在該站的入境邊防檢查站出示護照後被邊檢警察帶入“留置室”;大約7點左右,北京鐵路西客站出入境邊防檢查站(以下簡稱“邊防站”)副站長殷明先生向我正式傳達上級決定:“由於你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現決定拒絕你入境,由你自己購買機票,返回你的原出境地香港”(大意,下同);直到當晚9點左右被遣送到飛往香港的國泰CX2039航班登機口,失去人身自由約四小時。在這約四個小時中,邊檢警察除了“根據上級指示”、“要等上級決定”、“傳達上級決定”等口頭說法之外,盡管我一再要求和抗議,也沒有出示任何有權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以及將我遣送出境的文字,既沒有向我出示任何相關的司法文書,也沒有辦理任何相關的行政手續,甚至連口頭說明的合法依據或條文引用都不存在。在整個過程中,唯一履行了法律程序的是:向我宣布要根據相關法規搜查我的身體和攜帶物品,為此要我在相關表格上簽字認可,我毫無異議地照辦了。(不過,邊檢警察除了幫我搬拖行李和押送我去機場是擠坐一車,並無任何人主動碰過我的身體和物品,對於這種人格上的尊重,我在此向殷明先生和所有當值警察表示由衷的感謝)。
根據我對中國法律、法規的了解,北京鐵路西客站出入境邊防檢查站根據所謂“上級指示”和“上級決定”對我的處置,有諸多涉嫌違法之處,現按時間發生順序列舉如下:
1)邊檢站將我“留置”,剝奪我的人身自由約四小時之久,既不辦理任何相關手續,也拒絕向我說明任何原由或法律依據,僅以“根據上級指示”來回答我的質疑和抗議;
2)邊檢站將我“留置”,剝奪我與家人打電話聯絡等基本權利約四小時之久,甚至拒絕我提出的由邊檢站打電話轉告我妻子(已在國內)有關我現狀的要求,也拒絕向我說明任何法律依據,僅以“要等上級決定”來回答我的質疑和抗議;
3)邊檢站傳達 “上級決定”,判定我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卻拒絕說明理由或依據,既提不出我有任何實際行為“危害國家安全”,也提不出根據哪條法規可以因此拒絕我這個持合法護照的中國公民入境本國,僅以“上級決定不作更多說明”來回答我的質疑和抗議;
4)邊檢站傳達 “上級決定”,完全空口無憑,沒有任何文字記錄,既沒有出示文字依據,也沒有辦理任何手續,更沒有任何當事人的簽名蓋章,甚至連如此處理是依據什麼法規都說不出來,針對我的質疑和抗議的回答僅僅是:“這個決定只作口頭宣布,如果你要投訴,就向我追究責任好了,我是北京鐵路西客站出入境邊防檢查站副站長,名叫殷明。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和職務記錄下來。”
5)邊檢站傳達 “上級決定”,卻拒絕說明上級機關的名稱。我抗議說,邊檢站的上級也是公安機關,但據我對中國法規的了解,公安機關根本無權如此判定並處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類刑事問題,因此這個“上級決定”顯然是違反司法程序的……針對我的質疑和抗議的回答僅僅是:這個“上級決定”不是“公安機關”的決定。
根據我對中國法律的了解,邊檢站的“上級”無論是哪個國家機關或領導人,最高也無非國務院和您這位總理,但即使是位高權重的您,也無權剝奪任何中國公民持合法護照入境本國的權利。
我於1981年底出國留學後在國外工作和居住(簡歷參見附件一),25年多來一直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此之前回國探親和出差,出入國境數十次,直到此前包括2005年5月的上次都沒有出現任何問題,連被邊檢站質疑訊問都不曾發生過,也不曾被任何公安或國家安全部門查問過一次(即使是這次遭處置,除了被問過是否有錢買機票以外,也未被正式問及其它任何問題)。
自前年5月回國兩星期後出境以來,我也沒有與以前根本不同的言行,只是在前年10月起擔任了我於2002年已加入的獨立中文筆會的祕書長,更多參與了本筆會以及國際筆會的事務。獨立中文筆會於2001年成立,在美國紐約注冊,根據章程為“全世界用中文寫作、編輯、翻譯、研究和出版文學作品之人士自由結合的非政府、非營利、非政黨的跨國界組織”,也是國際筆會的分會之一(簡介參見附件二)。獨立中文筆會秉承國際筆會“弘揚文學和捍衛言論自由”的基本宗旨,目前有近200名會員,其中近半數生活在中國大陸,所從事的筆會事務與中國法律並無沖突,本人所承擔的筆會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絲毫“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在筆會以外,本人從事的社會活動也只有2000年起就業余擔任的《北歐華人通訊》總編輯,這是挪威政府資助的一份為僑居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的華人提供當地信息和文化服務的刊物,我作為其總編的作為也根本不可能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綜上所述,北京鐵路西客站邊檢站所執行的“上級決定”,完全是無中生有肆意侵權的產物,至今未向本人查證或哪怕詢問一句,就如此輕率地剝奪了我作為中國公民一直享有的出入境自由的基本權利。這個決定還意味着無限期地剝奪了我回國探親的權利,包括不讓我探望已86歲高齡且已半身不遂的母親,而且很有可能不再給我們母子見面的機會,也未免太不人道,太過殘忍。一個連機構名稱都不肯告訴被處置者的“上級”,作出連文字都不肯出示給處置者的“決定”,無論於情、於理、於法,都根本站不住腳,顯然是一起嚴重枉法違法的錯案。
由於這個據稱不是公安機關的“上級”的名稱不明,因此我只好向您這個可以明確肯定是公安機關上級的國務院總理投訴,請您責成有關部門按照合法程序處理本案,依法改正拒絕我入境並遣送香港的錯誤“上級決定”,並賠償我由此產生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損失。
此致
敬禮
張鈺
2007年4月10日
抄送: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
公安部長周永康

獨立中文筆會原祕書長張鈺博士
以己及人說人權
張裕
與許多同代上下的人一樣, 1989年的“六四屠殺”改變了我的生涯。雖然我當時已在國外從事科研工作,但也因家庭因素有着與難以磨滅的經歷,對中國的人權狀況一直感同身受,影響至今。這家庭因素就是先父當年的入獄與獲釋。
先父張鍾是1941年就加入過中共的“老干部”,80年代初“離休”,在家專心研究中共早期歷史,發表了一些相關考證文章。1989年9月,他突然被武漢市公安局抄家後帶走,據稱是涉嫌給中共高層寫了一些“嚴重政治錯誤”的信(後來知道是批評了毛澤東、鄧小平等“第一代”領導人的理論和實踐),被“收容審查”。我母親當時也早已離休,不知案情,托了親友打聽,一直不得要領,有說案情嚴重得“通了天”,屬於不得打聽的“國家機密”。
我當時在瑞典留學和工作已近八年,與父母只是一月一信。他們當時捨不得裝電話,母親的信中不提父親被捕,只說他忙於寫作,因此當我從親戚那裡聽說此事,已過去了近三個月。我只好托有電話的親戚找到母親,得知她除了打聽到上述一點情況以外,只根據公安局的要求托帶過冬衣和錢,再也不知如何是好。我提出要在國外公開呼吁此事,因為根據當時法規,先父本不應屬於“收容審查”的對象(有流竄作案嫌疑的人,或有犯罪行為又不講真實姓名、住址的來歷不明者),且“收審” 最高時限也不得超過三個月,如果改為拘留和逮捕,也不應三個月仍不通知家屬,當局顯然是知法犯法,難以對它們再報希望。母親堅決反對,說是怕父親更遭報復。於是我答應只給國內各級領導人和部門寫信,再等當局三個月的反應時間。我共發了30多封信,上至黨總書記江澤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下至武漢市公檢法各機關,通過使館轉交,內容大同小異,無非詢問父親現狀和關押依據,說明我所知父親經歷和年老體弱,請有關當局依法釋放他,即使已進入司法程序不是違法關押,也應該允許他“保外就醫”或“取保候審”。一個多月以後,武漢市檢察院回信通知我母親,說是收到我的詢問信,但此案目前仍屬武漢市公安局處理,與檢察院無關,如果該院受理此案,自會及時通知。除此之外,再無其它回音。
三個月後的1990年3月底,我對母親表示,檢察院既然知道此案而仍與此無關,自然是未批准逮捕,無論是“收容審查”或“拘留”到半年也大大超過時限,其它有關部門對我的投訴沒有反應,可以證明當局因違法關押而無言以對;我們對當局已算仁至義盡,不得不向國際社會求助,否則也沒有其它辦法。母親說最好還是不要公開造輿論,先私下求助一些有影響的國際機構。於是,我就給“國際特赦”等人權組織寫信,不到一個月就收到其總部的回信,說是已決定接受我父親的個案,並交瑞典和法國的兩個小組專門關注和處理,不久兩個小組分別與我聯系,問了一些相關情況,說是將動員會員向包括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內的各方面去信呼吁釋放。
5月中旬,瑞典的一些留學生和流亡人士到當時在斯市城內的使館門前示威,紀念北京學生絕食抗議一周年,我也去了。其間,大使館一參贊夫人(剛好認識我並看過我的投訴信)要乘車離開,有些示威者上前向她宣講當局的鎮壓罪過,她反駁後爭論起來,我走過去時正好聽到她說“無論如何,你們這樣反黨反政府的行動也是錯誤的。”我接上話說:“您錯了,不是我們老百姓要反對貴黨和政府,而是貴黨和政府鎮壓我們老百姓。您知道我父親的案子,他可是所謂‘離休干部’,至多也不過是寫信批評了貴黨領導,貴黨就把他抓起來關了8個月還不放,完全違反了貴黨和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您怎麼能怪我這個做兒子的不反對貴黨和政府的這類違法鎮壓行動呢?”她啞口無言,但她的司機幫腔說:“你父親肯定是老反革命,抓起來活該!”於是激起了眾怒,罵聲四起。參贊夫人制止了司機爭吵,開車離開了。
有位新華社記者一直在路邊觀看示威,這時就過來問是怎麼回事,有認識他的人介紹說我是在皇家工學院工作的博士後,父親是“老革命”,只因給中央寫信就被警察抓去至今不放。他就過來要我自己再具體談一下,聽完後表示,如果確如我所說,很可能是一冤錯案件,他可以寫一內參給有關方面,請他們盡快調查處理此案,無論如何象這樣不說明理由而無限期的關押顯然是不當的。他留給我一張名片,讓我把原來寫的材料寄給他一份,我回家後就辦了。半個月後是“六四”一周年,我去市中心參加周年祭活動,又碰見那位記者,他說已把我父親的案子寫入內參,幾天前剛遞交上去了,或許在一兩個月內能有消息。另外,我也碰到“國際特赦”負責我父親案子的小組負責人,她說一個多星期前已發出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件。
6月下旬,我接到母親的電話,說是當天公安局來找她,首次讓她和我妹妹等三親屬去看守所見先父,並讓她們勸說他認錯,只要認了就可以立即釋放。她們就去勸了,並說我也是同樣的意見,但我父親仍然拒絕。不過,在我父親離開後,在場的負責人對我母親說,他們覺得先父的問題不很嚴重,仍決定釋放,不過這案子是“上面”交辦的,還必須經過上報審批,估計需要十天半月就可以結案放人。會面九天後的七月上旬,我父親就被釋放了,只是帶了一個有“尾巴”的結論:“有反革命的言論和行動,但罪行較輕,免予處理。”(大意如此)
父親出獄後說,他被“收審”的前三月常被提審,但他什麼也不認。89年12月,檢察院去人提審一次後,再就沒有任何提審了,估計是檢察院駁回了此案,因此他預料最多就是可能由公安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判他勞教三年。看守所裡不讓家屬探望,條件又很差,他還傳染上了乙型肝炎,因此他還不時要求快點判他(因為同一看守所中被“收審”時間最長者已達七年!),當局一直不理他的要求。90年6月下旬,看守所指導員找他“談判”,說是只要他“認錯”就可以立即放他,如果他不相信,甚至可立下字據,簽名蓋章。父親說不能接受這種“交易”,不能為釋放就承認自己沒干的事。於是又讓他見母親等,但他也不聽勸,沒想到結果還是放了。
我們估計,這個結果是那位記者和人權組織兩方面努力所致——“國際特赦”等人權組織的呼吁形成外壓,使要面子的中央領導人不能不顧及國際輿論;而記者內參的提醒顯然能起催化作用,使此案得以迅速結案,否則釋放程序可能要緩慢得多。當我對那位記者表示感謝時,他謙虛地說只是盡了一個記者應盡的義務而已,正象“國際特赦”的朋友們說他們只是盡了人權工作者應盡的責任一樣。
令人遺憾和感傷的是,先父還是被釋放得晚了兩、三個月——他在90年夏天因看守所裡流行的乙型肝炎感染,出獄後一直沒法治愈,時好是壞,拖到96年初,終因“肝昏迷”引起“腦中毒”不治而逝,成了當局“以言治罪”和“六四鎮壓”的又一犧牲品。
也正是基於先父因“六四鎮壓” 而“因言獲罪”的入獄與獲釋,我深深體會到人權運動的必要和有效,因此從那時起先後加入了國際特赦、紐約科學院、國際筆會等國際人權組織,近年來主要參與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的事務,特別關注中國的“言論自由”的問題,希望能象別人幫助曾是“獄中作家”的先父那樣,我也能幫助與他類似的“因言獲罪”者。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有關當局近來倒行逆施,居然將我參加這類活動視為“危害國家安全”,在我去年2月回國探親到北京入境時,邊境檢查站不經任何程序,未辦任何手續,不問不查不答不理,只以不明機構的口頭決定,將我這個25年多來一直來去自由的中國公民遣返,實在荒唐透頂。有關當局一直不與我本人直接打交道,不但不理睬我對拒絕入境的先後向溫家寶總理、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申訴(見附錄),而且在今年一月我從香港返回瑞典飛到北京機場轉機時把我強行扣留並“遣返”香港,邊檢承認我的中國護照合法但聲稱只在國外才能有效使用,更在今年四月連香港也拒絕我入境了,甚至還聲稱將來可能連台灣也不讓我去了——因為現在兩岸關系正“走向統一”。尤其可惡的是,有關當局近兩年來還不時騷擾和驚嚇對我的近況毫不了解的家人和親戚,完全是本末倒置亂株連。
當局近年來一直大力鼓吹“和諧社會”,但對於包括我家在內的很多普通中國人而言,顯然已淪為假話。我母親已高齡87歲,幾年前因中風而半身不遂,近年來又不時因病住院,而我連隔一兩探望一次的機會都被當局給“和諧”得沒有了。這也更顯示了改善中國人權狀況仍然任重道遠,還有待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犧牲,為了大家也為我們自己。
2007年6月3日一稿,2008年10月31日修改。
【張鈺簡歷】
張鈺,常用筆名張裕,男,漢族, 1952年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 1969年作為“知識青年”下鄉務農,1970至1974年在湖北省化工廠當工人,1977年畢業於武漢化工學院,1981年底到瑞典皇家理工學院留學,1987年獲工科博士學位,此後留在該校從事科研工作至今,其間於1991年至1993年曾應西班牙教育和科技部邀請到巴塞羅那自治大學作訪問學者。1990年參加“國際特赦”組織,業余創辦《北歐華人》月報。1998年參加紐約科學院(科學家人權組織)。2000年起擔任《北歐華人通訊》雜志總編輯。2002年加入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2004年起擔任該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協調人,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擔任該筆會祕書長;2004年起作為獨立中文筆會代表參加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四屆年會,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兩屆雙年會,以及2007年2月舉行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
十一月十九號,星期三,獨立中文筆會前祕書長,居住在瑞典的張鈺博士也接到駐瑞典的中國使館的通知,拒絕給他延長護照。有關這個事件的情況,記者采訪了張鈺博士,他向自由亞洲記者天溢介紹說:(錄音)“上個月我去換護照了,我的護照是明年二月到期,大概需要三周。所以昨天我就去了使館,他說根據外交部方面的指示,不能給我換護照。我問,為什麼?他說,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我說,我知道我沒有做什麼壞事。你必須告訴我!他說根據外交部領事司的批復,說是我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以不予換照。”
對此,張鈺博士要求他們具體講明是根據什麼法律,(錄音)“他們說,你自己去查,我就說有幾百條法律,我自己如何去查。他就說,反正是根據法律。我說,恐怕是沒有這條法律吧!外交部外事司也沒有權力決定一個人的罪名。這罪名是司法部門決定的。你們憑什麼?他說,你要有意見可以向外交部領事司去投訴。你跟我們說也沒有用,我們是執行命令的。”
為此,張鈺博士退一步要求他們給予一個書面答復,(錄音)“他說,我們這麼多人在這兒,我們還會騙你!我說,要是按照你的道理,法庭法官說,當着那麼多人宣判了,那人家就不出判決書了!哪有這個道理!我正式申請,你正式答復卻是口頭的。他說,我們就是口頭的,我們作為外事機構是有權力給成文的東西,也可以給不成文的東西。我說,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你有義務為我服務。他沒話說,然後就說,反正你不管怎麼說,你的事,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張鈺(右),萬之,齊思盈2005年11月在紐約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新聞自由獎發獎晚會上
對此,張鈺博士聯系到最近包括多位德國漢學家在內的四十九人維護中國政府的公開信說,(錄音)“我就想起來了,四十九人寫的回信說,我們在爭論中國政府是個流氓政府,還是值得信任的伙伴。這整個是個流氓無賴嗎!”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政府感到已經難以像以前那樣保持國內統治的的穩定,因此對於海外的異議人士采取吊銷護照,對於國內的異議人士采取驅逐出國的做法。最近幾年,這種做法沒有因為國內所謂經濟形勢的好轉而有所緩和,反而更加擴大。
【附錄 】給胡錦濤主席的申訴信
胡錦濤主席:
我歡迎您到瑞典訪問,不僅是因為您可以向瑞典的先進社會制度學習,而且還因為您所提倡的“和諧社會”可能有希望改正貴黨政府處理本案所犯的錯誤,包括非法剝奪我入境祖國的中國公民權利。
我估計您沒有收到我在今年四月給溫家寶總理信的副本(如下所示),我是通過電郵請貴州省的國安部門轉交的,因為當我妻子在今年初帶着幾個小孩回國探望她父母時,這個部門的人員就多次傳訊她,詢問有關我的情況,到她回瑞典後也未放松。我還未收到溫總理那方面的答復,只聽說國安又驚擾了我在國內更多的親屬。事實上,他們至少在一年前就開始這麼做了,只是在我被拒絕入境前沒讓我們夫妻知道而已。
由於國內有關當局至今未答復我的問題,我不得不利用您來訪的機會向您提出申訴,希望您所關注的“和諧社會”能具有現實意義,也包括同是中國公民的我本人及親屬,希望您在百忙之中責成有關部門:
1)讓警察停止驚擾我的家庭成員和親戚——因為他們與我的言行毫無關系,甚至都不曾聽說我的近況,所以無論警方用什麼罪名來對付我,也沒有任何理由株連他們。
2)敦促處理此案的部門盡快改正錯誤,尊重我回國和探母的基本權利。
望您或貴黨政府早日給我一個答復。預祝你訪瑞及提倡全民和諧社會的成功。
張鈺
2007年6月4日

獨立中文筆會原祕書長張鈺博士
就在北京西站被拒入境事給溫家寶總理的信
溫家寶總理:您好!
我是旅居瑞典的中國公民,現因今年2月7日下午在北京鐵路西客站入境被拒事,不得已向您投訴。
2007年2月7日下午4點35分,我所乘的T98次京港直通快車在晚點一個多小時後到達北京西客站;大約剛過5點,我在該站的入境邊防檢查站出示護照後被邊檢警察帶入“留置室”;大約7點左右,北京鐵路西客站出入境邊防檢查站(以下簡稱“邊防站”)副站長殷明先生向我正式傳達上級決定:“由於你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現決定拒絕你入境,由你自己購買機票,返回你的原出境地香港”(大意,下同);直到當晚9點左右被遣送到飛往香港的國泰CX2039航班登機口,失去人身自由約四小時。在這約四個小時中,邊檢警察除了“根據上級指示”、“要等上級決定”、“傳達上級決定”等口頭說法之外,盡管我一再要求和抗議,也沒有出示任何有權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以及將我遣送出境的文字,既沒有向我出示任何相關的司法文書,也沒有辦理任何相關的行政手續,甚至連口頭說明的合法依據或條文引用都不存在。在整個過程中,唯一履行了法律程序的是:向我宣布要根據相關法規搜查我的身體和攜帶物品,為此要我在相關表格上簽字認可,我毫無異議地照辦了。(不過,邊檢警察除了幫我搬拖行李和押送我去機場是擠坐一車,並無任何人主動碰過我的身體和物品,對於這種人格上的尊重,我在此向殷明先生和所有當值警察表示由衷的感謝)。
根據我對中國法律、法規的了解,北京鐵路西客站出入境邊防檢查站根據所謂“上級指示”和“上級決定”對我的處置,有諸多涉嫌違法之處,現按時間發生順序列舉如下:
1)邊檢站將我“留置”,剝奪我的人身自由約四小時之久,既不辦理任何相關手續,也拒絕向我說明任何原由或法律依據,僅以“根據上級指示”來回答我的質疑和抗議;
2)邊檢站將我“留置”,剝奪我與家人打電話聯絡等基本權利約四小時之久,甚至拒絕我提出的由邊檢站打電話轉告我妻子(已在國內)有關我現狀的要求,也拒絕向我說明任何法律依據,僅以“要等上級決定”來回答我的質疑和抗議;
3)邊檢站傳達 “上級決定”,判定我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卻拒絕說明理由或依據,既提不出我有任何實際行為“危害國家安全”,也提不出根據哪條法規可以因此拒絕我這個持合法護照的中國公民入境本國,僅以“上級決定不作更多說明”來回答我的質疑和抗議;
4)邊檢站傳達 “上級決定”,完全空口無憑,沒有任何文字記錄,既沒有出示文字依據,也沒有辦理任何手續,更沒有任何當事人的簽名蓋章,甚至連如此處理是依據什麼法規都說不出來,針對我的質疑和抗議的回答僅僅是:“這個決定只作口頭宣布,如果你要投訴,就向我追究責任好了,我是北京鐵路西客站出入境邊防檢查站副站長,名叫殷明。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和職務記錄下來。”
5)邊檢站傳達 “上級決定”,卻拒絕說明上級機關的名稱。我抗議說,邊檢站的上級也是公安機關,但據我對中國法規的了解,公安機關根本無權如此判定並處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類刑事問題,因此這個“上級決定”顯然是違反司法程序的……針對我的質疑和抗議的回答僅僅是:這個“上級決定”不是“公安機關”的決定。
根據我對中國法律的了解,邊檢站的“上級”無論是哪個國家機關或領導人,最高也無非國務院和您這位總理,但即使是位高權重的您,也無權剝奪任何中國公民持合法護照入境本國的權利。
我於1981年底出國留學後在國外工作和居住(簡歷參見附件一),25年多來一直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此之前回國探親和出差,出入國境數十次,直到此前包括2005年5月的上次都沒有出現任何問題,連被邊檢站質疑訊問都不曾發生過,也不曾被任何公安或國家安全部門查問過一次(即使是這次遭處置,除了被問過是否有錢買機票以外,也未被正式問及其它任何問題)。
自前年5月回國兩星期後出境以來,我也沒有與以前根本不同的言行,只是在前年10月起擔任了我於2002年已加入的獨立中文筆會的祕書長,更多參與了本筆會以及國際筆會的事務。獨立中文筆會於2001年成立,在美國紐約注冊,根據章程為“全世界用中文寫作、編輯、翻譯、研究和出版文學作品之人士自由結合的非政府、非營利、非政黨的跨國界組織”,也是國際筆會的分會之一(簡介參見附件二)。獨立中文筆會秉承國際筆會“弘揚文學和捍衛言論自由”的基本宗旨,目前有近200名會員,其中近半數生活在中國大陸,所從事的筆會事務與中國法律並無沖突,本人所承擔的筆會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絲毫“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在筆會以外,本人從事的社會活動也只有2000年起就業余擔任的《北歐華人通訊》總編輯,這是挪威政府資助的一份為僑居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的華人提供當地信息和文化服務的刊物,我作為其總編的作為也根本不可能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綜上所述,北京鐵路西客站邊檢站所執行的“上級決定”,完全是無中生有肆意侵權的產物,至今未向本人查證或哪怕詢問一句,就如此輕率地剝奪了我作為中國公民一直享有的出入境自由的基本權利。這個決定還意味着無限期地剝奪了我回國探親的權利,包括不讓我探望已86歲高齡且已半身不遂的母親,而且很有可能不再給我們母子見面的機會,也未免太不人道,太過殘忍。一個連機構名稱都不肯告訴被處置者的“上級”,作出連文字都不肯出示給處置者的“決定”,無論於情、於理、於法,都根本站不住腳,顯然是一起嚴重枉法違法的錯案。
由於這個據稱不是公安機關的“上級”的名稱不明,因此我只好向您這個可以明確肯定是公安機關上級的國務院總理投訴,請您責成有關部門按照合法程序處理本案,依法改正拒絕我入境並遣送香港的錯誤“上級決定”,並賠償我由此產生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損失。
此致
敬禮
張鈺
2007年4月10日
抄送: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
公安部長周永康

獨立中文筆會原祕書長張鈺博士
以己及人說人權
張裕
與許多同代上下的人一樣, 1989年的“六四屠殺”改變了我的生涯。雖然我當時已在國外從事科研工作,但也因家庭因素有着與難以磨滅的經歷,對中國的人權狀況一直感同身受,影響至今。這家庭因素就是先父當年的入獄與獲釋。
先父張鍾是1941年就加入過中共的“老干部”,80年代初“離休”,在家專心研究中共早期歷史,發表了一些相關考證文章。1989年9月,他突然被武漢市公安局抄家後帶走,據稱是涉嫌給中共高層寫了一些“嚴重政治錯誤”的信(後來知道是批評了毛澤東、鄧小平等“第一代”領導人的理論和實踐),被“收容審查”。我母親當時也早已離休,不知案情,托了親友打聽,一直不得要領,有說案情嚴重得“通了天”,屬於不得打聽的“國家機密”。
我當時在瑞典留學和工作已近八年,與父母只是一月一信。他們當時捨不得裝電話,母親的信中不提父親被捕,只說他忙於寫作,因此當我從親戚那裡聽說此事,已過去了近三個月。我只好托有電話的親戚找到母親,得知她除了打聽到上述一點情況以外,只根據公安局的要求托帶過冬衣和錢,再也不知如何是好。我提出要在國外公開呼吁此事,因為根據當時法規,先父本不應屬於“收容審查”的對象(有流竄作案嫌疑的人,或有犯罪行為又不講真實姓名、住址的來歷不明者),且“收審” 最高時限也不得超過三個月,如果改為拘留和逮捕,也不應三個月仍不通知家屬,當局顯然是知法犯法,難以對它們再報希望。母親堅決反對,說是怕父親更遭報復。於是我答應只給國內各級領導人和部門寫信,再等當局三個月的反應時間。我共發了30多封信,上至黨總書記江澤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下至武漢市公檢法各機關,通過使館轉交,內容大同小異,無非詢問父親現狀和關押依據,說明我所知父親經歷和年老體弱,請有關當局依法釋放他,即使已進入司法程序不是違法關押,也應該允許他“保外就醫”或“取保候審”。一個多月以後,武漢市檢察院回信通知我母親,說是收到我的詢問信,但此案目前仍屬武漢市公安局處理,與檢察院無關,如果該院受理此案,自會及時通知。除此之外,再無其它回音。
三個月後的1990年3月底,我對母親表示,檢察院既然知道此案而仍與此無關,自然是未批准逮捕,無論是“收容審查”或“拘留”到半年也大大超過時限,其它有關部門對我的投訴沒有反應,可以證明當局因違法關押而無言以對;我們對當局已算仁至義盡,不得不向國際社會求助,否則也沒有其它辦法。母親說最好還是不要公開造輿論,先私下求助一些有影響的國際機構。於是,我就給“國際特赦”等人權組織寫信,不到一個月就收到其總部的回信,說是已決定接受我父親的個案,並交瑞典和法國的兩個小組專門關注和處理,不久兩個小組分別與我聯系,問了一些相關情況,說是將動員會員向包括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內的各方面去信呼吁釋放。
5月中旬,瑞典的一些留學生和流亡人士到當時在斯市城內的使館門前示威,紀念北京學生絕食抗議一周年,我也去了。其間,大使館一參贊夫人(剛好認識我並看過我的投訴信)要乘車離開,有些示威者上前向她宣講當局的鎮壓罪過,她反駁後爭論起來,我走過去時正好聽到她說“無論如何,你們這樣反黨反政府的行動也是錯誤的。”我接上話說:“您錯了,不是我們老百姓要反對貴黨和政府,而是貴黨和政府鎮壓我們老百姓。您知道我父親的案子,他可是所謂‘離休干部’,至多也不過是寫信批評了貴黨領導,貴黨就把他抓起來關了8個月還不放,完全違反了貴黨和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您怎麼能怪我這個做兒子的不反對貴黨和政府的這類違法鎮壓行動呢?”她啞口無言,但她的司機幫腔說:“你父親肯定是老反革命,抓起來活該!”於是激起了眾怒,罵聲四起。參贊夫人制止了司機爭吵,開車離開了。
有位新華社記者一直在路邊觀看示威,這時就過來問是怎麼回事,有認識他的人介紹說我是在皇家工學院工作的博士後,父親是“老革命”,只因給中央寫信就被警察抓去至今不放。他就過來要我自己再具體談一下,聽完後表示,如果確如我所說,很可能是一冤錯案件,他可以寫一內參給有關方面,請他們盡快調查處理此案,無論如何象這樣不說明理由而無限期的關押顯然是不當的。他留給我一張名片,讓我把原來寫的材料寄給他一份,我回家後就辦了。半個月後是“六四”一周年,我去市中心參加周年祭活動,又碰見那位記者,他說已把我父親的案子寫入內參,幾天前剛遞交上去了,或許在一兩個月內能有消息。另外,我也碰到“國際特赦”負責我父親案子的小組負責人,她說一個多星期前已發出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件。
6月下旬,我接到母親的電話,說是當天公安局來找她,首次讓她和我妹妹等三親屬去看守所見先父,並讓她們勸說他認錯,只要認了就可以立即釋放。她們就去勸了,並說我也是同樣的意見,但我父親仍然拒絕。不過,在我父親離開後,在場的負責人對我母親說,他們覺得先父的問題不很嚴重,仍決定釋放,不過這案子是“上面”交辦的,還必須經過上報審批,估計需要十天半月就可以結案放人。會面九天後的七月上旬,我父親就被釋放了,只是帶了一個有“尾巴”的結論:“有反革命的言論和行動,但罪行較輕,免予處理。”(大意如此)
父親出獄後說,他被“收審”的前三月常被提審,但他什麼也不認。89年12月,檢察院去人提審一次後,再就沒有任何提審了,估計是檢察院駁回了此案,因此他預料最多就是可能由公安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判他勞教三年。看守所裡不讓家屬探望,條件又很差,他還傳染上了乙型肝炎,因此他還不時要求快點判他(因為同一看守所中被“收審”時間最長者已達七年!),當局一直不理他的要求。90年6月下旬,看守所指導員找他“談判”,說是只要他“認錯”就可以立即放他,如果他不相信,甚至可立下字據,簽名蓋章。父親說不能接受這種“交易”,不能為釋放就承認自己沒干的事。於是又讓他見母親等,但他也不聽勸,沒想到結果還是放了。
我們估計,這個結果是那位記者和人權組織兩方面努力所致——“國際特赦”等人權組織的呼吁形成外壓,使要面子的中央領導人不能不顧及國際輿論;而記者內參的提醒顯然能起催化作用,使此案得以迅速結案,否則釋放程序可能要緩慢得多。當我對那位記者表示感謝時,他謙虛地說只是盡了一個記者應盡的義務而已,正象“國際特赦”的朋友們說他們只是盡了人權工作者應盡的責任一樣。
令人遺憾和感傷的是,先父還是被釋放得晚了兩、三個月——他在90年夏天因看守所裡流行的乙型肝炎感染,出獄後一直沒法治愈,時好是壞,拖到96年初,終因“肝昏迷”引起“腦中毒”不治而逝,成了當局“以言治罪”和“六四鎮壓”的又一犧牲品。
也正是基於先父因“六四鎮壓” 而“因言獲罪”的入獄與獲釋,我深深體會到人權運動的必要和有效,因此從那時起先後加入了國際特赦、紐約科學院、國際筆會等國際人權組織,近年來主要參與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的事務,特別關注中國的“言論自由”的問題,希望能象別人幫助曾是“獄中作家”的先父那樣,我也能幫助與他類似的“因言獲罪”者。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有關當局近來倒行逆施,居然將我參加這類活動視為“危害國家安全”,在我去年2月回國探親到北京入境時,邊境檢查站不經任何程序,未辦任何手續,不問不查不答不理,只以不明機構的口頭決定,將我這個25年多來一直來去自由的中國公民遣返,實在荒唐透頂。有關當局一直不與我本人直接打交道,不但不理睬我對拒絕入境的先後向溫家寶總理、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申訴(見附錄),而且在今年一月我從香港返回瑞典飛到北京機場轉機時把我強行扣留並“遣返”香港,邊檢承認我的中國護照合法但聲稱只在國外才能有效使用,更在今年四月連香港也拒絕我入境了,甚至還聲稱將來可能連台灣也不讓我去了——因為現在兩岸關系正“走向統一”。尤其可惡的是,有關當局近兩年來還不時騷擾和驚嚇對我的近況毫不了解的家人和親戚,完全是本末倒置亂株連。
當局近年來一直大力鼓吹“和諧社會”,但對於包括我家在內的很多普通中國人而言,顯然已淪為假話。我母親已高齡87歲,幾年前因中風而半身不遂,近年來又不時因病住院,而我連隔一兩探望一次的機會都被當局給“和諧”得沒有了。這也更顯示了改善中國人權狀況仍然任重道遠,還有待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犧牲,為了大家也為我們自己。
2007年6月3日一稿,2008年10月31日修改。
【張鈺簡歷】
張鈺,常用筆名張裕,男,漢族, 1952年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 1969年作為“知識青年”下鄉務農,1970至1974年在湖北省化工廠當工人,1977年畢業於武漢化工學院,1981年底到瑞典皇家理工學院留學,1987年獲工科博士學位,此後留在該校從事科研工作至今,其間於1991年至1993年曾應西班牙教育和科技部邀請到巴塞羅那自治大學作訪問學者。1990年參加“國際特赦”組織,業余創辦《北歐華人》月報。1998年參加紐約科學院(科學家人權組織)。2000年起擔任《北歐華人通訊》雜志總編輯。2002年加入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2004年起擔任該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協調人,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擔任該筆會祕書長;2004年起作為獨立中文筆會代表參加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四屆年會,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兩屆雙年會,以及2007年2月舉行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