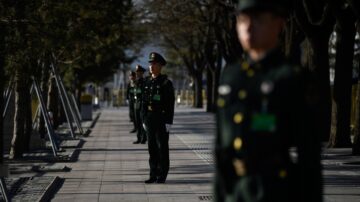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10月8日訊】【編者的話】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邊「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五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完成了《夾邊溝記事》,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
《夾邊溝記事》連載 李祥年的愛情故事(五)
去年在甘肅省靖遠縣採訪的時候,我就聽人說,有個名叫李祥年的夾邊溝右派住在縣城裡。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曾在蘭州市體委工作,五七年定為右派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勞教期間,他又升了一級,被正式判刑送勞改農場。勞改期滿後留場就業,幾經周折落戶在靖遠縣城,在縣體委工作。
聽到這個殘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訪,卻未能謀面。他家的門上掛著鎖。鄰居告訴我,十多年前他就在蘭州市紅山根體育場附近開設了一間字畫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兒。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作為天津市的作家,我終於聽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夾邊溝的故事;他是怎麼由勞教升級為勞改的?「升級」這兩個字我已經聽到多次了,但還沒有見到過一個「升級」的人;他原先在蘭州市體委工作,落實政策應該回到原單位去,卻又怎麼到了黃河北岸的乾旱山區靖遠縣?
我立即返回了蘭州,並且去紅山根體育場附近尋找李祥年,卻未能覓到。
無巧不成書,今年秋季又一次來蘭州採訪,與一位名叫關啟興的畫家朋友聊天時談到這件事,他說,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嗎?我領你去。關啟興告訴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蘭州市舉辦書法展覽,他們就認識且熟悉了。
難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畫店,原來它就在蘭州鐵路局旁邊的街道上,我卻在紅山根附近鐵路新村的地段上轉來轉去。
掀開軟塑料門簾進了門,我的畫家朋友就和一位高個子年近七旬的人說話。我立即就意識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凈的臉上歲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跡,鼻翼兩旁的八字紋刀刻斧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後我就說明了來意。他毫不推辭,爽快地說:「你要問我在夾邊溝為什麼『升級』、怎麼升的級、最後怎麼又流落到了靖遠縣的,這可是一言難盡呀,我得慢慢道來。」
我是1958年9月被蘭州體委送到夾邊溝去的。是體委辦公室副主任和國防體育科的射擊教練送我去的。為什麼叫個射擊教練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夾邊溝勞動教養,我已經跑過一回了,我是被抓回蘭州來之後送夾邊溝的。這次送夾邊溝,怕我逃跑,專門派了個射擊教練提個小口徑步槍押著。
我在夾邊溝的境遇還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生,體魄好,身手靈活;我從小就跟著父親進戲院子,懂京劇,能唱能表演。到了夾邊溝,在大田勞動了幾天,就被抽出來參加演出隊,排練慶祝國慶十周年的節目,演戲。我還能畫能寫。我的爺爺是清代舉人,開家館,寫得一手好字。父親母親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父親做過開灤煤礦的財務主任,也是寫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鶴年後來成為全國著名的書法家,天津市書法家協會的主席……出生在這樣一個書香門第,我當然也是能寫能畫。國慶節演出全本京劇《失·空·斬》我飾諸葛亮,一炮打響了,引起管教幹部的注意,演出結束後叫我去寫黑板報……我在大田裡就沒有干過幾天——有時候,領導看我一塊黑板寫三天,就發怒,知道我是偷懶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勞動。可是下大田沒幾天,就又把我調出來搞黑板報。我是偷懶耍滑了,可是,不偷懶耍滑的時候我一天能寫十塊黑板報,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寫又畫,連稿子都是我自編自寫,用不著管教幹部操心。夾邊溝的能人多得很,有畫家,有詩人,有專業演員,但他們不如我多面手什麼都能幹。
由於能寫能畫能演能導能畫布景,經常做零工做雜活,所以我到夾邊溝一年的時間裡沒受太大的苦,身體沒有累垮,也沒太挨餓。我經常在黑板報上表揚食堂的炊事員——這很重要。農場制定出的獎懲制度裡有這樣的條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勞動教養。我表揚誰誰就在管教幹部心裡留下好印象,有利於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員們的關係好,去食堂打飯就打得多。我表揚了衛生所,醫生就給我開病假條,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體力勞動,保存體力。
初進夾邊溝的時候我也曾有過想法:不就是勞教一年半載嗎?領導就是這麼說的,鍛煉鍛煉幾個月就回來了,接著工作。按照我當時的處境,的確還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強多了,所以我就下決心熬下去,熬出這幾個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幾個月,一點兒摘帽釋放的音訊也沒有,我就覺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對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麼也不想幹了,覺得活著沒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見一面,和她敘一敘思念之情。也想告訴她我已經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勞動教養,你還愛我嗎?如果她說還愛我,願意等著我,我就回來再接著熬。她要是變心了,我就再也不回來了,我寧願到處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時正在北師大讀書。她是石家莊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師範大學——那時校址在天津市—— 搞畢業實習,我在石家莊第二中學代課認識了她。那時我23歲,風華正茂的時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實習期間正遇上河北省的運動會在石家莊舉行,我擔任籃球比賽的裁判——那是我的長項 ——出足了風頭。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長,我們體育系的足球隊和河北省足球隊比賽了三場球,我也出了風頭。結果,就在我們實習結束的時候,我發現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齡還小,也就17歲。可那是個早熟的姑娘,不光身體發育早——大個子,胸脯挺飽滿——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熱烈的目光看我。咱們都是過來人,不用我說你們就明白,一個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另外,就在我們離開石家莊第二中學的前幾天,我代表在這個學校實習的十幾名各系的同學寫感謝信,俞淑敏就圍著我轉,很殷勤。她一會兒去找墨汁,一會兒又去找毛筆。感謝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寫的,我捉筆抄在紅虎皮宣紙上。我的楷書是寫得很好的,小學五年級,我的作品就獲天津市小學生書法大賽第一名;初中時天津市搞中學生書畫展,我的字畫佔了整間展廳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觀,斗大的楷書——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大橫幅是我寫的,在天津市文化館展出。
感謝信寫完,俞淑敏滿心歡喜地在旁邊說,李老師,你的字寫得真好,寫得真好!
她真是從心底裡欽佩我,看上了我。當然,我也喜歡上了她。這是個很漂亮的姑娘,她雖然年齡還小,但的確是個美人,千裡挑一萬裡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嫵媚的臉蛋,真是漂亮極了。
我確切地認識到她愛上了我是在我離開石家莊前的最後兩三天,她叫我去她家。從她家出來,她又叫我去公園。她說,李老師咱們去公園吧,你急著回學校幹什麼? 過兩天你就回天津了,還不在石家莊好好玩玩嗎?在公園裡她跟我說,李老師,實習完了,回到天津還能記得我麼?我說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會把我忘了。她說我不會忘記你的,只要你不忘記我。
回到學校後就畢業了,等待分配工作,這時她又請假到天津來看我了。她有個姨媽在天津,她住在姨媽家裡,但每天往我們學校跑,或者約我出去逛公園。這次相見,我把自己的相冊和幾幅字給了她。她回到石家莊不久就寄信來,說她父親看了我寫的字,誇獎我說,這小子這兩筆字確是精彩。
我在蘭州工作以後,我們之間書信不斷。那時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們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時候郵票上邊要貼一枚藍色的標籤,印有 「航空」兩個字。1956年春節第一次回家探親,路過石家莊我去她家看她,她父親就對我說這樣的話:淑敏年齡還小,你要愛護她,不要耽誤她的學習。
我的家原來是在天津,由於姐姐天津大學畢業後分到北京國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蘇學生,是建工部設計院的總工程師,我的父母都已賦閑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親是到我姐家去。這次我把淑敏也帶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幾天,我父母很喜歡她,說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見了我母親叫娘,對我父親稱爸,儼然是我們家庭的成員了,樂得我母親合不攏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間房。她性格活潑,愛唱歌,還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歡她。
這裡有個小插曲應該說一下。1956年的全國籃球比賽在武漢舉行,我身兼甘肅省男籃和女籃兩支隊伍的教練去武漢打比賽。那時甘肅省沒有專業球隊,都是從各廠礦企業抽來的運動員,可是那次我們的男籃打了個第三名,是迄今為止甘肅省籃球史上最好的成績,以後的幾十年也沒超過這個紀錄。集訓一個月就去打比賽,我在比賽中指揮得當,出了風頭,結果女籃的一個運動員竟看上我了,頻送秋波。最後的冠亞軍決賽之後又搞了個表演賽,建工部隊對福建隊賽委會叫我當裁判,這時候那位女隊員給我拿衣裳端水;返回蘭州的火車上,她也是一會兒給我倒茶水,一會兒削蘋果給我,其他隊員都看出來她愛上我了。回到蘭州後她每個周末都約我去看戲,星期天去逛公園,都是她花錢。這個姑娘是上海同濟大學的學生,比我早畢業兩年,是省建工局的技術員,工資比我還要高一級,月薪 84元。她元旦回家探親——她的家也在北京——臨走問我帶什麼東西不?我買了點哈密瓜乾和葡萄乾叫她捎去。碰巧她父親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聽就把這些東西送到我家去了,與我的家人見了面。她回家探親還沒回到蘭州,我父親就來了信,說,你托楊某帶的瓜干收到了。楊某對你的評價很好。我們全家人都看出來她對你有好感。她的學歷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們認為還是淑敏優點多。我們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靈受到打擊和傷害。你可不要喜新厭舊顧此失彼。過了幾天,我姐也來了信,說,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預感,看起來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覺得遠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畢業,還要上大學,你等不住,怕她將來有什麼變化,把你的婚事耽誤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見,還是楊某對你更合適也更現實。
其實,我從心眼裡是喜歡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楊的姑娘就是個子高一些,長得白,可長了個單眼皮,是個胖丫頭,身材長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過我覺得姐姐說的話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學。四年,可不是四天四個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學變了心,可真就把我閃下了!於是我把姐姐的話寫信告訴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訴她,我等著你,你可不能變心呀。她很快就複信了,信中說,我是真愛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蘭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跡。就是我父母親攔我,我也不聽他們的。
不是在蘭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節,我回家探親——我先到石家莊看她,然後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車,去我家之前,我們在廣武門的旅社裡同居了一天。只是我運氣不好,我回家就一個星期的假期,而那幾天她正好來例假。我們雖然在一間房子裡住了一夜卻未能嘗到禁果。這次探親後回到蘭州,再寫信的時候,我稱呼她愛妻。她呢,也在信中寫:祥年,我的夫。她還在信中說,將來我們有了孩子,要把他培養成一名出色的畫家,或者是運動健將。我和她還沒有成為夫妻,但從感情上卻勝似夫妻。我們魚雁傳書,頻繁地表達著自己的感情和對於愛情生活的渴望,設計著未來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鬥爭開始了……我成了右派!
從1957年底開始,我就再也沒給她寫信,因為這時已經宣布我為右派了。我覺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戀愛了。再要是給她寫信,再戀著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為,不再給她寫信了,就可以切斷我們的戀情了,可是我錯了,到了夾邊溝的艱苦環境之後,我對於她的思念竟然愈發強烈了。在勞教分子的宿捨裡,在寒冷難眠的長夜裡,我經常想起她嫵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軟的身體,想起兩個春節我回北京探親,她住在我家裡,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們倆一起唱歌的情景……
終於,我對淑敏的想念發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時候我什麼都不顧了,心想一定要見她一次,然後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節一樣,1960年的春節到來之前半個月,農場又把右派當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來排練節目,準備節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劇團、秦腔劇團的幾個演員以及幾個票友演了整場的京劇《失·空·斬》,今年我們還是演《失·空·斬》。由於長期飢餓和勞累,演員們都兩腿發軟,沒有了排新戲的創新精神,演戲只不過是為了逃避勞動,混一頓夜間的加餐。我的腿也發軟,發飄,但相比而言比別人強些,因為我參加重體力勞動少,體能的消耗比別人少。
離著春節還有一個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裡我們點著汽燈排練節目,到12點鐘吃完加餐,就都散夥了,回宿捨睡覺。我也躺下了,裝睡,沒脫衣裳。睡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我就爬起來了。把一隻皮箱塞進被窩裡,枕頭擺好,枕頭上還放了一頂前兩天揀來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種假相:李祥年睡在這裡。如果隊長或管教幹部進來查夜,不拉被子是發現不了的。這樣,天亮之前不會有人發現我逃跑了。
那時候夜裡院子裡有人值班巡邏,防止右派逃跑。右派們初到夾邊溝的時候沒人逃跑,大都對黨很虔誠,都想經過勞動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養回家去,爭取個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國慶節開大會的時候,全農場只有三個人摘了帽子,解除勞動教養,卻還必須在夾邊溝就業,一月掙24 元。於是人們明白了,勞動教養改造思想是一片謊言,是欺騙,所有的人實質上都判了無期徒刑,勞動改造遙遙無期。人們都絕望了,鋌而走險逃跑的人隨之多了起來。為了預防逃跑,農場每到夜間就派管教幹部和右派中的積極分子值班和巡邏。為了避免遇到值班幹部和積極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壺和幾個存下的干饃饃藏在貼身的棉襖裡邊,外邊披了一件藍棉布大衣,裝成上廁所的樣子進了廁所,然後從院牆上翻過去落在農場大院的外邊。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
《夾邊溝記事》連載 李祥年的愛情故事(五)
去年在甘肅省靖遠縣採訪的時候,我就聽人說,有個名叫李祥年的夾邊溝右派住在縣城裡。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曾在蘭州市體委工作,五七年定為右派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勞教期間,他又升了一級,被正式判刑送勞改農場。勞改期滿後留場就業,幾經周折落戶在靖遠縣城,在縣體委工作。
聽到這個殘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訪,卻未能謀面。他家的門上掛著鎖。鄰居告訴我,十多年前他就在蘭州市紅山根體育場附近開設了一間字畫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兒。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作為天津市的作家,我終於聽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夾邊溝的故事;他是怎麼由勞教升級為勞改的?「升級」這兩個字我已經聽到多次了,但還沒有見到過一個「升級」的人;他原先在蘭州市體委工作,落實政策應該回到原單位去,卻又怎麼到了黃河北岸的乾旱山區靖遠縣?
我立即返回了蘭州,並且去紅山根體育場附近尋找李祥年,卻未能覓到。
無巧不成書,今年秋季又一次來蘭州採訪,與一位名叫關啟興的畫家朋友聊天時談到這件事,他說,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嗎?我領你去。關啟興告訴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蘭州市舉辦書法展覽,他們就認識且熟悉了。
難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畫店,原來它就在蘭州鐵路局旁邊的街道上,我卻在紅山根附近鐵路新村的地段上轉來轉去。
掀開軟塑料門簾進了門,我的畫家朋友就和一位高個子年近七旬的人說話。我立即就意識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凈的臉上歲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跡,鼻翼兩旁的八字紋刀刻斧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後我就說明了來意。他毫不推辭,爽快地說:「你要問我在夾邊溝為什麼『升級』、怎麼升的級、最後怎麼又流落到了靖遠縣的,這可是一言難盡呀,我得慢慢道來。」
我是1958年9月被蘭州體委送到夾邊溝去的。是體委辦公室副主任和國防體育科的射擊教練送我去的。為什麼叫個射擊教練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夾邊溝勞動教養,我已經跑過一回了,我是被抓回蘭州來之後送夾邊溝的。這次送夾邊溝,怕我逃跑,專門派了個射擊教練提個小口徑步槍押著。
我在夾邊溝的境遇還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生,體魄好,身手靈活;我從小就跟著父親進戲院子,懂京劇,能唱能表演。到了夾邊溝,在大田勞動了幾天,就被抽出來參加演出隊,排練慶祝國慶十周年的節目,演戲。我還能畫能寫。我的爺爺是清代舉人,開家館,寫得一手好字。父親母親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父親做過開灤煤礦的財務主任,也是寫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鶴年後來成為全國著名的書法家,天津市書法家協會的主席……出生在這樣一個書香門第,我當然也是能寫能畫。國慶節演出全本京劇《失·空·斬》我飾諸葛亮,一炮打響了,引起管教幹部的注意,演出結束後叫我去寫黑板報……我在大田裡就沒有干過幾天——有時候,領導看我一塊黑板寫三天,就發怒,知道我是偷懶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勞動。可是下大田沒幾天,就又把我調出來搞黑板報。我是偷懶耍滑了,可是,不偷懶耍滑的時候我一天能寫十塊黑板報,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寫又畫,連稿子都是我自編自寫,用不著管教幹部操心。夾邊溝的能人多得很,有畫家,有詩人,有專業演員,但他們不如我多面手什麼都能幹。
由於能寫能畫能演能導能畫布景,經常做零工做雜活,所以我到夾邊溝一年的時間裡沒受太大的苦,身體沒有累垮,也沒太挨餓。我經常在黑板報上表揚食堂的炊事員——這很重要。農場制定出的獎懲制度裡有這樣的條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勞動教養。我表揚誰誰就在管教幹部心裡留下好印象,有利於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員們的關係好,去食堂打飯就打得多。我表揚了衛生所,醫生就給我開病假條,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體力勞動,保存體力。
初進夾邊溝的時候我也曾有過想法:不就是勞教一年半載嗎?領導就是這麼說的,鍛煉鍛煉幾個月就回來了,接著工作。按照我當時的處境,的確還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強多了,所以我就下決心熬下去,熬出這幾個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幾個月,一點兒摘帽釋放的音訊也沒有,我就覺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對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麼也不想幹了,覺得活著沒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見一面,和她敘一敘思念之情。也想告訴她我已經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勞動教養,你還愛我嗎?如果她說還愛我,願意等著我,我就回來再接著熬。她要是變心了,我就再也不回來了,我寧願到處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時正在北師大讀書。她是石家莊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師範大學——那時校址在天津市—— 搞畢業實習,我在石家莊第二中學代課認識了她。那時我23歲,風華正茂的時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實習期間正遇上河北省的運動會在石家莊舉行,我擔任籃球比賽的裁判——那是我的長項 ——出足了風頭。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長,我們體育系的足球隊和河北省足球隊比賽了三場球,我也出了風頭。結果,就在我們實習結束的時候,我發現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齡還小,也就17歲。可那是個早熟的姑娘,不光身體發育早——大個子,胸脯挺飽滿——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熱烈的目光看我。咱們都是過來人,不用我說你們就明白,一個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另外,就在我們離開石家莊第二中學的前幾天,我代表在這個學校實習的十幾名各系的同學寫感謝信,俞淑敏就圍著我轉,很殷勤。她一會兒去找墨汁,一會兒又去找毛筆。感謝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寫的,我捉筆抄在紅虎皮宣紙上。我的楷書是寫得很好的,小學五年級,我的作品就獲天津市小學生書法大賽第一名;初中時天津市搞中學生書畫展,我的字畫佔了整間展廳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觀,斗大的楷書——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大橫幅是我寫的,在天津市文化館展出。
感謝信寫完,俞淑敏滿心歡喜地在旁邊說,李老師,你的字寫得真好,寫得真好!
她真是從心底裡欽佩我,看上了我。當然,我也喜歡上了她。這是個很漂亮的姑娘,她雖然年齡還小,但的確是個美人,千裡挑一萬裡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嫵媚的臉蛋,真是漂亮極了。
我確切地認識到她愛上了我是在我離開石家莊前的最後兩三天,她叫我去她家。從她家出來,她又叫我去公園。她說,李老師咱們去公園吧,你急著回學校幹什麼? 過兩天你就回天津了,還不在石家莊好好玩玩嗎?在公園裡她跟我說,李老師,實習完了,回到天津還能記得我麼?我說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會把我忘了。她說我不會忘記你的,只要你不忘記我。
回到學校後就畢業了,等待分配工作,這時她又請假到天津來看我了。她有個姨媽在天津,她住在姨媽家裡,但每天往我們學校跑,或者約我出去逛公園。這次相見,我把自己的相冊和幾幅字給了她。她回到石家莊不久就寄信來,說她父親看了我寫的字,誇獎我說,這小子這兩筆字確是精彩。
我在蘭州工作以後,我們之間書信不斷。那時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們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時候郵票上邊要貼一枚藍色的標籤,印有 「航空」兩個字。1956年春節第一次回家探親,路過石家莊我去她家看她,她父親就對我說這樣的話:淑敏年齡還小,你要愛護她,不要耽誤她的學習。
我的家原來是在天津,由於姐姐天津大學畢業後分到北京國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蘇學生,是建工部設計院的總工程師,我的父母都已賦閑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親是到我姐家去。這次我把淑敏也帶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幾天,我父母很喜歡她,說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見了我母親叫娘,對我父親稱爸,儼然是我們家庭的成員了,樂得我母親合不攏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間房。她性格活潑,愛唱歌,還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歡她。
這裡有個小插曲應該說一下。1956年的全國籃球比賽在武漢舉行,我身兼甘肅省男籃和女籃兩支隊伍的教練去武漢打比賽。那時甘肅省沒有專業球隊,都是從各廠礦企業抽來的運動員,可是那次我們的男籃打了個第三名,是迄今為止甘肅省籃球史上最好的成績,以後的幾十年也沒超過這個紀錄。集訓一個月就去打比賽,我在比賽中指揮得當,出了風頭,結果女籃的一個運動員竟看上我了,頻送秋波。最後的冠亞軍決賽之後又搞了個表演賽,建工部隊對福建隊賽委會叫我當裁判,這時候那位女隊員給我拿衣裳端水;返回蘭州的火車上,她也是一會兒給我倒茶水,一會兒削蘋果給我,其他隊員都看出來她愛上我了。回到蘭州後她每個周末都約我去看戲,星期天去逛公園,都是她花錢。這個姑娘是上海同濟大學的學生,比我早畢業兩年,是省建工局的技術員,工資比我還要高一級,月薪 84元。她元旦回家探親——她的家也在北京——臨走問我帶什麼東西不?我買了點哈密瓜乾和葡萄乾叫她捎去。碰巧她父親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聽就把這些東西送到我家去了,與我的家人見了面。她回家探親還沒回到蘭州,我父親就來了信,說,你托楊某帶的瓜干收到了。楊某對你的評價很好。我們全家人都看出來她對你有好感。她的學歷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們認為還是淑敏優點多。我們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靈受到打擊和傷害。你可不要喜新厭舊顧此失彼。過了幾天,我姐也來了信,說,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預感,看起來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覺得遠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畢業,還要上大學,你等不住,怕她將來有什麼變化,把你的婚事耽誤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見,還是楊某對你更合適也更現實。
其實,我從心眼裡是喜歡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楊的姑娘就是個子高一些,長得白,可長了個單眼皮,是個胖丫頭,身材長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過我覺得姐姐說的話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學。四年,可不是四天四個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學變了心,可真就把我閃下了!於是我把姐姐的話寫信告訴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訴她,我等著你,你可不能變心呀。她很快就複信了,信中說,我是真愛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蘭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跡。就是我父母親攔我,我也不聽他們的。
不是在蘭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節,我回家探親——我先到石家莊看她,然後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車,去我家之前,我們在廣武門的旅社裡同居了一天。只是我運氣不好,我回家就一個星期的假期,而那幾天她正好來例假。我們雖然在一間房子裡住了一夜卻未能嘗到禁果。這次探親後回到蘭州,再寫信的時候,我稱呼她愛妻。她呢,也在信中寫:祥年,我的夫。她還在信中說,將來我們有了孩子,要把他培養成一名出色的畫家,或者是運動健將。我和她還沒有成為夫妻,但從感情上卻勝似夫妻。我們魚雁傳書,頻繁地表達著自己的感情和對於愛情生活的渴望,設計著未來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鬥爭開始了……我成了右派!
從1957年底開始,我就再也沒給她寫信,因為這時已經宣布我為右派了。我覺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戀愛了。再要是給她寫信,再戀著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為,不再給她寫信了,就可以切斷我們的戀情了,可是我錯了,到了夾邊溝的艱苦環境之後,我對於她的思念竟然愈發強烈了。在勞教分子的宿捨裡,在寒冷難眠的長夜裡,我經常想起她嫵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軟的身體,想起兩個春節我回北京探親,她住在我家裡,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們倆一起唱歌的情景……
終於,我對淑敏的想念發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時候我什麼都不顧了,心想一定要見她一次,然後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節一樣,1960年的春節到來之前半個月,農場又把右派當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來排練節目,準備節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劇團、秦腔劇團的幾個演員以及幾個票友演了整場的京劇《失·空·斬》,今年我們還是演《失·空·斬》。由於長期飢餓和勞累,演員們都兩腿發軟,沒有了排新戲的創新精神,演戲只不過是為了逃避勞動,混一頓夜間的加餐。我的腿也發軟,發飄,但相比而言比別人強些,因為我參加重體力勞動少,體能的消耗比別人少。
離著春節還有一個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裡我們點著汽燈排練節目,到12點鐘吃完加餐,就都散夥了,回宿捨睡覺。我也躺下了,裝睡,沒脫衣裳。睡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我就爬起來了。把一隻皮箱塞進被窩裡,枕頭擺好,枕頭上還放了一頂前兩天揀來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種假相:李祥年睡在這裡。如果隊長或管教幹部進來查夜,不拉被子是發現不了的。這樣,天亮之前不會有人發現我逃跑了。
那時候夜裡院子裡有人值班巡邏,防止右派逃跑。右派們初到夾邊溝的時候沒人逃跑,大都對黨很虔誠,都想經過勞動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養回家去,爭取個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國慶節開大會的時候,全農場只有三個人摘了帽子,解除勞動教養,卻還必須在夾邊溝就業,一月掙24 元。於是人們明白了,勞動教養改造思想是一片謊言,是欺騙,所有的人實質上都判了無期徒刑,勞動改造遙遙無期。人們都絕望了,鋌而走險逃跑的人隨之多了起來。為了預防逃跑,農場每到夜間就派管教幹部和右派中的積極分子值班和巡邏。為了避免遇到值班幹部和積極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壺和幾個存下的干饃饃藏在貼身的棉襖裡邊,外邊披了一件藍棉布大衣,裝成上廁所的樣子進了廁所,然後從院牆上翻過去落在農場大院的外邊。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