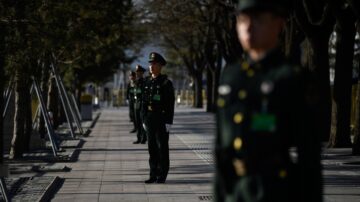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10月9日訊】【編者的話】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邊「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五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完成了《夾邊溝記事》,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

《夾邊溝記事》一本關於四十年前中國飢餓與死亡的真實報告。
《夾邊溝記事》連載 李祥年的愛情故事(六)
我沒敢走當年從酒泉來夾邊溝的公路。我不清楚,從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夾邊溝的五公裡必經大道上會不會有人巡邏;從這條公路走要經過兩條河流上的兩道便橋,這條路最便捷。我順著基建隊大院外邊的通往新添墩分場的大道往西走,經過五八年建的鍊鋼廠——幾間平房,早就改為農場衛生所的太平間了——再往南拐,穿過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邊。由於是三九隆冬,河上結了厚厚的冰,我踩著白冰過了河。穿過一片田野,又走過同樣是冰封雪蓋的北大河,我的腳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當然我不敢大搖大擺地順著公路走。我僅僅沿著公路快速地走了幾公裡,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離得夾邊溝遠一些,然後就下了公路,在長滿了芨芨草或鹼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腳淺一腳的。我還不能離公路太遠,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趕路:一旦農場發現我逃跑了,管教幹部就會騎著馬追上來。
我原計劃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縣的,可是八點多了,天已拂曉了卻還看不見縣城,只有黃沙鋪就的公路和殘雪映襯下顯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蕩蕩展開。兩輛拉麥草的大軲轆車吱吱咕咕地行駛在公路上,還有趕車的農民。
又走了兩個小時,我才走進縣城。
進了城我立即在一個小旅館裡用偷來的一位蘭州煉油廠的右派的工作證登記了一間房子。我估計夾邊溝農場已經發現我逃跑了,領導派出的管教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已經坐著汽車或騎著馬往縣城和火車站來追捕我了。他們估計我不敢進旅館,我卻偏要住在旅館裡。
在旅館藏匿了一天一夜,轉天清晨,我趕到了酒泉火車站,躲在站台對面的一個土坑裡。

年關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擠得車廂裡水泄不通。(網絡圖片)
大約九點多鍾,一列從哈密開來的客車進了站。我沒敢去買車票,從車下鑽過去之後我立即融進了擁擠著上車的人群裡鑽進車廂。年關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擠得車廂裡水泄不通。我坐在車廂中間的過道裡垂著頭打盹,一次車票都沒有查,二十幾個小時之後我就到了蘭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著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東走了一截,找到支線上閑置著的一截車廂爬了進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從西寧開往北京的快車。我的運氣真好,從蘭州去北京的客車比從哈密開來的更擁擠,也沒人查票,四十多個小時,我蜷縮在一排座椅下邊睡到了石家莊。
對於石家莊我已經很熟悉了,我在這兒實習過,1956年和1957年兩次回家探親我都來過這兒,五七年還在淑敏家住過半個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在離著淑敏家不遠的一條街道上下車,找了一家旅館住下來。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發,然後去市場買了兩隻雞提到旅館。我的氣色難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著雞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還沒走到淑敏家門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倆推著一輛自行車和我走了個迎面。我當時戴著口罩,沒戴帽子,她一眼就認了出來,驚訝地叫了一聲:呀!這不是祥年嗎?
我從她的表情看出來,她看見我很驚訝,但聲音裡又充滿了驚喜。這時我倒有點難為情和尷尬了。自從1957年年底我被劃成右派之後,就再也沒給她寫過信,她幾次寄信給我我也沒複信。她可能早就以為我變心了,不愛她了,所以這次見她才表現出如此的驚詫。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我只覺得我的心揪緊了,身上發冷,臉卻發燒。我支吾了一聲,算是和她打招呼。接著,為了避免她再問我什麼,我採取主動說,你們這是上哪兒去?
她姐回答,我們想到一個老師家去看看。
我說去吧,你們去吧。我去你們家。
淑敏說不去了,不去了,走,咱們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讓進她家。
自從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過半個月之後已經近三年了,我沒有來過她家,也沒有寫過信。我擔心這次來她家她會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縮縮進了她家。沒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熱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獨門小院,我一進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來了。這是裡外兩間的套房,裡間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間是客廳,所有來她家的客人都在這間房接待。她的父親是醫生,除了她的父親還保持著家長的矜持和尊嚴,說話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靜之外,其他人都對我的到來顯得驚喜和熱情。她的母親一見面就問我吃過飯沒有,並立即催大女兒去做飯。我說吃過飯了,老人立即責怪我:為什麼在外邊吃飯!怕我們不給飯嗎!接著又問幾點鐘到石家莊的……說著話,老人突然問了一句:祥年,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難看,又黑又瘦?蘭州吃不飽嗎?我是比前兩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變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陽是很毒的,空氣乾燥,我又長年在露天勞動和工作,能不黑嗎?淑敏進了房子立即給我倒洗臉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邊看我,時不時地插句話。
但是,這種熱情很快就冷落下來,他們全家人像是約好的一樣突然都不說話了,房間裡出現了令人難堪的靜默。除了鐵皮爐子散發出的溫暖宜人的空氣依舊之外,我突然感到了異常和尷尬。我明白,最初的驚喜過去之後,她的一家人都在心裡想:這個李祥年兩三年沒音訊了,怎麼突然又冒出來了?
這時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對於這個家庭來說,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見了我叫姐夫,成天圍著我轉,可現在他靜靜地站在卧室的門口,一句話不說,靜靜地看著我,似乎在審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隨意的:喝水嗎?自己倒;或者是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麼說什麼。這天晚上她給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後,就退到角落裡在一隻板凳上坐著,不說一句話。我看見她有時候直著眼睛看我,有時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謹地捏著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見了她的比從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別著的北師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陣陣發冷:她是名牌大學的學生了,而我已經變成階下囚了,流放夾邊溝…… 我已經不配她了!行了,見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屬於這個家庭的一員了。再說,將來的日子我還不知要走什麼樣的路……
坐了一會兒,在一陣靜默中我站了起來,說,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見……
我是九點鐘離開淑敏家的。淑敏沒攔我,只是她母親客氣地問了我一句:這麼晚你上哪兒去?我說我住在旅社裡。她母親就沒再說什麼。淑敏送我到院門口才說了這天晚上的第一句話:你明天來,早晨八點鐘來……
我沒回答她。還有必要來嗎?我心裡這樣想。我只是說了句你進去吧,回房去吧,就轉身離開了她。但這時她弟弟跑了出來,喊了聲姐夫,然後說,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裡,我住裡屋去。
從前我來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這個中學生的心情,已往的兩年中他已經熟悉我了,把我當成他家的一個成員了。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問我這問我那。他喜歡踢足球,我就給他講足球,並比劃著教他踢球的技術動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願意我這樣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可能作為一個初中少年他還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我為什麼這樣匆匆離去。我在他家時說,我是回北京探親的,順便在石家莊下車來看看的,此時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謊:不行,有一個朋友在旅社裡等著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車,明天早上再來。
離開淑敏家,我在心裡想著:不來了,我再也不來了,我與她見一面就行了,我們的緣分盡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輾轉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後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捨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訴她我的真實情況,我想問一句,她願不願等我,願不願和一個囚犯保持戀愛關係。我是為了這件事來的,我一定要把話說出來,並且還要請求她:不要拋棄我,我是真正愛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將來成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嫵媚的臉,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聽聽她說話的熱烈親切的聲音……
我往她家去。路過集市,我看見了她母親,她姐姐。她們在買菜。看來,她母親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沒必要親自來買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醫學院的學生,22歲了,完全可以辦好這件事的。她們母女大清早出來買菜,是為了給我和淑敏創造個談話的環境!淑敏的父親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門口了,卻又突然躊躇起來,猶豫了:我是個右派,勞動教養的囚犯,逃亡在外,這輩子都沒希望了,還有什麼臉面、資格去見淑敏?淑敏是大學生了,將來的中學教師或者大學教師,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還愛我,許諾等著我,我不是害了她嗎?我會毀掉她的前程的,會毀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門口站了幾分鐘,在心裡默默地祝願她幸福,祝願她找一個好丈夫,然後就轉身走開了。
當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為想念淑敏,我逃離了夾邊溝。我見到淑敏了,但是由於我的自慚形穢,我又失去了她,逃離了她,現在我該幹什麼呢? 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還愛我,只要她說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還是等著你,那我就會義無反顧地返回夾邊溝繼續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經葬送,愛情也已然葬送,整個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還有必要自投羅網重返囹圄嗎?沒有,沒有這個必要了。我已經不對心愛的人承擔義務了,我生活的全部意義就是活著了,那就想辦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認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歲,雖然在夾邊溝餓了一年多身體有點虛弱,但我畢竟年輕,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還充滿活力。我只要能找到個活干,無論多苦多累,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進石頭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來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處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護和接濟吧。那天離開了石家莊,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見見我的父母,然後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臨之後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設計院工作。他們的家在北京去通縣二十裡遠處的管莊。解放後國家在那兒蓋了大片的樓房,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幹部家屬們都住這。但是,我乘坐的最後一趟公共汽車到了管莊,到了姐姐家門口,我卻猶豫再三不敢敲門。
1957年的夏季,蘭州市的各級機關大鳴大放和開展反右鬥爭,到了11月,我就被定為右派。最初,我並未列入去夾邊溝的名單之中,因為我是個一般的右派,不是極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僅僅是舊職員,雖不是無產階級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資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夾邊溝的名單。但是,我被定為右派之後,不叫我做教練了,也不叫我當裁判了。我從河北師大畢業後僅僅在蘭州體委工作了兩年,可是在蘭州的體育界我是出風頭的。那時候蘭州體校設在市中心的蘭園,我給學生們上課。蘭園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燈光籃球場,每一場蘭州市的或者省級的籃球比賽,都是我執法,滿場跑,動作漂亮,反應敏捷,判斷準確……我走在街上許多年輕人認識我,叫我蘭園裁判。我還是甘肅日報的特約體育撰稿人,寫過介紹五六年赫爾辛基奧運會新規則的文章,寫過介紹小足球的文章。我還是甘肅人民廣播電台的體育解說員。重大的比賽,我坐在球場邊上對著麥克風解說,電台現場轉播比賽。但是,定為右派之後,我的工作就是比賽前畫線,抬保溫桶,抬開水,燒開水。往常叫我李指導的學員和運動員,現在在水房遇見我,這樣跟我說話:李祥年,把水燒熱了,我們要洗衣裳。李祥年,這水沒燒熱,怎麼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麼累,氣卻不好受。我一生氣乾脆就不幹了,不管領導怎麼批評我都不幹了,每天跑到蘭園北門的茶館聽人說書。於是,到了這年六月的一天,領導在大會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態度惡劣開除公職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我對這一決定極為不滿,領導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來了一個警察,他們原計劃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帶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應。我說,我不去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黨對右派的處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敵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對於開除公職的幹部允許其自謀生計自尋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謀生計。不等領導說話我又說,這是黨的政策,我按黨的政策辦的,你們如果違背黨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夾邊溝勞動教養,那就是反黨,反對黨中央。我要告你們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黨中央。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

《夾邊溝記事》一本關於四十年前中國飢餓與死亡的真實報告。
《夾邊溝記事》連載 李祥年的愛情故事(六)
我沒敢走當年從酒泉來夾邊溝的公路。我不清楚,從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夾邊溝的五公裡必經大道上會不會有人巡邏;從這條公路走要經過兩條河流上的兩道便橋,這條路最便捷。我順著基建隊大院外邊的通往新添墩分場的大道往西走,經過五八年建的鍊鋼廠——幾間平房,早就改為農場衛生所的太平間了——再往南拐,穿過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邊。由於是三九隆冬,河上結了厚厚的冰,我踩著白冰過了河。穿過一片田野,又走過同樣是冰封雪蓋的北大河,我的腳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當然我不敢大搖大擺地順著公路走。我僅僅沿著公路快速地走了幾公裡,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離得夾邊溝遠一些,然後就下了公路,在長滿了芨芨草或鹼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腳淺一腳的。我還不能離公路太遠,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趕路:一旦農場發現我逃跑了,管教幹部就會騎著馬追上來。
我原計劃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縣的,可是八點多了,天已拂曉了卻還看不見縣城,只有黃沙鋪就的公路和殘雪映襯下顯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蕩蕩展開。兩輛拉麥草的大軲轆車吱吱咕咕地行駛在公路上,還有趕車的農民。
又走了兩個小時,我才走進縣城。
進了城我立即在一個小旅館裡用偷來的一位蘭州煉油廠的右派的工作證登記了一間房子。我估計夾邊溝農場已經發現我逃跑了,領導派出的管教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已經坐著汽車或騎著馬往縣城和火車站來追捕我了。他們估計我不敢進旅館,我卻偏要住在旅館裡。
在旅館藏匿了一天一夜,轉天清晨,我趕到了酒泉火車站,躲在站台對面的一個土坑裡。

年關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擠得車廂裡水泄不通。(網絡圖片)
大約九點多鍾,一列從哈密開來的客車進了站。我沒敢去買車票,從車下鑽過去之後我立即融進了擁擠著上車的人群裡鑽進車廂。年關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擠得車廂裡水泄不通。我坐在車廂中間的過道裡垂著頭打盹,一次車票都沒有查,二十幾個小時之後我就到了蘭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著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東走了一截,找到支線上閑置著的一截車廂爬了進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從西寧開往北京的快車。我的運氣真好,從蘭州去北京的客車比從哈密開來的更擁擠,也沒人查票,四十多個小時,我蜷縮在一排座椅下邊睡到了石家莊。
對於石家莊我已經很熟悉了,我在這兒實習過,1956年和1957年兩次回家探親我都來過這兒,五七年還在淑敏家住過半個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在離著淑敏家不遠的一條街道上下車,找了一家旅館住下來。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發,然後去市場買了兩隻雞提到旅館。我的氣色難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著雞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還沒走到淑敏家門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倆推著一輛自行車和我走了個迎面。我當時戴著口罩,沒戴帽子,她一眼就認了出來,驚訝地叫了一聲:呀!這不是祥年嗎?
我從她的表情看出來,她看見我很驚訝,但聲音裡又充滿了驚喜。這時我倒有點難為情和尷尬了。自從1957年年底我被劃成右派之後,就再也沒給她寫過信,她幾次寄信給我我也沒複信。她可能早就以為我變心了,不愛她了,所以這次見她才表現出如此的驚詫。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我只覺得我的心揪緊了,身上發冷,臉卻發燒。我支吾了一聲,算是和她打招呼。接著,為了避免她再問我什麼,我採取主動說,你們這是上哪兒去?
她姐回答,我們想到一個老師家去看看。
我說去吧,你們去吧。我去你們家。
淑敏說不去了,不去了,走,咱們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讓進她家。
自從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過半個月之後已經近三年了,我沒有來過她家,也沒有寫過信。我擔心這次來她家她會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縮縮進了她家。沒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熱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獨門小院,我一進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來了。這是裡外兩間的套房,裡間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間是客廳,所有來她家的客人都在這間房接待。她的父親是醫生,除了她的父親還保持著家長的矜持和尊嚴,說話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靜之外,其他人都對我的到來顯得驚喜和熱情。她的母親一見面就問我吃過飯沒有,並立即催大女兒去做飯。我說吃過飯了,老人立即責怪我:為什麼在外邊吃飯!怕我們不給飯嗎!接著又問幾點鐘到石家莊的……說著話,老人突然問了一句:祥年,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難看,又黑又瘦?蘭州吃不飽嗎?我是比前兩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變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陽是很毒的,空氣乾燥,我又長年在露天勞動和工作,能不黑嗎?淑敏進了房子立即給我倒洗臉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邊看我,時不時地插句話。
但是,這種熱情很快就冷落下來,他們全家人像是約好的一樣突然都不說話了,房間裡出現了令人難堪的靜默。除了鐵皮爐子散發出的溫暖宜人的空氣依舊之外,我突然感到了異常和尷尬。我明白,最初的驚喜過去之後,她的一家人都在心裡想:這個李祥年兩三年沒音訊了,怎麼突然又冒出來了?
這時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對於這個家庭來說,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見了我叫姐夫,成天圍著我轉,可現在他靜靜地站在卧室的門口,一句話不說,靜靜地看著我,似乎在審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隨意的:喝水嗎?自己倒;或者是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麼說什麼。這天晚上她給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後,就退到角落裡在一隻板凳上坐著,不說一句話。我看見她有時候直著眼睛看我,有時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謹地捏著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見了她的比從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別著的北師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陣陣發冷:她是名牌大學的學生了,而我已經變成階下囚了,流放夾邊溝…… 我已經不配她了!行了,見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屬於這個家庭的一員了。再說,將來的日子我還不知要走什麼樣的路……
坐了一會兒,在一陣靜默中我站了起來,說,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見……
我是九點鐘離開淑敏家的。淑敏沒攔我,只是她母親客氣地問了我一句:這麼晚你上哪兒去?我說我住在旅社裡。她母親就沒再說什麼。淑敏送我到院門口才說了這天晚上的第一句話:你明天來,早晨八點鐘來……
我沒回答她。還有必要來嗎?我心裡這樣想。我只是說了句你進去吧,回房去吧,就轉身離開了她。但這時她弟弟跑了出來,喊了聲姐夫,然後說,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裡,我住裡屋去。
從前我來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這個中學生的心情,已往的兩年中他已經熟悉我了,把我當成他家的一個成員了。在一起的時候,他總是問我這問我那。他喜歡踢足球,我就給他講足球,並比劃著教他踢球的技術動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願意我這樣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可能作為一個初中少年他還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我為什麼這樣匆匆離去。我在他家時說,我是回北京探親的,順便在石家莊下車來看看的,此時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謊:不行,有一個朋友在旅社裡等著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車,明天早上再來。
離開淑敏家,我在心裡想著:不來了,我再也不來了,我與她見一面就行了,我們的緣分盡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輾轉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後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捨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訴她我的真實情況,我想問一句,她願不願等我,願不願和一個囚犯保持戀愛關係。我是為了這件事來的,我一定要把話說出來,並且還要請求她:不要拋棄我,我是真正愛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將來成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嫵媚的臉,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聽聽她說話的熱烈親切的聲音……
我往她家去。路過集市,我看見了她母親,她姐姐。她們在買菜。看來,她母親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沒必要親自來買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醫學院的學生,22歲了,完全可以辦好這件事的。她們母女大清早出來買菜,是為了給我和淑敏創造個談話的環境!淑敏的父親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門口了,卻又突然躊躇起來,猶豫了:我是個右派,勞動教養的囚犯,逃亡在外,這輩子都沒希望了,還有什麼臉面、資格去見淑敏?淑敏是大學生了,將來的中學教師或者大學教師,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還愛我,許諾等著我,我不是害了她嗎?我會毀掉她的前程的,會毀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門口站了幾分鐘,在心裡默默地祝願她幸福,祝願她找一個好丈夫,然後就轉身走開了。
當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為想念淑敏,我逃離了夾邊溝。我見到淑敏了,但是由於我的自慚形穢,我又失去了她,逃離了她,現在我該幹什麼呢? 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還愛我,只要她說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還是等著你,那我就會義無反顧地返回夾邊溝繼續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經葬送,愛情也已然葬送,整個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還有必要自投羅網重返囹圄嗎?沒有,沒有這個必要了。我已經不對心愛的人承擔義務了,我生活的全部意義就是活著了,那就想辦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認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歲,雖然在夾邊溝餓了一年多身體有點虛弱,但我畢竟年輕,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還充滿活力。我只要能找到個活干,無論多苦多累,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進石頭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來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處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護和接濟吧。那天離開了石家莊,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見見我的父母,然後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臨之後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設計院工作。他們的家在北京去通縣二十裡遠處的管莊。解放後國家在那兒蓋了大片的樓房,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幹部家屬們都住這。但是,我乘坐的最後一趟公共汽車到了管莊,到了姐姐家門口,我卻猶豫再三不敢敲門。
1957年的夏季,蘭州市的各級機關大鳴大放和開展反右鬥爭,到了11月,我就被定為右派。最初,我並未列入去夾邊溝的名單之中,因為我是個一般的右派,不是極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僅僅是舊職員,雖不是無產階級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資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夾邊溝的名單。但是,我被定為右派之後,不叫我做教練了,也不叫我當裁判了。我從河北師大畢業後僅僅在蘭州體委工作了兩年,可是在蘭州的體育界我是出風頭的。那時候蘭州體校設在市中心的蘭園,我給學生們上課。蘭園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燈光籃球場,每一場蘭州市的或者省級的籃球比賽,都是我執法,滿場跑,動作漂亮,反應敏捷,判斷準確……我走在街上許多年輕人認識我,叫我蘭園裁判。我還是甘肅日報的特約體育撰稿人,寫過介紹五六年赫爾辛基奧運會新規則的文章,寫過介紹小足球的文章。我還是甘肅人民廣播電台的體育解說員。重大的比賽,我坐在球場邊上對著麥克風解說,電台現場轉播比賽。但是,定為右派之後,我的工作就是比賽前畫線,抬保溫桶,抬開水,燒開水。往常叫我李指導的學員和運動員,現在在水房遇見我,這樣跟我說話:李祥年,把水燒熱了,我們要洗衣裳。李祥年,這水沒燒熱,怎麼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麼累,氣卻不好受。我一生氣乾脆就不幹了,不管領導怎麼批評我都不幹了,每天跑到蘭園北門的茶館聽人說書。於是,到了這年六月的一天,領導在大會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態度惡劣開除公職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我對這一決定極為不滿,領導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來了一個警察,他們原計劃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帶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應。我說,我不去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黨對右派的處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敵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對於開除公職的幹部允許其自謀生計自尋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謀生計。不等領導說話我又說,這是黨的政策,我按黨的政策辦的,你們如果違背黨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夾邊溝勞動教養,那就是反黨,反對黨中央。我要告你們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黨中央。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