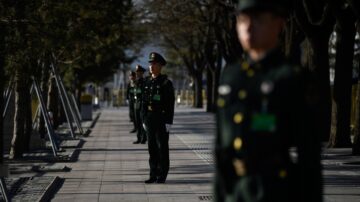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3月20日訊】8月24日——老捨的忌日。這個對普通人來說可能異常普通的日子,對我卻早具有了一種濃郁的歷史的「羅生門」意味。它時而明晰,時而模糊。有時,我覺得離它越來越近,但瞬間又彷彿覺得它漸行漸遠了。我多麼希望能成為一個幸運者,可以捕捉到歷史的影子。
歷史是我正努力從中醒來的一場噩夢
我是1993年開始從追蹤採訪調查老捨之死,切入來研究老捨的。剛開始想法極其簡單,就是想找到跟1966年8月23日老捨先生生前所在單位北京文聯遭受紅衛兵批鬥相關的親歷者、見證人,通過對他們的採訪,記錄他們的歷史文本敘事,我覺著可能會反映出歷史的真相。於是,從1993年開始,歷經11年,不斷地尋找見證者、當事人,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採訪,我的困惑一次又一次增加,隨著年齡和閱歷的不斷增長,我對於歷史的迷惑,又稍稍地變得清晰起來。我經歷了一段可以說是對歷史的迷途時期,把我領到了混亂之中。我被歷史弄迷惑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知道該相信誰。可以說,我對老捨之死的研究,使我的歷史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老捨之死是一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文化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事件,但是要將它還原,需要藉助於口述史的敘述。而口述史的敘述來自於不同之口,口口非常複雜。我們現在講到那個「古」字,「古」字怎麼寫?十口相加為古,就是口太多,口口相傳,把別人的口述逐一記下來,這就是產生文字最初時候的歷史。
歷史是什麼,可以任人隨意打扮嗎?你抹一把,我抹一把,歷史就五光十色了?可哪個才是真正的歷史,從哪個塗彩之中才能追本溯源,貼近那個歷史的史實真相呢?不知道。也許正因為此,20世紀愛爾蘭偉大作家喬伊斯在他享有天書之譽的《尤利西斯》一書中,借主人公之口說出了他對於歷史的見解。我十分心儀這句話,他說「歷史是我正努力從中醒來的一場惡夢。」我一直在做這樣一個夢,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醒來。不知道大家聽完這場講座,是淪入了夢中,還是能使你從夢中變得清醒一些?人人各異,看待事物、看待問題的角度都不一樣,因而對於人與事的理解也不一樣。
美國密蘇裡大學「口頭傳統研究中心」的開創者約翰·邁爾斯·弗裡教授,他寫了一本書叫《口頭詩學:帕裡-洛德理論》,這本書是引導我從老捨之死的採訪追蹤向探詢口述史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切入點。看這本書,我首先直觀地感受到口頭詩學與口頭史學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在某種程度上兩者還是兼而有之的。弗裡先生在書裡舉了很多的例子來說明許多民族最早的文學創作樣式,幾乎都是像《荷馬史詩》那樣的英雄史詩或神話傳說。而且,大多是現代民間口頭承傳經過長期的累積形成確定的文本創作。
1925年,美國年輕的古希臘文學專家米爾曼·帕裡開始對《荷馬史詩》產生濃厚的興趣,認為這兩部被後人稱為偉大史詩的總數約達兩萬八千詩行的敘述作品《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遠非荷馬一人所能創作,而肯定是希臘人集體的遺產。
事實上,在荷馬時代稍後不久的歲月裡,關於誰是荷馬,他是什麼時候創作出那些我們慣常歸功於他的詩作的,就已經成為懸而未決的公案,變得撲朔迷離。由於沒有留下關於《荷馬史詩》創作者的確切記載,後世的學者們只能根據零星的線索,來做各式各樣的主觀推斷。主要形成了分辯派與統一派的爭端,即「荷馬多人說」和「荷馬一人說」兩個截然對立的學術派別,即有人主張《荷馬史詩》是很多人寫的,歷代累積的,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傳說,然後到了荷馬這兒,他是一個修訂、寫定者。還有的人認為,《荷馬史詩》就是由荷馬一個人獨立完成的。雙方各執一詞,沒有更實證的考證來證明,學術探索步履維艱。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帕裡同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或思想者一樣開始做口述史的田野調查採訪。開始是自己,後來跟他的學生一起深入到口述史流傳風氣很濃的前南斯拉夫地區進行實地的考察,田野作業,發現《荷馬史詩》中有相當多的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詞」,這些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詞」決定了《荷馬史詩》既是程式的,又是傳統的。同時他發現這種傳統的史詩唱法只能是口頭的。為了印證這個,他就深入去做田野作業。經過16個月紮實而縱深的田野作業,搜集和記錄了總共約達1500種的史詩文本,在掌握了如此豐富的口頭史料之後,他宣稱:「我相信我將要帶回美國去的手稿和口頭磁碟的集成,對於研究口頭敘事詩歌的生命力和功能而言,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我借帕裡的話說,從1993年開始我追蹤採訪調查老捨之死,這11年間所作的口述筆錄及錄下的幾十盤錄音帶,就其史料價值來說,同樣是獨一無二的。

昔日的太平湖真的帶著老捨之死的記憶永遠消失了嗎?(網路圖片)
我們都是歷史「歌手」 時常將它唱成「荷馬史詩」
帕裡去世以後,他的學生洛德接過他的學術薪火,他後來在1960年專門出版了一本書叫《故事的歌手》。這裡出現了一個「歌手」的概念,我們記住這個「歌手」,後面我會多次提到。洛德在這本書的開篇引言中就強調,「這是一部關於荷馬的書。荷馬是我們的故事的歌手。而且在一個更大的意義上,荷馬也代表了從洪荒難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的歌手。我們的這部著作也是關於荷馬以外的其他歌手的書。他們中的每一位,即使是最平庸的一位歌手,也和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荷馬一樣,都屬於口頭史詩演唱傳統的一部分。現代歌手無人可以與荷馬並駕齊驅。」
同時,他在對另兩位學者就《伊利亞特》之中關於希臘人和特洛伊人的分類描述所進行的闡述,提出了質疑。他說:「任何一個主題,甚至包括一種分類,都會在時間的推移中顯示出其間的變異。故此,不能企望它保存著『歷史的真實』。……在史詩中呈現了事件,但是,相應的年代編排是混亂無序的。時間被縮微到了一支望遠鏡中。歲月流逝,各個不同時期全都被排列組合到了眼下的表演之中,……口頭史詩呈現的只是關於過去的一副拼圖。」
由這兒,我就想到我所調查的老捨之死,以及以前我們印象當中的老捨之死從何而來。它是不是有很多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關於過去的一副「拼圖」?或者說,老捨之死是不是只是在人們的記憶當中重新塑造和建構起來的?人們口述的關於老捨之死的那些敘述跟老捨之死真實的歷史真相是不是相吻合呢?換言之,今天我們所了解到的老捨之死,是否也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了許多「特定形容詞」編纂而成的另外一種形式的「荷馬史詩」?
裡面到底有多少是歷史的真實?但是這個給我們的困惑是什麼呢?並非它的作者是誰,因為所有向我口述的人,也就是我所採訪的這些人,都是有真名實姓的,誰誰誰,什麼單位,多大年紀,1966年的時候擔任什麼職務,等等,全是具體而翔實的,同荷馬不一樣。困惑來自於史詩本身,並非作者,因為「歌手」都是有名的。而洛德講到「歌手」作用的時候,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對歌手來說,歌就是故事本身,歌是不能改變的(因為在歌手看來,改變它就意味著講述了一個不真實的故事,或歪曲了歷史。)在歌手的觀念中,他專註的穩定性並不包括詞語,對他來說,詞語從來沒有固定過,而且故事的那些非實質性部分也從來沒有固定過。他把自己的表演和我們所認為的歌,建構在穩定的敘事框架上,這就是歌手感覺到的歌。」顯然,「歌手」感覺到的歌是真實的,他便拿它當真實的再一代一代地往下傳,而一代一代聽了「歌手」敘述的歌的「歌手」,又將他所接收到的敘述一代一代往下傳,到了我們所能夠接收的「歌手」向我們描述歷史情形的時候,離那個最初的「歌手」就已經相距甚遠了。而最初的「歌手」所傳唱的故事,也可能早就已經不是歷史原來的本真了。

老捨(1939年)(網路圖片)
歷史是一隻精緻的瓷瓶 發生的瞬間就打碎了
對於老捨,我們把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紅衛兵批鬥時所發生的事情,簡稱叫「八二三事件」。當幾十位敘述人把歷史的記憶凝固在那一天講述的時候,如果你只面對一個敘述者,你相信他說的是歷史真實,便記錄下來。然後,與其他一個或兩個或三個再去作對比,你會發現怎麼差得那麼遠,怎麼那麼多人會在某一個歷史的細節上,說法截然不同。比如,1966年8月23日,老捨先生為什麼那天要去北京市文聯參加「文化大革命」,眾說紛紜。這還算簡單的。那天上午,老捨先生是幾點到的?不一樣。老捨先生是由他的司機用專車接他去的,還是他自己坐的公共汽車?說法不一樣。老捨先生是穿著白襯衣、藍襯衣,還是穿了外套?不一樣。中午,老捨先生沒有回家,是因為司機罷工不拉他了,還是因為什麼原因?也是各說各話。下午,發生紅衛兵衝擊文聯,把許多文化人揪斗,後來押到孔廟去「焚書坑儒」,文聯內部到底是誰打電話叫來的紅衛兵?到今天這個迷都沒有解開。
試想,經歷過那一事件的人,在事情過去了三十年以後,當他想到自己可能要為那個事件承擔某種個人歷史責任的時候,他敢承認是自己打電話叫來的紅衛兵嗎?所以,這也就帶出了口述歷史的一個明顯特徵,即隨著時過境遷,歷史的當事人可能調整了心態。可能因為當初自己所處那個歷史事件當中的角色和立場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構記憶的時候,便很自然地將它重新編排了。換言之,如果說「八二三事件」是一個瓷瓶,在它發生的瞬間就已經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們今天只是在撿拾過去遺留下來的一些碎片而已,並儘可能地將這些碎片還原拼接。但可能再還原成那一個精緻的瓷瓶嗎?絕對不可能!西方有史學家強調,在歷史發生的瞬間,已發生的歷史就已經不復存在了;而且,歷史永遠不可能和它見證者的口吻相一致。
這樣的話,已經過去的歷史對於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我們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來,儘可能地逼近那個歷史真相,還原出它的歷史意義和歷史價值,這是歷史所帶給我們應有的啟迪或啟發。如果歷史陷入了虛無,我們也沒必要讀歷史,因為沒有真實可言,歷史就是故事,歷史就是小說,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老捨先生的遺體在太平湖被發現後,是如何打撈的,有三位「歌手」所唱的三個版本,該如何甄別?這對於研究老捨及整個事件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關於老捨在1966年8月23日,如何被紅衛兵揪出來?如何被送到孔廟去批鬥挨打?又如何被送迴文聯?如何在那天晚上被扭送到派出所?一天中所發生的很多事情的細節,諸多的口述者所說,很難在某一個點上完全統一,支離破碎,都是散在地上的一個個碎片,幾乎無法把它拼接起來。如果能找到哪個事情和哪個事情能夠相連,或許還容易把它做成一個複原品,但是現在,這片和那片根本就找不著,根本就不相連。因此,這也就造成了製造神話的空間,這是歷史產生這種被塑造成神話的很重要的一個可能性。
關於「老捨之死」從認識上,主要是三種說法,「抗爭說」、「絕望說」、「脆弱說」。大體上有三類學者。第一種把「老捨之死」理解成是用死來表明自己的清白,抗議「文革」,是要捨生取義,與屈原同例。
持「絕望說」者,認為老捨先生一直在掙扎。中共建政以後,老捨先生曾經度過一個相對平穩的生活,精神狀態也很好。但隨著50年代初批判知識分子的運動一個接一個,老捨先生感到內心困惑,掙扎,煎熬。雖然在「文革」以前,很多政治運動都沒有牽扯到他,但他已經看到自己的很多朋友被牽連進去,被批判,被批鬥,直到「文革」,災難找上門來,躲不開了。他絕望,用今天的時髦詞叫失去了精神家園,於是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持「脆弱說」者認為,老捨先生是因為內心脆弱而經受不起打擊而投湖。他們多是經歷過中共建政以後一次或兩次甚至三次的「老運動員」,經歷過一些磨難,所以到「文革」時,他們覺得「文革」的災難對於自己來說不過是舊傷口上又添了一個新傷而已,可能比以前疼得更厲害點,卻可以忍受。他們覺得,老捨先生從中共建政以後,一直是在政治上坐順風船,一帆風順,從來沒有經受過任何的磕磕絆絆。所以當「文革」的風雨來了以後,一下受不了了,他脆弱的心靈,脆弱的精神根本承受不住這命運的一擊,倒下了。
老捨之死就是一場歷史的「羅生門」
原來我在某一段時間,也有點傾向於這說或那說,似乎都有道理。但後來,我慢慢地發現,「老捨之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就像我們很難相信那三個打撈屍體的人哪一個說的是真的一樣,我們也不能輕易地把「老捨之死」的結論下在某一說上。因為「老捨之死」是複雜的,是由複雜的因素導致的,有他自身性格的因素,文本中文學形象的因素,政治因素,等等,都有。
巴金先生在1984年為話劇《老捨之死》劇作寫的一篇序中,說過一段我覺得可以作為我們更深一層理解「老捨之死」的很有啟迪的話。他說,「關於老捨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殺抗爭,不過這抗爭指消極抵抗,並不是勇敢的行為,這裡沒有勇敢的問題,但是當時確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受過士可殺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老捨同志可能有幻滅,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後的心情是悲壯的。沒有結論。那個時候也不會做出什麼結論。」我們看,巴金先生的意思是,既不能簡簡單單地把自殺歸為勇敢的行為,他特彆強調這裡沒有「勇敢」的問題。他說老捨在抗爭的同時,有幻滅,痛苦,疑惑,等等,即有很多種的因素導致了老捨先生的自殺。
我覺得,如果要做一種對比的話,簡單地把它和屈原式掛鉤,是有點太過直接了,我倒願意把「老捨之死」跟王國維之死做個比較。如果從文化類型上來說,他們倆可能更有可比性。
第一點,在自殺方式上可以說都與屈原同例,為什麼?投的都是水。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年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魚藻軒,終年50歲;老捨1966年8月24日於太平湖投水,享年67歲。兩者相隔39年。
第二點,兩人死得都很平靜,是一種理智性的自殺,而非病態的表現。他們死前都很平靜,看不出有任何的異動,不是說情緒低落、抑鬱,流露出一反常態的神情,沒有。而且,王國維還留了一封遺書,就是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後面還有幾句話,但這幾句話是很關鍵的,人們始終探討。什麼叫「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了50歲,就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世變」的世,是世界的世,不是事情的事。這個「世變」是什麼?「義務再辱,」「再」,那前面的那個「辱」是什麼?留下了困惑,給研究王國維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老捨先生自殺前,沒有留下任何隻言片語,雖然後來有很多「歌手」在傳唱的時候,說在太平湖上漂了很多碎紙片,紙片上寫滿了字,人們打撈上那些字,發現是毛xx詩詞《詠梅》:「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但是,據更多的目擊者說,那天湖上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你看,不同的「歌手」所演唱的故事內容不一樣。我們該相信哪一個呢?
第三,對於王國維為什麼自殺,看法「一直眾說紛紜,甚至聚訟不已。」較經典的四個版本是「殉清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說」,還有「殉文化說。」像剛才說老捨之死有三說一樣,關於王國維主要有這四說。
第四點,王國維死後,對他的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說法,對老捨之死同樣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並由此做出不同的猜測和推論,兩者的共同點是「羅生門」的模式。大家有看過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竹林中》或是黑澤明由此改編成的著名電影《羅生門》的嗎?講一個男人身負刀傷死在竹林中,為了查明這一案件訊問了好幾個有關人物,每個人都有各不相同的供訴,而每一種供訴則又都不完全可信。那是因為,每一個相關人物都莫不想為自己的卑鄙做掩飾,為自己的虛榮做辯護。從這個細節,來看王國維之死和「老捨之死」,是不是都有這種「羅生門」的意味?
第五,從王國維留下的遺書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個「世變」和「再辱」是不是可以用在老捨先生身上?「世變,」「文革」對於老捨來說是不是「世變」?如果對老捨先生來說,「文革」是「再辱」,那在這個「辱」之前有沒有「前辱」,「前辱」又是什麼?因為在此之前確實發生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老捨先生雖然沒有受到牽連,但他可能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他至少看到自己有很多朋友卷進去了,他至少可能也會思考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運動,或許他給自己劃了一個底線,假如說自己碰上這樣的運動,要以死抗爭,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第六,王國維在民國以後留辮子,這和老捨在中共建政以後依然穿洋裝,是不是都暗示著要堅守自己原有的理念?我們知道,民國成立以後王國維留起了小辮子,梳著小辮子的國學大師也成為清華園的一道獨特風景。而老捨在中共建政以後,幾乎是作家當中唯一一個穿西裝的,戴禮帽,拄拐棍,洋派十足。兩者在這一點上有共同的象徵意味嗎?這都是留給我們思考的。
另外,關於老捨先生選擇投水自殺的方式,和他作品當中描述的一些人物最後是以投水作為自己生命的結局,有內在聯繫嗎?還有,老捨先生在自殺之前,走出自己的院落,跟自己的小孫女說了一句話,「來,跟爺爺說再見。」跟哪個劇本一樣?《茶館》。《茶館》的最後一幕,王掌櫃決定要自殺了,他讓家人先走。家人往外走的時候,他把小孫女叫住,說:「叫爺爺再看一眼」,兒媳婦又讓小孫女「跟爺爺說再見。」這跟老捨先生臨死之前是一樣的。老捨先生在1957年初寫《茶館》時設定的這個情節,是為自己在九年之後的自殺前從家裡出走做讖語嗎?再看《茶館》的最後一幕,那三個老人,圍著桌子向空中撒紙錢,這個情節印象都很深,對吧?由這個情節,是不是就生出了有些「歌手」關於太平湖面上漂浮著紙片的傳唱?如果我們相信有的話,這個紙片就和《茶館》的最後一幕,便是藝術的真實跟歷史的真實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了。假如是真的,這可是太絕妙的悲劇了!即老捨在《茶館》當中,營造了一個藝術的悲劇,他自己真實的生命終局,又用死書寫了一個史實的悲劇。
關於老捨之死,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會涉及到方方面面,兩個小時怎麼可能說盡。關於老捨為什麼會死,為什麼要投太平湖,都是可以獨立成章的題目。總之,有一點,我想用法國作家加繆的話作為結語。加繆說:「自殺的行動是在內心中默默醞釀著的,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作品。」不管對於老捨,對於王國維,自殺都是他們在深思熟慮中默默醞釀的偉大作品。同時也把這個作品的思想意義留給了「無言」的歷史,留給了「有聲」的後人。歷史是「無言」的,我們是「有聲」的,但是「無言」的歷史無法呈現歷史的答案,「有聲」的我們就能給歷史做定論嗎?
最後,我還是帶著疑問。所以,我不知道此時此刻,大家對於歷史是有了些清晰的了解呢,還是開始陷入到了一場噩夢當中。
原標題:口述歷史下的老捨之死(此篇原為演講稿)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2年8月21日
相關視頻:歷史回顧 - 老捨的悲哀
歷史回顧 - 老捨的悲哀
歷史是我正努力從中醒來的一場噩夢
我是1993年開始從追蹤採訪調查老捨之死,切入來研究老捨的。剛開始想法極其簡單,就是想找到跟1966年8月23日老捨先生生前所在單位北京文聯遭受紅衛兵批鬥相關的親歷者、見證人,通過對他們的採訪,記錄他們的歷史文本敘事,我覺著可能會反映出歷史的真相。於是,從1993年開始,歷經11年,不斷地尋找見證者、當事人,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採訪,我的困惑一次又一次增加,隨著年齡和閱歷的不斷增長,我對於歷史的迷惑,又稍稍地變得清晰起來。我經歷了一段可以說是對歷史的迷途時期,把我領到了混亂之中。我被歷史弄迷惑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知道該相信誰。可以說,我對老捨之死的研究,使我的歷史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老捨之死是一個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文化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事件,但是要將它還原,需要藉助於口述史的敘述。而口述史的敘述來自於不同之口,口口非常複雜。我們現在講到那個「古」字,「古」字怎麼寫?十口相加為古,就是口太多,口口相傳,把別人的口述逐一記下來,這就是產生文字最初時候的歷史。
歷史是什麼,可以任人隨意打扮嗎?你抹一把,我抹一把,歷史就五光十色了?可哪個才是真正的歷史,從哪個塗彩之中才能追本溯源,貼近那個歷史的史實真相呢?不知道。也許正因為此,20世紀愛爾蘭偉大作家喬伊斯在他享有天書之譽的《尤利西斯》一書中,借主人公之口說出了他對於歷史的見解。我十分心儀這句話,他說「歷史是我正努力從中醒來的一場惡夢。」我一直在做這樣一個夢,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醒來。不知道大家聽完這場講座,是淪入了夢中,還是能使你從夢中變得清醒一些?人人各異,看待事物、看待問題的角度都不一樣,因而對於人與事的理解也不一樣。
美國密蘇裡大學「口頭傳統研究中心」的開創者約翰·邁爾斯·弗裡教授,他寫了一本書叫《口頭詩學:帕裡-洛德理論》,這本書是引導我從老捨之死的採訪追蹤向探詢口述史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切入點。看這本書,我首先直觀地感受到口頭詩學與口頭史學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在某種程度上兩者還是兼而有之的。弗裡先生在書裡舉了很多的例子來說明許多民族最早的文學創作樣式,幾乎都是像《荷馬史詩》那樣的英雄史詩或神話傳說。而且,大多是現代民間口頭承傳經過長期的累積形成確定的文本創作。
1925年,美國年輕的古希臘文學專家米爾曼·帕裡開始對《荷馬史詩》產生濃厚的興趣,認為這兩部被後人稱為偉大史詩的總數約達兩萬八千詩行的敘述作品《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遠非荷馬一人所能創作,而肯定是希臘人集體的遺產。
事實上,在荷馬時代稍後不久的歲月裡,關於誰是荷馬,他是什麼時候創作出那些我們慣常歸功於他的詩作的,就已經成為懸而未決的公案,變得撲朔迷離。由於沒有留下關於《荷馬史詩》創作者的確切記載,後世的學者們只能根據零星的線索,來做各式各樣的主觀推斷。主要形成了分辯派與統一派的爭端,即「荷馬多人說」和「荷馬一人說」兩個截然對立的學術派別,即有人主張《荷馬史詩》是很多人寫的,歷代累積的,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傳說,然後到了荷馬這兒,他是一個修訂、寫定者。還有的人認為,《荷馬史詩》就是由荷馬一個人獨立完成的。雙方各執一詞,沒有更實證的考證來證明,學術探索步履維艱。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帕裡同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或思想者一樣開始做口述史的田野調查採訪。開始是自己,後來跟他的學生一起深入到口述史流傳風氣很濃的前南斯拉夫地區進行實地的考察,田野作業,發現《荷馬史詩》中有相當多的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詞」,這些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詞」決定了《荷馬史詩》既是程式的,又是傳統的。同時他發現這種傳統的史詩唱法只能是口頭的。為了印證這個,他就深入去做田野作業。經過16個月紮實而縱深的田野作業,搜集和記錄了總共約達1500種的史詩文本,在掌握了如此豐富的口頭史料之後,他宣稱:「我相信我將要帶回美國去的手稿和口頭磁碟的集成,對於研究口頭敘事詩歌的生命力和功能而言,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我借帕裡的話說,從1993年開始我追蹤採訪調查老捨之死,這11年間所作的口述筆錄及錄下的幾十盤錄音帶,就其史料價值來說,同樣是獨一無二的。

昔日的太平湖真的帶著老捨之死的記憶永遠消失了嗎?(網路圖片)
我們都是歷史「歌手」 時常將它唱成「荷馬史詩」
帕裡去世以後,他的學生洛德接過他的學術薪火,他後來在1960年專門出版了一本書叫《故事的歌手》。這裡出現了一個「歌手」的概念,我們記住這個「歌手」,後面我會多次提到。洛德在這本書的開篇引言中就強調,「這是一部關於荷馬的書。荷馬是我們的故事的歌手。而且在一個更大的意義上,荷馬也代表了從洪荒難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的歌手。我們的這部著作也是關於荷馬以外的其他歌手的書。他們中的每一位,即使是最平庸的一位歌手,也和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荷馬一樣,都屬於口頭史詩演唱傳統的一部分。現代歌手無人可以與荷馬並駕齊驅。」
同時,他在對另兩位學者就《伊利亞特》之中關於希臘人和特洛伊人的分類描述所進行的闡述,提出了質疑。他說:「任何一個主題,甚至包括一種分類,都會在時間的推移中顯示出其間的變異。故此,不能企望它保存著『歷史的真實』。……在史詩中呈現了事件,但是,相應的年代編排是混亂無序的。時間被縮微到了一支望遠鏡中。歲月流逝,各個不同時期全都被排列組合到了眼下的表演之中,……口頭史詩呈現的只是關於過去的一副拼圖。」
由這兒,我就想到我所調查的老捨之死,以及以前我們印象當中的老捨之死從何而來。它是不是有很多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關於過去的一副「拼圖」?或者說,老捨之死是不是只是在人們的記憶當中重新塑造和建構起來的?人們口述的關於老捨之死的那些敘述跟老捨之死真實的歷史真相是不是相吻合呢?換言之,今天我們所了解到的老捨之死,是否也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了許多「特定形容詞」編纂而成的另外一種形式的「荷馬史詩」?
裡面到底有多少是歷史的真實?但是這個給我們的困惑是什麼呢?並非它的作者是誰,因為所有向我口述的人,也就是我所採訪的這些人,都是有真名實姓的,誰誰誰,什麼單位,多大年紀,1966年的時候擔任什麼職務,等等,全是具體而翔實的,同荷馬不一樣。困惑來自於史詩本身,並非作者,因為「歌手」都是有名的。而洛德講到「歌手」作用的時候,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對歌手來說,歌就是故事本身,歌是不能改變的(因為在歌手看來,改變它就意味著講述了一個不真實的故事,或歪曲了歷史。)在歌手的觀念中,他專註的穩定性並不包括詞語,對他來說,詞語從來沒有固定過,而且故事的那些非實質性部分也從來沒有固定過。他把自己的表演和我們所認為的歌,建構在穩定的敘事框架上,這就是歌手感覺到的歌。」顯然,「歌手」感覺到的歌是真實的,他便拿它當真實的再一代一代地往下傳,而一代一代聽了「歌手」敘述的歌的「歌手」,又將他所接收到的敘述一代一代往下傳,到了我們所能夠接收的「歌手」向我們描述歷史情形的時候,離那個最初的「歌手」就已經相距甚遠了。而最初的「歌手」所傳唱的故事,也可能早就已經不是歷史原來的本真了。

老捨(1939年)(網路圖片)
歷史是一隻精緻的瓷瓶 發生的瞬間就打碎了
對於老捨,我們把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紅衛兵批鬥時所發生的事情,簡稱叫「八二三事件」。當幾十位敘述人把歷史的記憶凝固在那一天講述的時候,如果你只面對一個敘述者,你相信他說的是歷史真實,便記錄下來。然後,與其他一個或兩個或三個再去作對比,你會發現怎麼差得那麼遠,怎麼那麼多人會在某一個歷史的細節上,說法截然不同。比如,1966年8月23日,老捨先生為什麼那天要去北京市文聯參加「文化大革命」,眾說紛紜。這還算簡單的。那天上午,老捨先生是幾點到的?不一樣。老捨先生是由他的司機用專車接他去的,還是他自己坐的公共汽車?說法不一樣。老捨先生是穿著白襯衣、藍襯衣,還是穿了外套?不一樣。中午,老捨先生沒有回家,是因為司機罷工不拉他了,還是因為什麼原因?也是各說各話。下午,發生紅衛兵衝擊文聯,把許多文化人揪斗,後來押到孔廟去「焚書坑儒」,文聯內部到底是誰打電話叫來的紅衛兵?到今天這個迷都沒有解開。
試想,經歷過那一事件的人,在事情過去了三十年以後,當他想到自己可能要為那個事件承擔某種個人歷史責任的時候,他敢承認是自己打電話叫來的紅衛兵嗎?所以,這也就帶出了口述歷史的一個明顯特徵,即隨著時過境遷,歷史的當事人可能調整了心態。可能因為當初自己所處那個歷史事件當中的角色和立場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構記憶的時候,便很自然地將它重新編排了。換言之,如果說「八二三事件」是一個瓷瓶,在它發生的瞬間就已經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們今天只是在撿拾過去遺留下來的一些碎片而已,並儘可能地將這些碎片還原拼接。但可能再還原成那一個精緻的瓷瓶嗎?絕對不可能!西方有史學家強調,在歷史發生的瞬間,已發生的歷史就已經不復存在了;而且,歷史永遠不可能和它見證者的口吻相一致。
這樣的話,已經過去的歷史對於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我們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來,儘可能地逼近那個歷史真相,還原出它的歷史意義和歷史價值,這是歷史所帶給我們應有的啟迪或啟發。如果歷史陷入了虛無,我們也沒必要讀歷史,因為沒有真實可言,歷史就是故事,歷史就是小說,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老捨先生的遺體在太平湖被發現後,是如何打撈的,有三位「歌手」所唱的三個版本,該如何甄別?這對於研究老捨及整個事件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關於老捨在1966年8月23日,如何被紅衛兵揪出來?如何被送到孔廟去批鬥挨打?又如何被送迴文聯?如何在那天晚上被扭送到派出所?一天中所發生的很多事情的細節,諸多的口述者所說,很難在某一個點上完全統一,支離破碎,都是散在地上的一個個碎片,幾乎無法把它拼接起來。如果能找到哪個事情和哪個事情能夠相連,或許還容易把它做成一個複原品,但是現在,這片和那片根本就找不著,根本就不相連。因此,這也就造成了製造神話的空間,這是歷史產生這種被塑造成神話的很重要的一個可能性。
關於「老捨之死」從認識上,主要是三種說法,「抗爭說」、「絕望說」、「脆弱說」。大體上有三類學者。第一種把「老捨之死」理解成是用死來表明自己的清白,抗議「文革」,是要捨生取義,與屈原同例。
持「絕望說」者,認為老捨先生一直在掙扎。中共建政以後,老捨先生曾經度過一個相對平穩的生活,精神狀態也很好。但隨著50年代初批判知識分子的運動一個接一個,老捨先生感到內心困惑,掙扎,煎熬。雖然在「文革」以前,很多政治運動都沒有牽扯到他,但他已經看到自己的很多朋友被牽連進去,被批判,被批鬥,直到「文革」,災難找上門來,躲不開了。他絕望,用今天的時髦詞叫失去了精神家園,於是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持「脆弱說」者認為,老捨先生是因為內心脆弱而經受不起打擊而投湖。他們多是經歷過中共建政以後一次或兩次甚至三次的「老運動員」,經歷過一些磨難,所以到「文革」時,他們覺得「文革」的災難對於自己來說不過是舊傷口上又添了一個新傷而已,可能比以前疼得更厲害點,卻可以忍受。他們覺得,老捨先生從中共建政以後,一直是在政治上坐順風船,一帆風順,從來沒有經受過任何的磕磕絆絆。所以當「文革」的風雨來了以後,一下受不了了,他脆弱的心靈,脆弱的精神根本承受不住這命運的一擊,倒下了。
老捨之死就是一場歷史的「羅生門」
原來我在某一段時間,也有點傾向於這說或那說,似乎都有道理。但後來,我慢慢地發現,「老捨之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就像我們很難相信那三個打撈屍體的人哪一個說的是真的一樣,我們也不能輕易地把「老捨之死」的結論下在某一說上。因為「老捨之死」是複雜的,是由複雜的因素導致的,有他自身性格的因素,文本中文學形象的因素,政治因素,等等,都有。
巴金先生在1984年為話劇《老捨之死》劇作寫的一篇序中,說過一段我覺得可以作為我們更深一層理解「老捨之死」的很有啟迪的話。他說,「關於老捨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殺抗爭,不過這抗爭指消極抵抗,並不是勇敢的行為,這裡沒有勇敢的問題,但是當時確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受過士可殺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老捨同志可能有幻滅,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後的心情是悲壯的。沒有結論。那個時候也不會做出什麼結論。」我們看,巴金先生的意思是,既不能簡簡單單地把自殺歸為勇敢的行為,他特彆強調這裡沒有「勇敢」的問題。他說老捨在抗爭的同時,有幻滅,痛苦,疑惑,等等,即有很多種的因素導致了老捨先生的自殺。
我覺得,如果要做一種對比的話,簡單地把它和屈原式掛鉤,是有點太過直接了,我倒願意把「老捨之死」跟王國維之死做個比較。如果從文化類型上來說,他們倆可能更有可比性。
第一點,在自殺方式上可以說都與屈原同例,為什麼?投的都是水。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年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魚藻軒,終年50歲;老捨1966年8月24日於太平湖投水,享年67歲。兩者相隔39年。
第二點,兩人死得都很平靜,是一種理智性的自殺,而非病態的表現。他們死前都很平靜,看不出有任何的異動,不是說情緒低落、抑鬱,流露出一反常態的神情,沒有。而且,王國維還留了一封遺書,就是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後面還有幾句話,但這幾句話是很關鍵的,人們始終探討。什麼叫「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了50歲,就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世變」的世,是世界的世,不是事情的事。這個「世變」是什麼?「義務再辱,」「再」,那前面的那個「辱」是什麼?留下了困惑,給研究王國維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老捨先生自殺前,沒有留下任何隻言片語,雖然後來有很多「歌手」在傳唱的時候,說在太平湖上漂了很多碎紙片,紙片上寫滿了字,人們打撈上那些字,發現是毛xx詩詞《詠梅》:「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但是,據更多的目擊者說,那天湖上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你看,不同的「歌手」所演唱的故事內容不一樣。我們該相信哪一個呢?
第三,對於王國維為什麼自殺,看法「一直眾說紛紜,甚至聚訟不已。」較經典的四個版本是「殉清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說」,還有「殉文化說。」像剛才說老捨之死有三說一樣,關於王國維主要有這四說。
第四點,王國維死後,對他的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說法,對老捨之死同樣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並由此做出不同的猜測和推論,兩者的共同點是「羅生門」的模式。大家有看過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竹林中》或是黑澤明由此改編成的著名電影《羅生門》的嗎?講一個男人身負刀傷死在竹林中,為了查明這一案件訊問了好幾個有關人物,每個人都有各不相同的供訴,而每一種供訴則又都不完全可信。那是因為,每一個相關人物都莫不想為自己的卑鄙做掩飾,為自己的虛榮做辯護。從這個細節,來看王國維之死和「老捨之死」,是不是都有這種「羅生門」的意味?
第五,從王國維留下的遺書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個「世變」和「再辱」是不是可以用在老捨先生身上?「世變,」「文革」對於老捨來說是不是「世變」?如果對老捨先生來說,「文革」是「再辱」,那在這個「辱」之前有沒有「前辱」,「前辱」又是什麼?因為在此之前確實發生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老捨先生雖然沒有受到牽連,但他可能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他至少看到自己有很多朋友卷進去了,他至少可能也會思考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運動,或許他給自己劃了一個底線,假如說自己碰上這樣的運動,要以死抗爭,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第六,王國維在民國以後留辮子,這和老捨在中共建政以後依然穿洋裝,是不是都暗示著要堅守自己原有的理念?我們知道,民國成立以後王國維留起了小辮子,梳著小辮子的國學大師也成為清華園的一道獨特風景。而老捨在中共建政以後,幾乎是作家當中唯一一個穿西裝的,戴禮帽,拄拐棍,洋派十足。兩者在這一點上有共同的象徵意味嗎?這都是留給我們思考的。
另外,關於老捨先生選擇投水自殺的方式,和他作品當中描述的一些人物最後是以投水作為自己生命的結局,有內在聯繫嗎?還有,老捨先生在自殺之前,走出自己的院落,跟自己的小孫女說了一句話,「來,跟爺爺說再見。」跟哪個劇本一樣?《茶館》。《茶館》的最後一幕,王掌櫃決定要自殺了,他讓家人先走。家人往外走的時候,他把小孫女叫住,說:「叫爺爺再看一眼」,兒媳婦又讓小孫女「跟爺爺說再見。」這跟老捨先生臨死之前是一樣的。老捨先生在1957年初寫《茶館》時設定的這個情節,是為自己在九年之後的自殺前從家裡出走做讖語嗎?再看《茶館》的最後一幕,那三個老人,圍著桌子向空中撒紙錢,這個情節印象都很深,對吧?由這個情節,是不是就生出了有些「歌手」關於太平湖面上漂浮著紙片的傳唱?如果我們相信有的話,這個紙片就和《茶館》的最後一幕,便是藝術的真實跟歷史的真實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了。假如是真的,這可是太絕妙的悲劇了!即老捨在《茶館》當中,營造了一個藝術的悲劇,他自己真實的生命終局,又用死書寫了一個史實的悲劇。
關於老捨之死,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會涉及到方方面面,兩個小時怎麼可能說盡。關於老捨為什麼會死,為什麼要投太平湖,都是可以獨立成章的題目。總之,有一點,我想用法國作家加繆的話作為結語。加繆說:「自殺的行動是在內心中默默醞釀著的,猶如醞釀一部偉大的作品。」不管對於老捨,對於王國維,自殺都是他們在深思熟慮中默默醞釀的偉大作品。同時也把這個作品的思想意義留給了「無言」的歷史,留給了「有聲」的後人。歷史是「無言」的,我們是「有聲」的,但是「無言」的歷史無法呈現歷史的答案,「有聲」的我們就能給歷史做定論嗎?
最後,我還是帶著疑問。所以,我不知道此時此刻,大家對於歷史是有了些清晰的了解呢,還是開始陷入到了一場噩夢當中。
原標題:口述歷史下的老捨之死(此篇原為演講稿)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2年8月21日
相關視頻:歷史回顧 - 老捨的悲哀
歷史回顧 - 老捨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