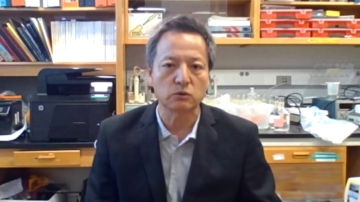吊銬是一種酷刑,又被稱為上大掛。影視作品中將人吊起進行折磨的吊刑,大都是用繩子將人的雙手綁住,然後吊起。而要是將人的雙手用手銬銬上後再吊起,那痛苦的滋味該有多大?因為手銬都是用鋼鑄成的,厚度不到半厘米,那真如刀割一樣疼痛。而且惡警在實施這種酷刑時,往往再加上其它酷刑合併使用,或者超長時間用這一種酷刑,使人生不如死。

(作者提供)
長時間吊銬
湖南省湘西花垣縣峨碧村法輪功學員肖永康,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被花垣縣「六一零辦公室」主任石廣斌、政法委龍光勇等人綁架到懷化市「法制教育基地」。在這個洗腦班,她被毒打嘴巴、耳光,用手銬懸空吊著雙手,腳不沾地,吊了五天兩夜,手腕的皮被扯掉好大一塊,鑽心的痛,全身就象五馬分屍般痛苦難熬,身體不停的顫抖,心慌,口乾,全身出虛汗。花垣縣團結鎮政府工作人員吳吉平,參與了對她的迫害,還對身邊的人說:「對肖永康要狠、要毒。」並不准肖永康吃飯、上廁所、睡覺及用水。

(作者提供)
今年六十三歲的重慶法輪功學員喻群芳女士,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被長安一分局綁架,後被惡警晏詳明、饒江做黑材料將她非法勞教一年。在茅家山女子勞教所,喻群芳被惡警艾某某、許某某連續吊銬二十天,
吊銬+腳鐐+電擊
安徽省淮南市法輪功學員徐春,二零零三年遭枉判九年,被投入宿州監獄。期間,惡警先將徐春的雙手吊在鐵門上,雙腳砸上鐵鐐,只剩腳尖觸地,每天二十四小時(除吃飯時放下一隻手和有限次的上廁所外),就這麼吊著,前後有三至四個月。惡警為了加大轉化力度,每天晚上六點以後,又將他強制拖到嚴管隊用幾根電棒電他。
大字形吊銬
在甘肅省第一勞教所,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一個姓胡的惡警把甘肅張掖市運輸公司職工、法輪功學員鄭超英吊銬在獄警辦公室的窗子上,使其腳尖離地,連續九天。同時胡還用拳頭打她的胸部,打耳光,還用惡言穢語辱罵她。九天下來她的整個手腕都是膿和血,十幾年後還留有痕跡。
還有一次,鄭超英又被吊了起來,這回是大字形吊銬,手腕被壓了一個深槽,手銬被深深地嵌在手腕裡。姓胡的惡警用手指抓破鄭超英的大腿內側,鄭超英頭耷拉下來,汗水不停的流著,意識也不清楚了。姓胡的惡警用警棍把鄭超英的頭頂了起來問:「是汗水還是眼淚?」
用帶刺的手銬吊銬
一九九九年臘月二十八晚上,河北遷西縣商業局退休職工張瑞英被劫持到河北唐山開平勞教所。在勞教所,她曾被銬在籃球架子上,腳跟不著地,懸著,手銬是帶刺的,一會就剎進了肉裡,越動越緊,鑽心難忍。一會犯人又端一臉盆水,從下往上往臉上潑,嗆的出不來氣。就這樣銬了幾個小時,她被放下來時,手腕血肉模糊,手已經沒有了知覺,捏都不知道疼。在這樣的迫害中,她被折磨的骨瘦如柴,一頭黑髮變成白髮。手腕的血印好幾年才下去。
在特製的刑架上弔銬
重慶市大渡口區看守所第一提訊室內設置了一個特製的刑具,這個刑具就是為實施吊銬而製作的。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午,重慶市合川區雲門鎮雙眼小學教師高婕遭到了這種酷刑的摧殘。高婕在文章中這樣自述:「他們就把我吊銬在提訊室的屋角用鋼條與角鋼焊接成的切角壁上,踢掉我穿的拖鞋,光著腳,腳跟踩在角鋼口上,雙手臂分開被斜直吊銬在鋼條壁的最高處,如果腳踩在平地上,手銬就越勒越緊,所以腳尖只好踮著;眼前上方吊著幾百瓦的電燈烤著。……王東陵(大渡口國保惡警)用塑料袋擰成繩索,一端系在手銬上,拉著另一端往一邊用力拽,疼得我的手腕幾乎失去知覺,王卻說:「我們是虐待狂,你是被虐待狂,我們就是要這樣虐待你。」劉光靜(大渡口國保惡警)坐在椅子上用力蹬鋼條壁,鋼條壁來回彈動,猛烈的撞擊我的尾骨、背部和頭部,尤其是銬著的手腕象鞦韆一樣盪著,皮快被勒破了,疼痛難忍。劉還惡狠狠的說:「我們是警官,讓你也久關,多做你幾年,關死你。」
背銬著來回吊起再摔下
二零零三年三月,撫順法輪功學員黃桂榮被綁架到遼寧女子監獄。在那裡,惡徒把黃桂榮兩手背銬起來,在兩手中間繫上鋼絲,雙腳踩在一個六厘米寬、二十厘米長的小板凳上,吊在女監的小舞台上方,後面還有一個大柱子。然後惡人手拉鋼絲,將黃桂榮高高吊起。被銬的雙手失去知覺時,又快速將鋼絲鬆手,手掉下來正好砸在大柱子上,疼得她連話都說不出來。剛得到點緩解時,惡徒又拉鋼絲把她再次高吊起來了,再快速鬆手,手又被砸在大柱子上。而黃桂榮腳下的小凳子雙腳踩上就會翻,只能兩腳換著踩。就這樣反覆地折磨黃桂榮。

(作者提供)
還有一次,一個叫王寶茹的犯人,用手銬將黃桂榮雙手銬到鐵床上,人就懸起來了。惡人拽著兩條腿一邊抻一邊前後晃動著,加大下垂力,折磨黃桂榮。
「古代高跟鞋」
在遼寧女子監獄,黃桂榮還遭受過一種叫做「古代高跟鞋」的酷刑。
有一天晚上,警察劉英傑值班,對黃桂榮開始實施這種叫作古代高跟鞋的吊刑。就是在木板上釘上四、五個釘子,不釘到底,釘帽朝上露出半厘米高。然後把你雙手吊起來,讓你光著腳踏在釘子木板上,一腳一個釘子板,你不踩釘子板,吊著的手痛得很,你若踩釘子板,釘帽往肉裡鑽,腳又痛不欲生。黃桂榮就是這樣被中共酷刑折磨得腳上是眼,手上是痕。
冷凍型吊銬
黃桂榮在遼寧女子監獄還受到過這樣一種吊銬的酷刑。惡人將一個塗料桶灌上涼水,讓黃桂榮站在水桶裡,雙手吊銬在牆壁上固定好的鐵管上。當時是三九嚴冬,東北的寒冬有時氣溫可達零下30℃左右。就是在這樣的氣候下,從早上一直吊到晚上八、九點鐘,長達十幾個小時。
窯頂吊銬
寧夏的銀川監獄河東監區的「窯頂吊銬」酷刑,是用高溫的方法折磨法輪功學員的。這種酷刑是河東監區的教導員李永欣發明的。監區裡的磚窯約有兩層樓高,窯頂上栽著輸送動力電的木質電線杆,磚窯內的高溫將窯頂烤的熾熱。二零零一年八月的一天,天氣炎熱,窯頂溫度至少有攝氏四、五十度。因法輪功學員路向東、王玉柱不轉化,李永欣就想出這樣一個陰招來:將人兩臂反剪戴上手銬,用長繩子從電線杆高處的卡子內穿出來,再從手銬內穿過去,然後使勁拉繩子讓人後腳跟離地。王玉柱被李永欣,和一中隊指導員岳懷寧這樣銬在磚窯頂上四十多分鐘,雙臂冰冷麻木、大汗淋漓、呼吸困難。路向東被這樣吊銬後,一個多月雙臂還是麻木的,生活已不能自理。
她就這樣被吊銬著致殘
重慶大學研究生、法輪功學員魏星艷在看守所被惡警強姦一事在國際上被報道出來後,重慶當局異常驚恐,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瘋狂迫害。重慶市北碚區法輪功學員劉范欽被綁架後,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被大渡口區公安分局惡警從看守所用小車拉到一個祕密的地方。在大渡口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陳波等人的指使下,公安分局主任華勇、國保支隊長文方火現場指揮,警察李軻、譚旭、胡彬、黃小月(女)等人分成兩組,輪番對她進行酷刑折磨。
他們將她雙手強制吊銬在窗戶外牆的鐵欄上,人站在室內背靠著牆,雙手被吊銬在頭頂上方往窗外斜拉,中間隔著幾十厘米厚的磚牆,腰部正好被窗沿頂著根本無法站直,整個身軀只能向後仰,腳尖著地。半小時不到,她就已經氣喘吁吁。
由於腰椎向後彎曲承受不住,劉范欽只能艱難的不斷左右微微側身,但雙手被拉抻吊銬,腰部又被窗沿頂著,身軀也動不了多少。而惡警卻根本不顧她的死活,也不準吃飯、打盹、上廁所。就這樣,在身軀變形扭曲的高強度拉抻吊銬下,連續三十多個小時撕心裂肺的劇痛和多次昏迷後,惡警才把她放下。那時,她的雙上肢早已沒有知覺,當即殘廢。
從此,劉范欽從一個四肢功能健全、身心健康的正常人,變成雙上肢完全喪失功能的殘廢人。經重慶市骨科醫院、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重慶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等多家醫院診斷後得知:雙臂臂叢神經損傷、雙肩關節韌帶損傷,並由神經和韌帶損傷引起兩個肩關節脫位(此外,還造成腰骶部損傷)。對此,就診醫院全都束手無策,醫生只能搖頭嘆息,認為上肢功能恢復無望。
吊銬、毒打致死

(作者提供)
大連法輪功學員劉永來,在大連勞動教養院遭到殘酷折磨。二零零一年七月六日晚,劉永來被吊銬折磨六個小時,嘴角兩邊被惡警用鐵絲鉤開,流著血昏迷過去。惡警解開手銬,劉永來已不能行走,送回監室時幾乎不能說話了,但仍拒絕寫放棄修鍊的保證。惡警又把他帶走從新吊銬,開始下毒手毒打,腿被打斷,後腦被打塌陷,劉永來被活活打死,年僅三十六歲。
她在吊銬中死去

(作者提供)
甘肅民勤縣中醫院藥劑師劉蘭香,在蘭州金港城自己家中被蘭州七裡河分局惡警非法綁架。她絕食抗議,被蘭州七裡河分局惡警提審過程中暴打致重傷,送回西果園看守所。在看守所,她絕食反迫害,遭到毒打。惡警給她戴上了手銬、腳鐐,並指使犯人把她抬到院子裡強行灌鹽水。四月九日晚戴上銬子吊起來被毒打了幾個小時。二零零一年四月十日,劉蘭香在酷刑中死亡。當時劉蘭香兩手腕嚴重損傷,雙腳腳尖與腿成直線狀,僵硬垂直向下,而且死後還在架上弔著。
吊銬這種酷刑的殘忍,是別人無法想象的,恐怕只有親身經歷者才能感受到那種痛苦。有人會說:那些實施吊銬的惡徒,他們還是人嗎?簡直是禽獸不如。我們說,這些人,只是披了一張人皮,徒有一個人形,實質上他們早已不是人了,而是一群活在世上的惡魔。

(作者提供)
長時間吊銬
湖南省湘西花垣縣峨碧村法輪功學員肖永康,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被花垣縣「六一零辦公室」主任石廣斌、政法委龍光勇等人綁架到懷化市「法制教育基地」。在這個洗腦班,她被毒打嘴巴、耳光,用手銬懸空吊著雙手,腳不沾地,吊了五天兩夜,手腕的皮被扯掉好大一塊,鑽心的痛,全身就象五馬分屍般痛苦難熬,身體不停的顫抖,心慌,口乾,全身出虛汗。花垣縣團結鎮政府工作人員吳吉平,參與了對她的迫害,還對身邊的人說:「對肖永康要狠、要毒。」並不准肖永康吃飯、上廁所、睡覺及用水。

(作者提供)
今年六十三歲的重慶法輪功學員喻群芳女士,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被長安一分局綁架,後被惡警晏詳明、饒江做黑材料將她非法勞教一年。在茅家山女子勞教所,喻群芳被惡警艾某某、許某某連續吊銬二十天,
吊銬+腳鐐+電擊
安徽省淮南市法輪功學員徐春,二零零三年遭枉判九年,被投入宿州監獄。期間,惡警先將徐春的雙手吊在鐵門上,雙腳砸上鐵鐐,只剩腳尖觸地,每天二十四小時(除吃飯時放下一隻手和有限次的上廁所外),就這麼吊著,前後有三至四個月。惡警為了加大轉化力度,每天晚上六點以後,又將他強制拖到嚴管隊用幾根電棒電他。
大字形吊銬
在甘肅省第一勞教所,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一個姓胡的惡警把甘肅張掖市運輸公司職工、法輪功學員鄭超英吊銬在獄警辦公室的窗子上,使其腳尖離地,連續九天。同時胡還用拳頭打她的胸部,打耳光,還用惡言穢語辱罵她。九天下來她的整個手腕都是膿和血,十幾年後還留有痕跡。
還有一次,鄭超英又被吊了起來,這回是大字形吊銬,手腕被壓了一個深槽,手銬被深深地嵌在手腕裡。姓胡的惡警用手指抓破鄭超英的大腿內側,鄭超英頭耷拉下來,汗水不停的流著,意識也不清楚了。姓胡的惡警用警棍把鄭超英的頭頂了起來問:「是汗水還是眼淚?」
用帶刺的手銬吊銬
一九九九年臘月二十八晚上,河北遷西縣商業局退休職工張瑞英被劫持到河北唐山開平勞教所。在勞教所,她曾被銬在籃球架子上,腳跟不著地,懸著,手銬是帶刺的,一會就剎進了肉裡,越動越緊,鑽心難忍。一會犯人又端一臉盆水,從下往上往臉上潑,嗆的出不來氣。就這樣銬了幾個小時,她被放下來時,手腕血肉模糊,手已經沒有了知覺,捏都不知道疼。在這樣的迫害中,她被折磨的骨瘦如柴,一頭黑髮變成白髮。手腕的血印好幾年才下去。
在特製的刑架上弔銬
重慶市大渡口區看守所第一提訊室內設置了一個特製的刑具,這個刑具就是為實施吊銬而製作的。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午,重慶市合川區雲門鎮雙眼小學教師高婕遭到了這種酷刑的摧殘。高婕在文章中這樣自述:「他們就把我吊銬在提訊室的屋角用鋼條與角鋼焊接成的切角壁上,踢掉我穿的拖鞋,光著腳,腳跟踩在角鋼口上,雙手臂分開被斜直吊銬在鋼條壁的最高處,如果腳踩在平地上,手銬就越勒越緊,所以腳尖只好踮著;眼前上方吊著幾百瓦的電燈烤著。……王東陵(大渡口國保惡警)用塑料袋擰成繩索,一端系在手銬上,拉著另一端往一邊用力拽,疼得我的手腕幾乎失去知覺,王卻說:「我們是虐待狂,你是被虐待狂,我們就是要這樣虐待你。」劉光靜(大渡口國保惡警)坐在椅子上用力蹬鋼條壁,鋼條壁來回彈動,猛烈的撞擊我的尾骨、背部和頭部,尤其是銬著的手腕象鞦韆一樣盪著,皮快被勒破了,疼痛難忍。劉還惡狠狠的說:「我們是警官,讓你也久關,多做你幾年,關死你。」
背銬著來回吊起再摔下
二零零三年三月,撫順法輪功學員黃桂榮被綁架到遼寧女子監獄。在那裡,惡徒把黃桂榮兩手背銬起來,在兩手中間繫上鋼絲,雙腳踩在一個六厘米寬、二十厘米長的小板凳上,吊在女監的小舞台上方,後面還有一個大柱子。然後惡人手拉鋼絲,將黃桂榮高高吊起。被銬的雙手失去知覺時,又快速將鋼絲鬆手,手掉下來正好砸在大柱子上,疼得她連話都說不出來。剛得到點緩解時,惡徒又拉鋼絲把她再次高吊起來了,再快速鬆手,手又被砸在大柱子上。而黃桂榮腳下的小凳子雙腳踩上就會翻,只能兩腳換著踩。就這樣反覆地折磨黃桂榮。

(作者提供)
還有一次,一個叫王寶茹的犯人,用手銬將黃桂榮雙手銬到鐵床上,人就懸起來了。惡人拽著兩條腿一邊抻一邊前後晃動著,加大下垂力,折磨黃桂榮。
「古代高跟鞋」
在遼寧女子監獄,黃桂榮還遭受過一種叫做「古代高跟鞋」的酷刑。
有一天晚上,警察劉英傑值班,對黃桂榮開始實施這種叫作古代高跟鞋的吊刑。就是在木板上釘上四、五個釘子,不釘到底,釘帽朝上露出半厘米高。然後把你雙手吊起來,讓你光著腳踏在釘子木板上,一腳一個釘子板,你不踩釘子板,吊著的手痛得很,你若踩釘子板,釘帽往肉裡鑽,腳又痛不欲生。黃桂榮就是這樣被中共酷刑折磨得腳上是眼,手上是痕。
冷凍型吊銬
黃桂榮在遼寧女子監獄還受到過這樣一種吊銬的酷刑。惡人將一個塗料桶灌上涼水,讓黃桂榮站在水桶裡,雙手吊銬在牆壁上固定好的鐵管上。當時是三九嚴冬,東北的寒冬有時氣溫可達零下30℃左右。就是在這樣的氣候下,從早上一直吊到晚上八、九點鐘,長達十幾個小時。
窯頂吊銬
寧夏的銀川監獄河東監區的「窯頂吊銬」酷刑,是用高溫的方法折磨法輪功學員的。這種酷刑是河東監區的教導員李永欣發明的。監區裡的磚窯約有兩層樓高,窯頂上栽著輸送動力電的木質電線杆,磚窯內的高溫將窯頂烤的熾熱。二零零一年八月的一天,天氣炎熱,窯頂溫度至少有攝氏四、五十度。因法輪功學員路向東、王玉柱不轉化,李永欣就想出這樣一個陰招來:將人兩臂反剪戴上手銬,用長繩子從電線杆高處的卡子內穿出來,再從手銬內穿過去,然後使勁拉繩子讓人後腳跟離地。王玉柱被李永欣,和一中隊指導員岳懷寧這樣銬在磚窯頂上四十多分鐘,雙臂冰冷麻木、大汗淋漓、呼吸困難。路向東被這樣吊銬後,一個多月雙臂還是麻木的,生活已不能自理。
她就這樣被吊銬著致殘
重慶大學研究生、法輪功學員魏星艷在看守所被惡警強姦一事在國際上被報道出來後,重慶當局異常驚恐,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瘋狂迫害。重慶市北碚區法輪功學員劉范欽被綁架後,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被大渡口區公安分局惡警從看守所用小車拉到一個祕密的地方。在大渡口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陳波等人的指使下,公安分局主任華勇、國保支隊長文方火現場指揮,警察李軻、譚旭、胡彬、黃小月(女)等人分成兩組,輪番對她進行酷刑折磨。
他們將她雙手強制吊銬在窗戶外牆的鐵欄上,人站在室內背靠著牆,雙手被吊銬在頭頂上方往窗外斜拉,中間隔著幾十厘米厚的磚牆,腰部正好被窗沿頂著根本無法站直,整個身軀只能向後仰,腳尖著地。半小時不到,她就已經氣喘吁吁。
由於腰椎向後彎曲承受不住,劉范欽只能艱難的不斷左右微微側身,但雙手被拉抻吊銬,腰部又被窗沿頂著,身軀也動不了多少。而惡警卻根本不顧她的死活,也不準吃飯、打盹、上廁所。就這樣,在身軀變形扭曲的高強度拉抻吊銬下,連續三十多個小時撕心裂肺的劇痛和多次昏迷後,惡警才把她放下。那時,她的雙上肢早已沒有知覺,當即殘廢。
從此,劉范欽從一個四肢功能健全、身心健康的正常人,變成雙上肢完全喪失功能的殘廢人。經重慶市骨科醫院、第三軍醫大學西南醫院、重慶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等多家醫院診斷後得知:雙臂臂叢神經損傷、雙肩關節韌帶損傷,並由神經和韌帶損傷引起兩個肩關節脫位(此外,還造成腰骶部損傷)。對此,就診醫院全都束手無策,醫生只能搖頭嘆息,認為上肢功能恢復無望。
吊銬、毒打致死

(作者提供)
大連法輪功學員劉永來,在大連勞動教養院遭到殘酷折磨。二零零一年七月六日晚,劉永來被吊銬折磨六個小時,嘴角兩邊被惡警用鐵絲鉤開,流著血昏迷過去。惡警解開手銬,劉永來已不能行走,送回監室時幾乎不能說話了,但仍拒絕寫放棄修鍊的保證。惡警又把他帶走從新吊銬,開始下毒手毒打,腿被打斷,後腦被打塌陷,劉永來被活活打死,年僅三十六歲。
她在吊銬中死去

(作者提供)
甘肅民勤縣中醫院藥劑師劉蘭香,在蘭州金港城自己家中被蘭州七裡河分局惡警非法綁架。她絕食抗議,被蘭州七裡河分局惡警提審過程中暴打致重傷,送回西果園看守所。在看守所,她絕食反迫害,遭到毒打。惡警給她戴上了手銬、腳鐐,並指使犯人把她抬到院子裡強行灌鹽水。四月九日晚戴上銬子吊起來被毒打了幾個小時。二零零一年四月十日,劉蘭香在酷刑中死亡。當時劉蘭香兩手腕嚴重損傷,雙腳腳尖與腿成直線狀,僵硬垂直向下,而且死後還在架上弔著。
吊銬這種酷刑的殘忍,是別人無法想象的,恐怕只有親身經歷者才能感受到那種痛苦。有人會說:那些實施吊銬的惡徒,他們還是人嗎?簡直是禽獸不如。我們說,這些人,只是披了一張人皮,徒有一個人形,實質上他們早已不是人了,而是一群活在世上的惡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