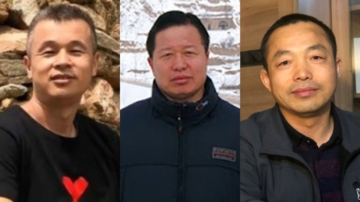【新唐人2016年10月04日訊】(編者按:大紀元獲高律師家人授權,節選刊登高智晟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的部分內容。這本書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師在整個十年被非法關押期間經歷的酷刑、牢獄生活、軍營武警的暴虐、最高層的膽小如鼠等鮮為人知的內幕。高智晟律師承受了地獄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著走出了監獄,並看清了中共的邪惡、虛弱、腐爛和崩亡。)
2011年12月14日半夜,我在睡夢中被人搖醒,睜眼一看是六中隊中隊隊長,說接上面緊急通知,讓我立即起床接受談話。我起床不一會兒門被打開進來三人,倆人就是我前述文字中提到的「惡煞一郎」和「惡煞同一郎」,另一官員模樣者倒背雙手站在桌子後面,「一郎」提著手銬,「同一郎」一手提著黑頭套,三人進囚室並不說一句話。我被示意站起來,兩位「惡煞」走過來扳轉我的身體,將我壓坐在床上,然後煞有介事地開始拍摸搜查我的身體,有一人蹲下搜查我的下半身和鞋襪,搜查完畢後將黑頭套套在我頭上,然後兩人將我的手擰在背後給銬住。
我被架了起來,感到自己被架出了門,又開始架著上樓梯,我感到自己被架著走出了門外,這是二十一個月來的第一次,一股涼爽通灌身體,第一次在戶外聽到警犬「小瘸」雄厚渾實的磣人的嗷叫聲。我被架上了車坐下,左右各一人壓著我的肩膀,汽車開動,一路無一人說話。汽車行進兩個多小時後停了下來,我被架下了車,然後感到被架進一個門,「媽的低頭」,終於聽見有人說話,後腦勺被人狠勁往前壓了一把,我們站在一個地方。
「還是把頭套給取了吧。」又有人說話了,我的頭套被取下。我發現我站在一個很空曠的大廳中央,左右各立一人抓著我的肩,我遠視一眼,發現之是一處龐大的醫院掛號、劃價、收費大廳,「一郎」又蠻橫地一邊喊低頭一邊伸手扳壓我的頭。這時又走過來數人,後面跟著一群警察,有攝像的、照相者。領頭的是一位老者,頗儒雅,後來知道他是那所大醫院的院長。「人全部到齊,上去吧。」那位老者說。然後他轉身前行,我被人押著躡其後走。上了二樓,聽到身後有人說應該給他把手銬取了,到了一個掛著「抽血」的牌下,一群人停下,有人從後面開手銬。我被攙到抽血桌前,一位女士在口罩後面發話,說給你抽血化驗。
我終於明白這半夜把人架出囚室原來是要做檢查,這種體檢,我只需跟著走即可。從我看到的現象倒推,這次體檢是至少提前一天即安排好的,由院長帶領指揮,凡要涉及的科室,必有人早已守候在那裡,整座大樓,每上一層,只我一位「就醫」者。顯然,這種安排意圖是在天亮前,對我的體檢必須進行完畢。所有人員都是黑夜趕到,而到場人員則有中共公安系統、中共司法系統及醫務人員三方。
我無需動腦,架至那裡檢查即可,只是在耳鼻喉科檢查時,女醫生突然驚問:「這人聲帶怎麼成這樣啦?」四周靜寂無語,那雙驚異的眼盯著我。「我已經二十個月沒發聲說話了。」我說了一句算是回答了她。心腦檢查結束後,「一郎」又給我套上了黑頭套,雙手又被人擰在背後銬了起來,開始有人架著我下樓。
汽車在路上顛簸的時間很長,我並不知要被弄到甚麼地方去,不知道會不會又回到那個被囚了二十一個月的地下室?終於又聽到警犬「小瘸」那熟悉的嗥叫聲,大致上是因為已到了白天而塞車,故而導致了遠遠長於去的時間。我又被架著回到那個囚室,已到了十二點多鐘,證明了在路途顛簸的時間有四五個小時。站在一旁的哨兵見我回來,就很關心地悄悄詢問我外出幾個小時的遭遇,說很多士兵都關心你的下落。
回到囚室,我想又要開始較長一輪囚禁,亦做好被長期囚禁的心理準備。不料,當天夜裡到了睡覺時間,又有軍官進來通知說,上面來電話,讓你先不要睡覺,說要找你談話。
大約夜裡十點鐘左右,囚室門被打開,進來的還是昨天夜裡來的那三個人,並不說話,那頭目在桌子上鋪開了幾張紙,說了句開始,那「一郎」和「同一郎」過來就把我挾在中間,然後就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全掌壓在一副黑印台上,使我手上各指都蘸上印色,然後強行抓住我的手開始往他們鋪好的紙上摁手印、掌印。我看那些紙都是空白的。
我迄今不知這次「摁」了那麼多手印的意圖。但我也從未因此生出過心理顧慮,任何計謀手段亦無法染黑了我的心,更別說賣身。
2011年12月16日早飯剛過,囚室門又從外面被打開,又是那些人闖了進來,又對我進行了搜身後給戴上了黑頭套,手又被背拷起來,我被架著出了門。沒想到這竟是這次祕密囚禁的終結。這一幕我曾經夢到過,哨兵恰好就是夢裡看到的湖南籍士兵「周老英雄」,但其時我渾然不知要去做甚麼。
我又聽到戶外的人間聲息,又被架到車上,這十年裡,我在祕密警察手裡,無論坐車時間有多長,他們絕不會因為在車裡面而取下我頭上的黑頭套,車上坐著被背銬著是很不好受的,因為無論多累你也不能向後靠,況且更多情況下還有人在你背上壓著,將你身體壓成躬身狀。車在路上走了有兩個多小時,我的內心在這種過程中從不做任何揣忖,不想,是那種狀況裡最符合利益的選擇。
汽車停了,竟然在車上抓下了我的頭套,這可是前所未有的破例。「一郎」幾乎是咬著牙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媽那個X,你丫的一會兒下車要是敢把頭抬起來,一會兒回去有你好果子吃。」我不願在一些非剛性原則的環節上招致激烈衝突,下了車,我沒有抬頭,仍被他們倆架著前行,但我的餘光發現,一下車走了幾步後路兩旁鎂光燈閃爍,並有許多攝像機在攝像,我就抬頭平視,那陣勢足夠壯觀。
進入一棟大樓,樓道兩旁幾十米的距離內足有幾十名穿警服的人員,各自在忙碌著擺弄手中的攝像機、照相機。偶有一兩名穿黑藍西服的男女間雜其中,而胸前綴飾有檢察院或法院系統的徽標。我頗詫異,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推架至一個房間門口,兩位警察上前來替換下了那兩位「惡煞」後將我推進房間。
一進門才發現那是一個小型法庭。我一進門,兩位警察左右攙扶著我至被告席,我明白這是要「開庭」了,幾位「法官」正襟危坐,是清一色的女「法官」,法警打開了我的手銬,「法官」問了一下我的家庭住址,突然說現在「開庭」,全體起立,一起立就念了一份裁定書,說我在緩刑考驗內繼續不思悔改,違反監管規定,經北京市公安局申請,撤銷緩刑判決,改為實刑並予收監。一念完就說現在簽收裁定書,法警立即扭轉我的身把筆遞在我的手中,簽完字即把我押出法庭,前後時間,我印象中絕不超過兩三分鐘。
我當時心裡突起兩個詞,再多一個字亦屬多餘。一個是:賊,這是在那種氛圍裡最恰確形容當局的一個詞,再多一個字亦屬多餘。一個是:水性楊花,這是在那種氛圍裡最恰切形描「法官」們的一個詞。但我終於沒有說出口,因為三位「法官」全是女性。這一點上頗顯於泓源的老到,他心很細,很了解我。
一個「賊」字,任何經歷那個過程的人,除了那些賊的活道具們,你不可能找到比這更貼切的詞形容他們。整個過程,你感覺到這就是個做賊的過程,是由一群賊操辦著這一切的過程。所不同的是這是一群頭頂著國徽的賊,但賊終於是賊,無論他們嘯聚的場面有多麼大觀,頭頂上戴的是甚麼,究竟無法掩隱流在血脈裡的賊的怯懼。
整個過程,表面看是一個法院的庭審過程,但這個過程中唯一不被顧及的就是法律。我在你的黑牢裡,從物理層面上看,我全被掌控在你的手裡,基本的法律程序便是再不耐煩,硬著頭皮也該走上一遍,你怕甚麼?「依法治國」是你們自己死皮賴臉要掛著的人相,一個頗受關注的案件中,連裝都懶得裝一下。
最起碼在法律程序上,你應當提前三天將開庭書面通知我,法庭上你至少當確認一下我的身份,告知我當有的權利義務,最起碼也應該公布一下「法院」及「法官」的名字,詢問一下有無迴避請求,至少也當問一下北京市公安局指斥的違反緩刑規定是不是事實?詢問一下我對裁定的意見。全部過程就是等於給你送達個早已打印好的裁定書。
我算是這個世界上最了解於泓源的人之一,從頭至尾,這個「司法程序」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這是一個法盲,沒有比「法盲」這名詞更適合於他的「執法者」身份。我曾在東北的法學教授王玉琦訴姚志萍案開庭時說過:「中國法盲最集中的人群是我黨的政法幹部隊伍,其中最頂級的法盲群體是我黨寶愛的法學專家教授。」
在我的案件中,中央領導同志周永康是專案組組長,實際上他並不具體管這個案件,他只是定基調、定框架,具體操辦這個案子的實質就是專案組副組長於泓源。他曾在2009年5月份的一次勸說我換一個祕密身份被「強行送出國」的激情演說中,他踱著方步,一副氣昂昂狀,激動中說了許多有氣魄的話,其中「你還沒有最後得罪我,就等於沒有得罪國家,你要是惹惱了我,就等於惹惱了國家」,這氣魄是怎樣的雄大,他可以以專案組組長身份摶捏所有程序。
這裡最令人哀傷的是中國的「法官」們,便是為了個人尊嚴故,亦應當堅持進行表面上應有的程序。令人痛心的是,他們不僅是職業身份上有著毫不掩隱的水性楊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們個人人性方面的水性楊花。職業尊嚴、個人尊嚴一瀉千裡而全然沒有了掙扎的衝動。他們在「法庭」上個個昂首挺肚,這是令我痛心的另一個理由,在這樣一個乾脆的反法治過程中,做出這般姿態,這要有著怎樣客觀的無恥底氣?被一個愚昧而凶殘的祕密警察頭子摶捏在手中,不以為恥辱而竟當作榮耀,這是怎樣的一種人格失守和損毀?
但這一群賊的「法律劇」表演還沒有就此休止,而更令人目瞪口呆的賊行還在後面呢,只是其時,我連目瞪口呆的條件都被剝奪。兩三分鐘的「庭審」出來,我實在憋不住了想要解小手,因為他們是突然來到囚室將我架走的,沒有來得及上廁所,所以在去的路上就憋的難受,幾次請求被呵斥,可這人道能力實在不能被喝退。「法庭」出來我立即又提出上洗手間而被拒絕。
我很快被押上了車,車門一關,他們立即撕下了人相,先是給我戴上了頭套,然後打開手銬將我的手擰向背後銬住,我將裁定書捏得緊緊的,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它的內容,我擔心他們一會兒搶走這份裁定書,我知道於泓源、孫荻是甚麼都幹得出來的,2006年12月24日的判決書就是他們後來在家裡給抄走的。
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故伎重演,突然感到有人搶奪我手裡的裁定書,我頗驚異我那時的手勁,竟然沒有成功。但反抗只剩情緒和本能,便是把這兩樣發揮至極致也決然徒勞無益。我死攥著不放,究竟還是他們的經驗精到,刺啦一聲,有人捏緊我的手銬,驟至的巨痛使我立即鬆了手,他們成功了,那裁定書永遠離我而去。其實,那裁定書對我毫無價值,它跟國家司法審判權力沒有關係,只是中共黑幫的一塊遮羞布耳。即便如此,戲剛演完他們就搶了回去。
汽車終於停了下來,我被押下了車。下車前竟又給抓下了頭套。我被押進一座大樓,樓道裡又是許多穿著制服的攝影攝像人員,二位「惡煞」推著我走進了一個裡面全是警察的房間,這是我由不掛牌地獄轉向掛牌地獄的開始。
終於,我結束了在部隊的祕密囚禁,在中共武警部隊祕密囚禁兩年(其中榆林武警部隊囚禁三個月,北京武警部隊囚禁二十一個月),我稱之為不掛牌地獄。我先後在十年時間裡,累計被囚禁竟達七年時間,在不掛牌地獄的近四年的囚禁中,其中二十四個月就在中共武警部隊的囚禁中。#
附:高智晟新書訂購鏈接
https://www.amazon.com/dp/B01JTGUFU0/ (電子版)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55(精裝)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48(平裝)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版權歸高智晟及其家人。)
(責任編輯:李明心)
2011年12月14日半夜,我在睡夢中被人搖醒,睜眼一看是六中隊中隊隊長,說接上面緊急通知,讓我立即起床接受談話。我起床不一會兒門被打開進來三人,倆人就是我前述文字中提到的「惡煞一郎」和「惡煞同一郎」,另一官員模樣者倒背雙手站在桌子後面,「一郎」提著手銬,「同一郎」一手提著黑頭套,三人進囚室並不說一句話。我被示意站起來,兩位「惡煞」走過來扳轉我的身體,將我壓坐在床上,然後煞有介事地開始拍摸搜查我的身體,有一人蹲下搜查我的下半身和鞋襪,搜查完畢後將黑頭套套在我頭上,然後兩人將我的手擰在背後給銬住。
我被架了起來,感到自己被架出了門,又開始架著上樓梯,我感到自己被架著走出了門外,這是二十一個月來的第一次,一股涼爽通灌身體,第一次在戶外聽到警犬「小瘸」雄厚渾實的磣人的嗷叫聲。我被架上了車坐下,左右各一人壓著我的肩膀,汽車開動,一路無一人說話。汽車行進兩個多小時後停了下來,我被架下了車,然後感到被架進一個門,「媽的低頭」,終於聽見有人說話,後腦勺被人狠勁往前壓了一把,我們站在一個地方。
「還是把頭套給取了吧。」又有人說話了,我的頭套被取下。我發現我站在一個很空曠的大廳中央,左右各立一人抓著我的肩,我遠視一眼,發現之是一處龐大的醫院掛號、劃價、收費大廳,「一郎」又蠻橫地一邊喊低頭一邊伸手扳壓我的頭。這時又走過來數人,後面跟著一群警察,有攝像的、照相者。領頭的是一位老者,頗儒雅,後來知道他是那所大醫院的院長。「人全部到齊,上去吧。」那位老者說。然後他轉身前行,我被人押著躡其後走。上了二樓,聽到身後有人說應該給他把手銬取了,到了一個掛著「抽血」的牌下,一群人停下,有人從後面開手銬。我被攙到抽血桌前,一位女士在口罩後面發話,說給你抽血化驗。
我終於明白這半夜把人架出囚室原來是要做檢查,這種體檢,我只需跟著走即可。從我看到的現象倒推,這次體檢是至少提前一天即安排好的,由院長帶領指揮,凡要涉及的科室,必有人早已守候在那裡,整座大樓,每上一層,只我一位「就醫」者。顯然,這種安排意圖是在天亮前,對我的體檢必須進行完畢。所有人員都是黑夜趕到,而到場人員則有中共公安系統、中共司法系統及醫務人員三方。
我無需動腦,架至那裡檢查即可,只是在耳鼻喉科檢查時,女醫生突然驚問:「這人聲帶怎麼成這樣啦?」四周靜寂無語,那雙驚異的眼盯著我。「我已經二十個月沒發聲說話了。」我說了一句算是回答了她。心腦檢查結束後,「一郎」又給我套上了黑頭套,雙手又被人擰在背後銬了起來,開始有人架著我下樓。
汽車在路上顛簸的時間很長,我並不知要被弄到甚麼地方去,不知道會不會又回到那個被囚了二十一個月的地下室?終於又聽到警犬「小瘸」那熟悉的嗥叫聲,大致上是因為已到了白天而塞車,故而導致了遠遠長於去的時間。我又被架著回到那個囚室,已到了十二點多鐘,證明了在路途顛簸的時間有四五個小時。站在一旁的哨兵見我回來,就很關心地悄悄詢問我外出幾個小時的遭遇,說很多士兵都關心你的下落。
回到囚室,我想又要開始較長一輪囚禁,亦做好被長期囚禁的心理準備。不料,當天夜裡到了睡覺時間,又有軍官進來通知說,上面來電話,讓你先不要睡覺,說要找你談話。
大約夜裡十點鐘左右,囚室門被打開,進來的還是昨天夜裡來的那三個人,並不說話,那頭目在桌子上鋪開了幾張紙,說了句開始,那「一郎」和「同一郎」過來就把我挾在中間,然後就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全掌壓在一副黑印台上,使我手上各指都蘸上印色,然後強行抓住我的手開始往他們鋪好的紙上摁手印、掌印。我看那些紙都是空白的。
我迄今不知這次「摁」了那麼多手印的意圖。但我也從未因此生出過心理顧慮,任何計謀手段亦無法染黑了我的心,更別說賣身。
2011年12月16日早飯剛過,囚室門又從外面被打開,又是那些人闖了進來,又對我進行了搜身後給戴上了黑頭套,手又被背拷起來,我被架著出了門。沒想到這竟是這次祕密囚禁的終結。這一幕我曾經夢到過,哨兵恰好就是夢裡看到的湖南籍士兵「周老英雄」,但其時我渾然不知要去做甚麼。
我又聽到戶外的人間聲息,又被架到車上,這十年裡,我在祕密警察手裡,無論坐車時間有多長,他們絕不會因為在車裡面而取下我頭上的黑頭套,車上坐著被背銬著是很不好受的,因為無論多累你也不能向後靠,況且更多情況下還有人在你背上壓著,將你身體壓成躬身狀。車在路上走了有兩個多小時,我的內心在這種過程中從不做任何揣忖,不想,是那種狀況裡最符合利益的選擇。
汽車停了,竟然在車上抓下了我的頭套,這可是前所未有的破例。「一郎」幾乎是咬著牙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媽那個X,你丫的一會兒下車要是敢把頭抬起來,一會兒回去有你好果子吃。」我不願在一些非剛性原則的環節上招致激烈衝突,下了車,我沒有抬頭,仍被他們倆架著前行,但我的餘光發現,一下車走了幾步後路兩旁鎂光燈閃爍,並有許多攝像機在攝像,我就抬頭平視,那陣勢足夠壯觀。
進入一棟大樓,樓道兩旁幾十米的距離內足有幾十名穿警服的人員,各自在忙碌著擺弄手中的攝像機、照相機。偶有一兩名穿黑藍西服的男女間雜其中,而胸前綴飾有檢察院或法院系統的徽標。我頗詫異,還沒有反應過來就被推架至一個房間門口,兩位警察上前來替換下了那兩位「惡煞」後將我推進房間。
一進門才發現那是一個小型法庭。我一進門,兩位警察左右攙扶著我至被告席,我明白這是要「開庭」了,幾位「法官」正襟危坐,是清一色的女「法官」,法警打開了我的手銬,「法官」問了一下我的家庭住址,突然說現在「開庭」,全體起立,一起立就念了一份裁定書,說我在緩刑考驗內繼續不思悔改,違反監管規定,經北京市公安局申請,撤銷緩刑判決,改為實刑並予收監。一念完就說現在簽收裁定書,法警立即扭轉我的身把筆遞在我的手中,簽完字即把我押出法庭,前後時間,我印象中絕不超過兩三分鐘。
我當時心裡突起兩個詞,再多一個字亦屬多餘。一個是:賊,這是在那種氛圍裡最恰確形容當局的一個詞,再多一個字亦屬多餘。一個是:水性楊花,這是在那種氛圍裡最恰切形描「法官」們的一個詞。但我終於沒有說出口,因為三位「法官」全是女性。這一點上頗顯於泓源的老到,他心很細,很了解我。
一個「賊」字,任何經歷那個過程的人,除了那些賊的活道具們,你不可能找到比這更貼切的詞形容他們。整個過程,你感覺到這就是個做賊的過程,是由一群賊操辦著這一切的過程。所不同的是這是一群頭頂著國徽的賊,但賊終於是賊,無論他們嘯聚的場面有多麼大觀,頭頂上戴的是甚麼,究竟無法掩隱流在血脈裡的賊的怯懼。
整個過程,表面看是一個法院的庭審過程,但這個過程中唯一不被顧及的就是法律。我在你的黑牢裡,從物理層面上看,我全被掌控在你的手裡,基本的法律程序便是再不耐煩,硬著頭皮也該走上一遍,你怕甚麼?「依法治國」是你們自己死皮賴臉要掛著的人相,一個頗受關注的案件中,連裝都懶得裝一下。
最起碼在法律程序上,你應當提前三天將開庭書面通知我,法庭上你至少當確認一下我的身份,告知我當有的權利義務,最起碼也應該公布一下「法院」及「法官」的名字,詢問一下有無迴避請求,至少也當問一下北京市公安局指斥的違反緩刑規定是不是事實?詢問一下我對裁定的意見。全部過程就是等於給你送達個早已打印好的裁定書。
我算是這個世界上最了解於泓源的人之一,從頭至尾,這個「司法程序」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這是一個法盲,沒有比「法盲」這名詞更適合於他的「執法者」身份。我曾在東北的法學教授王玉琦訴姚志萍案開庭時說過:「中國法盲最集中的人群是我黨的政法幹部隊伍,其中最頂級的法盲群體是我黨寶愛的法學專家教授。」
在我的案件中,中央領導同志周永康是專案組組長,實際上他並不具體管這個案件,他只是定基調、定框架,具體操辦這個案子的實質就是專案組副組長於泓源。他曾在2009年5月份的一次勸說我換一個祕密身份被「強行送出國」的激情演說中,他踱著方步,一副氣昂昂狀,激動中說了許多有氣魄的話,其中「你還沒有最後得罪我,就等於沒有得罪國家,你要是惹惱了我,就等於惹惱了國家」,這氣魄是怎樣的雄大,他可以以專案組組長身份摶捏所有程序。
這裡最令人哀傷的是中國的「法官」們,便是為了個人尊嚴故,亦應當堅持進行表面上應有的程序。令人痛心的是,他們不僅是職業身份上有著毫不掩隱的水性楊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們個人人性方面的水性楊花。職業尊嚴、個人尊嚴一瀉千裡而全然沒有了掙扎的衝動。他們在「法庭」上個個昂首挺肚,這是令我痛心的另一個理由,在這樣一個乾脆的反法治過程中,做出這般姿態,這要有著怎樣客觀的無恥底氣?被一個愚昧而凶殘的祕密警察頭子摶捏在手中,不以為恥辱而竟當作榮耀,這是怎樣的一種人格失守和損毀?
但這一群賊的「法律劇」表演還沒有就此休止,而更令人目瞪口呆的賊行還在後面呢,只是其時,我連目瞪口呆的條件都被剝奪。兩三分鐘的「庭審」出來,我實在憋不住了想要解小手,因為他們是突然來到囚室將我架走的,沒有來得及上廁所,所以在去的路上就憋的難受,幾次請求被呵斥,可這人道能力實在不能被喝退。「法庭」出來我立即又提出上洗手間而被拒絕。
我很快被押上了車,車門一關,他們立即撕下了人相,先是給我戴上了頭套,然後打開手銬將我的手擰向背後銬住,我將裁定書捏得緊緊的,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它的內容,我擔心他們一會兒搶走這份裁定書,我知道於泓源、孫荻是甚麼都幹得出來的,2006年12月24日的判決書就是他們後來在家裡給抄走的。
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故伎重演,突然感到有人搶奪我手裡的裁定書,我頗驚異我那時的手勁,竟然沒有成功。但反抗只剩情緒和本能,便是把這兩樣發揮至極致也決然徒勞無益。我死攥著不放,究竟還是他們的經驗精到,刺啦一聲,有人捏緊我的手銬,驟至的巨痛使我立即鬆了手,他們成功了,那裁定書永遠離我而去。其實,那裁定書對我毫無價值,它跟國家司法審判權力沒有關係,只是中共黑幫的一塊遮羞布耳。即便如此,戲剛演完他們就搶了回去。
汽車終於停了下來,我被押下了車。下車前竟又給抓下了頭套。我被押進一座大樓,樓道裡又是許多穿著制服的攝影攝像人員,二位「惡煞」推著我走進了一個裡面全是警察的房間,這是我由不掛牌地獄轉向掛牌地獄的開始。
終於,我結束了在部隊的祕密囚禁,在中共武警部隊祕密囚禁兩年(其中榆林武警部隊囚禁三個月,北京武警部隊囚禁二十一個月),我稱之為不掛牌地獄。我先後在十年時間裡,累計被囚禁竟達七年時間,在不掛牌地獄的近四年的囚禁中,其中二十四個月就在中共武警部隊的囚禁中。#
附:高智晟新書訂購鏈接
https://www.amazon.com/dp/B01JTGUFU0/ (電子版)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55(精裝)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48(平裝)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版權歸高智晟及其家人。)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