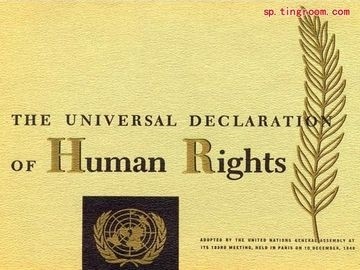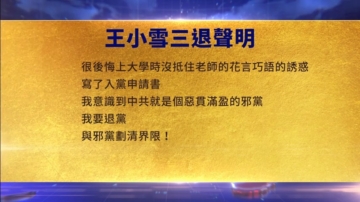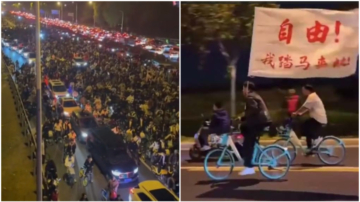過去十多年,我幾乎每天都在堅持寫時評博文,但現在,無論是博客還是公眾號,時評博文越來越難寫,也越來越不好發出來了。一個月前,只是在公眾號上發了幾張天堂如此美麗的夜景照片,又被禁言一個月,實際上離上次解禁才10天,公眾號又一次被封,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這個公眾號被永久封掉,現在的言論環境讓每一個寫作者處於焦灼無奈之中。
許多讀者常常問我,為什麼公眾號上的文章不能及時更新?我只能如實回答:寫出來的文章常常發不出來,每一次發文對我來說都是一次折磨,無論怎麼修改編排,總是達不到幕後審查者的標準,毫無疑問,自由言說的空間己經越來越少,不僅社會問題現實問題不能碰觸,連國際問題也不能有自己的觀點,信息時代的封禁與隔絕只能讓奴才犬儒盛行。
有個讀者給我留言說:雖然我們不曾相識,也不了解、但是我始終關注著您的文章,雖然您的文章經常被封,但您的文章我都曾仔細閱讀過。分享著您的快樂與憂傷,但更多的是憂傷和焦慮!從您的字裡行間,透露出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深深的熱愛,正可謂愛之深恨之切!能夠認識您,真可謂三生有幸!
這是對我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對我的鞭策和警醒!實際上,做為一個社會批評者,並不是在抹黑這個社會,而是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改變,變得更公正,變得更光明,變得更美好!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漠不關心,那就真是一個民族的恥辱一個時代的悲哀。
梁發芾先生在《晚清百姓為什麼不那麼愛國》的文章中就敘述過這樣的場景:當英軍登陸後,中國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糧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艦隊突破虎門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時,江兩岸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他們以冷漠的、十分平靜的神情觀看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一場表演,當掛青龍黃旗的官船被擊沉清軍紛紛跳水,兩岸居民竟然發出像看馬戲看到精彩處的喝彩聲。
巴金生前一直呼籲國人說真話,李悅在《一個時代的終結》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懺悔的晚年也是說真話的晚年。李悅認為,有人發現,中國的大多數民眾在一個政治運動到來的時候,會選擇集體下跪說:我懺悔!但在那個運動結束之後,又集體昂首站起來說:我控訴!
但巴金卻在文革十年動亂結束後,仍然跪著說:「我懺悔!」「我懺悔!」這才是巴金一生中最閃光的時刻,也是巴金最值得後人紀念的可貴之處。巴金曾說:「一個美國人敢站出來說真話,因為他知道身後會有千萬個美國人用行動支持他。一個中國人不敢站出來說真話,因為他知道周圍的同胞會默默地與他保持距離。」
美國知名學者喬姆斯基曾經來中國講學,曾經目睹過這樣的一幕:我在北大校門口看到三個警察追著一位60多歲的上訪老婦用警棍暴打。老婦被打得大吐鮮血、大喊救命!當時在場的上千名學生、教授,竟然沒人理睬!看到這場景,我上前阻止,警察指我罵道:洋鬼子,敢管閑事,連你一起打!那一刻我後悔了,我竟然來這樣一個麻木變態的國家做訪問學者。
巴金和喬姆斯基的話還隱含著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一個美國人敢於站出來主持公道敢說真話,是因為沒有恐懼。而一個中國人不敢站出來主持公道不敢說真話,常常是因為恐懼,免於恐懼的自由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匱乏也是最珍貴的訴求,一個文明社會,要仰賴免於恐懼的自由,才能維持互信,維繫正常的政治社會生活秩序。
1941年,羅斯福在給美國國會的咨文中提出,美國人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們都應該有權享有言論和表達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今天,在戰爭漸行漸遠之後,免於恐懼的自由,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也寫進了聯合國人權宣言。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應該讓自己的民眾遠離恐懼的威脅,無論是何種恐懼,同時應建立一種鼓勵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實現自己與生俱來的潛能的秩序。
朱學東先生在其舊文中坦言:即便面對恐懼,我們也當如昂山素季所言:「但也許,我們只是破碎的玻璃,不堪一握。細小而銳利的玻璃碎片,閃爍著捍衛自己抗拒壓榨的力量,是勇氣之光的生動象徵。而這樣的勇氣,正是那些志在擺脫壓迫桎梏的人們的精魂所在。」
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是恩賜,也不會從天而降,而是需要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攜力同行才能真正擁有。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許多讀者常常問我,為什麼公眾號上的文章不能及時更新?我只能如實回答:寫出來的文章常常發不出來,每一次發文對我來說都是一次折磨,無論怎麼修改編排,總是達不到幕後審查者的標準,毫無疑問,自由言說的空間己經越來越少,不僅社會問題現實問題不能碰觸,連國際問題也不能有自己的觀點,信息時代的封禁與隔絕只能讓奴才犬儒盛行。
有個讀者給我留言說:雖然我們不曾相識,也不了解、但是我始終關注著您的文章,雖然您的文章經常被封,但您的文章我都曾仔細閱讀過。分享著您的快樂與憂傷,但更多的是憂傷和焦慮!從您的字裡行間,透露出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深深的熱愛,正可謂愛之深恨之切!能夠認識您,真可謂三生有幸!
這是對我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對我的鞭策和警醒!實際上,做為一個社會批評者,並不是在抹黑這個社會,而是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改變,變得更公正,變得更光明,變得更美好!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漠不關心,那就真是一個民族的恥辱一個時代的悲哀。
梁發芾先生在《晚清百姓為什麼不那麼愛國》的文章中就敘述過這樣的場景:當英軍登陸後,中國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糧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艦隊突破虎門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時,江兩岸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他們以冷漠的、十分平靜的神情觀看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一場表演,當掛青龍黃旗的官船被擊沉清軍紛紛跳水,兩岸居民竟然發出像看馬戲看到精彩處的喝彩聲。
巴金生前一直呼籲國人說真話,李悅在《一個時代的終結》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懺悔的晚年也是說真話的晚年。李悅認為,有人發現,中國的大多數民眾在一個政治運動到來的時候,會選擇集體下跪說:我懺悔!但在那個運動結束之後,又集體昂首站起來說:我控訴!
但巴金卻在文革十年動亂結束後,仍然跪著說:「我懺悔!」「我懺悔!」這才是巴金一生中最閃光的時刻,也是巴金最值得後人紀念的可貴之處。巴金曾說:「一個美國人敢站出來說真話,因為他知道身後會有千萬個美國人用行動支持他。一個中國人不敢站出來說真話,因為他知道周圍的同胞會默默地與他保持距離。」
美國知名學者喬姆斯基曾經來中國講學,曾經目睹過這樣的一幕:我在北大校門口看到三個警察追著一位60多歲的上訪老婦用警棍暴打。老婦被打得大吐鮮血、大喊救命!當時在場的上千名學生、教授,竟然沒人理睬!看到這場景,我上前阻止,警察指我罵道:洋鬼子,敢管閑事,連你一起打!那一刻我後悔了,我竟然來這樣一個麻木變態的國家做訪問學者。
巴金和喬姆斯基的話還隱含著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一個美國人敢於站出來主持公道敢說真話,是因為沒有恐懼。而一個中國人不敢站出來主持公道不敢說真話,常常是因為恐懼,免於恐懼的自由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匱乏也是最珍貴的訴求,一個文明社會,要仰賴免於恐懼的自由,才能維持互信,維繫正常的政治社會生活秩序。
1941年,羅斯福在給美國國會的咨文中提出,美國人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們都應該有權享有言論和表達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今天,在戰爭漸行漸遠之後,免於恐懼的自由,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也寫進了聯合國人權宣言。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應該讓自己的民眾遠離恐懼的威脅,無論是何種恐懼,同時應建立一種鼓勵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實現自己與生俱來的潛能的秩序。
朱學東先生在其舊文中坦言:即便面對恐懼,我們也當如昂山素季所言:「但也許,我們只是破碎的玻璃,不堪一握。細小而銳利的玻璃碎片,閃爍著捍衛自己抗拒壓榨的力量,是勇氣之光的生動象徵。而這樣的勇氣,正是那些志在擺脫壓迫桎梏的人們的精魂所在。」
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是恩賜,也不會從天而降,而是需要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攜力同行才能真正擁有。
──轉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