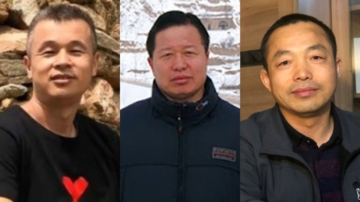在任何一個國家,觀察他們的人權狀況,評價這個國家、社會中人道價值的高度乃至人倫道德的現狀,你最好去瞭解他們的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普遍處境。我絕沒有任何誇張的衝動,在中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道處境絕不在地獄以上。物理領域的黑暗是有限的,而人性的黑暗則是一個漫無邊際、吞噬一切的黑洞,這是幾千年來中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監獄罪犯們永遠面對的,1949年後只是進入了它的最黑暗時期。
中國歷史上一直的是刑民不分,司法、行政合體,而更其可怕的是數千年竟沒有生出過「刑事訴訟」這麼個人間文明概念。偵、控、審合為一體,數千年的習慣就是,這些權力永遠操控在一人之手,成就了人類司法史上最為野蠻、最為恐怖的惡記錄,而從無改變衝動。
共產黨搶得政權後,像其它所有領域一樣,它在所有環節上會認認真真摹仿人類文明共有的形式。與公、檢、法對應的偵、控、審,主導刑事訴訟的三大形式環節它一個不少。如果說封建專制時代,悉由地方行政長官一手在明處操控司法的話,共產黨卻是躲在暗處的黑手。表面上,凡文明制度下的一切形式要件它一樣不缺,所謂金玉其表。凡前臺施實形式過程的所謂偵、控、審人員,他們就是傳統藝人手裡的提線木偶,他們背後提線操縱的就是中共的政法委。由於法院是最後的決論環節,所以它乾脆在法院設立了一種日常的「提線操作」制度叫「審判委員會」制度(檢察院設有黨委控制的「檢委會」),其成員由黨的職務人員組成,他們並不具體審案,而案件的最終判決結論卻必須由他們作出。真正具體審案的所謂「審判員」卻只能在臺前作煞有介事的欺騙性表演。
永忘不了律師資格考前輔導一位講課老師在課堂上提到的一個事例。講到燒死三百多個孩子的克拉瑪依大火案開庭審理時,法庭設在一樓大庭,新疆政法委領導就坐陣二樓指揮,審判長中途數次休庭上樓匯報、接受具體指令。他說:「你覺得這就是人家的家事,辯護人就是個擺設。」
以我的案子為例,一切基調都由祕密警察頭子於泓源定調,臺前所有表演都得以定下的基調為劇本進行。從效益及實現目的的成本角度論,共匪體制下的司法運作情形較封建專制時代更其的反動外加荒謬。
刑事訴訟的功能及普世價值便是為了保衛人的權利、安全及社會秩序,但很多情形下,中共恐怖組織主導的「刑事訴訟」卻是公開地走了向反面。它就是一個冷酷吞噬人權的黑洞,而它本身即成了一個恐怖的犯罪過程。在中國,一個個體人的命運常會被不確定的環節所左右,而這種左右別人命運的力量則永遠是確定的,那就是黑幫權力。大部分情形下它們會以臺前道具的面孔「決定」行動,但一旦遇到法盲、流氓外加絕不怕羞恥的「領導同志」,表演便不會循著它們尋常的欺騙套路進行。諸如,以常規表演套路,對被告人的批捕及偵控得由「法定」的部門決定,至少在紙面上還是會「依法」雲雲。
但我曾在海口市中級法院主審的一起貪腐案件中,在檢察院階段閱卷時竟看到一份令人啼笑不適的《起訴意見書》,該起訴書一改以往依據什麼什麼法律的表演模式,起首直接為:根據吳長猿副省長的指示對被告人進行訴訟。但在後來的中級法院閱卷時則發現又歸循了傳統表演套路,戴上了「法律」的臉譜。
楊子立先生被構陷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卷中,竟然出現「重要思想」家、曾「在華萊氏面前談笑風生」的江澤民的要求嚴懲的親筆批示。在這種批示下,一切過程均得符合貫徹「嚴懲」的批示精神進行。在任何現代文明國家,案卷裡出現「國家領導」的批示,這是會使整個政壇巨震的大醜聞。但這卻是一個有著特色的國度,上下一鍋糊粥的法盲們,倒置人間的美醜、善惡、榮恥正是他們所以立足的根本。楊子案申訴階段,我向外界公開了這一不加遮掩的反文明醜聞,邪惡當局安之若泰。但這種上下一桶漿糊的昏亂運作,給無數無聲的人民造成了人生的巨大不幸,有的甚至是人生徹底的毀滅。我短暫的訴訟律師生涯,卻經歷過多起赤裸裸的冤案,鑄就了我職業生涯裡揮之不去的痛。
烏魯木齊騰威市場被盜案,就是一起由沙區公安局刑警大隊一個叫孟林富者主辦的一起大冤案。我個人與孟只見過兩面,未有過一次語言接觸,無有個人芥蒂,但他卻是我個人記憶生涯裡面目最為猙獰的個體之一。孟只是利用了制度的惡,或竟是不自覺地被導入了制度的惡。
中共刑事訴訟程序與文明司法制度下以審判為主的價值運作狀態不同,它們是完全以偵查價值為主。由偵查程序提挈著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局面。就是實踐中形容它們是公安備料,檢察院做飯,法院吃下模式。偵查階段最恐怖的制度設計是由公安機關先抓人,然後在七天內提請檢察院批准逮捕,這七日內公安就得「拿出」其自行決定抓人合法的證據,而人就在他們手裡、不受任何監督,酷刑成了普遍的「取證」方式——直接、方便、快捷而無任何風險。而檢察批准逮捕後,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就剩下一種結局——無論如何得「有罪」,否則,公安、檢方就算辦了錯案。名義上,檢察院對公安辦案過程有法律監督權,但批准逮捕後兩家在同一案件上卻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共同體,那就是被抓的人必須有罪,他們兩家才能正確,冷酷的手段就成了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保證。對於冤獄者而言,這個過程生不如死,沒有任何人會聽他的申辯,而申辯又定會被認為是「不老實交待罪行」。冷血的酷刑,最終必能使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如實交待犯罪事實」。
烏魯木齊騰威市場原屬烏市郵政系統的臨街樓產,租與別人而單位收取租金。市場主要銷售高檔音響及其它電器。案發夜被盜價值十餘萬元的電器。我的委託人孫利軍,與另外我記不起姓名者三個年輕人當晚在郵政局門衛處值夜,市場是在二樓,郵政單位值班室是一樓,事發當夜,孫他們值班室門口的一副梯子成了盜竊者的工具。因當天夜裡有雪,梯子移動痕跡明顯,案發後沙區分局刑警中隊孟林富主辦此案。
孟於第二天勘驗完現場後認為當晚郵政局夜值的孫利軍等三人有盜竊嫌疑,便抓捕了孫等三人,接下來,孟所有的一切「工作」就是使他們三個人承認盜竊。三個年輕人真所謂禍從天降,地獄般的噩運從被抓的當天夜裡開始。孟當天夜裡對孫利軍實施了駭人聽聞的酷刑,就是反覆將人懸空吊起來毆打、使勁捏孫的睪丸,每至生不如死時,孫大叫承認「盜竊」,一放下來就覺得太冤不肯配合「筆錄」,經多次野蠻的過程後,孫「承認」了盜竊,並全按孟的口述,作出了與現場勘驗情形完全「吻合」的「犯罪交待」。其他兩人亦經歷了同樣生不如死的過程後也被逼「交待了犯罪事實」。孟因這個大案的「迅速破獲」而立了功受獎,而孫等三個年輕人則需在監獄裡度過每人十幾年的囚禁。
中共公安在公、檢、法三個環節裡是最強勢的,有時就是以赤裸裸的威脅來主導整個訴訟程序向著他們已設計好的方向進行。有一個絕對規律是,凡公安偵查人員心知肚明的冤案,他們百分之百地會來「旁聽」案件審理,就在現場盯著檢方、法院順著他們的意思進行。該案「庭審」時,孟赫然在「法庭」就坐。警察的濫權只是恐怖的一部分,更其恐怖的是沒有獨立的審判。
十幾年過去了,判決書定罪理由中的一句話使我永不能忘,即:「被告方也沒有證據證明自己沒有犯罪。」這裡公然地昭示了一切反動司法制度下的一個共有的邪惡規律——即雖然控方證據不能證明被告有罪,而被告也無法證明自己無罪,因此你就有罪。這種野蠻的定罪價值觀使人毛骨悚然。在這個案件裡,案發半年後,孟仍不停地補充「新的證據」,法院需要什麼證據就補充什麼!
孫利軍們被迫「認罪」前被實施酷刑的場所對我們辯方,包括三名被告人本人都是個謎。這個案件「審理」中,對於「疑罪從無原則」、「法非證據排除原則」、「不得自證有罪原則」都是公然反動的。我在起草憲法時反覆思考過這個案件中我們需要吸取的記憶及思想,諸如我憲法裡特別提到,對拘禁者的監禁,只能在法定的場所或設施中進行。這個案件中,我們看到的是無底線的私念驅使下的人性的可怖,而更可怕的是可被這種壞人性恣肆利用,並總能予這種壞人性以實質性褒獎的邪惡制度。
我在執業中發現,中共公安偵查制度中竟存在一種被稱為「特勤」的機制。這種機制的實際運行,是被我在不同時間裡、在不同的法院閱卷時親眼看到過三回的,證明了它的普遍存在。就是發展一種隱形的偵查人員,是刑事領域設置的不為外人所知的祕密警察。他們甚至原本即是犯罪人員被僱用,有時就是赤裸裸地去培植、蠱惑犯罪,更其邪惡的是有時直接用毒品作道具製造犯罪。「特勤」就生活在普通社會人中間,伺機製造「大案」出來,以換取他們所在單位的立功、受獎或個人士途上的好處。但我印象中這類過程均發生在緝毒案中。
1997年,我被烏魯木齊市中級法院指定為一起販賣毒品案的被告人張衣不拉(東鄉族)辯護。閱卷中我吃驚地發現卷中夾了些「機密」的材料。這起案件從頭至尾就是「我公安特勤人員」經過精心籌劃而導演的一起案件。
被告人張子善(張衣不拉的胞哥)多年不見的戰友突然來找他,「對人熱心,花錢又大方」。這「特勤」在一年的時間裡於張子善營造了類親兄弟般的關係,張子善對其總是大手大腳花錢很羨慕而又好奇,開始問及則必「不肯講」,追問的多了則「很不情願」地告訴了張,且發誓賭咒不允許外傳。原來這老戰友是在販賣毒品,且告訴張「錢來的很快,非常的保險」,還大方地給張子善買了一輛農用車,然後便數月不見,後來又出現在張子善家,說是又去甘肅東鄉縣「做了一趟生藝(指販毒),又賺了不少」,並說只要在甘肅東鄉縣有熟人便能弄到貨(毒品),要能弄回來的話是一本萬利,有多少他要多少。而張家兄弟老家正是甘肅東鄉縣(張是當兵復原後留在新疆的)。記憶中好像還提供了八千元的資金,張家兄弟的貪婪吞噬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張衣不拉的生命。
在這個案件中,我與審判人員進行過交涉,但無濟於事。這「特勤人員」顯然構成了犯罪,不能因著他有「我方特勤人員」的身份便可以逍遙法外。結果審判人說我腦子有病,說這是「我公安緝毒戰線上常用的一種手段」。
在這個案件中,我們再次看到貪慾人性的黑洞。「我方特勤」與其背後的操縱力量,他們精心並耐心地籌劃、製造成了這樣一起「特大販毒案」。他們由於「經過一年多艱苦的偵查工作」破獲了這起「特大販毒案」而立了功、領了些獎金,可本案三被告(由於張家兄弟無現錢,他們把東鄉縣毒品賣主給帶到新疆來,欲將八百克毒品賣給「特勤」時被抓)除了張子善被判死緩外,其餘兩名被告馬尤都斯(貨主)和張衣不拉都已被槍決。
惡制度本身就是犯罪的一部分,他們利用了制度之惡,自己製造「大案要案」而「迅速偵破」,而法院成了肯定他們犯罪成績的制度化工具。所以對公民權利保護的思索,於刑事訴訟這方面我考慮的也最多。每個權利或人身保護的具體條款,都會與過去律師工作中的一些痛苦記憶相聯繫。
如不得在未成年子女面前暴力抓捕他們的父母,便與一個具體案件的野蠻暴行記憶有關。被告人嚴正在自己的家裡被暴力抓捕過程成了其妻權女士尤其是未成年孩子記憶中揮之不去的惡夢。她說幾個月後自己還常在夢中被驚醒——因為孩子自那次受到驚嚇後經常半夜驚叫、哭嚎。這野蠻制度的罪惡,是我們成年人對孩子們的心靈安全的一種虧欠。在非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得入室拘禁、不得夜晚入室執行法院生效的判決、不得在夜裡進行搜查諸條款形成,都與我在1998年嚴正案中的記憶有關,與孩子受驚嚇後的痛苦感情及記憶有著聯繫。
諸如關於禁止在法定的場所及設施中拘禁的問題,我自己親身經歷的野蠻囚禁過程中,近八年的囚禁,在「法定」場所關押累計三年,其餘被非法囚禁在共產黨私設的牢獄內的時間竟有近五年。國家,成了黑幫犯罪集團任意壓迫人民的工具。
在對公民權利確定的起草過程中,另一個於思想感情裡最醒目的權利保障內容便是,公民在公共場所被公職人員任意盤查、被要求出示身份證件,對公民人身、隨身物品的任意搜查問題,這在中共製下的中國是稀鬆平常的日常現象。事實上,中共從打家劫捨開始便歷來如此,凡有它立足的地方,便會對控制區的人民實行這種野蠻的侮辱性的行徑。這是對公民或直接是對人的一項基本自由權利的野蠻侵犯,是對人的人格尊嚴恣意踐踏的活標本。
美國憲政史上也發生過公共場所對公民隨身物品搜查的案例,卻引發了大規模的辯論,終於還是對人權及憲法價值守護佔據了上風,凡未經公民同意,公共場所的任意搜查,即便發現了諸如毒品等犯罪證據,亦不得對該公民進行指控,以保衛人權、保衛憲法原則不可撼動的神聖。社會、國家可以放縱明顯的犯罪,但不可以為了一個具體的案件,而撼動國家法治原則的底線。這是未來中國人權及公民權利保護實踐所必須持守的價值原則。
附:高智晟《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案全文下載。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中國歷史上一直的是刑民不分,司法、行政合體,而更其可怕的是數千年竟沒有生出過「刑事訴訟」這麼個人間文明概念。偵、控、審合為一體,數千年的習慣就是,這些權力永遠操控在一人之手,成就了人類司法史上最為野蠻、最為恐怖的惡記錄,而從無改變衝動。
共產黨搶得政權後,像其它所有領域一樣,它在所有環節上會認認真真摹仿人類文明共有的形式。與公、檢、法對應的偵、控、審,主導刑事訴訟的三大形式環節它一個不少。如果說封建專制時代,悉由地方行政長官一手在明處操控司法的話,共產黨卻是躲在暗處的黑手。表面上,凡文明制度下的一切形式要件它一樣不缺,所謂金玉其表。凡前臺施實形式過程的所謂偵、控、審人員,他們就是傳統藝人手裡的提線木偶,他們背後提線操縱的就是中共的政法委。由於法院是最後的決論環節,所以它乾脆在法院設立了一種日常的「提線操作」制度叫「審判委員會」制度(檢察院設有黨委控制的「檢委會」),其成員由黨的職務人員組成,他們並不具體審案,而案件的最終判決結論卻必須由他們作出。真正具體審案的所謂「審判員」卻只能在臺前作煞有介事的欺騙性表演。
永忘不了律師資格考前輔導一位講課老師在課堂上提到的一個事例。講到燒死三百多個孩子的克拉瑪依大火案開庭審理時,法庭設在一樓大庭,新疆政法委領導就坐陣二樓指揮,審判長中途數次休庭上樓匯報、接受具體指令。他說:「你覺得這就是人家的家事,辯護人就是個擺設。」
以我的案子為例,一切基調都由祕密警察頭子於泓源定調,臺前所有表演都得以定下的基調為劇本進行。從效益及實現目的的成本角度論,共匪體制下的司法運作情形較封建專制時代更其的反動外加荒謬。
刑事訴訟的功能及普世價值便是為了保衛人的權利、安全及社會秩序,但很多情形下,中共恐怖組織主導的「刑事訴訟」卻是公開地走了向反面。它就是一個冷酷吞噬人權的黑洞,而它本身即成了一個恐怖的犯罪過程。在中國,一個個體人的命運常會被不確定的環節所左右,而這種左右別人命運的力量則永遠是確定的,那就是黑幫權力。大部分情形下它們會以臺前道具的面孔「決定」行動,但一旦遇到法盲、流氓外加絕不怕羞恥的「領導同志」,表演便不會循著它們尋常的欺騙套路進行。諸如,以常規表演套路,對被告人的批捕及偵控得由「法定」的部門決定,至少在紙面上還是會「依法」雲雲。
但我曾在海口市中級法院主審的一起貪腐案件中,在檢察院階段閱卷時竟看到一份令人啼笑不適的《起訴意見書》,該起訴書一改以往依據什麼什麼法律的表演模式,起首直接為:根據吳長猿副省長的指示對被告人進行訴訟。但在後來的中級法院閱卷時則發現又歸循了傳統表演套路,戴上了「法律」的臉譜。
楊子立先生被構陷顛覆國家政權罪案卷中,竟然出現「重要思想」家、曾「在華萊氏面前談笑風生」的江澤民的要求嚴懲的親筆批示。在這種批示下,一切過程均得符合貫徹「嚴懲」的批示精神進行。在任何現代文明國家,案卷裡出現「國家領導」的批示,這是會使整個政壇巨震的大醜聞。但這卻是一個有著特色的國度,上下一鍋糊粥的法盲們,倒置人間的美醜、善惡、榮恥正是他們所以立足的根本。楊子案申訴階段,我向外界公開了這一不加遮掩的反文明醜聞,邪惡當局安之若泰。但這種上下一桶漿糊的昏亂運作,給無數無聲的人民造成了人生的巨大不幸,有的甚至是人生徹底的毀滅。我短暫的訴訟律師生涯,卻經歷過多起赤裸裸的冤案,鑄就了我職業生涯裡揮之不去的痛。
烏魯木齊騰威市場被盜案,就是一起由沙區公安局刑警大隊一個叫孟林富者主辦的一起大冤案。我個人與孟只見過兩面,未有過一次語言接觸,無有個人芥蒂,但他卻是我個人記憶生涯裡面目最為猙獰的個體之一。孟只是利用了制度的惡,或竟是不自覺地被導入了制度的惡。
中共刑事訴訟程序與文明司法制度下以審判為主的價值運作狀態不同,它們是完全以偵查價值為主。由偵查程序提挈著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局面。就是實踐中形容它們是公安備料,檢察院做飯,法院吃下模式。偵查階段最恐怖的制度設計是由公安機關先抓人,然後在七天內提請檢察院批准逮捕,這七日內公安就得「拿出」其自行決定抓人合法的證據,而人就在他們手裡、不受任何監督,酷刑成了普遍的「取證」方式——直接、方便、快捷而無任何風險。而檢察批准逮捕後,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就剩下一種結局——無論如何得「有罪」,否則,公安、檢方就算辦了錯案。名義上,檢察院對公安辦案過程有法律監督權,但批准逮捕後兩家在同一案件上卻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共同體,那就是被抓的人必須有罪,他們兩家才能正確,冷酷的手段就成了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保證。對於冤獄者而言,這個過程生不如死,沒有任何人會聽他的申辯,而申辯又定會被認為是「不老實交待罪行」。冷血的酷刑,最終必能使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如實交待犯罪事實」。
烏魯木齊騰威市場原屬烏市郵政系統的臨街樓產,租與別人而單位收取租金。市場主要銷售高檔音響及其它電器。案發夜被盜價值十餘萬元的電器。我的委託人孫利軍,與另外我記不起姓名者三個年輕人當晚在郵政局門衛處值夜,市場是在二樓,郵政單位值班室是一樓,事發當夜,孫他們值班室門口的一副梯子成了盜竊者的工具。因當天夜裡有雪,梯子移動痕跡明顯,案發後沙區分局刑警中隊孟林富主辦此案。
孟於第二天勘驗完現場後認為當晚郵政局夜值的孫利軍等三人有盜竊嫌疑,便抓捕了孫等三人,接下來,孟所有的一切「工作」就是使他們三個人承認盜竊。三個年輕人真所謂禍從天降,地獄般的噩運從被抓的當天夜裡開始。孟當天夜裡對孫利軍實施了駭人聽聞的酷刑,就是反覆將人懸空吊起來毆打、使勁捏孫的睪丸,每至生不如死時,孫大叫承認「盜竊」,一放下來就覺得太冤不肯配合「筆錄」,經多次野蠻的過程後,孫「承認」了盜竊,並全按孟的口述,作出了與現場勘驗情形完全「吻合」的「犯罪交待」。其他兩人亦經歷了同樣生不如死的過程後也被逼「交待了犯罪事實」。孟因這個大案的「迅速破獲」而立了功受獎,而孫等三個年輕人則需在監獄裡度過每人十幾年的囚禁。
中共公安在公、檢、法三個環節裡是最強勢的,有時就是以赤裸裸的威脅來主導整個訴訟程序向著他們已設計好的方向進行。有一個絕對規律是,凡公安偵查人員心知肚明的冤案,他們百分之百地會來「旁聽」案件審理,就在現場盯著檢方、法院順著他們的意思進行。該案「庭審」時,孟赫然在「法庭」就坐。警察的濫權只是恐怖的一部分,更其恐怖的是沒有獨立的審判。
十幾年過去了,判決書定罪理由中的一句話使我永不能忘,即:「被告方也沒有證據證明自己沒有犯罪。」這裡公然地昭示了一切反動司法制度下的一個共有的邪惡規律——即雖然控方證據不能證明被告有罪,而被告也無法證明自己無罪,因此你就有罪。這種野蠻的定罪價值觀使人毛骨悚然。在這個案件裡,案發半年後,孟仍不停地補充「新的證據」,法院需要什麼證據就補充什麼!
孫利軍們被迫「認罪」前被實施酷刑的場所對我們辯方,包括三名被告人本人都是個謎。這個案件「審理」中,對於「疑罪從無原則」、「法非證據排除原則」、「不得自證有罪原則」都是公然反動的。我在起草憲法時反覆思考過這個案件中我們需要吸取的記憶及思想,諸如我憲法裡特別提到,對拘禁者的監禁,只能在法定的場所或設施中進行。這個案件中,我們看到的是無底線的私念驅使下的人性的可怖,而更可怕的是可被這種壞人性恣肆利用,並總能予這種壞人性以實質性褒獎的邪惡制度。
我在執業中發現,中共公安偵查制度中竟存在一種被稱為「特勤」的機制。這種機制的實際運行,是被我在不同時間裡、在不同的法院閱卷時親眼看到過三回的,證明了它的普遍存在。就是發展一種隱形的偵查人員,是刑事領域設置的不為外人所知的祕密警察。他們甚至原本即是犯罪人員被僱用,有時就是赤裸裸地去培植、蠱惑犯罪,更其邪惡的是有時直接用毒品作道具製造犯罪。「特勤」就生活在普通社會人中間,伺機製造「大案」出來,以換取他們所在單位的立功、受獎或個人士途上的好處。但我印象中這類過程均發生在緝毒案中。
1997年,我被烏魯木齊市中級法院指定為一起販賣毒品案的被告人張衣不拉(東鄉族)辯護。閱卷中我吃驚地發現卷中夾了些「機密」的材料。這起案件從頭至尾就是「我公安特勤人員」經過精心籌劃而導演的一起案件。
被告人張子善(張衣不拉的胞哥)多年不見的戰友突然來找他,「對人熱心,花錢又大方」。這「特勤」在一年的時間裡於張子善營造了類親兄弟般的關係,張子善對其總是大手大腳花錢很羨慕而又好奇,開始問及則必「不肯講」,追問的多了則「很不情願」地告訴了張,且發誓賭咒不允許外傳。原來這老戰友是在販賣毒品,且告訴張「錢來的很快,非常的保險」,還大方地給張子善買了一輛農用車,然後便數月不見,後來又出現在張子善家,說是又去甘肅東鄉縣「做了一趟生藝(指販毒),又賺了不少」,並說只要在甘肅東鄉縣有熟人便能弄到貨(毒品),要能弄回來的話是一本萬利,有多少他要多少。而張家兄弟老家正是甘肅東鄉縣(張是當兵復原後留在新疆的)。記憶中好像還提供了八千元的資金,張家兄弟的貪婪吞噬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張衣不拉的生命。
在這個案件中,我與審判人員進行過交涉,但無濟於事。這「特勤人員」顯然構成了犯罪,不能因著他有「我方特勤人員」的身份便可以逍遙法外。結果審判人說我腦子有病,說這是「我公安緝毒戰線上常用的一種手段」。
在這個案件中,我們再次看到貪慾人性的黑洞。「我方特勤」與其背後的操縱力量,他們精心並耐心地籌劃、製造成了這樣一起「特大販毒案」。他們由於「經過一年多艱苦的偵查工作」破獲了這起「特大販毒案」而立了功、領了些獎金,可本案三被告(由於張家兄弟無現錢,他們把東鄉縣毒品賣主給帶到新疆來,欲將八百克毒品賣給「特勤」時被抓)除了張子善被判死緩外,其餘兩名被告馬尤都斯(貨主)和張衣不拉都已被槍決。
惡制度本身就是犯罪的一部分,他們利用了制度之惡,自己製造「大案要案」而「迅速偵破」,而法院成了肯定他們犯罪成績的制度化工具。所以對公民權利保護的思索,於刑事訴訟這方面我考慮的也最多。每個權利或人身保護的具體條款,都會與過去律師工作中的一些痛苦記憶相聯繫。
如不得在未成年子女面前暴力抓捕他們的父母,便與一個具體案件的野蠻暴行記憶有關。被告人嚴正在自己的家裡被暴力抓捕過程成了其妻權女士尤其是未成年孩子記憶中揮之不去的惡夢。她說幾個月後自己還常在夢中被驚醒——因為孩子自那次受到驚嚇後經常半夜驚叫、哭嚎。這野蠻制度的罪惡,是我們成年人對孩子們的心靈安全的一種虧欠。在非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得入室拘禁、不得夜晚入室執行法院生效的判決、不得在夜裡進行搜查諸條款形成,都與我在1998年嚴正案中的記憶有關,與孩子受驚嚇後的痛苦感情及記憶有著聯繫。
諸如關於禁止在法定的場所及設施中拘禁的問題,我自己親身經歷的野蠻囚禁過程中,近八年的囚禁,在「法定」場所關押累計三年,其餘被非法囚禁在共產黨私設的牢獄內的時間竟有近五年。國家,成了黑幫犯罪集團任意壓迫人民的工具。
在對公民權利確定的起草過程中,另一個於思想感情裡最醒目的權利保障內容便是,公民在公共場所被公職人員任意盤查、被要求出示身份證件,對公民人身、隨身物品的任意搜查問題,這在中共製下的中國是稀鬆平常的日常現象。事實上,中共從打家劫捨開始便歷來如此,凡有它立足的地方,便會對控制區的人民實行這種野蠻的侮辱性的行徑。這是對公民或直接是對人的一項基本自由權利的野蠻侵犯,是對人的人格尊嚴恣意踐踏的活標本。
美國憲政史上也發生過公共場所對公民隨身物品搜查的案例,卻引發了大規模的辯論,終於還是對人權及憲法價值守護佔據了上風,凡未經公民同意,公共場所的任意搜查,即便發現了諸如毒品等犯罪證據,亦不得對該公民進行指控,以保衛人權、保衛憲法原則不可撼動的神聖。社會、國家可以放縱明顯的犯罪,但不可以為了一個具體的案件,而撼動國家法治原則的底線。這是未來中國人權及公民權利保護實踐所必須持守的價值原則。
附:高智晟《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案全文下載。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