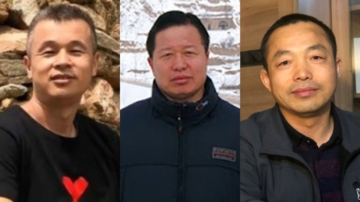耿和按:今天又看了一遍女兒最初在奧斯陸演講準備的初稿,覺得有發表的必要。她最終演講部分的內容不足這個初稿的四分之一。初稿裡,女兒用她幼年記憶來記述她的爸爸,能給關心高智晟的朋友們多一個瞭解他的過去的角度,感謝朋友們!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感謝你們!在這裡,我還要特別感謝奧斯陸給我一個這樣與大家交流的機會。與如此多的朋友們交流是我的光榮,讓我自豪!
我想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對我的父親有所瞭解,但是我還是想簡略介紹一下我的父親高智晟,他是一個律師,一個人權律師。依然需要在此痛苦提到的是,因著他對人類基本權利堅守的不屈,過去12年裡,他經歷了四次駭人聽聞的酷刑折磨、多次的驚心動魄的暴力綁架和背離人類感情的野蠻囚禁,目前他依然被軟禁在中國西北部的一個偏僻山村裡與世隔離,而這是我最不願提及的痛所在。關於父親,如果需要更準確的話,他是一個activist,他同樣有著諸如一個丈夫,一個父親這些角色。他的故事大家可以在中國大陸以外的網上輕易的查詢到,我今天並不想說那個多數人都知道的他,我想說說我記憶裡的父親。
提到我的父親,首先出現在我腦海裡面的是「離別」這個詞。從我可以記事開始,我就一直在跟他說再見,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總是不在我們身邊,可是好在,有他在的時候的記憶都是快樂的。
父親曾講述過一個關於我的故事。一次他回來樓下看到幾個大人帶著各自的孩子玩耍,我在一邊呆看著。看見爸爸後我撲過去抱住他的腿哭得很傷心,爸爸撫摸著我的頭安慰我,說爸爸買了你愛吃的巧克力,結果我止住了哭聲,抬起頭來很認真地對他說:「我想要一個工人爸爸,一個律師爸爸。工人爸爸常陪我玩,律師爸爸常給我買好吃的。」他說他拉著我上樓時心裡難受極啦!
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期間我們家住在郊區,每週至少會有一兩次,放學後總被媽媽帶著擠公交車去父親辦公室看他是我童年記憶裡最清晰的部分。印象中的父親總被許多人圍著,有坐輪椅的、拄雙拐的,也常有人在哭著說些那時我不大懂但很好奇的話,有時也能看見爸爸與那些人一起流淚。印象最深的是父親的辦公室裡總有很多人,我和媽媽趕到後總要在律師樓大廳裡等待很長時間,中間父親會匆匆出來幾次,每次都會過來在我頭上輕輕撫摸兩下,給媽媽說些應該是歉疚的話,然後一轉身又把等待留給我們。而終於結束等待後的結果幾乎是一律的,父親會帶我們到樓下飯館吃餃子。
在新疆時,我幼小心靈中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盼著爸爸腰疼病發,滿足這幼稚願望的是因為他腰疼嚴重時有時會在家裡躺上幾天,讓我總能見到爸爸。今天回想起來,那該是爸爸極困難的經歷,他有時翻個身要咬牙騰挪幾分鐘、甚至十幾分鐘,像蟲子一樣在地毯上蠕動,這是他經年累月在辦公室接待那些永遠無窮盡冤民苦主的成績。可這幼稚的盼望後來也失去了意義。每至腰疼的不堪,他的助理就會將辦公室的大沙發放開,爸爸就會躺著接待那些從全國各地趕來巴望他接待的人,媽媽會每天下班後帶上我去給爸爸送飯,去給他按摩腰。我稍大點後,在北京我曾質疑過父親這種捨已接待冤民的意義,父親的回答增進了我對他的瞭解和敬重。他說,「爸爸從來都不是以一個法律專業人的身份接待他們,在一個法律被權力任意踩踏在腳下的國家裡,律師是沒有力量的。爸爸只是以一個人的感情來接觸他們,因為他們是抱著尚未死滅的信念來找我的,我當然無力改變他們的命運,但我能傾聽他們的哭訴,對他們的苦難以實在的理解、同情和尊重,與他們一同承受痛苦,他們見到我之前有著一律的苦不堪言遭遇,被毆打、被侮辱、被非法拘禁等,我認為讓他們向我傾訴是有意義的。」
我對父親在新疆忙碌的記憶是深刻的,但卻很不具體,更談不上對這種忙碌意義的認識。2009年在泰國滯留期間,媽媽對此有過不少的講述,許多具體的事例我迄今清晰記得。
許多被爸爸援助過的窮人都長期與他保持著感情聯繫,有些更有著像親戚般的聯繫。甘肅退役軍人陳建榮攜家來新疆謀生計,因車禍手術時將醫用紗布遺留體內兩年狀告無門,父親為他提供法律援助後一直保持著聯繫。一日他打通父親的電話大哭,說「不得了啦!不得了啦高律師,家裡的腳蹬三輪車被人偷走了,那是借了四百多元買來的啊。」窮人出身的爸爸深知一輛價值數百元錢的三輪車對一個極貧家庭活命的意義,爸爸讓他搭車來辦公室給了他六百元錢,幫他渡過困難。
遼寧丹東兒童鄒偉毅出生三個月時被瀋陽鐵路醫院錯誤用藥致雙耳重度耳聾,他母親和六十多歲的外婆帶著孩子上訪至六歲時仍不能得一分錢的賠償,期間經歷的屈辱、迫害使人絕望。爸爸攜助理自費奔突於新疆至丹東間,終於為他們贏得了賠償後,每至逢年過節及鄒偉毅的生日,他都會讓媽媽寄些錢給他們,孩子的外婆像對自己的兒子般關愛著爸爸,2006年父親被綁架,孩子的外婆連夜趕到北京我家樓下,舉著父親的照片哭著喊他的名字,其情至為感人。
1998年隆冬的一天,烏魯木齊市大西門過街天橋上跪著一家三口人,他們就是後來爸爸援助的被部隊醫院致殘的九歲腦癱兒童王惠惠一家。孩子的父親雙手高舉一張寫著「請求幫助尋找高智晟律師」的報紙在嚴寒中大聲呼求,路經那裡的爸爸的朋友朱勁松先生電話告知了他。後來,爸爸數次趕到塔城地區為她們提供法律援助,最終為孩子一家爭得了賠償。而這樣的故事幾天幾夜也講不完。
我最後一次去父親在新疆的辦公室看他是在我七歲時的一個週末,媽媽帶著我,我喜歡在公車裡看路邊修剪整齊的植物,然後在心裡想像著躺在那上面遊玩的美好,總想著,如果我爸爸有時間,我肯定會拉著他跟我一起躺在上面玩。可能因為知道離別是每次見面的必然結局,對於這樣的見面我一直都不會興致很高,在我小小的腦袋裡一直認為,我可以把高興都攢著,攢到有一天再也不需要跟爸爸說再見就可以全部釋放出來,那個時候的高興才是真高興。那一次見面做了什麼我不記得了,但是我記得離別。離別的時候我坐在公交車裡,從窗戶看著站在高樓陽臺裡的爸爸,他穿著白色的襯衫,很小很遠,可是我知道他也看著我們,說來很好笑,六七歲的我忽然感受到了心痛,有點類似長大以後失戀的那種心痛,公共車慢慢駛遠,我哭的喘不上氣,就是覺得我視線看不見他的時候就再也看不見了爸爸了。真沒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後一次去那個去過無數次的父親在新疆的辦公室。
當我長大了,瞭解並明白了父親這種忙碌的意義後,開始知道了父親的不易,甚至於他內心的痛苦。他有著在那個無情世界裡極罕見的、極敏感、細膩的同情心,這似乎注定了他在今天中國的許多人眼裡的可怕處境。我常不堪在這方面的認識及感情梳理,從對父親私愛的角度,這種感情梳理常給我帶來不堪承受之痛。於個體生命而言,人類群體中無法抗拒的苦難、不如意哪裡都會發生,而人類社會組織化的第一意義即在於它對這種苦難的消解或緩釋,這也是人類組建國家的最樸素的感情所在。共產極權專制正好相反,它不單是一切人禍苦難的根本起因,更是人們減少及消滅這種禍難努力的最不可理喻的障礙,這便是父親今天困難處境的根本原因和結果。而常年圍著他的那些人卻是在當下中國生活最不如意的人群。遠遠超出外界想像能力的、更其遠遠超出人類黑暗政治經驗的共產極權專制就盛產著這樣的人群。在我的記憶裡,幫助這樣的人群幾乎成了父親的全部事業,佔去了他幾乎全部的精力和感情,他不僅不能得到任何有組織的幫助,相反,對他有組織的冷酷壓迫卻如影相隨。
父親曾告訴過我,他之所以選擇去北京執業,是意在減輕那些全國各地求助者的負擔。他說有權勢的人不需要去新疆找他,到新疆求助者百分之百的是走投無路的窮苦冤民。去遙遠的新疆,無論從經濟還是心理方面,於窮苦冤民都是個不小的負擔。
2001年過年後,父親接了我和媽媽搬去北京。他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我們就住在律師樓的樓上,我喜歡這個安排,這樣我可以更多的見到我爸爸,事實也確實是這樣,除了更多的見到他,更多的,我會看見一些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景象。有一天,我看見一大批衣衫襤褸的中老年的民工,從他們臉上的皺紋看得出他們歲月的多艱,我從未見過這樣深刻的皺紋,這樣土色的皮膚,他們跪在我爸爸的辦公桌前面,嗚嗚的哭,連流出的眼淚都是黑色的,那種委屈悲傷震撼的連我也跟著哭,就像我的父親是他們溺水唯一抓住的稻草,淚流滿面的父親扶起了他們。後來從父親嘴裡得知這些人是來自山西方山縣的民工,政府拖欠他們二十幾人的工資達七十多萬元,十幾年不給。而因為討要工錢,幾乎被地方貪佔他們工錢的官員給逼的妻離子散,完全沒有了正常人的生活。每遇北京有重要的權力活動,每至重要的節日,他們都不敢回家,因為地方政府把他們當成可能會上訪的不穩定因素而被抓捕,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一位秦應泉老人有六十多歲,他一見到我的父親就像個委屈的孩子一樣嗚嗚大哭,他先後被拘留十幾次,我看見父親站在他的一旁默默地垂淚。他們是在鄉村的路上聽人說北京的高智晟可以幫助他們,可憐一群人一路要飯來北京找到我父親。爸爸後來去了山西,這是第一次我深刻理解與父親分離背後的意義,因為這世界上有比我更迫切需要他的人,這樣的理解讓我此後都可以更坦然的面對與父親的離別。那些民工那樣急迫的絕望感後來我在逃亡困境中有過深切的體驗。偷渡到泰國的時候,我跟媽媽被關了起來,四歲弟弟完全失蹤,媽媽絕望的給泰國的民兵長官長跪不起,那種痛苦終生不能忘!
時間過度到我的青少年,政府頻繁的綁架走父親,處在那樣一個爸爸隨時會失蹤,媽媽每天以淚洗面,家裡住滿了警察,學校的同學也被老師警告過不可以跟我說話,不然父母就會進監獄,大家都像躲瘟疫般躲著我,在這樣的環境下,我真覺得自己也成了這麻木世界的一部分了,但我與父親的最後一次離別依然給我留下了感情及人性的深痛。
2009年的1月9日,那是最普通的一天,沒有下雨,沒有艷陽,沒有陰天,但是那卻是我們一家人最後一次團聚在一起。早上起來,我覺得家裡的氣氛很異樣的,哪裡不同我也說不上,就是感覺好像誰要出遠門,可是卻沒有任何人收拾了任何行李,當我看到爸爸用力地抱了弟弟,抱著他親了又親,然後又擁抱親吻我和媽媽時,我完全意識到將會發生什麼一一這是要離別了,一次嚴重的、非同尋常的生離!我們都哭出了聲,父親在這哭聲裡轉身走出了家門。
他必須離開家裡,以帶走樓下的絕大部分眼睛,沒想到不一會他又走了進來,又一次地逐一擁抱親吻了我和弟弟、媽媽後毅然地轉身離去,我們望著他的背影絕望的低聲嗚咽,這是我記憶中關於爸爸的最後定格,已經第九個年頭了!
在父親的《2017年,起來中國》書裡面,他用了「悲莫悲兮生離,痛莫痛兮死別。」來描述他與我們的分離之痛。從他的書裡,我得知了我們離開之後,當天夜裡他回到家坐在沙發上,把我和弟弟、媽媽的拖鞋擺放在各自臥室門口往日的位置上,幻想著我們三個人都在臥室睡覺,連連幾天,他都拒絕進入臥室,他不能接受突然間沒有了我們的現實。非常難以想像,在一個科技無比發達的今天,由於人為的原因,整整八年多了,甚至一家人連彼此現在長什麼樣子都不能見到。
從2005年年底開始,每天專門有六至八名的祕密警察全天候執行著對我的盯蹤騷擾,那種如影相隨的凶悍和流氓無賴式欺辱實在是超出了人的生活經驗,而那時我只有十二歲。夜裡我常在惡夢中驚醒,我的心裡怨氣過爸爸。記得有一天,我很正式地找爸爸談了一次,哭著要求他把自己交給家人,回家作一盞照亮家人的燈。他沉默了一會說請再給爸爸幾年時間,他一定會回家作一盞照亮全家的燈,我看到了他臉上下湧的淚水,今天每回想那一幕,總覺得那是一次自己對父親的罪錯。
2016年,一位朋友轉來一段他與爸爸聊天的文字,看的我和媽媽大哭,心痛的不能自持,我珍藏了這段迄今人生中見到的最具力量的文字。他說:「我的確經歷了些困難過程,於生理而言,最大的苦楚還不算是那幾次在旁人看來毛骨悚然的酷刑經歷,這些年給我生理上製造了最刻骨銘心苦楚的是在軍隊冬天不給暖氣的地下室囚禁。我的此生從未像那幾個冬天那樣嚴重地在乎過冬天,那種寒冷的附著力、穿透力,以及它永不得擺脫的綿延之苦威力在任何酷刑以上。而這些年我所經歷的任何苦楚,悉不在我對耿和她們娘仨的思念及歉疚苦楚以上。她們娘仨所經歷的坎坷和苦難是我人生中最不堪承受之重,我總不忍聞她們的承受。不幸孩子們生在這國,更其不幸的攤上了我這個父親,使姐弟倆小小的心靈上總承受著思親遠盼之痛,而這痛於我永不可彌復,而又總覺著中國又不能少了我這種父親,常為這種不得擺脫的糾葛之苦轄制著!」
在中國,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有千千萬萬,可悲劇的製造者只有一個,那就是共產黨的政府。前幾天我看到中國著名人權律師謝陽夫人不堪當局的野蠻迫害而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偷渡至泰國的消息,心裡感到一種刺痛。作為曾經的偷渡逃亡人,我明白這樣的家庭會經歷怎樣的人間悲慘經驗,時間又往逝了八年,中國的情形更其使人揪心,新近父親的《2016年中國的人權報告》序言中的幾段文字有現成描述,在這裡,我想與大家共同分享這種描述,以期使大家對今天中國人真實的生存現實及父親們的處境能有個大概瞭解,更將這幾段文字作為本次演講的結束語。其中一段是:
「2016年,是中共國繼毛澤東超出人類黑暗政治經驗統治結束後的、繼『六.四』屠殺及法輪功鎮壓以來政治壓迫最為嚴酷及暴虐的一年。其有目共睹的特點及規律正是對毛暴虐恐怖管制政治的全面而快速回歸。共產黨對社會組織、對人私屬權利的強勢及蠻橫控制再顯38年來最惡劣記錄。在過的一年裡,在這片國上,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當局與人類普世文明價值展現的全面抗戰。黨的安全力量無處不至而意志堅定,與人類天然的宗教信仰感情抗戰;與人類的天性自由感情抗戰;與人類的同情心、愛及正義感情抗戰;與人類的財產所有權、居住權、自由遷徙權抗戰;與律師、記者、女權人士、環保公益者、勞工權益維護者、訪民抗戰;與民主憲政、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抗戰;與凡有意義的人類文明成績抗戰,其情至瘋狂地步。這種倒行逆施現象之荒謬及其意義完全超出人類已有的經驗和記錄,讓人目瞪口呆,本報告惟能述其概貌。」
另一文字中爸爸慨嘆道:「在人類群體中討論是否該拒斥人類權利本是個極荒謬絕倫的命題,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年復一年面對的黑暗現實!而於人類群體裡討論人類權利成了公開的禁忌,被一個政府當作極恐怖的危險而以更恐怖的方式予打壓,任何倘有人類正常感情者都能曉明,這國存在著反人類的政府。不難想像這種政府的野蠻及對人類文明前景和聲譽的反動和危害至怎樣嚴酷的程度,這正是鐵的事實。」父親的報告中對自己的所處的環境有著清醒的認知,他寫道:「極端仇視人權的殘酷現實決定著,書寫中國的人權現實是這世界最危險的事業之一。前階段德國一位副總理就中國人權律師被失蹤事件的聲明中,特別強調了其聲援的個人身份色彩之現實表明,他對他的副總理身份所代表了的西方政治主流價值與人權、人類道義及人類基本正義價值不相見容現狀的心知肚明。儘管如此,他的勇氣,仍作了龐大西方政客群體的偶然的鮮例。這種荒謬現狀表明,共產黨以漫天邊際貧窮人民的血、淚及苦勞生成的經濟利益作後盾的恐怖威懾在全世界得了驚人的成績。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野蠻的人權壓迫者、被壓迫者,同樣野蠻的全世界分髒者,大家對這種毀滅人類名譽的現狀沒有不心知肚明的。這現實的另一面則更證實並更強化著中國反抗者身陷的超出想像的孤助及危險處境。而我們,作為中國人權好將來的負軛前驅者,是最無條件躲避的,儘管我們對自己處境的孤助及危險同樣的心知肚明。」
我想,任何有正常感情的人讀了這些文字,不難得出我的父親內心的對世界文明力量有著怎樣的期待,謝謝大家,再次感謝你們!
2017年5月23日
──轉自《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感謝你們!在這裡,我還要特別感謝奧斯陸給我一個這樣與大家交流的機會。與如此多的朋友們交流是我的光榮,讓我自豪!
我想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對我的父親有所瞭解,但是我還是想簡略介紹一下我的父親高智晟,他是一個律師,一個人權律師。依然需要在此痛苦提到的是,因著他對人類基本權利堅守的不屈,過去12年裡,他經歷了四次駭人聽聞的酷刑折磨、多次的驚心動魄的暴力綁架和背離人類感情的野蠻囚禁,目前他依然被軟禁在中國西北部的一個偏僻山村裡與世隔離,而這是我最不願提及的痛所在。關於父親,如果需要更準確的話,他是一個activist,他同樣有著諸如一個丈夫,一個父親這些角色。他的故事大家可以在中國大陸以外的網上輕易的查詢到,我今天並不想說那個多數人都知道的他,我想說說我記憶裡的父親。
提到我的父親,首先出現在我腦海裡面的是「離別」這個詞。從我可以記事開始,我就一直在跟他說再見,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總是不在我們身邊,可是好在,有他在的時候的記憶都是快樂的。
父親曾講述過一個關於我的故事。一次他回來樓下看到幾個大人帶著各自的孩子玩耍,我在一邊呆看著。看見爸爸後我撲過去抱住他的腿哭得很傷心,爸爸撫摸著我的頭安慰我,說爸爸買了你愛吃的巧克力,結果我止住了哭聲,抬起頭來很認真地對他說:「我想要一個工人爸爸,一個律師爸爸。工人爸爸常陪我玩,律師爸爸常給我買好吃的。」他說他拉著我上樓時心裡難受極啦!
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期間我們家住在郊區,每週至少會有一兩次,放學後總被媽媽帶著擠公交車去父親辦公室看他是我童年記憶裡最清晰的部分。印象中的父親總被許多人圍著,有坐輪椅的、拄雙拐的,也常有人在哭著說些那時我不大懂但很好奇的話,有時也能看見爸爸與那些人一起流淚。印象最深的是父親的辦公室裡總有很多人,我和媽媽趕到後總要在律師樓大廳裡等待很長時間,中間父親會匆匆出來幾次,每次都會過來在我頭上輕輕撫摸兩下,給媽媽說些應該是歉疚的話,然後一轉身又把等待留給我們。而終於結束等待後的結果幾乎是一律的,父親會帶我們到樓下飯館吃餃子。
在新疆時,我幼小心靈中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盼著爸爸腰疼病發,滿足這幼稚願望的是因為他腰疼嚴重時有時會在家裡躺上幾天,讓我總能見到爸爸。今天回想起來,那該是爸爸極困難的經歷,他有時翻個身要咬牙騰挪幾分鐘、甚至十幾分鐘,像蟲子一樣在地毯上蠕動,這是他經年累月在辦公室接待那些永遠無窮盡冤民苦主的成績。可這幼稚的盼望後來也失去了意義。每至腰疼的不堪,他的助理就會將辦公室的大沙發放開,爸爸就會躺著接待那些從全國各地趕來巴望他接待的人,媽媽會每天下班後帶上我去給爸爸送飯,去給他按摩腰。我稍大點後,在北京我曾質疑過父親這種捨已接待冤民的意義,父親的回答增進了我對他的瞭解和敬重。他說,「爸爸從來都不是以一個法律專業人的身份接待他們,在一個法律被權力任意踩踏在腳下的國家裡,律師是沒有力量的。爸爸只是以一個人的感情來接觸他們,因為他們是抱著尚未死滅的信念來找我的,我當然無力改變他們的命運,但我能傾聽他們的哭訴,對他們的苦難以實在的理解、同情和尊重,與他們一同承受痛苦,他們見到我之前有著一律的苦不堪言遭遇,被毆打、被侮辱、被非法拘禁等,我認為讓他們向我傾訴是有意義的。」
我對父親在新疆忙碌的記憶是深刻的,但卻很不具體,更談不上對這種忙碌意義的認識。2009年在泰國滯留期間,媽媽對此有過不少的講述,許多具體的事例我迄今清晰記得。
許多被爸爸援助過的窮人都長期與他保持著感情聯繫,有些更有著像親戚般的聯繫。甘肅退役軍人陳建榮攜家來新疆謀生計,因車禍手術時將醫用紗布遺留體內兩年狀告無門,父親為他提供法律援助後一直保持著聯繫。一日他打通父親的電話大哭,說「不得了啦!不得了啦高律師,家裡的腳蹬三輪車被人偷走了,那是借了四百多元買來的啊。」窮人出身的爸爸深知一輛價值數百元錢的三輪車對一個極貧家庭活命的意義,爸爸讓他搭車來辦公室給了他六百元錢,幫他渡過困難。
遼寧丹東兒童鄒偉毅出生三個月時被瀋陽鐵路醫院錯誤用藥致雙耳重度耳聾,他母親和六十多歲的外婆帶著孩子上訪至六歲時仍不能得一分錢的賠償,期間經歷的屈辱、迫害使人絕望。爸爸攜助理自費奔突於新疆至丹東間,終於為他們贏得了賠償後,每至逢年過節及鄒偉毅的生日,他都會讓媽媽寄些錢給他們,孩子的外婆像對自己的兒子般關愛著爸爸,2006年父親被綁架,孩子的外婆連夜趕到北京我家樓下,舉著父親的照片哭著喊他的名字,其情至為感人。
1998年隆冬的一天,烏魯木齊市大西門過街天橋上跪著一家三口人,他們就是後來爸爸援助的被部隊醫院致殘的九歲腦癱兒童王惠惠一家。孩子的父親雙手高舉一張寫著「請求幫助尋找高智晟律師」的報紙在嚴寒中大聲呼求,路經那裡的爸爸的朋友朱勁松先生電話告知了他。後來,爸爸數次趕到塔城地區為她們提供法律援助,最終為孩子一家爭得了賠償。而這樣的故事幾天幾夜也講不完。
我最後一次去父親在新疆的辦公室看他是在我七歲時的一個週末,媽媽帶著我,我喜歡在公車裡看路邊修剪整齊的植物,然後在心裡想像著躺在那上面遊玩的美好,總想著,如果我爸爸有時間,我肯定會拉著他跟我一起躺在上面玩。可能因為知道離別是每次見面的必然結局,對於這樣的見面我一直都不會興致很高,在我小小的腦袋裡一直認為,我可以把高興都攢著,攢到有一天再也不需要跟爸爸說再見就可以全部釋放出來,那個時候的高興才是真高興。那一次見面做了什麼我不記得了,但是我記得離別。離別的時候我坐在公交車裡,從窗戶看著站在高樓陽臺裡的爸爸,他穿著白色的襯衫,很小很遠,可是我知道他也看著我們,說來很好笑,六七歲的我忽然感受到了心痛,有點類似長大以後失戀的那種心痛,公共車慢慢駛遠,我哭的喘不上氣,就是覺得我視線看不見他的時候就再也看不見了爸爸了。真沒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後一次去那個去過無數次的父親在新疆的辦公室。
當我長大了,瞭解並明白了父親這種忙碌的意義後,開始知道了父親的不易,甚至於他內心的痛苦。他有著在那個無情世界裡極罕見的、極敏感、細膩的同情心,這似乎注定了他在今天中國的許多人眼裡的可怕處境。我常不堪在這方面的認識及感情梳理,從對父親私愛的角度,這種感情梳理常給我帶來不堪承受之痛。於個體生命而言,人類群體中無法抗拒的苦難、不如意哪裡都會發生,而人類社會組織化的第一意義即在於它對這種苦難的消解或緩釋,這也是人類組建國家的最樸素的感情所在。共產極權專制正好相反,它不單是一切人禍苦難的根本起因,更是人們減少及消滅這種禍難努力的最不可理喻的障礙,這便是父親今天困難處境的根本原因和結果。而常年圍著他的那些人卻是在當下中國生活最不如意的人群。遠遠超出外界想像能力的、更其遠遠超出人類黑暗政治經驗的共產極權專制就盛產著這樣的人群。在我的記憶裡,幫助這樣的人群幾乎成了父親的全部事業,佔去了他幾乎全部的精力和感情,他不僅不能得到任何有組織的幫助,相反,對他有組織的冷酷壓迫卻如影相隨。
父親曾告訴過我,他之所以選擇去北京執業,是意在減輕那些全國各地求助者的負擔。他說有權勢的人不需要去新疆找他,到新疆求助者百分之百的是走投無路的窮苦冤民。去遙遠的新疆,無論從經濟還是心理方面,於窮苦冤民都是個不小的負擔。
2001年過年後,父親接了我和媽媽搬去北京。他開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我們就住在律師樓的樓上,我喜歡這個安排,這樣我可以更多的見到我爸爸,事實也確實是這樣,除了更多的見到他,更多的,我會看見一些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景象。有一天,我看見一大批衣衫襤褸的中老年的民工,從他們臉上的皺紋看得出他們歲月的多艱,我從未見過這樣深刻的皺紋,這樣土色的皮膚,他們跪在我爸爸的辦公桌前面,嗚嗚的哭,連流出的眼淚都是黑色的,那種委屈悲傷震撼的連我也跟著哭,就像我的父親是他們溺水唯一抓住的稻草,淚流滿面的父親扶起了他們。後來從父親嘴裡得知這些人是來自山西方山縣的民工,政府拖欠他們二十幾人的工資達七十多萬元,十幾年不給。而因為討要工錢,幾乎被地方貪佔他們工錢的官員給逼的妻離子散,完全沒有了正常人的生活。每遇北京有重要的權力活動,每至重要的節日,他們都不敢回家,因為地方政府把他們當成可能會上訪的不穩定因素而被抓捕,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一位秦應泉老人有六十多歲,他一見到我的父親就像個委屈的孩子一樣嗚嗚大哭,他先後被拘留十幾次,我看見父親站在他的一旁默默地垂淚。他們是在鄉村的路上聽人說北京的高智晟可以幫助他們,可憐一群人一路要飯來北京找到我父親。爸爸後來去了山西,這是第一次我深刻理解與父親分離背後的意義,因為這世界上有比我更迫切需要他的人,這樣的理解讓我此後都可以更坦然的面對與父親的離別。那些民工那樣急迫的絕望感後來我在逃亡困境中有過深切的體驗。偷渡到泰國的時候,我跟媽媽被關了起來,四歲弟弟完全失蹤,媽媽絕望的給泰國的民兵長官長跪不起,那種痛苦終生不能忘!
時間過度到我的青少年,政府頻繁的綁架走父親,處在那樣一個爸爸隨時會失蹤,媽媽每天以淚洗面,家裡住滿了警察,學校的同學也被老師警告過不可以跟我說話,不然父母就會進監獄,大家都像躲瘟疫般躲著我,在這樣的環境下,我真覺得自己也成了這麻木世界的一部分了,但我與父親的最後一次離別依然給我留下了感情及人性的深痛。
2009年的1月9日,那是最普通的一天,沒有下雨,沒有艷陽,沒有陰天,但是那卻是我們一家人最後一次團聚在一起。早上起來,我覺得家裡的氣氛很異樣的,哪裡不同我也說不上,就是感覺好像誰要出遠門,可是卻沒有任何人收拾了任何行李,當我看到爸爸用力地抱了弟弟,抱著他親了又親,然後又擁抱親吻我和媽媽時,我完全意識到將會發生什麼一一這是要離別了,一次嚴重的、非同尋常的生離!我們都哭出了聲,父親在這哭聲裡轉身走出了家門。
他必須離開家裡,以帶走樓下的絕大部分眼睛,沒想到不一會他又走了進來,又一次地逐一擁抱親吻了我和弟弟、媽媽後毅然地轉身離去,我們望著他的背影絕望的低聲嗚咽,這是我記憶中關於爸爸的最後定格,已經第九個年頭了!
在父親的《2017年,起來中國》書裡面,他用了「悲莫悲兮生離,痛莫痛兮死別。」來描述他與我們的分離之痛。從他的書裡,我得知了我們離開之後,當天夜裡他回到家坐在沙發上,把我和弟弟、媽媽的拖鞋擺放在各自臥室門口往日的位置上,幻想著我們三個人都在臥室睡覺,連連幾天,他都拒絕進入臥室,他不能接受突然間沒有了我們的現實。非常難以想像,在一個科技無比發達的今天,由於人為的原因,整整八年多了,甚至一家人連彼此現在長什麼樣子都不能見到。
從2005年年底開始,每天專門有六至八名的祕密警察全天候執行著對我的盯蹤騷擾,那種如影相隨的凶悍和流氓無賴式欺辱實在是超出了人的生活經驗,而那時我只有十二歲。夜裡我常在惡夢中驚醒,我的心裡怨氣過爸爸。記得有一天,我很正式地找爸爸談了一次,哭著要求他把自己交給家人,回家作一盞照亮家人的燈。他沉默了一會說請再給爸爸幾年時間,他一定會回家作一盞照亮全家的燈,我看到了他臉上下湧的淚水,今天每回想那一幕,總覺得那是一次自己對父親的罪錯。
2016年,一位朋友轉來一段他與爸爸聊天的文字,看的我和媽媽大哭,心痛的不能自持,我珍藏了這段迄今人生中見到的最具力量的文字。他說:「我的確經歷了些困難過程,於生理而言,最大的苦楚還不算是那幾次在旁人看來毛骨悚然的酷刑經歷,這些年給我生理上製造了最刻骨銘心苦楚的是在軍隊冬天不給暖氣的地下室囚禁。我的此生從未像那幾個冬天那樣嚴重地在乎過冬天,那種寒冷的附著力、穿透力,以及它永不得擺脫的綿延之苦威力在任何酷刑以上。而這些年我所經歷的任何苦楚,悉不在我對耿和她們娘仨的思念及歉疚苦楚以上。她們娘仨所經歷的坎坷和苦難是我人生中最不堪承受之重,我總不忍聞她們的承受。不幸孩子們生在這國,更其不幸的攤上了我這個父親,使姐弟倆小小的心靈上總承受著思親遠盼之痛,而這痛於我永不可彌復,而又總覺著中國又不能少了我這種父親,常為這種不得擺脫的糾葛之苦轄制著!」
在中國,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有千千萬萬,可悲劇的製造者只有一個,那就是共產黨的政府。前幾天我看到中國著名人權律師謝陽夫人不堪當局的野蠻迫害而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偷渡至泰國的消息,心裡感到一種刺痛。作為曾經的偷渡逃亡人,我明白這樣的家庭會經歷怎樣的人間悲慘經驗,時間又往逝了八年,中國的情形更其使人揪心,新近父親的《2016年中國的人權報告》序言中的幾段文字有現成描述,在這裡,我想與大家共同分享這種描述,以期使大家對今天中國人真實的生存現實及父親們的處境能有個大概瞭解,更將這幾段文字作為本次演講的結束語。其中一段是:
「2016年,是中共國繼毛澤東超出人類黑暗政治經驗統治結束後的、繼『六.四』屠殺及法輪功鎮壓以來政治壓迫最為嚴酷及暴虐的一年。其有目共睹的特點及規律正是對毛暴虐恐怖管制政治的全面而快速回歸。共產黨對社會組織、對人私屬權利的強勢及蠻橫控制再顯38年來最惡劣記錄。在過的一年裡,在這片國上,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當局與人類普世文明價值展現的全面抗戰。黨的安全力量無處不至而意志堅定,與人類天然的宗教信仰感情抗戰;與人類的天性自由感情抗戰;與人類的同情心、愛及正義感情抗戰;與人類的財產所有權、居住權、自由遷徙權抗戰;與律師、記者、女權人士、環保公益者、勞工權益維護者、訪民抗戰;與民主憲政、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抗戰;與凡有意義的人類文明成績抗戰,其情至瘋狂地步。這種倒行逆施現象之荒謬及其意義完全超出人類已有的經驗和記錄,讓人目瞪口呆,本報告惟能述其概貌。」
另一文字中爸爸慨嘆道:「在人類群體中討論是否該拒斥人類權利本是個極荒謬絕倫的命題,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年復一年面對的黑暗現實!而於人類群體裡討論人類權利成了公開的禁忌,被一個政府當作極恐怖的危險而以更恐怖的方式予打壓,任何倘有人類正常感情者都能曉明,這國存在著反人類的政府。不難想像這種政府的野蠻及對人類文明前景和聲譽的反動和危害至怎樣嚴酷的程度,這正是鐵的事實。」父親的報告中對自己的所處的環境有著清醒的認知,他寫道:「極端仇視人權的殘酷現實決定著,書寫中國的人權現實是這世界最危險的事業之一。前階段德國一位副總理就中國人權律師被失蹤事件的聲明中,特別強調了其聲援的個人身份色彩之現實表明,他對他的副總理身份所代表了的西方政治主流價值與人權、人類道義及人類基本正義價值不相見容現狀的心知肚明。儘管如此,他的勇氣,仍作了龐大西方政客群體的偶然的鮮例。這種荒謬現狀表明,共產黨以漫天邊際貧窮人民的血、淚及苦勞生成的經濟利益作後盾的恐怖威懾在全世界得了驚人的成績。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野蠻的人權壓迫者、被壓迫者,同樣野蠻的全世界分髒者,大家對這種毀滅人類名譽的現狀沒有不心知肚明的。這現實的另一面則更證實並更強化著中國反抗者身陷的超出想像的孤助及危險處境。而我們,作為中國人權好將來的負軛前驅者,是最無條件躲避的,儘管我們對自己處境的孤助及危險同樣的心知肚明。」
我想,任何有正常感情的人讀了這些文字,不難得出我的父親內心的對世界文明力量有著怎樣的期待,謝謝大家,再次感謝你們!
2017年5月23日
──轉自《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