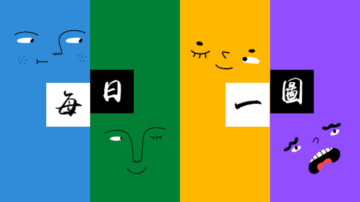三十年前,聽著鄧麗君的歌,向自由飛翔,我從四川飛到西德留學;三十年後,心懷鄧麗君的中國夢,我持德國護照首旅臺北,調研三月。
飛抵臺北後,頗多驚喜,鄧麗君歌唱的夜來香像中央研究院的桂花一樣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我人還在中研院的學人招待所中,就已開始琢磨下一次如何才能從德國再來。臺灣已不是鄧麗君歌中的復興基地,但依然是可以為自由奮鬥,把人權伸張的好地方。
我去臺北前人生地不熟,三個月中結識了百樣自由人,長了不少見識,而我帶著在德國養成的習慣去臺北,免不了出洋相。
在臺北,地鐵被稱為捷運,堪稱名符其實。臺北的地鐵便捷準時,也簡單易懂,但為了坐車觀景,我選擇乘公車。
本來我熱衷以步代車,但從臺大走到國家圖書館後,發現臺北的車輛太多,尤其是摩托車群污染了空氣,敗壞了徒步觀景的環境。此後,只要時間允許,我都坐公車,雖然與捷運相比,乘公車比較麻煩,因為公車五花八門,數目龐大,一般人不清楚,既容易混淆,還容易錯過。
下榻中研院後,第一次外出,到院門口上公車後,我告知司機目的地,得知需要30臺幣,我便將錢包裡的50臺幣投進售票機,以為面前的售票機會像德國的售票機一樣既出票又找零,等了一會兒,我驚奇地問司機,才知臺北的售票機只收錢。
可喜的是,有位乘客見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雞,便走上前來,掏出錢包想彌補我的損失,我才笑著答謝,告訴她我不在乎交20臺幣的學費,否則,我不明白為何一再聽說,到臺北後要買張100臺幣的卡以便乘車,尤其是搭乘捷運。
我對數字過目即忘,買卡來刷後就不清楚車費了,但有次我坐306路公車去益群書店買書,坐車觀人,好不開心,估計有一小時,刷卡才扣15臺幣,這次我過目不忘。也是在這路車上我發現一個主動關心每個乘客的司機,讓我深感行行出狀元。
一般的公車司機不是狀元,但也友善,豈知在快離開臺北時,卻碰到德國人所說的黑羊。那晚在我搭乘的212路公車中的乘客見司機態度惡劣,使我不知所措,便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如何抵達南昌路,最後我聽從一對夫婦的建議,先與他們一起乘212路抵達終點站青年公園,再換乘630路,如願及時抵達目的地。
本來坐飛機外出旅行是一件很愜意的事,但自2001年恐怖份子劫機撞毀紐約的世貿中心,發生911恐怖襲擊後,機場上的安檢加強,並逐漸異化成對乘客的困擾,甚至刁難。以安檢為名,收繳乘客的用品已司空見慣。我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過安檢時,就被迫交出剛買的一瓶護膚液。因安檢發生的荒謬事情層出不窮。
為了避免有損尊嚴的安檢,拒絕被當作潛在的恐怖份子,我2009年從紐約飛回德國後,就寧可不飛行,甚至不旅行。可為了中國夢,我只好豁出去了,但我還是避免法蘭克福機場,寧可到杜拜轉機,從熟悉的杜塞爾朵夫機場起飛。 果然在杜塞爾朵夫機場過安檢時,一切順利,愉悅上機。 可是在臺北機場我卻不得安寧,只因一個只有我的小拇指粗的日用品。這個瑞士用品很精緻,含小剪刀與小刀,已跟隨我多年,人見人愛,這次在臺北有位大姐也表示喜愛,我還打算送她,可她不要,我覺得也不是新的,就沒多說。 當臺北安檢員要我拿出他們發現的威脅品後,我表示可以送人,但安檢員說只能拋棄。我於是據理力爭,當我無法說服面前的安檢員向德國的同行學習,不必把我的袖珍物件視為恐怖份子的作案工具後,我選擇從新趕向行李托運處,請航班工作人員解難。 在阿聯酋航班的托運處,我碰上一位聰明的臺灣小姐,她見我身帶一提一掛的兩個肉紅色包,便建議我騰一個出來給小刀當包裝,然後像大箱子一樣把小包交給她辦托運。 當一個肉紅色的小掛包出現在載滿各種大件行李的傳送帶上時,站在杜塞爾朵夫機場的我頓時心花怒發。不在臺北機場為了珍惜物品而奔走折騰,豈能獲得這份快樂?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飛抵臺北後,頗多驚喜,鄧麗君歌唱的夜來香像中央研究院的桂花一樣沁人心脾,令人陶醉,我人還在中研院的學人招待所中,就已開始琢磨下一次如何才能從德國再來。臺灣已不是鄧麗君歌中的復興基地,但依然是可以為自由奮鬥,把人權伸張的好地方。
我去臺北前人生地不熟,三個月中結識了百樣自由人,長了不少見識,而我帶著在德國養成的習慣去臺北,免不了出洋相。
乘公車
在臺北,地鐵被稱為捷運,堪稱名符其實。臺北的地鐵便捷準時,也簡單易懂,但為了坐車觀景,我選擇乘公車。
本來我熱衷以步代車,但從臺大走到國家圖書館後,發現臺北的車輛太多,尤其是摩托車群污染了空氣,敗壞了徒步觀景的環境。此後,只要時間允許,我都坐公車,雖然與捷運相比,乘公車比較麻煩,因為公車五花八門,數目龐大,一般人不清楚,既容易混淆,還容易錯過。
下榻中研院後,第一次外出,到院門口上公車後,我告知司機目的地,得知需要30臺幣,我便將錢包裡的50臺幣投進售票機,以為面前的售票機會像德國的售票機一樣既出票又找零,等了一會兒,我驚奇地問司機,才知臺北的售票機只收錢。
可喜的是,有位乘客見我站在原地呆若木雞,便走上前來,掏出錢包想彌補我的損失,我才笑著答謝,告訴她我不在乎交20臺幣的學費,否則,我不明白為何一再聽說,到臺北後要買張100臺幣的卡以便乘車,尤其是搭乘捷運。
我對數字過目即忘,買卡來刷後就不清楚車費了,但有次我坐306路公車去益群書店買書,坐車觀人,好不開心,估計有一小時,刷卡才扣15臺幣,這次我過目不忘。也是在這路車上我發現一個主動關心每個乘客的司機,讓我深感行行出狀元。
一般的公車司機不是狀元,但也友善,豈知在快離開臺北時,卻碰到德國人所說的黑羊。那晚在我搭乘的212路公車中的乘客見司機態度惡劣,使我不知所措,便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如何抵達南昌路,最後我聽從一對夫婦的建議,先與他們一起乘212路抵達終點站青年公園,再換乘630路,如願及時抵達目的地。
過安檢
本來坐飛機外出旅行是一件很愜意的事,但自2001年恐怖份子劫機撞毀紐約的世貿中心,發生911恐怖襲擊後,機場上的安檢加強,並逐漸異化成對乘客的困擾,甚至刁難。以安檢為名,收繳乘客的用品已司空見慣。我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過安檢時,就被迫交出剛買的一瓶護膚液。因安檢發生的荒謬事情層出不窮。
為了避免有損尊嚴的安檢,拒絕被當作潛在的恐怖份子,我2009年從紐約飛回德國後,就寧可不飛行,甚至不旅行。可為了中國夢,我只好豁出去了,但我還是避免法蘭克福機場,寧可到杜拜轉機,從熟悉的杜塞爾朵夫機場起飛。 果然在杜塞爾朵夫機場過安檢時,一切順利,愉悅上機。 可是在臺北機場我卻不得安寧,只因一個只有我的小拇指粗的日用品。這個瑞士用品很精緻,含小剪刀與小刀,已跟隨我多年,人見人愛,這次在臺北有位大姐也表示喜愛,我還打算送她,可她不要,我覺得也不是新的,就沒多說。 當臺北安檢員要我拿出他們發現的威脅品後,我表示可以送人,但安檢員說只能拋棄。我於是據理力爭,當我無法說服面前的安檢員向德國的同行學習,不必把我的袖珍物件視為恐怖份子的作案工具後,我選擇從新趕向行李托運處,請航班工作人員解難。 在阿聯酋航班的托運處,我碰上一位聰明的臺灣小姐,她見我身帶一提一掛的兩個肉紅色包,便建議我騰一個出來給小刀當包裝,然後像大箱子一樣把小包交給她辦托運。 當一個肉紅色的小掛包出現在載滿各種大件行李的傳送帶上時,站在杜塞爾朵夫機場的我頓時心花怒發。不在臺北機場為了珍惜物品而奔走折騰,豈能獲得這份快樂?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