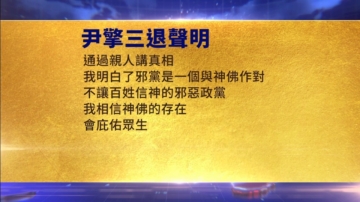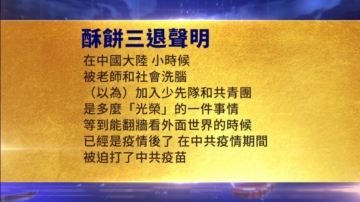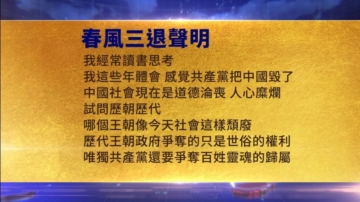【新唐人2004年3月3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报导)六月四日是“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 十五年前的这一天, 在中国北京, 人民子弟兵奉命对和平抗争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 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 十五年来中国官方一直竭力掩盖事实真相, 拒绝承认镇压和屠杀。 然而墨写的谎言难以掩盖血写的事实。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高文谦先生将以他的亲身经历, 为六四作证。
【高文谦】 我们家住在宽街,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我们都有意识的骑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那儿绕一圈。 到六月三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时候气氛已经不对了。 六月三号就在六部口那儿已经有一辆军车给截住了, 还有一辆卡车也被围住了, 那卡车后来不是在电视镜头上全都有嘛。 有的人站在上面, 把钢盔, 刺刀展览。 而且我当时我已经感觉到, 他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放到那块儿, 就是在制造一种口实。 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我又跑到六部口再看, 我第一次看到流血了。 就是从中南海的西南角有个边门, 一大堆武警拿着棍子, 三角铁朝人那就打, 最后把那一车东西都给抢回去了。
我的岳父家就住在北京饭店的后面的红霞公寓里面﹐ 就是在南河沿的把口那儿, 所以我们吃完饭之后呢, 我跟我的妻子又到这个广场上来看, 那个时候我已经真是闻到血腥味儿了。 我当时真想留在广场, 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现代史的这一页, 将是铭心刻骨的, 我希望作历史的见证人。 我妻子不愿意让我冒这个险, 千劝万劝, 我就是不听。 不行。 最后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让我在当时那么一种激昂的,昂奋的, 说不清的一种情绪下冷静下来了。 我妻子说: 你是研究历史的, 你可以有你更大的作用。 你死在广场上你的作用就没有发挥。 听了这话之后, 我一想这话也有道理, 我说: 那好吧, 我就回家去。
我当时心情呢, 虽然一方面我同意我妻子说的, 我回去。 但我心里非常之内疚。 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人们纷纷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 往天安门广场骑, 而我是由南向北往, 往相反的方向骑。 当时骑车的时候, 我自己我都觉得擡不起头来, 内心上就是有那么一种自责。 觉得这种时候人家到天安门广场去, 我要回到自己的家去, 我就是怀着这么一个心情回到家到家里边。 回到家以后, 我就把电视打开了, 连篇的北京市政府的通告, 要求市民呆在里边﹐ 这时我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是必然动手无疑了。 接下来的话, 那当然是老百姓的血肉之躯, 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坦克车和冲锋枪呢。
到了六月四号天亮之后, 美国之音已经报道了学生已经从广场撤离了, 我当时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去。 离沙滩儿路口还有三四十米这么远, 正在这时候几辆军车开得飞快, 哗, 开过来。车上当兵的就往车底下扔了两颗催泪瓦斯, 非常闷的声音就炸开了, 然后就是一梭子子弹。 然后这当兵的还哈哈大笑。 就是那一下子, 两个人, 一个人的腿就被穿了, 还有一个人是侧着把肩膀给穿了。 我当时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那么一种感觉, 但是我还想往前骑, 这时候我看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个大学生, 一边骑呀一边哭, 有人就围着他问, 那边情况怎么样? 他就下来, 泣不成声说: 中国完了, 中国完了, 没希望了。 还一个人 是护士长, 刚忙了一晚上回来, 她的那个白大褂下边这都是血。 太惨了, 太惨了, 真是没想到啊, 别的什么也不说。
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一幕发生了, 而且发生的比我原来所想的还血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天安门镇压, 无非就是工人民兵用棍棒, 把这人们给打散了就算了。这个可好, 我在沙滩那儿, 就已经是机关枪朝着人就扫啊。
说着话我就到了南河沿口儿了, 西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正面就是公安部大门, 我当时印象是最里面是一排坦克车, 已经就是把广场的口给封上了, 然后呢坦克车前面是一排端着冲锋枪的士兵, 端着枪这排士兵前面是一批拿着三角铁的士兵, 距离封锁线七八百米开外是一帮市民, 冲着他们喊: 打倒法西斯,李鹏政府杀人。 就在这时候, 从东面开来两辆面包车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因为它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必须先要经过市民这群人, 然后才能进入到广场里面去, 市民就把它们两个面包车就给拦下来了, 问你们干什么去? 两个面包车的其中的第一个司机就说: 我们到广场去给戒严部队送汽水和面包。 这帮市民一听就火了, 他们还吃面包, 还喝汽水。 结果拉下来就把司机一通揍, 结果第二辆车乘着这个乱乎劲儿, 一个拐弯一下就冲过去了。 这边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呢, 那边我就听见哒哒哒, 哒哒哒,枪声响了。 我们一看不好, 哗一下又都散了, 从广场往南河沿儿里边跑, 我们几个跑得比较快的就到了欧美同学会。 我们想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去,但传达室这个老大爷死活不让这帮人进。 他说:你们可千万别进来呀, 你们要进来, 他们会追进来杀你们的, 这个我可担待不起, 你可千万别进来呀。 这时候有那么一个人四十二军的复员兵, 他一口东北话, 他说: 大爷啊, 你如果不让我们进来的话, 我们都死在你这个欧美同学会这门口儿,这一辈子你心里也不得安生。 大爷一听这话也是啊, 就说: 你们赶紧进来 , 你们赶紧进来吧。 就开门儿让我们进去了。 我们就蹲在欧美同学会的这个门洞里面, 然后就听见街上继续有枪声, 哒哒哒 , 哒哒哒。 我当时听声音判断, 他已经不是在天安门那块儿了,而是拐到了南河沿的胡同里﹐ 追着进来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就看到, 就那一阵子打死了四个人。 这是我亲眼看见, 就在天安门广场, 在公安部门口, 共和国士兵, 用老百姓劳动所制造出来的子弹来杀自己的人民
六月四号那天上午我们心情都很沈重, 包括像我岳父他们这样共产党的老干部当时也觉得怎么能这样做呢? 后来我妻子说她要给家里买点菜去。 她下去了没有多一会儿, 街面儿上就响起枪声了, 哒哒哒, 哒哒哒。 每打一声我的心就咯噔一下子。 后来我岳父叫我赶紧到外面去找我妻子去。 我一看不好, 我赶紧到街上去了。 我一到街上就发现, 戒严部队三个人一组, 三个人站在马路这边, 三个人站在马路那一边。 端着枪, 一边往前走,一边开枪。 我们一看情况不好, 就不敢再在南河沿儿走了, 我们就躲到南河沿儿边上,皇城根的小胡同里面去了, 我们就蹲在墙根底下。 这时候巧了, 跟我蹲一块的是一个凳平板车的一个老大爷, 这大爷就自言自语地说: 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 都没有这么杀人呐, 真是伤天害理啊。 他看我一眼,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会不会去告发他去, 但是他讲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就是当年日本人进北京都没有这么样的大开杀戒。
你要真是说从六四镇压我看到的这么有限的几个场面, 那你想一想,至于说天安门广场死没死人, 什么什么地方死没死人, 那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林丹】您为一个历史学者, 您能不能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历史为我们分析一下, 六四血案是一个必然发生的, 还是一个偶然事件?
【高文谦】当然啦, 这个必然跟偶然这两者有的时候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有的时候的很多必然性的东西, 是通过偶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认为从必然性来讲, 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肯放弃权力, 任何一个老百姓,哪怕是善意的, 希望共产党在政治上有所进步, 有所变化, 更能够反映民意, 都被认为是企图否定共产党。
六四最后是以这么一个血腥的一面给了结, 虽然我自己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 也有预感, 但是最后这个局面这么惨烈, 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为什么我思想上有所准备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毕竟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 和建国以后的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 他怎么样子对待自己的人民。 从镇反, 肃反,到反右, 到文革, 这一幕幕的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觉得非常奇怪。 但我觉得经过文革之后, 共产党应该从文革的惨痛的教训中吸取这教训了, 不能再重蹈覆彻了。 但是恰恰相反,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是这个制度的符号, 他要为这个制度来?话。 而这个制度决定了他最终要走向这一步。 为什么? 就是本质上他不想放弃这个权力, 用陈云的话讲: “我们这个共和国是两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不能够在我们手里这么一朝一夕就给它丢掉”。 天下就是姓共产党的, 就是王震讲的话, “这茅坑是老子挖的, 你别人谁也别想占”。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共产党最后没有完成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始终还是这么一个逻辑: 打天下要坐天下。 中共现存的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万恶之源, 必须下大力气改革。
【林丹】那您认为共产党自身能够完成这种变革吗?
【高文谦】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乐观。
【林丹】有舆论说, 如果当年学生见好就收, 撤离广场就不会发生这个流血事件, 您对这个看法怎么评价呢?
【高文谦】可能不会发生这么惨烈, 但是所有的秋后算账一样也不会少, 一样也不会少。
【林丹】历史以它沈重的笔墨,记载了“六四”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悲剧。 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新中国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惊异地发现, 五十多年来, 我们民族的悲剧从没间断。 从镇反, 肃反, 到反右, 从十年文革, 六四血案, 到镇压法轮功,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 都与一个个悲剧相联。 当文革过后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文革的发生?当六四过后人们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六四的发生?也许您当年的答案并不悲观, 那么您今天的答案呢?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历史学者高文谦先生的答案。
点击进入透视中国Youtube官方频道
【高文谦】 我们家住在宽街,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我们都有意识的骑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那儿绕一圈。 到六月三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那时候气氛已经不对了。 六月三号就在六部口那儿已经有一辆军车给截住了, 还有一辆卡车也被围住了, 那卡车后来不是在电视镜头上全都有嘛。 有的人站在上面, 把钢盔, 刺刀展览。 而且我当时我已经感觉到, 他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放到那块儿, 就是在制造一种口实。 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我又跑到六部口再看, 我第一次看到流血了。 就是从中南海的西南角有个边门, 一大堆武警拿着棍子, 三角铁朝人那就打, 最后把那一车东西都给抢回去了。
我的岳父家就住在北京饭店的后面的红霞公寓里面﹐ 就是在南河沿的把口那儿, 所以我们吃完饭之后呢, 我跟我的妻子又到这个广场上来看, 那个时候我已经真是闻到血腥味儿了。 我当时真想留在广场, 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现代史的这一页, 将是铭心刻骨的, 我希望作历史的见证人。 我妻子不愿意让我冒这个险, 千劝万劝, 我就是不听。 不行。 最后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让我在当时那么一种激昂的,昂奋的, 说不清的一种情绪下冷静下来了。 我妻子说: 你是研究历史的, 你可以有你更大的作用。 你死在广场上你的作用就没有发挥。 听了这话之后, 我一想这话也有道理, 我说: 那好吧, 我就回家去。
我当时心情呢, 虽然一方面我同意我妻子说的, 我回去。 但我心里非常之内疚。 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人们纷纷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 往天安门广场骑, 而我是由南向北往, 往相反的方向骑。 当时骑车的时候, 我自己我都觉得擡不起头来, 内心上就是有那么一种自责。 觉得这种时候人家到天安门广场去, 我要回到自己的家去, 我就是怀着这么一个心情回到家到家里边。 回到家以后, 我就把电视打开了, 连篇的北京市政府的通告, 要求市民呆在里边﹐ 这时我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是必然动手无疑了。 接下来的话, 那当然是老百姓的血肉之躯, 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坦克车和冲锋枪呢。
到了六月四号天亮之后, 美国之音已经报道了学生已经从广场撤离了, 我当时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去。 离沙滩儿路口还有三四十米这么远, 正在这时候几辆军车开得飞快, 哗, 开过来。车上当兵的就往车底下扔了两颗催泪瓦斯, 非常闷的声音就炸开了, 然后就是一梭子子弹。 然后这当兵的还哈哈大笑。 就是那一下子, 两个人, 一个人的腿就被穿了, 还有一个人是侧着把肩膀给穿了。 我当时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那么一种感觉, 但是我还想往前骑, 这时候我看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个大学生, 一边骑呀一边哭, 有人就围着他问, 那边情况怎么样? 他就下来, 泣不成声说: 中国完了, 中国完了, 没希望了。 还一个人 是护士长, 刚忙了一晚上回来, 她的那个白大褂下边这都是血。 太惨了, 太惨了, 真是没想到啊, 别的什么也不说。
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一幕发生了, 而且发生的比我原来所想的还血腥。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天安门镇压, 无非就是工人民兵用棍棒, 把这人们给打散了就算了。这个可好, 我在沙滩那儿, 就已经是机关枪朝着人就扫啊。
说着话我就到了南河沿口儿了, 西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正面就是公安部大门, 我当时印象是最里面是一排坦克车, 已经就是把广场的口给封上了, 然后呢坦克车前面是一排端着冲锋枪的士兵, 端着枪这排士兵前面是一批拿着三角铁的士兵, 距离封锁线七八百米开外是一帮市民, 冲着他们喊: 打倒法西斯,李鹏政府杀人。 就在这时候, 从东面开来两辆面包车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因为它要进入天安门广场, 必须先要经过市民这群人, 然后才能进入到广场里面去, 市民就把它们两个面包车就给拦下来了, 问你们干什么去? 两个面包车的其中的第一个司机就说: 我们到广场去给戒严部队送汽水和面包。 这帮市民一听就火了, 他们还吃面包, 还喝汽水。 结果拉下来就把司机一通揍, 结果第二辆车乘着这个乱乎劲儿, 一个拐弯一下就冲过去了。 这边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呢, 那边我就听见哒哒哒, 哒哒哒,枪声响了。 我们一看不好, 哗一下又都散了, 从广场往南河沿儿里边跑, 我们几个跑得比较快的就到了欧美同学会。 我们想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去,但传达室这个老大爷死活不让这帮人进。 他说:你们可千万别进来呀, 你们要进来, 他们会追进来杀你们的, 这个我可担待不起, 你可千万别进来呀。 这时候有那么一个人四十二军的复员兵, 他一口东北话, 他说: 大爷啊, 你如果不让我们进来的话, 我们都死在你这个欧美同学会这门口儿,这一辈子你心里也不得安生。 大爷一听这话也是啊, 就说: 你们赶紧进来 , 你们赶紧进来吧。 就开门儿让我们进去了。 我们就蹲在欧美同学会的这个门洞里面, 然后就听见街上继续有枪声, 哒哒哒 , 哒哒哒。 我当时听声音判断, 他已经不是在天安门那块儿了,而是拐到了南河沿的胡同里﹐ 追着进来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以后, 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就看到, 就那一阵子打死了四个人。 这是我亲眼看见, 就在天安门广场, 在公安部门口, 共和国士兵, 用老百姓劳动所制造出来的子弹来杀自己的人民
六月四号那天上午我们心情都很沈重, 包括像我岳父他们这样共产党的老干部当时也觉得怎么能这样做呢? 后来我妻子说她要给家里买点菜去。 她下去了没有多一会儿, 街面儿上就响起枪声了, 哒哒哒, 哒哒哒。 每打一声我的心就咯噔一下子。 后来我岳父叫我赶紧到外面去找我妻子去。 我一看不好, 我赶紧到街上去了。 我一到街上就发现, 戒严部队三个人一组, 三个人站在马路这边, 三个人站在马路那一边。 端着枪, 一边往前走,一边开枪。 我们一看情况不好, 就不敢再在南河沿儿走了, 我们就躲到南河沿儿边上,皇城根的小胡同里面去了, 我们就蹲在墙根底下。 这时候巧了, 跟我蹲一块的是一个凳平板车的一个老大爷, 这大爷就自言自语地说: 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 都没有这么杀人呐, 真是伤天害理啊。 他看我一眼,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会不会去告发他去, 但是他讲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就是当年日本人进北京都没有这么样的大开杀戒。
你要真是说从六四镇压我看到的这么有限的几个场面, 那你想一想,至于说天安门广场死没死人, 什么什么地方死没死人, 那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林丹】您为一个历史学者, 您能不能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历史为我们分析一下, 六四血案是一个必然发生的, 还是一个偶然事件?
【高文谦】当然啦, 这个必然跟偶然这两者有的时候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有的时候的很多必然性的东西, 是通过偶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认为从必然性来讲, 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不肯放弃权力, 任何一个老百姓,哪怕是善意的, 希望共产党在政治上有所进步, 有所变化, 更能够反映民意, 都被认为是企图否定共产党。
六四最后是以这么一个血腥的一面给了结, 虽然我自己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 也有预感, 但是最后这个局面这么惨烈, 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为什么我思想上有所准备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毕竟是研究历史的, 我知道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 和建国以后的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 他怎么样子对待自己的人民。 从镇反, 肃反,到反右, 到文革, 这一幕幕的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觉得非常奇怪。 但我觉得经过文革之后, 共产党应该从文革的惨痛的教训中吸取这教训了, 不能再重蹈覆彻了。 但是恰恰相反,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是这个制度的符号, 他要为这个制度来?话。 而这个制度决定了他最终要走向这一步。 为什么? 就是本质上他不想放弃这个权力, 用陈云的话讲: “我们这个共和国是两千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不能够在我们手里这么一朝一夕就给它丢掉”。 天下就是姓共产党的, 就是王震讲的话, “这茅坑是老子挖的, 你别人谁也别想占”。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共产党最后没有完成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始终还是这么一个逻辑: 打天下要坐天下。 中共现存的这种一党专政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万恶之源, 必须下大力气改革。
【林丹】那您认为共产党自身能够完成这种变革吗?
【高文谦】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乐观。
【林丹】有舆论说, 如果当年学生见好就收, 撤离广场就不会发生这个流血事件, 您对这个看法怎么评价呢?
【高文谦】可能不会发生这么惨烈, 但是所有的秋后算账一样也不会少, 一样也不会少。
【林丹】历史以它沈重的笔墨,记载了“六四”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悲剧。 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新中国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惊异地发现, 五十多年来, 我们民族的悲剧从没间断。 从镇反, 肃反, 到反右, 从十年文革, 六四血案, 到镇压法轮功,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丰功伟绩, 都与一个个悲剧相联。 当文革过后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文革的发生?当六四过后人们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防止另一个六四的发生?也许您当年的答案并不悲观, 那么您今天的答案呢?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历史学者高文谦先生的答案。
点击进入透视中国Youtube官方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