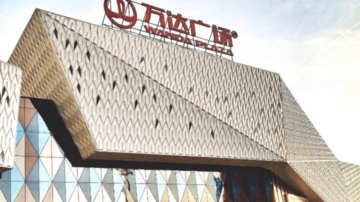【新唐人记者林丹综合报道】中国政府再次由于惧怕异议人士的不同声音,拒绝给独立中文笔会前秘书长,现居瑞典的张钰博士延长护照。
十一月十九号,星期三,独立中文笔会前秘书长,居住在瑞典的张钰博士也接到驻瑞典的中国使馆的通知,拒绝给他延长护照。有关这个事件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张钰博士,他向自由亚洲记者天溢介绍说:(录音)“上个月我去换护照了,我的护照是明年二月到期,大概需要三周。所以昨天我就去了使馆,他说根据外交部方面的指示,不能给我换护照。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我说,我知道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你必须告诉我!他说根据外交部领事司的批复,说是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不予换照。”
对此,张钰博士要求他们具体讲明是根据什么法律,(录音)“他们说,你自己去查,我就说有几百条法律,我自己如何去查。他就说,反正是根据法律。我说,恐怕是没有这条法律吧!外交部外事司也没有权力决定一个人的罪名。这罪名是司法部门决定的。你们凭什么?他说,你要有意见可以向外交部领事司去投诉。你跟我们说也没有用,我们是执行命令的。”
为此,张钰博士退一步要求他们给予一个书面答复,(录音)“他说,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我们还会骗你!我说,要是按照你的道理,法庭法官说,当着那么多人宣判了,那人家就不出判决书了!哪有这个道理!我正式申请,你正式答复却是口头的。他说,我们就是口头的,我们作为外事机构是有权力给成文的东西,也可以给不成文的东西。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有义务为我服务。他没话说,然后就说,反正你不管怎么说,你的事,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张钰(右),万之,齐思盈2005年11月在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自由奖发奖晚会上
对此,张钰博士联系到最近包括多位德国汉学家在内的四十九人维护中国政府的公开信说,(录音)“我就想起来了,四十九人写的回信说,我们在争论中国政府是个流氓政府,还是值得信任的伙伴。这整个是个流氓无赖吗!”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感到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保持国内统治的的稳定,因此对于海外的异议人士采取吊销护照,对于国内的异议人士采取驱逐出国的做法。最近几年,这种做法没有因为国内所谓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有所缓和,反而更加扩大。
【附录 】给胡锦涛主席的申诉信
胡锦涛主席:
我欢迎您到瑞典访问,不仅是因为您可以向瑞典的先进社会制度学习,而且还因为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可能有希望改正贵党政府处理本案所犯的错误,包括非法剥夺我入境祖国的中国公民权利。
我估计您没有收到我在今年四月给温家宝总理信的副本(如下所示),我是通过电邮请贵州省的国安部门转交的,因为当我妻子在今年初带着几个小孩回国探望她父母时,这个部门的人员就多次传讯她,询问有关我的情况,到她回瑞典后也未放松。我还未收到温总理那方面的答复,只听说国安又惊扰了我在国内更多的亲属。事实上,他们至少在一年前就开始这么做了,只是在我被拒绝入境前没让我们夫妻知道而已。
由于国内有关当局至今未答复我的问题,我不得不利用您来访的机会向您提出申诉,希望您所关注的“和谐社会”能具有现实意义,也包括同是中国公民的我本人及亲属,希望您在百忙之中责成有关部门:
1)让警察停止惊扰我的家庭成员和亲戚——因为他们与我的言行毫无关系,甚至都不曾听说我的近况,所以无论警方用什么罪名来对付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株连他们。
2)敦促处理此案的部门尽快改正错误,尊重我回国和探母的基本权利。
望您或贵党政府早日给我一个答复。预祝你访瑞及提倡全民和谐社会的成功。
张钰
2007年6月4日

独立中文笔会原秘书长张钰博士
就在北京西站被拒入境事给温家宝总理的信
温家宝总理:您好!
我是旅居瑞典的中国公民,现因今年2月7日下午在北京铁路西客站入境被拒事,不得已向您投诉。
2007年2月7日下午4点35分,我所乘的T98次京港直通快车在晚点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北京西客站;大约刚过5点,我在该站的入境边防检查站出示护照后被边检警察带入“留置室”;大约7点左右,北京铁路西客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下简称“边防站”)副站长殷明先生向我正式传达上级决定:“由于你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现决定拒绝你入境,由你自己购买机票,返回你的原出境地香港”(大意,下同);直到当晚9点左右被遣送到飞往香港的国泰CX2039航班登机口,失去人身自由约四小时。在这约四个小时中,边检警察除了“根据上级指示”、“要等上级决定”、“传达上级决定”等口头说法之外,尽管我一再要求和抗议,也没有出示任何有权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以及将我遣送出境的文字,既没有向我出示任何相关的司法文书,也没有办理任何相关的行政手续,甚至连口头说明的合法依据或条文引用都不存在。在整个过程中,唯一履行了法律程序的是:向我宣布要根据相关法规搜查我的身体和携带物品,为此要我在相关表格上签字认可,我毫无异议地照办了。(不过,边检警察除了帮我搬拖行李和押送我去机场是挤坐一车,并无任何人主动碰过我的身体和物品,对于这种人格上的尊重,我在此向殷明先生和所有当值警察表示由衷的感谢)。
根据我对中国法律、法规的了解,北京铁路西客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根据所谓“上级指示”和“上级决定”对我的处置,有诸多涉嫌违法之处,现按时间发生顺序列举如下:
1)边检站将我“留置”,剥夺我的人身自由约四小时之久,既不办理任何相关手续,也拒绝向我说明任何原由或法律依据,仅以“根据上级指示”来回答我的质疑和抗议;
2)边检站将我“留置”,剥夺我与家人打电话联络等基本权利约四小时之久,甚至拒绝我提出的由边检站打电话转告我妻子(已在国内)有关我现状的要求,也拒绝向我说明任何法律依据,仅以“要等上级决定”来回答我的质疑和抗议;
3)边检站传达 “上级决定”,判定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却拒绝说明理由或依据,既提不出我有任何实际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也提不出根据哪条法规可以因此拒绝我这个持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本国,仅以“上级决定不作更多说明”来回答我的质疑和抗议;
4)边检站传达 “上级决定”,完全空口无凭,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既没有出示文字依据,也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更没有任何当事人的签名盖章,甚至连如此处理是依据什么法规都说不出来,针对我的质疑和抗议的回答仅仅是:“这个决定只作口头宣布,如果你要投诉,就向我追究责任好了,我是北京铁路西客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名叫殷明。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和职务记录下来。”
5)边检站传达 “上级决定”,却拒绝说明上级机关的名称。我抗议说,边检站的上级也是公安机关,但据我对中国法规的了解,公安机关根本无权如此判定并处置“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类刑事问题,因此这个“上级决定”显然是违反司法程序的……针对我的质疑和抗议的回答仅仅是:这个“上级决定”不是“公安机关”的决定。
根据我对中国法律的了解,边检站的“上级”无论是哪个国家机关或领导人,最高也无非国务院和您这位总理,但即使是位高权重的您,也无权剥夺任何中国公民持合法护照入境本国的权利。
我于1981年底出国留学后在国外工作和居住(简历参见附件一),25年多来一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此之前回国探亲和出差,出入国境数十次,直到此前包括2005年5月的上次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连被边检站质疑讯问都不曾发生过,也不曾被任何公安或国家安全部门查问过一次(即使是这次遭处置,除了被问过是否有钱买机票以外,也未被正式问及其它任何问题)。
自前年5月回国两星期后出境以来,我也没有与以前根本不同的言行,只是在前年10月起担任了我于2002年已加入的独立中文笔会的秘书长,更多参与了本笔会以及国际笔会的事务。独立中文笔会于2001年成立,在美国纽约注册,根据章程为“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之人士自由结合的非政府、非营利、非政党的跨国界组织”,也是国际笔会的分会之一(简介参见附件二)。独立中文笔会秉承国际笔会“弘扬文学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宗旨,目前有近200名会员,其中近半数生活在中国大陆,所从事的笔会事务与中国法律并无冲突,本人所承担的笔会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丝毫“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在笔会以外,本人从事的社会活动也只有2000年起就业余担任的《北欧华人通讯》总编辑,这是挪威政府资助的一份为侨居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华人提供当地信息和文化服务的刊物,我作为其总编的作为也根本不可能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综上所述,北京铁路西客站边检站所执行的“上级决定”,完全是无中生有肆意侵权的产物,至今未向本人查证或哪怕询问一句,就如此轻率地剥夺了我作为中国公民一直享有的出入境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个决定还意味着无限期地剥夺了我回国探亲的权利,包括不让我探望已86岁高龄且已半身不遂的母亲,而且很有可能不再给我们母子见面的机会,也未免太不人道,太过残忍。一个连机构名称都不肯告诉被处置者的“上级”,作出连文字都不肯出示给处置者的“决定”,无论于情、于理、于法,都根本站不住脚,显然是一起严重枉法违法的错案。
由于这个据称不是公安机关的“上级”的名称不明,因此我只好向您这个可以明确肯定是公安机关上级的国务院总理投诉,请您责成有关部门按照合法程序处理本案,依法改正拒绝我入境并遣送香港的错误“上级决定”,并赔偿我由此产生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损失。
此致
敬礼
张钰
2007年4月10日
抄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
公安部长周永康

独立中文笔会原秘书长张钰博士
以己及人说人权
张裕
与许多同代上下的人一样, 1989年的“六四屠杀”改变了我的生涯。虽然我当时已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但也因家庭因素有着与难以磨灭的经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感同身受,影响至今。这家庭因素就是先父当年的入狱与获释。
先父张钟是1941年就加入过中共的“老干部”,80年代初“离休”,在家专心研究中共早期历史,发表了一些相关考证文章。1989年9月,他突然被武汉市公安局抄家后带走,据称是涉嫌给中共高层写了一些“严重政治错误”的信(后来知道是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被“收容审查”。我母亲当时也早已离休,不知案情,托了亲友打听,一直不得要领,有说案情严重得“通了天”,属于不得打听的“国家机密”。
我当时在瑞典留学和工作已近八年,与父母只是一月一信。他们当时舍不得装电话,母亲的信中不提父亲被捕,只说他忙于写作,因此当我从亲戚那里听说此事,已过去了近三个月。我只好托有电话的亲戚找到母亲,得知她除了打听到上述一点情况以外,只根据公安局的要求托带过冬衣和钱,再也不知如何是好。我提出要在国外公开呼吁此事,因为根据当时法规,先父本不应属于“收容审查”的对象(有流窜作案嫌疑的人,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来历不明者),且“收审” 最高时限也不得超过三个月,如果改为拘留和逮捕,也不应三个月仍不通知家属,当局显然是知法犯法,难以对它们再报希望。母亲坚决反对,说是怕父亲更遭报复。于是我答应只给国内各级领导人和部门写信,再等当局三个月的反应时间。我共发了30多封信,上至党总书记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下至武汉市公检法各机关,通过使馆转交,内容大同小异,无非询问父亲现状和关押依据,说明我所知父亲经历和年老体弱,请有关当局依法释放他,即使已进入司法程序不是违法关押,也应该允许他“保外就医”或“取保候审”。一个多月以后,武汉市检察院回信通知我母亲,说是收到我的询问信,但此案目前仍属武汉市公安局处理,与检察院无关,如果该院受理此案,自会及时通知。除此之外,再无其它回音。
三个月后的1990年3月底,我对母亲表示,检察院既然知道此案而仍与此无关,自然是未批准逮捕,无论是“收容审查”或“拘留”到半年也大大超过时限,其它有关部门对我的投诉没有反应,可以证明当局因违法关押而无言以对;我们对当局已算仁至义尽,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助,否则也没有其它办法。母亲说最好还是不要公开造舆论,先私下求助一些有影响的国际机构。于是,我就给“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写信,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其总部的回信,说是已决定接受我父亲的个案,并交瑞典和法国的两个小组专门关注和处理,不久两个小组分别与我联系,问了一些相关情况,说是将动员会员向包括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各方面去信呼吁释放。
5月中旬,瑞典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人士到当时在斯市城内的使馆门前示威,纪念北京学生绝食抗议一周年,我也去了。其间,大使馆一参赞夫人(刚好认识我并看过我的投诉信)要乘车离开,有些示威者上前向她宣讲当局的镇压罪过,她反驳后争论起来,我走过去时正好听到她说“无论如何,你们这样反党反政府的行动也是错误的。”我接上话说:“您错了,不是我们老百姓要反对贵党和政府,而是贵党和政府镇压我们老百姓。您知道我父亲的案子,他可是所谓‘离休干部’,至多也不过是写信批评了贵党领导,贵党就把他抓起来关了8个月还不放,完全违反了贵党和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您怎么能怪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反对贵党和政府的这类违法镇压行动呢?”她哑口无言,但她的司机帮腔说:“你父亲肯定是老反革命,抓起来活该!”于是激起了众怒,骂声四起。参赞夫人制止了司机争吵,开车离开了。
有位新华社记者一直在路边观看示威,这时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有认识他的人介绍说我是在皇家工学院工作的博士后,父亲是“老革命”,只因给中央写信就被警察抓去至今不放。他就过来要我自己再具体谈一下,听完后表示,如果确如我所说,很可能是一冤错案件,他可以写一内参给有关方面,请他们尽快调查处理此案,无论如何象这样不说明理由而无限期的关押显然是不当的。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让我把原来写的材料寄给他一份,我回家后就办了。半个月后是“六四”一周年,我去市中心参加周年祭活动,又碰见那位记者,他说已把我父亲的案子写入内参,几天前刚递交上去了,或许在一两个月内能有消息。另外,我也碰到“国际特赦”负责我父亲案子的小组负责人,她说一个多星期前已发出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
6月下旬,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当天公安局来找她,首次让她和我妹妹等三亲属去看守所见先父,并让她们劝说他认错,只要认了就可以立即释放。她们就去劝了,并说我也是同样的意见,但我父亲仍然拒绝。不过,在我父亲离开后,在场的负责人对我母亲说,他们觉得先父的问题不很严重,仍决定释放,不过这案子是“上面”交办的,还必须经过上报审批,估计需要十天半月就可以结案放人。会面九天后的七月上旬,我父亲就被释放了,只是带了一个有“尾巴”的结论:“有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但罪行较轻,免予处理。”(大意如此)
父亲出狱后说,他被“收审”的前三月常被提审,但他什么也不认。89年12月,检察院去人提审一次后,再就没有任何提审了,估计是检察院驳回了此案,因此他预料最多就是可能由公安以“反革命宣传煽动”判他劳教三年。看守所里不让家属探望,条件又很差,他还传染上了乙型肝炎,因此他还不时要求快点判他(因为同一看守所中被“收审”时间最长者已达七年!),当局一直不理他的要求。90年6月下旬,看守所指导员找他“谈判”,说是只要他“认错”就可以立即放他,如果他不相信,甚至可立下字据,签名盖章。父亲说不能接受这种“交易”,不能为释放就承认自己没干的事。于是又让他见母亲等,但他也不听劝,没想到结果还是放了。
我们估计,这个结果是那位记者和人权组织两方面努力所致——“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的呼吁形成外压,使要面子的中央领导人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而记者内参的提醒显然能起催化作用,使此案得以迅速结案,否则释放程序可能要缓慢得多。当我对那位记者表示感谢时,他谦虚地说只是尽了一个记者应尽的义务而已,正象“国际特赦”的朋友们说他们只是尽了人权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一样。
令人遗憾和感伤的是,先父还是被释放得晚了两、三个月——他在90年夏天因看守所里流行的乙型肝炎感染,出狱后一直没法治愈,时好是坏,拖到96年初,终因“肝昏迷”引起“脑中毒”不治而逝,成了当局“以言治罪”和“六四镇压”的又一牺牲品。
也正是基于先父因“六四镇压” 而“因言获罪”的入狱与获释,我深深体会到人权运动的必要和有效,因此从那时起先后加入了国际特赦、纽约科学院、国际笔会等国际人权组织,近年来主要参与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事务,特别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希望能象别人帮助曾是“狱中作家”的先父那样,我也能帮助与他类似的“因言获罪”者。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有关当局近来倒行逆施,居然将我参加这类活动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在我去年2月回国探亲到北京入境时,边境检查站不经任何程序,未办任何手续,不问不查不答不理,只以不明机构的口头决定,将我这个25年多来一直来去自由的中国公民遣返,实在荒唐透顶。有关当局一直不与我本人直接打交道,不但不理睬我对拒绝入境的先后向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申诉(见附录),而且在今年一月我从香港返回瑞典飞到北京机场转机时把我强行扣留并“遣返”香港,边检承认我的中国护照合法但声称只在国外才能有效使用,更在今年四月连香港也拒绝我入境了,甚至还声称将来可能连台湾也不让我去了——因为现在两岸关系正“走向统一”。尤其可恶的是,有关当局近两年来还不时骚扰和惊吓对我的近况毫不了解的家人和亲戚,完全是本末倒置乱株连。
当局近年来一直大力鼓吹“和谐社会”,但对于包括我家在内的很多普通中国人而言,显然已沦为假话。我母亲已高龄87岁,几年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近年来又不时因病住院,而我连隔一两探望一次的机会都被当局给“和谐”得没有了。这也更显示了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仍然任重道远,还有待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了大家也为我们自己。
2007年6月3日一稿,2008年10月31日修改。
【张钰简历】
张钰,常用笔名张裕,男,汉族, 1952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务农,1970至1974年在湖北省化工厂当工人,1977年毕业于武汉化工学院,1981年底到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留学,1987年获工科博士学位,此后留在该校从事科研工作至今,其间于1991年至1993年曾应西班牙教育和科技部邀请到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作访问学者。1990年参加“国际特赦”组织,业余创办《北欧华人》月报。1998年参加纽约科学院(科学家人权组织)。2000年起担任《北欧华人通讯》杂志总编辑。2002年加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2004年起担任该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担任该笔会秘书长;2004年起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参加了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四届年会,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两届双年会,以及2007年2月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
十一月十九号,星期三,独立中文笔会前秘书长,居住在瑞典的张钰博士也接到驻瑞典的中国使馆的通知,拒绝给他延长护照。有关这个事件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张钰博士,他向自由亚洲记者天溢介绍说:(录音)“上个月我去换护照了,我的护照是明年二月到期,大概需要三周。所以昨天我就去了使馆,他说根据外交部方面的指示,不能给我换护照。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我说,我知道我没有做什么坏事。你必须告诉我!他说根据外交部领事司的批复,说是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不予换照。”
对此,张钰博士要求他们具体讲明是根据什么法律,(录音)“他们说,你自己去查,我就说有几百条法律,我自己如何去查。他就说,反正是根据法律。我说,恐怕是没有这条法律吧!外交部外事司也没有权力决定一个人的罪名。这罪名是司法部门决定的。你们凭什么?他说,你要有意见可以向外交部领事司去投诉。你跟我们说也没有用,我们是执行命令的。”
为此,张钰博士退一步要求他们给予一个书面答复,(录音)“他说,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我们还会骗你!我说,要是按照你的道理,法庭法官说,当着那么多人宣判了,那人家就不出判决书了!哪有这个道理!我正式申请,你正式答复却是口头的。他说,我们就是口头的,我们作为外事机构是有权力给成文的东西,也可以给不成文的东西。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有义务为我服务。他没话说,然后就说,反正你不管怎么说,你的事,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张钰(右),万之,齐思盈2005年11月在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新闻自由奖发奖晚会上
对此,张钰博士联系到最近包括多位德国汉学家在内的四十九人维护中国政府的公开信说,(录音)“我就想起来了,四十九人写的回信说,我们在争论中国政府是个流氓政府,还是值得信任的伙伴。这整个是个流氓无赖吗!”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感到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保持国内统治的的稳定,因此对于海外的异议人士采取吊销护照,对于国内的异议人士采取驱逐出国的做法。最近几年,这种做法没有因为国内所谓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有所缓和,反而更加扩大。
【附录 】给胡锦涛主席的申诉信
胡锦涛主席:
我欢迎您到瑞典访问,不仅是因为您可以向瑞典的先进社会制度学习,而且还因为您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可能有希望改正贵党政府处理本案所犯的错误,包括非法剥夺我入境祖国的中国公民权利。
我估计您没有收到我在今年四月给温家宝总理信的副本(如下所示),我是通过电邮请贵州省的国安部门转交的,因为当我妻子在今年初带着几个小孩回国探望她父母时,这个部门的人员就多次传讯她,询问有关我的情况,到她回瑞典后也未放松。我还未收到温总理那方面的答复,只听说国安又惊扰了我在国内更多的亲属。事实上,他们至少在一年前就开始这么做了,只是在我被拒绝入境前没让我们夫妻知道而已。
由于国内有关当局至今未答复我的问题,我不得不利用您来访的机会向您提出申诉,希望您所关注的“和谐社会”能具有现实意义,也包括同是中国公民的我本人及亲属,希望您在百忙之中责成有关部门:
1)让警察停止惊扰我的家庭成员和亲戚——因为他们与我的言行毫无关系,甚至都不曾听说我的近况,所以无论警方用什么罪名来对付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株连他们。
2)敦促处理此案的部门尽快改正错误,尊重我回国和探母的基本权利。
望您或贵党政府早日给我一个答复。预祝你访瑞及提倡全民和谐社会的成功。
张钰
2007年6月4日

独立中文笔会原秘书长张钰博士
就在北京西站被拒入境事给温家宝总理的信
温家宝总理:您好!
我是旅居瑞典的中国公民,现因今年2月7日下午在北京铁路西客站入境被拒事,不得已向您投诉。
2007年2月7日下午4点35分,我所乘的T98次京港直通快车在晚点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北京西客站;大约刚过5点,我在该站的入境边防检查站出示护照后被边检警察带入“留置室”;大约7点左右,北京铁路西客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下简称“边防站”)副站长殷明先生向我正式传达上级决定:“由于你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现决定拒绝你入境,由你自己购买机票,返回你的原出境地香港”(大意,下同);直到当晚9点左右被遣送到飞往香港的国泰CX2039航班登机口,失去人身自由约四小时。在这约四个小时中,边检警察除了“根据上级指示”、“要等上级决定”、“传达上级决定”等口头说法之外,尽管我一再要求和抗议,也没有出示任何有权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以及将我遣送出境的文字,既没有向我出示任何相关的司法文书,也没有办理任何相关的行政手续,甚至连口头说明的合法依据或条文引用都不存在。在整个过程中,唯一履行了法律程序的是:向我宣布要根据相关法规搜查我的身体和携带物品,为此要我在相关表格上签字认可,我毫无异议地照办了。(不过,边检警察除了帮我搬拖行李和押送我去机场是挤坐一车,并无任何人主动碰过我的身体和物品,对于这种人格上的尊重,我在此向殷明先生和所有当值警察表示由衷的感谢)。
根据我对中国法律、法规的了解,北京铁路西客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根据所谓“上级指示”和“上级决定”对我的处置,有诸多涉嫌违法之处,现按时间发生顺序列举如下:
1)边检站将我“留置”,剥夺我的人身自由约四小时之久,既不办理任何相关手续,也拒绝向我说明任何原由或法律依据,仅以“根据上级指示”来回答我的质疑和抗议;
2)边检站将我“留置”,剥夺我与家人打电话联络等基本权利约四小时之久,甚至拒绝我提出的由边检站打电话转告我妻子(已在国内)有关我现状的要求,也拒绝向我说明任何法律依据,仅以“要等上级决定”来回答我的质疑和抗议;
3)边检站传达 “上级决定”,判定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却拒绝说明理由或依据,既提不出我有任何实际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也提不出根据哪条法规可以因此拒绝我这个持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本国,仅以“上级决定不作更多说明”来回答我的质疑和抗议;
4)边检站传达 “上级决定”,完全空口无凭,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既没有出示文字依据,也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更没有任何当事人的签名盖章,甚至连如此处理是依据什么法规都说不出来,针对我的质疑和抗议的回答仅仅是:“这个决定只作口头宣布,如果你要投诉,就向我追究责任好了,我是北京铁路西客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名叫殷明。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和职务记录下来。”
5)边检站传达 “上级决定”,却拒绝说明上级机关的名称。我抗议说,边检站的上级也是公安机关,但据我对中国法规的了解,公安机关根本无权如此判定并处置“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类刑事问题,因此这个“上级决定”显然是违反司法程序的……针对我的质疑和抗议的回答仅仅是:这个“上级决定”不是“公安机关”的决定。
根据我对中国法律的了解,边检站的“上级”无论是哪个国家机关或领导人,最高也无非国务院和您这位总理,但即使是位高权重的您,也无权剥夺任何中国公民持合法护照入境本国的权利。
我于1981年底出国留学后在国外工作和居住(简历参见附件一),25年多来一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此之前回国探亲和出差,出入国境数十次,直到此前包括2005年5月的上次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连被边检站质疑讯问都不曾发生过,也不曾被任何公安或国家安全部门查问过一次(即使是这次遭处置,除了被问过是否有钱买机票以外,也未被正式问及其它任何问题)。
自前年5月回国两星期后出境以来,我也没有与以前根本不同的言行,只是在前年10月起担任了我于2002年已加入的独立中文笔会的秘书长,更多参与了本笔会以及国际笔会的事务。独立中文笔会于2001年成立,在美国纽约注册,根据章程为“全世界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之人士自由结合的非政府、非营利、非政党的跨国界组织”,也是国际笔会的分会之一(简介参见附件二)。独立中文笔会秉承国际笔会“弘扬文学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宗旨,目前有近200名会员,其中近半数生活在中国大陆,所从事的笔会事务与中国法律并无冲突,本人所承担的笔会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丝毫“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在笔会以外,本人从事的社会活动也只有2000年起就业余担任的《北欧华人通讯》总编辑,这是挪威政府资助的一份为侨居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华人提供当地信息和文化服务的刊物,我作为其总编的作为也根本不可能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综上所述,北京铁路西客站边检站所执行的“上级决定”,完全是无中生有肆意侵权的产物,至今未向本人查证或哪怕询问一句,就如此轻率地剥夺了我作为中国公民一直享有的出入境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个决定还意味着无限期地剥夺了我回国探亲的权利,包括不让我探望已86岁高龄且已半身不遂的母亲,而且很有可能不再给我们母子见面的机会,也未免太不人道,太过残忍。一个连机构名称都不肯告诉被处置者的“上级”,作出连文字都不肯出示给处置者的“决定”,无论于情、于理、于法,都根本站不住脚,显然是一起严重枉法违法的错案。
由于这个据称不是公安机关的“上级”的名称不明,因此我只好向您这个可以明确肯定是公安机关上级的国务院总理投诉,请您责成有关部门按照合法程序处理本案,依法改正拒绝我入境并遣送香港的错误“上级决定”,并赔偿我由此产生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损失。
此致
敬礼
张钰
2007年4月10日
抄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
公安部长周永康

独立中文笔会原秘书长张钰博士
以己及人说人权
张裕
与许多同代上下的人一样, 1989年的“六四屠杀”改变了我的生涯。虽然我当时已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但也因家庭因素有着与难以磨灭的经历,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感同身受,影响至今。这家庭因素就是先父当年的入狱与获释。
先父张钟是1941年就加入过中共的“老干部”,80年代初“离休”,在家专心研究中共早期历史,发表了一些相关考证文章。1989年9月,他突然被武汉市公安局抄家后带走,据称是涉嫌给中共高层写了一些“严重政治错误”的信(后来知道是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人的理论和实践),被“收容审查”。我母亲当时也早已离休,不知案情,托了亲友打听,一直不得要领,有说案情严重得“通了天”,属于不得打听的“国家机密”。
我当时在瑞典留学和工作已近八年,与父母只是一月一信。他们当时舍不得装电话,母亲的信中不提父亲被捕,只说他忙于写作,因此当我从亲戚那里听说此事,已过去了近三个月。我只好托有电话的亲戚找到母亲,得知她除了打听到上述一点情况以外,只根据公安局的要求托带过冬衣和钱,再也不知如何是好。我提出要在国外公开呼吁此事,因为根据当时法规,先父本不应属于“收容审查”的对象(有流窜作案嫌疑的人,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来历不明者),且“收审” 最高时限也不得超过三个月,如果改为拘留和逮捕,也不应三个月仍不通知家属,当局显然是知法犯法,难以对它们再报希望。母亲坚决反对,说是怕父亲更遭报复。于是我答应只给国内各级领导人和部门写信,再等当局三个月的反应时间。我共发了30多封信,上至党总书记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下至武汉市公检法各机关,通过使馆转交,内容大同小异,无非询问父亲现状和关押依据,说明我所知父亲经历和年老体弱,请有关当局依法释放他,即使已进入司法程序不是违法关押,也应该允许他“保外就医”或“取保候审”。一个多月以后,武汉市检察院回信通知我母亲,说是收到我的询问信,但此案目前仍属武汉市公安局处理,与检察院无关,如果该院受理此案,自会及时通知。除此之外,再无其它回音。
三个月后的1990年3月底,我对母亲表示,检察院既然知道此案而仍与此无关,自然是未批准逮捕,无论是“收容审查”或“拘留”到半年也大大超过时限,其它有关部门对我的投诉没有反应,可以证明当局因违法关押而无言以对;我们对当局已算仁至义尽,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助,否则也没有其它办法。母亲说最好还是不要公开造舆论,先私下求助一些有影响的国际机构。于是,我就给“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写信,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其总部的回信,说是已决定接受我父亲的个案,并交瑞典和法国的两个小组专门关注和处理,不久两个小组分别与我联系,问了一些相关情况,说是将动员会员向包括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各方面去信呼吁释放。
5月中旬,瑞典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人士到当时在斯市城内的使馆门前示威,纪念北京学生绝食抗议一周年,我也去了。其间,大使馆一参赞夫人(刚好认识我并看过我的投诉信)要乘车离开,有些示威者上前向她宣讲当局的镇压罪过,她反驳后争论起来,我走过去时正好听到她说“无论如何,你们这样反党反政府的行动也是错误的。”我接上话说:“您错了,不是我们老百姓要反对贵党和政府,而是贵党和政府镇压我们老百姓。您知道我父亲的案子,他可是所谓‘离休干部’,至多也不过是写信批评了贵党领导,贵党就把他抓起来关了8个月还不放,完全违反了贵党和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您怎么能怪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反对贵党和政府的这类违法镇压行动呢?”她哑口无言,但她的司机帮腔说:“你父亲肯定是老反革命,抓起来活该!”于是激起了众怒,骂声四起。参赞夫人制止了司机争吵,开车离开了。
有位新华社记者一直在路边观看示威,这时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有认识他的人介绍说我是在皇家工学院工作的博士后,父亲是“老革命”,只因给中央写信就被警察抓去至今不放。他就过来要我自己再具体谈一下,听完后表示,如果确如我所说,很可能是一冤错案件,他可以写一内参给有关方面,请他们尽快调查处理此案,无论如何象这样不说明理由而无限期的关押显然是不当的。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让我把原来写的材料寄给他一份,我回家后就办了。半个月后是“六四”一周年,我去市中心参加周年祭活动,又碰见那位记者,他说已把我父亲的案子写入内参,几天前刚递交上去了,或许在一两个月内能有消息。另外,我也碰到“国际特赦”负责我父亲案子的小组负责人,她说一个多星期前已发出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
6月下旬,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当天公安局来找她,首次让她和我妹妹等三亲属去看守所见先父,并让她们劝说他认错,只要认了就可以立即释放。她们就去劝了,并说我也是同样的意见,但我父亲仍然拒绝。不过,在我父亲离开后,在场的负责人对我母亲说,他们觉得先父的问题不很严重,仍决定释放,不过这案子是“上面”交办的,还必须经过上报审批,估计需要十天半月就可以结案放人。会面九天后的七月上旬,我父亲就被释放了,只是带了一个有“尾巴”的结论:“有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但罪行较轻,免予处理。”(大意如此)
父亲出狱后说,他被“收审”的前三月常被提审,但他什么也不认。89年12月,检察院去人提审一次后,再就没有任何提审了,估计是检察院驳回了此案,因此他预料最多就是可能由公安以“反革命宣传煽动”判他劳教三年。看守所里不让家属探望,条件又很差,他还传染上了乙型肝炎,因此他还不时要求快点判他(因为同一看守所中被“收审”时间最长者已达七年!),当局一直不理他的要求。90年6月下旬,看守所指导员找他“谈判”,说是只要他“认错”就可以立即放他,如果他不相信,甚至可立下字据,签名盖章。父亲说不能接受这种“交易”,不能为释放就承认自己没干的事。于是又让他见母亲等,但他也不听劝,没想到结果还是放了。
我们估计,这个结果是那位记者和人权组织两方面努力所致——“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的呼吁形成外压,使要面子的中央领导人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而记者内参的提醒显然能起催化作用,使此案得以迅速结案,否则释放程序可能要缓慢得多。当我对那位记者表示感谢时,他谦虚地说只是尽了一个记者应尽的义务而已,正象“国际特赦”的朋友们说他们只是尽了人权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一样。
令人遗憾和感伤的是,先父还是被释放得晚了两、三个月——他在90年夏天因看守所里流行的乙型肝炎感染,出狱后一直没法治愈,时好是坏,拖到96年初,终因“肝昏迷”引起“脑中毒”不治而逝,成了当局“以言治罪”和“六四镇压”的又一牺牲品。
也正是基于先父因“六四镇压” 而“因言获罪”的入狱与获释,我深深体会到人权运动的必要和有效,因此从那时起先后加入了国际特赦、纽约科学院、国际笔会等国际人权组织,近年来主要参与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事务,特别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希望能象别人帮助曾是“狱中作家”的先父那样,我也能帮助与他类似的“因言获罪”者。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有关当局近来倒行逆施,居然将我参加这类活动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在我去年2月回国探亲到北京入境时,边境检查站不经任何程序,未办任何手续,不问不查不答不理,只以不明机构的口头决定,将我这个25年多来一直来去自由的中国公民遣返,实在荒唐透顶。有关当局一直不与我本人直接打交道,不但不理睬我对拒绝入境的先后向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申诉(见附录),而且在今年一月我从香港返回瑞典飞到北京机场转机时把我强行扣留并“遣返”香港,边检承认我的中国护照合法但声称只在国外才能有效使用,更在今年四月连香港也拒绝我入境了,甚至还声称将来可能连台湾也不让我去了——因为现在两岸关系正“走向统一”。尤其可恶的是,有关当局近两年来还不时骚扰和惊吓对我的近况毫不了解的家人和亲戚,完全是本末倒置乱株连。
当局近年来一直大力鼓吹“和谐社会”,但对于包括我家在内的很多普通中国人而言,显然已沦为假话。我母亲已高龄87岁,几年前因中风而半身不遂,近年来又不时因病住院,而我连隔一两探望一次的机会都被当局给“和谐”得没有了。这也更显示了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仍然任重道远,还有待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了大家也为我们自己。
2007年6月3日一稿,2008年10月31日修改。
【张钰简历】
张钰,常用笔名张裕,男,汉族, 1952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务农,1970至1974年在湖北省化工厂当工人,1977年毕业于武汉化工学院,1981年底到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留学,1987年获工科博士学位,此后留在该校从事科研工作至今,其间于1991年至1993年曾应西班牙教育和科技部邀请到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作访问学者。1990年参加“国际特赦”组织,业余创办《北欧华人》月报。1998年参加纽约科学院(科学家人权组织)。2000年起担任《北欧华人通讯》杂志总编辑。2002年加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2004年起担任该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2005年10月至2008年6月担任该笔会秘书长;2004年起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参加了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四届年会,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两届双年会,以及2007年2月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