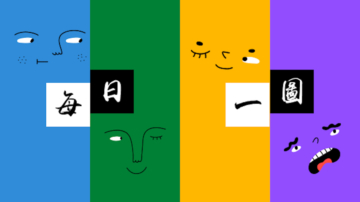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2月22日讯】7月24日,因民企建龙集团参股重组国企通钢集团,吉林省通化市爆发骚乱,愤怒的通钢工人先将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扣为人质,继而毒打致死,直至政府屈服,先由通化电视台反复播放公告,声称“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后由吉林省国资委下发正式文件,发誓“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通钢工人听到官府屈服的消息后,才逐渐散去,事态得以平息。
这意味着什么呢?恐怕白吃都能明白。
政府是告诉弱势群体,政府吃硬不吃软,不来真格的,不打死人闹出大乱子来,则无论尔等要求是否合理,政府都绝不会理睬。官府只懂暴力一门语言,只有它才是百姓和官府交流的唯一工具,不是政府动用暴力迫使百姓屈服,便是百姓动用暴力迫使官府屈服,“中间道路是木有的”!
不仅如此,官府的屈服还未必靠得住。君不见同一个吉林国资委,在骚乱高潮时可以宣布“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但等骚乱平息后,27日便发布消息称,“该事件是极少数担心既得利益和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一起严重的群访事件”。连白吃都知道,但凡政府使用这“极少数人”的阴森森话语,那就等于是为事件定了“反革命暴乱”的性,接之而来的便是暴力镇压。待到枪打出头鸟之后,谁还敢再记得国资委当初“永不翻案”的神圣誓言?到时候政府想怎么办还不是该怎么办,无组织无器械无训练的暴民的自发暴力,岂是有组织的政府暴力的对手?于是我党又成功地摆平了一桩骚乱事件。
但问题是:这能是治国之道么?朝野之间的“对话”只能是暴力语言,这算是什么土匪国家?除了秦朝那个短短的时代,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这么烂污过?
无论古今中外,哪怕是所谓“封建皇朝”也罢,官府好歹还在民事冲突中扮演居中裁判或调停的第三者。当年林则徐处理云南回汉互杀事件,就曾反对某些官员提出的“护汉杀回”,主张“只分良莠,不辨汉回”,并在奏折中强调,处理时一定要使回汉双方都觉得官府没有偏袒一方。这就是传统社会处理民间族群冲突采取的典型立场──不偏不倚,秉公行事。
即使是百姓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仍然可有朝廷作为超脱的第三者出来裁判。着名的杨乃武案件被平反,大批高级地方官被惩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国时代“民告官”胜诉的案例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是官僚社会,但过去的官僚未必都是大富豪,治下的百姓未必是其雇员或是他的三亲六戚的雇员。
而今我党却造出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其他国家也从未见过的独一无二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再也不扮演第三者,而是成了不折不扣的资方代理人,劳资矛盾也就是官民矛盾,中国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本家的乐园,不但是外国资本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萧功秦教授在《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一文中说: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3000万的矿山,你100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我知道的情况可比他说的严重得多,哪有什么“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的好事?我原来在的那家厂子“改制”,从头到尾工人毫无发言权,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
在《闲话“朱镕基神话”》中,我还严厉批评了主持“改制”的朱镕基,告诉政客们不能把国家当成企业经营。我给朱的定谳是:
“他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经济动物,不是个国务家而是个企业家,可担任的最高职务便是计委主任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第一,朱没有尽己所能减轻人民的苦痛,他根本也就不关心人民死活,因为钱迷心窍,毫无必要地制造并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第二,在转型过程中,朱最大限度地默许、纵容甚至推动了社会不公的出现。老朱确实推动中国实行了私有化,可惜是烂污私有化。中国也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可惜那是类似南美的烂污资本主义,后患无穷。老马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恰是中国恶性走资的最逼真写照。”
朱镕基和现在的当道者们的区别,只在于朱是个所谓“清官”,自己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地坑害百姓,属于“自发的”资本家的护院家丁,而现在的当道者则是“自觉的”资本家打手,毫不含糊地自觉捍卫资本家利益,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枪杆子。我党的施政目标,就是千方百计维护现有社会结构,不容许任何人改变,力图防患于未然,在骚乱爆发前消灭一切“事故苗子”,在事后毫不留情地镇压之,永远只会把一切动乱当成是“境外敌对势力”或是“一小撮阶级敌人”颠覆中共政权的阴谋,绝无勇气承认那是社会弊病乃至社会危机的表现。社会上之所以出现“群体事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我党罔顾弱势群体的利益,直接就把他们视若无物。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可能正常表达自己意愿,通过合法渠道与政府(也就是资方代理人)谈判,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人家给逼得无路可走,忍无可忍,最后当然只能诉诸暴力。因此,说到底,我党才是当今中国社会上最大的动乱苗子与震源。
就拿通钢那规模如此之大的骚乱来说吧。我不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何,也不知道陈国军是否无辜受害的牺牲品,我甚至能同意,通钢重组后,效益可能会较前有大幅度提升,但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我知道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重工业集团,它的产权重组必然要涉及到大量工人的基本福利乃至生机。因此,工人当然有权利过问厂子前途,当然有足够权利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如果在西方,哪怕是国企也罢,工会都可以代工人出头,与资方谈判,如果结果不满意,还可以举行罢工,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中国那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能享受类似权利,在厂方作出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决定时有一定发言权,那又岂会被“极少数人”煽动起来,大规模犯罪?这乱子不是我党酿造的,还能赖到谁的头上去?
总而言之,中国国情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作为资方代理集团,我党似乎吃定了弱势集团,认定它是一头可以永远靠暴力摁住的饿狼,奉行的是“棒头出孝子,枪下出顺民”的“枪杆子里面保政权”哲学。百姓表示自己正当诉求的一切和平方式都被铁腕禁止,朝野双方唯一的“对话”方式便是暴力,这就必然导致“官逼民反”,最后逼得弱势集团使用官方唯一能听懂的语言来“说服”官方。
这该是何等背时恐怖的景象?已有文明史几千年的中国人,而今的统治集团怎么会如此彻底丧失政治智慧,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可惜这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无论在哪个方向,我党都在奉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而且还天才地、创造性地将其发展为“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唯一形式”。无论是对付汉族普罗大众,还是对付边疆少数民族,我党都只会用这门“语言”与对方“谈判”。前段发生在新疆的暴乱,论本质与通钢事件并无差别,我党的应对也一模一样:通钢“群体事件”是极少数人旨在颠覆政权的破坏捣乱,而维族或藏族的闹事则是旨在“分裂国家”的“恐怖主义犯罪”。这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官逼民反,害得人家原来不想颠覆的也要颠覆了,不想独立分裂的也要分裂独立了。《廿四史》上白痴君王不罕见,如此白痴的统治者倒也少见。
我党似乎正按“放台独,拖藏独,灭疆独” 的国策行事,准备拖死只追求真正自治、愿意与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达赖喇嘛,换上以暴力追求西藏独立的“藏青帮”,把同样追求高度自治、愿意与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热比娅老太太等人打成本拉登式的回教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此策当然可以苟安于一时,但若我党发生内讧,或是碰上了重大天灾人祸,则神州大地一定会化为修罗场。
当然这不在我党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家最后是否会分裂,甚至也不是政权最终是否会被推翻,而是确保统治新疆、西藏、内地的庞大的资本家集团如何在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实现前提当然是持续剥夺弱势集团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为此,他们当然不会恩赐给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权,也绝不会将公民的基本权利恩赐给内地普罗大众,只会反复捏造“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别有用心”之类老掉牙的罪名,以此作为使用暴力的藉口,“雄辩地”“说服”各族百姓,只要这些蠢动的饿狼能在自己生前给牢牢摁住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我为何要在去年年底预言“明年可能是个骚乱年”,看来这预言将逐年兑现下去,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这意味着什么呢?恐怕白吃都能明白。
政府是告诉弱势群体,政府吃硬不吃软,不来真格的,不打死人闹出大乱子来,则无论尔等要求是否合理,政府都绝不会理睬。官府只懂暴力一门语言,只有它才是百姓和官府交流的唯一工具,不是政府动用暴力迫使百姓屈服,便是百姓动用暴力迫使官府屈服,“中间道路是木有的”!
不仅如此,官府的屈服还未必靠得住。君不见同一个吉林国资委,在骚乱高潮时可以宣布“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但等骚乱平息后,27日便发布消息称,“该事件是极少数担心既得利益和别有用心者制造的一起严重的群访事件”。连白吃都知道,但凡政府使用这“极少数人”的阴森森话语,那就等于是为事件定了“反革命暴乱”的性,接之而来的便是暴力镇压。待到枪打出头鸟之后,谁还敢再记得国资委当初“永不翻案”的神圣誓言?到时候政府想怎么办还不是该怎么办,无组织无器械无训练的暴民的自发暴力,岂是有组织的政府暴力的对手?于是我党又成功地摆平了一桩骚乱事件。
但问题是:这能是治国之道么?朝野之间的“对话”只能是暴力语言,这算是什么土匪国家?除了秦朝那个短短的时代,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这么烂污过?
无论古今中外,哪怕是所谓“封建皇朝”也罢,官府好歹还在民事冲突中扮演居中裁判或调停的第三者。当年林则徐处理云南回汉互杀事件,就曾反对某些官员提出的“护汉杀回”,主张“只分良莠,不辨汉回”,并在奏折中强调,处理时一定要使回汉双方都觉得官府没有偏袒一方。这就是传统社会处理民间族群冲突采取的典型立场──不偏不倚,秉公行事。
即使是百姓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仍然可有朝廷作为超脱的第三者出来裁判。着名的杨乃武案件被平反,大批高级地方官被惩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国时代“民告官”胜诉的案例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是官僚社会,但过去的官僚未必都是大富豪,治下的百姓未必是其雇员或是他的三亲六戚的雇员。
而今我党却造出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其他国家也从未见过的独一无二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再也不扮演第三者,而是成了不折不扣的资方代理人,劳资矛盾也就是官民矛盾,中国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本家的乐园,不但是外国资本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萧功秦教授在《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一文中说: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3000万的矿山,你100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我知道的情况可比他说的严重得多,哪有什么“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的好事?我原来在的那家厂子“改制”,从头到尾工人毫无发言权,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
在《闲话“朱镕基神话”》中,我还严厉批评了主持“改制”的朱镕基,告诉政客们不能把国家当成企业经营。我给朱的定谳是:
“他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经济动物,不是个国务家而是个企业家,可担任的最高职务便是计委主任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第一,朱没有尽己所能减轻人民的苦痛,他根本也就不关心人民死活,因为钱迷心窍,毫无必要地制造并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第二,在转型过程中,朱最大限度地默许、纵容甚至推动了社会不公的出现。老朱确实推动中国实行了私有化,可惜是烂污私有化。中国也确实进入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可惜那是类似南美的烂污资本主义,后患无穷。老马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恰是中国恶性走资的最逼真写照。”
朱镕基和现在的当道者们的区别,只在于朱是个所谓“清官”,自己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地坑害百姓,属于“自发的”资本家的护院家丁,而现在的当道者则是“自觉的”资本家打手,毫不含糊地自觉捍卫资本家利益,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枪杆子。我党的施政目标,就是千方百计维护现有社会结构,不容许任何人改变,力图防患于未然,在骚乱爆发前消灭一切“事故苗子”,在事后毫不留情地镇压之,永远只会把一切动乱当成是“境外敌对势力”或是“一小撮阶级敌人”颠覆中共政权的阴谋,绝无勇气承认那是社会弊病乃至社会危机的表现。社会上之所以出现“群体事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我党罔顾弱势群体的利益,直接就把他们视若无物。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可能正常表达自己意愿,通过合法渠道与政府(也就是资方代理人)谈判,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人家给逼得无路可走,忍无可忍,最后当然只能诉诸暴力。因此,说到底,我党才是当今中国社会上最大的动乱苗子与震源。
就拿通钢那规模如此之大的骚乱来说吧。我不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何,也不知道陈国军是否无辜受害的牺牲品,我甚至能同意,通钢重组后,效益可能会较前有大幅度提升,但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我知道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重工业集团,它的产权重组必然要涉及到大量工人的基本福利乃至生机。因此,工人当然有权利过问厂子前途,当然有足够权利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如果在西方,哪怕是国企也罢,工会都可以代工人出头,与资方谈判,如果结果不满意,还可以举行罢工,直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中国那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能享受类似权利,在厂方作出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决定时有一定发言权,那又岂会被“极少数人”煽动起来,大规模犯罪?这乱子不是我党酿造的,还能赖到谁的头上去?
总而言之,中国国情最令人担忧的就是:作为资方代理集团,我党似乎吃定了弱势集团,认定它是一头可以永远靠暴力摁住的饿狼,奉行的是“棒头出孝子,枪下出顺民”的“枪杆子里面保政权”哲学。百姓表示自己正当诉求的一切和平方式都被铁腕禁止,朝野双方唯一的“对话”方式便是暴力,这就必然导致“官逼民反”,最后逼得弱势集团使用官方唯一能听懂的语言来“说服”官方。
这该是何等背时恐怖的景象?已有文明史几千年的中国人,而今的统治集团怎么会如此彻底丧失政治智慧,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可惜这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无论在哪个方向,我党都在奉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而且还天才地、创造性地将其发展为“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唯一形式”。无论是对付汉族普罗大众,还是对付边疆少数民族,我党都只会用这门“语言”与对方“谈判”。前段发生在新疆的暴乱,论本质与通钢事件并无差别,我党的应对也一模一样:通钢“群体事件”是极少数人旨在颠覆政权的破坏捣乱,而维族或藏族的闹事则是旨在“分裂国家”的“恐怖主义犯罪”。这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官逼民反,害得人家原来不想颠覆的也要颠覆了,不想独立分裂的也要分裂独立了。《廿四史》上白痴君王不罕见,如此白痴的统治者倒也少见。
我党似乎正按“放台独,拖藏独,灭疆独” 的国策行事,准备拖死只追求真正自治、愿意与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达赖喇嘛,换上以暴力追求西藏独立的“藏青帮”,把同样追求高度自治、愿意与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热比娅老太太等人打成本拉登式的回教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此策当然可以苟安于一时,但若我党发生内讧,或是碰上了重大天灾人祸,则神州大地一定会化为修罗场。
当然这不在我党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家最后是否会分裂,甚至也不是政权最终是否会被推翻,而是确保统治新疆、西藏、内地的庞大的资本家集团如何在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实现前提当然是持续剥夺弱势集团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为此,他们当然不会恩赐给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权,也绝不会将公民的基本权利恩赐给内地普罗大众,只会反复捏造“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别有用心”之类老掉牙的罪名,以此作为使用暴力的藉口,“雄辩地”“说服”各族百姓,只要这些蠢动的饿狼能在自己生前给牢牢摁住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我为何要在去年年底预言“明年可能是个骚乱年”,看来这预言将逐年兑现下去,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