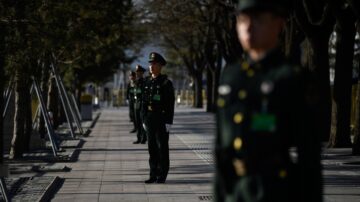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讯】【导读】这是一篇见证大凉山彝族人民1949年后的凄惨命运,和中共对大凉山彝族人民所犯罪行的文章。作者三度滞留大凉山,见证彝族人的沉重苦难。读后感慨,刊出分享: 没有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才会有中国汉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内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可言……
(接上期)二十六岁 “凉山月饼”拯救过我
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前夕,时任中共南充县委书纪的李家骥曾指着我的额头说:“你张先痴如果不当右派分子,我这个南充县就再也找不到右派分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后,当中共南充县委下达红头文件宣布:“张先痴同志原划右派属扩大化的结果,应予改正。”这份档案读罢,南充县就当真没有一个右派份子了。所以那位李书记的“英明论断”似乎也有正确的方面,纵观全国,55万右派中,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无几的那么几个,但中共中央对数学不感兴趣,仍然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至于扩大到什么程度,中央文件没有说,我只好佯装不知。
不过当李家骥书记作为党的化身作出那个判断时,张先痴得到的是极右份子的称号,享受的是右派分子顶尖级的处分: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进谈虎色变的劳改队了,该张先痴当年在反右运动时处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班。

许多彝族家庭一直为生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网路图片)
1958年3月,南充地区某批送劳教的右派份子在冲锋枪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转运站,几天后便转运到自贡市,最后跋山涉水步行到云南盐津县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称的山坳。劳教队长命令道,你们将在这里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后从内江开来的火车穿过这条隧道开往昆明。几乎“脱胎换骨”地苦干了一年半以后,才说这条线路设计有误,下马停建。近万名劳教分子的汗水、难以数计的钢材水泥都化为官僚们缴纳的“学费”付诸东流。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正轰轰烈烈地为所谓的三面红旗交纳一笔史无前例的“学费”,交罢学费老百姓便开始饿肚子,直到四千万同胞被剥夺了生存权变成饿死鬼。一直享受着井下重体力劳动的高粮食定量标准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减少粮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场上消声匿迹,饥饿象流行病一样侵入每个劳教分子的肠胃。昔日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有的在打饭时混饭,有的半夜三更到厨房去偷东西吃,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严去作交换。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传说,我们这个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将转移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去修成昆铁路。类似这类人员大规模流动的举措,劳教队的干部们守口如瓶,为了避免这些阶级敌人趁人心惶惶之机捣鬼。正式宣布这个调动的时间,通常是在出发的前夕,这些名为干部实为专政工具一个个使尽全身解数,喋喋不休地“睁起眼睛说瞎话”地宣布:“凉山里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标准比汉族地区高六斤……”恨不得把大凉山乌鸦的羽毛也说成是彩色的。众右派劳教分子刚刚被“阴谋阳谋”的语言魔术愚弄得晕头转向心有馀悸,他们象所有的专政物件一样,唯一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逆来顺受的无奈。反正次日凌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枪实弹地在汽车边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点名报数然后挤进大卡车就别无选择。
久别重逢的凉山,已是满目苍凉,经过所谓的剿灭叛匪,又所谓的民主改革,几乎使每一个家庭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而正在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对传统耕作秩序的粗暴颠覆,使这个原本生产水平不高,仅靠粗茶淡饭维持生计的古老民族的元气大伤,往日的歌声欢笑再也听不见看不到了,这种令我沮丧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到达凉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节,我几乎忘掉了我生平度过的所有的中秋节,而这一个回到大凉山后的中秋节却让我没齿难忘。因为那是大饥荒的年代,我们这群干着挥汗如雨的重体力劳动的劳教分子,每顿饭充其量只能吃个半饱,忍受着饥饿的煎熬。那种年代的人最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便是有关“吃”的新闻,那天有小道消息说,今晚每人将会得到两个中秋月饼。对终日被饥饿困扰着的劳教分子而言,那包裹着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传统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发月饼之前,“管教”干事何体寿集合全队劳教份子“训话”(请注意这个只适用于专政单位特殊辞汇的含金量)说:“虽然你们负罪在身,国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给你们每人配给了两个月饼,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讲话,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着大声问道:“张先痴来了没有?”一贯将他们这类信口雌黄的假话视作耳边风的我,正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裹叶子烟,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在这里”,听到我的回答,这位“训话”者简直象饿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门接着说:“这个月饼不准发给反改造分子张先痴!”自从出现了饥荒,共产党对劳教分子的奖惩就新增了一个手段,如奖励二两饭或者扣掉两个月饼都能给无产阶级专政助一臂之力。我认为就凭这一点便应了毛泽东那句颠扑不破的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剥夺吃饭权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

四川大凉山深处(网路图片)
当晚,除我以外,全队的劳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钱买下了两个所谓的月饼。我通过“友情赞助”品尝了这个玩意,它是用大凉山特产的荞麦面合着糖精水烤制而成。只有在荒诞的毛泽东时代,才可能用这种粗制烂造的东西去败坏中秋月饼的名声。这种所谓月饼除了它的外观是圆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点传统月饼的特征。幸亏这假冒伪劣的月饼是以政府的名义配发的,如果是我张先痴制作的,肯定会在我日后的判决书上增加一条罪行说:“张犯竟敢用劣质月饼来丑化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云云。
这难道就是我重返凉山的“见面礼”吗?它可是我魂牵梦绕的一块土地啊,这里是我踏上充满荆棘的文学之路的出发点,她的人民珍惜亲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们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统治者用打碎奴隶镣铐的神圣名义、却用血腥的手段,给人民戴上了更残酷的僚铐。狭隘自私的暴君对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夺得的权力,征服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连两个劣质月饼都可以当作武器,这个黔驴技穷的执政党,在它败坏了月饼名声的同时,也正在不遗馀力的败坏着中华民族的名声,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为气候土壤和耕作习惯的关系,大凉山基本不种水稻,他们最大宗的农产品是洋芋和一种名叫“圆根”的萝卜,如果把这两种块根作物当作公粮交给了政府,还不说它们易于腐烂难于存贮,单凭它需要占用的库房面积就不知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切因素综合的结果是,吃粗粮的凉山地区在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人比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西部平坝地区还少得多。而在连续三年大饥荒中最为饥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这个以粗粮为主食的贫困山区度过。我这个冒名木直南楼的假彝胞竟然也从中受益。
这事情说来话长,历史上彝族的民风就是有饭大家吃,你走进任何一个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礼遇。很可能从所谓的“自然灾害”到来之后,粮食的依人定粮和稀缺改变了他们这个传统习惯。他们出门时也要用布口袋装上两三个直径约十五、六公分的干粮饼子,大多是用玉米和着洋芋块蒸成。既然中秋节发的荞面饼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饼,彝胞们装在布袋里的干粮饼子,我将它称为“凉山月饼”也决非溢美之词。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劳教中队是一个隧道中队。在凉山,这个中队担负的任务是打通一条根据彝族地名而取的尔普地隧道,全长五百多米。所有的铁路动工之前,都必须先修一条简易公路,以便运送水泥炸药钢材木材这些铁路建设中必须消耗的物资,还得加上修路人员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修这条便道时,正是所谓大跃进的高潮期,一个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几十方的牛皮喜报频传,结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对这些假大空提出质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论处。我们这个中队以跃进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桥墩,喜报还没送到支队部,桥墩却已经垮塌,这类笑话层出不穷。
这条假大空公路便道载重汽车爬不上来,但人在上面行走则比那些崎岖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终点是一个名叫两河口的区政府所在地,那里是通有等级公路的集镇,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归来的集散之处。我们搭建在尔普地隧道附近的简易工棚,也成为彝胞们来来往往的必经之地,更妙的是这必经之地即非中队部门口,也不在劳教分子宿舍的对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后,这就既远离了监管人员的所谓“革命警惕性”的监视,又避开了分化后的劳教积极分子相互监督的杀伤力,这就为我的“自由活动”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时安排提供了“天时”;我初通的彝语是“人和”的桥梁。试想想,中国人在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个祖传的“成功三要素”以后还有办不好的事吗?
饥荒中不少劳教份子患上了水肿病,工程进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却仍在干部监督下照常周转。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们全天饥饿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边,耐心地等待过路彝胞的到来。见到来者后,我首先微笑着用彝语问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语言中,彝语这种直奔生活主题的问好的方式可称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乐吗?听到我这句比较地道的彝语问话,他们先是一脸惊愕然后微笑点头回答:“格沙”(快乐)。这时我会从他肩上挂着的布口袋的外观形状上,判断里面是否装有“凉山月饼”,这沉重的象一个微缩铁饼的东西,大体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圆周,绝大部分彝胞出门都会自备干粮,因为上饭馆既需粮票又需现金,这两种东西他们都极为稀缺。我还会进一步问:“偶分脚脚?”(“有‘凉山月饼吗’?”)这时他们会下意识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饿得心慌的我赶紧问:“乌乌?”(卖吗?)彝族人没有卖食物的习惯,他们会取出“凉山月饼”多数情况是分半个递给我,有时是给一整个,我也会给一元钱给他,多数情况对方都不要,有时是十分感谢地收下。若要问这“凉山月饼”究竟多大,我只能这样说,一个约等于我们一天的口粮。正是这些慷慨的“凉山月饼”,帮助我度过了饥肠辘辘的1960年,我避开了水肿病对身体的摧残,健康地存活至今,“凉山月饼”功不可没。
大约是1961年初,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为中共上交的“学费”,我们又奉命搬迁到旺苍县快活场,修筑一条广元至旺苍的铁路支线,九个月后我越狱逃跑,捕回后法院在判决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处张犯先痴有期徒刑十八年”。对法律条文一无所知的我,为了证明自己并无智力障碍,强烈抗议这一无理判决,索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读究竟,见其第十一条赫然在目:“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其实我从来远离国境县一千公里以上,怎样偷越?然而上诉按惯例驳回。
不过,我的内心却很清楚,此番逃跑确与“凉山月饼”不无关系。
(待续)
原标题:大凉山咏叹调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三期
(接上期)二十六岁 “凉山月饼”拯救过我
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前夕,时任中共南充县委书纪的李家骥曾指着我的额头说:“你张先痴如果不当右派分子,我这个南充县就再也找不到右派分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后,当中共南充县委下达红头文件宣布:“张先痴同志原划右派属扩大化的结果,应予改正。”这份档案读罢,南充县就当真没有一个右派份子了。所以那位李书记的“英明论断”似乎也有正确的方面,纵观全国,55万右派中,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无几的那么几个,但中共中央对数学不感兴趣,仍然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至于扩大到什么程度,中央文件没有说,我只好佯装不知。
不过当李家骥书记作为党的化身作出那个判断时,张先痴得到的是极右份子的称号,享受的是右派分子顶尖级的处分: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进谈虎色变的劳改队了,该张先痴当年在反右运动时处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班。

许多彝族家庭一直为生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网路图片)
1958年3月,南充地区某批送劳教的右派份子在冲锋枪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转运站,几天后便转运到自贡市,最后跋山涉水步行到云南盐津县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称的山坳。劳教队长命令道,你们将在这里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后从内江开来的火车穿过这条隧道开往昆明。几乎“脱胎换骨”地苦干了一年半以后,才说这条线路设计有误,下马停建。近万名劳教分子的汗水、难以数计的钢材水泥都化为官僚们缴纳的“学费”付诸东流。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正轰轰烈烈地为所谓的三面红旗交纳一笔史无前例的“学费”,交罢学费老百姓便开始饿肚子,直到四千万同胞被剥夺了生存权变成饿死鬼。一直享受着井下重体力劳动的高粮食定量标准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减少粮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场上消声匿迹,饥饿象流行病一样侵入每个劳教分子的肠胃。昔日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有的在打饭时混饭,有的半夜三更到厨房去偷东西吃,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严去作交换。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传说,我们这个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将转移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去修成昆铁路。类似这类人员大规模流动的举措,劳教队的干部们守口如瓶,为了避免这些阶级敌人趁人心惶惶之机捣鬼。正式宣布这个调动的时间,通常是在出发的前夕,这些名为干部实为专政工具一个个使尽全身解数,喋喋不休地“睁起眼睛说瞎话”地宣布:“凉山里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标准比汉族地区高六斤……”恨不得把大凉山乌鸦的羽毛也说成是彩色的。众右派劳教分子刚刚被“阴谋阳谋”的语言魔术愚弄得晕头转向心有馀悸,他们象所有的专政物件一样,唯一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逆来顺受的无奈。反正次日凌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枪实弹地在汽车边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点名报数然后挤进大卡车就别无选择。
久别重逢的凉山,已是满目苍凉,经过所谓的剿灭叛匪,又所谓的民主改革,几乎使每一个家庭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而正在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对传统耕作秩序的粗暴颠覆,使这个原本生产水平不高,仅靠粗茶淡饭维持生计的古老民族的元气大伤,往日的歌声欢笑再也听不见看不到了,这种令我沮丧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到达凉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节,我几乎忘掉了我生平度过的所有的中秋节,而这一个回到大凉山后的中秋节却让我没齿难忘。因为那是大饥荒的年代,我们这群干着挥汗如雨的重体力劳动的劳教分子,每顿饭充其量只能吃个半饱,忍受着饥饿的煎熬。那种年代的人最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便是有关“吃”的新闻,那天有小道消息说,今晚每人将会得到两个中秋月饼。对终日被饥饿困扰着的劳教分子而言,那包裹着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传统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发月饼之前,“管教”干事何体寿集合全队劳教份子“训话”(请注意这个只适用于专政单位特殊辞汇的含金量)说:“虽然你们负罪在身,国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给你们每人配给了两个月饼,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讲话,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着大声问道:“张先痴来了没有?”一贯将他们这类信口雌黄的假话视作耳边风的我,正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裹叶子烟,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在这里”,听到我的回答,这位“训话”者简直象饿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门接着说:“这个月饼不准发给反改造分子张先痴!”自从出现了饥荒,共产党对劳教分子的奖惩就新增了一个手段,如奖励二两饭或者扣掉两个月饼都能给无产阶级专政助一臂之力。我认为就凭这一点便应了毛泽东那句颠扑不破的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剥夺吃饭权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

四川大凉山深处(网路图片)
当晚,除我以外,全队的劳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钱买下了两个所谓的月饼。我通过“友情赞助”品尝了这个玩意,它是用大凉山特产的荞麦面合着糖精水烤制而成。只有在荒诞的毛泽东时代,才可能用这种粗制烂造的东西去败坏中秋月饼的名声。这种所谓月饼除了它的外观是圆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点传统月饼的特征。幸亏这假冒伪劣的月饼是以政府的名义配发的,如果是我张先痴制作的,肯定会在我日后的判决书上增加一条罪行说:“张犯竟敢用劣质月饼来丑化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云云。
这难道就是我重返凉山的“见面礼”吗?它可是我魂牵梦绕的一块土地啊,这里是我踏上充满荆棘的文学之路的出发点,她的人民珍惜亲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们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统治者用打碎奴隶镣铐的神圣名义、却用血腥的手段,给人民戴上了更残酷的僚铐。狭隘自私的暴君对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夺得的权力,征服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连两个劣质月饼都可以当作武器,这个黔驴技穷的执政党,在它败坏了月饼名声的同时,也正在不遗馀力的败坏着中华民族的名声,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为气候土壤和耕作习惯的关系,大凉山基本不种水稻,他们最大宗的农产品是洋芋和一种名叫“圆根”的萝卜,如果把这两种块根作物当作公粮交给了政府,还不说它们易于腐烂难于存贮,单凭它需要占用的库房面积就不知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切因素综合的结果是,吃粗粮的凉山地区在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人比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西部平坝地区还少得多。而在连续三年大饥荒中最为饥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这个以粗粮为主食的贫困山区度过。我这个冒名木直南楼的假彝胞竟然也从中受益。
这事情说来话长,历史上彝族的民风就是有饭大家吃,你走进任何一个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礼遇。很可能从所谓的“自然灾害”到来之后,粮食的依人定粮和稀缺改变了他们这个传统习惯。他们出门时也要用布口袋装上两三个直径约十五、六公分的干粮饼子,大多是用玉米和着洋芋块蒸成。既然中秋节发的荞面饼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饼,彝胞们装在布袋里的干粮饼子,我将它称为“凉山月饼”也决非溢美之词。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劳教中队是一个隧道中队。在凉山,这个中队担负的任务是打通一条根据彝族地名而取的尔普地隧道,全长五百多米。所有的铁路动工之前,都必须先修一条简易公路,以便运送水泥炸药钢材木材这些铁路建设中必须消耗的物资,还得加上修路人员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修这条便道时,正是所谓大跃进的高潮期,一个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几十方的牛皮喜报频传,结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对这些假大空提出质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论处。我们这个中队以跃进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桥墩,喜报还没送到支队部,桥墩却已经垮塌,这类笑话层出不穷。
这条假大空公路便道载重汽车爬不上来,但人在上面行走则比那些崎岖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终点是一个名叫两河口的区政府所在地,那里是通有等级公路的集镇,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归来的集散之处。我们搭建在尔普地隧道附近的简易工棚,也成为彝胞们来来往往的必经之地,更妙的是这必经之地即非中队部门口,也不在劳教分子宿舍的对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后,这就既远离了监管人员的所谓“革命警惕性”的监视,又避开了分化后的劳教积极分子相互监督的杀伤力,这就为我的“自由活动”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时安排提供了“天时”;我初通的彝语是“人和”的桥梁。试想想,中国人在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个祖传的“成功三要素”以后还有办不好的事吗?
饥荒中不少劳教份子患上了水肿病,工程进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却仍在干部监督下照常周转。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们全天饥饿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边,耐心地等待过路彝胞的到来。见到来者后,我首先微笑着用彝语问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语言中,彝语这种直奔生活主题的问好的方式可称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乐吗?听到我这句比较地道的彝语问话,他们先是一脸惊愕然后微笑点头回答:“格沙”(快乐)。这时我会从他肩上挂着的布口袋的外观形状上,判断里面是否装有“凉山月饼”,这沉重的象一个微缩铁饼的东西,大体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圆周,绝大部分彝胞出门都会自备干粮,因为上饭馆既需粮票又需现金,这两种东西他们都极为稀缺。我还会进一步问:“偶分脚脚?”(“有‘凉山月饼吗’?”)这时他们会下意识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饿得心慌的我赶紧问:“乌乌?”(卖吗?)彝族人没有卖食物的习惯,他们会取出“凉山月饼”多数情况是分半个递给我,有时是给一整个,我也会给一元钱给他,多数情况对方都不要,有时是十分感谢地收下。若要问这“凉山月饼”究竟多大,我只能这样说,一个约等于我们一天的口粮。正是这些慷慨的“凉山月饼”,帮助我度过了饥肠辘辘的1960年,我避开了水肿病对身体的摧残,健康地存活至今,“凉山月饼”功不可没。
大约是1961年初,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为中共上交的“学费”,我们又奉命搬迁到旺苍县快活场,修筑一条广元至旺苍的铁路支线,九个月后我越狱逃跑,捕回后法院在判决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处张犯先痴有期徒刑十八年”。对法律条文一无所知的我,为了证明自己并无智力障碍,强烈抗议这一无理判决,索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读究竟,见其第十一条赫然在目:“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其实我从来远离国境县一千公里以上,怎样偷越?然而上诉按惯例驳回。
不过,我的内心却很清楚,此番逃跑确与“凉山月饼”不无关系。
(待续)
原标题:大凉山咏叹调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二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