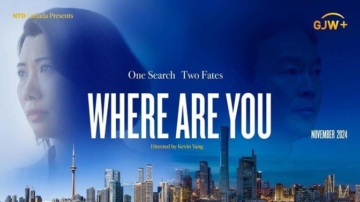【新唐人2016年11月30日讯】 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还没开过,候车亭里,还有两个和我一样晚归的人,都是女人。
一个穿着某酒店黑色工作服的大姐,应该有五十岁左右了吧,岁月的痕迹比较明显,额头上,眼角边,都被光阴的锉刀刻上了细细的皱纹。她似乎很有些倦怠,倚着站牌,无精打采的,一个接一个地打哈欠。

宁静的夜晚(manseok/Pixabay)
另一个年轻些,妆化的很浓,时髦的梨花头染成酒红色,一直在不停的打电话。她说的是方言,我很费劲的听,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只是隐隐感觉到,她是要去见什么人。
车子还没有来,天空中,气流里,马路上,全都冷冷清清,再加上寒风,陡添了几分凄凉。
前面慢慢地滑来了一辆卖麻辣烫的餐车,上面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用竹签穿好的各类荤素食材,旁边支着一口大锅,红红的汤汁正热气腾腾的翻滚着。这是一个中年男子,长着一张苦大仇深的狭长脸。

夜归(LouAnna/Pixabay)
“这破车又晚点了,到现在还没来。”黑衣大姐用四川话对狭长脸男人说。
“N路车最不准时了。”男子说的也是四川话。他们是熟人。
又等了几分钟,N路车终于来了,黑衣大姐抢先一步跨上了车,我尾随其后,年轻女子跟在我后面,叽叽咕咕的,还在跟人通电话。车上没几个人,位置很空,我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子,穿着咖啡色的破旧夹克,脚上的旅游鞋沾满泥痕,早已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脚边还有一个蛇皮袋,里面放着瓦刀𨱍头铁锤等工具,看样子应该是装修工。也不知他今天是否有所获,可以让他满足的随着车轮的滚动奔向属于他的那一盏灯火。

炊烟傍晚的乡村(AdinaVoicu/Pixabay)
我前边的黑衣大姐一坐下就打起了盹,不一会儿,微微的鼾声就飘进了我的耳膜。看得出,她太累了。
车子七拐八拐,拐进了我家附近的那条热闹的小商品街。现在,这条街上的所有店铺都已打烊,只有昏暗的路灯和天上的缺月,一个暗黄,一个清冷,散发着朦胧的光晕。

风雪的夜晚(qimono/Pixabay)
到站后,车还没停稳,我就急不可耐的跳了下去。我的平底波鞋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我,走在寂静的巷子里,影子斜斜的印在墙上,如同一个黑色的幽灵。
——本文经《纪元心语》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李丹
一个穿着某酒店黑色工作服的大姐,应该有五十岁左右了吧,岁月的痕迹比较明显,额头上,眼角边,都被光阴的锉刀刻上了细细的皱纹。她似乎很有些倦怠,倚着站牌,无精打采的,一个接一个地打哈欠。

宁静的夜晚(manseok/Pixabay)
另一个年轻些,妆化的很浓,时髦的梨花头染成酒红色,一直在不停的打电话。她说的是方言,我很费劲的听,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只是隐隐感觉到,她是要去见什么人。
车子还没有来,天空中,气流里,马路上,全都冷冷清清,再加上寒风,陡添了几分凄凉。
前面慢慢地滑来了一辆卖麻辣烫的餐车,上面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用竹签穿好的各类荤素食材,旁边支着一口大锅,红红的汤汁正热气腾腾的翻滚着。这是一个中年男子,长着一张苦大仇深的狭长脸。

夜归(LouAnna/Pixabay)
“这破车又晚点了,到现在还没来。”黑衣大姐用四川话对狭长脸男人说。
“N路车最不准时了。”男子说的也是四川话。他们是熟人。
又等了几分钟,N路车终于来了,黑衣大姐抢先一步跨上了车,我尾随其后,年轻女子跟在我后面,叽叽咕咕的,还在跟人通电话。车上没几个人,位置很空,我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子,穿着咖啡色的破旧夹克,脚上的旅游鞋沾满泥痕,早已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脚边还有一个蛇皮袋,里面放着瓦刀𨱍头铁锤等工具,看样子应该是装修工。也不知他今天是否有所获,可以让他满足的随着车轮的滚动奔向属于他的那一盏灯火。

炊烟傍晚的乡村(AdinaVoicu/Pixabay)
我前边的黑衣大姐一坐下就打起了盹,不一会儿,微微的鼾声就飘进了我的耳膜。看得出,她太累了。
车子七拐八拐,拐进了我家附近的那条热闹的小商品街。现在,这条街上的所有店铺都已打烊,只有昏暗的路灯和天上的缺月,一个暗黄,一个清冷,散发着朦胧的光晕。

风雪的夜晚(qimono/Pixabay)
到站后,车还没停稳,我就急不可耐的跳了下去。我的平底波鞋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我,走在寂静的巷子里,影子斜斜的印在墙上,如同一个黑色的幽灵。
——本文经《纪元心语》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