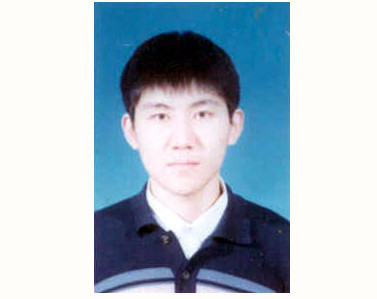“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1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这是瞿延来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的自述。
瞿延来,1977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1997年7月开始接触法轮功,一直到迫害开始,才看完第一遍《转法轮》。
2002年9月30日深夜,瞿延来被上海警方劫持,被非法判刑五年。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期间多次遭受毒打,野蛮灌食造成4次严重胃出血,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
为瞿延来提供辩护的大陆律师郭国汀说:“瞿延来先生是我的第二位法轮功当事人,(他)也是引起我对法轮功极大兴趣的原因,因为他竟能连续绝食绝水780天!直到我正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为止。”
“开始时我一直不相信一个人竟能连续绝食绝水两年多!然而,事实是在这绝食期间,他曾先后四次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抢救四个月。在该绝食期间,他一直拒绝进食,长期被强制灌食。而强制灌食实质上是一种极难忍受的酷行。”至少有约1千名法轮功学员因灌食酷刑致死,郭国汀说。
“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
以下是瞿延来的个人经历自述:
(接上文)
2003年4月下旬,当时中国正遭遇严重的“萨斯”,我当时在提篮桥监狱医院内科,医院决定把内科整个从医院大楼搬走,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篮桥监狱八号监一中队。
4月下旬我被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我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号监三楼,但还住二号病床。
换了病房没几天,一个医生早上巡视病房时,和劳役犯讲,不能让我老这样躺在床上,要给我活动活动筋骨,还说了一句:“我最会整你这样的人了。”
医生巡视病房结束后,劳役犯就经常抓着我的手在病房内跑着拖来拖去,拖完后再把我放在床上,在我身上用力到处乱捏。这回我倒没像以前那样闭上眼睛,而是默默看着他们表演。
其实自从被关押那天起,我心中就有一个信念:无论遇到任何苦难,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都要坚强地忍下去,不能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不管身心被折磨得再痛苦,我都不能靠大喊大叫来发泄!可能我这种无动于衷的表现让他们很泄气,再说这样搞他们也很累,几天过后他们就不这样整我了。
这回住院,护士一个月给我换一次胃管,胃管用橡皮膏固定在鼻子上。时间长了,我发现鼻子疼得厉害,一次护士告诉我,鼻子贴橡皮膏的部分已经溃烂了,又换了一截橡皮膏粘在我没有烂的皮肤上。
静脉输液时,有时一瓶药水快滴完了,劳役犯还没发现,我就提醒他们换药水。可能他们觉得让我长时间的输液会更痛苦,人会受不了,就开始故意把药水滴速调得很慢,本来3瓶药水3、4个小时就能滴完,这回要从早上8、9点钟一直滴到下半夜的3点多,输液过后手臂肿得很粗。这样一直到5月底,输液的速度才重新恢复正常。
2003年6月2日早上,我被劳役犯用轮椅从8号监传染病区推进了医院大楼,这时房间里进来几个人,说是给我开庭。公诉人草草地读了一遍起诉书,上海市普陀区法院给我指定的律师就问我用不用他给辩护;我还没回答,他就直接说拒绝为我辩护,请求退出法庭,就走了。
接着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15分钟后再开庭时,法官宣布判我5年有期徒刑。对我的这次审判就这样荒唐的以最快速度结束了,走了个过场。我本来是和大约10名法轮功学员一同被非法起诉,现在则被改为单独开庭审理,并且开庭时也不通知家人,连法院都没让我去。
7月2日,主管病房的王队长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来看我,他自称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监狱的警察。他拿出了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文件想让我签名,我拒绝了,他就强行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我正式从新收犯监狱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9月13日上午,护士把我的胃管拔掉了,接着董队长用轮椅把我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劳役犯推轮椅)。出了病房,我发现陈建翎等在外面,他们两人把我带出了医院大楼,进了一个布置成会客室的房间。两个我没见过的警察坐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我看到妈妈在一位家乡大法弟子的陪伴下走进来,她们手里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不少东西。妈妈看到我,扑向了轮椅,抱着我痛哭起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家里人都想死我了。警察抓了我也没通知家里,开庭审判也照样没通知家里。直到今年7月2日才收到普陀区法院发来的判决书,9月9日,妈妈在一位大法弟子的陪同下从黑龙江来到了上海,这几天找过普陀区法院、普陀区看守所、青浦新收监。
我才得知一个叫唐敏的普陀区法官威胁我母亲说:“啊!你还打电话哪!抓捕你!监控你!”12日,妈妈找到了提篮桥监狱,打听了门卫值班的警察,才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二中队。
2003年12月6日,护士给我灌食时,发现胃管里流出的液体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给了医生。经过化验,结果是4个+,也就是大出血。住了10天医院,12月15日医院通知一中队把我接回去。
第2天早上,在警察的带领下,犯人用轮椅把我推到了2号监(死刑犯中队),又架着我的胳膊上到了5楼的东部。把我交给了那里的警察和犯人。
死刑犯一进到这里,监狱总医院的医生就会来为他验血,同时在看管犯的逼迫下在器官移植捐献书上签字。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也就是他的器官被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日子。
转眼来死刑犯中队20多天了,我监房的看管犯突然都被换走了。这回换成了4个人来看我。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中有一人是从楼下调上来的,名叫陈家伟,他在楼下负责看管的学员刚刚被转化;另外三人则是本中队的。本中队的这3人刚刚迫使一名从送到楼上严管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他们告诉了我是怎么转化的:“警察用约束带把他铐紧,整天逼他笔直的坐好;每天给他只吃一点点饭,喝一点点水;给他少穿衣服,少盖被子,冻他;还总打他,打完后做好记录给警察看。这样折磨了那个法轮功学员将近一个月,他被迫屈服了。”
2005年3月17日,妈妈又来监狱看我了,这次还是电话接见。20分钟也谈不了什么,妈妈没马上回老家,而是找了个旅店住下。
3月底、4月初又见了我两次,也都是20分钟电话接见。谈话中妈妈告诉我,家人为我聘请郭国汀律师为我申诉,郭律师先后4次申请会见我,被提篮桥监狱无理拒绝。期间上海市政法委28次找郭国汀律师,对他施加压力,但他没有屈服,他对妈妈说“无私才能无畏”,坚持为我伸张正义,并公开发表《百无一用的中国律师》一文。但最终共产党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国汀律师的家,并非法关押他半个月,现郭国汀律师已被迫流亡加拿大。
妈妈还告诉我现在出了本书《九评共产党》,由于有警察监听,妈妈在电话里只说了个大概,就被监听的警察阻止了。
9月1日,我被带去医院体检。因为听说监狱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我就拒绝走路了。警察就命令犯人拖我。从医院检查回来,我没被送回青中,而是进了2楼西部42号监。这个楼面属于维修中队。很快倪永斌来了,他给我上了约束带。上刑具的时候,他笑着和旁边的一个警察说:“腰都这么细了!”我当时瘦得很厉害,用“皮包骨头”形容也不过分。
这回看我的犯人增加到5人,一人总负责,2人值白班,2人值夜班。当时我身上只穿了短袖衬衫和短裤,到了晚上,就被冻得有些发抖了。可是监房外面还有一个鼓风机故意向监房吹风。
(2005年)9月13日上午,经历了种种折磨的我被用轮椅到了六号监。2个犯人看着我。后来又安排了一个犯人曹惠华负责给我做流食、灌食。
一天晚上7点左右,我突然觉得人很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我出了监房,想去厕所大便。监房离厕所有30多米,走了几步路,就觉得人越来越难受,身上内脏器官似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当时那极度的痛苦我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但我却觉得极其的漫长。
瞬间我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脑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我想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苦了、解脱了。人生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人浑浑噩噩的多活几十年又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忙忙碌碌一辈子,就算有幸福、愉快的感受,也只是一时的,人哪有3天好日子过?更何况我还剩下两年的刑期,要继续在狱中受苦。但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要死了,他们精神不得崩溃吗?以后让他们怎么活呀!我又想到了我的师父,我从中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师父给予我太多太多,洗涤了我的心灵,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我还是应该活下来啊。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的背上,当时我一直出冷汗,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在往外面渗水。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出冷汗了,人才恢复过来。
上海的冬天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以下,监房里很冷。由于手长时间裸露在外面,手指的关节处冻出了一个个大口子,肉都往外翻着,还淌血。我没有因此影响炼功,只是从棉被里撕了些棉花出来,粘在开裂淌血的地方。
2006年11月3日,爸爸来看我了。接见前,我身上的约束带被解了下来。这次是宽松接见,我和爸爸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想让爸爸知道监狱又给我上刑了,为我担心,所以没说这事。爸爸告诉我,我大爷和五叔在那一年相继去世。大爷在临死前还找我呢!
12月26日,六大队的马副大队长进了监房和我谈话后,我知道很快我就要离开6号监了,就把自己的棉被给了这里的看管犯,换回了他的旧被子。他在监狱已经7年了,被子都透光了,他说自己晚上睡觉太冷了。当时我的棉袄、棉裤、毛衣、毛裤都送光了,自己只穿着单衣过冬。
2007年9月29日上午,我身上的(约束)绳子被解了下来。我终于出狱,获得自由。
回到家,我开始认真全面的学法炼功。仅仅20天,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将近30斤,以后体重开始平稳缓慢的增加。仅1个月,我的身体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时我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加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
2007年12月初,我可以双盘了,到了12月底,我又达到能够无限制双盘了,也长出了一头浓密黑发(刚回家时我头发稀疏),人也彻底恢复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瞿延来,1977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品学兼优,曾获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数学一等奖。1997年7月开始接触法轮功,一直到迫害开始,才看完第一遍《转法轮》。
2002年9月30日深夜,瞿延来被上海警方劫持,被非法判刑五年。从被绑架的那一刻起,他一直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非法关押。期间多次遭受毒打,野蛮灌食造成4次严重胃出血,几度生命垂危,原本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四十多斤的壮小伙子,被折磨得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
为瞿延来提供辩护的大陆律师郭国汀说:“瞿延来先生是我的第二位法轮功当事人,(他)也是引起我对法轮功极大兴趣的原因,因为他竟能连续绝食绝水780天!直到我正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为止。”
“开始时我一直不相信一个人竟能连续绝食绝水两年多!然而,事实是在这绝食期间,他曾先后四次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抢救四个月。在该绝食期间,他一直拒绝进食,长期被强制灌食。而强制灌食实质上是一种极难忍受的酷行。”至少有约1千名法轮功学员因灌食酷刑致死,郭国汀说。
“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
以下是瞿延来的个人经历自述:
(接上文)
因应“萨斯”换监
2003年4月下旬,当时中国正遭遇严重的“萨斯”,我当时在提篮桥监狱医院内科,医院决定把内科整个从医院大楼搬走,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篮桥监狱八号监一中队。
4月下旬我被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我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号监三楼,但还住二号病床。
换了病房没几天,一个医生早上巡视病房时,和劳役犯讲,不能让我老这样躺在床上,要给我活动活动筋骨,还说了一句:“我最会整你这样的人了。”
医生巡视病房结束后,劳役犯就经常抓着我的手在病房内跑着拖来拖去,拖完后再把我放在床上,在我身上用力到处乱捏。这回我倒没像以前那样闭上眼睛,而是默默看着他们表演。
其实自从被关押那天起,我心中就有一个信念:无论遇到任何苦难,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都要坚强地忍下去,不能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不管身心被折磨得再痛苦,我都不能靠大喊大叫来发泄!可能我这种无动于衷的表现让他们很泄气,再说这样搞他们也很累,几天过后他们就不这样整我了。
这回住院,护士一个月给我换一次胃管,胃管用橡皮膏固定在鼻子上。时间长了,我发现鼻子疼得厉害,一次护士告诉我,鼻子贴橡皮膏的部分已经溃烂了,又换了一截橡皮膏粘在我没有烂的皮肤上。
静脉输液时,有时一瓶药水快滴完了,劳役犯还没发现,我就提醒他们换药水。可能他们觉得让我长时间的输液会更痛苦,人会受不了,就开始故意把药水滴速调得很慢,本来3瓶药水3、4个小时就能滴完,这回要从早上8、9点钟一直滴到下半夜的3点多,输液过后手臂肿得很粗。这样一直到5月底,输液的速度才重新恢复正常。
荒唐的审判
2003年6月2日早上,我被劳役犯用轮椅从8号监传染病区推进了医院大楼,这时房间里进来几个人,说是给我开庭。公诉人草草地读了一遍起诉书,上海市普陀区法院给我指定的律师就问我用不用他给辩护;我还没回答,他就直接说拒绝为我辩护,请求退出法庭,就走了。
接着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15分钟后再开庭时,法官宣布判我5年有期徒刑。对我的这次审判就这样荒唐的以最快速度结束了,走了个过场。我本来是和大约10名法轮功学员一同被非法起诉,现在则被改为单独开庭审理,并且开庭时也不通知家人,连法院都没让我去。
7月2日,主管病房的王队长带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来看我,他自称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监狱的警察。他拿出了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文件想让我签名,我拒绝了,他就强行抓住我的手按了手印,并说我正式从新收犯监狱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母子相见
9月13日上午,护士把我的胃管拔掉了,接着董队长用轮椅把我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劳役犯推轮椅)。出了病房,我发现陈建翎等在外面,他们两人把我带出了医院大楼,进了一个布置成会客室的房间。两个我没见过的警察坐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我看到妈妈在一位家乡大法弟子的陪伴下走进来,她们手里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不少东西。妈妈看到我,扑向了轮椅,抱着我痛哭起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妈妈告诉我,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家里人都想死我了。警察抓了我也没通知家里,开庭审判也照样没通知家里。直到今年7月2日才收到普陀区法院发来的判决书,9月9日,妈妈在一位大法弟子的陪同下从黑龙江来到了上海,这几天找过普陀区法院、普陀区看守所、青浦新收监。
我才得知一个叫唐敏的普陀区法官威胁我母亲说:“啊!你还打电话哪!抓捕你!监控你!”12日,妈妈找到了提篮桥监狱,打听了门卫值班的警察,才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二中队。
换到死刑犯中队
2003年12月6日,护士给我灌食时,发现胃管里流出的液体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给了医生。经过化验,结果是4个+,也就是大出血。住了10天医院,12月15日医院通知一中队把我接回去。
第2天早上,在警察的带领下,犯人用轮椅把我推到了2号监(死刑犯中队),又架着我的胳膊上到了5楼的东部。把我交给了那里的警察和犯人。
死刑犯一进到这里,监狱总医院的医生就会来为他验血,同时在看管犯的逼迫下在器官移植捐献书上签字。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也就是他的器官被移植到病人身上的日子。
转眼来死刑犯中队20多天了,我监房的看管犯突然都被换走了。这回换成了4个人来看我。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中有一人是从楼下调上来的,名叫陈家伟,他在楼下负责看管的学员刚刚被转化;另外三人则是本中队的。本中队的这3人刚刚迫使一名从送到楼上严管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他们告诉了我是怎么转化的:“警察用约束带把他铐紧,整天逼他笔直的坐好;每天给他只吃一点点饭,喝一点点水;给他少穿衣服,少盖被子,冻他;还总打他,打完后做好记录给警察看。这样折磨了那个法轮功学员将近一个月,他被迫屈服了。”
郭国汀律师坚持伸张正义
2005年3月17日,妈妈又来监狱看我了,这次还是电话接见。20分钟也谈不了什么,妈妈没马上回老家,而是找了个旅店住下。
3月底、4月初又见了我两次,也都是20分钟电话接见。谈话中妈妈告诉我,家人为我聘请郭国汀律师为我申诉,郭律师先后4次申请会见我,被提篮桥监狱无理拒绝。期间上海市政法委28次找郭国汀律师,对他施加压力,但他没有屈服,他对妈妈说“无私才能无畏”,坚持为我伸张正义,并公开发表《百无一用的中国律师》一文。但最终共产党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国汀律师的家,并非法关押他半个月,现郭国汀律师已被迫流亡加拿大。
妈妈还告诉我现在出了本书《九评共产党》,由于有警察监听,妈妈在电话里只说了个大概,就被监听的警察阻止了。
9月1日,我被带去医院体检。因为听说监狱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我就拒绝走路了。警察就命令犯人拖我。从医院检查回来,我没被送回青中,而是进了2楼西部42号监。这个楼面属于维修中队。很快倪永斌来了,他给我上了约束带。上刑具的时候,他笑着和旁边的一个警察说:“腰都这么细了!”我当时瘦得很厉害,用“皮包骨头”形容也不过分。
这回看我的犯人增加到5人,一人总负责,2人值白班,2人值夜班。当时我身上只穿了短袖衬衫和短裤,到了晚上,就被冻得有些发抖了。可是监房外面还有一个鼓风机故意向监房吹风。
换到六大队
(2005年)9月13日上午,经历了种种折磨的我被用轮椅到了六号监。2个犯人看着我。后来又安排了一个犯人曹惠华负责给我做流食、灌食。
一天晚上7点左右,我突然觉得人很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我出了监房,想去厕所大便。监房离厕所有30多米,走了几步路,就觉得人越来越难受,身上内脏器官似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当时那极度的痛苦我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一分钟不到,但我却觉得极其的漫长。
瞬间我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脑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我想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苦了、解脱了。人生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人浑浑噩噩的多活几十年又有什么意思啊!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忙忙碌碌一辈子,就算有幸福、愉快的感受,也只是一时的,人哪有3天好日子过?更何况我还剩下两年的刑期,要继续在狱中受苦。但是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要死了,他们精神不得崩溃吗?以后让他们怎么活呀!我又想到了我的师父,我从中都实实在在受益了,师父给予我太多太多,洗涤了我的心灵,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我还是应该活下来啊。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的背上,当时我一直出冷汗,身上所有的汗毛孔都在往外面渗水。过了一段时间,我不出冷汗了,人才恢复过来。
上海的冬天气温也能达到零度以下,监房里很冷。由于手长时间裸露在外面,手指的关节处冻出了一个个大口子,肉都往外翻着,还淌血。我没有因此影响炼功,只是从棉被里撕了些棉花出来,粘在开裂淌血的地方。
2006年11月3日,爸爸来看我了。接见前,我身上的约束带被解了下来。这次是宽松接见,我和爸爸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想让爸爸知道监狱又给我上刑了,为我担心,所以没说这事。爸爸告诉我,我大爷和五叔在那一年相继去世。大爷在临死前还找我呢!
12月26日,六大队的马副大队长进了监房和我谈话后,我知道很快我就要离开6号监了,就把自己的棉被给了这里的看管犯,换回了他的旧被子。他在监狱已经7年了,被子都透光了,他说自己晚上睡觉太冷了。当时我的棉袄、棉裤、毛衣、毛裤都送光了,自己只穿着单衣过冬。
终获自由
2007年9月29日上午,我身上的(约束)绳子被解了下来。我终于出狱,获得自由。
回到家,我开始认真全面的学法炼功。仅仅20天,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将近30斤,以后体重开始平稳缓慢的增加。仅1个月,我的身体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这时我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我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加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
2007年12月初,我可以双盘了,到了12月底,我又达到能够无限制双盘了,也长出了一头浓密黑发(刚回家时我头发稀疏),人也彻底恢复了。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