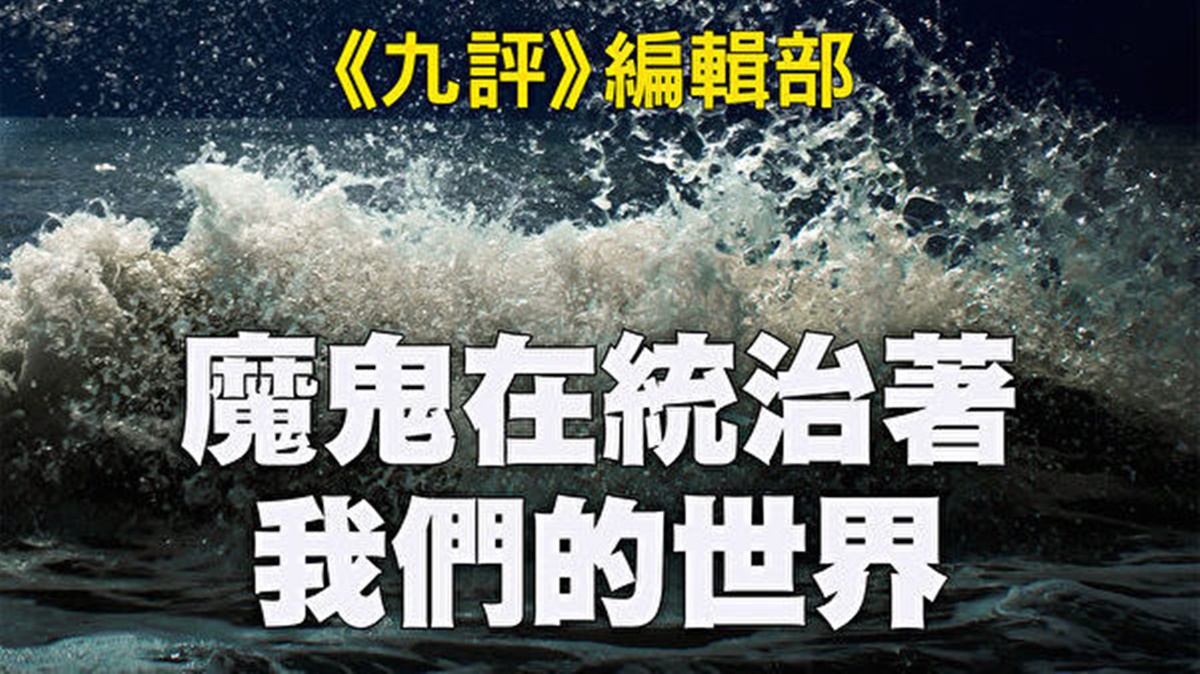编按:“九评编辑部”两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发更多共鸣,特此推荐,以飨读者。第七章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上)
目录
引言
1.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2.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3.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4.共产政权下的共产共妻实践
1)前苏联的共产共妻
2)延安的性开放
5.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
引言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女权、性解放、同性恋权利等各类反传统运动在西方甚嚣尘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传统家庭。美国1969年加州离婚法开启单方离婚绿灯,各州竞相效仿,离婚—结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长超过一倍﹔50年代大约11%的诞生于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离婚,到了70年代这个比率窜升至50%。[1]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2016年美国新生婴儿中超过40%属于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这个数字不到5%。在东西方传统社会里,贞洁的两性关系被视为美德,如今变成被嘲弄的可笑观念。伴随女权运动而来的“同性婚姻权利”运动更寻求法律上重新定义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现任美国联邦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员的一名法学教授曾在2006年发起签署一项宣言,名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们家庭关系的战略新视角”,鼓吹人们按自己的任何欲望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两对同性恋组成一个家庭等等),并宣称传统婚姻家庭不应该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权。[2]在公立学校里,几千年来被传统社会视为可耻的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但被灌输为正常的,甚至有的学校干脆把任何形式的以传统理念教育孩子视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倾向能够“自由”发展(即毫无阻碍地发展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罗德岛学区宣布禁止公立学校举行父-女、母-子舞会,宣称“公立学校无权给孩子灌输诸如女孩喜欢跳舞、男孩喜欢棒球之类的观念”。[3]
传统家庭被逐步摧毁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所宣扬的“消灭家庭”将先于“消灭阶级”成为现实。
在西方社会里,摧毁家庭的因素有许多方面,不但有女权、性解放、同性恋运动的变异观念冲击,还伴有左派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等打着“自由”、“公平”、“权利”、“解放”的旗帜变异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以各种显性、隐性的形式推波助澜,诱导人们抛弃和变异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而所有这一切所谓现代思潮、运动,从19世纪初发端,就带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深深烙印。共产邪灵善于不断变化和欺骗,这使人们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动听的口号迷惑,最终却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统家庭被摧毁、人心被变异的局面,实际上是共产邪灵近两百年来精心策划、逐步实施的结果。
这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被破坏,由神的教诲而确立的传统道德被摧毁,通过家庭承传、培养熏陶下一代传统信仰、价值理念的功能丧失,使年轻一代人没有传统理念约束,由共产邪灵直接来掌控其灵魂。
1.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设立,为“天作之合”,不可毁弃﹔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众生,但同时神也让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别,并为男女双方规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传统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妻子,甚至不惜“舍己”维护妻子﹔而女人则应当配合与帮助丈夫,使“二人成为一体”。男人负责在外“汗流满面才得餬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都源于人的不同原罪。类似的,在东方传统文化中,男人为阳像天,当自强不息,有承载风雨、呵护家庭的责任﹔女人为阴像地,以厚德载物,当柔顺体贴,有相夫教子的义务。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阴阳和合,子女才会健康成长。
传统的家庭发挥着承传信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摇篮、价值承传的纽带。孩子的人生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孩子如果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到无私、谦卑、感恩、坚韧等等传统美德,必将会使其受益终生。
传统的婚姻生活也促进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长,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体贴包容对方。这一点和变异的同居生活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的情感总有阴晴变化,两人高兴了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分手,这种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没有区别,并不需要婚姻来约束。马克思则鼓吹情感上“无任何约束的性爱”[4],当然就是要解体传统婚姻,消灭家庭。
2.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共产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灭私有制,必然要消灭家庭。原教旨共产主义把经济因素作为主导家庭关系的关键,当代的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再把人的性欲视为理解家庭问题的钥匙,二者相同之处都是把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抛在了一边,崇尚物质、欲望,实际是把人变为兽,从而通过变异人的理念来摧毁家庭。
共产主义有一个很迷惑人的学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类自身。解放的对立面是压迫。那么在人类自身的“解放”中压迫来自哪里呢?共产主义给出的回答是,压迫来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由社会传统道德强加的:传统的“父权”家庭观念压迫女性﹔传统的性道德压迫人性。共产主义“解放自己”的理论被后世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继承发展,导致反对传统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恋等等反传统的观念大行其道,成为魔鬼消灭家庭的重要工具。共产主义要推翻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3.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传统家庭。早在19世纪初,魔鬼选择了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种子。共产主义思想开拓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New Harmony)乌托邦公社(两年后以失败告终)。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称公社把人类从“三位一体的巨大恶魔”中解救出来,对“巨大的恶魔”一词他解释说,“我是指私有财产,以及以私产为基础、荒谬的宗教和婚姻。”[5]
欧文死后,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是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他死后,其门徒将其思想带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随后又扩散到美国。傅立叶首次编造了“女权”(法文“féminisme”)一词。在他的理想共产社会(称作“法朗吉”Phalanx)中,传统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欢派对被高度赞颂为充分解放了人类的内在激情(passion),并宣称公平社会应该对“性弱势者”(如年老、长相丑陋者)给予照顾,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满足的“权利”。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性满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员乱伦乃至兽交,只要不是强迫的,都应该允许。因此他堪称当代同性恋运动(LGBTQ)新兴分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先驱。受欧文,特别是傅立叶影响,19世纪在美国先后出现数十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公社,但大都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叶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昂内达(Oneida)公社,维持了32年。该公社鄙视传统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滥交。社员通过每周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仪之人“性爱”的机会。最终创办者约翰‧汉普瑞‧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惧怕教会的法律诉讼而秘密逃亡,公社被迫放弃公妻制。诺伊斯后来着书立说成为“圣经共产主义”(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从一开始共产主义魔鬼就诱惑人背弃神的教诲,否认神,否认原罪。依照这种逻辑,本来是人类道德堕落造成的社会问题,其罪恶根源被归结为私有制。共产主义让人相信,消灭了私有财产,人就不会为此纷争,但即使财产公有之后,人还可能为配偶尔产生纷争,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公然以“公妻制”为解决方案。
这些共产主义播种者创办的共产“乐园”,或者直接挑战传统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于各社区、教会、政府都认为这对社会道德伦理构成了挑战,从而一致采取行动压制。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狼藉声名不胫而走。
失败的乌托邦公社给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教训:公开鼓吹淫乱的公妻制的时机还不成熟。虽然《共产党宣言》中“消灭家庭”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采用了隐晦的方式陈述其毁灭家庭的理论。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关于家庭的论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婚姻观。书中指出,“历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并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为了保存和继承私有财产产生的。这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称这种“一夫一妻制”是基于财产的“古典”模式。他认为财产公有化之后一种“崭新”的纯粹基于爱情的“婚姻”模式将会出现。没有财产的束缚,基于纯爱慕之心的婚姻,听起来多么的高尚!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解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者那里显得苍白无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这不就等于是在鼓励性乱吗?前苏联和中共政权建立之后的乱性(见下一节),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结果。
夫妻之间的情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而传统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离”既是对神的誓约,其本身也表明了双方在婚姻之始就准备着未来的情感可能会遇到困境,以及双方共同应对这种困境的决心。维系婚姻的不仅仅是情感,更是责任,对另一方、对孩子、家庭的体贴照顾,把夫妻双方变成了有道德责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产社会中,财产公有,家务劳动职业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担心,因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国家负责,“这样,完全不必担忧任何‘后果’──而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经济和道德压力,妨碍了姑娘把自己彻底献给所爱的男子。这难道不足以带来无任何约束的性交,以及随之而来社会更宽容对待女人贞洁的荣耀和失贞的耻辱吗?”
马恩所鼓吹的,尽管常常用“自由”、“解放”、“爱”等辞汇掩盖其真实含义,实际是放弃人的道德责任,使人的行为完全受欲望主宰。但无论是傅立叶还是马克思时代,多数民众还没有彻底背离神的教诲,对于共产主义的淫乱思想尚有相当的戒备,即便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纪以后的人类是如何以各种藉口接受其淫乱思想和实施其消灭家庭的目标的。
红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乱变异的种子,也系统安排了引诱人类屈从欲望而背离神的教诲,逐步堕落,最终让其实现“消灭家庭”、变异人心之目标,使人落入红魔掌控。
4.共产政权下的共产共妻实践
如前所述,淫乱是共产主义的内在基因。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奸污女仆,并产下孩子让恩格斯抚养﹔恩格斯与两姐妹同居﹔苏联共产党党魁列宁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他还嫖妓并染上梅毒。另一个党魁斯大林同样是淫乱无比,霸占他人妻子。
苏共夺权成功之后,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共妻实践,当时的苏联堪称西方“性解放”的先导。1990年第10期俄国《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进行全面揭露,称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等人,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
1)前苏联的共产共妻
早在1904年,列宁写道:“淫荡,能使精神的能量获得释放,不是为了伪装的家庭价值,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扔出这个血块。”[6]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党代会议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尔甚维克一旦夺权胜利后,就要制定新的两性关系原则。共产主义理论要求摧毁家庭,过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时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全部交给国家。
1911年,托洛茨基给列宁写信称:“毫无疑问,性压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压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资产阶级结构的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宁回覆说:“不仅仅是家庭。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禁忌都必须废除……我们可以向女权学习,甚至有关同性恋的禁令都必须废除。”[7]
布尔甚维克夺权后,于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宁条令》中,包括“废除婚姻”、“取消惩罚同性恋”等内容。[8]
当时苏联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布尔甚维克为了尽快地打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人类”,就通过街头裸体漫游来变异人的思想。他们四处游荡,狂热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耻!”“廉耻,是苏维埃人民过去的资产阶级。”[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为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女同性恋团体举行庆祝活动。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此事。他说,女同性恋游行庆祝的消息令列宁非常高兴。列宁还鼓励更多人裸体走出来:“继续努力吧,同志们!”[10]
1923年,苏联小说《三代人的爱》使“杯水主义”一词不胫而走。小说作者是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伦泰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甚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解放”的斗士。小说宣扬的“杯水主义”,实质上就是性放纵的代名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杯水主义”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
当时的苏联非婚性爱大量出现,青年的性放纵已然公开,没有性经验的大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2%。莫斯科劳动大学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44.8%。反之,带有短期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11]
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资料显示,1924年到1927年间的离婚率从5%激增到20%,其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占到33%。莫斯科还出现了裸体游行、数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会强奸案件时有发生。[12]
前苏联性解放期间还出现“瑞典家庭”现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愿者组成“家庭”。虽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的俄式。这一现象大开乱交和性乱之门,造成伦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恋、性病、强奸等事件激增。[13]
随着社会主义公社的发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苏遍地开花。这一现象称为妇女“国有化”或“社会主义化”。以1918年3月叶卡捷琳堡的“社会主义女性”为例。布尔甚维克夺取这座城市后,就在《苏维埃消息报》上颁布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16岁至25岁的年轻女子都必须“社会化”,由内务部委员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议推行,并下达命令。于是指挥官卡拉谢夫执行任务,当即就“社会化”了10名年轻女子。[14]
不过,布尔甚维克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末收紧了性政策,列宁在与妇女活动家蔡特金的谈话中痛斥“杯水主义”,给它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他们无人看管抚养,家庭解体最终会导致社会瓦解。
2)延安的性开放
中共诞生之初,情况与苏联类似。当然,这都是同一棵毒树上结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就以私生活放荡着称,郑超麟、陈碧兰的回忆录中,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乱,性态度堪比前苏联杯水主义盛行时期。
不只是上层知识份子型领袖,早期开辟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体现“性自由”。由于提倡妇女平等、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出现了大量“因满足性欲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况。苏区青年还往往以“拜干娘”接近群众为名谈恋爱,年轻女性拥有六七名性伴侣的不在少数。据《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红安、黄麻、黄陂、光山等地方党内负责人“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15]
1931年春末,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后,即发现梅毒流行甚广,不得不报告中央索求“诊梅毒疥疮的医生”。多年后,其回忆录中对当时苏区“调戏妇女的事”、“对妇女乱来”和某些高级将领的“姘头”仍记忆犹新。
1937年李克农担任中共八路军驻京办主任,负责领取军饷、医药、物资等。一次,国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八路军的医药清单时,发现其中治疗花柳病的药品数量相当大。经办人员就问李克农:“难道贵军中得这种病的人很多吗?”李克农一时语塞,只好编谎搪塞说是给当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纪30年代的性自由同样危及了政权,不但有和苏俄相同的社会瓦解问题,还使已婚的红军战士军心动摇,担心参军后妻子出轨、改嫁,影响部队战斗力。而且,这种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实了其“共产共妻”的恶名。为此,苏区才不得不颁布了保护军婚、限制离婚次数等政策。
5.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邪灵的各种变异思潮自19世纪开始,在西方经过上百年蜕变、演进之后,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大规模登场。
20世纪60年代,在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鼓励下,邪灵操纵的各种社会文化运动在美国先后登场,如嬉皮士反正统文化运动、新左派激进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性革命思潮等。这些思潮、运动如汹涌的潮水,激烈地冲击、腐蚀美国的政治体制、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肌体,并随即波及欧洲。西方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性观念与文化价值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与此同时,同性恋“权利”运动也不断高涨。这些都导致西方传统家庭价值观念不断削弱和传统家庭模式日渐式微。同时,社会的动荡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色情文化氾滥、吸毒现象蔓延、性道德崩溃、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会福利群体扩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随后在全世界的迅速扩散,对人类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传统家庭观念、性道德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让性解放在西方社会肆虐,邪灵经过了充分准备,尤其通过“性爱自由”运动(Free love,也称性激进主义)为其铺垫,逐步侵蚀瓦解传统理念。从19世纪兴起的“性爱自由”鄙视传统家庭道德观念,主张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应当不受干预,个人的性活动,包括婚姻、堕胎、淫乱行为不应受政府、法律制约。
傅立叶的追随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诺伊斯首次提出“性爱自由”概念。
“性爱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者,如:英国“性爱自由”先锋是社会主义哲学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早期倡导人﹔该运动最知名的倡导者、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也曾是费边社成员,他声称道德不应限制人类本能的快乐,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法国“性爱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尔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后来发展了傅立叶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开创了法国个人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鼓吹滥交、同性恋、双性恋﹔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者弗来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亚的“性爱自由”开拓者等等。
“性爱自由”运动在美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杂志采用铜版纸,给人一种“艺术”的错觉,再加上造价不菲的彩色印刷,传统观念中被视为下三滥的粗俗色情题材一下子跃入主流社会,成了“高档”休闲杂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扩散给全球普通民众,肆意侵袭着传统性道德观念。
到20世纪中叶,随着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爱自由”观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称性解放)正式登场。“性革命”是共产主义精神分析鼻祖、德国共产党员赖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前者将人从“经济压迫”下解放,而后者将人从“性压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论的奠基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中使性解放观念深入人心。此后,随着动物学家金赛(Alfred Kinsey)发表《人类男性性行为报告》和《人类女性性行为报告》以及口服避孕药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观念在60年代红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学者发现金赛在所谓的人类性行为报告中,采用了夸大、过分简化等等手法扭曲统计数据,使很多人误以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对性解放、同性恋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
一时间“性解放”成为现代社会的时髦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放纵的性生活被视为正常,十几岁的女孩若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同伴的耻笑。资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间达到15岁的美国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岁之前有过婚前性经验。[18]到2010年代,结婚前仍为处女的新娘仅为5%﹔18%的新娘婚前有过10个以上的性伴侣。[19]“性”成为大众文化的流行主题,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文学作品”充斥市场,“儿童不宜”的X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1)女权运动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
女权运动是共产邪灵利用来破坏家庭的另一驾轻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权运动(也称第一波女权运动)18世纪发端于欧洲,主张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第一波女权运动发生时,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基础依旧强盛,这时的女权运动并不主张直接挑战传统家庭。当时影响力显着的女权主义者,如18世纪英国的玛莉‧乌丝东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纪美国的玛格丽特‧芙乐(Margaret Fuller)、19世纪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主张一般女性婚后应以家庭为主,女性的潜能主要是在家庭领域里发展,女人充实自己是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别优秀的特殊女性,应该不受任何阻碍,自由发挥她们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较长短。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妇女选举权获得各国法律承认,第一波女权运动渐趋平静。此后随着大萧条的冲击和二战的影响,女权运动基本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也早早埋下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观念的种子。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就为现代激进女权运动奠定了方向。被称作女权主义之父的傅立叶宣称婚姻把妇女变成了私有财产,欧文把婚姻诅咒为“邪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权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如19世纪女权主义者莱特(Frances Wright)继承了傅立叶的思想,主张实现女性的性观念自由。英国女权活动家惠勒(Anna Wheeler)继承了欧文的思想,激烈谴责婚姻把女人变成了奴隶等等。同时,社会主义女权活动者也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权刊物,如法国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妇女》(La Femme libre,后更名为《妇女论坛》)、《妇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妇女评论》(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创办者或是圣西门乌托邦主义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叶的追随者。由于当时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遭到当局严厉审查。
我们看到,当第一波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同时,红魔也同时安排了各种激进思潮冲击传统家庭、婚姻观念,为随后到来的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作了铺垫。
第二波女权运动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随后波及到西欧及北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伴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纷纷抬头。女权主义趁机以更激进变异的面目出现并风行世界。
奠定这一波女权运动第一块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以及该书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起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该书作者从一个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角度,激烈批评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认为传统的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所谓“父权社会”塑造的迷思。她认为中产阶级的郊区家庭是“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应该跳出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20]
数年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宰了全国妇女组织,继承并发展了弗里丹的女权思想。她们认为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的。她们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并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传统文化,在经济、教育、文化、家庭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实现女性的“平等”。
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从而鼓吹“斗争”和“解放”、“平等”,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地位划分人群,新女权主义则以性别划分人群。
事实上,《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并非如书中所暗示的,是一个厌倦家庭琐事的中产阶级郊区家庭妇女。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热维茨(Daniel Horowitz)于1999年写了传记《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奥秘〉的出笼》。他调查揭示弗里丹从大学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个斯大林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为左翼工人运动报刊写作,霍热维茨并找到她当年写的这些文章。她甚至一度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核物理学家的情妇。[21]
美国学者凯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红色女权主义》一书中指出,实际上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国并没有沉寂。包括安东妮(Susan Anthony)、弗来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背景的红色女权主义作者,在这一时期为随后到来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安东妮早在1946年就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压迫黑人作类比,指出男性同样压迫着女性。只是由于受麦卡锡反共影响,共产主义臭名昭着,她们从此闭口不谈自己的红色背景。[22]
在欧洲,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领第二波女权风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1941年她与共产主义者、哲学家保罗‧萨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创建了法国地下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随着60年代其女权主义声名鹊起,她宣称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只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她主张“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虽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性别(gender)则是在人的社会性的影响下后天所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心理概念﹔认为女孩顺从、乖巧、爱撒娇、赋予母性的“女性气质”全都来自后天的“父权社会”精心设计的“神话”,为的是维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主张女性冲破传统理念,实现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思想实际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等各类变异观念提供了温床。此后各类形形色色的女权思想层出不穷,基本都继承了女性不平等来自于传统“父权社会”的压迫。因此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家庭婚姻观念是实现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碍。[23]
波伏娃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丈夫,“同妓女一样令人噁心”。她同萨特保持终身情人关系而拒绝结婚,与此同时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爱情”,同样的,萨特也拥有几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爱情”。她的婚姻观是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态度。事实上,这种复杂混乱的性关系正是乌托邦共产主义先行者傅立叶19世纪所设想的公妻制。(未完待续)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
[1] W. Bradford Wilcox, “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National Affairs, Number 35, Spring 2018. https://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the-evolution-of-divorce.
[2] “Beyond Same-Sex Marriage: A New Strategic Vision for All Ou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9:2 (July 1, 2006): 161-171. DOI:10.1080/15240650801935198.
[3] Victoria Cavaliere, “Rhode Island school district bans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event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national/rhode-island-school-district-bans-father-daughter-mother-son-events-article-1.1162289#nt=byline.
[4] [德]恩格斯着,谷风出版社编辑部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台北:谷风出版社,1989年)。
[5] Robert Owen, “Oration Containing a Declaration of Mental Independence,” Public Hall, New Harmony, Indiana (July, 4, 1826), http://www.indiana.edu/~kdhist/H105-documents-web/week11/Owen1826.html.
[6]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夏侯:〈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性解放〉,大纪元新闻网,http://www.epochtimes.com/gb/17/4/9/n9018949.htm。
[12] 同上。
[13]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st/21/velikaya_oktyabrskaya_seksualnaya_revolyuciya/.
[14] 夏侯:〈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性解放〉,大纪元新闻网,http://www.epochtimes.com/gb/17/4/9/n9018949.htm。
[15] 中央档案馆等:《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16] 杨宁:〈八路军为何大量购买治花柳病的药品?〉,大纪元新闻网,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8/n10069025.htm。
[17] 揭露金赛报告学术造假的众多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是莱斯曼博士的研究(Judith A. Reisman, Ph.D., Edward W. Eichel, Kinsey, Sex and Fraud: The Indoctrination of a People (Lafayette, Louisiana: Lochinvar-Huntington House, 1990)。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评价其工作说:“朱蒂‧莱斯曼博士和她的同事摧毁了两个金赛报告的基础。”( “Dr. Judith A. Reisman and her colleagues demolis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wo (Kinsey) reports.”)(“Really, Dr Kinsey?”, The Lancet, Vol. 337 (March 2, 1991): 547)
[18] Finer LB, “Trends in Premarital Sex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2003,”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2(1) (2007): 73-78.
[19] Nicholas H. Wolfinger, “Counterintuitive Trends in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Sex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counterintuitive-trends-in-the-link-between-premarital-sex-and-marital-stability.
[20]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3).
[21] 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v.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22] Kate Weigand, Red Feminism: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责任编辑:刘明湘)
相关链接: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9):信仰篇 点击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