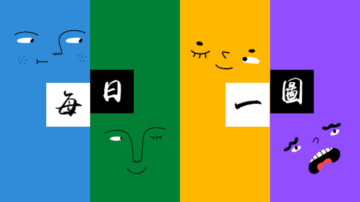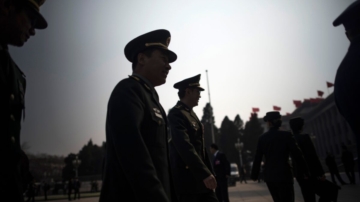正如近来开放的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20世纪50年代初是行动强度最高的时期;从来不曾有这么多人被拘押在营地、强制劳动流放区和罪犯流放地。这也是该系统前所未有的危机期。
1953年头几个月,古拉格容纳着275万名囚犯,分为三类:
• 在所有地区发现的约500个劳改流放区里被监禁的人。这些劳改流放区平均容纳1,000至3,000名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普通罪犯,刑期不足5年。
• 在约60个大型综合刑罚设施或劳改营里被监禁的人。这些劳改营主要在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每座关押着数万名囚犯、普通罪犯和刑期均超过10年的政治犯。
• 在约15个有特殊体制的营地(special-regime camps)里被监禁的人。这些营地于1948年2月7日依据内务部的秘密指示而建立,仅供收容被认为特别危险的政治犯。他们共计约20万人。
就这样,这个庞大的集中营世界容纳了275万名囚犯;另275万“特殊移民”由古拉格管理局另一个不同部门所控制。这些数字在管理、控制及经济效益方面,造成了严重问题。1951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将军对劳改犯(penal workers)中生产率不断下降感到担忧。他发起了大规模的检查运动,来评估古拉格的状况。当委员会发回报告时,揭示了极其紧张的局势。
首先,自1945年以来一直有“政治”囚犯抵达特殊体制营地。他们来自被击败的游击队组织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来自新并入地区的“外来分子”、真实或假想的“通敌者”以及其他的“祖国叛徒”。这些被拘押者比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的敌人”要坚定许多。后者曾是党的干部,确信他们被监禁是严重误解的结果。相比之下,这些新人被判刑20或25年,没有提早释放的希望,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而且,特殊体制营地将他们隔离,消除了普通犯罪对他们的影响。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正是普通罪犯的存在,防止了囚犯中形成团结的氛围。一旦这个障碍被清除,这些特别营地就迅速变成抵制与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温床。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囚犯在反抗该体系中特别活跃。罢工、绝食抗议、大规模逃跑以及暴动,均变得越来越普遍。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1950至1952年,发生了16起大规模的暴动和反抗,每起涉及数百名囚犯。
克鲁格洛夫1951年的检查也揭示出,该系统在普通营地每况愈下。后来,那里被觉察到“普遍存在纪律松弛问题”。1951年,由于囚犯的抗议和罢工,古拉格损失了百万个工作日(译者注:是指参与的囚犯每人损失的工作日之总和)。还有,这些营地里的犯罪率上升,囚犯和看守之间的暴力对抗日益增多,受刑罚的劳动力的生产率下降。据当局说,这种情况主要是由敌对的囚犯帮派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一群囚犯拒绝工作,并鄙视其它工作的群体,称他们为“通敌者”。派系间的混战、囚犯间的斗殴,对纪律都具有腐蚀作用,通常会造成混乱。刺死比饿死或病死更为常见。195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古拉格指挥官会议承认,“当局本可以从各群囚犯间的敌对行动中获得某种优势,但现在正开始失去对形势的掌控……在一些地方,某些派别甚至开始按照自己的路线运作营地。”为了瓦解群体和派系,当局决定,应在各营地之间更频繁地转移囚犯,而在经常关押着4万至6万人的最大监狱里,应当永久性地改组成分开的区域。
除了指出由不同派系造成的颇多问题外,1951年和1952年的许多检查报告还承认,既需要彻底重组监狱及其生产系统,又需要对整个行动进行大幅缩减。1952年1月,关着69,000名囚犯的诺里尔斯克集中营的指挥官──尼古拉.兹韦列夫(Nikolai Zverev)上校,发报告给古拉格总司令伊万.多尔吉赫(Ivan Dolgikh)将军,提出以下建议:
1. 隔离派系。“但是”,兹韦列夫指出,“鉴于囚犯派系林立、相互敌对的现状,如果我们能索性将领导者隔离,就算走运了。” 2. 放弃巨大的生产区。在那里,成千上万属于各种派别的囚犯,目前正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工作。 3. 建立更小的生产单位,以确保更好地监控囚犯。 4. 增加看守人数。“但是”,兹韦列夫补充说,“以希望的方式组织看守,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需要将看守人数增加一倍。” 5. 将自由工人与所有生产场所的囚犯分开。“但组成诺里尔斯克综合设施的不同公司之间的技术联系,以及生产持续的要求,再加上严重的住房短缺,都意味着目前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囚犯与自由工人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生产率和不间断生产的问题只可能靠提前释放15,000名囚犯来解决。他们无论如何都将被迫留在同一地点。”
鉴于当时的舆论气氛,兹韦列夫的最后一项提议相当合乎时宜。1951年1月,克鲁格洛夫要贝利亚提前释放6,000名囚犯。之后,他们要作为自由工人被发配到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一处巨大建筑工地。当时,那里的25,000名囚犯以一种被认为是极其无效的方式辛苦劳作着。提前释放的做法,特别是释放具备某些资格的囚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相当常见。它也对集中营过时系统的经济价值提出了疑问。
面对囚犯(他们远不及过去的囚犯那么驯服)数量的这种巨幅增长,以及整个一系列后勤和监控问题(古拉格人数此时约达20万8,000人),这架庞大的行政机器发现越来越难以炮制出所谓的“成功”(tufta)。为了解决这个持久性问题,当局有两种解决方案可选:要么最大限度利用所有人力,而不考虑人员损失,要么通过更大程度地顾惜人力,来确保古拉格的生存。在1948年以前,第一个解决方案成为首选;但在1940年代末,党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战争已经榨干了这个国家,每个经济部门人力都很稀缺,因此,以一种更经济的方式使用囚犯劳动力,更为合乎情理。为尝试刺激生产,引入了奖金和工资,并给完成定额的囚犯增加食物配给。结果,死亡率立即下降了2~3%。但这些改革很快就遭遇集中营生活的严酷现实。
到20世纪50年代初,生产基础设施大体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期投资并未获得任何收益。关押着数以万计囚犯、为将大量劳动力用于当时的大型项目而建立的巨大监狱,极难进行重组,尽管1949年至1952年间曾多次尝试将其分成较小的生产单位。给囚犯的微薄薪水,一般为每年几百卢布(比自由工人的薪水少15至20倍),并不足以刺激提高生产率。越来越多的囚犯在罢工、拒绝工作,并正形成一个需日益密切监视的有组织的团队。不管他们获得更高薪水,还是遭更严密的看守,所有囚犯在经济方面都开始花费得越来越多。他们中既有与当局合作的人,也有宁愿声援其他罢工者的人。
从1951年和1952年的检查报告中获得的所有信息,均指向同一个方向:古拉格已成为一个更难以控制的机制。主要靠使用受刑人力(penal manpower)建造的斯大林主义大型工程,都大大落后于预定计划,包括古比雪夫(Kuibyshev)和斯大林格勒的水电站、土库曼斯坦运河,以及伏尔加—顿河运河(Volga-Don canal)。为加快工作进度,当局被迫另外引进大批自由工人,并准许一些囚犯提前获释,试图激励其他人。
古拉格危机有助于说明1953年3月27日斯大林死后不到三周,由贝利亚所下令的对120万囚犯的大赦。当然,仅仅是政治原因,本来无法激发斯大林的潜在继任者们凝聚起来宣布部分大赦。所有人都意识到,管理过度拥挤和无利可图的古拉格存在巨大困难。然而,就在所有刑事当局要求减少囚犯人数之际,晚年日益遭受偏执狂折磨的斯大林,正在酝酿第二次大恐怖。在斯大林主义政权最后和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 在所有地区发现的约500个劳改流放区里被监禁的人。这些劳改流放区平均容纳1,000至3,000名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普通罪犯,刑期不足5年。
• 在约60个大型综合刑罚设施或劳改营里被监禁的人。这些劳改营主要在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每座关押着数万名囚犯、普通罪犯和刑期均超过10年的政治犯。
• 在约15个有特殊体制的营地(special-regime camps)里被监禁的人。这些营地于1948年2月7日依据内务部的秘密指示而建立,仅供收容被认为特别危险的政治犯。他们共计约20万人。
就这样,这个庞大的集中营世界容纳了275万名囚犯;另275万“特殊移民”由古拉格管理局另一个不同部门所控制。这些数字在管理、控制及经济效益方面,造成了严重问题。1951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将军对劳改犯(penal workers)中生产率不断下降感到担忧。他发起了大规模的检查运动,来评估古拉格的状况。当委员会发回报告时,揭示了极其紧张的局势。
首先,自1945年以来一直有“政治”囚犯抵达特殊体制营地。他们来自被击败的游击队组织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来自新并入地区的“外来分子”、真实或假想的“通敌者”以及其他的“祖国叛徒”。这些被拘押者比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的敌人”要坚定许多。后者曾是党的干部,确信他们被监禁是严重误解的结果。相比之下,这些新人被判刑20或25年,没有提早释放的希望,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而且,特殊体制营地将他们隔离,消除了普通犯罪对他们的影响。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正是普通罪犯的存在,防止了囚犯中形成团结的氛围。一旦这个障碍被清除,这些特别营地就迅速变成抵制与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温床。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囚犯在反抗该体系中特别活跃。罢工、绝食抗议、大规模逃跑以及暴动,均变得越来越普遍。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1950至1952年,发生了16起大规模的暴动和反抗,每起涉及数百名囚犯。
克鲁格洛夫1951年的检查也揭示出,该系统在普通营地每况愈下。后来,那里被觉察到“普遍存在纪律松弛问题”。1951年,由于囚犯的抗议和罢工,古拉格损失了百万个工作日(译者注:是指参与的囚犯每人损失的工作日之总和)。还有,这些营地里的犯罪率上升,囚犯和看守之间的暴力对抗日益增多,受刑罚的劳动力的生产率下降。据当局说,这种情况主要是由敌对的囚犯帮派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一群囚犯拒绝工作,并鄙视其它工作的群体,称他们为“通敌者”。派系间的混战、囚犯间的斗殴,对纪律都具有腐蚀作用,通常会造成混乱。刺死比饿死或病死更为常见。195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古拉格指挥官会议承认,“当局本可以从各群囚犯间的敌对行动中获得某种优势,但现在正开始失去对形势的掌控……在一些地方,某些派别甚至开始按照自己的路线运作营地。”为了瓦解群体和派系,当局决定,应在各营地之间更频繁地转移囚犯,而在经常关押着4万至6万人的最大监狱里,应当永久性地改组成分开的区域。
除了指出由不同派系造成的颇多问题外,1951年和1952年的许多检查报告还承认,既需要彻底重组监狱及其生产系统,又需要对整个行动进行大幅缩减。1952年1月,关着69,000名囚犯的诺里尔斯克集中营的指挥官──尼古拉.兹韦列夫(Nikolai Zverev)上校,发报告给古拉格总司令伊万.多尔吉赫(Ivan Dolgikh)将军,提出以下建议:
1. 隔离派系。“但是”,兹韦列夫指出,“鉴于囚犯派系林立、相互敌对的现状,如果我们能索性将领导者隔离,就算走运了。” 2. 放弃巨大的生产区。在那里,成千上万属于各种派别的囚犯,目前正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工作。 3. 建立更小的生产单位,以确保更好地监控囚犯。 4. 增加看守人数。“但是”,兹韦列夫补充说,“以希望的方式组织看守,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需要将看守人数增加一倍。” 5. 将自由工人与所有生产场所的囚犯分开。“但组成诺里尔斯克综合设施的不同公司之间的技术联系,以及生产持续的要求,再加上严重的住房短缺,都意味着目前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囚犯与自由工人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生产率和不间断生产的问题只可能靠提前释放15,000名囚犯来解决。他们无论如何都将被迫留在同一地点。”
鉴于当时的舆论气氛,兹韦列夫的最后一项提议相当合乎时宜。1951年1月,克鲁格洛夫要贝利亚提前释放6,000名囚犯。之后,他们要作为自由工人被发配到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一处巨大建筑工地。当时,那里的25,000名囚犯以一种被认为是极其无效的方式辛苦劳作着。提前释放的做法,特别是释放具备某些资格的囚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相当常见。它也对集中营过时系统的经济价值提出了疑问。
面对囚犯(他们远不及过去的囚犯那么驯服)数量的这种巨幅增长,以及整个一系列后勤和监控问题(古拉格人数此时约达20万8,000人),这架庞大的行政机器发现越来越难以炮制出所谓的“成功”(tufta)。为了解决这个持久性问题,当局有两种解决方案可选:要么最大限度利用所有人力,而不考虑人员损失,要么通过更大程度地顾惜人力,来确保古拉格的生存。在1948年以前,第一个解决方案成为首选;但在1940年代末,党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战争已经榨干了这个国家,每个经济部门人力都很稀缺,因此,以一种更经济的方式使用囚犯劳动力,更为合乎情理。为尝试刺激生产,引入了奖金和工资,并给完成定额的囚犯增加食物配给。结果,死亡率立即下降了2~3%。但这些改革很快就遭遇集中营生活的严酷现实。
到20世纪50年代初,生产基础设施大体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期投资并未获得任何收益。关押着数以万计囚犯、为将大量劳动力用于当时的大型项目而建立的巨大监狱,极难进行重组,尽管1949年至1952年间曾多次尝试将其分成较小的生产单位。给囚犯的微薄薪水,一般为每年几百卢布(比自由工人的薪水少15至20倍),并不足以刺激提高生产率。越来越多的囚犯在罢工、拒绝工作,并正形成一个需日益密切监视的有组织的团队。不管他们获得更高薪水,还是遭更严密的看守,所有囚犯在经济方面都开始花费得越来越多。他们中既有与当局合作的人,也有宁愿声援其他罢工者的人。
从1951年和1952年的检查报告中获得的所有信息,均指向同一个方向:古拉格已成为一个更难以控制的机制。主要靠使用受刑人力(penal manpower)建造的斯大林主义大型工程,都大大落后于预定计划,包括古比雪夫(Kuibyshev)和斯大林格勒的水电站、土库曼斯坦运河,以及伏尔加—顿河运河(Volga-Don canal)。为加快工作进度,当局被迫另外引进大批自由工人,并准许一些囚犯提前获释,试图激励其他人。
古拉格危机有助于说明1953年3月27日斯大林死后不到三周,由贝利亚所下令的对120万囚犯的大赦。当然,仅仅是政治原因,本来无法激发斯大林的潜在继任者们凝聚起来宣布部分大赦。所有人都意识到,管理过度拥挤和无利可图的古拉格存在巨大困难。然而,就在所有刑事当局要求减少囚犯人数之际,晚年日益遭受偏执狂折磨的斯大林,正在酝酿第二次大恐怖。在斯大林主义政权最后和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