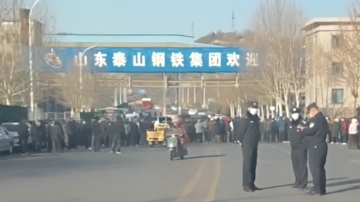编者按:刘华,一个普通中国农民,曾因上访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中,期间想尽办法偷偷记下《劳教日记》,后用各种方式包括用女性身体将日记秘密带出,这些高墙内原生态的散乱信息,拼凑出来的内容震惊中外,揭开了劳教所的黑幕一角,成为当年推动劳教制度废除的关键案例之一。
*****
刘华与其丈夫岳永进2002年开始带领村民维权,揭发村党支书记非法转卖土地及贪腐,遭受到连番的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官官相护,使他们不得不进京上访,期间,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劳教,刘华还因与导演杜斌合作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遭受刑讯逼供。
这对年轻时就已经是农村万元户的夫妇,如今流落北京,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但疾病缠身的刘华说:“我为自己维权,老天就不会饿死我。我就是过穷日子,我也不怕,我没钱,一年到头我都不买菜,我可以去拣菜。谁都不站出来,还有正义吗?我要站出来说话!人人都起来抗争,那这体制就完蛋了,就会解体。”
一、小时候我背一个小草蛇上学

刘华(本人提供)
我妈说,我是庙里偷跑的花大姐托生的,不好养活。我出生在1963年黄历四月初八,这个生日大,是释迦牟尼佛生日,也是大庙开门的日子,这天生的人苦难多。后来我给村里老百姓维权,他们就特别恐惧嘛,镇里有个书记就拿我的生辰八字,找个女的算命,算命的说,“你别碰她,别跟她争,她绝对不会服,这个官司打到底也是你们输,她这个人特别有毅力,会坚持到底的。”这是后来算命人的姐姐传出来的。
小时候我家地不多,因房前屋后有点树,就给定了富农。我5岁那阵,吃集体大锅饭,贫农都上小队吃大锅饭,端个碗、盆,分一大锅粥。我们只能在小队铁门边,扒着小眼看。我也要进去,为什么他们吃,不让咱们吃?我妈拽着我,不让我去,我就哭闹,我妈说,“不懂事!咱家是富农,人家是贫农。”
我爸1.8米的大个儿,每天一样出工,在小队干活一点不差,只能挣二三等工分,就因为咱家是“富农”。
8岁时,小队秋天分笤帚草,扒堆,每家一堆,我家那堆小。我问:“干哈他们家大堆,我们家小堆呀?”我妈说:“你不懂,人家是队长。”“队长就要大堆?我也要大堆!”我就上小队队长家,抱一堆就走,小队长说:“这死丫头!为什么把我家的往你家抱!”我说:“你家堆大,我家堆小。”我哭,怎么富农就倒楣呀?为什么他贫农就多要?我妈说,“贫农是好人,这丫头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这么厉害呢!”
小时不知道党不党的,就知道政府坏,那时目标就很明确了,知道一定要反抗,不反抗就受欺负。
我刚上学时,说咱是富农孩子,想戴红领巾都不给戴呀,走道都给你隔开,人家贫农走一伴,路上她们拦着我就打一顿,欺负我,回家还不敢告诉我妈。后来我就背一个小草蛇或者几个壁虎上学,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她们一打我,我就把蛇往她们身上扔,她们吓跑了,我再把蛇捡回来,第二天上学再背上,这样放学我就能一路畅通回家了。
全家七口人,吃不饱,我大哥上山东背猪大油、背大馒头、背地瓜干。二哥上黑龙江背黄豆,第一回背了50斤,到车站,人一搜是黄豆,说他“投机倒把”,车站就给截留了。本来就是借钱弄的黄豆,结果空手回来。
12岁时,我放学看游斗“四类分子”,一看那不是我二哥吗?让人剃秃了,挂个大牌子,写个“投机倒把”,上面还打个叉,就因为他把槐树干削吧削吧就做了铁锹把,就给抓了游斗!
二、为村民的土地维权

刘华(本人提供)
17岁我就下学了(毕业),然后在小队干了几年活。1984年我22岁结婚,然后一直在沈阳苏家屯红菱镇的张良村里做生意。
2002年的时候,村书记不告诉村民,就把村里一千亩地给卖了。
人家说:“看你们两口子,好赖还做点生意,比我们有能耐,就帮我们写点材料,往上反映反映呗。”我虽然不种地,但地也有咱的,他抢、他非法卖,咱是应该要回一点。不就是写点材料往上反映吗?我想得特别简单。
以前也有人到村委会那个大院反映过土地的事,被村书记打了好几个耳光,大伙都在怵他。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就去找他,和他理论这个事。
书记说:“我当了24年的大队书记,我一个吐沫就是一个钉,我就是土皇上。”
“这回就不让你当钉!”我说,“把你这根针撅折了,你拿什么穿?我不路过你这针鼻儿,我告到联合国又怎样?”“你告吧,你告到联合国,也要穿过我这个小针鼻儿!”
我说:“我不穿,我越过你,我把你这个针撅折了,拿什么穿?你从开始卖地到现在,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土地局给你批条了吗?你拿得出来?没有,你就是抢!”书记的头低下来了。
我接着说:“高速公路拨下来这么多款,还有95年救灾款都哪去了?这二十多年,你们贪污这么多钱,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现在你卖地,也牵扯到我的地了,你要有个说法!还有《土地法》呐!”
村里老百姓就说,“噢,咋还有《土地法》呀?你咋知道有《土地法》呀?”
村里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在他们眼里就是有文化的了,虽然我初中没念满,但是我学习非常好,平时爱看书,愿意买书,什么《妇女杂志》啥的,都看。我上新华书店,买了一大摞《土地法》,村里一家发一本。我自己花钱买,让他们学。
那时候村书记他们已经卖了一块集体土地,都盖上房子了。我到市里上访要说法,说《土地法》怎么讲的,一条一条的,大队怎么违章的等等,他们认为我讲得有道理,就说:“回去你们扒房子吧,不犯法。”于是我回去我就组织村民,把《沈阳晚报》、《晨报》都给弄来了,把房子一天就扒完了。
扒完以后,区里和镇里的领导,天天穿个大风衣,戴个大口罩,上那地里挑小石头,因为要恢复成农田地,盖房的砖瓦块要挑出来嘛。
当时我脑子就有意识:查帐。我去沈阳会计所问,他们说查帐需要费用,于是我们就抬(村民集资)了6万块钱,二分钱利息抬的高利,让我丈夫代签借用。2002年时,村民已经选我丈夫当了村长,我丈夫是村长、法人,他有权利去审那个帐,所以说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公允的,是合法的。
还得把帐抢出来,会计师才能审查。曾经有的村去查帐,大队叫人给打成植物人了。所以抢帐那天,他们说“刘华你可要掂量好,抢帐就是你拿人家脑袋,人家就会拿你脑袋的”。当时我就想,可不能出差错,出差错我不就废了,孩子还小呢。
我们先去跟他们要帐,不给。我就让那书记坐在沙发上,让几个人看着他,我再把所有的电话全给薅下来了,让电话里外不通。
抢了帐,装上轿车,往村里小路上走,不上大道,转了几个地方,然后就又换面包车,一路换了四次车,才把这一车将近三十玻璃丝(塑料)袋子的帐目,全部拿到了沈阳荣正会计所。十二个审计人员审了大半年,查出我们村干部出卖集体土地、违法摊派、侵吞村民水电费和侵占救灾款等,审计发现有问题的金额达260馀万元,涉及前任书记王景财及现任书记刘家安等。列出审计报表报到公安部后,公安部就说要抓大队书记,但大队书记给公安送了一万斤大米及数万元钱,公安部就不了了之了。
但这块地没有让他卖成。俺们村靠法律维权,真的把官司给打赢了。
区里头还是不甘心,还要卖这块地,说不卖给老张,也要卖给老李,还要卖。公章在大队里,我半夜就去村委会,把公章偷回来,找个地方挖个坑埋起来了。我丈夫是村长,他们要是抢过公章,扣上公章把地就给卖了,我丈夫也有罪过啊。
哪想到他们会设计陷害我丈夫呢。2002年12月12号,那时下雪了,外面全上冻了。村里一个打更的,故意把村委办公室的地用湿拖布拖,之后把门窗打开,水磨石瓷砖的地,就冻上了薄薄一层冰。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漏水让我丈夫赶去处理。我丈夫赶到大队,哪知道地上有冰,大步流星走过去,一兹溜腿就撞到大队一楼中间的柱子上,整个膝盖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三级残疾,左腿和右腿差2寸,不能长时间走路了。后来问那个打更的,为什么大冷天拖地还开窗?他说是书记让他干的。
书记还想要公章,说有个妇女要开流产介绍信,要用公章,让我上大队去。我去了说:“村里老百姓选的妇女主任不用,你大队书记又当妇女主任又当大队书记。你在违法。你看这个妇女要个避孕套哇、要流产哪、要带环,还要找你大队书记,多别扭哇。”我说“你要那些避孕套干哈呀”?他说我寒碜他,一拳把我打倒,当时我就昏过去了。醒过来我就去了他家,脱了外衣就上他家炕,躺下睡觉。我说:“我不走了,今天就跟你过了,你不是把我丈夫的腿害残了吗?我就跟你过了。”他一看确实把我给打伤了,他就报警。派出所来了,警察说:“刘华,走,上医院给你看病去,你不能在人家待着。”我说我丈夫让他害残了,他还把我打了,我就跟他过了,我就不跟我丈夫过了。他们傻了,都过来哄我上医院去看病。
一天半夜12点,我正睡觉呢,一个电话把我弄醒:“我告诉你刘华,你再告,我把你脑袋拿下来!”是大队书记的侄子张富强。我马上打了110,010-110,北京的110。北京转到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的公安开着七八辆警车就去了他家。半夜1点,他家转圈全是警灯闪,张富强一下子就毛了。警察把门踢开,进门就拽他脖子:“你他妈大半夜去打恐吓电话,你知道刘华把电话打到哪了?打到北京,北京转到省公安厅了,我们还活不活了,为你小破事省公安厅都别睡觉!”霹雳吧啦把他揍了一顿。
后来书记又打了我一次,经过沈阳市法医鉴定“轻伤”,“轻伤”他就得坐牢啊,但官官相护,派出所所长包庇他,也不追究,就给他一个“警告”完事,还弄个笔误,说我把大队书记打了,我还得给大队书记拿二百块钱。这事谁能服哇,我被打了,我还要给他钱!我当然要告他!我就上北京告状。那时我丈夫正在当村长,到北京和我待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待续)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
刘华与其丈夫岳永进2002年开始带领村民维权,揭发村党支书记非法转卖土地及贪腐,遭受到连番的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官官相护,使他们不得不进京上访,期间,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劳教,刘华还因与导演杜斌合作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遭受刑讯逼供。
这对年轻时就已经是农村万元户的夫妇,如今流落北京,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权。但疾病缠身的刘华说:“我为自己维权,老天就不会饿死我。我就是过穷日子,我也不怕,我没钱,一年到头我都不买菜,我可以去拣菜。谁都不站出来,还有正义吗?我要站出来说话!人人都起来抗争,那这体制就完蛋了,就会解体。”
一、小时候我背一个小草蛇上学

刘华(本人提供)
我妈说,我是庙里偷跑的花大姐托生的,不好养活。我出生在1963年黄历四月初八,这个生日大,是释迦牟尼佛生日,也是大庙开门的日子,这天生的人苦难多。后来我给村里老百姓维权,他们就特别恐惧嘛,镇里有个书记就拿我的生辰八字,找个女的算命,算命的说,“你别碰她,别跟她争,她绝对不会服,这个官司打到底也是你们输,她这个人特别有毅力,会坚持到底的。”这是后来算命人的姐姐传出来的。
小时候我家地不多,因房前屋后有点树,就给定了富农。我5岁那阵,吃集体大锅饭,贫农都上小队吃大锅饭,端个碗、盆,分一大锅粥。我们只能在小队铁门边,扒着小眼看。我也要进去,为什么他们吃,不让咱们吃?我妈拽着我,不让我去,我就哭闹,我妈说,“不懂事!咱家是富农,人家是贫农。”
我爸1.8米的大个儿,每天一样出工,在小队干活一点不差,只能挣二三等工分,就因为咱家是“富农”。
8岁时,小队秋天分笤帚草,扒堆,每家一堆,我家那堆小。我问:“干哈他们家大堆,我们家小堆呀?”我妈说:“你不懂,人家是队长。”“队长就要大堆?我也要大堆!”我就上小队队长家,抱一堆就走,小队长说:“这死丫头!为什么把我家的往你家抱!”我说:“你家堆大,我家堆小。”我哭,怎么富农就倒楣呀?为什么他贫农就多要?我妈说,“贫农是好人,这丫头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这么厉害呢!”
小时不知道党不党的,就知道政府坏,那时目标就很明确了,知道一定要反抗,不反抗就受欺负。
我刚上学时,说咱是富农孩子,想戴红领巾都不给戴呀,走道都给你隔开,人家贫农走一伴,路上她们拦着我就打一顿,欺负我,回家还不敢告诉我妈。后来我就背一个小草蛇或者几个壁虎上学,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她们一打我,我就把蛇往她们身上扔,她们吓跑了,我再把蛇捡回来,第二天上学再背上,这样放学我就能一路畅通回家了。
全家七口人,吃不饱,我大哥上山东背猪大油、背大馒头、背地瓜干。二哥上黑龙江背黄豆,第一回背了50斤,到车站,人一搜是黄豆,说他“投机倒把”,车站就给截留了。本来就是借钱弄的黄豆,结果空手回来。
12岁时,我放学看游斗“四类分子”,一看那不是我二哥吗?让人剃秃了,挂个大牌子,写个“投机倒把”,上面还打个叉,就因为他把槐树干削吧削吧就做了铁锹把,就给抓了游斗!
二、为村民的土地维权

刘华(本人提供)
17岁我就下学了(毕业),然后在小队干了几年活。1984年我22岁结婚,然后一直在沈阳苏家屯红菱镇的张良村里做生意。
2002年的时候,村书记不告诉村民,就把村里一千亩地给卖了。
人家说:“看你们两口子,好赖还做点生意,比我们有能耐,就帮我们写点材料,往上反映反映呗。”我虽然不种地,但地也有咱的,他抢、他非法卖,咱是应该要回一点。不就是写点材料往上反映吗?我想得特别简单。
以前也有人到村委会那个大院反映过土地的事,被村书记打了好几个耳光,大伙都在怵他。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就去找他,和他理论这个事。
书记说:“我当了24年的大队书记,我一个吐沫就是一个钉,我就是土皇上。”
“这回就不让你当钉!”我说,“把你这根针撅折了,你拿什么穿?我不路过你这针鼻儿,我告到联合国又怎样?”“你告吧,你告到联合国,也要穿过我这个小针鼻儿!”
我说:“我不穿,我越过你,我把你这个针撅折了,拿什么穿?你从开始卖地到现在,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土地局给你批条了吗?你拿得出来?没有,你就是抢!”书记的头低下来了。
我接着说:“高速公路拨下来这么多款,还有95年救灾款都哪去了?这二十多年,你们贪污这么多钱,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现在你卖地,也牵扯到我的地了,你要有个说法!还有《土地法》呐!”
村里老百姓就说,“噢,咋还有《土地法》呀?你咋知道有《土地法》呀?”
村里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在他们眼里就是有文化的了,虽然我初中没念满,但是我学习非常好,平时爱看书,愿意买书,什么《妇女杂志》啥的,都看。我上新华书店,买了一大摞《土地法》,村里一家发一本。我自己花钱买,让他们学。
那时候村书记他们已经卖了一块集体土地,都盖上房子了。我到市里上访要说法,说《土地法》怎么讲的,一条一条的,大队怎么违章的等等,他们认为我讲得有道理,就说:“回去你们扒房子吧,不犯法。”于是我回去我就组织村民,把《沈阳晚报》、《晨报》都给弄来了,把房子一天就扒完了。
扒完以后,区里和镇里的领导,天天穿个大风衣,戴个大口罩,上那地里挑小石头,因为要恢复成农田地,盖房的砖瓦块要挑出来嘛。
当时我脑子就有意识:查帐。我去沈阳会计所问,他们说查帐需要费用,于是我们就抬(村民集资)了6万块钱,二分钱利息抬的高利,让我丈夫代签借用。2002年时,村民已经选我丈夫当了村长,我丈夫是村长、法人,他有权利去审那个帐,所以说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公允的,是合法的。
还得把帐抢出来,会计师才能审查。曾经有的村去查帐,大队叫人给打成植物人了。所以抢帐那天,他们说“刘华你可要掂量好,抢帐就是你拿人家脑袋,人家就会拿你脑袋的”。当时我就想,可不能出差错,出差错我不就废了,孩子还小呢。
我们先去跟他们要帐,不给。我就让那书记坐在沙发上,让几个人看着他,我再把所有的电话全给薅下来了,让电话里外不通。
抢了帐,装上轿车,往村里小路上走,不上大道,转了几个地方,然后就又换面包车,一路换了四次车,才把这一车将近三十玻璃丝(塑料)袋子的帐目,全部拿到了沈阳荣正会计所。十二个审计人员审了大半年,查出我们村干部出卖集体土地、违法摊派、侵吞村民水电费和侵占救灾款等,审计发现有问题的金额达260馀万元,涉及前任书记王景财及现任书记刘家安等。列出审计报表报到公安部后,公安部就说要抓大队书记,但大队书记给公安送了一万斤大米及数万元钱,公安部就不了了之了。
但这块地没有让他卖成。俺们村靠法律维权,真的把官司给打赢了。
区里头还是不甘心,还要卖这块地,说不卖给老张,也要卖给老李,还要卖。公章在大队里,我半夜就去村委会,把公章偷回来,找个地方挖个坑埋起来了。我丈夫是村长,他们要是抢过公章,扣上公章把地就给卖了,我丈夫也有罪过啊。
哪想到他们会设计陷害我丈夫呢。2002年12月12号,那时下雪了,外面全上冻了。村里一个打更的,故意把村委办公室的地用湿拖布拖,之后把门窗打开,水磨石瓷砖的地,就冻上了薄薄一层冰。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漏水让我丈夫赶去处理。我丈夫赶到大队,哪知道地上有冰,大步流星走过去,一兹溜腿就撞到大队一楼中间的柱子上,整个膝盖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三级残疾,左腿和右腿差2寸,不能长时间走路了。后来问那个打更的,为什么大冷天拖地还开窗?他说是书记让他干的。
书记还想要公章,说有个妇女要开流产介绍信,要用公章,让我上大队去。我去了说:“村里老百姓选的妇女主任不用,你大队书记又当妇女主任又当大队书记。你在违法。你看这个妇女要个避孕套哇、要流产哪、要带环,还要找你大队书记,多别扭哇。”我说“你要那些避孕套干哈呀”?他说我寒碜他,一拳把我打倒,当时我就昏过去了。醒过来我就去了他家,脱了外衣就上他家炕,躺下睡觉。我说:“我不走了,今天就跟你过了,你不是把我丈夫的腿害残了吗?我就跟你过了。”他一看确实把我给打伤了,他就报警。派出所来了,警察说:“刘华,走,上医院给你看病去,你不能在人家待着。”我说我丈夫让他害残了,他还把我打了,我就跟他过了,我就不跟我丈夫过了。他们傻了,都过来哄我上医院去看病。
一天半夜12点,我正睡觉呢,一个电话把我弄醒:“我告诉你刘华,你再告,我把你脑袋拿下来!”是大队书记的侄子张富强。我马上打了110,010-110,北京的110。北京转到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的公安开着七八辆警车就去了他家。半夜1点,他家转圈全是警灯闪,张富强一下子就毛了。警察把门踢开,进门就拽他脖子:“你他妈大半夜去打恐吓电话,你知道刘华把电话打到哪了?打到北京,北京转到省公安厅了,我们还活不活了,为你小破事省公安厅都别睡觉!”霹雳吧啦把他揍了一顿。
后来书记又打了我一次,经过沈阳市法医鉴定“轻伤”,“轻伤”他就得坐牢啊,但官官相护,派出所所长包庇他,也不追究,就给他一个“警告”完事,还弄个笔误,说我把大队书记打了,我还得给大队书记拿二百块钱。这事谁能服哇,我被打了,我还要给他钱!我当然要告他!我就上北京告状。那时我丈夫正在当村长,到北京和我待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待续)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