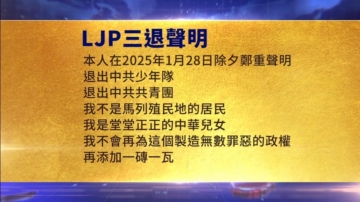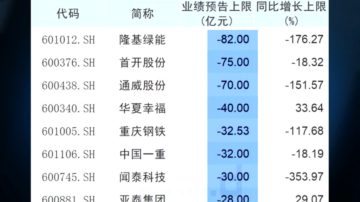“天安门事件”,发生在25年前的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中国政府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25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世界各国,包括日本,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改变不了血写的史实。
主持人告诉我,面对八九后的日本年轻人,我应该讲讲自己的故事,从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论家、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红色纸老虎内幕》(赤い中国消灭-张子の虎の内幕)一书中,叙说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从我能记事的三岁起,呈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场景:暴力、血腥与恐怖。我的父亲,一个中学教师,因为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断的迫害。被捆绑,被毒打,下跪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
我八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在长年的惊吓和贫病交加中,突然离开人世。父亲曾带上母亲,从西部的四川去东部的南京治病。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就连我们平时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当我惊异莫名,父亲说,那是骨灰盒。母亲在里面。原来,曾经美丽的母亲,已经像蜡烛一样,燃成了灰烬。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灾难。父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四个孩子长大。为了生存下去,从八岁开始,我就被迫从事沉重的劳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鱼,饲养鸡、猪、兔子、蜜蜂等,从早劳作到晚。别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正在干活的我,只能羡慕地看着。笼罩在家庭背景的阴影下,小学毕业后,我几乎失去升初中的机会。
1976年,统治中国长达27年的大独裁者毛泽东死亡,按照他临死前的指定,华国锋成为过渡时期的领导人,但毛的真正意图,却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为最高领导人;而在江青之后,将是毛的侄子毛远新。然而,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毛远新。以这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时代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经济建设年代。
毛泽东的死亡,让中国、也让我的人生出现转机。中国恢复了曾经被毛废止的高等教育。在家里排行最小的我,赶上了考大学的机会。十六岁那一年,我考上了位于毛故乡的湖南大学。
北京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停止。邓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紧紧追随毛泽东,但毛发动文革后,一度将他打入冷宫。华国锋开恩,允许邓再次出来担任领导职务。但邓恩将仇报,凭藉他的老谋深算,几年后,邓小平把华国锋赶下了台。
从1979年开始,75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当代中国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邓小平为首,有一个“老人帮”,其主要人物,被称为“八大元老”,他们控制了中国政治,越过宪法和党章,挑选或罢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后者相对年轻一些。
邓小平主张经济改革,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出任总书记和总理。在胡、赵主政下,198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最宽松、最开放的年代。曾经封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难,让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爱阅读,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十八岁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学图书馆,读到一本书:《斯大林与中央委员会》,作者是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中文的翻译本,只有在大学的图书馆才能见到。
这本书,让我陷入深思,继而霍然醒悟:中国的灾难,就像苏联的灾难一样,都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制度;毛泽东就像斯大林一样,都是冷血、残暴的独裁者。我意识到,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人民必须当家做主;中国的出路,在于民主化。从那以后,我暗暗立誓,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
思想变成行动,我开始在同学中谈论民主价值。1985年,当我在上海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我与身边的两个同学,用悄悄散发传单的方式,启蒙民主与自由。有一天,我踩着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独自到另一所大学散发传单,回去的路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精神很空虚,周围的人,都悠哉游哉、得过且过,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边的知音越来越多。1985年冬天,22岁那一年,我写了一封“万言书”,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中国政府,推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联合另外9名研究生,共10人,在万言书上连署签名。在中国,民间人士给领导人写信,通常冒着风险,如果领导人发怒,写信的人可能坐牢。
然而,胡耀邦没有发怒,反而派遣了两名官员,到上海来听取我们的意见。我感受到鼓舞,于是幻想,有胡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中国的民主进程,或许可以从政府的改革开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场却是,被“老人帮”赶下台。
1986年冬天,发源于安徽省的学生运动,波及到全国十几个城市,其中,以上海学生运动的规模最大,持续一周,每天上街示威的学生,都有几万人。12月20日那天,形成高潮,参加游行的学生,多达7万人,跟随和围观的市民更多。我引领游行队伍,踏遍了上海的几十条大街,一路领呼口号,直到嗓音完全沙哑。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我度过了难忘的23岁生日。
学生运动自发结束。在北京,胡耀邦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围攻、责难,经过一个多星期羞辱性的内部批判会,胡遭到罢黜,黯然下台。这一事件显示,手握实权的政治老人,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总书记的,是时任总理的赵紫阳,也是一位开明派、改革派,只不过,与胡耀邦相比,他显得更为沉稳、机敏,暂时获得邓小平和老人帮的信任。
八六学潮后,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出任经济系助教。到达广州后,我迅即开始在当地传播民主思想,并寻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给我泼冷水,说:广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人们热衷做生意,没人关心政治,没人对民主感兴趣。
但我并不气馁。不久,在我身边,就形成了一个向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1988年,我们开始计划,要在1989年发动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以纪念中国“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我发起每周民主沙龙,探讨中国前途,吸引了更多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参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这一突发事件,改变了我们原定在广州的计划。中国民主运动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包括广州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作为大学教师,我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名誉主席,除了组织示威游行,更奋笔疾书文告和大字报,每天书写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给学生领袖,成为他们的演讲稿;有的张贴在校园中心,启蒙思想;有的制成传单,成为街上的宣传品。
那段时间,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我们憧憬着,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
然而,老人政治,继续成为中国的顽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三十多万解放军,包围北京。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罢免了主张与学生对话、开启政治改革的开明派总书记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冲锋枪和机关枪扫射人群,用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燃烧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朝自己的人民开枪!
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最终不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经过一夜屠城,解放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镇压之后,当局展开了大逮捕。我被列为广东省的四大通缉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监狱。用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封闭的黑牢,彷如一座坟墓。在这样的坟墓里,我被活埋了三年。因为长年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皮肤变薄,一碰就会出血、溃烂,而且,伤口长时间不愈。头发变干,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来,直到三年刑满释放。
出狱后,我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再次受到当局传讯。我逃往香港,却遭香港警方遣返。于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狱。这回,当局未经审判,就将我判处两年劳教。为了报复我,当局将我发配到一处山区,白天,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在劳教场制作人造花。在管教干部和犯人头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们像奴隶一样劳作。彷如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场面。
我发现,我们生产的人造花,被贴上了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因而怀疑,中国当局非法出口奴工产品。于是,我暗中写信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揭露劳教场的黑暗,并附上人造花商标,供他们查证。我的密信,经过曲折的路径,到达美国。人权组织在美国商店发现了这类商品,证明中国当局非法出口有我参与制作的奴工产品。由此,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劳教场也不愿再容留我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这两重因素下,我被提前释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获自由。
出狱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信件受检查,电话遭窃听,行走被跟踪,并经常被公安官员约谈。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还困在监狱中。其实,整个中国,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大监狱。我同时发现,“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社会整体沉沦,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铜臭薰天,中国政府有意将中国人民引导到一个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境界,让中共政权免受挑战。公安官员对我表示:愿意协助办理护照,让我出国。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民运人士,要么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么出走海外。
1996年冬天,我前往美国。沈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心切,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为流亡者,我可以去任何国家,唯独不能去中国——自己的祖国。我多次造访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故国方向,心中苦痛,犹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
流亡中,我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同时没有放弃对民主事业的坚守。我勤于笔耕,经常发表政论;不断出版着作,解析中国政局。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和电台上,我逐渐成为频繁出镜的政论嘉宾。我的思考和政见,通过网际网路和翻墙技术,持续影响着海内外中国人。
儿时的磨练,民主运动的洗礼,铁窗下的坚韧,所有这些经验,积累成顽强的生存力,以至于,在流亡中,我仍然能够创业,在美国白手起家,成功开创了一所商业学校。被周围人誉为又一个成功的“美国故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天安门事件,过去了25年;我的流亡生涯,也过去了17年。当年的民主运动,口号是“反腐败”、“要民主”。今天的中国官场,更加腐败,百倍、千倍的腐败,中国官员,凭藉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并将财富、家属、子女大量转移外国。
今天的中国政治,更加黑暗。当权者陷入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毫无安全感;异见人士下狱,前仆后继;新疆爆炸声不断;各地砍杀事件频发;西藏人接连自焚……作为独裁政权,中国政府对内镇压的同时,也强化对外威胁,穷兵黩武,四面树敌,显露危险的军国主义倾向。
这一切证明,所谓“中国威胁”,其实是中共威胁,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而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惠泽于中国人民,也将惠泽于世界人民。
2014年5月29日,于东京日本大学
我在红色恐惧中长大
主持人告诉我,面对八九后的日本年轻人,我应该讲讲自己的故事,从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论家、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红色纸老虎内幕》(赤い中国消灭-张子の虎の内幕)一书中,叙说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从我能记事的三岁起,呈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场景:暴力、血腥与恐怖。我的父亲,一个中学教师,因为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断的迫害。被捆绑,被毒打,下跪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
我八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在长年的惊吓和贫病交加中,突然离开人世。父亲曾带上母亲,从西部的四川去东部的南京治病。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就连我们平时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当我惊异莫名,父亲说,那是骨灰盒。母亲在里面。原来,曾经美丽的母亲,已经像蜡烛一样,燃成了灰烬。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灾难。父亲一人,拉扯着我们四个孩子长大。为了生存下去,从八岁开始,我就被迫从事沉重的劳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鱼,饲养鸡、猪、兔子、蜜蜂等,从早劳作到晚。别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正在干活的我,只能羡慕地看着。笼罩在家庭背景的阴影下,小学毕业后,我几乎失去升初中的机会。
毛泽东死亡,中国的转机
1976年,统治中国长达27年的大独裁者毛泽东死亡,按照他临死前的指定,华国锋成为过渡时期的领导人,但毛的真正意图,却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为最高领导人;而在江青之后,将是毛的侄子毛远新。然而,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毛远新。以这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时代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经济建设年代。
毛泽东的死亡,让中国、也让我的人生出现转机。中国恢复了曾经被毛废止的高等教育。在家里排行最小的我,赶上了考大学的机会。十六岁那一年,我考上了位于毛故乡的湖南大学。
北京高层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停止。邓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紧紧追随毛泽东,但毛发动文革后,一度将他打入冷宫。华国锋开恩,允许邓再次出来担任领导职务。但邓恩将仇报,凭藉他的老谋深算,几年后,邓小平把华国锋赶下了台。
邓小平开启老人政治
从1979年开始,75岁高龄的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当代中国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邓小平为首,有一个“老人帮”,其主要人物,被称为“八大元老”,他们控制了中国政治,越过宪法和党章,挑选或罢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后者相对年轻一些。
邓小平主张经济改革,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出任总书记和总理。在胡、赵主政下,198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最宽松、最开放的年代。曾经封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难,让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爱阅读,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十八岁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学图书馆,读到一本书:《斯大林与中央委员会》,作者是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中文的翻译本,只有在大学的图书馆才能见到。
这本书,让我陷入深思,继而霍然醒悟:中国的灾难,就像苏联的灾难一样,都是因为一党专政的制度;毛泽东就像斯大林一样,都是冷血、残暴的独裁者。我意识到,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人民必须当家做主;中国的出路,在于民主化。从那以后,我暗暗立誓,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奋斗。
胡耀邦,1986年的学生运动
思想变成行动,我开始在同学中谈论民主价值。1985年,当我在上海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我与身边的两个同学,用悄悄散发传单的方式,启蒙民主与自由。有一天,我踩着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独自到另一所大学散发传单,回去的路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精神很空虚,周围的人,都悠哉游哉、得过且过,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边的知音越来越多。1985年冬天,22岁那一年,我写了一封“万言书”,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中国政府,推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联合另外9名研究生,共10人,在万言书上连署签名。在中国,民间人士给领导人写信,通常冒着风险,如果领导人发怒,写信的人可能坐牢。
然而,胡耀邦没有发怒,反而派遣了两名官员,到上海来听取我们的意见。我感受到鼓舞,于是幻想,有胡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中国的民主进程,或许可以从政府的改革开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场却是,被“老人帮”赶下台。
1986年冬天,发源于安徽省的学生运动,波及到全国十几个城市,其中,以上海学生运动的规模最大,持续一周,每天上街示威的学生,都有几万人。12月20日那天,形成高潮,参加游行的学生,多达7万人,跟随和围观的市民更多。我引领游行队伍,踏遍了上海的几十条大街,一路领呼口号,直到嗓音完全沙哑。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我度过了难忘的23岁生日。
学生运动自发结束。在北京,胡耀邦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围攻、责难,经过一个多星期羞辱性的内部批判会,胡遭到罢黜,黯然下台。这一事件显示,手握实权的政治老人,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总书记的,是时任总理的赵紫阳,也是一位开明派、改革派,只不过,与胡耀邦相比,他显得更为沉稳、机敏,暂时获得邓小平和老人帮的信任。
八六学潮后,我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出任经济系助教。到达广州后,我迅即开始在当地传播民主思想,并寻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给我泼冷水,说:广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人们热衷做生意,没人关心政治,没人对民主感兴趣。
天安门事件,民主运动的高潮
但我并不气馁。不久,在我身边,就形成了一个向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1988年,我们开始计划,要在1989年发动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以纪念中国“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我发起每周民主沙龙,探讨中国前途,吸引了更多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参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这一突发事件,改变了我们原定在广州的计划。中国民主运动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包括广州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作为大学教师,我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的名誉主席,除了组织示威游行,更奋笔疾书文告和大字报,每天书写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给学生领袖,成为他们的演讲稿;有的张贴在校园中心,启蒙思想;有的制成传单,成为街上的宣传品。
那段时间,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我们憧憬着,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
“六四”大屠杀,中国的希望破灭
然而,老人政治,继续成为中国的顽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三十多万解放军,包围北京。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罢免了主张与学生对话、开启政治改革的开明派总书记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冲锋枪和机关枪扫射人群,用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燃烧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朝自己的人民开枪!
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最终不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经过一夜屠城,解放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身陷囹圄,揭露中国黑狱丑闻
镇压之后,当局展开了大逮捕。我被列为广东省的四大通缉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监狱。用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封闭的黑牢,彷如一座坟墓。在这样的坟墓里,我被活埋了三年。因为长年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皮肤变薄,一碰就会出血、溃烂,而且,伤口长时间不愈。头发变干,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来,直到三年刑满释放。
出狱后,我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再次受到当局传讯。我逃往香港,却遭香港警方遣返。于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狱。这回,当局未经审判,就将我判处两年劳教。为了报复我,当局将我发配到一处山区,白天,在码头抬石头装船;晚上,在劳教场制作人造花。在管教干部和犯人头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们像奴隶一样劳作。彷如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场面。
我发现,我们生产的人造花,被贴上了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因而怀疑,中国当局非法出口奴工产品。于是,我暗中写信给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揭露劳教场的黑暗,并附上人造花商标,供他们查证。我的密信,经过曲折的路径,到达美国。人权组织在美国商店发现了这类商品,证明中国当局非法出口有我参与制作的奴工产品。由此,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劳教场也不愿再容留我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在这两重因素下,我被提前释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获自由。
出狱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监控。信件受检查,电话遭窃听,行走被跟踪,并经常被公安官员约谈。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还困在监狱中。其实,整个中国,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大监狱。我同时发现,“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社会整体沉沦,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铜臭薰天,中国政府有意将中国人民引导到一个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境界,让中共政权免受挑战。公安官员对我表示:愿意协助办理护照,让我出国。他们说:像你这样的民运人士,要么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么出走海外。
流亡生涯,坚守民主事业
1996年冬天,我前往美国。沈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心切,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为流亡者,我可以去任何国家,唯独不能去中国——自己的祖国。我多次造访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故国方向,心中苦痛,犹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
流亡中,我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同时没有放弃对民主事业的坚守。我勤于笔耕,经常发表政论;不断出版着作,解析中国政局。在美国的中文电视和电台上,我逐渐成为频繁出镜的政论嘉宾。我的思考和政见,通过网际网路和翻墙技术,持续影响着海内外中国人。
儿时的磨练,民主运动的洗礼,铁窗下的坚韧,所有这些经验,积累成顽强的生存力,以至于,在流亡中,我仍然能够创业,在美国白手起家,成功开创了一所商业学校。被周围人誉为又一个成功的“美国故事”。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天安门事件,过去了25年;我的流亡生涯,也过去了17年。当年的民主运动,口号是“反腐败”、“要民主”。今天的中国官场,更加腐败,百倍、千倍的腐败,中国官员,凭藉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并将财富、家属、子女大量转移外国。
今天的中国政治,更加黑暗。当权者陷入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毫无安全感;异见人士下狱,前仆后继;新疆爆炸声不断;各地砍杀事件频发;西藏人接连自焚……作为独裁政权,中国政府对内镇压的同时,也强化对外威胁,穷兵黩武,四面树敌,显露危险的军国主义倾向。
这一切证明,所谓“中国威胁”,其实是中共威胁,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而中国的民主化,不仅惠泽于中国人民,也将惠泽于世界人民。
2014年5月29日,于东京日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