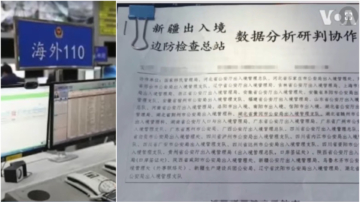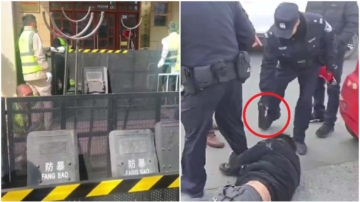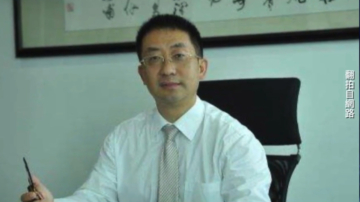(编者按语:北京法轮功学员许那,曾经在北京女子监狱经历过11种酷刑后,活着走了出来。她凭着记忆,记录下了那段骇人的历史真相。如今她又身陷囹圄,读着她的记述,令人感触至深。)
一
我多么希望自己被关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不是中国的监狱。因为在纳粹的毒气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监狱,它让你活着生不如死。反覆经历漫长的酷刑,酷刑中他们配备懂医的犯人看护,随时检测你的体征。我在那儿多日不被允许睡觉,被发现心律不齐。于是警察命令说:“让她睡一小时,休息一下。”
各种各样隐蔽而精致的酷刑被发明,比如:劈叉,将双腿拉开成180度,命令三个犯人坐在受刑人的双腿及后背上,反覆按压。警察自豪于这个发明:“这个办法好,因为疼痛难忍,但又不伤及骨头。”
纳粹反人类的目的是消灭犹太人的身体,而它们的目的是摧毁人的精神、良知。当我在酷刑与洗脑中更加挺直腰板时,一个警察认真地对我说:“应该申请对你进行开颅手术,把你的大脑摘掉。”
那些自以为自己在中国自由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摘除了精神,生活于一个无形的大监狱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认同它存在、认同它应该继续存在,获罪于天,岂能长久?
所以每一个被扭紧的螺丝钉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这个机器的邪恶运转。那些想从它那里得到名利和各种好处的,正如孔子所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二
我受到传媒的最深刻的教育,不是在大学课堂,而是在监狱。2003年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徐滔采访北京女子监狱,我被隔离在警察办公室。四个犯人,以人肉铐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听到不远处采访现场,对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讲它们如何文明执法,而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的嘴里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共同受教于以培养党的喉舌为宗旨的中国传媒大学,如今她是北京电视台的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
这次采访后不久,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监。最后称她为病死,我因检举、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实,再次被投入小号折磨。
几年后,同样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与他同一监室的在押人员承认,他为于宙的死做了伪证,但他说:“我不敢讲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灭口。”
我的好朋友孙毅,因为从马三家劳教所成功寄出一封求救信,讲述了他被奴役迫害的事实,最后即使他到了印尼的一个小岛,也没躲过它伸长的手。
三十多年前,我因政审不合格,不是团员,尽管分数远远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也被拒收,误入传媒大学。
89学潮时,我和我的同学上街游行,共同打出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标语。
“六四”以后,我决心远离它,离开广电部改行成为一个自由画家,对世事不闻不问,以为从此可以岁月静好。
多年的亲身经历使我觉醒,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不公义都离我很近,我不能装作看不见,它最后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世界每一件不公义,即使离你很远,也与你息息相关,因为他时刻拷问着你的良知。
有些事于我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我无可逃避。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