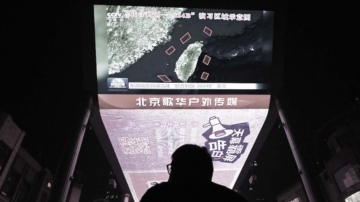史学泰斗余英时8月1日于美国寓所睡梦中溘然长逝,享耆寿91岁。余英时先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第一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他具足独立思考能力,勇于坚持真理、拒绝中共极权统治,诚为一代“士大夫”。
总统蔡英文高度赞扬余英时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领域的学术成就,同时,蔡英文也力赞余英时深具入世关怀,敢于批判共党专制、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坚持平反六四,到关注台湾的民主自由发展,从来不曾对强权低头。“余英时一辈子的学思言行,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蔡英文表示,近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和反送中运动,余英时都不忘挺身为年轻人声援打气。他提醒“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蔡总统表示会谨记在心,更会身体力行。
余英时鲜为人知的小粉红过往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位反共立场鲜明的一代大儒,曾于1949年中共刚建政时,被动加入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团员。余英时回忆年少就读中学时的这段经验表示,在申请入团的时期,他在精神上发生了一次变异。这一变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染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另一则是‘左倾幼稚病’。这两种精神变态互相支持,有时一触即发,造成个人的罪过。”1949年12月下旬,有一位安徽同乡到余英时家中造访他的堂兄,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安徽芜湖传教。他告诉余英时安徽的近况,主要是中共地方干部怎样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及穷人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困难等等。
然而,这位牧师的话还没有讲完,当时加入中共团员,是“小粉红”的余英时立刻气极攻心,“我的左倾幼稚病和狂热症已同时发作了。”于是余英时声色俱厉地驳斥牧师的事实陈述,所持理由大致是中共当局的宣传八股,什么他国敌对势力的谎言攻击之类。“我当时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无几。”牧师猝不及防,满脸错愕,狼狈而去。
大概十几天后,余英时去香港,在上海亲戚家中住了两三天,听到南方的实际情况比那位牧师所说的更为可怕。“我虽然还勉强为之辩护,然而心中已后悔不应该对那位牧师如此粗暴无礼了。时间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余英时每一思及此事便觉得无地自容。“如果说这件事对我起过什么教训作用,那便是让我认识到人心中深藏着种种邪恶,一旦释放出来,整个人一定会被吞蚀掉。”
事实上,影响少年余英时的邪恶对现在大陆与台湾民众来说实在太熟悉了。远者有周子瑜只因为拿着青天白日国旗就被疯狂攻击,被迫穿黑衣道歉;近者有作家方方只因为说出武汉疫情实况,着书出版,就被说成是给外国势力“递刀”,被谩骂到几无立足无地;近者如数天前小S蔡依林只因为替奥运国手加油就被大肆辱骂“台独”“辱华”,小S跟女儿立刻被厂商切割、取消代言;甚至中国桌球选手“双塔”李俊慧、刘雨辰因为输给台湾队,虽获得银牌也被小粉红“出征”……看来五毛粉红还真是不分国内外一律无差别攻击。
这个吞噬一切温情的怪兽不是源自于人之本性,而是中共组织洗脑灌输的“邪教教旨”,这个东西就像附身一样,一旦踩到它,马上就会“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失去理性与人性,一味往前杀、杀、杀。这完全不是人类正常的情感情绪与思维观念。
关键决定抛弃党性 走出“小粉红”附身
那么余英时是怎么走出“小粉红”附身的呢?说来非常惊险。原本少年余英时在燕京(今北京)读书,但他的父母与弟弟辗转到了香港,他为了探望父母与弟弟,费了很大周折申请到香港探亲,当时他一心一意只想利用寒假一个多月期间和家人重聚一次,之后仍回燕京继续学业。1949年最后一晚,余英时坐在深圳地上,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1950年元旦)经过深圳的罗湖桥进入香港。当时他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因为对中共认识不清,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刹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余英时说。
在多年之后,余英时才想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自己早年受学者胡适影响,已经认同了西方的科学、民主、个人主义等普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受到中共政府压迫的。然而在当时,少年余英时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可能是中共的压迫对象,但是潜意识里,早慧如他还是明白的。
“在潜意识中我一定极力压抑着原有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不让它们有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这一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和压抑积了好几个月之久,一旦回到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心理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精神变异便发生了。”
见过父母之后,余英时预备整装重返中国大陆,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北上火车故障,被迫留在广州几个小时,就在这几个小时中,他的“人性”一面起了关键作用,促使他进行深刻的反思。
他左思右想,顾念父亲年事已高,还是应该留在父母身旁陪伴,“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再者,当时韩战已经爆发,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出入日趋严格,回北京以后,再访香港的机会将十分渺茫,这次分手便成为不折不扣的“生离死别”了,“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悔心大起。”
但是中共当时鼓吹的“新民主主义”事业怎么办呢?余英时很快便找到了一种解脱之道:新民主主义团员不计其数,而且正在不断增加,少他一个人似乎无足轻重。他认为自己的新决定情理兼到,然而用当时中共的语言来表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结语
事实上,余英时当时做出关键决定,是因为他对家人的情感恩义超过了共产党鼓吹的“为党牺牲一切”的党性,让他毅然决定抛弃中共团员身分,回到家人身边。第二天余英时便重返香港,他说:“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在时局动荡、青年普遍左倾的潮流中,少年余英时能做出这样明智的决定真是万幸!也多亏这个关键决定,让世界上少了一位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凋零的知识分子,多了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国学泰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