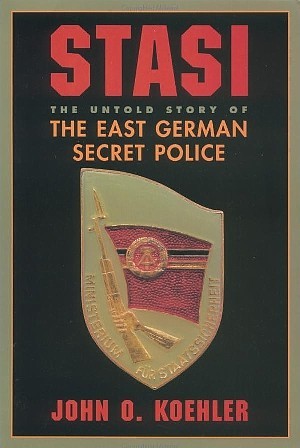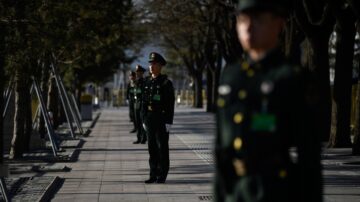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0年2月26日訊】
告密體系及其社會創傷——納粹德國的祕密警察與線人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八天後,東德國家安全部(MfS)更名爲國家安全辦公室(AfNS),但這沒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羅總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祕密警察組織之一終於走到了盡頭。
MfS有一個更廣爲人知的名稱:斯塔西(Stasi,德語“國安”一詞的縮寫)。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它構建起了一張由幾十萬線人組成的大網,將幾乎所有的東德公民罩在網中。身邊有形或無形的監視者、監聽者和告密者———無論他們是出於有據可查的事實,抑或只是來 自傳言、懷疑或想象,皆成爲東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現實。斯塔西及其似乎無處不在的祕密線人,就這樣定義著東德人的日常生活,成爲每個人言行起居中朝夕 相處,必不可少,有機而且動態的組成部分。
經由思想控制、經濟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龐大的祕密警察組織及其掌握的密織的線人網路,民主德國打造出了一個嚴密布控的社會,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對內(對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種頗爲安全與穩定的社會幻象。這種穩定的程度不僅大大強於其東部大家庭的兄弟們,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甚至超過了在1960-70年代經歷了巨烈動蕩的資本主義同胞、西鄰的近敵聯邦德國。然而,我們之所以稱之爲幻象,是因爲這種穩 定並無堅實的內在基礎。穩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內部的高壓和外部兩大強力集團難分伯仲的對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對抗失衡,內壓立刻決口,整個體系頃刻間瓦 解,國家瞬間不復存在。
二十年過去了,斯塔西對東德人造成的社會創傷、心理陰影和情感痛苦仍舊難以平復。
最強大最有效
東德似乎並不公開鼓勵檢舉揭發,亦不大力宣揚告密文化,而是通過廣泛、細密、有效的組織工作,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肌體,從上至下,層層布控,有效預防,對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言行實行全面監督。德國人爲共同目標而不惜冷對個體的哲學淵源,做事務求條理分明、執行 程式嚴謹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條主義的行事作風,均爲斯塔西發展成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效的祕密警察組織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創設以來,斯塔西的 雇員始終在穩定增長。1974年,該組織已有全職員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則達到91000人。這些人的親友往往知道 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數以十萬計的、散佈於社會各個行業、各個角落的非正式雇員,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告密者”(本文將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線人”,來代替感情色彩強烈的“告密者”一詞)。
1995年,根據已不完整的官方記錄(斯塔西在解散前已開始檔案銷毀行動),1989年時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員 17.4萬名,約占當時東德18-60周歲公民的2.5%.約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東德祕密警察祕史》(2000)一 書中認爲,其總人數可能接近50萬(另據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計,若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線人總數可能高達200萬人),平均每166位東德公民,便 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東德因此成爲世界上祕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國家。蘇聯克格勃有4.8萬雇員,監控全國2.8億人,平均每人負責5830位國民。若 計入非正式雇員,則斯塔西每人監控66人。如果連臨時雇員也包括在內,那麽每6.5個東德公民中,便有一人爲祕密警察工作。
東德所有的大企業中,均派駐有全職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樓亦指派一人,充任監視者,直接向管片民警報告。每有住戶的 親戚朋友在此過夜,斯塔西都會得到報告。賓館房間的牆壁通常開有祕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針孔照相機或攝影機進行祕密拍攝。若有敵對嫌疑人進入監控名 單,斯塔西便會在其家中布設設備,祕密監聽。大學和醫院亦被廣泛滲透。
斯塔西的座右銘是“黨的盾與劍”(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這句話在電影《竊聽風暴》中曾兩次被提及。線人的工作亦圍繞著這一目標展開,但因工作性質的不同,又有細分。據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統一後德國之罪疚與順從的敍述:斯塔西線人及其社會影響》(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書所述,人數最衆,分佈最廣的是非正式雇員(IMS),即民間線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綱領指 出,IMS“在全面確保國內安全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其工作是預防性的,爲“應對新的安全需求而進行早期的輔助偵察與落實”,特別是要弄清“誰是誰”的 問題。
斯塔西極爲看重IMS,其各個時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斷強調這一點。“非正式雇員是與階級敵人祕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 素”(1958):“非正式雇員是國家安全部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1968):“我們的政治工作所期望達成的政治與社會影響,有賴與非正式 雇員進行高質量與有效的配合,他們是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1979)。
沒有英雄
兩德統一最初的歡欣之後,原來的東德人很快發現,曾經憧憬的美好生活並未到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生活和職業保障卻一 去不返。失業率猛增,東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學習謀生技能,嘗試適應曾經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學會自己做決定。相對於國家替你決定一切的舊體制,統 一後的自由反而令許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於他們的歧視和怠慢,相較於舊體制的壓制,似乎更加不堪。現在,他們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個人或集體的理想 與自尊,過往的人生變得一錢不值。
在東部,自憐和戀舊的情緒高漲,已經不復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竟然在某種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 播出了一套系列紀錄片,講述東歐人對社會主義大家庭時代的回憶,好壞兼有。一位女士說,較之現在,東德時代的婦女更爲獨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對鏡頭說。
然而,國家不僅照料其公民,亦監控他們,而這種監控的深度和廣度,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政府可能都難望其項背。統一後斯 塔西祕密檔案的逐漸公開,對許多東部德國人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逼使某些人重新審視那個失樂園。“這些文件不僅有助於前東德人得知並瞭解自己的歷史,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們對過去重新定義。”芭芭拉·米勒女士寫道。
檔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驚,例如,1987年的記錄顯示,當時東德作協的19位最高委員中,竟有多達12人是斯塔 西的線人。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深受祕密警察之苦、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堅決反對在沒有甄別清算前東德作 家歷史污點的情況下,實行兩德作家組織的合併,並爲此於1997年宣佈退出德國筆會中心。
在德國東部地區,赫塔·米勒並不是很受歡迎的人。1999年,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的時候,她告訴RFE電臺羅馬尼亞語 -摩爾多瓦語部的米爾恰·約爾古萊斯庫,儘管已經統一多年,但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兩個德國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德國東部更近於東歐而非本國西部。“在東 部德國,有些人不請我去朗讀作品,”她說,因爲他們不想以直接了當的批判回望過去。但也有人請她。“可以說,在德國西部,大多數人只是對我的書抱有理論上 或文獻上的興趣,而東部人會通過我的書面對自己的過去和人生。有些人爲此覺得不快。許多次在德國東部,我朗讀完,首先就會聽到聽衆提問:”可羅馬尼亞的情 況當然比我們這兒惡劣。‘我告訴他們:“這要看你怎麽看待那些事。’”她說,許多東部人不願意相信的是,從整體上講,羅馬尼亞和東德之間的不同沒有他們願 意相信的那麽大,可聽衆不喜歡這種看法。
隨著祕密檔案的公開,線人們不斷曝光並受到譴責的同時,公衆也發現,自己每次都會落入相同的、極爲複雜的道德困境。 “斯塔西的線人們始終是(東德)國家機構中一個極爲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如果沒有大多數東德人的沈默作爲配合,這一體系斷然不會如此有效運轉。”芭芭拉·米 勒就此寫道,“作爲機會主義的盲從者,個人之所以與集體保持一致,是因爲他們在這種物質安全、社會安定的平庸圖景中安於渾渾噩噩,其中之個人,則堅定不疑 地服從於那種對簡單及相對和諧之生活的欲望。”
我認爲,當集體恥辱感逐漸增強到一個臨界點,這個集體就將面臨極大的風險———完全的自我否認。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承 認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從的、心甘情願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無意義的。出於本能,集體會避免讓自身落入這種深淵。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找到救贖 者。兩個月前,翁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裡尼的法西斯政權勒令全國1200位大學教授宣誓效忠,僅有12人拒絕,並爲此失去工作。其餘 皆爲保住教職而屈從。“也許這1188人是對的,”艾柯說,“但那12個人挽救了其大學、乃至我們國家的榮譽。這就是爲什麽你必須說不,即便這樣做毫無益 處。因爲有朝一日,你可以說,你說過不。”
十二君子僅僅是大學教授集體的百分之一,在全體義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們事後足以爲集體恥感提供一個排遣 的通道,雖不至完全脫罪,亦可讓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種平衡。如果一個集體找不到可引爲代表的英雄,幫他們卸去頸上的重軛,讓他們有理由說出:“我們也曾反抗 過,”那麽這個集體終將不能自如地面對過去。
東德卻沒有英雄。
羞恥與失憶
1993年初,前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裡絲塔·沃爾夫(Christa Wolf)被指認曾在1959至1961年間爲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員,代號“瑪格麗特”。沃爾夫女士的反應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認,半年多之後,檔案 將不可辯駁的證據呈現於前,她又改口,說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卻,並辯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線人大多保持沈默,直至白紙黑字的證據出現。然而對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芭芭拉·米勒在前述專著中,對上述情況做了分析:
傳統的記憶複製理論認爲,人的記憶是對過往事件的精確複製,但心理學家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自我記憶的機理往往與此相 反。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社會心理學教授邁克爾·羅斯發現,個體會使用“絕對自信的理論來構建其個人歷史”。也就是說,人們趨向於用當前對自我的理解來“推 斷”他們過去的行爲。除非有明確的資訊讓我們相信自己的態度和行爲已經發生了變化不然我們便很可能有意誇大過去與現在的相似性,並以此重構記憶。
“謝天謝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記了。”沃爾夫女士寫道,“如果我還記得那件事,我怎麽能活過那麽多年,怎麽還能繼續寫作,我還能相信誰?”
事發時,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擊。然而輿論最初的歇斯底裡過後,不斷出現的檔案逐漸還原出更爲客觀的歷史:沃 爾夫與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並且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不僅如此,自從年輕時的政治幼稚之後,她日益轉向政權的對立面(她被稱爲“忠誠的異 見者”,在批評政府的同時仍然保持社會主義信念),並爲此與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長達20年的不間斷監視,寫於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 的半自傳體小說《餘留之物》(Was bleibt),記述了那段監控之下的生活。
該書甫一面世,即遭指責。評論界指其僞善,以東德時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圖謀於新時代。三年後斯塔西祕檔曝光,輿論衆口一辭,大有將她打入地獄之勢。這正是面對歷史時的亂局與困境,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皆難以脫逃,亦難以承擔。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時間似乎漫長,卻又像彈指一揮間。它的幽靈仍然糾纏著許多人,也許每夜都來,徘徊於枕邊,讓他們至死不能釋懷。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
告密體系及其社會創傷——納粹德國的祕密警察與線人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八天後,東德國家安全部(MfS)更名爲國家安全辦公室(AfNS),但這沒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羅總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祕密警察組織之一終於走到了盡頭。
MfS有一個更廣爲人知的名稱:斯塔西(Stasi,德語“國安”一詞的縮寫)。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它構建起了一張由幾十萬線人組成的大網,將幾乎所有的東德公民罩在網中。身邊有形或無形的監視者、監聽者和告密者———無論他們是出於有據可查的事實,抑或只是來 自傳言、懷疑或想象,皆成爲東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現實。斯塔西及其似乎無處不在的祕密線人,就這樣定義著東德人的日常生活,成爲每個人言行起居中朝夕 相處,必不可少,有機而且動態的組成部分。
經由思想控制、經濟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龐大的祕密警察組織及其掌握的密織的線人網路,民主德國打造出了一個嚴密布控的社會,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對內(對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種頗爲安全與穩定的社會幻象。這種穩定的程度不僅大大強於其東部大家庭的兄弟們,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甚至超過了在1960-70年代經歷了巨烈動蕩的資本主義同胞、西鄰的近敵聯邦德國。然而,我們之所以稱之爲幻象,是因爲這種穩 定並無堅實的內在基礎。穩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內部的高壓和外部兩大強力集團難分伯仲的對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對抗失衡,內壓立刻決口,整個體系頃刻間瓦 解,國家瞬間不復存在。
二十年過去了,斯塔西對東德人造成的社會創傷、心理陰影和情感痛苦仍舊難以平復。
最強大最有效
東德似乎並不公開鼓勵檢舉揭發,亦不大力宣揚告密文化,而是通過廣泛、細密、有效的組織工作,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肌體,從上至下,層層布控,有效預防,對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言行實行全面監督。德國人爲共同目標而不惜冷對個體的哲學淵源,做事務求條理分明、執行 程式嚴謹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條主義的行事作風,均爲斯塔西發展成世界上最強大、最有效的祕密警察組織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創設以來,斯塔西的 雇員始終在穩定增長。1974年,該組織已有全職員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則達到91000人。這些人的親友往往知道 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數以十萬計的、散佈於社會各個行業、各個角落的非正式雇員,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告密者”(本文將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線人”,來代替感情色彩強烈的“告密者”一詞)。
1995年,根據已不完整的官方記錄(斯塔西在解散前已開始檔案銷毀行動),1989年時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員 17.4萬名,約占當時東德18-60周歲公民的2.5%.約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東德祕密警察祕史》(2000)一 書中認爲,其總人數可能接近50萬(另據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計,若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線人總數可能高達200萬人),平均每166位東德公民,便 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東德因此成爲世界上祕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國家。蘇聯克格勃有4.8萬雇員,監控全國2.8億人,平均每人負責5830位國民。若 計入非正式雇員,則斯塔西每人監控66人。如果連臨時雇員也包括在內,那麽每6.5個東德公民中,便有一人爲祕密警察工作。
東德所有的大企業中,均派駐有全職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樓亦指派一人,充任監視者,直接向管片民警報告。每有住戶的 親戚朋友在此過夜,斯塔西都會得到報告。賓館房間的牆壁通常開有祕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針孔照相機或攝影機進行祕密拍攝。若有敵對嫌疑人進入監控名 單,斯塔西便會在其家中布設設備,祕密監聽。大學和醫院亦被廣泛滲透。
斯塔西的座右銘是“黨的盾與劍”(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這句話在電影《竊聽風暴》中曾兩次被提及。線人的工作亦圍繞著這一目標展開,但因工作性質的不同,又有細分。據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統一後德國之罪疚與順從的敍述:斯塔西線人及其社會影響》(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書所述,人數最衆,分佈最廣的是非正式雇員(IMS),即民間線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綱領指 出,IMS“在全面確保國內安全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其工作是預防性的,爲“應對新的安全需求而進行早期的輔助偵察與落實”,特別是要弄清“誰是誰”的 問題。
斯塔西極爲看重IMS,其各個時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斷強調這一點。“非正式雇員是與階級敵人祕密活動作戰的最重要因 素”(1958):“非正式雇員是國家安全部所開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絕對核心”(1968):“我們的政治工作所期望達成的政治與社會影響,有賴與非正式 雇員進行高質量與有效的配合,他們是同敵人作戰時的主要武器”(1979)。
沒有英雄
兩德統一最初的歡欣之後,原來的東德人很快發現,曾經憧憬的美好生活並未到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生活和職業保障卻一 去不返。失業率猛增,東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學習謀生技能,嘗試適應曾經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學會自己做決定。相對於國家替你決定一切的舊體制,統 一後的自由反而令許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於他們的歧視和怠慢,相較於舊體制的壓制,似乎更加不堪。現在,他們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個人或集體的理想 與自尊,過往的人生變得一錢不值。
在東部,自憐和戀舊的情緒高漲,已經不復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竟然在某種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 播出了一套系列紀錄片,講述東歐人對社會主義大家庭時代的回憶,好壞兼有。一位女士說,較之現在,東德時代的婦女更爲獨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對鏡頭說。
然而,國家不僅照料其公民,亦監控他們,而這種監控的深度和廣度,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政府可能都難望其項背。統一後斯 塔西祕密檔案的逐漸公開,對許多東部德國人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衝擊,逼使某些人重新審視那個失樂園。“這些文件不僅有助於前東德人得知並瞭解自己的歷史,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們對過去重新定義。”芭芭拉·米勒女士寫道。
檔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驚,例如,1987年的記錄顯示,當時東德作協的19位最高委員中,竟有多達12人是斯塔 西的線人。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深受祕密警察之苦、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堅決反對在沒有甄別清算前東德作 家歷史污點的情況下,實行兩德作家組織的合併,並爲此於1997年宣佈退出德國筆會中心。
在德國東部地區,赫塔·米勒並不是很受歡迎的人。1999年,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的時候,她告訴RFE電臺羅馬尼亞語 -摩爾多瓦語部的米爾恰·約爾古萊斯庫,儘管已經統一多年,但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兩個德國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德國東部更近於東歐而非本國西部。“在東 部德國,有些人不請我去朗讀作品,”她說,因爲他們不想以直接了當的批判回望過去。但也有人請她。“可以說,在德國西部,大多數人只是對我的書抱有理論上 或文獻上的興趣,而東部人會通過我的書面對自己的過去和人生。有些人爲此覺得不快。許多次在德國東部,我朗讀完,首先就會聽到聽衆提問:”可羅馬尼亞的情 況當然比我們這兒惡劣。‘我告訴他們:“這要看你怎麽看待那些事。’”她說,許多東部人不願意相信的是,從整體上講,羅馬尼亞和東德之間的不同沒有他們願 意相信的那麽大,可聽衆不喜歡這種看法。
隨著祕密檔案的公開,線人們不斷曝光並受到譴責的同時,公衆也發現,自己每次都會落入相同的、極爲複雜的道德困境。 “斯塔西的線人們始終是(東德)國家機構中一個極爲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如果沒有大多數東德人的沈默作爲配合,這一體系斷然不會如此有效運轉。”芭芭拉·米 勒就此寫道,“作爲機會主義的盲從者,個人之所以與集體保持一致,是因爲他們在這種物質安全、社會安定的平庸圖景中安於渾渾噩噩,其中之個人,則堅定不疑 地服從於那種對簡單及相對和諧之生活的欲望。”
我認爲,當集體恥辱感逐漸增強到一個臨界點,這個集體就將面臨極大的風險———完全的自我否認。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承 認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從的、心甘情願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無意義的。出於本能,集體會避免讓自身落入這種深淵。通常情況下,他們會找到救贖 者。兩個月前,翁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裡尼的法西斯政權勒令全國1200位大學教授宣誓效忠,僅有12人拒絕,並爲此失去工作。其餘 皆爲保住教職而屈從。“也許這1188人是對的,”艾柯說,“但那12個人挽救了其大學、乃至我們國家的榮譽。這就是爲什麽你必須說不,即便這樣做毫無益 處。因爲有朝一日,你可以說,你說過不。”
十二君子僅僅是大學教授集體的百分之一,在全體義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們事後足以爲集體恥感提供一個排遣 的通道,雖不至完全脫罪,亦可讓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種平衡。如果一個集體找不到可引爲代表的英雄,幫他們卸去頸上的重軛,讓他們有理由說出:“我們也曾反抗 過,”那麽這個集體終將不能自如地面對過去。
東德卻沒有英雄。
羞恥與失憶
1993年初,前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裡絲塔·沃爾夫(Christa Wolf)被指認曾在1959至1961年間爲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員,代號“瑪格麗特”。沃爾夫女士的反應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認,半年多之後,檔案 將不可辯駁的證據呈現於前,她又改口,說已將這段往事完全忘卻,並辯稱從未對同胞造成實質性的傷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線人大多保持沈默,直至白紙黑字的證據出現。然而對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們真的有可能失憶嗎?芭芭拉·米勒在前述專著中,對上述情況做了分析:
傳統的記憶複製理論認爲,人的記憶是對過往事件的精確複製,但心理學家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自我記憶的機理往往與此相 反。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社會心理學教授邁克爾·羅斯發現,個體會使用“絕對自信的理論來構建其個人歷史”。也就是說,人們趨向於用當前對自我的理解來“推 斷”他們過去的行爲。除非有明確的資訊讓我們相信自己的態度和行爲已經發生了變化不然我們便很可能有意誇大過去與現在的相似性,並以此重構記憶。
“謝天謝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記了。”沃爾夫女士寫道,“如果我還記得那件事,我怎麽能活過那麽多年,怎麽還能繼續寫作,我還能相信誰?”
事發時,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擊。然而輿論最初的歇斯底裡過後,不斷出現的檔案逐漸還原出更爲客觀的歷史:沃 爾夫與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並且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不僅如此,自從年輕時的政治幼稚之後,她日益轉向政權的對立面(她被稱爲“忠誠的異 見者”,在批評政府的同時仍然保持社會主義信念),並爲此與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長達20年的不間斷監視,寫於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 的半自傳體小說《餘留之物》(Was bleibt),記述了那段監控之下的生活。
該書甫一面世,即遭指責。評論界指其僞善,以東德時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圖謀於新時代。三年後斯塔西祕檔曝光,輿論衆口一辭,大有將她打入地獄之勢。這正是面對歷史時的亂局與困境,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皆難以脫逃,亦難以承擔。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時間似乎漫長,卻又像彈指一揮間。它的幽靈仍然糾纏著許多人,也許每夜都來,徘徊於枕邊,讓他們至死不能釋懷。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