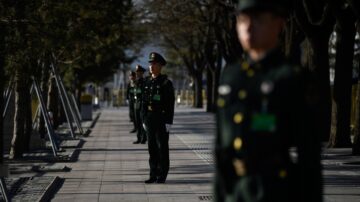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訊】整整一週,我懷著非常複雜的心情細閱「紅軍第一叛將」《龔楚將軍回憶錄》,內中有關早期紅軍的真實記述不時令我心瀾陣陣――「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但我沒有想到真正的高潮在臨結束的最後幾頁,精華之精濃縮於尾,真正一出「伏高潮於結束」的經典悲劇。心驚肉跳地合卷閉燈,竟一夜難眠 ― 聳然恐怖、慨然唏噓、邈然深思、怒然氣急……

龔楚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網路圖片)
紅軍代總參謀長
龔楚(1901~1995),粵北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巿立一中。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寧漢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指定與朱毛組成前敵委員會,頭顱也與朱毛同一價位――捉到兩萬大洋、擊斃一萬、報信五千。 1929年12月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幾入生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通緝匪首,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著走了,怎麼會離開革命隊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麼會自我否定呢?自然,龔楚之叛說來話長,有著主客觀複雜因素,須稍展述。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巖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龍巖,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共幹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處置,朱德不允,痛斥來要人的農會共幹。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戀愛」,真是說不出的喜悅。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巖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巖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巖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志,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同志(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衝衝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洩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裡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裡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洩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汙點」。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幹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嶽同時被殺。1927~1934年間,毛澤東也被清算過「富農路線」,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 1932年初,蕭勁光因「小資產階級意識」差點不得出任五軍團政委,5月又遭撤職與開除黨籍處分。革命遠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於文革的中共高幹流行語),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體與生命,抓住的則是乾巴巴的抽象概念與教條。
大陸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紅隊」,即刺殺顧順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紅隊,不知情者還以為以顏色為隊名,其全稱實為「中共紅色恐怖隊」。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龔楚赴長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在汝城遭攔截,白軍縱火燒山搜索,差點燒死。他潛回樂昌老家,靜養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著共產黨走。
有了這樣的思想,龔楚在紅軍中自然會格格難入,漸生異志。
龔楚因與周恩來發生工作意見上的分歧,被新賬老賬一起算,不僅高層檢討,也被大會批鬥,提前經歷文革。1933年5月,龔楚挨批,34師政委(龔曾任該師師長)黃甦揭發龔生活腐化,在廣西紅七軍時期花千元代價娶妻,實屬無中生有。散會後龔楚質之,黃答曰:「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書脫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雖然還有近3.7萬人馬,但蘇區已無可動員人力,存糧僅可維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萬,四周又是合圍日緊的中央軍。項英、龔楚、陳毅商量後,電請遠在貴州的中央,要求突圍,追隨「野戰軍」西進,爭取與其會合。中央即復:根據突圍西進經驗,中央軍區應放棄突圍,就地分散打游擊,另命龔楚率一步兵團轉進湘粵桂邊區,收容西進野戰軍散落人員,建立新根據地並成立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事宜均由龔楚負責。
龔楚即率1200人進至湖南彬縣黃茅,迅速打開局面,發展湘粵桂邊區赤色武裝。由於國民黨軍隊一時無力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饒了我吧!中國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這個負載中共湘粵桂三省軍政重任的「最高長官」,出於對遙控中共的「第三國際」的憤恨與黨內殘酷鬥爭的恐懼,竟撂了挑子。龔楚避開身邊特務員,隻身巧妙逃脫,留下一份聲明給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地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1971年初,龔楚在自序中陳述何以脫紅:「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聲
回鄉不久,龔楚先後出任余漢謀粵軍第1軍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1935年10月 13日,龔楚誘伏中共北山游擊隊,除幾人逃脫,30多名游擊隊員全被打死,此為「北山事件」。後來,龔楚與另一中共叛徒何長林誘捕項英、陳毅,被前來帶路的中共偵察員識破,鳴槍報警。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迅速逃走,躲過一劫。抗戰爆發後,龔楚先後任國軍上校參謀處長、少將參謀。抗戰勝利後,龔楚出任徐州市長,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1946年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第四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可謂「助紂為虐」、「雙手沾滿人民鮮血」。
1949年10月,共軍打到北江,龔楚率保安團逃到樂昌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寫信勸降,11月上旬龔楚率部下山投誠。12月,共軍準備進攻海南島,海南守將為龔楚樂昌同鄉薛岳。廣東省長葉劍英請示中央軍委,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龔滿口答應。到了香港,龔楚知道勸降薛岳不僅沒有成算,且有「通匪」殺身之險,但若無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決定滯港定居。此後,龔楚應邀赴臺遏蔣,蔣要他在港祕密收編殘部組織「反共救國軍」,伺機配合反攻大陸。但他明白國民黨大勢已去,婉拒委派,從此脫離政治旋渦,改名龔松庵,返港辦實業。龔在香港呆了40年,期間赴美,拿到「綠卡」,最終歸返香港,以寫作書畫自娛,一張墨跡可賣三五千元。1960年代後期撰寫回憶錄。
1980年代後期,中共發布公告:「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建國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龔楚萌發回鄉之念。樂昌當地政府為討好龔楚,撥款七萬原式原樣重建龔家老屋,占地面積320 多平米,建築面積170多平米,六房兩廳一廚兩衛,琉璃瓦頂,一副當年土豪宅第模樣。宅內配置全新家具,包括電視機、電話、冰箱、席夢思床、大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氣派。於是,龔楚決定回鄉。
但樂昌縣有關部門還有一道難題:以何種規格接待這位紅軍叛將?請示上峰,省統戰部批復: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1990年9月13日,龔楚攜夫人王蘭芬抵韶關,樂昌縣委統戰部、僑務辦擺酒接風,龔楚遞上三封信――分別致「老同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老家辭世,享年94歲。當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報:龔楚姪孫龔慶韶不僅個人回鄉投資,還牽線引資或與他人合作投資,僅1990年代就為樂昌引資四億餘,也算龔楚最後澤被鄉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歷史帷幕,這一代人已經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結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蓋棺之時,卻非論定之日。如何評說那場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稱量「階級鬥爭」在中國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當今中共從革命退至改良,從對抗折返和諧的「改革開放」?大革命一代留下龐大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一切並沒有簡單結束。逝去的歲月仍在「規定」著我們。雖然後人無法改變歷史,也不能假設歷史,但總還有總結歷史的權力吧?後人不能只有接受的義務沒有選擇的權利。封住歷史其實就是封住今天的前進,不讓還原歷史,底牌自然在於眾所周知的「歷史顧慮」。不過,這一次,寰內士林已經明白:對那場大革命的理解評析,可是一筆必須算清的歷史大賬目。
多餘的話
也許中共史家或紅色人士會詰問:「叛徒文章,一派胡言!豈可信乎?」不幸,儘管筆者抱疑讀之,然佐之各種史料(如《伍修權回憶錄》 、陳丕顯的《贛南三年游擊戰爭》 ),《龔楚將軍回憶錄》的真實性至少在95%以上。從利害關係角度,龔楚撰寫此傳於1960年代後期,乃一介平頭港民,並無多少需要捍衛的政治利益,純屬個人歷史回顧,需要顧忌之處遠遠低於官方。更可信的是:回憶錄細節清晰,邏輯完整,幾無虛寫遮掩之處。以筆者閱讀近千部(篇)傳記之經驗,未發現破綻。即便從研究中共黨史角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尤其對內地讀者來說,看多了盡是教條口號的原則性回憶,來自「叛徒」角度的聲音,而且是帶著細節汗液的敘述,實在值得伸頭一探。如聽聽龔楚對蘇維埃運動的最後陳述:
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工農)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
再根據這場大革命的結果來看,從革命成功後的生產實踐來看,從中共改革後所選擇的「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來看,以「打土豪、分田地」為標誌的蘇維埃運動,除了幫助中共奪取全國政權,還能有什麼值得保留與肯定的歷史內核麼?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

龔楚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網路圖片)
紅軍代總參謀長
龔楚(1901~1995),粵北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巿立一中。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寧漢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指定與朱毛組成前敵委員會,頭顱也與朱毛同一價位――捉到兩萬大洋、擊斃一萬、報信五千。 1929年12月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幾入生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通緝匪首,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著走了,怎麼會離開革命隊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麼會自我否定呢?自然,龔楚之叛說來話長,有著主客觀複雜因素,須稍展述。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巖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龍巖,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共幹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處置,朱德不允,痛斥來要人的農會共幹。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戀愛」,真是說不出的喜悅。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巖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巖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巖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志,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同志(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衝衝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洩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裡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裡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洩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汙點」。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幹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嶽同時被殺。1927~1934年間,毛澤東也被清算過「富農路線」,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 1932年初,蕭勁光因「小資產階級意識」差點不得出任五軍團政委,5月又遭撤職與開除黨籍處分。革命遠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於文革的中共高幹流行語),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體與生命,抓住的則是乾巴巴的抽象概念與教條。
大陸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紅隊」,即刺殺顧順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紅隊,不知情者還以為以顏色為隊名,其全稱實為「中共紅色恐怖隊」。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龔楚赴長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在汝城遭攔截,白軍縱火燒山搜索,差點燒死。他潛回樂昌老家,靜養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著共產黨走。
有了這樣的思想,龔楚在紅軍中自然會格格難入,漸生異志。
龔楚因與周恩來發生工作意見上的分歧,被新賬老賬一起算,不僅高層檢討,也被大會批鬥,提前經歷文革。1933年5月,龔楚挨批,34師政委(龔曾任該師師長)黃甦揭發龔生活腐化,在廣西紅七軍時期花千元代價娶妻,實屬無中生有。散會後龔楚質之,黃答曰:「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書脫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雖然還有近3.7萬人馬,但蘇區已無可動員人力,存糧僅可維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萬,四周又是合圍日緊的中央軍。項英、龔楚、陳毅商量後,電請遠在貴州的中央,要求突圍,追隨「野戰軍」西進,爭取與其會合。中央即復:根據突圍西進經驗,中央軍區應放棄突圍,就地分散打游擊,另命龔楚率一步兵團轉進湘粵桂邊區,收容西進野戰軍散落人員,建立新根據地並成立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事宜均由龔楚負責。
龔楚即率1200人進至湖南彬縣黃茅,迅速打開局面,發展湘粵桂邊區赤色武裝。由於國民黨軍隊一時無力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饒了我吧!中國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這個負載中共湘粵桂三省軍政重任的「最高長官」,出於對遙控中共的「第三國際」的憤恨與黨內殘酷鬥爭的恐懼,竟撂了挑子。龔楚避開身邊特務員,隻身巧妙逃脫,留下一份聲明給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地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1971年初,龔楚在自序中陳述何以脫紅:「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聲
回鄉不久,龔楚先後出任余漢謀粵軍第1軍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1935年10月 13日,龔楚誘伏中共北山游擊隊,除幾人逃脫,30多名游擊隊員全被打死,此為「北山事件」。後來,龔楚與另一中共叛徒何長林誘捕項英、陳毅,被前來帶路的中共偵察員識破,鳴槍報警。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迅速逃走,躲過一劫。抗戰爆發後,龔楚先後任國軍上校參謀處長、少將參謀。抗戰勝利後,龔楚出任徐州市長,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1946年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第四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可謂「助紂為虐」、「雙手沾滿人民鮮血」。
1949年10月,共軍打到北江,龔楚率保安團逃到樂昌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寫信勸降,11月上旬龔楚率部下山投誠。12月,共軍準備進攻海南島,海南守將為龔楚樂昌同鄉薛岳。廣東省長葉劍英請示中央軍委,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龔滿口答應。到了香港,龔楚知道勸降薛岳不僅沒有成算,且有「通匪」殺身之險,但若無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決定滯港定居。此後,龔楚應邀赴臺遏蔣,蔣要他在港祕密收編殘部組織「反共救國軍」,伺機配合反攻大陸。但他明白國民黨大勢已去,婉拒委派,從此脫離政治旋渦,改名龔松庵,返港辦實業。龔在香港呆了40年,期間赴美,拿到「綠卡」,最終歸返香港,以寫作書畫自娛,一張墨跡可賣三五千元。1960年代後期撰寫回憶錄。
1980年代後期,中共發布公告:「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建國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龔楚萌發回鄉之念。樂昌當地政府為討好龔楚,撥款七萬原式原樣重建龔家老屋,占地面積320 多平米,建築面積170多平米,六房兩廳一廚兩衛,琉璃瓦頂,一副當年土豪宅第模樣。宅內配置全新家具,包括電視機、電話、冰箱、席夢思床、大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氣派。於是,龔楚決定回鄉。
但樂昌縣有關部門還有一道難題:以何種規格接待這位紅軍叛將?請示上峰,省統戰部批復: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1990年9月13日,龔楚攜夫人王蘭芬抵韶關,樂昌縣委統戰部、僑務辦擺酒接風,龔楚遞上三封信――分別致「老同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老家辭世,享年94歲。當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報:龔楚姪孫龔慶韶不僅個人回鄉投資,還牽線引資或與他人合作投資,僅1990年代就為樂昌引資四億餘,也算龔楚最後澤被鄉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歷史帷幕,這一代人已經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結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蓋棺之時,卻非論定之日。如何評說那場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稱量「階級鬥爭」在中國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當今中共從革命退至改良,從對抗折返和諧的「改革開放」?大革命一代留下龐大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一切並沒有簡單結束。逝去的歲月仍在「規定」著我們。雖然後人無法改變歷史,也不能假設歷史,但總還有總結歷史的權力吧?後人不能只有接受的義務沒有選擇的權利。封住歷史其實就是封住今天的前進,不讓還原歷史,底牌自然在於眾所周知的「歷史顧慮」。不過,這一次,寰內士林已經明白:對那場大革命的理解評析,可是一筆必須算清的歷史大賬目。
多餘的話
也許中共史家或紅色人士會詰問:「叛徒文章,一派胡言!豈可信乎?」不幸,儘管筆者抱疑讀之,然佐之各種史料(如《伍修權回憶錄》 、陳丕顯的《贛南三年游擊戰爭》 ),《龔楚將軍回憶錄》的真實性至少在95%以上。從利害關係角度,龔楚撰寫此傳於1960年代後期,乃一介平頭港民,並無多少需要捍衛的政治利益,純屬個人歷史回顧,需要顧忌之處遠遠低於官方。更可信的是:回憶錄細節清晰,邏輯完整,幾無虛寫遮掩之處。以筆者閱讀近千部(篇)傳記之經驗,未發現破綻。即便從研究中共黨史角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稀史料」。尤其對內地讀者來說,看多了盡是教條口號的原則性回憶,來自「叛徒」角度的聲音,而且是帶著細節汗液的敘述,實在值得伸頭一探。如聽聽龔楚對蘇維埃運動的最後陳述:
我曾經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並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工農)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
再根據這場大革命的結果來看,從革命成功後的生產實踐來看,從中共改革後所選擇的「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來看,以「打土豪、分田地」為標誌的蘇維埃運動,除了幫助中共奪取全國政權,還能有什麼值得保留與肯定的歷史內核麼?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