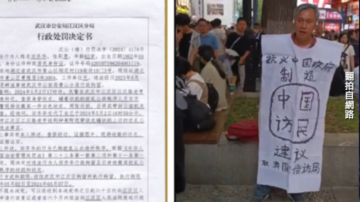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1月19日訊】1月8日在北京南站城管搶走了捐助流浪者的大衣,對此儘管不承認,但在寒冬臘月搗毀他們棲居的窩蓬這是事實,和強拆把他們趕出家園又有什麼兩樣?他們住著高樓大廈、設備齊全都嫌冷,數九寒天對他們進行驅趕,且問你們的人心在哪裡?你們家的狗兒貓兒又能如何,難道也露宿街頭嗎?這確實是一個人性問題。
都在同一藍天下,本應得到同樣的陽光,北京南站橋下路邊用廢棄物搭建窩蓬的流浪人員多是無家可歸或是有家難回的上訪一族。鳥兒在樹上可以搭個窩,兔兒可在地下掏個洞,人們都加以保護,這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且問我們人呢。在災難面前我們都感到無奈,非常渺小不可抗命,也感同身受,不分你我同舟共濟。可是遇到人禍呢,卻置之度外,有所超然,這不但是權力的扭曲也是人性的扭曲。
美麗的中國不但光鮮好看,更需要人文關懷,心靈之美,文化之美才是真正的美。人生天地間,橋下路邊在北京流浪者、上訪村、已形成了一個部落,難道連立命的權利也沒有嗎?原先四五十年代沒有戶籍制度,自然來自然去自由地遷徙。作為一個自然人不管流落到哪裡,搭起了窩蓬用土坯加上幾根棍子壘起房子就是他的家。原來的荒郊野外後來叫城鄉結合部,現在的城市人多數的前輩們有的是逃荒有的是落難,都是這樣定居下來的。後來當官的、當兵的、發財的、升學的、有門路的都進了城住上了高樓大廈,現在他們成了這座城市的主宰,然而當今這些流浪一族們仍定格在那個年代沒有被認同,對底層的不公平就是對社會的不公平。什麼叫正常職業,什麼又叫做非正常職業,都去打工,垃圾誰拾?這也是貢獻,社會是由各個階層組成的,必須公平的對待他們才能講得通。
首都不是你們一個人的首都,中國也不是你們一個人的中國,流浪一族夏去冬來他們以嚴寒酷暑為伴,以垃圾菜葉剩飯殘羹為生,幾根木棍可以支起帳篷,一塊泡沫可以席地而坐,一塊塑料可以遮風擋雨,雖算不上是建築材料對他們來說卻是生活所必須,那個能支撐他們睡覺的地方和那些高樓大廈相比同樣重要,且問城管們這些用品就是他們的唯一家當,你們還有什麼可清理的。
這是一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社會,我們現在已不是一個物資缺乏的年代,卻有一個物資貧乏的人群。有人以垃圾為寶,有人以寶為垃圾,這是何等的差異?流浪者能把廢物利用搭成一個他能夠睡覺的地方,只要睡著了我相信他們就會做夢,他們可能夢見了茅草屋也可能夢見了金鑾殿。且問皇宮太子們你們那些專制夢在當今世界還能繼續嗎?
每當工商們把那些三聚氰胺奶粉等垃圾食品還有垃圾衣物焚燒倒掉時,那些不得溫飽的人們見了卻心疼的流下了眼淚。五十年代民政部發放的救濟大多都是從戰場上繳獲的戰利品,有的分個軍用水壺,有的分個軍用書包,有的分個棉帽子,有的還分個日本軍用馬褲和棉襖都血跡斑斑,也從不嫌病毒而把它當成黨的溫暖。先前我們都生活在最底層,現在卻分天上人間三六九等,有的剛扔下討飯棍升了官就去打討飯的,真是天地良心。
剛建立起的共和國,老百姓最聽黨的話,有毒的不能吃犯法的不能做,一切都按指示辦事。「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教科書報刊廣播電台說什麼我們相信什麼。60年大飢荒,蔣匪幫要反攻大陸「千百萬人民要人頭落地」,我們貧下中農怕他們「反攻倒算」哭成一片,沿海地區經常撿到一些傳單,糖果和餅乾,當官的說有毒不能吃,我們都一一上交。大飢荒的年代,只要沒有毒,動物能吃的我們都吃了,當時還有個《代食品證》,什麼叫代食品,一家幾斤花生皮、幾斤玉米皮、幾斤地瓜秧、粉碎後像豆腐渣一樣並限斤限兩發給你,本來這是人不能吃的東西,什麼草根、樹皮為了填飽肚子又不得不吃,有的地方還有人吃人的現象。什麼叫窮急生瘋,狗急跳牆,有偷的、有搶的、蹲監獄也不恥辱一切都是為了活命。今天回想起那些上交的「糖果」確實有點單純幼稚可笑。
一邊是慈善者送衣送物愛心施救,一邊是城管搶走流浪者的大衣,搗毀流浪者的窩蓬,在道德人性上這是天與地的差別。
對弱者本應給予更多的呵護,權力對流浪者打著各種旗號進行騷擾侵犯,凍死餓死在街頭的仍以各種借口進行推脫,死活都不想承擔責任。這就叫做權大壓倒一切。
救濟站是否允許他們常住,工作人員是否又能把他們當人看,權力是否能把自己當成真正的施救工作者。有的流浪者為什麼不選擇救濟站,這是他們的權利,有的絕大多數是上訪一族,有的也可能有他無法言說的苦衷,這些都是問題。
我覺得一個文明的城市絕不能因為多了幾個流浪者它就不文明了,一個美麗的城市也不能因為搭了幾個窩蓬它就不美麗了。流浪也是一種文化應該包容。
2013年1月15日
都在同一藍天下,本應得到同樣的陽光,北京南站橋下路邊用廢棄物搭建窩蓬的流浪人員多是無家可歸或是有家難回的上訪一族。鳥兒在樹上可以搭個窩,兔兒可在地下掏個洞,人們都加以保護,這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且問我們人呢。在災難面前我們都感到無奈,非常渺小不可抗命,也感同身受,不分你我同舟共濟。可是遇到人禍呢,卻置之度外,有所超然,這不但是權力的扭曲也是人性的扭曲。
美麗的中國不但光鮮好看,更需要人文關懷,心靈之美,文化之美才是真正的美。人生天地間,橋下路邊在北京流浪者、上訪村、已形成了一個部落,難道連立命的權利也沒有嗎?原先四五十年代沒有戶籍制度,自然來自然去自由地遷徙。作為一個自然人不管流落到哪裡,搭起了窩蓬用土坯加上幾根棍子壘起房子就是他的家。原來的荒郊野外後來叫城鄉結合部,現在的城市人多數的前輩們有的是逃荒有的是落難,都是這樣定居下來的。後來當官的、當兵的、發財的、升學的、有門路的都進了城住上了高樓大廈,現在他們成了這座城市的主宰,然而當今這些流浪一族們仍定格在那個年代沒有被認同,對底層的不公平就是對社會的不公平。什麼叫正常職業,什麼又叫做非正常職業,都去打工,垃圾誰拾?這也是貢獻,社會是由各個階層組成的,必須公平的對待他們才能講得通。
首都不是你們一個人的首都,中國也不是你們一個人的中國,流浪一族夏去冬來他們以嚴寒酷暑為伴,以垃圾菜葉剩飯殘羹為生,幾根木棍可以支起帳篷,一塊泡沫可以席地而坐,一塊塑料可以遮風擋雨,雖算不上是建築材料對他們來說卻是生活所必須,那個能支撐他們睡覺的地方和那些高樓大廈相比同樣重要,且問城管們這些用品就是他們的唯一家當,你們還有什麼可清理的。
這是一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社會,我們現在已不是一個物資缺乏的年代,卻有一個物資貧乏的人群。有人以垃圾為寶,有人以寶為垃圾,這是何等的差異?流浪者能把廢物利用搭成一個他能夠睡覺的地方,只要睡著了我相信他們就會做夢,他們可能夢見了茅草屋也可能夢見了金鑾殿。且問皇宮太子們你們那些專制夢在當今世界還能繼續嗎?
每當工商們把那些三聚氰胺奶粉等垃圾食品還有垃圾衣物焚燒倒掉時,那些不得溫飽的人們見了卻心疼的流下了眼淚。五十年代民政部發放的救濟大多都是從戰場上繳獲的戰利品,有的分個軍用水壺,有的分個軍用書包,有的分個棉帽子,有的還分個日本軍用馬褲和棉襖都血跡斑斑,也從不嫌病毒而把它當成黨的溫暖。先前我們都生活在最底層,現在卻分天上人間三六九等,有的剛扔下討飯棍升了官就去打討飯的,真是天地良心。
剛建立起的共和國,老百姓最聽黨的話,有毒的不能吃犯法的不能做,一切都按指示辦事。「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教科書報刊廣播電台說什麼我們相信什麼。60年大飢荒,蔣匪幫要反攻大陸「千百萬人民要人頭落地」,我們貧下中農怕他們「反攻倒算」哭成一片,沿海地區經常撿到一些傳單,糖果和餅乾,當官的說有毒不能吃,我們都一一上交。大飢荒的年代,只要沒有毒,動物能吃的我們都吃了,當時還有個《代食品證》,什麼叫代食品,一家幾斤花生皮、幾斤玉米皮、幾斤地瓜秧、粉碎後像豆腐渣一樣並限斤限兩發給你,本來這是人不能吃的東西,什麼草根、樹皮為了填飽肚子又不得不吃,有的地方還有人吃人的現象。什麼叫窮急生瘋,狗急跳牆,有偷的、有搶的、蹲監獄也不恥辱一切都是為了活命。今天回想起那些上交的「糖果」確實有點單純幼稚可笑。
一邊是慈善者送衣送物愛心施救,一邊是城管搶走流浪者的大衣,搗毀流浪者的窩蓬,在道德人性上這是天與地的差別。
對弱者本應給予更多的呵護,權力對流浪者打著各種旗號進行騷擾侵犯,凍死餓死在街頭的仍以各種借口進行推脫,死活都不想承擔責任。這就叫做權大壓倒一切。
救濟站是否允許他們常住,工作人員是否又能把他們當人看,權力是否能把自己當成真正的施救工作者。有的流浪者為什麼不選擇救濟站,這是他們的權利,有的絕大多數是上訪一族,有的也可能有他無法言說的苦衷,這些都是問題。
我覺得一個文明的城市絕不能因為多了幾個流浪者它就不文明了,一個美麗的城市也不能因為搭了幾個窩蓬它就不美麗了。流浪也是一種文化應該包容。
2013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