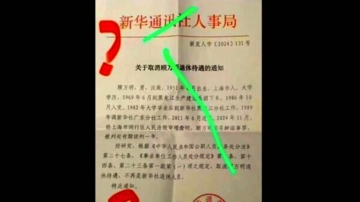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1月26日訊】一、南周編輯記者反抗的意義
近半年來,《南方週末》多次遭到省委宣傳部長庹震的橫暴干預,動輒得咎,苦不堪言,南周人這次出手帶有絕地反抗的性質。數日內,網絡輿論迅速發酵,各界輪番捲入,熱得發燙,據一般經驗,關鍵時刻只要有人站出來充當反抗支點,就足以使事態爆裂。1月6日夜間,當南周經濟部員工宣告罷工後,局面迅速突破臨界點;當夜新浪微博轉發南周消息者估計有數千萬人。這股熱潮順理成章地催生了次日街頭的直接抗議活動。
南周人作為體制內從業者,謀生受官方掣肘,能直接反抗殊為不易。他們敢於捍衛獨立人格和言論自由,是中產知識階層一次難能可貴的「良心起義」。
南周事件的性質至為簡明:反奴役,爭自由。有人以南周系黨報子媒、南周人不敢直接提出取消書報審查為由,而低估此次抗爭的意義。但憲政從來都不是一次性構建的,而是由諸多因素逐步積累而成。在政體革命中,保守審慎是建設性要素,而群體抗爭行動則是快變量,極具一線衝擊力。儘管在此事件後期——政治集會後,南周人受到中宣部以「敵對勢力插手」所威逼,稍有退讓,但歷史必將記載南周人的義舉:在特殊的時間點,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言論自由,因而點燃時代的火炬。
二、政治集會核心支撐者的主導作用及階層分析
事態之發生需要有人站出來擔當;抗爭現場的堅守及政治升級也有賴於追求自由的勇者和團隊的參與。
1月7日上午南方報業大門外的獻花聲援活動,是廣州網友自發進行的。之後,聲援活動迅速升級為政治集會,而這是廣州街頭民主抗爭力量直接推動的,這是現場真實發生的,並無任何拔高和虛誇之處,街頭民主抗爭力量並非政治集會的支流、側翼,而是實實在在的主體、主流。
1月5日、6日、7日,連續三天,老沈、葉隱、袁小華、劉珊娟、袁奉初、野渡、劉遠東等網友和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分別在南方報業大門外舉牌,使街頭直接行動步步升級。7日上午,袁奉初、野渡、劉遠東所直接打出的「庹毒不除,廣東自宮。新聞自由,憲政民主」的標語牌,為這場抗爭奠定了政治基調。一些網友反映,他們正是看到這一標語牌,才覺得現場值得「圍觀」。顯然,普遍權利訴求和理想價值是動員公民參與的真正牽引力。也正因為這一舉牌活動發揮了巨大的點火作用,獨立中文筆會副祕書長野渡(舉牌後他隨即做了兩分鐘的即席演講)和街頭民主抗爭活躍人士袁奉初才遭到國保的瘋狂報復:野渡被國保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傳喚,並遭到派出所警察脫光衣服搜身的人身侮辱;而袁奉初被闖入其臨時住所的國保和協警按在地上毆打,同住的黃賓也被國保打了兩個耳光。
街頭民主抗爭力量中的主要活躍人士劉遠東、徐琳、袁奉初、劉四仿、肖青山、黃賓、張茂忠、小彪、李錚然、歐榮貴、朱漢強、卓協、余剛、邵鐸、柴金元、游貴等參與了,甚至數日全力投入於現場活動,或者進行直接的、沒有任何遮掩的主題政治演講,或者堅持舉標語、做民主宣講,他們所在之處,成為政治集會的主要聚集點、政治主題的宣示者和推進者。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廣州街頭民主抗爭人士的累積能量的自然外溢。一年半以來,這一活躍在廣州的街頭、公園和廣場的當今中國唯一的一支街頭政治抗爭團隊,歷經打壓,愈挫愈奮,終於在新的政治變革起動之初,直接跨上了全國性政治事件的舞台。客觀評估,一般網友尚未成熟到直接主推政治行動階段,而有實際經驗的公民團隊,其勇猛堅韌和活動能量,要遠勝於僅僅停留在理論言說階段的自由人士。
從人口結構上看,數十位核心的街頭民主抗爭人士,其階層構成,基本上是底層與中產的結合。比如,舉牌活躍人士老沈、野渡、葉隱是中產知識者,政治集會主要演講人劉遠東是生物學家,徐琳是工程師、詩人,二人皆是有車族。袁奉初、肖青山、黃賓、小彪、李錚然則是草根英雄,是近年崛起的街頭活動的佼佼者。更難能的是,三日政治集會中,還有隋牧青、張紓等十幾位律師和維權推動者直接活躍在一線政治集會現場,他們堅決地履行公民權利,自然地找到了合適的維繫秩序、防止破壞和衝突的法律位置。
一般地來說,國內官民雙方都把作為開放前沿的廣東發生的社會衝突事件,作為未來中國的某種預演。三日政治集會中的底層和中產聯動模式,可能帶有巨大的預示性和經久性。23年來,公民社會已在波折和積累中崛起擴展,1980年代體制內力量和大學聯動模式,似已基本結束。從韓國轉型來看,大學動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且具有十分前衛激烈的鬥爭衝擊力。在中國,這樣的青年衝擊力被沿海和十大核心城市的流動人口,尤其是底層流動人口所部分替代了。但真正的民主化抗爭主體,應該已經轉到底層和中產耦合聯動的公民社會身上。比較而言,公民社會比大學抗爭主體要更堅韌、更理性、更具操盤力、更具建設力。而在可能動員的人口基數上,公民社會要遠遠超出大學抗爭主體。
三、政治集會的主要訴求、公民自我訓練和群體運作模式
在1989年中斷之後,地地道道的街頭政治,又從2013年1月開始了。三天政治集會直接以政治權利為訴求,直接地實際履行政治權利,直接突破了惡法的約束。
一場抗爭運動,社會多元參與,各有見解,非常自然,不可能協調一致。多元聲音,自然包括可以想見的最激烈的聲音,它不僅帶有對民眾的鼓動和對官方的施壓性質,也帶有初享政治權利者的政治探索和情緒宣洩性質。所以,三天政治集會既是一場政治抗爭,也是一場政治實驗。那些街頭民主抗爭活躍人士,在直接行動中體認到了想像和現實的距離。在現實中,他們必須考慮「公正的旁觀者」的感受,因而調整思維,由一元突進,走向更加多元平衡。
詩人徐琳曾提出三條溫和的訴求:要求庹震下台;要求照發南周原版新年獻詞;將南周工作微博帳號歸還給編輯們並解封所有因此事件被封掉的微博、QQ、博客。這三項訴求得到了大家的贊同(我隨後補加了一條:要求放開全國媒體和公民的言論自由)。詩人徐琳曾是最前衛的激進行動派,但他在享受了公民政治權利、在人群中充分表達了自我後,變得更加理性、寬和、開放、成熟,而成為走向建設性的積極公民,視野遼闊的民主鬥士,這讓我感觸良多。公民參加政治活動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民主、自我訓練的過程。真正的政治潮流,將誕生於實戰之中。通過集會遊行示威等政治抗爭行動中的自我訓練,真正合格的積極公民,甚至未來的各級議員、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都可能在其中成長。
三天的政治集會現場總體氛圍是有序、理性、溫和的。相比於過往珠三角發生的新塘事件、中山事件,此次南周現場秩序可謂良好,抗議僅僅限於言論,而無肢體衝突。這個溫和有序的局面的維繫,既有賴於南方一貫溫和的社會環境因素作用,也有賴於極左勢力反覆挑釁下和草根抗爭者急於升級的衝動下街頭抗爭活躍人士自身的冷靜反思和主動節制。極左隊伍定時出現,其來有自,他們逐日昇級挑釁規模,由言詞進攻,直至肢體進攻;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初期對此尚感突兀,一旦認識到其圖謀,隨即採取容忍、禮讓、沉默的方式應對。到了第三日,即1月9日,似乎即將清場,極左隊伍「應時而動」,主動從原本被警察隔離的大門外北端跨過來,警察「默契式」不予阻攔,極左隊伍為首者強行奪走一位街頭抗爭人士的電喇叭,發表了兩分鐘「打倒漢奸」的演說;街頭抗爭人士禮貌地問:「講完了嗎?」對方愣住了,街頭抗爭人士隨即把自己的電喇叭收回,一場可能的肢體衝突被化解於無形之中。一些年長的民運前輩更數人結伴,組成人牆,悄然阻止極左隊伍的跨界挑釁。
還有一個重要細節:每日傍晚5點半左右,警方建議離開,民主維權推動者和街頭民主抗爭力量互相招呼,主動撤走。在實際沒有政治組織的情勢下,大家通過晚餐和午餐的相互討論,形成多項共識,慢慢降低了政治演講的激切性,推動了形成政治訴求的切實性和對秩序的愛惜、對多元均衡的尊重。如果擁有政治組織,當然可能在分工協作後,使現場更加有序理性,抗議和政治宣講更具成效。但在公民街頭政治活動之初,人氣尚未高度凝聚之際,自發、扁平、飯局式協調,對個人自主性的激發可能更大。
四、政治集會背後的官民角色
採取直接行動,履行公民政治權利,享受公民政治權利,是三日政治集會最大的收穫。而官方的容忍,帶有對公民政治活動的合法性默認的巨大潛在意義。這對於官民雙方,對於整個中國未來,都具有重要昭示性。
儘管國保對野渡、袁奉初的侮辱、毆打,顯系出於高度仇恨和對未來極端恐懼下的洩憤作惡(這是不可接受的),但從北京到廣東的處置危機者,的確表現出多年罕見的溫和,除了並未到達現場的街頭民主抗爭活躍人士張聖雨被行政拘留7日,其餘政治演說者和活躍人士都未被抓捕,對其中一些人士的軟禁在週一(1月12日)也都取消,官方的應對措施大體克制。
如何研判這一情勢?首先,對此絕不可誤讀,以為是民間力量如何強大、逼退了對方。雖然全國輿論鼎沸,但在5-9日五天管制鬆弛的空隙、在此一較為中性事件參與危險明顯不大的基本情勢下,各省卻只有零星舉牌,而無群體呼應。這已證明,雖然輿論和背景潛力海量遼闊,但全國民間聯動力和直接行動力非常有限,不可高估。民間的主要反擊力,還在於道義影響,它會使得打壓成本非常巨大。作為當事人的一部分,參與者很清醒:在今日政體下,沒有官方的容忍,不可能有持續三日的政治集會。廣州街頭民主運動理論家和領頭人之一劉遠東在演講中曾指出,胡春華先生有責任保護履行公民權利的抗議者。我事後也通過新浪微博呼籲:對於公民社會的民主實驗,請胡春華先生做保護包產到戶的萬裡,而不要相反而行。
此次事件中,不僅廣州民間的政治集會帶有破冰意義,官方的容忍也具有標竿意義。體制內的善意,是值得重視的。1月7日孟建柱宣佈將報請人大批准今年內停止勞教,數日後此條新聞又在宣傳窗口收回,反而深刻地說明了體制內開明力量的存在、關鍵方位和未來潛能。
公民社會的民主實驗需要官民雙方的理性和遠見。官方無須支持,僅僅不反對、不破壞、不非法打壓,足矣。
操作者不是坐而論道者。必須以極大善意,增大憲政民主的滲透力,團結多數力量,爭取活動空間,並推進全社會的圓桌和共贏。對於官方的改革力量,我們必須抱持歡迎態度。未來北京的習近平、李克強等先生,廣東的胡春華、朱小丹、萬慶良、陳建華等先生,如果真誠地推動政治變革,我們必定做出有原則的、堅定的支持。所有的善意都可獲得善意的回應,所有的信用都會獲得信用的回應。
但是,正如我以前所說,獨立的公民社會不可能將政體轉型的主要希望寄託在體制內改革家身上,而會把公民政治社會作為推進和確保政治變革的主要實力基礎,因此我們必定主要致力於公民社會的耦合、擴展和自我規制、量能升級,從而以民力制衡官力,促成社會實力高於國家實力的歷史格局。不管官方是否轉,民間自己都會轉,並且一直都會自主發展。
我仍願作出具有風險而又具有操作借鑑意義的具體判斷:中國目前變革已經開始,已進入官變與民變同時進行的時代,悲觀是沒有根據的。轉型不是上飯店,點菜後廚師做好端上來,我們直接享受。轉型是公民自己做廚師,慢慢享受炒菜做飯的過程。慢有慢的大好處。在南周事件發作之初,有識者就提出:目前形勢一波一波升級,會不會出現20多年前的場面?我的回答是:這次會慢,會成。這一代負有將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國做成的使命,包括民間,也包括皈依自由的官方政治家。成功不必有我,成功我在其中。但對於每一步的機會,我們都必須像愛惜自己身體一樣愛惜,因為23年的煎熬時光和代代累積不會白白浪費。
五、南周抗爭後南方公民社會的未來走向
中國民間力量,已在威權有限任期制換屆後,進入推動公民政治權利階段。行動塑造思想。「公民」本意有二:擁有政治權利的人,履行政治權利的人。不行動,就不是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公民是積極公民。爭自由的時代,啟蒙基本完成後,行動已成為首要價值。積極公民不滿足於先行者的角色,而希望所有有能力行動者,都成為先行者。一代人的主體自證、主權實現,將通過行動完成。這就是行動的文化意義。民主政體不會走路,但人會走路,會把民主政體走出來。自古以來,做事的資源都需開發組合。火焰,必須走向乾柴。
全國自由力量在此次南周抗爭事件中的反應的確令我們感到失望。第一天政治集會後的晚間,參與者就判斷,未來兩日如果各省不作響應,此事就到此為止。說實在的,京城知識界近乎鱷魚,一動不動,讓我很震驚。我得部分修正我對啟蒙和中產階層的一貫肯定,重估維權運動帶來的行動氣質的意義了。維權運動曾經突破知識階層長於言說、拙於行動的侷限,通過系列社會運動,促進了反對力量的歷史性成型,政法委總結的「新黑五類」就是對這一反對力量的最好概括,而維權運動居功不小。今日民間反對力量升級之際,維權運動又不能不擔負做先驅者、鋪路者、犧牲者的使命。
中產階層和知識階層的基本惰性,不會因為微博和推特交際網絡的漲潮而克服,下一步怎麼辦?
大格局上,民間可推動以維權和街頭為先鋒的底層和中產聯動模式,除了繼續團結和依靠維權律師、民主先驅、民運鬥士、自由思想家、網絡意見領袖,維權板塊將會越來越多地接地氣,和公民社會的新生力量接觸、互動、耦合。新一代較少束縛,系自然公民。廣州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就是新一代光輝的代表,他們和他們背後所標誌的億萬新生代力量,將是未來民主憲政運動的主力。在什邡、啟東和寧波活躍的也是他們同類,在未來我們還會不斷看到他們崛起的身影。
廣州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在此次政治集會中自發成為主導性角色,為中國社會做出了一個重要的示範:公民應該通過直接行動,消除恐懼,堂堂正正地爭取公民政治權利,堅決地履行公民政治權利。但是,同時,民間也深知經濟維權和政治維權的內在關聯,不會急於將一切民間抗爭全部高度政治化,而會通過推動各類中性的、社會公益性的、草根經濟性的、環保性的維權,為底層和中產社會做出各種具體幫助,贏得大家的基本信任,從而建立起各類建設性的、有限的、目標明確的抗爭聯盟和支援模型,進而動員更多的人士參加公民政治活動。長期高壓下民間社會的恐懼感尚未消除,不可根據微博和推特上的高調言詞,誤判了民間行動力。民氣壯懷激烈,民力尚需累積。
時代和政治版圖悄然間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可能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具體操作,將走上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南方的民主實驗,是諸多可行的選項之一。民間主體,直接行動,不摻水,不全押,有序可控,實踐而後法治程序化,是民間審慎深遠的思慮。這條路總是要走的。經濟形勢尚好之際,官方誤讀和敵視較少,民間更宜大膽推進。各種可能性都會存在,即使是1987年的漢城抗爭在中國大陸重演,也應該是北京和廣州等合力而成。以中國之大,越多元越好,未來的上海、武漢、西安、成都能崛起為政治中心,都具有多元均衡意義,並影響選舉時代的政治格局。
當具體推進公民社會時,政治現實感是不能不具備的。面對各種變量約束,先突破,而後平衡,是基本方略。既然必須隨即平衡,突破目標便不宜過遠,故行動者需準確估計各種變量,將目標化為先後順序,以對未來資源開發功效最大、阻力較小者為突破口;以平和態、政治現實感通往共贏,即使遭遇強壓,也有利於防守反擊。
公民政治權利是最不消極的權利,是直接行動的權利,是結成團隊的權利,是維護人權的權利,是謀求國家與世界公正的權利,是主動爭取其它一切權利的權利。
推動憲政民主進程,建設公民社會,必從直接行動、履行公民政治權利開始。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近半年來,《南方週末》多次遭到省委宣傳部長庹震的橫暴干預,動輒得咎,苦不堪言,南周人這次出手帶有絕地反抗的性質。數日內,網絡輿論迅速發酵,各界輪番捲入,熱得發燙,據一般經驗,關鍵時刻只要有人站出來充當反抗支點,就足以使事態爆裂。1月6日夜間,當南周經濟部員工宣告罷工後,局面迅速突破臨界點;當夜新浪微博轉發南周消息者估計有數千萬人。這股熱潮順理成章地催生了次日街頭的直接抗議活動。
南周人作為體制內從業者,謀生受官方掣肘,能直接反抗殊為不易。他們敢於捍衛獨立人格和言論自由,是中產知識階層一次難能可貴的「良心起義」。
南周事件的性質至為簡明:反奴役,爭自由。有人以南周系黨報子媒、南周人不敢直接提出取消書報審查為由,而低估此次抗爭的意義。但憲政從來都不是一次性構建的,而是由諸多因素逐步積累而成。在政體革命中,保守審慎是建設性要素,而群體抗爭行動則是快變量,極具一線衝擊力。儘管在此事件後期——政治集會後,南周人受到中宣部以「敵對勢力插手」所威逼,稍有退讓,但歷史必將記載南周人的義舉:在特殊的時間點,勇敢地站出來捍衛言論自由,因而點燃時代的火炬。
二、政治集會核心支撐者的主導作用及階層分析
事態之發生需要有人站出來擔當;抗爭現場的堅守及政治升級也有賴於追求自由的勇者和團隊的參與。
1月7日上午南方報業大門外的獻花聲援活動,是廣州網友自發進行的。之後,聲援活動迅速升級為政治集會,而這是廣州街頭民主抗爭力量直接推動的,這是現場真實發生的,並無任何拔高和虛誇之處,街頭民主抗爭力量並非政治集會的支流、側翼,而是實實在在的主體、主流。
1月5日、6日、7日,連續三天,老沈、葉隱、袁小華、劉珊娟、袁奉初、野渡、劉遠東等網友和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分別在南方報業大門外舉牌,使街頭直接行動步步升級。7日上午,袁奉初、野渡、劉遠東所直接打出的「庹毒不除,廣東自宮。新聞自由,憲政民主」的標語牌,為這場抗爭奠定了政治基調。一些網友反映,他們正是看到這一標語牌,才覺得現場值得「圍觀」。顯然,普遍權利訴求和理想價值是動員公民參與的真正牽引力。也正因為這一舉牌活動發揮了巨大的點火作用,獨立中文筆會副祕書長野渡(舉牌後他隨即做了兩分鐘的即席演講)和街頭民主抗爭活躍人士袁奉初才遭到國保的瘋狂報復:野渡被國保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傳喚,並遭到派出所警察脫光衣服搜身的人身侮辱;而袁奉初被闖入其臨時住所的國保和協警按在地上毆打,同住的黃賓也被國保打了兩個耳光。
街頭民主抗爭力量中的主要活躍人士劉遠東、徐琳、袁奉初、劉四仿、肖青山、黃賓、張茂忠、小彪、李錚然、歐榮貴、朱漢強、卓協、余剛、邵鐸、柴金元、游貴等參與了,甚至數日全力投入於現場活動,或者進行直接的、沒有任何遮掩的主題政治演講,或者堅持舉標語、做民主宣講,他們所在之處,成為政治集會的主要聚集點、政治主題的宣示者和推進者。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廣州街頭民主抗爭人士的累積能量的自然外溢。一年半以來,這一活躍在廣州的街頭、公園和廣場的當今中國唯一的一支街頭政治抗爭團隊,歷經打壓,愈挫愈奮,終於在新的政治變革起動之初,直接跨上了全國性政治事件的舞台。客觀評估,一般網友尚未成熟到直接主推政治行動階段,而有實際經驗的公民團隊,其勇猛堅韌和活動能量,要遠勝於僅僅停留在理論言說階段的自由人士。
從人口結構上看,數十位核心的街頭民主抗爭人士,其階層構成,基本上是底層與中產的結合。比如,舉牌活躍人士老沈、野渡、葉隱是中產知識者,政治集會主要演講人劉遠東是生物學家,徐琳是工程師、詩人,二人皆是有車族。袁奉初、肖青山、黃賓、小彪、李錚然則是草根英雄,是近年崛起的街頭活動的佼佼者。更難能的是,三日政治集會中,還有隋牧青、張紓等十幾位律師和維權推動者直接活躍在一線政治集會現場,他們堅決地履行公民權利,自然地找到了合適的維繫秩序、防止破壞和衝突的法律位置。
一般地來說,國內官民雙方都把作為開放前沿的廣東發生的社會衝突事件,作為未來中國的某種預演。三日政治集會中的底層和中產聯動模式,可能帶有巨大的預示性和經久性。23年來,公民社會已在波折和積累中崛起擴展,1980年代體制內力量和大學聯動模式,似已基本結束。從韓國轉型來看,大學動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且具有十分前衛激烈的鬥爭衝擊力。在中國,這樣的青年衝擊力被沿海和十大核心城市的流動人口,尤其是底層流動人口所部分替代了。但真正的民主化抗爭主體,應該已經轉到底層和中產耦合聯動的公民社會身上。比較而言,公民社會比大學抗爭主體要更堅韌、更理性、更具操盤力、更具建設力。而在可能動員的人口基數上,公民社會要遠遠超出大學抗爭主體。
三、政治集會的主要訴求、公民自我訓練和群體運作模式
在1989年中斷之後,地地道道的街頭政治,又從2013年1月開始了。三天政治集會直接以政治權利為訴求,直接地實際履行政治權利,直接突破了惡法的約束。
一場抗爭運動,社會多元參與,各有見解,非常自然,不可能協調一致。多元聲音,自然包括可以想見的最激烈的聲音,它不僅帶有對民眾的鼓動和對官方的施壓性質,也帶有初享政治權利者的政治探索和情緒宣洩性質。所以,三天政治集會既是一場政治抗爭,也是一場政治實驗。那些街頭民主抗爭活躍人士,在直接行動中體認到了想像和現實的距離。在現實中,他們必須考慮「公正的旁觀者」的感受,因而調整思維,由一元突進,走向更加多元平衡。
詩人徐琳曾提出三條溫和的訴求:要求庹震下台;要求照發南周原版新年獻詞;將南周工作微博帳號歸還給編輯們並解封所有因此事件被封掉的微博、QQ、博客。這三項訴求得到了大家的贊同(我隨後補加了一條:要求放開全國媒體和公民的言論自由)。詩人徐琳曾是最前衛的激進行動派,但他在享受了公民政治權利、在人群中充分表達了自我後,變得更加理性、寬和、開放、成熟,而成為走向建設性的積極公民,視野遼闊的民主鬥士,這讓我感觸良多。公民參加政治活動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民主、自我訓練的過程。真正的政治潮流,將誕生於實戰之中。通過集會遊行示威等政治抗爭行動中的自我訓練,真正合格的積極公民,甚至未來的各級議員、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都可能在其中成長。
三天的政治集會現場總體氛圍是有序、理性、溫和的。相比於過往珠三角發生的新塘事件、中山事件,此次南周現場秩序可謂良好,抗議僅僅限於言論,而無肢體衝突。這個溫和有序的局面的維繫,既有賴於南方一貫溫和的社會環境因素作用,也有賴於極左勢力反覆挑釁下和草根抗爭者急於升級的衝動下街頭抗爭活躍人士自身的冷靜反思和主動節制。極左隊伍定時出現,其來有自,他們逐日昇級挑釁規模,由言詞進攻,直至肢體進攻;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初期對此尚感突兀,一旦認識到其圖謀,隨即採取容忍、禮讓、沉默的方式應對。到了第三日,即1月9日,似乎即將清場,極左隊伍「應時而動」,主動從原本被警察隔離的大門外北端跨過來,警察「默契式」不予阻攔,極左隊伍為首者強行奪走一位街頭抗爭人士的電喇叭,發表了兩分鐘「打倒漢奸」的演說;街頭抗爭人士禮貌地問:「講完了嗎?」對方愣住了,街頭抗爭人士隨即把自己的電喇叭收回,一場可能的肢體衝突被化解於無形之中。一些年長的民運前輩更數人結伴,組成人牆,悄然阻止極左隊伍的跨界挑釁。
還有一個重要細節:每日傍晚5點半左右,警方建議離開,民主維權推動者和街頭民主抗爭力量互相招呼,主動撤走。在實際沒有政治組織的情勢下,大家通過晚餐和午餐的相互討論,形成多項共識,慢慢降低了政治演講的激切性,推動了形成政治訴求的切實性和對秩序的愛惜、對多元均衡的尊重。如果擁有政治組織,當然可能在分工協作後,使現場更加有序理性,抗議和政治宣講更具成效。但在公民街頭政治活動之初,人氣尚未高度凝聚之際,自發、扁平、飯局式協調,對個人自主性的激發可能更大。
四、政治集會背後的官民角色
採取直接行動,履行公民政治權利,享受公民政治權利,是三日政治集會最大的收穫。而官方的容忍,帶有對公民政治活動的合法性默認的巨大潛在意義。這對於官民雙方,對於整個中國未來,都具有重要昭示性。
儘管國保對野渡、袁奉初的侮辱、毆打,顯系出於高度仇恨和對未來極端恐懼下的洩憤作惡(這是不可接受的),但從北京到廣東的處置危機者,的確表現出多年罕見的溫和,除了並未到達現場的街頭民主抗爭活躍人士張聖雨被行政拘留7日,其餘政治演說者和活躍人士都未被抓捕,對其中一些人士的軟禁在週一(1月12日)也都取消,官方的應對措施大體克制。
如何研判這一情勢?首先,對此絕不可誤讀,以為是民間力量如何強大、逼退了對方。雖然全國輿論鼎沸,但在5-9日五天管制鬆弛的空隙、在此一較為中性事件參與危險明顯不大的基本情勢下,各省卻只有零星舉牌,而無群體呼應。這已證明,雖然輿論和背景潛力海量遼闊,但全國民間聯動力和直接行動力非常有限,不可高估。民間的主要反擊力,還在於道義影響,它會使得打壓成本非常巨大。作為當事人的一部分,參與者很清醒:在今日政體下,沒有官方的容忍,不可能有持續三日的政治集會。廣州街頭民主運動理論家和領頭人之一劉遠東在演講中曾指出,胡春華先生有責任保護履行公民權利的抗議者。我事後也通過新浪微博呼籲:對於公民社會的民主實驗,請胡春華先生做保護包產到戶的萬裡,而不要相反而行。
此次事件中,不僅廣州民間的政治集會帶有破冰意義,官方的容忍也具有標竿意義。體制內的善意,是值得重視的。1月7日孟建柱宣佈將報請人大批准今年內停止勞教,數日後此條新聞又在宣傳窗口收回,反而深刻地說明了體制內開明力量的存在、關鍵方位和未來潛能。
公民社會的民主實驗需要官民雙方的理性和遠見。官方無須支持,僅僅不反對、不破壞、不非法打壓,足矣。
操作者不是坐而論道者。必須以極大善意,增大憲政民主的滲透力,團結多數力量,爭取活動空間,並推進全社會的圓桌和共贏。對於官方的改革力量,我們必須抱持歡迎態度。未來北京的習近平、李克強等先生,廣東的胡春華、朱小丹、萬慶良、陳建華等先生,如果真誠地推動政治變革,我們必定做出有原則的、堅定的支持。所有的善意都可獲得善意的回應,所有的信用都會獲得信用的回應。
但是,正如我以前所說,獨立的公民社會不可能將政體轉型的主要希望寄託在體制內改革家身上,而會把公民政治社會作為推進和確保政治變革的主要實力基礎,因此我們必定主要致力於公民社會的耦合、擴展和自我規制、量能升級,從而以民力制衡官力,促成社會實力高於國家實力的歷史格局。不管官方是否轉,民間自己都會轉,並且一直都會自主發展。
我仍願作出具有風險而又具有操作借鑑意義的具體判斷:中國目前變革已經開始,已進入官變與民變同時進行的時代,悲觀是沒有根據的。轉型不是上飯店,點菜後廚師做好端上來,我們直接享受。轉型是公民自己做廚師,慢慢享受炒菜做飯的過程。慢有慢的大好處。在南周事件發作之初,有識者就提出:目前形勢一波一波升級,會不會出現20多年前的場面?我的回答是:這次會慢,會成。這一代負有將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國做成的使命,包括民間,也包括皈依自由的官方政治家。成功不必有我,成功我在其中。但對於每一步的機會,我們都必須像愛惜自己身體一樣愛惜,因為23年的煎熬時光和代代累積不會白白浪費。
五、南周抗爭後南方公民社會的未來走向
中國民間力量,已在威權有限任期制換屆後,進入推動公民政治權利階段。行動塑造思想。「公民」本意有二:擁有政治權利的人,履行政治權利的人。不行動,就不是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公民是積極公民。爭自由的時代,啟蒙基本完成後,行動已成為首要價值。積極公民不滿足於先行者的角色,而希望所有有能力行動者,都成為先行者。一代人的主體自證、主權實現,將通過行動完成。這就是行動的文化意義。民主政體不會走路,但人會走路,會把民主政體走出來。自古以來,做事的資源都需開發組合。火焰,必須走向乾柴。
全國自由力量在此次南周抗爭事件中的反應的確令我們感到失望。第一天政治集會後的晚間,參與者就判斷,未來兩日如果各省不作響應,此事就到此為止。說實在的,京城知識界近乎鱷魚,一動不動,讓我很震驚。我得部分修正我對啟蒙和中產階層的一貫肯定,重估維權運動帶來的行動氣質的意義了。維權運動曾經突破知識階層長於言說、拙於行動的侷限,通過系列社會運動,促進了反對力量的歷史性成型,政法委總結的「新黑五類」就是對這一反對力量的最好概括,而維權運動居功不小。今日民間反對力量升級之際,維權運動又不能不擔負做先驅者、鋪路者、犧牲者的使命。
中產階層和知識階層的基本惰性,不會因為微博和推特交際網絡的漲潮而克服,下一步怎麼辦?
大格局上,民間可推動以維權和街頭為先鋒的底層和中產聯動模式,除了繼續團結和依靠維權律師、民主先驅、民運鬥士、自由思想家、網絡意見領袖,維權板塊將會越來越多地接地氣,和公民社會的新生力量接觸、互動、耦合。新一代較少束縛,系自然公民。廣州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就是新一代光輝的代表,他們和他們背後所標誌的億萬新生代力量,將是未來民主憲政運動的主力。在什邡、啟東和寧波活躍的也是他們同類,在未來我們還會不斷看到他們崛起的身影。
廣州街頭民主抗爭力量在此次政治集會中自發成為主導性角色,為中國社會做出了一個重要的示範:公民應該通過直接行動,消除恐懼,堂堂正正地爭取公民政治權利,堅決地履行公民政治權利。但是,同時,民間也深知經濟維權和政治維權的內在關聯,不會急於將一切民間抗爭全部高度政治化,而會通過推動各類中性的、社會公益性的、草根經濟性的、環保性的維權,為底層和中產社會做出各種具體幫助,贏得大家的基本信任,從而建立起各類建設性的、有限的、目標明確的抗爭聯盟和支援模型,進而動員更多的人士參加公民政治活動。長期高壓下民間社會的恐懼感尚未消除,不可根據微博和推特上的高調言詞,誤判了民間行動力。民氣壯懷激烈,民力尚需累積。
時代和政治版圖悄然間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可能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具體操作,將走上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南方的民主實驗,是諸多可行的選項之一。民間主體,直接行動,不摻水,不全押,有序可控,實踐而後法治程序化,是民間審慎深遠的思慮。這條路總是要走的。經濟形勢尚好之際,官方誤讀和敵視較少,民間更宜大膽推進。各種可能性都會存在,即使是1987年的漢城抗爭在中國大陸重演,也應該是北京和廣州等合力而成。以中國之大,越多元越好,未來的上海、武漢、西安、成都能崛起為政治中心,都具有多元均衡意義,並影響選舉時代的政治格局。
當具體推進公民社會時,政治現實感是不能不具備的。面對各種變量約束,先突破,而後平衡,是基本方略。既然必須隨即平衡,突破目標便不宜過遠,故行動者需準確估計各種變量,將目標化為先後順序,以對未來資源開發功效最大、阻力較小者為突破口;以平和態、政治現實感通往共贏,即使遭遇強壓,也有利於防守反擊。
公民政治權利是最不消極的權利,是直接行動的權利,是結成團隊的權利,是維護人權的權利,是謀求國家與世界公正的權利,是主動爭取其它一切權利的權利。
推動憲政民主進程,建設公民社會,必從直接行動、履行公民政治權利開始。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