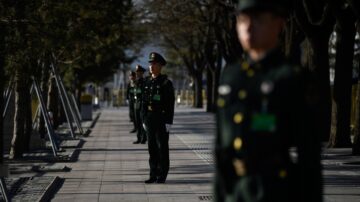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3月8日訊】【導讀】根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1976年以前中國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過巨額經濟援助,1973年以後這種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糾正。這些巨額援助,無疑是當時畸形外交理念的結果。文章以阿爾巴尼亞為例,一窺當年無視國家、民族利益的畸形外交的真實情形。
援助「兄弟國家」是「國際主義義務」
「革命援助」是世界共運的特殊現象。究其原因有二:一者,為擺脫孤立局面,蘇聯(俄)建政伊始,即致力於援助和輸出革命;二者,共運本身從理論到實踐都以階級為立足點,自然也就帶有超脫國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所以,近代以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也就從傳統的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外交關系」,變成了一種奇特以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兄弟關系」。
1958年l0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陳毅、李富春《關於加強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領導的請示報告》,批示中說:「認真做好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也是我國人民對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的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直接以文件的形式,將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外交關系,轉變成了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的兄弟關系——中國與阿爾巴尼亞自然也是「兄弟關系」。但在整個五十年代,兩國關系並不密切,中國雖然給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但總體來說,援助的總額不大,對本國民生沒有造成什麽影響,在阿爾巴尼亞接受的全部「革命援助」中所佔比例也很小(最大的援助國是蘇聯)。
在整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裡,阿爾巴尼亞國小力微,並不受蘇聯的重視。但阿爾巴尼亞卻對蘇聯模式——準確說來是斯大林模式的認同感最為強烈。所以,當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政權與蘇聯分道揚鑣時,阿爾巴尼亞堅決地站在了蘇聯一邊,在東歐共產黨中間,最早在自己黨內清洗所謂的「鐵托分子」。當然,阿爾巴尼亞如此做,除了意識形態上對斯大林模式的高度認同,也與阿爾巴尼亞一直受到來自南斯拉夫的控制有關。
蘇聯與南斯拉夫直接暴力衝突之後,阿爾巴尼亞藉助蘇聯的力量徹底擺脫了南斯拉夫的控制;蘇聯則因為阿爾巴尼亞的絕對支持,而成為其最大的援助國。但好景不長,隨著斯大林的去世,赫魯曉夫執政的蘇聯開始致力於改善同南斯拉夫的關系;在這一過程中,阿爾巴尼亞屢次發出強硬聲音,反對赫魯曉夫的做法。1956年蘇共二十大重新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極大地刺激了阿爾巴尼亞政府。
與阿爾巴尼亞相似,中國政府此一時期,也屢屢對赫魯曉夫的「蘇聯新政」提出批評。1958年全世界60多個共產黨參加的「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運動」,蘇共的批判如蜻蜓點水不痛不癢,中共的批判則有如急風驟雨並付諸實際行動,中國召回了駐南大使,南斯拉夫也召回了其駐華大使。中、阿兩國因為相同的意識形態越走越近。

1968年,中國媒體報道「阿爾巴尼亞青年熱情學習毛主席著作」(網路圖片)
蘇聯終止對阿援助
阿爾巴尼亞首次公開與中國站在一起,是1960年6月20至25日召開的布加勒斯特會議。這次會議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同一批東歐國家共產黨對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展開了猛烈的批判攻勢。
赫魯曉夫的主要意見,是人為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應該尋求和平共處的可能;同時指責中國「拒絕和平共處」、「希望戰爭」、在國際共運中「爭奪領導」、「要充當教員」、「當檢察官、當政委」、「企圖利用斯大林問題改變蘇共現在的領導」;並認為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治掛帥、大煉鋼鐵等都是錯誤的。(詳見閻明復《隨彭真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載《中共黨史資料102輯》)
在大多數與會共產黨選擇與赫魯曉夫統一立場的情況下,阿爾巴尼亞代表罕見地公開站出來表態支持中共,因此被赫魯曉夫斥責,並遭受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圍攻。布加勒斯特會後一個月,阿黨領袖謝胡在約見中國駐阿代辦時說:阿勞動黨將堅持馬列主義,堅決支持中共的觀點,阿爾巴尼亞黨和國家雖然都很小,但絕不向任何力量屈服,要為馬列主義而生,為馬列主義而死。此後多次共運會議,阿爾巴尼亞都選擇了與中國立場一致。但也因此徹底惹怒了赫魯曉夫,招致蘇聯於1961年單方面撕毀了對阿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和根據協議駐守在阿港口的蘇聯艦隊,並拒絕阿參加華約會議,12月更中斷了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系。
中國成為阿爾巴尼亞最大的援助國
蘇、阿關系徹底冰凍的同時,中、阿關系則迅速升溫。最引人註目的現象,是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不斷,且禮遇規格極高。周恩來訪阿時,阿方領導人往往全部出迎,且每次都會舉行10萬人以上的群眾歡迎集會;阿方領導人訪華時,除毛澤東外,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要前去機場迎接,北京還組織了百萬人規模的群眾夾道歡迎。當然,最實際的,還是中國接替蘇聯,成為了阿方最大的援助國。
據新華社高級編輯、前駐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駐斯科普裡分社首席記者王洪起回憶:1961年春,蘇聯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除了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幾十萬噸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幫助阿實現了瀕於夭折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解決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來,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其中一般物資佔28%強,軍事物資佔43%強,成套項目佔25%強,現匯佔2%強),阿成為我對外援助受援國人均數額最多的國家。中國援阿成套項目共計142個,其中已經建成的91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已經考察和進行設計的17個。
中國為阿爾巴尼亞興建了鋼鐵、化肥、制堿、制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通訊和廣播等部門的項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業化水平。應當強調指出的是,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以及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和遭受唐山地震,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180萬噸。同時也應承認,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有的援阿項目超過了中國的經濟和技術負擔能力,上馬顯得頗為吃力。為了完成阿的復雜項目,中國在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不得不先在國內進行大量試驗和試制工作,甚至動員了全國26個省市的100多個單位參加,並建立專門的實驗工廠。為此,中國還有兩人犧牲了生命。」
中國有 阿國也要有
1961年春,正值中國大饑荒時期。本國糧食尚需進口,此時援助阿爾巴尼亞「幾十萬噸糧食」,其難度可想而知。對這種影響到了本國民生的對外援助,曾短暫出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飈,在其晚年回憶錄中如此寫道:
特別令我感到憂慮的是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問題。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編輯註:此一時期,中國的人均年收入不過2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乎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1969年北京群眾隆重集會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25周年(網路圖片)
以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為標準向中國索要援助
阿爾巴尼亞當局按照歐洲發達國家的生活標準,向當時極度貧窮的中國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援助要求。據耿飈回憶: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麽多東西打算什麽時候還?他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當謝胡陪同先念同誌訪問阿中南部費裡區時,在長達六個小時的往返途中,謝胡幾乎談了六個小時,所談內容全是要東西。他說: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鋼』,還需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還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還說,在下一個五年計劃裡,將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先念同誌當即表示,你們計劃你們的需要,我們考慮我們的可能。
我通過對阿某些地區的實地調查了解到:阿在經濟建設方面,貪大求全,戰線拉得太長,非生產項目搞得太多。1969年,阿非生產建設項目的投資就占國家總投資的24%,因而造成勞動力嚴重缺乏。根據阿方自己的計算,在第五個五年計劃中,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簽訂的協定,我國援阿新項目的建築和投產就需要增加4.6萬名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約等於阿當時產業工人的38.3%。阿還存在一種不適當地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看齊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臺時說,計劃在阿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用說農村了。所以我當時就感到這種傾向很值得註意。
由於阿方領導人存在上述不切實際的想法,所以他們向我國提出了不少極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們幫他們搞了紡織廠,但他們沒有棉花,我們還要用外匯買進棉花給他們。他們織成布,做了成衣,還硬要賣給我們,倒過來賺我們的錢。記得有一次阿副總理查爾查尼向我提出,要我們幫助更換化肥廠的主要設備。該化肥廠是我國援建的,本應使用我國生產的機器設備,但阿方不要我國的機器,指定要用義大利的,我們只好用外匯從義大利買來機器安裝上。現在這臺機器壞了,查爾查尼還要我們從義大利買機器來更換。我當即拒絕了他的這個不合理要求。
用來賑濟大饑荒的進口糧援助阿方
最讓人寒心的是,中國勒緊褲腰帶不顧國內的嚴重饑荒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阿方卻對此毫無感知,反而浪費極度嚴重。據耿飈回憶: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阿方浪費極其嚴重。我在實地調查時看到:馬路邊的電線桿,都是用我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他們還把我國援助的水泥、鋼筋用來到處修建烈士紀念碑,在全國共修建了1萬多個。我們援助的化肥,被亂七八糟地堆在地裡,任憑日曬雨淋。諸如此類的浪費現象,不勝枚舉。
新華社高級編輯、前駐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駐斯科普裡分社首席記者王洪起也有相似的回憶:中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帶,萬裡迢迢,很不容易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裡,常年風吹雨打。我們的專家看到這樣嚴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淚。有些援阿專家(在援阿年代裡,先後有近6000名工程技術人員遠離家鄉,赴阿爾巴尼亞工作)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裡說了一句『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當我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系,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阿的胃口越來越大,什麽都想要,數額一次比一次加碼,幾億幾十億的要,填不滿的無底洞。阿以小欺大,強我所難,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當然,認為援助是中國天經地義的責任。
在上世紀60年代初,為了緩解饑餓,中國擠出極其寶貴的外匯,從國外進口一些糧食。但只要阿爾巴尼亞說需要,中國就把進口的糧食送給他們。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另據周恩來衛士喬金旺回憶: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旬加1961年來訪,主要是伸手,給少了還不行。阿爾巴尼亞不理解我們也很困難,雙方談得不好,總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來對來華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凱萊齊說:我們根據力所能及承擔國際義務,但由於我國連續遇到3年災荒,加上蘇聯撤退專家,所以我們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此援助不能像你們希望的那麽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蘇聯過去答應的援助全部包下來,你們自力更生還是主要的。盡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國還是與阿爾巴尼亞簽訂了五項援助議定書。
為阿方領導人專門生產特供香煙
最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當時的中國,居然還要替阿方領導人生產特供香煙,供其個人享受。王洪起回憶:阿在國際市場上賣不出去的一些劣質商品如香煙、童裝、紡織品等都強行塞給我們包銷。人們可能還記得,一毛二一盒的「鉆石」牌香煙,就是阿爾巴尼亞的。價格雖然便宜,但人們並不喜歡。就連他們自己的最高領導人霍查,也不吸本國煙而吸的是筒裝的「大中華」(霍查稱「天安門」香煙)。記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國使館突然分給使館和分社每人兩筒中華牌香煙,說是「贈品」。後來大家才知道,這些香煙是中國為霍查專門製造的,而且根據霍查的要求,香煙雖不帶過濾嘴,但對尼古丁做了專門的處理。1973年,霍查心臟病首次發作,醫生建議他戒煙,他才斷了43年的吸煙歷史,而由中國運去的最後一批香煙也就不要了,使館便分給了使館人員。
王稼的「三和一少」
阿爾巴尼亞只是中國六十年代諸多「革命援助」國家的一個而已。這樣一種問題百出的「革命援助」,不可避免會在國內引發諸多的異議。王稼祥就是其中之一。
1962的七千人大會,將全國民眾都在挨餓這一殘酷現實捅破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誌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裡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痛哭之後,王稼祥遂在小範圍內談了自己對調整對外方針的意見,並徵得中聯部黨委的同意,聯名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建議信。
王稼祥建議:「不要說必須在消滅美帝國主義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避免」;還批評那種認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處」「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有和平共處」的觀點;提出「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關於對外方針政策,提出:為了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加速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對外有必要採取緩和的方針,而不是採取加劇的方針。對外經濟援助,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建議,與毛澤東當日所實行的對外方針截然相反。1962年9月,陳毅在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的發言中批評了所謂『三和一少』的一股風(即主張對美國和緩一點,對蘇聯和緩一點,對印度和緩一點,對外經濟援助少一點)。陳毅的主旨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目光短淺,不能打小算盤,要打大算盤,不能只算經濟賬,要算政治賬。陳毅的發言得到毛澤東的贊同。1963年5月,毛澤東開始「算政治帳」,將「三和一少」上升為修正主義的路線。他在同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的談話中說: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們的鬥爭援助少一些。這就是修正主義路線。1964年2月,毛澤東再次會見威爾科克斯,又講了上述內容。並說:針對「三和一少」,我們的方針就是「三鬥一多」。「三和一少」是赫魯曉夫的口號,「三鬥一多」是我們的口號。隨後毛澤東在會見朝鮮勞動黨金日成和日本共產黨侉田裡見時也談了上述內容,並點名批評了王稼祥。
因為「三和一少」忤逆了毛澤東的「三鬥一多」,王稼祥被撤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政治生涯徹底結束。王稼祥本人被軟禁,妻子朱仲麗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動輒六七個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兒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鬥,投河自殺身亡。因難以承受和應對接連不斷的暴力批鬥,王稼祥精神極度緊張,最後產生了精神紊亂和幻覺、幻視癥,時常不斷叫喊:「我沒有罪!」1974年1月24日晚,王稼祥因心臟病突發猝然去世——此前兩天,《北京日報》刊文,再度批判所謂的「三和一少」的「妖風」。
耿飈直言批評
王稼祥的悲慘命運,卻沒有降臨到同樣批評「革命援助」、「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的耿飈頭上。耿飈目睹了阿爾巴尼亞大肆無節制揮霍中國援助之後,在1969年寫信反對這種無節制援助的做法。信最後到了毛澤東手裡,但同樣的意見,耿飈卻收獲了和王稼祥截然相反的命運。據耿飈回憶:
這種情況,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這符合國際主義原則,但必須註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的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現在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對我們來說,是把錢物倒進一個無底洞,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方來說,只能養成他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懶惰習慣,以及對外援的依賴心理,而無助於他們的經濟建設。因此我想把這種情況向國內反映,但是又存在顧慮。因為,在當時國內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誰敢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其後果難以預料。萬一給江青一夥人和造反派扣上幾頂「反對國際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繼續推行「三降一滅」路線的帽子,豈不要重進「牛棚」。
經過反復激烈的思想鬥爭,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和特命全權大使的政治責任感終於驅使我撇開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提起筆來給當時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同誌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詳細反映了上述情況,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提出,我國對阿援助是主客觀不一致,即主觀願望是好的,是為了幫助阿搞好經濟建設,但客觀效果並不好,不但沒有使他們的經濟得到發展,反而助長了他們的驕傲、懶惰和依賴思想。因此,我建議國內對援阿的規模、內容和方法,均須重新考慮,通盤修改。喬冠華看信後,對我如實反映情況表示贊賞,對我提的意見也表示贊同;但在當時情況下,他對此事也無能為力,只是將我的信轉報中央。後來我回國後遇到李先念副總理,他對我說:『耿飈,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我對這件事也有意見,但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周恩來有一次和我談話時也提起我寫信的事。他告訴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後說:「耿飈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也許正是由於毛說了這句話,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這件事整我。(《耿飈回憶錄(1949-1992)》,江蘇人民出版社)
耿、王二人命運如此迥異,個中原因,當然不是因為耿飈運氣好,而是因為中、阿關系此時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1962年,阿方竭力反蘇;稍後文革爆發,阿方又公開表示支持,還要求出版阿爾巴尼亞文的《毛主席語錄》,這些全都相當契合毛澤東的心意。但到了1969年,毛澤東在擔憂蘇聯可能會入侵中國、感嘆「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的同時,已經有意與美國緩和外交關系,並採取了實際行動。反觀阿爾巴尼亞,因中國1969年接待蘇聯總理柯西金過境及周恩來、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握手,阿方公開表示反對,並降低了出席中國建國20周年慶典的規格——這無疑令毛澤東相當不快,同時也是耿飈直言批評阿爾巴尼亞貪得無厭肆意揮霍中國援助,卻得到毛澤東「敢講真話」的贊揚的直接原因。
「革命援助」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自1969年之後,中阿關系迅速降溫,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謀求與蘇聯和解,阿方不能接受;二是中國謀求與美國關系正常化,阿方更斥責為「修正主義」。這讓主持這一外交政策大轉變的毛澤東很不滿意。
但毛澤東贊揚了耿飈對阿爾巴尼亞的批評,卻並沒有停止不切實際的「革命援助」。1970年,阿爾巴尼亞厚著臉皮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中國最後仍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沒有完全滿足阿爾巴尼亞的索求,一方面應該是其獅子大張口數額太大,另一方面,應該也與中方對阿方的不滿有關——也是在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曾主動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由此可見,毛澤東並沒有改變其不切實際的「革命援助」理念。而到了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阿方仍在繼續伸手要錢
1972年的尼克鬆訪華,極大地緩解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但卻使阿爾巴尼亞非常惱怒,阿領導人霍查不但親自寫萬言信給毛澤東抗議:「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鬆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我們堅信,其他國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會接受已宣布的尼克鬆對中國的訪問。……(中國的做法)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後來,阿方黨報又公開刊文批判毛澤東新鮮出爐的「三個世界理論」,稱其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是國際共運中的「機會主義變種」,旨在熄滅階級鬥爭;說「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據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載《炎黃春秋》)
「階級兄弟」的關系既然已經保不住,建立在這一關系基礎上的「革命援助」,自然也不可避免要開始大打折扣。1974年10月,阿方領導人謝胡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在阿第六個五年計劃(1976至1980)期間,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認為過去對阿的援助已經不少,這次要求數量過大,中國力不從心,無法滿足;且鑒於阿已有一定的自力史更生能力,中國決定少給援助。阿方堅決要求增加貸款,還提出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並再三要求中方提供糧油援助。一方面,中阿兄弟關系已經不復從前,另一方面中國此刻經濟已處於崩潰邊緣,最終只答應貸款1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對這個結果相當不滿,遂在國內掀起聲討中國的運動,說什麽「決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提供中國需要的原油和瀝青。
但批判歸批判,阿方仍在繼續伸手要錢。1975年,中、阿又簽訂了一批長期無息貸款議定書。直到1978年,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才正式作出終止對阿援助的決定。在那份公開發布的《中國外交部關於被迫停止對阿爾巴尼亞援助和接回專家問題的照會》裡,中方歷數了字50年代以來,中國不顧本國民生困苦,屢屢大規模援助阿方的事實。再無可能獲得援助後,這年年底,阿領導人霍查在公開講話中,遂公然把中國列為「主要敵人」,其隨後出版的著作《中國紀事》,則全面反華,甚至號召推翻中國現任領導人。
時至今日,竟然還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以「階級兄弟」為基本出發點的畸形外交,真是一個巨大的悲哀。看看阿爾巴尼亞這段「革命援助」的歷史,除了收獲堵心之外,給國計民生可曾帶來半點好處?
文章來源:《騰訊網》
援助「兄弟國家」是「國際主義義務」
「革命援助」是世界共運的特殊現象。究其原因有二:一者,為擺脫孤立局面,蘇聯(俄)建政伊始,即致力於援助和輸出革命;二者,共運本身從理論到實踐都以階級為立足點,自然也就帶有超脫國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所以,近代以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也就從傳統的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外交關系」,變成了一種奇特以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兄弟關系」。
1958年l0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陳毅、李富春《關於加強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領導的請示報告》,批示中說:「認真做好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也是我國人民對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的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直接以文件的形式,將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外交關系,轉變成了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的兄弟關系——中國與阿爾巴尼亞自然也是「兄弟關系」。但在整個五十年代,兩國關系並不密切,中國雖然給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但總體來說,援助的總額不大,對本國民生沒有造成什麽影響,在阿爾巴尼亞接受的全部「革命援助」中所佔比例也很小(最大的援助國是蘇聯)。
在整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裡,阿爾巴尼亞國小力微,並不受蘇聯的重視。但阿爾巴尼亞卻對蘇聯模式——準確說來是斯大林模式的認同感最為強烈。所以,當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政權與蘇聯分道揚鑣時,阿爾巴尼亞堅決地站在了蘇聯一邊,在東歐共產黨中間,最早在自己黨內清洗所謂的「鐵托分子」。當然,阿爾巴尼亞如此做,除了意識形態上對斯大林模式的高度認同,也與阿爾巴尼亞一直受到來自南斯拉夫的控制有關。
蘇聯與南斯拉夫直接暴力衝突之後,阿爾巴尼亞藉助蘇聯的力量徹底擺脫了南斯拉夫的控制;蘇聯則因為阿爾巴尼亞的絕對支持,而成為其最大的援助國。但好景不長,隨著斯大林的去世,赫魯曉夫執政的蘇聯開始致力於改善同南斯拉夫的關系;在這一過程中,阿爾巴尼亞屢次發出強硬聲音,反對赫魯曉夫的做法。1956年蘇共二十大重新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極大地刺激了阿爾巴尼亞政府。
與阿爾巴尼亞相似,中國政府此一時期,也屢屢對赫魯曉夫的「蘇聯新政」提出批評。1958年全世界60多個共產黨參加的「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運動」,蘇共的批判如蜻蜓點水不痛不癢,中共的批判則有如急風驟雨並付諸實際行動,中國召回了駐南大使,南斯拉夫也召回了其駐華大使。中、阿兩國因為相同的意識形態越走越近。

1968年,中國媒體報道「阿爾巴尼亞青年熱情學習毛主席著作」(網路圖片)
蘇聯終止對阿援助
阿爾巴尼亞首次公開與中國站在一起,是1960年6月20至25日召開的布加勒斯特會議。這次會議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同一批東歐國家共產黨對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展開了猛烈的批判攻勢。
赫魯曉夫的主要意見,是人為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應該尋求和平共處的可能;同時指責中國「拒絕和平共處」、「希望戰爭」、在國際共運中「爭奪領導」、「要充當教員」、「當檢察官、當政委」、「企圖利用斯大林問題改變蘇共現在的領導」;並認為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治掛帥、大煉鋼鐵等都是錯誤的。(詳見閻明復《隨彭真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載《中共黨史資料102輯》)
在大多數與會共產黨選擇與赫魯曉夫統一立場的情況下,阿爾巴尼亞代表罕見地公開站出來表態支持中共,因此被赫魯曉夫斥責,並遭受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圍攻。布加勒斯特會後一個月,阿黨領袖謝胡在約見中國駐阿代辦時說:阿勞動黨將堅持馬列主義,堅決支持中共的觀點,阿爾巴尼亞黨和國家雖然都很小,但絕不向任何力量屈服,要為馬列主義而生,為馬列主義而死。此後多次共運會議,阿爾巴尼亞都選擇了與中國立場一致。但也因此徹底惹怒了赫魯曉夫,招致蘇聯於1961年單方面撕毀了對阿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和根據協議駐守在阿港口的蘇聯艦隊,並拒絕阿參加華約會議,12月更中斷了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系。
中國成為阿爾巴尼亞最大的援助國
蘇、阿關系徹底冰凍的同時,中、阿關系則迅速升溫。最引人註目的現象,是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不斷,且禮遇規格極高。周恩來訪阿時,阿方領導人往往全部出迎,且每次都會舉行10萬人以上的群眾歡迎集會;阿方領導人訪華時,除毛澤東外,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要前去機場迎接,北京還組織了百萬人規模的群眾夾道歡迎。當然,最實際的,還是中國接替蘇聯,成為了阿方最大的援助國。
據新華社高級編輯、前駐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駐斯科普裡分社首席記者王洪起回憶:1961年春,蘇聯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除了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幾十萬噸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幫助阿實現了瀕於夭折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解決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來,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其中一般物資佔28%強,軍事物資佔43%強,成套項目佔25%強,現匯佔2%強),阿成為我對外援助受援國人均數額最多的國家。中國援阿成套項目共計142個,其中已經建成的91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已經考察和進行設計的17個。
中國為阿爾巴尼亞興建了鋼鐵、化肥、制堿、制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通訊和廣播等部門的項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業化水平。應當強調指出的是,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以及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和遭受唐山地震,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180萬噸。同時也應承認,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有的援阿項目超過了中國的經濟和技術負擔能力,上馬顯得頗為吃力。為了完成阿的復雜項目,中國在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不得不先在國內進行大量試驗和試制工作,甚至動員了全國26個省市的100多個單位參加,並建立專門的實驗工廠。為此,中國還有兩人犧牲了生命。」
中國有 阿國也要有
1961年春,正值中國大饑荒時期。本國糧食尚需進口,此時援助阿爾巴尼亞「幾十萬噸糧食」,其難度可想而知。對這種影響到了本國民生的對外援助,曾短暫出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飈,在其晚年回憶錄中如此寫道:
特別令我感到憂慮的是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問題。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編輯註:此一時期,中國的人均年收入不過2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乎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1969年北京群眾隆重集會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25周年(網路圖片)
以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為標準向中國索要援助
阿爾巴尼亞當局按照歐洲發達國家的生活標準,向當時極度貧窮的中國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援助要求。據耿飈回憶: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麽多東西打算什麽時候還?他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當謝胡陪同先念同誌訪問阿中南部費裡區時,在長達六個小時的往返途中,謝胡幾乎談了六個小時,所談內容全是要東西。他說: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鋼』,還需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還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還說,在下一個五年計劃裡,將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先念同誌當即表示,你們計劃你們的需要,我們考慮我們的可能。
我通過對阿某些地區的實地調查了解到:阿在經濟建設方面,貪大求全,戰線拉得太長,非生產項目搞得太多。1969年,阿非生產建設項目的投資就占國家總投資的24%,因而造成勞動力嚴重缺乏。根據阿方自己的計算,在第五個五年計劃中,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簽訂的協定,我國援阿新項目的建築和投產就需要增加4.6萬名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約等於阿當時產業工人的38.3%。阿還存在一種不適當地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看齊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臺時說,計劃在阿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用說農村了。所以我當時就感到這種傾向很值得註意。
由於阿方領導人存在上述不切實際的想法,所以他們向我國提出了不少極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們幫他們搞了紡織廠,但他們沒有棉花,我們還要用外匯買進棉花給他們。他們織成布,做了成衣,還硬要賣給我們,倒過來賺我們的錢。記得有一次阿副總理查爾查尼向我提出,要我們幫助更換化肥廠的主要設備。該化肥廠是我國援建的,本應使用我國生產的機器設備,但阿方不要我國的機器,指定要用義大利的,我們只好用外匯從義大利買來機器安裝上。現在這臺機器壞了,查爾查尼還要我們從義大利買機器來更換。我當即拒絕了他的這個不合理要求。
用來賑濟大饑荒的進口糧援助阿方
最讓人寒心的是,中國勒緊褲腰帶不顧國內的嚴重饑荒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阿方卻對此毫無感知,反而浪費極度嚴重。據耿飈回憶: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阿方浪費極其嚴重。我在實地調查時看到:馬路邊的電線桿,都是用我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他們還把我國援助的水泥、鋼筋用來到處修建烈士紀念碑,在全國共修建了1萬多個。我們援助的化肥,被亂七八糟地堆在地裡,任憑日曬雨淋。諸如此類的浪費現象,不勝枚舉。
新華社高級編輯、前駐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駐斯科普裡分社首席記者王洪起也有相似的回憶:中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帶,萬裡迢迢,很不容易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裡,常年風吹雨打。我們的專家看到這樣嚴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淚。有些援阿專家(在援阿年代裡,先後有近6000名工程技術人員遠離家鄉,赴阿爾巴尼亞工作)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裡說了一句『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當我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系,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阿的胃口越來越大,什麽都想要,數額一次比一次加碼,幾億幾十億的要,填不滿的無底洞。阿以小欺大,強我所難,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當然,認為援助是中國天經地義的責任。
在上世紀60年代初,為了緩解饑餓,中國擠出極其寶貴的外匯,從國外進口一些糧食。但只要阿爾巴尼亞說需要,中國就把進口的糧食送給他們。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另據周恩來衛士喬金旺回憶: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旬加1961年來訪,主要是伸手,給少了還不行。阿爾巴尼亞不理解我們也很困難,雙方談得不好,總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來對來華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凱萊齊說:我們根據力所能及承擔國際義務,但由於我國連續遇到3年災荒,加上蘇聯撤退專家,所以我們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此援助不能像你們希望的那麽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蘇聯過去答應的援助全部包下來,你們自力更生還是主要的。盡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國還是與阿爾巴尼亞簽訂了五項援助議定書。
為阿方領導人專門生產特供香煙
最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當時的中國,居然還要替阿方領導人生產特供香煙,供其個人享受。王洪起回憶:阿在國際市場上賣不出去的一些劣質商品如香煙、童裝、紡織品等都強行塞給我們包銷。人們可能還記得,一毛二一盒的「鉆石」牌香煙,就是阿爾巴尼亞的。價格雖然便宜,但人們並不喜歡。就連他們自己的最高領導人霍查,也不吸本國煙而吸的是筒裝的「大中華」(霍查稱「天安門」香煙)。記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國使館突然分給使館和分社每人兩筒中華牌香煙,說是「贈品」。後來大家才知道,這些香煙是中國為霍查專門製造的,而且根據霍查的要求,香煙雖不帶過濾嘴,但對尼古丁做了專門的處理。1973年,霍查心臟病首次發作,醫生建議他戒煙,他才斷了43年的吸煙歷史,而由中國運去的最後一批香煙也就不要了,使館便分給了使館人員。
王稼的「三和一少」
阿爾巴尼亞只是中國六十年代諸多「革命援助」國家的一個而已。這樣一種問題百出的「革命援助」,不可避免會在國內引發諸多的異議。王稼祥就是其中之一。
1962的七千人大會,將全國民眾都在挨餓這一殘酷現實捅破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誌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裡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痛哭之後,王稼祥遂在小範圍內談了自己對調整對外方針的意見,並徵得中聯部黨委的同意,聯名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建議信。
王稼祥建議:「不要說必須在消滅美帝國主義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避免」;還批評那種認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處」「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有和平共處」的觀點;提出「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關於對外方針政策,提出:為了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加速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對外有必要採取緩和的方針,而不是採取加劇的方針。對外經濟援助,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建議,與毛澤東當日所實行的對外方針截然相反。1962年9月,陳毅在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的發言中批評了所謂『三和一少』的一股風(即主張對美國和緩一點,對蘇聯和緩一點,對印度和緩一點,對外經濟援助少一點)。陳毅的主旨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目光短淺,不能打小算盤,要打大算盤,不能只算經濟賬,要算政治賬。陳毅的發言得到毛澤東的贊同。1963年5月,毛澤東開始「算政治帳」,將「三和一少」上升為修正主義的路線。他在同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的談話中說: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們的鬥爭援助少一些。這就是修正主義路線。1964年2月,毛澤東再次會見威爾科克斯,又講了上述內容。並說:針對「三和一少」,我們的方針就是「三鬥一多」。「三和一少」是赫魯曉夫的口號,「三鬥一多」是我們的口號。隨後毛澤東在會見朝鮮勞動黨金日成和日本共產黨侉田裡見時也談了上述內容,並點名批評了王稼祥。
因為「三和一少」忤逆了毛澤東的「三鬥一多」,王稼祥被撤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政治生涯徹底結束。王稼祥本人被軟禁,妻子朱仲麗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動輒六七個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兒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鬥,投河自殺身亡。因難以承受和應對接連不斷的暴力批鬥,王稼祥精神極度緊張,最後產生了精神紊亂和幻覺、幻視癥,時常不斷叫喊:「我沒有罪!」1974年1月24日晚,王稼祥因心臟病突發猝然去世——此前兩天,《北京日報》刊文,再度批判所謂的「三和一少」的「妖風」。
耿飈直言批評
王稼祥的悲慘命運,卻沒有降臨到同樣批評「革命援助」、「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的耿飈頭上。耿飈目睹了阿爾巴尼亞大肆無節制揮霍中國援助之後,在1969年寫信反對這種無節制援助的做法。信最後到了毛澤東手裡,但同樣的意見,耿飈卻收獲了和王稼祥截然相反的命運。據耿飈回憶:
這種情況,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這符合國際主義原則,但必須註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的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現在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對我們來說,是把錢物倒進一個無底洞,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方來說,只能養成他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懶惰習慣,以及對外援的依賴心理,而無助於他們的經濟建設。因此我想把這種情況向國內反映,但是又存在顧慮。因為,在當時國內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誰敢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其後果難以預料。萬一給江青一夥人和造反派扣上幾頂「反對國際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繼續推行「三降一滅」路線的帽子,豈不要重進「牛棚」。
經過反復激烈的思想鬥爭,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和特命全權大使的政治責任感終於驅使我撇開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提起筆來給當時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同誌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詳細反映了上述情況,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提出,我國對阿援助是主客觀不一致,即主觀願望是好的,是為了幫助阿搞好經濟建設,但客觀效果並不好,不但沒有使他們的經濟得到發展,反而助長了他們的驕傲、懶惰和依賴思想。因此,我建議國內對援阿的規模、內容和方法,均須重新考慮,通盤修改。喬冠華看信後,對我如實反映情況表示贊賞,對我提的意見也表示贊同;但在當時情況下,他對此事也無能為力,只是將我的信轉報中央。後來我回國後遇到李先念副總理,他對我說:『耿飈,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我對這件事也有意見,但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周恩來有一次和我談話時也提起我寫信的事。他告訴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後說:「耿飈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也許正是由於毛說了這句話,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這件事整我。(《耿飈回憶錄(1949-1992)》,江蘇人民出版社)
耿、王二人命運如此迥異,個中原因,當然不是因為耿飈運氣好,而是因為中、阿關系此時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1962年,阿方竭力反蘇;稍後文革爆發,阿方又公開表示支持,還要求出版阿爾巴尼亞文的《毛主席語錄》,這些全都相當契合毛澤東的心意。但到了1969年,毛澤東在擔憂蘇聯可能會入侵中國、感嘆「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的同時,已經有意與美國緩和外交關系,並採取了實際行動。反觀阿爾巴尼亞,因中國1969年接待蘇聯總理柯西金過境及周恩來、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握手,阿方公開表示反對,並降低了出席中國建國20周年慶典的規格——這無疑令毛澤東相當不快,同時也是耿飈直言批評阿爾巴尼亞貪得無厭肆意揮霍中國援助,卻得到毛澤東「敢講真話」的贊揚的直接原因。
「革命援助」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自1969年之後,中阿關系迅速降溫,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謀求與蘇聯和解,阿方不能接受;二是中國謀求與美國關系正常化,阿方更斥責為「修正主義」。這讓主持這一外交政策大轉變的毛澤東很不滿意。
但毛澤東贊揚了耿飈對阿爾巴尼亞的批評,卻並沒有停止不切實際的「革命援助」。1970年,阿爾巴尼亞厚著臉皮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中國最後仍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沒有完全滿足阿爾巴尼亞的索求,一方面應該是其獅子大張口數額太大,另一方面,應該也與中方對阿方的不滿有關——也是在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曾主動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由此可見,毛澤東並沒有改變其不切實際的「革命援助」理念。而到了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阿方仍在繼續伸手要錢
1972年的尼克鬆訪華,極大地緩解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但卻使阿爾巴尼亞非常惱怒,阿領導人霍查不但親自寫萬言信給毛澤東抗議:「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鬆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我們堅信,其他國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會接受已宣布的尼克鬆對中國的訪問。……(中國的做法)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後來,阿方黨報又公開刊文批判毛澤東新鮮出爐的「三個世界理論」,稱其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是國際共運中的「機會主義變種」,旨在熄滅階級鬥爭;說「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據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載《炎黃春秋》)
「階級兄弟」的關系既然已經保不住,建立在這一關系基礎上的「革命援助」,自然也不可避免要開始大打折扣。1974年10月,阿方領導人謝胡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在阿第六個五年計劃(1976至1980)期間,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認為過去對阿的援助已經不少,這次要求數量過大,中國力不從心,無法滿足;且鑒於阿已有一定的自力史更生能力,中國決定少給援助。阿方堅決要求增加貸款,還提出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並再三要求中方提供糧油援助。一方面,中阿兄弟關系已經不復從前,另一方面中國此刻經濟已處於崩潰邊緣,最終只答應貸款1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對這個結果相當不滿,遂在國內掀起聲討中國的運動,說什麽「決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提供中國需要的原油和瀝青。
但批判歸批判,阿方仍在繼續伸手要錢。1975年,中、阿又簽訂了一批長期無息貸款議定書。直到1978年,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才正式作出終止對阿援助的決定。在那份公開發布的《中國外交部關於被迫停止對阿爾巴尼亞援助和接回專家問題的照會》裡,中方歷數了字50年代以來,中國不顧本國民生困苦,屢屢大規模援助阿方的事實。再無可能獲得援助後,這年年底,阿領導人霍查在公開講話中,遂公然把中國列為「主要敵人」,其隨後出版的著作《中國紀事》,則全面反華,甚至號召推翻中國現任領導人。
時至今日,竟然還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以「階級兄弟」為基本出發點的畸形外交,真是一個巨大的悲哀。看看阿爾巴尼亞這段「革命援助」的歷史,除了收獲堵心之外,給國計民生可曾帶來半點好處?
文章來源:《騰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