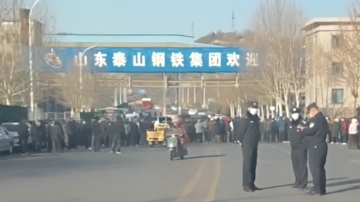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12月23日訊】親愛的西北政法大學的學生和校友們、尊敬的西北政法大學的領導和同事們:
請寬容我公開發表辭職聲明。
20多天前,我因去香港中文大學開學術會議,去機場路上突遭學校原因不明的勸阻。我堅持前往,出境和會議一切順利。回來後,我被學校以「找人代課違反教學紀律」為由,予以通報批評處分。對於這一處分,我完全接受。我很感激黃興超律師為我的學生奉獻的精彩課堂,學生大讚受益,令我無比欣慰。以前每學期,我照例總會請幾個校外知名學者律師到我課堂上給學生開闊視野。我承認這是違反文本上的教學紀律的,但我只好如此,甘願受罰。我從來沒有藉此懈怠正常教學,反倒是除了課堂上盡職盡責,願意多加課時之外,還常常以讀書會、沙龍講座、參與學生社團活動、書信網路深入交流等方式,和學生在一起。這沒什麼好炫耀的,不過是我作為教師最大的本分和樂趣而已。我問心無愧。
更嚴重的是,香港開會回來,我卻被吊銷了港澳通行證,令我錯愕不解。我數次去相關部門查詢、提供書面說明並申請恢復,皆無果。後得知學校也配合提供了一份材料,說我當時辦理通行證的簽字手續不全。嚴格說來,這是事實。8月份辦證時恰逢暑假,只口頭給一位副院長打了招呼,然後去黨政辦蓋了校領導簽章,開學後又因教學事務繁忙而沒及時補上表格。但我認為這一點並非註銷通行證的理由,因為它只屬程序瑕疵,我並沒有偽造任何身份證明。在港期間,我也無任何違法犯罪言行。此次內地同去香港開會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數個高校的教授,他們皆沒遭遇如此待遇。
但我仍然盡量理解這一處理決定。作為妥協,我一方面接受這一後果,另一方面提出:既然上次我手續不全,那麼這次我便嚴格按照程序要求申請補辦吧。剛好我也需要辦理一個因私護照,於是便提出了正式申請。沒想到處處遭遇推脫。連續一周,一天數次,從早到晚,我往返於學院、職能部門、黨政辦、校長辦公室、書記辦公室,甚至相關領導家門口,費盡心思口舌,主動溝通交流。每個人都態度很好,沒有人拒絕說你不能申請,卻也沒任何人說你可以辦理。我反覆申明,假如我因違法犯罪或政治問題而進入禁止出入境名單,或是有上面的禁令,我絕不會為難學校。但既然我是合法公民,既然所有教師都能辦理,為什麼我就不能?一切按規則辦事,誰到底能擔多大的責任呢?沒有任何實質回應,沒有下文,反覆告訴我的就是類似的話:洪果,算了吧,聽我的,從長計議,別想太多,等等。
上周四早晨,我又一次與學院的張書記和王院長交涉。他們是非常關心我的領導,也是非常了解我的師友。一個多小時,我們已沒法再重複說過多次的話,三個人坐在那裡,無奈地你嘆一口氣我嘆一口氣。我知道再無任何結局,流著淚,黯然走在霧霾籠罩的冰冷操場上。就在頭一天,我給即將上任的校黨委書記發簡訊說,我願意配合學校今後一切的和諧穩定工作;在之前的一次訴求時,我甚至有過向領導下跪的衝動。我終於理解了那些訪民,他們居無定所,一次一次地,傾盡所有家當,賭上整個人生,只為了徒勞無助地、毫無結果地討個說法;我還想到了這學期給學生講的卡夫卡筆下的K,在三十歲生日那天受到莫名其妙的追訴,從此不由自主捲入根本不知何罪的起訴,每個人都很關心他的處境,但總是使他徘徊於法律的門前,他從開初的理直氣壯慢慢被消耗得疲軟無力,直到31歲生日那天,不明不白地,像狗一樣地被處死。
在這期間還遇到另外兩件事情。12月初,我按之前的安排,應邀去外面一所大學作有關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司法改革問題的講座,卻再次遇到莫名的追問阻撓,但我當時還是堅持去了,無奈地想這次又該剝奪我怎樣的出行權。講座的內容全程有視頻可公開,完全屬於正常的建設性的學術探討。而在上一周某個晚上,有學生社團邀請我跟大一學生聊聊如何讀書和過好大學生活的問題,學生有前車之鑒,怕申請遇到麻煩,於是提前占上一個空閑教室,然後才通知我前往。我和本校學生進行這種本是光明正大的學習交流,如今都得如此偷偷摸摸進行,甚至還有學生因擔憂我政治敏感而不敢前來。作為一介普通教師和文弱書生,我為自己的這一被政治化的形象而感到悲涼。
這些年,我在大學裡做了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是熱衷於教學相長的活動,以各種方式和學生互動交流;不過是堅持請一些學者律師到學校講座,滿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學生的知識渴求;不過是堅持和學生開展讀書討論會,而公開正當坦然地做出過抗爭;不過是就學校一些具體的有違大學法治精神的規定和做法,提出過就事論事的建設性批評。我一向堅守理性、善意、坦誠的原則,堅守學術獨立、師生平等、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這些年來,我發表過一些公開言說,卻都是從學術專業的視角出發;我做出過一些底線抗爭,但從沒能力並且也本能地拒絕成為一個鬥士。我只是一個想保持獨立和說說真話的個體,只是一個想好好上上課看看書寫寫文字的學者。
然而,我的路卻越走越窄,進行教學探索和學術交流的空間也越來越小。我心目中的並且也身體力行的美好大學,就是學術的自由、開放與包容。我的各種行為選擇,包括我兩年前宣布拒絕參與評審教授,都是從這一原則出發。我喜歡面對學生各種嚴肅的批判和質疑,享受與青年學子探討知識和人生的狀態。我尊重他人不同的思想、個性、風格和自我規劃,所以也從不認為自己的觀點論證是正確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恰當的。但是,多樣性無比重要,我為這所大學提供的僅僅是多元存在中的一元。這是自我的獨立,不是標新立異,不是自以為是,它僅僅代表著我願意的生活。
我也從來不是反體制的人。在讀書會受阻期間,我說過,我熱愛這個國家這片土地,也從來不會反黨反政府。體制就是你願意不願意,它都在那裡。體制支配著你的全部生活,卻又看不見摸不著,有什麼好反抗能反抗的?反對對抗又能有什麼意義和結果?到哪不都一樣嗎?我因此從來不對此抱以期望和行動。然而,我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你能改變的只有你自己。正因為哪裡都一樣,所以到哪裡,我都有權為自己保留一點點獨立自由尊嚴的空間,那是我珍愛的精神家園。所以,與拒絕單一化的大學相對應,我也拒絕被體制化和規訓化的生活,我選擇不參與一些體制內的遊戲,卻也願意在體制下進行一些有益的推動合作。但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覺與體制保持某種獨立和距離,這種姿態,難道能叫反體制,跟體制過不去嗎?我不喜歡那種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維。
是的,我害怕被體制化,為自己在這次爭取基本權利的過程中幾欲下跪而後怕。這是我想要辭職的原因之一。恰好是通過與各種層次的領導、管理者們一次次深入的交流,一次次感受雙方的自說自話及溝通障礙,我才深味體制化力量的強大。那是一種每個人都對你很好、都在盡職盡責、都很無奈無辜的思維慣性。沒有作惡者,一個都沒有。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為什麼在剝奪一個人的權利時,各個機構部門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為什麼當事人想申請恢復或維護自己的權利時,卻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誰是決策者,誰為此負責,所有機構部門都顯得如此無奈和忙碌,顧不上孤獨的當事者的苦痛艱難?我認為這樣不好,這對很多很多底層掙扎的人們太殘忍。
這種體制化的強大力量使我幡然悔悟:一個人活在世上,不是為了說服別人,甚至不是為了說服自己。連續數個夜晚,我不斷懷疑自己,甚至徹底將自我否定,摧毀自己之前所有的信念和夢想。我如此脆弱而不堪一擊,完全陷入了虛空幻滅的深淵。然而,在經歷痛苦的掙扎後,我還是意識到自己付出如此代價堅守的位置,是最適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選擇,無論體制內外。我不反對任何東西,也無法改變任何東西。我雖然懷疑自己的辭職選擇是否正確,是否給我帶來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須回歸,回歸到那個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辭職理由,是我無顏再面對學生。我曾不止一次說過,我如此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如此喜歡跟學生在一起,這是我一直眷戀於此的緣由。但現在,我扛不住了。一個這麼簡單的小事,一項如此普通的權利,作為法學教師,我都無能爭取,我還有什麼資格站在講台上,給將來從事法律職業的學生們講什麼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權威、程序的價值、正義的底線、權利的重要?我不配,一點都不配。是的,我可以以曾努力過但沒結果作為開脫的理由。要知道,我們總能為自己的妥協找到說辭。但是,我很清楚,當我抱著委屈求全的姿態,繼續站在講台上,我不過是在自欺欺人,為苟且偷生而放棄自己曾經捍衛過的原則和底線。我內心不安,不願如此分裂。
親愛的同學們,自從2006年我博士畢業回西北政法大學任教,平均每年有上千名學生直接聽過我的授課,跟學生各種方式的交往交流更是不計其數。這是我這一生最幸福的時光,是我最為榮耀的經歷,是我最為寶貴的記憶。現在,我要離開這所學校了,儘管我是如此難過,但你們不必為此而憂傷。課堂只是大學教育一個微不足道的環節,大學應該超越課堂和圍牆,我們今後還可以以網路等方式進行探討交流。而且,事實上,不同老師的課,都有各自的風格,都能讓你們受益。西北政法大學有非常多敬業的學識深厚的優秀老師,他們好多人的課比我上得更好,也比我更加愛護學生。更何況,大學四年,重要的是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做好自我的定位規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重要的是你們自己,這是任何老師都不能取代也不該取代的。
西北政法大學是我的母校,從本科到工作,我在這裡生活了近二十年。我不想在此表白我對這所學校的感情有多深。有我這麼多年各種歡笑眼淚為證,有我與學生各種公開的教學學術活動記錄為證,有我各種愛與痛的行跡文字為證。也許我愛這所學校的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樣,如果這些年來我為教學學術底線的一些抗爭舉動、我對學校一些問題所做的公開批評損害了這所學校的聲譽,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次按照學校的規定程序內部維權的努力遭致失敗,迫使我提出公開辭職,也是給關心我的學生師友一個交代,為此我再次向學校致歉。但請學校放心,這是最後一次了,以後我再也不會給母校添亂惹麻煩了。今後,我也正式成了西北政法的校友,我盼望這所學校越辦越好。作為西北法律重鎮,學校近年來因各種原因而處於弱勢,能有今天的發展實在不易。所有師生校友都有責任在各自領域為學校的進步和聲譽做出綿薄之力。
西北政法的領導和管理者們,這麼多天反覆深入的交流,我真切地理解了你們的苦衷,你們的壓力,你們的付出,你們的辛勞。感謝賈宇校長、宋覺書記等對一名普通教職員工的尊重,感謝你們對我一次次訴說的耐心傾聽。我感激你們。在此我要特別向教務處長王麟和刑事法學院張處社書記鄭重道歉,請原諒在與你們交涉過程中我的誤會和情緒過激的言辭。不過,人之將走,其言也善,我還是想坦誠說上兩句。我不求多麼理想的大學,也承認這是黨和政府的大學,但這畢竟是一所大學,而且是培養法律人才的大學。我惟願學校在應對各種事情的時候,能夠不簡單機械地執行上面的命令,能夠多少深入了解一下師生做的事情,跟上面做一些溝通解釋的工作,能夠考慮一下政治與學術的邊界。我真的不願看到大家都在提法治的信仰,但一碰到問題,操持的話語和行事的方式就全變成了政治掛帥的考量。和諧的夢想說來不難,只要能更就事論事一點,更簡單一點,更講道理一點,更程序公正一點,更尊重大學規律一點。如果這些話多餘、不對、越俎代庖、甚至對你們的工作有曲解,我誠摯請你們海涵。
這麼多年尤其是最近一直關心著我的許多師友們,對不起,這次我沒採納你們要我別辭職的意見。不少師友勸我忍一忍,放一放,寧願被開除也不辭職,是的,之前我也是這麼想的,但現在我不再這麼認為了,我何必為了賭一口氣而耗在這裡,讓雙方都那麼不快樂?我是孤獨的一個人,面對無影無蹤的力量,我怎能耗得起?我很疲憊,像一個無知懵懂地闖入政治叢林的孩子,看不懂這裡複雜而捉摸不定的遊戲規則。連日來,我都在猶豫彷徨,不止一次後悔自己的道路,時時否定自我,但思前想後,最終還是決定走出這一步。也許這是糟糕的選擇,但也是我深思熟慮的結果,是我選擇自由尊嚴的生活而註定要付出的代價。我只能認命。
我知道,體制無處不在,我無處可逃。所以,請相信,我的辭職,不是在逃避退縮,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嚴、底線和原則。失去這些,我的生命就沒有依託,我就是行屍走肉,我不再是我。我的辭職與任何個人恩怨無關,與西北政法這所大學無關。請大家理解今日大學面臨的各種無力抵擋的壓力。我真的沒有情緒,沒有抱怨,我唯一要正視的,是自己的內心,我的內心是我唯一值得抗爭的對手。說到底,我是在跟自己較勁、跟自己過不去,就像少年派與他心目中的那隻老虎的搏鬥。
辭職後的日子很艱難,在體制內那麼多年,我深深懷疑自己能否還有獨自謀生的能力。而今臨近不惑,卻要像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尋找新的去處。實在對不起,芳寧,讓你無端承受了那麼多的委屈重負。實在對不起,園園,我不是個稱職的父親……。
文章來源:諶洪果的博客
請寬容我公開發表辭職聲明。
20多天前,我因去香港中文大學開學術會議,去機場路上突遭學校原因不明的勸阻。我堅持前往,出境和會議一切順利。回來後,我被學校以「找人代課違反教學紀律」為由,予以通報批評處分。對於這一處分,我完全接受。我很感激黃興超律師為我的學生奉獻的精彩課堂,學生大讚受益,令我無比欣慰。以前每學期,我照例總會請幾個校外知名學者律師到我課堂上給學生開闊視野。我承認這是違反文本上的教學紀律的,但我只好如此,甘願受罰。我從來沒有藉此懈怠正常教學,反倒是除了課堂上盡職盡責,願意多加課時之外,還常常以讀書會、沙龍講座、參與學生社團活動、書信網路深入交流等方式,和學生在一起。這沒什麼好炫耀的,不過是我作為教師最大的本分和樂趣而已。我問心無愧。
更嚴重的是,香港開會回來,我卻被吊銷了港澳通行證,令我錯愕不解。我數次去相關部門查詢、提供書面說明並申請恢復,皆無果。後得知學校也配合提供了一份材料,說我當時辦理通行證的簽字手續不全。嚴格說來,這是事實。8月份辦證時恰逢暑假,只口頭給一位副院長打了招呼,然後去黨政辦蓋了校領導簽章,開學後又因教學事務繁忙而沒及時補上表格。但我認為這一點並非註銷通行證的理由,因為它只屬程序瑕疵,我並沒有偽造任何身份證明。在港期間,我也無任何違法犯罪言行。此次內地同去香港開會的有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數個高校的教授,他們皆沒遭遇如此待遇。
但我仍然盡量理解這一處理決定。作為妥協,我一方面接受這一後果,另一方面提出:既然上次我手續不全,那麼這次我便嚴格按照程序要求申請補辦吧。剛好我也需要辦理一個因私護照,於是便提出了正式申請。沒想到處處遭遇推脫。連續一周,一天數次,從早到晚,我往返於學院、職能部門、黨政辦、校長辦公室、書記辦公室,甚至相關領導家門口,費盡心思口舌,主動溝通交流。每個人都態度很好,沒有人拒絕說你不能申請,卻也沒任何人說你可以辦理。我反覆申明,假如我因違法犯罪或政治問題而進入禁止出入境名單,或是有上面的禁令,我絕不會為難學校。但既然我是合法公民,既然所有教師都能辦理,為什麼我就不能?一切按規則辦事,誰到底能擔多大的責任呢?沒有任何實質回應,沒有下文,反覆告訴我的就是類似的話:洪果,算了吧,聽我的,從長計議,別想太多,等等。
上周四早晨,我又一次與學院的張書記和王院長交涉。他們是非常關心我的領導,也是非常了解我的師友。一個多小時,我們已沒法再重複說過多次的話,三個人坐在那裡,無奈地你嘆一口氣我嘆一口氣。我知道再無任何結局,流著淚,黯然走在霧霾籠罩的冰冷操場上。就在頭一天,我給即將上任的校黨委書記發簡訊說,我願意配合學校今後一切的和諧穩定工作;在之前的一次訴求時,我甚至有過向領導下跪的衝動。我終於理解了那些訪民,他們居無定所,一次一次地,傾盡所有家當,賭上整個人生,只為了徒勞無助地、毫無結果地討個說法;我還想到了這學期給學生講的卡夫卡筆下的K,在三十歲生日那天受到莫名其妙的追訴,從此不由自主捲入根本不知何罪的起訴,每個人都很關心他的處境,但總是使他徘徊於法律的門前,他從開初的理直氣壯慢慢被消耗得疲軟無力,直到31歲生日那天,不明不白地,像狗一樣地被處死。
在這期間還遇到另外兩件事情。12月初,我按之前的安排,應邀去外面一所大學作有關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司法改革問題的講座,卻再次遇到莫名的追問阻撓,但我當時還是堅持去了,無奈地想這次又該剝奪我怎樣的出行權。講座的內容全程有視頻可公開,完全屬於正常的建設性的學術探討。而在上一周某個晚上,有學生社團邀請我跟大一學生聊聊如何讀書和過好大學生活的問題,學生有前車之鑒,怕申請遇到麻煩,於是提前占上一個空閑教室,然後才通知我前往。我和本校學生進行這種本是光明正大的學習交流,如今都得如此偷偷摸摸進行,甚至還有學生因擔憂我政治敏感而不敢前來。作為一介普通教師和文弱書生,我為自己的這一被政治化的形象而感到悲涼。
這些年,我在大學裡做了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是熱衷於教學相長的活動,以各種方式和學生互動交流;不過是堅持請一些學者律師到學校講座,滿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學生的知識渴求;不過是堅持和學生開展讀書討論會,而公開正當坦然地做出過抗爭;不過是就學校一些具體的有違大學法治精神的規定和做法,提出過就事論事的建設性批評。我一向堅守理性、善意、坦誠的原則,堅守學術獨立、師生平等、價值中立的學者操守。這些年來,我發表過一些公開言說,卻都是從學術專業的視角出發;我做出過一些底線抗爭,但從沒能力並且也本能地拒絕成為一個鬥士。我只是一個想保持獨立和說說真話的個體,只是一個想好好上上課看看書寫寫文字的學者。
然而,我的路卻越走越窄,進行教學探索和學術交流的空間也越來越小。我心目中的並且也身體力行的美好大學,就是學術的自由、開放與包容。我的各種行為選擇,包括我兩年前宣布拒絕參與評審教授,都是從這一原則出發。我喜歡面對學生各種嚴肅的批判和質疑,享受與青年學子探討知識和人生的狀態。我尊重他人不同的思想、個性、風格和自我規劃,所以也從不認為自己的觀點論證是正確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恰當的。但是,多樣性無比重要,我為這所大學提供的僅僅是多元存在中的一元。這是自我的獨立,不是標新立異,不是自以為是,它僅僅代表著我願意的生活。
我也從來不是反體制的人。在讀書會受阻期間,我說過,我熱愛這個國家這片土地,也從來不會反黨反政府。體制就是你願意不願意,它都在那裡。體制支配著你的全部生活,卻又看不見摸不著,有什麼好反抗能反抗的?反對對抗又能有什麼意義和結果?到哪不都一樣嗎?我因此從來不對此抱以期望和行動。然而,我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你能改變的只有你自己。正因為哪裡都一樣,所以到哪裡,我都有權為自己保留一點點獨立自由尊嚴的空間,那是我珍愛的精神家園。所以,與拒絕單一化的大學相對應,我也拒絕被體制化和規訓化的生活,我選擇不參與一些體制內的遊戲,卻也願意在體制下進行一些有益的推動合作。但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覺與體制保持某種獨立和距離,這種姿態,難道能叫反體制,跟體制過不去嗎?我不喜歡那種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維。
是的,我害怕被體制化,為自己在這次爭取基本權利的過程中幾欲下跪而後怕。這是我想要辭職的原因之一。恰好是通過與各種層次的領導、管理者們一次次深入的交流,一次次感受雙方的自說自話及溝通障礙,我才深味體制化力量的強大。那是一種每個人都對你很好、都在盡職盡責、都很無奈無辜的思維慣性。沒有作惡者,一個都沒有。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為什麼在剝奪一個人的權利時,各個機構部門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為什麼當事人想申請恢復或維護自己的權利時,卻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誰是決策者,誰為此負責,所有機構部門都顯得如此無奈和忙碌,顧不上孤獨的當事者的苦痛艱難?我認為這樣不好,這對很多很多底層掙扎的人們太殘忍。
這種體制化的強大力量使我幡然悔悟:一個人活在世上,不是為了說服別人,甚至不是為了說服自己。連續數個夜晚,我不斷懷疑自己,甚至徹底將自我否定,摧毀自己之前所有的信念和夢想。我如此脆弱而不堪一擊,完全陷入了虛空幻滅的深淵。然而,在經歷痛苦的掙扎後,我還是意識到自己付出如此代價堅守的位置,是最適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選擇,無論體制內外。我不反對任何東西,也無法改變任何東西。我雖然懷疑自己的辭職選擇是否正確,是否給我帶來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須回歸,回歸到那個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辭職理由,是我無顏再面對學生。我曾不止一次說過,我如此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如此喜歡跟學生在一起,這是我一直眷戀於此的緣由。但現在,我扛不住了。一個這麼簡單的小事,一項如此普通的權利,作為法學教師,我都無能爭取,我還有什麼資格站在講台上,給將來從事法律職業的學生們講什麼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權威、程序的價值、正義的底線、權利的重要?我不配,一點都不配。是的,我可以以曾努力過但沒結果作為開脫的理由。要知道,我們總能為自己的妥協找到說辭。但是,我很清楚,當我抱著委屈求全的姿態,繼續站在講台上,我不過是在自欺欺人,為苟且偷生而放棄自己曾經捍衛過的原則和底線。我內心不安,不願如此分裂。
親愛的同學們,自從2006年我博士畢業回西北政法大學任教,平均每年有上千名學生直接聽過我的授課,跟學生各種方式的交往交流更是不計其數。這是我這一生最幸福的時光,是我最為榮耀的經歷,是我最為寶貴的記憶。現在,我要離開這所學校了,儘管我是如此難過,但你們不必為此而憂傷。課堂只是大學教育一個微不足道的環節,大學應該超越課堂和圍牆,我們今後還可以以網路等方式進行探討交流。而且,事實上,不同老師的課,都有各自的風格,都能讓你們受益。西北政法大學有非常多敬業的學識深厚的優秀老師,他們好多人的課比我上得更好,也比我更加愛護學生。更何況,大學四年,重要的是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做好自我的定位規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重要的是你們自己,這是任何老師都不能取代也不該取代的。
西北政法大學是我的母校,從本科到工作,我在這裡生活了近二十年。我不想在此表白我對這所學校的感情有多深。有我這麼多年各種歡笑眼淚為證,有我與學生各種公開的教學學術活動記錄為證,有我各種愛與痛的行跡文字為證。也許我愛這所學校的方式和很多人不一樣,如果這些年來我為教學學術底線的一些抗爭舉動、我對學校一些問題所做的公開批評損害了這所學校的聲譽,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次按照學校的規定程序內部維權的努力遭致失敗,迫使我提出公開辭職,也是給關心我的學生師友一個交代,為此我再次向學校致歉。但請學校放心,這是最後一次了,以後我再也不會給母校添亂惹麻煩了。今後,我也正式成了西北政法的校友,我盼望這所學校越辦越好。作為西北法律重鎮,學校近年來因各種原因而處於弱勢,能有今天的發展實在不易。所有師生校友都有責任在各自領域為學校的進步和聲譽做出綿薄之力。
西北政法的領導和管理者們,這麼多天反覆深入的交流,我真切地理解了你們的苦衷,你們的壓力,你們的付出,你們的辛勞。感謝賈宇校長、宋覺書記等對一名普通教職員工的尊重,感謝你們對我一次次訴說的耐心傾聽。我感激你們。在此我要特別向教務處長王麟和刑事法學院張處社書記鄭重道歉,請原諒在與你們交涉過程中我的誤會和情緒過激的言辭。不過,人之將走,其言也善,我還是想坦誠說上兩句。我不求多麼理想的大學,也承認這是黨和政府的大學,但這畢竟是一所大學,而且是培養法律人才的大學。我惟願學校在應對各種事情的時候,能夠不簡單機械地執行上面的命令,能夠多少深入了解一下師生做的事情,跟上面做一些溝通解釋的工作,能夠考慮一下政治與學術的邊界。我真的不願看到大家都在提法治的信仰,但一碰到問題,操持的話語和行事的方式就全變成了政治掛帥的考量。和諧的夢想說來不難,只要能更就事論事一點,更簡單一點,更講道理一點,更程序公正一點,更尊重大學規律一點。如果這些話多餘、不對、越俎代庖、甚至對你們的工作有曲解,我誠摯請你們海涵。
這麼多年尤其是最近一直關心著我的許多師友們,對不起,這次我沒採納你們要我別辭職的意見。不少師友勸我忍一忍,放一放,寧願被開除也不辭職,是的,之前我也是這麼想的,但現在我不再這麼認為了,我何必為了賭一口氣而耗在這裡,讓雙方都那麼不快樂?我是孤獨的一個人,面對無影無蹤的力量,我怎能耗得起?我很疲憊,像一個無知懵懂地闖入政治叢林的孩子,看不懂這裡複雜而捉摸不定的遊戲規則。連日來,我都在猶豫彷徨,不止一次後悔自己的道路,時時否定自我,但思前想後,最終還是決定走出這一步。也許這是糟糕的選擇,但也是我深思熟慮的結果,是我選擇自由尊嚴的生活而註定要付出的代價。我只能認命。
我知道,體制無處不在,我無處可逃。所以,請相信,我的辭職,不是在逃避退縮,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嚴、底線和原則。失去這些,我的生命就沒有依託,我就是行屍走肉,我不再是我。我的辭職與任何個人恩怨無關,與西北政法這所大學無關。請大家理解今日大學面臨的各種無力抵擋的壓力。我真的沒有情緒,沒有抱怨,我唯一要正視的,是自己的內心,我的內心是我唯一值得抗爭的對手。說到底,我是在跟自己較勁、跟自己過不去,就像少年派與他心目中的那隻老虎的搏鬥。
辭職後的日子很艱難,在體制內那麼多年,我深深懷疑自己能否還有獨自謀生的能力。而今臨近不惑,卻要像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尋找新的去處。實在對不起,芳寧,讓你無端承受了那麼多的委屈重負。實在對不起,園園,我不是個稱職的父親……。
文章來源:諶洪果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