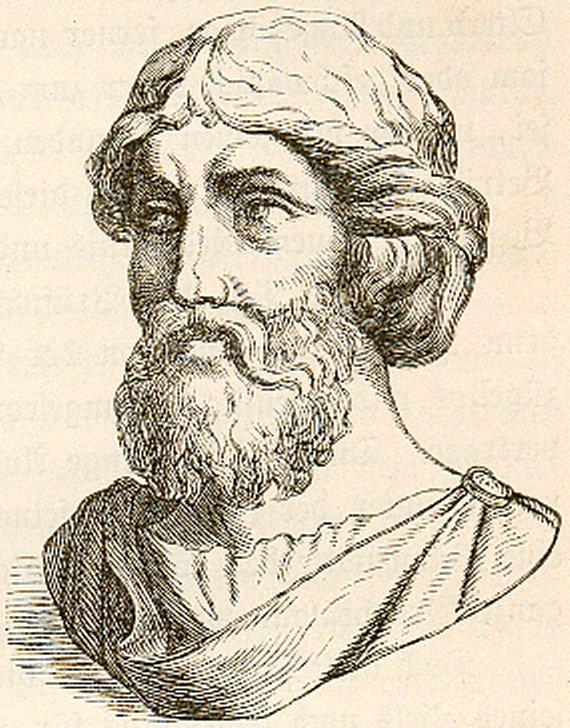【新唐人2014年3月2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一九五八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捲神州。一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一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一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一 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衝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一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儘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一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衝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一個難題相關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志服從共同的意志。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飢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一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孔子(網路圖片)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克制個人的私慾,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一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 (註一)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 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姦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註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裡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裡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你。」他認為,如果你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你就是自私的。(註三)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一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一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儘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一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柏拉圖(網路圖片)
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話和欺騙。」(註四)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一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佔優勢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採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註五)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一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一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你的鄰人」,不要「愛你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一樣如此有力的思想。」(註六)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劃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臟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註七)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的至上性這一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這條規則的唯一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註八)
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蕩過程中,逐漸轉變成一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慾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註九)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交給一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一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製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製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製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迭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註解:
[註一]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二十八頁下。
[註二] 宋元人註《四書五經》中冊,北京,中國書店,精裝影印本,一九八五年,第一二一頁。
[註三] 柏拉圖:《法律篇》,轉引自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九年,第一卷,第二百頁。
[註四] 柏拉圖:《理想篇》,第五卷,收自《影響世界的著名文獻》政治•社會卷,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二三頁。
[註五] 《飲冰室文集》之十二,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影印本,第八十六頁。
[註六] 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卷,第二零二頁。
[註七]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十一頁。
[註八] 同上,第一九五-一九六頁。
[註九]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五六頁。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
(接上期)
第二十七章 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一九五八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的口號鋪天蓋地,共產主義的狂潮席捲神州。一時,中國的多數人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振奮。正是在這美好理想的旗幟下,鑄成了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但是,這共產主義的狂潮不是空穴來風,不是少數人一時的瘋狂。它源遠流長,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極端化。為了探索這一理想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從它的源流說起。
一 對千古難題的探索
人是萬物之靈,又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級動物,他自私、貪婪、殘忍、淫蕩,而且無休無盡,在這些惡劣的方面遠遠超過其它高級動物。但人有同情心,有關愛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這是其它高等動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說人類「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說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獸」)。人是群居的,有社會性。作為「魔鬼」的人經常和其社會性相衝突,而作為「天使」的人使他們和諧相處。為了維護其社會性,使其不至於相互殘殺而自滅,人類的精英們一直想方設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現了種種宗教,種種學說。然而,在這種種宗教、種種學說之間的相互鬥爭中,人類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盡致,那些執行抑制人類魔鬼性的精英們,自己常常變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三年間,這種執行者的魔鬼性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類是智能高度發達的動物,正是智能的創造性才使人類社會從茹毛飲血發展為現代文明。儘管人類的創造是在社會中相互啟發、相互激勵和相互合作中發展的,但作為創造性的本源還是每一個人的腦力和體力。但是,人的創造性衝動常常與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類的魔鬼性的過程中,同時把個人的創造性抑制了,人類社會就會出現停頓的危機。計劃經濟制度和與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證明了這一點。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發揮其創造性,成了千古難題。
人是社會動物,如果沒有社會,單個的人是無法生存的。和上一個難題相關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把成千上萬既具有創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組織起來和諧相處?即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組織社會生活需要權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問題上眾多的意志服從共同的意志。然而,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為「依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馬克思語)。控制眾人的權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過於強大,就會變成力量強大的魔鬼。毛澤東組織社會的方式就是運用秦始皇遺留下來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權威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惡魔,大飢荒年代表現得最為突出。怎樣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這也是人們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難題。
人類社會對上述千古難題經歷了漫長的探索。在長達數千年時間內,人類依靠超乎眾人之上的最高權威力量來壓制人性惡劣的一面。這個最高權威有的在人類之上,如上帝以及種種神;有的在人類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結合。但控制最高權威、防止他不變為魔鬼的難題直到現代才在部分國家中得到解決。

孔子(網路圖片)
與服從權威相適應的理念是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人主義。崇尚集體、壓抑個體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圖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淵源。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求人們克制個人的私慾,把自己的行為限制在「禮」的規範之中。漢字中有一個「公」字,這個字是由「八」和「厶」組成的。「厶」即古「私」字,《說文解字》說:「公,平分也,從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為公。」 (註一)中國的「公」是和個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國很早就有「天下為公」的說法,其本來意義是「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 儒家經典之一的《禮記.禮運第九》從「天下為公」出發,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姦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註二)
「天下為公」,「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
人類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交通極不發達的遠古,相隔萬裡的異域也會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遠隔萬裡的柏拉圖認為:「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但整體並不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體而被創造,而整體的被創造並非為了你。」他認為,如果你不能為了整體而犧牲自己的利益,那麼你就是自私的。(註三)柏拉圖承認的首要準則是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處於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圖主張「共有財產」。在同一書中,他寫道:
妻子們、孩子們及其所有的奴隸們都有他們的一份共有財產。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要儘可能地根除各種形式的私人或個人行為。只要這點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為私人或個人的,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家的共有財產。就像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視、聽和行動--好似它們不是屬於個人而是屬於社會一樣。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讓他們能最大限度地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讓他們甚至在相同的時間內,對相同的事情感到歡喜或悲傷。所有這些法律因把國家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而更加完善。

柏拉圖(網路圖片)
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柏拉圖主張控制輿論,主張對文藝作品的檢查制度。他甚至認為:「治理者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時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話和欺騙。」(註四)
在中國,幾千年來,是王權支配一切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王權是至上的,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統治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個人都是國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權思想就是專制思想。這種專制思想,由秦始皇構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實體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實現了「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所謂「格式化」,就是消滅了個性。
人類社會發展到近代,距今幾百年前,對上述千古難題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由於個人主義的興起,工商文明的發展,從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梁啟超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引述了頡德(即英國哲學家基德,著有《社會進化論》)的話:「今之德國,有最佔優勢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即馬克思最早漢語譯名)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採的早期漢語譯名)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劣者所鉗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註五)
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兩種理論,使得人類對千古難題的探索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路線:
第一條線:集體主義-行政整合-公有制-計劃經濟-專制政治-封閉社會;
第二條線:個人主義-契約整合-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
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兩條平行線。這兩條平行線不能交叉,卻相互感應,在感應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對方積極因素。
在這兩條平行線之間,因專製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這兩條平等線的極端把對方當成勢不兩立的異端加以攻擊,兩個極端還不停地爭奪中間地帶。數百年來,這兩條線是不斷地磨擦、碰撞、互補、融合。但從總的趨勢來看,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個性不斷得到解放,自由主義不斷得到張揚。
個人主義是與集體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和利己主義、自私自利不是一個概念,利己主義是和利他主義相對應的。個人主義可以和利他主義相結合,用利他主義來抑制人類的魔鬼性。而利他主義也是出於人類的同情心和關愛心。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相結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聖經》上說,「愛你的鄰人」,不要「愛你的部落」),也是產生於西方文明並促進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學說的核心。波普爾認為,「在人類道德的發展歷程中,還沒有其它跟它一樣如此有力的思想。」(註六)波普爾批評柏拉圖「簡單地把所有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同起來,把所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劃上等號。」這就為集體主義穿上了無私的外衣,為個人主義披上了自私的臟外套。
個人主義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了基本原則,在文藝復興時期得到了發展,此後成長和發展為西方文明。也就是說,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社會政治生活的基礎。「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把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縱然這個範圍可能被限制得很狹隘,也就是相信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天賦與愛好。」(註七)無緣無故地壓制別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錯誤的。基督教徒會說,其錯誤就在於違背了上帝對人的設計。
個人主義的美德是:尊重和寬容別人和他人的意見;獨立精神;敢冒風險;有首創精神;自力更生;堅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隨波逐流;為維護自己的意見不受上級左右(剛直不阿);對弱者的關懷;尊重別人的隱私,對別人的善意懷有信任;不干涉別人的事務;寬容異端;對權力和權威的適度懷疑……這些美德減少了社會交往中的磨擦。
個人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只能在個人能負責任的範圍內才是真正的道德。在個人不能負責的範圍,個人沒有權力作決定,談不上惡和善,沒有機會獲得道德評價。任何人沒有權力以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博取無私的美名。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負責,不是用強力威逼出來的善行,自己決定在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他人做出犧牲,自己對這個決定的後果負完全責任,這才是真正的道德。
「個人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都必須完全地、永久地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的至上性這一觀念水火不容。自由社會絕不能從屬於某個單一目的,這條規則的唯一例外就是戰爭和它暫時性的災難。」(註八)
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由於商業的發展,歐洲那種有嚴格組織的壓抑個性的等級制度,在劇烈的社會震蕩過程中,逐漸轉變成一種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下,個人從束縛他的種種習慣和成規中解放出來,個人能夠創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商業規範逐漸代替了等級規範,自由競爭逐漸代替了行政壟斷,契約整合逐漸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運用人類天才的阻礙,人類很快就能滿足不斷擴大的慾望。個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結果是科學技術的大進步,生產力的大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如是說。(註九)
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這種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保護個人的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是國家的目的。政府的權力不能無限擴張,必須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這種制度不承認有「內聖外王」的超人,卻承認任何一個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兩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會的全權交給任何一個人,也不能交給一個不受外力制衡的獨立的組織。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些都是為了防止組織社會生活的權威變成壓迫人類的惡魔。
如上所述,人類是群居的,是有社會性的。除了協調人性以外,還有一個如何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在組織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種種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極而言之分為兩類: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專制獨裁製度。在二者之間,因民主和專制的程度不同,有著種種不同的情況。專制獨裁製度通常是以代表大眾利益的面目出現的。專制獨裁製度的統治者總是宣稱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從人的生理本源上看,專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人的動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會性動物的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的領袖取得權力靠的是強力征服,維護權力靠的是強力鎮壓。其征服和鎮壓是極其殘酷、極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蟻群也是如此。隨著人類的進化,人性的成份逐漸增多,動物性成份逐漸減少。政權更迭方式和執政手段逐漸人性化。專制制度逐漸被民主制度取代。
註解:
[註一]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二十八頁下。
[註二] 宋元人註《四書五經》中冊,北京,中國書店,精裝影印本,一九八五年,第一二一頁。
[註三] 柏拉圖:《法律篇》,轉引自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九年,第一卷,第二百頁。
[註四] 柏拉圖:《理想篇》,第五卷,收自《影響世界的著名文獻》政治•社會卷,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二三頁。
[註五] 《飲冰室文集》之十二,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影印本,第八十六頁。
[註六] 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卷,第二零二頁。
[註七]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十一頁。
[註八] 同上,第一九五-一九六頁。
[註九]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二五六頁。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