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7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二 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二月二十六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註十七)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註十八)
西樓會議以及二月二十六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西樓會議會址及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調整經濟的報告上的批示。(書中圖片)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 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慨,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註十九)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飢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註二十)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經減少了一千萬,一九六二年再減少一千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註二十一)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松下來,以為雷霆已過。(註二十二)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裡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裡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彙報的那些事。(註二十三)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一九六二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 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鐧
對於一九五八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一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一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註二十四)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著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一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一九五八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飢餓,到一九六一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一九六二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安徽達百分之八十,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百分之七十。(註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四月十一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彙報時說:「單莊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麼都要實事求是。」(註二十六)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彙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佔一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註二十七)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註二十八)陳雲七月向毛彙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飢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一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一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一月二十七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一段話。這段話大約一千一百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註二十九)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一個長達八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其它方面也一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鬆動和寬鬆。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鬆動中,出現了一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一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註三十)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一九七九年,陸定一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註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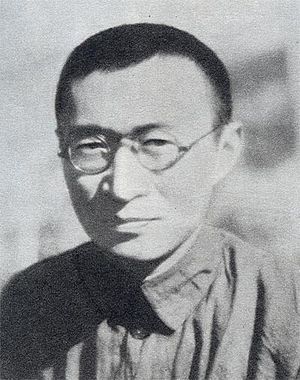
王稼祥 (網路圖片)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一)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二)要儘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三)我們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四)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五)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註三十二)
一九六二年七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彙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註三十三)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注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後算賬」的意味。一九六二年三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頭,醞釀著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一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一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一九五八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一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四天(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但預備會開了二十九天(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七月二十五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八月六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註三十四)。他又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八月五日)「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八月六日)「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八月九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八月十一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八月十五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八月二十日)(註三十五)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一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八月五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八月六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八月九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八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 他沒有聯繫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註三十六)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六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八月二十二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八月五日,毛澤東說:「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九月一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註三十七)九月三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註三十八)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註三十九)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徵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註四十)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斗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一九五四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係的饒漱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註四十一)《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一九六二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九月八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七十二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註四十二)。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勛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註四十三)九月二十七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註四十四)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註四十五)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它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裡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
會後,各省都把抓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用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和分析各種社會現象,發現了很多「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及時將這些「新動向」上報中央,其實,這些「新動向」不是神經過敏,就是子虛烏有的。但是,信息的上下互動,使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三類隊」的「民主革命補課」發展到全國的「四清運動」。(註四十六)
註解:
[註十七] 陳雲:《目前的財政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陳雲文選,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頁。
[註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五一-一零五二頁。
[註十九] 劉少奇:《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載《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四四四-四四五頁。
[註二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三頁。
[註二十一] 鄧小平:《克服當前困難的辦法》(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載《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三一九頁。
[註二十二]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九十頁。
[註二十三] 周伯萍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二十四] 陳雲:《目前的財政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陳雲文選,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頁。
[註二十五]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七四頁。
[註二十六] 鄧子恢:《關於龍勝縣的包產到戶問題》,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載《鄧子恢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四四頁。
[註二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八四-一零八五頁。
[註二十八] 鄧小平:《怎樣恢復農業生產》(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三二三頁。
[註二十九]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北京,內部資料,一九六七年,第二零六-二零八頁。
[註三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九九八頁。
[註三十一] 陸定一:《懷念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光明日報》。
[註三十二] 朱良:《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九六二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義罪名的真相》,載《炎黃春秋》二零零六年第八期。
[註三十三] 閻明復:《從我親歷的幾件事看康生》,載《炎黃春秋》二零零五年第五期。
[註三十四]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一-一九六八)第二十九-三十頁。
[註三十五]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四-一零七七頁。
[註三十六] 同上,第一零七四-一零八八頁。
[註三十七] 同上,第一零九二-一零九三頁。
[註三十八] 同上,第一零九三頁。
[註三十九]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頁。
[註四十] 高崗祕書趙家梁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四十一] 同上。
[註四十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九六頁。
[註四十三] 同上,第一零九六頁。
[註四十四]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頁。
[註四十五] 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文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九六-一九七頁。
[註四十六]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載《領導者》二零零六年十月號。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
(接上期)
二 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進一步觸怒毛澤東
不少文獻說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一散會,毛澤東就去武漢了。劉少奇又召開了「西樓會議」,研究克服困難的辦法。
「西樓會議」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開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
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陳雲二月二十六日的講話中把嚴峻形勢歸納為五個方面:其一,農業近幾年有很大幅度的減產;其二,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不相適應;其三,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其四,城市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出現了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註十七)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註十八)
西樓會議以及二月二十六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和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

西樓會議會址及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調整經濟的報告上的批示。(書中圖片)
鑒於前三年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幹部又怕把困難估計過重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 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共產黨人的革命氣慨,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註十九)毛澤東曾要求他們不要把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劉卻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計困難。是不是劉有意和毛作對呢?不是。
在中國當時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財政統收統支,重要物資統收統配。「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為了從中央財政治和中央統配物資中多分一塊蛋糕,各地經濟業務部門總是向中央業務部門叫困難。就是省委第一書記,在毛澤東面前說形勢大好,但向中央業務部門要東西,也是寸步不讓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面前說糧食夠吃,但為了減少四川省的徵購任務,曾和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多次討價還價(見本書「天府飢魂」一章)。所以,主管實際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總覺得困難很大。毛澤東不管這些具體事,聽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見,感受到困難的壓力比劉少奇、周恩來要小一些。「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徵詢過一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註二十)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點放在恢復上,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其二,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經減少了一千萬,一九六二年再減少一千萬。其三,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降低生產建設的高指標;其四,恢復農業生產,搞好市場供應;其五,抑制通貨膨脹。更重要的是,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黨員甄別平反,「五月會議」上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註二十一)鄧子恢主張適當地擴大自留地。對各地的包產到戶,實際也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春天,採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廬山會議後全都否定了,這一次「退夠」的措施,毛澤東會同意嗎?對一貫主張「冒進是馬列主義」、「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要積極平衡,不要消極平衡」的毛澤東來說,他能容忍劉少奇等人的調整嗎?劉少奇心裡沒底,還是要請示毛主席。
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澤東從炎熱的南方回到涼爽的北京。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澤東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陳雲感覺毛不反對這些意見,只是在考慮。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游泳。劉少奇趕到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劉少奇平靜下來向毛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繼續搞下去。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松下來,以為雷霆已過。(註二十二)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曾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書作者談了一件與此有關的事。西樓會義後不久,陳雲到了上海。讓陳國棟、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務,陳雲說:你們到一些省去看看,農村真實情況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裡幹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發表意見,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糧食產區,看到的情況是,集體的大田幾乎荒蕪,而自留地裡糧食作物長勢非常好。農民是靠自留地吃飯的。他們到上海向陳雲談了所看到的情形。陳雲說:「看來是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陳雲告誡他們幾人回北京以後什麼也不要說。還是陳雲親自向毛談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七月陳雲向毛彙報的那些事。(註二十三)
並沒有像劉少奇預計的那樣雷霆已過。一旦度過了難關,毛澤東就重新發難。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清算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這筆賬。
毛澤東之所以對一九六二年的調整耿耿於懷,是因為他把與他不同的看法視為階級鬥爭,視為要推翻他。這種看法終於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來了。
三 八屆十中全會祭起「階級鬥爭」的殺手鐧
對於一九五八年以來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和經濟形勢的估計,在中國共產黨的上層有著不同的看法。毛澤東總是低估大躍進所造成的困難,對當時的形勢的估計也較為樂觀。持毛澤東這種看法的有柯慶施、林彪等後來被稱為左派的幹部。而以「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為代表的一批幹部則對困難的估計比較嚴重,對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當然,這種不同的估計,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發點也會不同。
在解決困難第一線工作的陳雲對這種不同的估計深有感受。他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上說:「對於困難的程度,克服困難的快慢,在高級幹部中看法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恢復的速度是快還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計。」「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註二十四)
如前所述,這種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有著工作崗位不同的原因。當然也和各種不同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不管怎樣,對形勢不同的估計,是一種正常現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過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決定政策。在專制制度下,處於最高權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見不好貫徹。而對一九五八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開放了自由市場,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遠。如包產到戶大面積推行。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把這些壓回去了。由於飢餓,到一九六一年,又大面積推行起包產到戶。一九六二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安徽達百分之八十,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百分之七十。(註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鄧子恢就曾多次主張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主張包產到戶的講話。如四月十一日,他在廣西桂林聽取地區負責人彙報時說:「單莊獨戶,離村莊遠的就包產到戶,或者讓他們單幹吧。這樣有好處,不要有顧慮,怕說單幹,怕說右傾,什麼都要實事求是。」(註二十六)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局關於安徽省「責任田」的彙報。中共中央華東局持嚴厲批評的態度。但出席這個會議的人,支持和批評的各佔一半。鄧子恢認為安徽省的「責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錯誤。鄧小平發言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試試看。」(註二十七)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七屆三中全會代表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也說過「劉伯承同志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註二十八)陳雲七月向毛彙報時,也講過重新讓農民分田的事。如本書前面所說的,正是這些「倒退」才是走出飢荒、減少死亡最為有效的措施。但這和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當時毛澤東的憂慮中,還有一股「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一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一月二十七日的口頭講話中,特別講到彭德懷問題。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時,刪去了這一段話。這段話大約一千一百字左右,其主要內容是:廬山會議上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不是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封信。信中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廬山會議其所以要開展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他們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的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等等。(註二十九)
彭德懷沒有參加七千人大會。會後他得知劉少奇的這些誣陷之詞以後,倍感委曲,不得不奮起為自己申辯。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寫作,他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送上了一個長達八萬字的申訴材料(後被稱之為「八萬言書」)。這個「八萬言書」不僅否定了劉少奇上述誣陷,還把廬山會議以及其後對他批判和結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懷翻案,這是毛澤東很不愉快的事。
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其它方面也一改過去緊張的狀況,開始出現鬆動和寬鬆。如對冤假錯案大規模的甄別平反,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讓步,對民主黨派有所尊重,等。在這些鬆動中,出現了一些「過頭」情況,使毛不快。如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等講了一些尊重知識分子的話,陳毅還提出了「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註三十)周、陳的「脫帽加冕」引起了上層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強烈反對「脫帽加冕」的說法。直到一九七九年,陸定一才在這個問題上認錯,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是「左的,所以是錯誤的。」(註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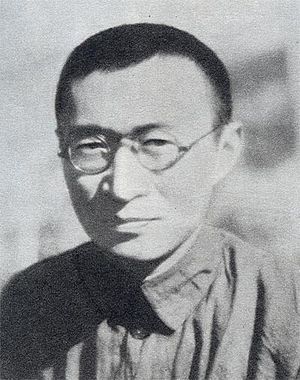
王稼祥 (網路圖片)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以《黨內通訊》的形式送上去的。這封信有五點內容:一)對外政策有必要採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二)要儘可能避免中蘇關係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三)我們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裡參戰;四)中國和印度的關係要打開目前的僵局,要高舉中印友好、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旗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五)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註三十二)
一九六二年七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到毛澤東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一的彙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註三十三)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一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一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卻密切注視北京。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一股「秋後算賬」的意味。一九六二年三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劉的這番話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頭,醞釀著反擊復辟。
從統購統銷到農業集體化;從城市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鬥爭;這一系政策嚴重侵犯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因此,在實施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力量。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高壓下,這股反對力量只是一股潛流。身居權力最高層的毛澤東,是會感受到這股潛流的壓力的。一九五八年以後,幾千萬人餓死,這是一樁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紅旗」造成如此嚴重的惡果,使黨內對「三面紅旗」持懷疑或反對意見的力量成了對毛澤東的離心力,而且離心力有日益強大之勢。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一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一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挑起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四天(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但預備會開了二十九天(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七月二十五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八月六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註三十四)。他又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黑暗風」是指「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以及前後與其相似的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在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多次講話說:「有些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八月五日)「現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八月六日)「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八月九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八月十一日)「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八月十五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八月二十日)(註三十五)從毛澤東的這些言論來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以來的教訓。一九五八年冬以後他雖然也做了一些糾正錯誤的工作,但對這幾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於懷。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八月五日毛澤東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八月六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八月九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志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志,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八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一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繫的。」「 他沒有聯繫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註三十六)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一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六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八月二十二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八月五日,毛澤東說:「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九月一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註三十七)九月三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註三十八)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註三十九)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徵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註四十)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斗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一九五四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係的饒漱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註四十一)《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一九六二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九月八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七十二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註四十二)。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勛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註四十三)九月二十七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註四十四)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註四十五)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它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裡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
會後,各省都把抓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用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和分析各種社會現象,發現了很多「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及時將這些「新動向」上報中央,其實,這些「新動向」不是神經過敏,就是子虛烏有的。但是,信息的上下互動,使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三類隊」的「民主革命補課」發展到全國的「四清運動」。(註四十六)
註解:
[註十七] 陳雲:《目前的財政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陳雲文選,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頁。
[註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五一-一零五二頁。
[註十九] 劉少奇:《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載《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四四四-四四五頁。
[註二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三頁。
[註二十一] 鄧小平:《克服當前困難的辦法》(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載《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三一九頁。
[註二十二]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九十頁。
[註二十三] 周伯萍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二十四] 陳雲:《目前的財政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陳雲文選,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頁。
[註二十五]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七四頁。
[註二十六] 鄧子恢:《關於龍勝縣的包產到戶問題》,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載《鄧子恢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四四頁。
[註二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八四-一零八五頁。
[註二十八] 鄧小平:《怎樣恢復農業生產》(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三二三頁。
[註二十九]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北京,內部資料,一九六七年,第二零六-二零八頁。
[註三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九九八頁。
[註三十一] 陸定一:《懷念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光明日報》。
[註三十二] 朱良:《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九六二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義罪名的真相》,載《炎黃春秋》二零零六年第八期。
[註三十三] 閻明復:《從我親歷的幾件事看康生》,載《炎黃春秋》二零零五年第五期。
[註三十四] 《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一-一九六八)第二十九-三十頁。
[註三十五]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四-一零七七頁。
[註三十六] 同上,第一零七四-一零八八頁。
[註三十七] 同上,第一零九二-一零九三頁。
[註三十八] 同上,第一零九三頁。
[註三十九]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頁。
[註四十] 高崗祕書趙家梁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註四十一] 同上。
[註四十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九六頁。
[註四十三] 同上,第一零九六頁。
[註四十四]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頁。
[註四十五] 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文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九六-一九七頁。
[註四十六]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載《領導者》二零零六年十月號。
(待續)
作者授權發表,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