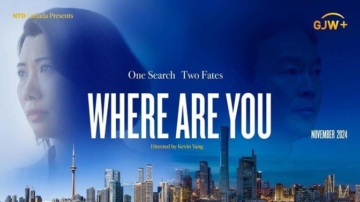【新唐人2016年11月30日訊】 最後一班公共汽車還沒開過,候車亭裡,還有兩個和我一樣晚歸的人,都是女人。
一個穿著某酒店黑色工作服的大姐,應該有五十歲左右了吧,歲月的痕跡比較明顯,額頭上,眼角邊,都被光陰的銼刀刻上了細細的皺紋。她似乎很有些倦怠,倚著站牌,無精打采的,一個接一個地打哈欠。

寧靜的夜晚(manseok/Pixabay)
另一個年輕些,妝化的很濃,時髦的梨花頭染成酒紅色,一直在不停的打電話。她說的是方言,我很費勁的聽,也沒聽出個所以然來。只是隱隱感覺到,她是要去見什麼人。
車子還沒有來,天空中,氣流裡,馬路上,全都冷冷清清,再加上寒風,陡添了幾分淒涼。
前面慢慢地滑來了一輛賣麻辣燙的餐車,上面整齊有序地擺放著用竹籤穿好的各類葷素食材,旁邊支著一口大鍋,紅紅的湯汁正熱氣騰騰的翻滾著。這是一個中年男子,長著一張苦大仇深的狹長臉。

夜歸(LouAnna/Pixabay)
「這破車又晚點了,到現在還沒來。」黑衣大姐用四川話對狹長臉男人說。
「N路車最不准時了。」男子說的也是四川話。他們是熟人。
又等了幾分鐘,N路車終於來了,黑衣大姐搶先一步跨上了車,我尾隨其後,年輕女子跟在我後面,嘰嘰咕咕的,還在跟人通電話。車上沒幾個人,位置很空,我旁邊坐著一個頭髮蓬亂的男子,穿著咖啡色的破舊夾克,腳上的旅遊鞋沾滿泥痕,早已看不出原先的顏色。腳邊還有一個蛇皮袋,裡面放著瓦刀鎯頭鐵錘等工具,看樣子應該是裝修工。也不知他今天是否有所獲,可以讓他滿足的隨著車輪的滾動奔向屬於他的那一盞燈火。

炊煙傍晚的鄉村(AdinaVoicu/Pixabay)
我前邊的黑衣大姐一坐下就打起了盹,不一會兒,微微的鼾聲就飄進了我的耳膜。看得出,她太累了。
車子七拐八拐,拐進了我家附近的那條熱鬧的小商品街。現在,這條街上的所有店舖都已打烊,只有昏暗的路燈和天上的缺月,一個暗黃,一個清冷,散發著朦朧的光暈。

風雪的夜晚(qimono/Pixabay)
到站後,車還沒停穩,我就急不可耐的跳了下去。我的平底波鞋沒有聲音,沒有聲音的我,走在寂靜的巷子裡,影子斜斜的印在牆上,如同一個黑色的幽靈。
——本文經《紀元心語》授權發布
責任編輯:李丹
一個穿著某酒店黑色工作服的大姐,應該有五十歲左右了吧,歲月的痕跡比較明顯,額頭上,眼角邊,都被光陰的銼刀刻上了細細的皺紋。她似乎很有些倦怠,倚著站牌,無精打采的,一個接一個地打哈欠。

寧靜的夜晚(manseok/Pixabay)
另一個年輕些,妝化的很濃,時髦的梨花頭染成酒紅色,一直在不停的打電話。她說的是方言,我很費勁的聽,也沒聽出個所以然來。只是隱隱感覺到,她是要去見什麼人。
車子還沒有來,天空中,氣流裡,馬路上,全都冷冷清清,再加上寒風,陡添了幾分淒涼。
前面慢慢地滑來了一輛賣麻辣燙的餐車,上面整齊有序地擺放著用竹籤穿好的各類葷素食材,旁邊支著一口大鍋,紅紅的湯汁正熱氣騰騰的翻滾著。這是一個中年男子,長著一張苦大仇深的狹長臉。

夜歸(LouAnna/Pixabay)
「這破車又晚點了,到現在還沒來。」黑衣大姐用四川話對狹長臉男人說。
「N路車最不准時了。」男子說的也是四川話。他們是熟人。
又等了幾分鐘,N路車終於來了,黑衣大姐搶先一步跨上了車,我尾隨其後,年輕女子跟在我後面,嘰嘰咕咕的,還在跟人通電話。車上沒幾個人,位置很空,我旁邊坐著一個頭髮蓬亂的男子,穿著咖啡色的破舊夾克,腳上的旅遊鞋沾滿泥痕,早已看不出原先的顏色。腳邊還有一個蛇皮袋,裡面放著瓦刀鎯頭鐵錘等工具,看樣子應該是裝修工。也不知他今天是否有所獲,可以讓他滿足的隨著車輪的滾動奔向屬於他的那一盞燈火。

炊煙傍晚的鄉村(AdinaVoicu/Pixabay)
我前邊的黑衣大姐一坐下就打起了盹,不一會兒,微微的鼾聲就飄進了我的耳膜。看得出,她太累了。
車子七拐八拐,拐進了我家附近的那條熱鬧的小商品街。現在,這條街上的所有店舖都已打烊,只有昏暗的路燈和天上的缺月,一個暗黃,一個清冷,散發著朦朧的光暈。

風雪的夜晚(qimono/Pixabay)
到站後,車還沒停穩,我就急不可耐的跳了下去。我的平底波鞋沒有聲音,沒有聲音的我,走在寂靜的巷子裡,影子斜斜的印在牆上,如同一個黑色的幽靈。
——本文經《紀元心語》授權發布
責任編輯: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