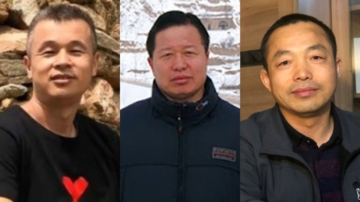中國是人類權利的洪荒地帶,整個國家的歷史,乃至它的哲學領域、社會倫理思想領域,個體權利從未成為一種被注意的對象。它實際上沒被當作一種具體的存在而有意識地對待過。而有意識地壓制、消滅個體人的權利、消滅部分人已生出的權利意識則是過去68年裡制度永不倦怠的意志。
先是以一切恐怖的手段壓制,消滅客觀的權利行為,後是徹底消滅與權利有關的思想。權利作為一種行為現象幾被根絕,權利思想或叫意識實際亦被消滅殆盡。面對赤裸裸的,有時是極其野蠻的濫權行為,人們習慣於逆來順受,長此以往,完全混淆、顛倒了正當與非正當、合法與非法的本來。導致了濫權的更加肆無忌憚。
權力如何行動,其核心的積極的監督和規制對象恰恰是公民自己的保衛自身權利的意識及積極的行動。行政、司法的監督則是消極的,間接的和被動的。這兩種監督或叫救濟行為依然是要以公民的積極告申為前提。一般情況下,公民若不積極告申,後者監督或救濟功能則更是形同無物。
所有人類的經驗普遍地表明,權力失去監督便會走向毀滅,但在它終於毀滅前的邪惡及禍害的恐怖是罄竹難書的。一味地詛咒黑暗而忘了自己作為個體對社會、說白了就是對自己應當擔負的責任,這實在的是個不可饒恕的罪錯。我個人有過多次這方面的經歷證明了我判斷的意義——抗爭、保衛自己權利的意義。
我在列車上從未接受過身分證檢查。每次坐列車,百分之百在臥鋪車廂裡會要求出示身分證供警察逐一登記。我百分之百絕不配合,其實身分證就在我身上。我每次都直接說自己不同意出示身分證件,無疑大都會出現進一步的糾纏情節,但結果他們必敗無疑。道理很簡單,乘坐火車只是我與承運方之間建立的合同關係行為,與任何第三方不發生關係。除非我實施了必須與第三方發生關係的法律關係行為。
我從未見到過類似情形下其他人拒絕的行為,相反,有時這種過程中警察會堅韌不棄,不特如此,還會呼來一大群同類旁助,場面宏大則氣氛緊張。對我的堅決不從,不少其他乘客會加入勸說大陣,我更具堅韌精神——絕不妥協,迄今他們從未得逞過。有時會有些乘客陰陽怪氣地問我這樣做有意義嗎?當然有,我只要不違法,我作我自己的主,我就是我的絕對統治者,任何人無權侵蝕屬於我自己的權利。
一次在新疆南疆的一個縣城,我乘坐的大巴被一群全副武裝的共匪特警攔下,車剛停穩,匪警蹬車大喊全部下車接受檢查,那種跋扈使人感到一種無理的羞辱。
我是全車唯一拒絕下車者,這顯然是不得了的大事——於蠻橫慣了的他們。一位頭目與另一位特警上來問我怎麼回事?想幹什麼?我未回答他們的問題,我一字一頓告訴了他們從停車至實施檢查過程的程序違法之處,指出迄止現在我依然不清楚你們是警是匪?指出平端槍口對人是違反行政規則的。結果他們不屑地互視了一下後,那頭目突然說,請我下車幫他們訓練一下他們的特警,教練大家如何端槍。我盯著他的眼說:「如果你是匪徒,我就開始奪槍,如果你是公職人員,我卻沒有訓練你們的義務,但卻有批評監督你們的權利。」雙方沉默對視足有一分鐘,結果那頭目輕揚了下巴後,幾人默默地下了車。
我是那天50多人中唯一沒有接受搜身檢查的人。當然這種結局在共匪治下的中國是極具偶然性的。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張長江律師遭遇到的情形恐怕換了誰亦例外不了。
張律師儒雅風度不凡,2002年的一個晚上12點時駕著豪車回家。北京還實在的是個典型的北方城市,一到晚上12點鐘後街上道上幾無行人,除了疾馳的車輛。在一個立交橋底下他的車被一群大蓋帽攔下,說要檢查身分證,出於律師的習慣意識,張律師要求對方出示公職人員身分證件,不料這冒犯了這群匪徒的變態權威心理。權威立即兌換成了流氓行徑,他們掏出了槍耍開了流氓,用槍指著這位文雅氣質滿溢的律師,說這東西可以證明身分了吧?
第二天上午辦公室一見面他講述這一過程時,說彼時他感到震驚不已,說畢竟這裡是首都北京,人際身分水深莫測,他們就敢公然在大街上這麼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述完一臉困惑地問我:「高律師你說他們怎麼會這樣?」
於我而言,我從不慮及過多,依然堅持我自己應當堅持的,這種堅持多不勝數。有一次我開車在東三環三元橋下被攔下,警察過來就一句「好傢伙,不知道單雙號限行的規定嗎?今天限制雙號車上路,你怎麼開著雙號車滿世界跑?」「沒有人告知我」,我回答。「嚯,北京晚報天天公告,您幹嘛去了?」對方來了一句。「看報紙不是公民的強制義務,我從不看報紙。」我說。「您還給我說這個,北京市政府下達的命令,我們只是執行者,您接受處罰吧」,對方顯得很不耐煩。「我在合法行使我的財產所有權,凡涉及公民人身、財產等基本權利的規範只能由基本法律來調整,《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得很清楚,你不是在執行,而是在破壞法律秩序。」我沒有任何讓步的意思,他們最後亦不了了之。
我不厭其煩地述說這些經歷,實在是想使人們知道,只要你理直氣壯地堅持,不用害怕失敗,必須使濫權行為碰壁,至少使他們覺得不易隨心所欲。我在北京期間,除了停車被像鬼一樣偷著貼上罰單,當面的處罰他們從未成功過。
一次,我在新華門至天安門間紅綠前被攔下,一下車未告知我任何程序權利便劈頭一句:「駕駛證、行車證交來。」「沒有駕照」,我回答(我是遼寧省駕照,正適一年一度審照之際)。「你沒有駕照怎麼開車?」對方顯得很驚訝。「你親眼看到了我會開車的事實,這事實正是你想處罰我的基礎」,我說。「行車證拿來」,彼伸手說。「沒有行車證」,我又說。「沒有行車證怎麼證明這車是你的?」他更顯吃驚地問。「你親眼看到我是本車的控制者,且並無旁人對此控制提出異議」,我說。「什麼外國情理?走,到馬路對面接受處罰,扣車,人留滯說清問題。」彼說完便藉著綠燈昂首過了馬路,待過了馬路才發現我沒有跟在其身後便向我招手。我並不理他,等下一個綠燈亮起,彼跑了過來,我正拿著筆在紙上記錄他所有過程中違反法律程序的情節,總共有六個方面的程序硬傷。
我就這麼認真,我並不是想逃避接受處罰。你在其它過程中怎麼恣肆濫權我沒有力量管,但你處罰我即必須是合法處罰,否則處罰完就去起訴你。所有情況下,都是最後一臉不耐煩地揮手讓你「走走走,不處罰你還不行嗎?」放棄職責雖是他的事,我依然會提醒他們,不處罰更是違法的,與此同時,他們幾乎是推著讓你上車走人。
我在北京一家房管所辦理房產證的荒謬遭遇值得一提。我清醒地知道面對這種野蠻無人性的制度,個人一已之力的較真是沒有多少實質性價值的——除非大家都這麼做,但在具體的辦事環節上,我要的實質性的價值就是達到把事辦成的目的。依著他們的規定本當順理成章成就的事,卻每必得採取令人屈辱、有失尊嚴的非常手段才有可能達到目的,因為你面對的就是一群無賴。
我去房管所辦理房產手續,你具體的工作人員的職責就是為公民辦理房產文件,可他偏就不給你辦。我排在第四位,隊排了很長,更長的是等待時間。不高的櫃檯那邊,幾位公務大爺在那裡高蹺著腿目空一切地海侃著。每一位遞過去的材料都遭了一把被推開的命運:「明天來。」裡面那位公務大爺語氣乾脆、不容置疑。排在我前面的三位碰壁者都鐵青著臉旁立在不大的大廳裡。
我一直在心裡快速地盤算如何對付這「公僕」潑皮。終於臨到了我,躲是躲不開了,我一手托著櫃檯面猛地一躍跳進櫃檯裡面,還沒等他反應過來,我撲過去抓住他的胸依居高臨下把他壓制在椅子上。彼大驚失色,語無倫次,明顯地有些恐慌,不斷地也是本能地掙扎著,口裡重複著:「你幹嘛?你幹嘛?」我說,「我是來解放你的。你的領導都是一群冷血的畜生,把你安置在讓你如此痛苦的位置上」,我盯著彼說。「你罵我們領導,你罵我們領導」,彼像抓住了一絲救命索似的。我一把拉他起來,「走,一起去罵你的王八蛋領導去。」不料他突然猛地掙脫了我的手,一躍跳出櫃檯,發瘋似地從那些剛才被他拒絕但還沒離開的人手裡搶過了手續,嘴裡不停地嚷嚷:「我這就給大夥兒趕緊辦還不成嗎?」進了櫃檯後一邊辦理一邊還不停地重複著這句話。
雖然經歷了些波折,但那天我實現了辦事的目的。人們常說共產黨政權是流氓,這實際上是矮化了流氓的標準。第二週我又去那裡取辦理好的房產證,他一眼看見排在隊列中的我,熱情招手,嘴裡竟說:「您不用排隊,您怎麼能排隊?」「你連醒來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回了一句。
人是很難要求一律的。對別人的苦難、不如意無動於衷已是使人失望的事了,尚連保衛自己正當利益的衝動都不再有,你期待這個社會好起來,這無異於期望雄雞去下蛋。只有自己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整個社會重視個體權利的局面才會實現,每個個體均不當貪得份外利益,把期望冀於別人,至少當絕不含糊地保衛自己的正當利益。
社會安全的載體就是每一個具體的個體,每個個體便是社會這張大網上的一個具體的綰結,你的放棄便導致一個現實的漏洞,這是個並不複雜的道理。正是我們作為個體的無底線遷就、放棄,公共權力才會生成長著一個猙獰面目的冷酷怪物。而絕大多數逆來順受的情形下,極個別人的抗爭也就常作了犧牲的材料,於大環境的改變猶一箭入海之效。
相關鏈接: 附:高智晟《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案全文下載 (點擊這裡)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先是以一切恐怖的手段壓制,消滅客觀的權利行為,後是徹底消滅與權利有關的思想。權利作為一種行為現象幾被根絕,權利思想或叫意識實際亦被消滅殆盡。面對赤裸裸的,有時是極其野蠻的濫權行為,人們習慣於逆來順受,長此以往,完全混淆、顛倒了正當與非正當、合法與非法的本來。導致了濫權的更加肆無忌憚。
權力如何行動,其核心的積極的監督和規制對象恰恰是公民自己的保衛自身權利的意識及積極的行動。行政、司法的監督則是消極的,間接的和被動的。這兩種監督或叫救濟行為依然是要以公民的積極告申為前提。一般情況下,公民若不積極告申,後者監督或救濟功能則更是形同無物。
所有人類的經驗普遍地表明,權力失去監督便會走向毀滅,但在它終於毀滅前的邪惡及禍害的恐怖是罄竹難書的。一味地詛咒黑暗而忘了自己作為個體對社會、說白了就是對自己應當擔負的責任,這實在的是個不可饒恕的罪錯。我個人有過多次這方面的經歷證明了我判斷的意義——抗爭、保衛自己權利的意義。
我在列車上從未接受過身分證檢查。每次坐列車,百分之百在臥鋪車廂裡會要求出示身分證供警察逐一登記。我百分之百絕不配合,其實身分證就在我身上。我每次都直接說自己不同意出示身分證件,無疑大都會出現進一步的糾纏情節,但結果他們必敗無疑。道理很簡單,乘坐火車只是我與承運方之間建立的合同關係行為,與任何第三方不發生關係。除非我實施了必須與第三方發生關係的法律關係行為。
我從未見到過類似情形下其他人拒絕的行為,相反,有時這種過程中警察會堅韌不棄,不特如此,還會呼來一大群同類旁助,場面宏大則氣氛緊張。對我的堅決不從,不少其他乘客會加入勸說大陣,我更具堅韌精神——絕不妥協,迄今他們從未得逞過。有時會有些乘客陰陽怪氣地問我這樣做有意義嗎?當然有,我只要不違法,我作我自己的主,我就是我的絕對統治者,任何人無權侵蝕屬於我自己的權利。
一次在新疆南疆的一個縣城,我乘坐的大巴被一群全副武裝的共匪特警攔下,車剛停穩,匪警蹬車大喊全部下車接受檢查,那種跋扈使人感到一種無理的羞辱。
我是全車唯一拒絕下車者,這顯然是不得了的大事——於蠻橫慣了的他們。一位頭目與另一位特警上來問我怎麼回事?想幹什麼?我未回答他們的問題,我一字一頓告訴了他們從停車至實施檢查過程的程序違法之處,指出迄止現在我依然不清楚你們是警是匪?指出平端槍口對人是違反行政規則的。結果他們不屑地互視了一下後,那頭目突然說,請我下車幫他們訓練一下他們的特警,教練大家如何端槍。我盯著他的眼說:「如果你是匪徒,我就開始奪槍,如果你是公職人員,我卻沒有訓練你們的義務,但卻有批評監督你們的權利。」雙方沉默對視足有一分鐘,結果那頭目輕揚了下巴後,幾人默默地下了車。
我是那天50多人中唯一沒有接受搜身檢查的人。當然這種結局在共匪治下的中國是極具偶然性的。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張長江律師遭遇到的情形恐怕換了誰亦例外不了。
張律師儒雅風度不凡,2002年的一個晚上12點時駕著豪車回家。北京還實在的是個典型的北方城市,一到晚上12點鐘後街上道上幾無行人,除了疾馳的車輛。在一個立交橋底下他的車被一群大蓋帽攔下,說要檢查身分證,出於律師的習慣意識,張律師要求對方出示公職人員身分證件,不料這冒犯了這群匪徒的變態權威心理。權威立即兌換成了流氓行徑,他們掏出了槍耍開了流氓,用槍指著這位文雅氣質滿溢的律師,說這東西可以證明身分了吧?
第二天上午辦公室一見面他講述這一過程時,說彼時他感到震驚不已,說畢竟這裡是首都北京,人際身分水深莫測,他們就敢公然在大街上這麼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述完一臉困惑地問我:「高律師你說他們怎麼會這樣?」
於我而言,我從不慮及過多,依然堅持我自己應當堅持的,這種堅持多不勝數。有一次我開車在東三環三元橋下被攔下,警察過來就一句「好傢伙,不知道單雙號限行的規定嗎?今天限制雙號車上路,你怎麼開著雙號車滿世界跑?」「沒有人告知我」,我回答。「嚯,北京晚報天天公告,您幹嘛去了?」對方來了一句。「看報紙不是公民的強制義務,我從不看報紙。」我說。「您還給我說這個,北京市政府下達的命令,我們只是執行者,您接受處罰吧」,對方顯得很不耐煩。「我在合法行使我的財產所有權,凡涉及公民人身、財產等基本權利的規範只能由基本法律來調整,《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得很清楚,你不是在執行,而是在破壞法律秩序。」我沒有任何讓步的意思,他們最後亦不了了之。
我不厭其煩地述說這些經歷,實在是想使人們知道,只要你理直氣壯地堅持,不用害怕失敗,必須使濫權行為碰壁,至少使他們覺得不易隨心所欲。我在北京期間,除了停車被像鬼一樣偷著貼上罰單,當面的處罰他們從未成功過。
一次,我在新華門至天安門間紅綠前被攔下,一下車未告知我任何程序權利便劈頭一句:「駕駛證、行車證交來。」「沒有駕照」,我回答(我是遼寧省駕照,正適一年一度審照之際)。「你沒有駕照怎麼開車?」對方顯得很驚訝。「你親眼看到了我會開車的事實,這事實正是你想處罰我的基礎」,我說。「行車證拿來」,彼伸手說。「沒有行車證」,我又說。「沒有行車證怎麼證明這車是你的?」他更顯吃驚地問。「你親眼看到我是本車的控制者,且並無旁人對此控制提出異議」,我說。「什麼外國情理?走,到馬路對面接受處罰,扣車,人留滯說清問題。」彼說完便藉著綠燈昂首過了馬路,待過了馬路才發現我沒有跟在其身後便向我招手。我並不理他,等下一個綠燈亮起,彼跑了過來,我正拿著筆在紙上記錄他所有過程中違反法律程序的情節,總共有六個方面的程序硬傷。
我就這麼認真,我並不是想逃避接受處罰。你在其它過程中怎麼恣肆濫權我沒有力量管,但你處罰我即必須是合法處罰,否則處罰完就去起訴你。所有情況下,都是最後一臉不耐煩地揮手讓你「走走走,不處罰你還不行嗎?」放棄職責雖是他的事,我依然會提醒他們,不處罰更是違法的,與此同時,他們幾乎是推著讓你上車走人。
我在北京一家房管所辦理房產證的荒謬遭遇值得一提。我清醒地知道面對這種野蠻無人性的制度,個人一已之力的較真是沒有多少實質性價值的——除非大家都這麼做,但在具體的辦事環節上,我要的實質性的價值就是達到把事辦成的目的。依著他們的規定本當順理成章成就的事,卻每必得採取令人屈辱、有失尊嚴的非常手段才有可能達到目的,因為你面對的就是一群無賴。
我去房管所辦理房產手續,你具體的工作人員的職責就是為公民辦理房產文件,可他偏就不給你辦。我排在第四位,隊排了很長,更長的是等待時間。不高的櫃檯那邊,幾位公務大爺在那裡高蹺著腿目空一切地海侃著。每一位遞過去的材料都遭了一把被推開的命運:「明天來。」裡面那位公務大爺語氣乾脆、不容置疑。排在我前面的三位碰壁者都鐵青著臉旁立在不大的大廳裡。
我一直在心裡快速地盤算如何對付這「公僕」潑皮。終於臨到了我,躲是躲不開了,我一手托著櫃檯面猛地一躍跳進櫃檯裡面,還沒等他反應過來,我撲過去抓住他的胸依居高臨下把他壓制在椅子上。彼大驚失色,語無倫次,明顯地有些恐慌,不斷地也是本能地掙扎著,口裡重複著:「你幹嘛?你幹嘛?」我說,「我是來解放你的。你的領導都是一群冷血的畜生,把你安置在讓你如此痛苦的位置上」,我盯著彼說。「你罵我們領導,你罵我們領導」,彼像抓住了一絲救命索似的。我一把拉他起來,「走,一起去罵你的王八蛋領導去。」不料他突然猛地掙脫了我的手,一躍跳出櫃檯,發瘋似地從那些剛才被他拒絕但還沒離開的人手裡搶過了手續,嘴裡不停地嚷嚷:「我這就給大夥兒趕緊辦還不成嗎?」進了櫃檯後一邊辦理一邊還不停地重複著這句話。
雖然經歷了些波折,但那天我實現了辦事的目的。人們常說共產黨政權是流氓,這實際上是矮化了流氓的標準。第二週我又去那裡取辦理好的房產證,他一眼看見排在隊列中的我,熱情招手,嘴裡竟說:「您不用排隊,您怎麼能排隊?」「你連醒來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回了一句。
人是很難要求一律的。對別人的苦難、不如意無動於衷已是使人失望的事了,尚連保衛自己正當利益的衝動都不再有,你期待這個社會好起來,這無異於期望雄雞去下蛋。只有自己理直氣壯地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整個社會重視個體權利的局面才會實現,每個個體均不當貪得份外利益,把期望冀於別人,至少當絕不含糊地保衛自己的正當利益。
社會安全的載體就是每一個具體的個體,每個個體便是社會這張大網上的一個具體的綰結,你的放棄便導致一個現實的漏洞,這是個並不複雜的道理。正是我們作為個體的無底線遷就、放棄,公共權力才會生成長著一個猙獰面目的冷酷怪物。而絕大多數逆來順受的情形下,極個別人的抗爭也就常作了犧牲的材料,於大環境的改變猶一箭入海之效。
相關鏈接: 附:高智晟《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草案全文下載 (點擊這裡)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