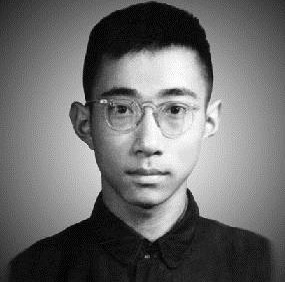(接上文)與顧文選在同一份材料上還有瀋元。
瀋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從上海位育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年,位育中學另一名學生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這兩名學生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中,都被劃為「右派份子」。位育中學中學1955年的925名畢業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份子」,包括兩個考入北大清華的人。
瀋元被定為「右派份子」開除學籍遣送北京郊區勞動。1961年「摘帽」後,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產黨人歷史學者黎澍等人的幫助,到中國科學院現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時相對寬鬆了一點的條件下,他在《歷史研究》和《人民日報》上多次發表了論文。與其他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同學相比,他算是「幸運」的。這也說明他試圖努力和當時的主流社會合拍而不是對抗(其他「右派份子」當時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許)。但到了1965年初,他發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
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發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調入歷史研究所工作,成為幫助過他的領導幹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體塗黑,裝扮成黑人而進入馬裡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自己離開中國。瀋元也被判處死刑。當時的中國,不僅批評當政者,哪怕是輕微的批評,可以是死罪,想要逃走,想要離開中國,也是死罪。瀋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殺害。
假使瀋元活在今天,他會是報紙上刊出的「高考狀元」,會是他的中學的驕傲。但是在毛氏時代,他不但被劃為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右派份子」類別,還被進而判處死刑。關於一個人的遭遇和政治的這種密切相關關係,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在1970年他被槍殺時,權力當局的說法是:
十九、現行反革命分子瀋元,男,32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份子。其母系右派份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瀋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瀋元的母親和哥哥,也成為判處瀋元死刑的理由,這種設立罪名的方式,需要被歷史系或者法律系的學生作專題論文來從學理方面做出分析和解釋。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處死刑。他1956年從北大數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1957年5月,他把北大圖書館英文《工人日報》上刊載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題為《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1956年2月25日)翻譯了一些段落,貼在學校閱報欄上。一名受訪者說,當時有很多人站在閱報欄前看報紙,同時也看了任大熊陸續貼出的翻譯稿,每次一頁兩頁,手抄在普通稿紙上。這名受訪者後來也被劃成了「右派份子」。
赫魯曉夫的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實行大規模迫害、監禁和殺戮的部分事實,譴責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這在當時是很大的震動。赫魯曉夫的報告在蘇聯內部發往共產黨的各層組織,在蘇聯人人皆知。蘇聯共產黨也把這份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但是報告文本從來沒有在蘇聯報紙或者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因此才被西方媒體稱為「祕密報告」。這個報告之後,斯大林的受難者在俄國已經開始大批得到「平反」(從現在公佈的資料看,1956年有130萬受難者在俄國得到了「平反」),在中國,任大熊卻因翻譯了這個報告的一些段落,先在北大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又被指為「反革命」判刑,在文革中又被判處死刑。從筆者收集到的判決書上可以看到,判處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沒有援引任何法律條文依據(人類文明自有了法律,判刑就要寫上法律根據,哪怕是裝樣子呢,文革在這方面非常「徹底」),隻寫著:
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准,特依法判決如下:……
所謂「一.三一」指示,指毛氏批准發出的「中發[1970]3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毛氏在此文件上批的「照辦」二字就是判處死刑的依據。這是人類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決書格式。
在13人中,任大熊被列為第三。關於他,判決書寫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歲,舊職員出身,學生成分,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臺灣。該犯一九六零年因糾集反革命集團、企圖叛國投敵,被判處無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積極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共聯」,任小組長。參加制定反革命綱領,發展反革命成員,預謀搶奪我保衛人員武器。先後書寫「時事述評」等反動文章九篇,極其惡毒地誣蔑、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禁閉室挖穿獄牆,與主犯常瀛清訂立攻守同盟,妄圖負隅頑抗。反動透頂,猖狂至極。罪惡纍纍,死有餘辜,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仍然記得任大熊的北大同學說,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樣子,南方人,很瘦,是個很聰明的人,畢業留校後住在校內全齋(文革中改名為「紅七樓」),被劃成「右派份子」時還沒有結婚。他的同學一直不知道他已經在文革中被處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還有家人在。
上引判決書,是一名和任大熊關在同一監獄的人莫興齡的兒子提供的。莫興齡是一名基督教醫院的醫生,曾到美國醫院學習,因為這些原因,1954年被逮捕並被判刑15年。莫興齡在還有17天刑滿時死於獄中,監獄當局說他「自殺」了。文革後莫興齡的兒子到山西大同監獄尋找父親的埋葬處並給父親築墓。他沒有能得到關於他父親的文字記錄,但得到了這份有任大熊在內的死刑判決書。他給筆者提供了判決書的複印件。
吳思慧,男,四川榮縣人,生於1932年或者1933年(判決書上說他在1970年3月「時年37歲」),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他的父親吳祖楠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軍人,在1949年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1962年去世。吳思慧與他的哥哥和妹妹留在大陸。他在1951年和班上三個同學一起參軍。(四個人中,一人被槍決,兩人後來「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並非通常意義上說的自殺,而是迫害的結果。必須注意到這種迫害密度)。1953年他從軍隊復員後到北大物理系(清華物理系已經在1952年被取消)繼續讀書,畢業後在北大讀研究生。1958年2月他被劃成「右派份子」。(從時間看,他是在1957年已經劃定5%的「右派份子」後又被「補課」進去的。上文已經寫到,「補課」後,北京大學的「右派份子」比例提高到了7%。)
1959年,他被分配去洛陽工學院。同年12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勞動教養」兩年。(那是一種工作單位就可以決定的刑罰。每個工作單位的領導人可以有權把那裡的工作人員送去「勞動教養」,這一點就足夠恐怖的了,更不要說他們的標準是多麼荒唐與狠毒。)「勞動教養」期滿後,他在洛陽修鞋為生。1965年被指控「盜竊」判刑十年。1970年「打擊反革命」運動開始後,他被「揭發」和同牢的人說了咒罵毛氏和其妻子江青的話。他被河南省革命委員會(這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權力機構的名稱,除了行政權力,還有權判死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後,1981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案件,撤銷1970年的死刑判決。報告說,原判認定的「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越獄投敵叛國」兩項的事實,「均構不成反革命罪」。他們也同時撤銷了1965年的判決。
張錫錕是化學系學生,畢業於成都列五中學(後改名為第五中學),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學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園的短暫的「鳴放」時期,他貼出了題為「衛道者的邏輯大綱」的大字報:
一、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二、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三、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四、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五、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七、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八、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九、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這些「邏輯」,也都被運用到對他的指控上。張錫錕被劃為「右派份子」後,對他的處分是「勞動考察」,送工廠勞動。1965年他試圖逃往國外被抓,並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這雖然會被判重罪,但是還不至於如文革中那樣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專區鹽源農場「勞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發「企圖組織越獄」,在鹽源農場被槍斃。
文革結束兩年後,開始給「右派份子」「改正」。北京大學有關辦公室的一名楊姓幹部曾經到四川該勞改農場交涉。但是那邊不給張錫錕「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陽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園書屋)書中,作者楊澤泉記錄了他所瞭解的張錫錕在勞改農場的最後的日子。楊澤泉當時也被關在那個勞改農場,當然無從得到張錫錕的死刑判決文件。他記得,判決是由當時的西昌地區革命委員會人保組發出的。死刑執行地是鹽源農場農七隊的監院門口。
一名受訪者說,他和張錫錕幾乎同時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們集體乘坐同一輛大蓬卡車,沿川陝公路北上,到寶雞換火車去了北京。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們都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後他得到「改正」。他記著35年前被殺害的張錫錕。
七名被判處死刑的北大「右派份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殺害。這六人中,有四人是在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活動」運動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由權力當局用國家機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所謂「群眾專政」來實行)的迫害行動。僅從他們的死亡時間,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死亡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他們的死亡是一場群體性的迫害的結果,他們死於集中領導下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之中;他們的死亡清楚體現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續,同時還是「反右」迫害的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方面,請參閱筆者的文章,〈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份子」中,吳思慧的名字是筆者在查訪多年後,在2009年底最後找到的。筆者曾經問吳思慧的同學,你們為什麼不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呢?今天,你們可以紀念死者,說出真相。你們中有的是聰明才俊之士,寫出他的事情對你們來說完全不是困難的事情。你們為什麼要把吳思慧的故事隱藏在你們班的幾個同學之間呢?為什麼要讓吳思慧成為一個至今都不得公佈名字的受難者呢?
我聽到一些解釋。一個說法是,不瞭解情況啊,吳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學)應該比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經另外結婚,丈夫還是個所長。——現在是什麼時代,難道還會有人指責他的女朋友嫁給了別人沒有為他「守節」?她的丈夫也還會不准她講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還有一個說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學擔任過較高的職位,認為吳思慧的事情要緩辦,降溫,避免不良影響。——吳思慧已經被殺害40年了,還要「緩辦」到什麼時候去?曾任較高職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學嗎?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對北大瀋克琦教授更加懷有敬意。他出生於1921年,抗戰期間畢業於西南聯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鬥爭」,被長期關在「牛棚」中。文革後他曾經擔任北大副校長,退休後他編寫了《西南聯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年修訂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139個「右派份子」的名單。其中教員8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這139人中,有吳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吳思慧離開北大後的遭遇。
據筆者所知,這樣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單全面系統地寫出來,記錄下來,印刷出來,是很少見的。儘管文革後的當局給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記載、報告和發表他們的遭遇一直是被禁止的。這是我對瀋老師充滿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條有理。和他談話,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種由理性和道德煥發出來的文雅力量。
關於「右派份子」的「處理」(這是當時用的動詞),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8》中,沒有記錄數百名「右派份子」被大卡車到學校來裝去「勞教」和「監督勞動」的事情,也沒有記錄被殺害的人。關於那一時期北大發生的事情,有一行記載是:
(1958年)4月22日4月19日至21日,全校突擊圍剿麻雀。三天共殲滅麻雀502隻。
以北大一萬多人停課停工三天的代價打死502隻麻雀,確實像瘋子傻子所為,然而那時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準的北京大學校園裡發生了。這並不僅僅是北大一個學校的行為,那時候在最高權力當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這一歷史的醜聞當然應該記錄。但是,北京大學的「右派份子」受到的迫害,是更應該記錄下來的。
本文的目的,是記載在殺死麻雀之前和同時發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瀋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份子」名字寫出來,就能知道到底應該是多少人了)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北大教員學生中被判處了死刑的七個人。
調查不夠深入仔細,敬請讀者補正。
成文時間:2010年6月5日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瀋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從上海位育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年,位育中學另一名學生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這兩名學生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中,都被劃為「右派份子」。位育中學中學1955年的925名畢業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份子」,包括兩個考入北大清華的人。
瀋元被定為「右派份子」開除學籍遣送北京郊區勞動。1961年「摘帽」後,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產黨人歷史學者黎澍等人的幫助,到中國科學院現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時相對寬鬆了一點的條件下,他在《歷史研究》和《人民日報》上多次發表了論文。與其他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同學相比,他算是「幸運」的。這也說明他試圖努力和當時的主流社會合拍而不是對抗(其他「右派份子」當時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許)。但到了1965年初,他發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
文革開始後,他遭到批判鬥爭。發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調入歷史研究所工作,成為幫助過他的領導幹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體塗黑,裝扮成黑人而進入馬裡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自己離開中國。瀋元也被判處死刑。當時的中國,不僅批評當政者,哪怕是輕微的批評,可以是死罪,想要逃走,想要離開中國,也是死罪。瀋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殺害。
假使瀋元活在今天,他會是報紙上刊出的「高考狀元」,會是他的中學的驕傲。但是在毛氏時代,他不但被劃為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右派份子」類別,還被進而判處死刑。關於一個人的遭遇和政治的這種密切相關關係,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在1970年他被槍殺時,權力當局的說法是:
十九、現行反革命分子瀋元,男,32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份子。其母系右派份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瀋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瀋元的母親和哥哥,也成為判處瀋元死刑的理由,這種設立罪名的方式,需要被歷史系或者法律系的學生作專題論文來從學理方面做出分析和解釋。
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處死刑。他1956年從北大數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1957年5月,他把北大圖書館英文《工人日報》上刊載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題為《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1956年2月25日)翻譯了一些段落,貼在學校閱報欄上。一名受訪者說,當時有很多人站在閱報欄前看報紙,同時也看了任大熊陸續貼出的翻譯稿,每次一頁兩頁,手抄在普通稿紙上。這名受訪者後來也被劃成了「右派份子」。
赫魯曉夫的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實行大規模迫害、監禁和殺戮的部分事實,譴責了斯大林的「個人迷信」。這在當時是很大的震動。赫魯曉夫的報告在蘇聯內部發往共產黨的各層組織,在蘇聯人人皆知。蘇聯共產黨也把這份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但是報告文本從來沒有在蘇聯報紙或者出版物上公開發表,因此才被西方媒體稱為「祕密報告」。這個報告之後,斯大林的受難者在俄國已經開始大批得到「平反」(從現在公佈的資料看,1956年有130萬受難者在俄國得到了「平反」),在中國,任大熊卻因翻譯了這個報告的一些段落,先在北大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又被指為「反革命」判刑,在文革中又被判處死刑。從筆者收集到的判決書上可以看到,判處任大熊等13人死刑,沒有援引任何法律條文依據(人類文明自有了法律,判刑就要寫上法律根據,哪怕是裝樣子呢,文革在這方面非常「徹底」),隻寫著:
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准,特依法判決如下:……
所謂「一.三一」指示,指毛氏批准發出的「中發[1970]3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毛氏在此文件上批的「照辦」二字就是判處死刑的依據。這是人類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決書格式。
在13人中,任大熊被列為第三。關於他,判決書寫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歲,舊職員出身,學生成分,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臺灣。該犯一九六零年因糾集反革命集團、企圖叛國投敵,被判處無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積極參加反革命暴亂集團「共聯」,任小組長。參加制定反革命綱領,發展反革命成員,預謀搶奪我保衛人員武器。先後書寫「時事述評」等反動文章九篇,極其惡毒地誣蔑、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禁閉室挖穿獄牆,與主犯常瀛清訂立攻守同盟,妄圖負隅頑抗。反動透頂,猖狂至極。罪惡纍纍,死有餘辜,民憤極大。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仍然記得任大熊的北大同學說,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樣子,南方人,很瘦,是個很聰明的人,畢業留校後住在校內全齋(文革中改名為「紅七樓」),被劃成「右派份子」時還沒有結婚。他的同學一直不知道他已經在文革中被處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還有家人在。
上引判決書,是一名和任大熊關在同一監獄的人莫興齡的兒子提供的。莫興齡是一名基督教醫院的醫生,曾到美國醫院學習,因為這些原因,1954年被逮捕並被判刑15年。莫興齡在還有17天刑滿時死於獄中,監獄當局說他「自殺」了。文革後莫興齡的兒子到山西大同監獄尋找父親的埋葬處並給父親築墓。他沒有能得到關於他父親的文字記錄,但得到了這份有任大熊在內的死刑判決書。他給筆者提供了判決書的複印件。
吳思慧,男,四川榮縣人,生於1932年或者1933年(判決書上說他在1970年3月「時年37歲」),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他的父親吳祖楠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軍人,在1949年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1962年去世。吳思慧與他的哥哥和妹妹留在大陸。他在1951年和班上三個同學一起參軍。(四個人中,一人被槍決,兩人後來「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並非通常意義上說的自殺,而是迫害的結果。必須注意到這種迫害密度)。1953年他從軍隊復員後到北大物理系(清華物理系已經在1952年被取消)繼續讀書,畢業後在北大讀研究生。1958年2月他被劃成「右派份子」。(從時間看,他是在1957年已經劃定5%的「右派份子」後又被「補課」進去的。上文已經寫到,「補課」後,北京大學的「右派份子」比例提高到了7%。)
1959年,他被分配去洛陽工學院。同年12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勞動教養」兩年。(那是一種工作單位就可以決定的刑罰。每個工作單位的領導人可以有權把那裡的工作人員送去「勞動教養」,這一點就足夠恐怖的了,更不要說他們的標準是多麼荒唐與狠毒。)「勞動教養」期滿後,他在洛陽修鞋為生。1965年被指控「盜竊」判刑十年。1970年「打擊反革命」運動開始後,他被「揭發」和同牢的人說了咒罵毛氏和其妻子江青的話。他被河南省革命委員會(這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權力機構的名稱,除了行政權力,還有權判死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後,1981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案件,撤銷1970年的死刑判決。報告說,原判認定的「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越獄投敵叛國」兩項的事實,「均構不成反革命罪」。他們也同時撤銷了1965年的判決。
張錫錕是化學系學生,畢業於成都列五中學(後改名為第五中學),1954年夏考入北大化學系。在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北大校園的短暫的「鳴放」時期,他貼出了題為「衛道者的邏輯大綱」的大字報:
一、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二、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三、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四、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五、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六、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七、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八、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九、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十、「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這些「邏輯」,也都被運用到對他的指控上。張錫錕被劃為「右派份子」後,對他的處分是「勞動考察」,送工廠勞動。1965年他試圖逃往國外被抓,並一次被判徒刑13年(文革前,這雖然會被判重罪,但是還不至於如文革中那樣被判死刑),在四川西昌專區鹽源農場「勞改」。1975年9月,他被人揭發「企圖組織越獄」,在鹽源農場被槍斃。
文革結束兩年後,開始給「右派份子」「改正」。北京大學有關辦公室的一名楊姓幹部曾經到四川該勞改農場交涉。但是那邊不給張錫錕「平反」。
在2009年出版的《回眸一笑—我在太陽部落的年代》(香港田園書屋)書中,作者楊澤泉記錄了他所瞭解的張錫錕在勞改農場的最後的日子。楊澤泉當時也被關在那個勞改農場,當然無從得到張錫錕的死刑判決文件。他記得,判決是由當時的西昌地區革命委員會人保組發出的。死刑執行地是鹽源農場農七隊的監院門口。
一名受訪者說,他和張錫錕幾乎同時在成都收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1954年8月19日,是星期四,他們集體乘坐同一輛大蓬卡車,沿川陝公路北上,到寶雞換火車去了北京。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們都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後他得到「改正」。他記著35年前被殺害的張錫錕。
七名被判處死刑的北大「右派份子」中六人在文革中被殺害。這六人中,有四人是在1970年的「打擊反革命活動」運動中被判死刑的,那是文革中規模最大的由權力當局用國家機器直接施害(另一些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所謂「群眾專政」來實行)的迫害行動。僅從他們的死亡時間,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死亡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他們的死亡是一場群體性的迫害的結果,他們死於集中領導下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之中;他們的死亡清楚體現了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延續,同時還是「反右」迫害的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方面,請參閱筆者的文章,〈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
在七名被判死刑的北大「右派份子」中,吳思慧的名字是筆者在查訪多年後,在2009年底最後找到的。筆者曾經問吳思慧的同學,你們為什麼不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呢?今天,你們可以紀念死者,說出真相。你們中有的是聰明才俊之士,寫出他的事情對你們來說完全不是困難的事情。你們為什麼要把吳思慧的故事隱藏在你們班的幾個同學之間呢?為什麼要讓吳思慧成為一個至今都不得公佈名字的受難者呢?
我聽到一些解釋。一個說法是,不瞭解情況啊,吳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學)應該比較知道1957年的事,但是她已經另外結婚,丈夫還是個所長。——現在是什麼時代,難道還會有人指責他的女朋友嫁給了別人沒有為他「守節」?她的丈夫也還會不准她講述50年前的男朋友受迫害的事情?還有一個說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學擔任過較高的職位,認為吳思慧的事情要緩辦,降溫,避免不良影響。——吳思慧已經被殺害40年了,還要「緩辦」到什麼時候去?曾任較高職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同班同學嗎?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對北大瀋克琦教授更加懷有敬意。他出生於1921年,抗戰期間畢業於西南聯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鬥爭」,被長期關在「牛棚」中。文革後他曾經擔任北大副校長,退休後他編寫了《西南聯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北大物理系九十年》2008年修訂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139個「右派份子」的名單。其中教員8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9人。這139人中,有吳思慧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吳思慧離開北大後的遭遇。
據筆者所知,這樣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單全面系統地寫出來,記錄下來,印刷出來,是很少見的。儘管文革後的當局給大量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作出了「改正」和「平反」以及「昭雪」等等,但是記載、報告和發表他們的遭遇一直是被禁止的。這是我對瀋老師充滿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條有理。和他談話,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種由理性和道德煥發出來的文雅力量。
關於「右派份子」的「處理」(這是當時用的動詞),是在1958年做的。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8》中,沒有記錄數百名「右派份子」被大卡車到學校來裝去「勞教」和「監督勞動」的事情,也沒有記錄被殺害的人。關於那一時期北大發生的事情,有一行記載是:
(1958年)4月22日4月19日至21日,全校突擊圍剿麻雀。三天共殲滅麻雀502隻。
以北大一萬多人停課停工三天的代價打死502隻麻雀,確實像瘋子傻子所為,然而那時候就堂而皇之地在具有最高平均教育水準的北京大學校園裡發生了。這並不僅僅是北大一個學校的行為,那時候在最高權力當局的命令下,北京全市都在打麻雀。這一歷史的醜聞當然應該記錄。但是,北京大學的「右派份子」受到的迫害,是更應該記錄下來的。
本文的目的,是記載在殺死麻雀之前和同時發生的715或者716名(如果有人能加入瀋克琦教授的工作把全校的「右派份子」名字寫出來,就能知道到底應該是多少人了)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北大教員學生中被判處了死刑的七個人。
調查不夠深入仔細,敬請讀者補正。
成文時間:2010年6月5日
──轉自《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