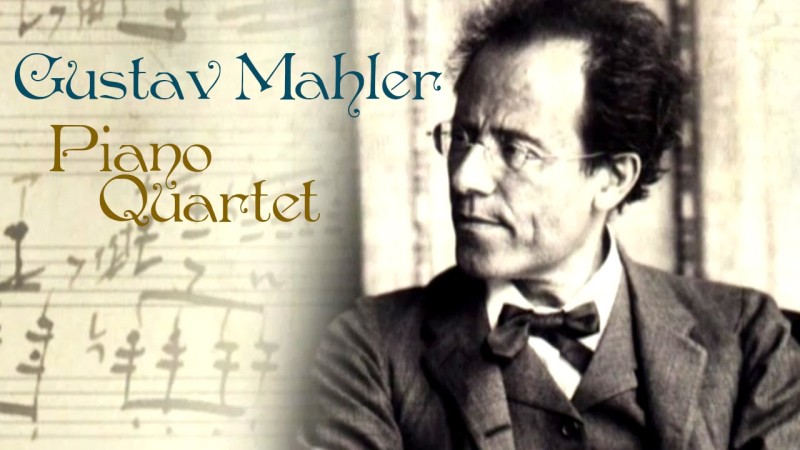老子說,少則得,多則惑。在這一段聽馬勒的交響樂,以及對於音樂及文化的思索和探究中,我深切地體會到了這一點。因為越聽得多、看得多,我就越覺得自己依然不很理解西方音樂及西方文化,為此也就越來越不敢多說了。為此,寫下的文字不過是分享我的困惑。
在我最近兩三年的思想研究中,尤其是對於政教分離、十九世紀後的後基督教社會問題的研究中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時,我在多處談到關於Romantik,浪漫派的看法,其中特別談到它的中文翻譯,「浪漫的」、「浪漫主義」問題。我認為,中文把Romantik翻譯成「浪漫主義」嚴重地,導了人們對這個術語及思想文化傾向的理解。在我看來,大約翻譯成濫漫或者濫蠻主義倒是更為恰當一些。因為它是在描述一種主觀意念佔主導地位的傾向。但是現在,在經歷了這一段聽馬勒的音樂,對馬勒音樂的體會及探究後,這個Romantik究竟在十九世紀,在歐洲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地位影響是什麼,通過聽馬勒音樂及對於不同作曲家及指揮家的認識,非但沒有讓我更為清晰,反而讓我越來越感到困惑。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準確地定位及描述它,不知道我是離西方音樂越來越遠了,還是現在才有點入門了?
在對它的了解中,以交響樂為例,它幾乎可以說是和Romantik一起發生展開的形式。它不過是發生於巴赫的宗教音樂之後,經過海頓、莫扎特的所謂古典音樂形式到貝多芬才開始展開的形式,及至到了馬勒,才可以說它的規模及形式較為成熟,但是卻立即就變得有些不可收拾。並且就在此嘎然而止,轉向了現代音樂。這時間不過幾十年,它幾乎亦步亦趨地伴隨着政教分離的社會文化潮流發生、發展。而有意思的是,第一,這個過程竟然幾乎完全是和中國京劇的發生、發展時間同期。
第二,注意到上述這點,在閱讀馬勒時就讓我進一步發現,同期的西方歌劇及演員、劇目等在劇院及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也幾乎和京劇等戲曲在中國社會的地位相同。而交響樂不過是歌劇,這個西方「戲曲」的序曲和間奏曲發展出來的形式。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國人不必那麼神化西方的交響樂和歌劇,它不是永恆的令人眩暈的神廟,而不過是和京劇一樣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情,也是剛剛走出幼稚就拐了彎,步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妄自菲薄會敗壞你的審美口味及能力。
為此,第三,了解了這個過程讓我更加理解,西方人對於京劇的驚嘆和佩服是發自內心的,發自對於文化及藝術的理解深處的。因為他們的歌劇除了音樂外,表演藝術實際上是非常粗糙,這個粗糙保持到了今天。他們的歌劇的輝煌在於布景和外置的設置。而演員的表演始終沒有進入人文的場景——中國人的所謂藝術的修養中。
我之所以說到這個歌劇,是因為那個Romantik,即濫蠻主義實際上是音樂受歌劇、文學、詩歌,乃至各種社會性的觀念的影響的產物。Romantik,不是純藝術的追求結果,而是一種世俗化的人的衝動的產物。Romantik的藝術追求的不再是精神——超越的宗教性的精神,而是人的物化及欲化。它不折不扣地是人的觀念化的產物。所以我實實在在地開始懷疑,貝多芬的Romantik和十八世紀末期後產生的意識形態具有類似的傾向及性質,從而在一些方面是和其後,即今天的物質化、人的慾望的無休止的膨脹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的。而馬勒則卻是因為感到了這種傾向,而產生了困惑及痛苦。
在這意義上,在聽馬勒音樂的時候,我感到,馬勒的音樂可以說是比貝多芬帶有更多的精神內容,並且努力試圖重新向精神音樂回復。
這些被常人看來奇怪的問題,既讓我詫異,也讓我不安。這也包括一位朋友問我,托斯卡尼尼指揮過馬勒的交響樂嗎?托斯卡尼尼是如何看馬勒,如何詮釋馬勒音樂的?因為這個問題讓我更加感到我對於西方文化及其歷史的陌生。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它打開了我另外一扇好奇的窗戶。事實上正是托斯卡尼尼到紐約後取代了馬勒的位置,並且把馬勒從紐約交響樂團擠走的。在對於音樂的理解和處理上,他和馬勒也完全是兩個傾向。
作為指揮及對音樂詮釋的理解,托斯卡尼尼極為反感馬勒及德國的Romantik傳統。他認為要對音樂的理解要回到樂符及音樂本身,不能夠隨意按照主觀的理解詮釋修改。這讓我感到非常奇怪。在對音樂的態度上,這和我們一向的教條性的理解相反,這位意大利人要的是音樂的客觀性,而反對德國人的Romantik,濫蠻性,隨意地發揮詮釋。流俗的觀點認為德奧傳統嚴格、拘泥,意大利人天性熱情、活躍,不拘一格。可在這兒居然完全是相反的。對我來說,矛盾的還有,如前所述,照我的理解,馬勒及其音樂是對Romantik,濫蠻主義的反彈的產物。可幾乎所有的樂評都把他作為最後一位Romantik,濫蠻主義的作曲家。為此,這就讓我的思想陷入混亂和苦惱,不知我究竟到了什麼地方,不知究竟如何定位,如何理解這些問題?
為此,它也就再次讓我回到了前面的問題,Romantik,濫蠻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這個十八世紀末期發生,十九世紀末期式微的傾向究竟是什麼——它和德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關係是什麼?在巴赫之後的交響樂除經過所謂古典主義立即進入濫蠻主義外,還有別的發展的道路及可能嗎?近代發生的交響樂可以說是濫蠻主義的結果嗎?或者說它一直掙扎於濫蠻的暴力影響下?而時下,難道濫蠻主義過去了,為此交響樂的時代也就過去了?難道以巴赫為代表的音樂中的精神是被貝多芬們結束的?
我真的是越來越糊塗了!
這個世界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最近二百年中發生的,世界的變化不僅太快,而且太粗糙了!被人們驚嘆的輝煌,實際上人們從沒有仔細地觀看過它,細緻地加工過它,充分地消化過它,研究過它。因為我們所經歷的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根本不給你這種細嚼慢咽的可能。毀滅的速度難道不是比建設的速度快上千百倍?
所有這一切,我大約還是必須要回到文藝復興、啟蒙思想、政教分離帶來的文化和社會變化中去尋找。這也就是說世俗化、人本化帶來的究竟是什麼?我問的不僅是它給歐洲,而且更是它給人類帶來的究竟是什麼。因為古往今來到今天為止,這種文化,也只有這種文化具有能力並且已經席捲了人類存在的所有地方,摧毀了所有其它文化。
我們面對的是什麼?可能我們還來不及思索就已經掉入深淵。這一點突然讓我看到,半個多世紀前物理學家提出的黑洞學說,這個理論不僅存在於人類對宇宙的理解,而且也適用於對人類文化宇宙的認識,為此,它可能是一種對人類的反諷。
我們在試圖理解宇宙黑洞時,卻沒有發現還有一個文化黑洞,我們在還沒有遇到宇宙黑洞之前,卻已經落入了文化黑洞……!
如果用數學的語言來模擬理解文化,那麼描述西方文化的方程也有一個奇點。在歷史和現實中,這個二元的文化的分母已經顯示出了這個奇點:因為在歷史上,基督教導致的政教合一的歷史時期及社會,被歷史證明是一條死路,所以發生了文藝復興。在現實中,沒了基督教,即政教分離、基督教退出後的時期,它卻或者是導致世俗的政教合一——極權主義,或者是無盡的政治上的排他、悖謬和衝突,如最近二十年世界所發生的問題,它讓我們看到一百年前,以及今天,我們都在直接並且激烈地面臨這些問題帶來的災難及壓力。
究竟什麼導致了這個文化的分母等於零,這二百年的歷史似乎應該對此是有答案的。音樂的探索或許比思想的探索更為敏感和直接。你覺得炫目、輝煌無比的東西,馬勒們覺得它粗陋、問題重重。在這個意義上,馬勒的努力可能是在解答在音樂上出現了奇點的麥克斯韋爾方程,他告訴我們,它的協變需要新的假說,即新的形而上學前提。我們現在才感到並且經受的黑暗和災難,可馬勒早就感覺到,並且在尋找出路。
這一百年的歷史讓我們看到,普世的人權和普適的民主價值如同光速不變那樣,是文化問題的電磁方程協變的前提!對馬勒來說,它導致了四海之內皆兄弟,導致自然萬物、生命之間的聯繫,那個在東方早就存在的假說。
在這個意義上,馬勒甚至又是走到了當代物理學家的前面。因為現代物理學家提出黑洞假說,從「無」中理解宇宙,走向東方神祕主義之路,是在馬勒去世後很久的事了。
在這個東西方的問題上,當你覺得西方及現代化,包括交響樂是一座神廟的時候——因為你見到它就已經在膜拜它。所以你就是經歷了災難,犧牲掉了生命,因為你俯首、叩頭、閉目,你什麼都看不到。可當你和西方人一樣上了船,你看到和經歷的是茫茫大海,是風浪,你就會覺得船上的一切,海上的一切都是問題,稍不注意,船就會被狂風險浪打翻。而最嚴重的是甚至注意了可能也沒用,因為製造這艘船的材料和工藝可能先天地存在問題,那材料到了一定時候就會脆裂、溶化,也可能因為海洋、宇宙太浩瀚難以預料了!
我們真的很無辜,本來是可以不上這條船,或者像日本人一樣穿着自己的救生衣,可我們主動上船,主動粉碎了傳統——這道抵禦危難的衣物,比船上的西方人還赤身裸體,所以我們的災難不僅自找,而且一定會更為嚴重。
聽馬勒的音樂,聽另外一種宇宙神韻,生命聯繫的呼喚,也許能讓你感到亡羊補牢、重新回歸,為時未晚……!
2017-6-19 德國·埃森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在我最近兩三年的思想研究中,尤其是對於政教分離、十九世紀後的後基督教社會問題的研究中涉及到意識形態問題時,我在多處談到關於Romantik,浪漫派的看法,其中特別談到它的中文翻譯,「浪漫的」、「浪漫主義」問題。我認為,中文把Romantik翻譯成「浪漫主義」嚴重地,導了人們對這個術語及思想文化傾向的理解。在我看來,大約翻譯成濫漫或者濫蠻主義倒是更為恰當一些。因為它是在描述一種主觀意念佔主導地位的傾向。但是現在,在經歷了這一段聽馬勒的音樂,對馬勒音樂的體會及探究後,這個Romantik究竟在十九世紀,在歐洲的發生和發展及其地位影響是什麼,通過聽馬勒音樂及對於不同作曲家及指揮家的認識,非但沒有讓我更為清晰,反而讓我越來越感到困惑。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準確地定位及描述它,不知道我是離西方音樂越來越遠了,還是現在才有點入門了?
在對它的了解中,以交響樂為例,它幾乎可以說是和Romantik一起發生展開的形式。它不過是發生於巴赫的宗教音樂之後,經過海頓、莫扎特的所謂古典音樂形式到貝多芬才開始展開的形式,及至到了馬勒,才可以說它的規模及形式較為成熟,但是卻立即就變得有些不可收拾。並且就在此嘎然而止,轉向了現代音樂。這時間不過幾十年,它幾乎亦步亦趨地伴隨着政教分離的社會文化潮流發生、發展。而有意思的是,第一,這個過程竟然幾乎完全是和中國京劇的發生、發展時間同期。
第二,注意到上述這點,在閱讀馬勒時就讓我進一步發現,同期的西方歌劇及演員、劇目等在劇院及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也幾乎和京劇等戲曲在中國社會的地位相同。而交響樂不過是歌劇,這個西方「戲曲」的序曲和間奏曲發展出來的形式。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國人不必那麼神化西方的交響樂和歌劇,它不是永恆的令人眩暈的神廟,而不過是和京劇一樣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情,也是剛剛走出幼稚就拐了彎,步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妄自菲薄會敗壞你的審美口味及能力。
為此,第三,了解了這個過程讓我更加理解,西方人對於京劇的驚嘆和佩服是發自內心的,發自對於文化及藝術的理解深處的。因為他們的歌劇除了音樂外,表演藝術實際上是非常粗糙,這個粗糙保持到了今天。他們的歌劇的輝煌在於布景和外置的設置。而演員的表演始終沒有進入人文的場景——中國人的所謂藝術的修養中。
我之所以說到這個歌劇,是因為那個Romantik,即濫蠻主義實際上是音樂受歌劇、文學、詩歌,乃至各種社會性的觀念的影響的產物。Romantik,不是純藝術的追求結果,而是一種世俗化的人的衝動的產物。Romantik的藝術追求的不再是精神——超越的宗教性的精神,而是人的物化及欲化。它不折不扣地是人的觀念化的產物。所以我實實在在地開始懷疑,貝多芬的Romantik和十八世紀末期後產生的意識形態具有類似的傾向及性質,從而在一些方面是和其後,即今天的物質化、人的慾望的無休止的膨脹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的。而馬勒則卻是因為感到了這種傾向,而產生了困惑及痛苦。
在這意義上,在聽馬勒音樂的時候,我感到,馬勒的音樂可以說是比貝多芬帶有更多的精神內容,並且努力試圖重新向精神音樂回復。
這些被常人看來奇怪的問題,既讓我詫異,也讓我不安。這也包括一位朋友問我,托斯卡尼尼指揮過馬勒的交響樂嗎?托斯卡尼尼是如何看馬勒,如何詮釋馬勒音樂的?因為這個問題讓我更加感到我對於西方文化及其歷史的陌生。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它打開了我另外一扇好奇的窗戶。事實上正是托斯卡尼尼到紐約後取代了馬勒的位置,並且把馬勒從紐約交響樂團擠走的。在對於音樂的理解和處理上,他和馬勒也完全是兩個傾向。
作為指揮及對音樂詮釋的理解,托斯卡尼尼極為反感馬勒及德國的Romantik傳統。他認為要對音樂的理解要回到樂符及音樂本身,不能夠隨意按照主觀的理解詮釋修改。這讓我感到非常奇怪。在對音樂的態度上,這和我們一向的教條性的理解相反,這位意大利人要的是音樂的客觀性,而反對德國人的Romantik,濫蠻性,隨意地發揮詮釋。流俗的觀點認為德奧傳統嚴格、拘泥,意大利人天性熱情、活躍,不拘一格。可在這兒居然完全是相反的。對我來說,矛盾的還有,如前所述,照我的理解,馬勒及其音樂是對Romantik,濫蠻主義的反彈的產物。可幾乎所有的樂評都把他作為最後一位Romantik,濫蠻主義的作曲家。為此,這就讓我的思想陷入混亂和苦惱,不知我究竟到了什麼地方,不知究竟如何定位,如何理解這些問題?
為此,它也就再次讓我回到了前面的問題,Romantik,濫蠻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這個十八世紀末期發生,十九世紀末期式微的傾向究竟是什麼——它和德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關係是什麼?在巴赫之後的交響樂除經過所謂古典主義立即進入濫蠻主義外,還有別的發展的道路及可能嗎?近代發生的交響樂可以說是濫蠻主義的結果嗎?或者說它一直掙扎於濫蠻的暴力影響下?而時下,難道濫蠻主義過去了,為此交響樂的時代也就過去了?難道以巴赫為代表的音樂中的精神是被貝多芬們結束的?
我真的是越來越糊塗了!
這個世界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最近二百年中發生的,世界的變化不僅太快,而且太粗糙了!被人們驚嘆的輝煌,實際上人們從沒有仔細地觀看過它,細緻地加工過它,充分地消化過它,研究過它。因為我們所經歷的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根本不給你這種細嚼慢咽的可能。毀滅的速度難道不是比建設的速度快上千百倍?
所有這一切,我大約還是必須要回到文藝復興、啟蒙思想、政教分離帶來的文化和社會變化中去尋找。這也就是說世俗化、人本化帶來的究竟是什麼?我問的不僅是它給歐洲,而且更是它給人類帶來的究竟是什麼。因為古往今來到今天為止,這種文化,也只有這種文化具有能力並且已經席捲了人類存在的所有地方,摧毀了所有其它文化。
我們面對的是什麼?可能我們還來不及思索就已經掉入深淵。這一點突然讓我看到,半個多世紀前物理學家提出的黑洞學說,這個理論不僅存在於人類對宇宙的理解,而且也適用於對人類文化宇宙的認識,為此,它可能是一種對人類的反諷。
我們在試圖理解宇宙黑洞時,卻沒有發現還有一個文化黑洞,我們在還沒有遇到宇宙黑洞之前,卻已經落入了文化黑洞……!
如果用數學的語言來模擬理解文化,那麼描述西方文化的方程也有一個奇點。在歷史和現實中,這個二元的文化的分母已經顯示出了這個奇點:因為在歷史上,基督教導致的政教合一的歷史時期及社會,被歷史證明是一條死路,所以發生了文藝復興。在現實中,沒了基督教,即政教分離、基督教退出後的時期,它卻或者是導致世俗的政教合一——極權主義,或者是無盡的政治上的排他、悖謬和衝突,如最近二十年世界所發生的問題,它讓我們看到一百年前,以及今天,我們都在直接並且激烈地面臨這些問題帶來的災難及壓力。
究竟什麼導致了這個文化的分母等於零,這二百年的歷史似乎應該對此是有答案的。音樂的探索或許比思想的探索更為敏感和直接。你覺得炫目、輝煌無比的東西,馬勒們覺得它粗陋、問題重重。在這個意義上,馬勒的努力可能是在解答在音樂上出現了奇點的麥克斯韋爾方程,他告訴我們,它的協變需要新的假說,即新的形而上學前提。我們現在才感到並且經受的黑暗和災難,可馬勒早就感覺到,並且在尋找出路。
這一百年的歷史讓我們看到,普世的人權和普適的民主價值如同光速不變那樣,是文化問題的電磁方程協變的前提!對馬勒來說,它導致了四海之內皆兄弟,導致自然萬物、生命之間的聯繫,那個在東方早就存在的假說。
在這個意義上,馬勒甚至又是走到了當代物理學家的前面。因為現代物理學家提出黑洞假說,從「無」中理解宇宙,走向東方神祕主義之路,是在馬勒去世後很久的事了。
在這個東西方的問題上,當你覺得西方及現代化,包括交響樂是一座神廟的時候——因為你見到它就已經在膜拜它。所以你就是經歷了災難,犧牲掉了生命,因為你俯首、叩頭、閉目,你什麼都看不到。可當你和西方人一樣上了船,你看到和經歷的是茫茫大海,是風浪,你就會覺得船上的一切,海上的一切都是問題,稍不注意,船就會被狂風險浪打翻。而最嚴重的是甚至注意了可能也沒用,因為製造這艘船的材料和工藝可能先天地存在問題,那材料到了一定時候就會脆裂、溶化,也可能因為海洋、宇宙太浩瀚難以預料了!
我們真的很無辜,本來是可以不上這條船,或者像日本人一樣穿着自己的救生衣,可我們主動上船,主動粉碎了傳統——這道抵禦危難的衣物,比船上的西方人還赤身裸體,所以我們的災難不僅自找,而且一定會更為嚴重。
聽馬勒的音樂,聽另外一種宇宙神韻,生命聯繫的呼喚,也許能讓你感到亡羊補牢、重新回歸,為時未晚……!
2017-6-19 德國·埃森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