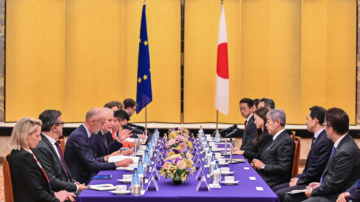只有依照明文憲法所規定的程序和步驟所締結的國家、所產生的權力、所組建的政府,才是合格的國家、正當的權力、合法的政府。——從那以後,統治合法性的前提就不可能再是「打下來的江山」或「祖宗的江山」,也不可能再是奉天承運的天命神話或教皇的加冕儀式,而首先是統治者和政府的合憲性,也就是說,只有嚴格依照憲法而產生的權力(而不是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才有起碼的資格宣稱它是合法的權力。
一、關於非憲政民主
民主、憲政各有多種分類口徑,但就其相互限制與相互依存的關係而言,憲政可分為兩種:民主憲政與非民主的憲政,民主也可分為兩種:憲政民主與非憲政的民主。
在人類歷史上,民主與憲政的誕生相距遙遠。民主有它的古典時代,而憲政,則是近現代的新生事物——公允地說,憲政的發生、發展主要是英美政治傳統的近現代產物。
在憲政誕生之前的民主,自然都是非憲政的民主——比如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臘民主,既是一種沒有選舉制度、代議制度作為中介的,由「人民大會」以公開辯論、現場辦公、投票決策方式行使各種統治權力的直接民主制度,也是「人民大會」的統治權力幾乎不受任何既定的明文規範所限制和約束的非憲政民主制度。這樣的民主並不一定「是個好東西」,因為人性有侷限,「人民」不是神,「人民」既可以是朝令夕改的,也可以是為所欲為的。蘇格拉底之死成了雅典式民主永恆的污點,而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色諾芬、亞裡士多德的批判民主的傳統,則時刻提醒後人,即使是「人民」本身,當他們行使政治權力的時候,也必須接受分權、法治的限制和約束,而不應該擁有所謂「一切權力」(現行中國憲法)。
在憲政誕生之後,當世界上幾乎所有或文明、或野蠻的國家都陸陸續續制定了或優良、或差強人意、或完全不及格的憲法之後,仍然有許多國家因各種事變,以各種理由,拖延、推諉憲法的全面履行,拒絕落實以分權、限權的方式捍衛人權與自由的憲政主義基本原則,在這樣的國家,假如他們的政體採取了定期、公開、普遍的選舉以更迭政府的制度的話,那麼他們的民主,當然也是非憲政的民主。比如在當今的伊朗、敘利亞、巴基斯坦,在俄羅斯、土耳其、哈薩克斯坦,雖然他們的政體實行定期、公開的民主選舉以更迭政府或國會,但是,他們的政體卻允許存在一位權大無邊的總統(如阿薩德),或允許存在一位權力高於憲法、高於民選總統的精神領袖(如哈梅內伊),或允許存在一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改變憲法規定、調整自己任期的超級總統(如普京)。
而至於所謂「社會主義民主」,雖然它也有一部經常修來改去的憲法,還有「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高大上政治承諾,但它的政體自始至終既不是民主的,更不是憲政的,無論對民主與憲政作何種寬泛的定義,它都與憲政或民主不沾邊。
二、大憲章、美國憲法、憲政主義對政治體制的革命性意義
1215年,英國約翰王頒布《大憲章》,由此開啟了以分權、限權的方式,憲政、法治的原則以保障自由和人權的偉大的英國政治傳統。這份《大憲章》雖然以詔書和特許狀的形式寫成,但它實質上是一份國王與貴族以及其他一切自由人之間帶有社會契約性質的法律文件。它以條款化具文對以往至高無上的王權進行了瓜分和限制,在法律上承認了貴族和自由民不可侵奪的權利,並確立了以法治保障自由的政治大原則。從此,英國的政治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
《大憲章》是英國法治與自由傳統最重要的奠基石之一,但它還沒有、也不足以發展出現代憲政主義。直至1776年起成文憲法在北美各殖民地相繼湧現,1787年產生了人類政制史上劃時代的美國聯邦憲法,1791年產生了以憲法修正案形式存在的美國權利法案,以及1791年產生了法國憲法和附著於其中的1789年人權宣言,憲政主義才獲得了它的全球化機緣並展現其蓬勃的生機。
美國憲法和法國憲法與英國《大憲章》的顯著不同之處在於,它們並不是以法律的形式對一種已經存在並已被確認為合法的國家統治權力進行修正與限制,而是以社會契約、最高法律的形式重新構造一種新型的國家統治權。這一事實表明,人們已經開始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只有依照明文憲法所規定的程序和步驟所締結的國家、所產生的權力、所組建的政府,才是合格的國家、正當的權力、合法的政府。——從那以後,統治合法性的前提就不可能再是「打下來的江山」或「祖宗的江山」,也不可能再是奉天承運的天命神話或教皇的加冕儀式,而首先是統治者和政府的合憲性,也就是說,只有嚴格依照憲法而產生的權力(而不是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才有起碼的資格宣稱它是合法的權力。
憲政主義除了對統治合法性的涵義進行了革命性的更新,在對統治權力的法律限制方面,也交出了革命性的全新答卷。現代憲政主義已不再滿足於如《大憲章》那樣只是對統治權力在個別方面、局部領域進行針對性的限制與約束,而是對國家統治權進行系統性、全方位的限制與約束,且不論這種統治權力是屬於君主的權力,還是屬於人民的權力,都概莫能外必須受到憲政的系統性、全方位的限制與約束。
三、憲政是對民主的規範與制約
毛澤東在延安曾經作過一次關於憲政的演講,毛說:「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毛還說,共產黨人愛憲政,將來也要搞憲政,但他們愛的不是英、法、美那樣「資產階級專政的憲政」——毛輕蔑地說,英、法、美的憲政都是「反動的東西」、是「吃人政治」,也不是國民政府試圖推行的那種假憲政——毛「一針見血」地說,蔣介石、國民黨所宣揚的憲政其實是「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毛澤東將來要搞的憲政,據他說,是什麼「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但是,從1949年建政至今,共產黨已經在中國「專政」了近七十年,別說中國人無緣見識「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是何方神聖,就連憲政二字,從毛到鄧,從江到習,也從此絕口不提了。大概是因為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共產黨對憲政主義尚無基本常識,後來多多少少瞭解了一些憲政ABC,知道憲政與「專政」、與「黨領導一切」乃為天敵,所以,管它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憲政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憲政,就都不敢再提了。連悼詞裡出現憲政二字,也都是不允許的。
回到毛澤東「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毛的意思似乎是說,憲政即等同於民主,二者是同義詞。這種說法,顯然不正確。憲政主義並不一般地排斥立憲君主制或立憲的貴族制、寡頭制,甚至包括「黨主立憲」這樣的設想,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憲政化的。在憲法上規定一種君主權力或政黨權力,為其設定系統化、全方位的法律限制與約束,使其符合憲政法治的基本原則,憲政與君權或黨權這樣的搭配——雖然它們看起來確實有些不搭——在憲政理論上既可以敷衍其詞,在政治實踐中,大概也是可以勉強成立的。
在政治學上,憲政與民主所回答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民主所回答的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問題,即統治權力應該向誰求取、由誰授權,而憲政回答的則是國家權力應該如何組建、如何分割、如何分配、如何制約、如何制衡、如何行使。人類政制史早已表明,憲政未必是民主的,民主更未必是憲政的。傑斐遜曾經抱怨美國憲法不夠民主,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曾經擔憂民意機構挾民主以亂憲政的現象出現(麥迪遜指出,即使是在政治上最先進的英國,立法機關藉民意支持而更改選期、延長任期等反憲政的行為也一再出現)。
憲政與民主豈止是不能互相劃等號,實際上,憲政是對純粹民主的修正與制約。在憲政國家,任何一位政治領袖,即使他真的(真的是真的)有超高的民意支持率,他也不可能獲得憲法所沒有規定的職務頭銜或封號,不可能超出憲法的規定行使其職務權力之外的任何權力,不可能擁有超出憲法規定的延長任期;在憲政國家,哪怕是經由嚴格的民主程序所通過的法律,民選總統依照多數民意所作出的決策,也都有可能被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判為違憲而歸於無效。簡而言之,在憲政民主國家,憲政不僅是對民主的保障和支撐,也是對民主的修正和制約。不管是人民的代表、民選的官員,還是「人民」本身,在憲政體制之下,都沒有背離憲法、為所欲為的權力。像中共憲法那樣標榜所謂「一切權力屬於某某」的思路,就是一種反憲政的思路,因為在憲政主義中,決不允許存在由單一勢力、單一機構掌控「一切權力」這種體制。
四、憲政與民主是最佳搭配
雖然憲政與民主並非毛澤東理解的那樣是二語一義,然而,憲政促進了民主,憲政使民主更規範、更健康,為民主的全球化發展開闢了新的渠道和新的空間,卻是不爭的事實:二百多年來,隨著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倣傚美國、法國制定了成文憲法,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認同憲政、實踐憲政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認同民主、接受民主,從而,越來越多的國家憲法裡加入了民主的內容,越來越多的憲政國家也就逐漸變成了真正的、堅定的民主國家。
也許,我們應該說,雖然憲政與民主並非固定搭配,卻是最佳搭配。二百多年裡,拿破崙的立憲帝制崩潰了,德國、日本強化君主權力的立憲君主制垮臺了,英國式君主與議會並駕齊驅的立憲君主制也最終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虛君民主制,......事情就是這樣,一切反民主、不民主、缺民主的政治制度都在憲政主義的檢視、監控之下走向了衰落,唯有民主政體與憲政相得益彰,二者對接得最順利,貼合得最緊密,民主政體在憲政秩序下蓬勃發展,碩果纍纍。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的憲政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要麼是憲政國家,要麼或多或少接受了某些憲政主義的制度安排。
2017/10/23
──轉自《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一、關於非憲政民主
民主、憲政各有多種分類口徑,但就其相互限制與相互依存的關係而言,憲政可分為兩種:民主憲政與非民主的憲政,民主也可分為兩種:憲政民主與非憲政的民主。
在人類歷史上,民主與憲政的誕生相距遙遠。民主有它的古典時代,而憲政,則是近現代的新生事物——公允地說,憲政的發生、發展主要是英美政治傳統的近現代產物。
在憲政誕生之前的民主,自然都是非憲政的民主——比如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臘民主,既是一種沒有選舉制度、代議制度作為中介的,由「人民大會」以公開辯論、現場辦公、投票決策方式行使各種統治權力的直接民主制度,也是「人民大會」的統治權力幾乎不受任何既定的明文規範所限制和約束的非憲政民主制度。這樣的民主並不一定「是個好東西」,因為人性有侷限,「人民」不是神,「人民」既可以是朝令夕改的,也可以是為所欲為的。蘇格拉底之死成了雅典式民主永恆的污點,而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色諾芬、亞裡士多德的批判民主的傳統,則時刻提醒後人,即使是「人民」本身,當他們行使政治權力的時候,也必須接受分權、法治的限制和約束,而不應該擁有所謂「一切權力」(現行中國憲法)。
在憲政誕生之後,當世界上幾乎所有或文明、或野蠻的國家都陸陸續續制定了或優良、或差強人意、或完全不及格的憲法之後,仍然有許多國家因各種事變,以各種理由,拖延、推諉憲法的全面履行,拒絕落實以分權、限權的方式捍衛人權與自由的憲政主義基本原則,在這樣的國家,假如他們的政體採取了定期、公開、普遍的選舉以更迭政府的制度的話,那麼他們的民主,當然也是非憲政的民主。比如在當今的伊朗、敘利亞、巴基斯坦,在俄羅斯、土耳其、哈薩克斯坦,雖然他們的政體實行定期、公開的民主選舉以更迭政府或國會,但是,他們的政體卻允許存在一位權大無邊的總統(如阿薩德),或允許存在一位權力高於憲法、高於民選總統的精神領袖(如哈梅內伊),或允許存在一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改變憲法規定、調整自己任期的超級總統(如普京)。
而至於所謂「社會主義民主」,雖然它也有一部經常修來改去的憲法,還有「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高大上政治承諾,但它的政體自始至終既不是民主的,更不是憲政的,無論對民主與憲政作何種寬泛的定義,它都與憲政或民主不沾邊。
二、大憲章、美國憲法、憲政主義對政治體制的革命性意義
1215年,英國約翰王頒布《大憲章》,由此開啟了以分權、限權的方式,憲政、法治的原則以保障自由和人權的偉大的英國政治傳統。這份《大憲章》雖然以詔書和特許狀的形式寫成,但它實質上是一份國王與貴族以及其他一切自由人之間帶有社會契約性質的法律文件。它以條款化具文對以往至高無上的王權進行了瓜分和限制,在法律上承認了貴族和自由民不可侵奪的權利,並確立了以法治保障自由的政治大原則。從此,英國的政治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
《大憲章》是英國法治與自由傳統最重要的奠基石之一,但它還沒有、也不足以發展出現代憲政主義。直至1776年起成文憲法在北美各殖民地相繼湧現,1787年產生了人類政制史上劃時代的美國聯邦憲法,1791年產生了以憲法修正案形式存在的美國權利法案,以及1791年產生了法國憲法和附著於其中的1789年人權宣言,憲政主義才獲得了它的全球化機緣並展現其蓬勃的生機。
美國憲法和法國憲法與英國《大憲章》的顯著不同之處在於,它們並不是以法律的形式對一種已經存在並已被確認為合法的國家統治權力進行修正與限制,而是以社會契約、最高法律的形式重新構造一種新型的國家統治權。這一事實表明,人們已經開始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只有依照明文憲法所規定的程序和步驟所締結的國家、所產生的權力、所組建的政府,才是合格的國家、正當的權力、合法的政府。——從那以後,統治合法性的前提就不可能再是「打下來的江山」或「祖宗的江山」,也不可能再是奉天承運的天命神話或教皇的加冕儀式,而首先是統治者和政府的合憲性,也就是說,只有嚴格依照憲法而產生的權力(而不是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才有起碼的資格宣稱它是合法的權力。
憲政主義除了對統治合法性的涵義進行了革命性的更新,在對統治權力的法律限制方面,也交出了革命性的全新答卷。現代憲政主義已不再滿足於如《大憲章》那樣只是對統治權力在個別方面、局部領域進行針對性的限制與約束,而是對國家統治權進行系統性、全方位的限制與約束,且不論這種統治權力是屬於君主的權力,還是屬於人民的權力,都概莫能外必須受到憲政的系統性、全方位的限制與約束。
三、憲政是對民主的規範與制約
毛澤東在延安曾經作過一次關於憲政的演講,毛說:「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毛還說,共產黨人愛憲政,將來也要搞憲政,但他們愛的不是英、法、美那樣「資產階級專政的憲政」——毛輕蔑地說,英、法、美的憲政都是「反動的東西」、是「吃人政治」,也不是國民政府試圖推行的那種假憲政——毛「一針見血」地說,蔣介石、國民黨所宣揚的憲政其實是「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毛澤東將來要搞的憲政,據他說,是什麼「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但是,從1949年建政至今,共產黨已經在中國「專政」了近七十年,別說中國人無緣見識「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是何方神聖,就連憲政二字,從毛到鄧,從江到習,也從此絕口不提了。大概是因為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共產黨對憲政主義尚無基本常識,後來多多少少瞭解了一些憲政ABC,知道憲政與「專政」、與「黨領導一切」乃為天敵,所以,管它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憲政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憲政,就都不敢再提了。連悼詞裡出現憲政二字,也都是不允許的。
回到毛澤東「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毛的意思似乎是說,憲政即等同於民主,二者是同義詞。這種說法,顯然不正確。憲政主義並不一般地排斥立憲君主制或立憲的貴族制、寡頭制,甚至包括「黨主立憲」這樣的設想,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憲政化的。在憲法上規定一種君主權力或政黨權力,為其設定系統化、全方位的法律限制與約束,使其符合憲政法治的基本原則,憲政與君權或黨權這樣的搭配——雖然它們看起來確實有些不搭——在憲政理論上既可以敷衍其詞,在政治實踐中,大概也是可以勉強成立的。
在政治學上,憲政與民主所回答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民主所回答的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問題,即統治權力應該向誰求取、由誰授權,而憲政回答的則是國家權力應該如何組建、如何分割、如何分配、如何制約、如何制衡、如何行使。人類政制史早已表明,憲政未必是民主的,民主更未必是憲政的。傑斐遜曾經抱怨美國憲法不夠民主,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曾經擔憂民意機構挾民主以亂憲政的現象出現(麥迪遜指出,即使是在政治上最先進的英國,立法機關藉民意支持而更改選期、延長任期等反憲政的行為也一再出現)。
憲政與民主豈止是不能互相劃等號,實際上,憲政是對純粹民主的修正與制約。在憲政國家,任何一位政治領袖,即使他真的(真的是真的)有超高的民意支持率,他也不可能獲得憲法所沒有規定的職務頭銜或封號,不可能超出憲法的規定行使其職務權力之外的任何權力,不可能擁有超出憲法規定的延長任期;在憲政國家,哪怕是經由嚴格的民主程序所通過的法律,民選總統依照多數民意所作出的決策,也都有可能被最高法院(或憲法法院)判為違憲而歸於無效。簡而言之,在憲政民主國家,憲政不僅是對民主的保障和支撐,也是對民主的修正和制約。不管是人民的代表、民選的官員,還是「人民」本身,在憲政體制之下,都沒有背離憲法、為所欲為的權力。像中共憲法那樣標榜所謂「一切權力屬於某某」的思路,就是一種反憲政的思路,因為在憲政主義中,決不允許存在由單一勢力、單一機構掌控「一切權力」這種體制。
四、憲政與民主是最佳搭配
雖然憲政與民主並非毛澤東理解的那樣是二語一義,然而,憲政促進了民主,憲政使民主更規範、更健康,為民主的全球化發展開闢了新的渠道和新的空間,卻是不爭的事實:二百多年來,隨著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倣傚美國、法國制定了成文憲法,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認同憲政、實踐憲政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認同民主、接受民主,從而,越來越多的國家憲法裡加入了民主的內容,越來越多的憲政國家也就逐漸變成了真正的、堅定的民主國家。
也許,我們應該說,雖然憲政與民主並非固定搭配,卻是最佳搭配。二百多年裡,拿破崙的立憲帝制崩潰了,德國、日本強化君主權力的立憲君主制垮臺了,英國式君主與議會並駕齊驅的立憲君主制也最終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虛君民主制,......事情就是這樣,一切反民主、不民主、缺民主的政治制度都在憲政主義的檢視、監控之下走向了衰落,唯有民主政體與憲政相得益彰,二者對接得最順利,貼合得最緊密,民主政體在憲政秩序下蓬勃發展,碩果纍纍。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的憲政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而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國家,要麼是憲政國家,要麼或多或少接受了某些憲政主義的制度安排。
2017/10/23
──轉自《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