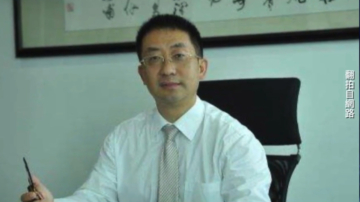編者按:劉華,一個普通中國農民,曾因上訪被關押在馬三家勞教所中,期間想盡辦法偷偷記下《勞教日記》,後用各種方式包括用女性身體將日記祕密帶出,這些高牆內原生態的散亂信息,拼湊出來的內容震驚中外,揭開了勞教所的黑幕一角,成為當年推動勞教制度廢除的關鍵案例之一。
*****
劉華與其丈夫岳永進2002年開始帶領村民維權,揭發村黨支書記非法轉賣土地及貪腐,遭受到連番的打擊報復,地方政府的官官相護,使他們不得不進京上訪,期間,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勞教,劉華還因與導演杜斌合作曝光馬三家勞教所的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遭受刑訊逼供。
這對年輕時就已經是農村萬元戶的夫婦,如今流落北京,被剝奪了基本的生存權。但疾病纏身的劉華說:「我為自己維權,老天就不會餓死我。我就是過窮日子,我也不怕,我沒錢,一年到頭我都不買菜,我可以去揀菜。誰都不站出來,還有正義嗎?我要站出來說話!人人都起來抗爭,那這體制就完蛋了,就會解體。」
一、小時候我背一個小草蛇上學

劉華(本人提供)
我媽說,我是廟裡偷跑的花大姐托生的,不好養活。我出生在1963年黃曆四月初八,這個生日大,是釋迦牟尼佛生日,也是大廟開門的日子,這天生的人苦難多。後來我給村裡老百姓維權,他們就特別恐懼嘛,鎮裡有個書記就拿我的生辰八字,找個女的算命,算命的說,「你別碰她,別跟她爭,她絕對不會服,這個官司打到底也是你們輸,她這個人特別有毅力,會堅持到底的。」這是後來算命人的姐姐傳出來的。
小時候我家地不多,因房前屋後有點樹,就給定了富農。我5歲那陣,吃集體大鍋飯,貧農都上小隊吃大鍋飯,端個碗、盆,分一大鍋粥。我們只能在小隊鐵門邊,扒著小眼看。我也要進去,為什麼他們吃,不讓咱們吃?我媽拽著我,不讓我去,我就哭鬧,我媽說,「不懂事!咱家是富農,人家是貧農。」
我爸1.8米的大個兒,每天一樣出工,在小隊幹活一點不差,只能掙二三等工分,就因為咱家是「富農」。
8歲時,小隊秋天分笤帚草,扒堆,每家一堆,我家那堆小。我問:「干哈他們家大堆,我們家小堆呀?」我媽說:「你不懂,人家是隊長。」「隊長就要大堆?我也要大堆!」我就上小隊隊長家,抱一堆就走,小隊長說:「這死丫頭!為什麼把我家的往你家抱!」我說:「你家堆大,我家堆小。」我哭,怎麼富農就倒楣呀?為什麼他貧農就多要?我媽說,「貧農是好人,這丫頭從小就和別人不一樣,這麼厲害呢!」
小時不知道黨不黨的,就知道政府壞,那時目標就很明確了,知道一定要反抗,不反抗就受欺負。
我剛上學時,說咱是富農孩子,想戴紅領巾都不給戴呀,走道都給你隔開,人家貧農走一伴,路上她們攔著我就打一頓,欺負我,回家還不敢告訴我媽。後來我就背一個小草蛇或者幾個壁虎上學,裝在一個罐頭瓶子裡。她們一打我,我就把蛇往她們身上扔,她們嚇跑了,我再把蛇撿回來,第二天上學再背上,這樣放學我就能一路暢通回家了。
全家七口人,吃不飽,我大哥上山東背豬大油、背大饅頭、背地瓜乾。二哥上黑龍江背黃豆,第一回背了50斤,到車站,人一搜是黃豆,說他「投機倒把」,車站就給截留了。本來就是借錢弄的黃豆,結果空手回來。
12歲時,我放學看遊鬥「四類分子」,一看那不是我二哥嗎?讓人剃禿了,掛個大牌子,寫個「投機倒把」,上面還打個叉,就因為他把槐樹幹削吧削吧就做了鐵鍬把,就給抓了遊鬥!
二、為村民的土地維權

劉華(本人提供)
17歲我就下學了(畢業),然後在小隊幹了幾年活。1984年我22歲結婚,然後一直在瀋陽蘇家屯紅菱鎮的張良村裡做生意。
2002年的時候,村書記不告訴村民,就把村裡一千畝地給賣了。
人家說:「看你們兩口子,好賴還做點生意,比我們有能耐,就幫我們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反映唄。」我雖然不種地,但地也有咱的,他搶、他非法賣,咱是應該要回一點。不就是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嗎?我想得特別簡單。
以前也有人到村委會那個大院反映過土地的事,被村書記打了好幾個耳光,大夥都在怵他。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就去找他,和他理論這個事。
書記說:「我當了24年的大隊書記,我一個吐沫就是一個釘,我就是土皇上。」
「這回就不讓你當釘!」我說,「把你這根針撅折了,你拿什麼穿?我不路過你這針鼻兒,我告到聯合國又怎樣?」「你告吧,你告到聯合國,也要穿過我這個小針鼻兒!」
我說:「我不穿,我越過你,我把你這個針撅折了,拿什麼穿?你從開始賣地到現在,你有什麼法律依據,土地局給你批條了嗎?你拿得出來?沒有,你就是搶!」書記的頭低下來了。
我接著說:「高速公路撥下來這麼多款,還有95年救災款都哪去了?這二十多年,你們貪污這麼多錢,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現在你賣地,也牽扯到我的地了,你要有個說法!還有《土地法》吶!」
村裡老百姓就說,「噢,咋還有《土地法》呀?你咋知道有《土地法》呀?」
村裡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在他們眼裡就是有文化的了,雖然我初中沒念滿,但是我學習非常好,平時愛看書,願意買書,什麼《婦女雜誌》啥的,都看。我上新華書店,買了一大摞《土地法》,村裡一家發一本。我自己花錢買,讓他們學。
那時候村書記他們已經賣了一塊集體土地,都蓋上房子了。我到市裡上訪要說法,說《土地法》怎麼講的,一條一條的,大隊怎麼違章的等等,他們認為我講得有道理,就說:「回去你們扒房子吧,不犯法。」於是我回去我就組織村民,把《瀋陽晚報》、《晨報》都給弄來了,把房子一天就扒完了。
扒完以後,區裡和鎮裡的領導,天天穿個大風衣,戴個大口罩,上那地裡挑小石頭,因為要恢復成農田地,蓋房的磚瓦塊要挑出來嘛。
當時我腦子就有意識:查帳。我去瀋陽會計所問,他們說查帳需要費用,於是我們就抬(村民集資)了6萬塊錢,二分錢利息抬的高利,讓我丈夫代簽借用。2002年時,村民已經選我丈夫當了村長,我丈夫是村長、法人,他有權利去審那個帳,所以說從頭到尾我們都是公允的,是合法的。
還得把帳搶出來,會計師才能審查。曾經有的村去查帳,大隊叫人給打成植物人了。所以搶帳那天,他們說「劉華你可要掂量好,搶帳就是你拿人家腦袋,人家就會拿你腦袋的」。當時我就想,可不能出差錯,出差錯我不就廢了,孩子還小呢。
我們先去跟他們要帳,不給。我就讓那書記坐在沙發上,讓幾個人看著他,我再把所有的電話全給薅下來了,讓電話裡外不通。
搶了帳,裝上轎車,往村裡小路上走,不上大道,轉了幾個地方,然後就又換麵包車,一路換了四次車,才把這一車將近三十玻璃絲(塑料)袋子的帳目,全部拿到了瀋陽榮正會計所。十二個審計人員審了大半年,查出我們村幹部出賣集體土地、違法攤派、侵吞村民水電費和侵占救災款等,審計發現有問題的金額達260餘萬元,涉及前任書記王景財及現任書記劉家安等。列出審計報表報到公安部後,公安部就說要抓大隊書記,但大隊書記給公安送了一萬斤大米及數萬元錢,公安部就不了了之了。
但這塊地沒有讓他賣成。俺們村靠法律維權,真的把官司給打贏了。
區裡頭還是不甘心,還要賣這塊地,說不賣給老張,也要賣給老李,還要賣。公章在大隊裡,我半夜就去村委會,把公章偷回來,找個地方挖個坑埋起來了。我丈夫是村長,他們要是搶過公章,扣上公章把地就給賣了,我丈夫也有罪過啊。
哪想到他們會設計陷害我丈夫呢。2002年12月12號,那時下雪了,外面全上凍了。村裡一個打更的,故意把村委辦公室的地用濕拖布拖,之後把門窗打開,水磨石瓷磚的地,就凍上了薄薄一層冰。然後他打電話給我丈夫,說漏水讓我丈夫趕去處理。我丈夫趕到大隊,哪知道地上有冰,大步流星走過去,一茲溜腿就撞到大隊一樓中間的柱子上,整個膝蓋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三級殘疾,左腿和右腿差2寸,不能長時間走路了。後來問那個打更的,為什麼大冷天拖地還開窗?他說是書記讓他幹的。
書記還想要公章,說有個婦女要開流產介紹信,要用公章,讓我上大隊去。我去了說:「村裡老百姓選的婦女主任不用,你大隊書記又當婦女主任又當大隊書記。你在違法。你看這個婦女要個避孕套哇、要流產哪、要帶環,還要找你大隊書記,多彆扭哇。」我說「你要那些避孕套干哈呀」?他說我寒磣他,一拳把我打倒,當時我就昏過去了。醒過來我就去了他家,脫了外衣就上他家炕,躺下睡覺。我說:「我不走了,今天就跟你過了,你不是把我丈夫的腿害殘了嗎?我就跟你過了。」他一看確實把我給打傷了,他就報警。派出所來了,警察說:「劉華,走,上醫院給你看病去,你不能在人家待著。」我說我丈夫讓他害殘了,他還把我打了,我就跟他過了,我就不跟我丈夫過了。他們傻了,都過來哄我上醫院去看病。
一天半夜12點,我正睡覺呢,一個電話把我弄醒:「我告訴你劉華,你再告,我把你腦袋拿下來!」是大隊書記的侄子張富強。我馬上打了110,010-110,北京的110。北京轉到了省公安廳。省公安廳的公安開著七八輛警車就去了他家。半夜1點,他家轉圈全是警燈閃,張富強一下子就毛了。警察把門踢開,進門就拽他脖子:「你他媽大半夜去打恐嚇電話,你知道劉華把電話打到哪了?打到北京,北京轉到省公安廳了,我們還活不活了,為你小破事省公安廳都別睡覺!」霹靂吧啦把他揍了一頓。
後來書記又打了我一次,經過瀋陽市法醫鑑定「輕傷」,「輕傷」他就得坐牢啊,但官官相護,派出所所長包庇他,也不追究,就給他一個「警告」完事,還弄個筆誤,說我把大隊書記打了,我還得給大隊書記拿二百塊錢。這事誰能服哇,我被打了,我還要給他錢!我當然要告他!我就上北京告狀。那時我丈夫正在當村長,到北京和我待了一個多月就回去了。(待續)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
劉華與其丈夫岳永進2002年開始帶領村民維權,揭發村黨支書記非法轉賣土地及貪腐,遭受到連番的打擊報復,地方政府的官官相護,使他們不得不進京上訪,期間,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勞教,劉華還因與導演杜斌合作曝光馬三家勞教所的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遭受刑訊逼供。
這對年輕時就已經是農村萬元戶的夫婦,如今流落北京,被剝奪了基本的生存權。但疾病纏身的劉華說:「我為自己維權,老天就不會餓死我。我就是過窮日子,我也不怕,我沒錢,一年到頭我都不買菜,我可以去揀菜。誰都不站出來,還有正義嗎?我要站出來說話!人人都起來抗爭,那這體制就完蛋了,就會解體。」
一、小時候我背一個小草蛇上學

劉華(本人提供)
我媽說,我是廟裡偷跑的花大姐托生的,不好養活。我出生在1963年黃曆四月初八,這個生日大,是釋迦牟尼佛生日,也是大廟開門的日子,這天生的人苦難多。後來我給村裡老百姓維權,他們就特別恐懼嘛,鎮裡有個書記就拿我的生辰八字,找個女的算命,算命的說,「你別碰她,別跟她爭,她絕對不會服,這個官司打到底也是你們輸,她這個人特別有毅力,會堅持到底的。」這是後來算命人的姐姐傳出來的。
小時候我家地不多,因房前屋後有點樹,就給定了富農。我5歲那陣,吃集體大鍋飯,貧農都上小隊吃大鍋飯,端個碗、盆,分一大鍋粥。我們只能在小隊鐵門邊,扒著小眼看。我也要進去,為什麼他們吃,不讓咱們吃?我媽拽著我,不讓我去,我就哭鬧,我媽說,「不懂事!咱家是富農,人家是貧農。」
我爸1.8米的大個兒,每天一樣出工,在小隊幹活一點不差,只能掙二三等工分,就因為咱家是「富農」。
8歲時,小隊秋天分笤帚草,扒堆,每家一堆,我家那堆小。我問:「干哈他們家大堆,我們家小堆呀?」我媽說:「你不懂,人家是隊長。」「隊長就要大堆?我也要大堆!」我就上小隊隊長家,抱一堆就走,小隊長說:「這死丫頭!為什麼把我家的往你家抱!」我說:「你家堆大,我家堆小。」我哭,怎麼富農就倒楣呀?為什麼他貧農就多要?我媽說,「貧農是好人,這丫頭從小就和別人不一樣,這麼厲害呢!」
小時不知道黨不黨的,就知道政府壞,那時目標就很明確了,知道一定要反抗,不反抗就受欺負。
我剛上學時,說咱是富農孩子,想戴紅領巾都不給戴呀,走道都給你隔開,人家貧農走一伴,路上她們攔著我就打一頓,欺負我,回家還不敢告訴我媽。後來我就背一個小草蛇或者幾個壁虎上學,裝在一個罐頭瓶子裡。她們一打我,我就把蛇往她們身上扔,她們嚇跑了,我再把蛇撿回來,第二天上學再背上,這樣放學我就能一路暢通回家了。
全家七口人,吃不飽,我大哥上山東背豬大油、背大饅頭、背地瓜乾。二哥上黑龍江背黃豆,第一回背了50斤,到車站,人一搜是黃豆,說他「投機倒把」,車站就給截留了。本來就是借錢弄的黃豆,結果空手回來。
12歲時,我放學看遊鬥「四類分子」,一看那不是我二哥嗎?讓人剃禿了,掛個大牌子,寫個「投機倒把」,上面還打個叉,就因為他把槐樹幹削吧削吧就做了鐵鍬把,就給抓了遊鬥!
二、為村民的土地維權

劉華(本人提供)
17歲我就下學了(畢業),然後在小隊幹了幾年活。1984年我22歲結婚,然後一直在瀋陽蘇家屯紅菱鎮的張良村裡做生意。
2002年的時候,村書記不告訴村民,就把村裡一千畝地給賣了。
人家說:「看你們兩口子,好賴還做點生意,比我們有能耐,就幫我們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反映唄。」我雖然不種地,但地也有咱的,他搶、他非法賣,咱是應該要回一點。不就是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嗎?我想得特別簡單。
以前也有人到村委會那個大院反映過土地的事,被村書記打了好幾個耳光,大夥都在怵他。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就去找他,和他理論這個事。
書記說:「我當了24年的大隊書記,我一個吐沫就是一個釘,我就是土皇上。」
「這回就不讓你當釘!」我說,「把你這根針撅折了,你拿什麼穿?我不路過你這針鼻兒,我告到聯合國又怎樣?」「你告吧,你告到聯合國,也要穿過我這個小針鼻兒!」
我說:「我不穿,我越過你,我把你這個針撅折了,拿什麼穿?你從開始賣地到現在,你有什麼法律依據,土地局給你批條了嗎?你拿得出來?沒有,你就是搶!」書記的頭低下來了。
我接著說:「高速公路撥下來這麼多款,還有95年救災款都哪去了?這二十多年,你們貪污這麼多錢,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現在你賣地,也牽扯到我的地了,你要有個說法!還有《土地法》吶!」
村裡老百姓就說,「噢,咋還有《土地法》呀?你咋知道有《土地法》呀?」
村裡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在他們眼裡就是有文化的了,雖然我初中沒念滿,但是我學習非常好,平時愛看書,願意買書,什麼《婦女雜誌》啥的,都看。我上新華書店,買了一大摞《土地法》,村裡一家發一本。我自己花錢買,讓他們學。
那時候村書記他們已經賣了一塊集體土地,都蓋上房子了。我到市裡上訪要說法,說《土地法》怎麼講的,一條一條的,大隊怎麼違章的等等,他們認為我講得有道理,就說:「回去你們扒房子吧,不犯法。」於是我回去我就組織村民,把《瀋陽晚報》、《晨報》都給弄來了,把房子一天就扒完了。
扒完以後,區裡和鎮裡的領導,天天穿個大風衣,戴個大口罩,上那地裡挑小石頭,因為要恢復成農田地,蓋房的磚瓦塊要挑出來嘛。
當時我腦子就有意識:查帳。我去瀋陽會計所問,他們說查帳需要費用,於是我們就抬(村民集資)了6萬塊錢,二分錢利息抬的高利,讓我丈夫代簽借用。2002年時,村民已經選我丈夫當了村長,我丈夫是村長、法人,他有權利去審那個帳,所以說從頭到尾我們都是公允的,是合法的。
還得把帳搶出來,會計師才能審查。曾經有的村去查帳,大隊叫人給打成植物人了。所以搶帳那天,他們說「劉華你可要掂量好,搶帳就是你拿人家腦袋,人家就會拿你腦袋的」。當時我就想,可不能出差錯,出差錯我不就廢了,孩子還小呢。
我們先去跟他們要帳,不給。我就讓那書記坐在沙發上,讓幾個人看著他,我再把所有的電話全給薅下來了,讓電話裡外不通。
搶了帳,裝上轎車,往村裡小路上走,不上大道,轉了幾個地方,然後就又換麵包車,一路換了四次車,才把這一車將近三十玻璃絲(塑料)袋子的帳目,全部拿到了瀋陽榮正會計所。十二個審計人員審了大半年,查出我們村幹部出賣集體土地、違法攤派、侵吞村民水電費和侵占救災款等,審計發現有問題的金額達260餘萬元,涉及前任書記王景財及現任書記劉家安等。列出審計報表報到公安部後,公安部就說要抓大隊書記,但大隊書記給公安送了一萬斤大米及數萬元錢,公安部就不了了之了。
但這塊地沒有讓他賣成。俺們村靠法律維權,真的把官司給打贏了。
區裡頭還是不甘心,還要賣這塊地,說不賣給老張,也要賣給老李,還要賣。公章在大隊裡,我半夜就去村委會,把公章偷回來,找個地方挖個坑埋起來了。我丈夫是村長,他們要是搶過公章,扣上公章把地就給賣了,我丈夫也有罪過啊。
哪想到他們會設計陷害我丈夫呢。2002年12月12號,那時下雪了,外面全上凍了。村裡一個打更的,故意把村委辦公室的地用濕拖布拖,之後把門窗打開,水磨石瓷磚的地,就凍上了薄薄一層冰。然後他打電話給我丈夫,說漏水讓我丈夫趕去處理。我丈夫趕到大隊,哪知道地上有冰,大步流星走過去,一茲溜腿就撞到大隊一樓中間的柱子上,整個膝蓋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三級殘疾,左腿和右腿差2寸,不能長時間走路了。後來問那個打更的,為什麼大冷天拖地還開窗?他說是書記讓他幹的。
書記還想要公章,說有個婦女要開流產介紹信,要用公章,讓我上大隊去。我去了說:「村裡老百姓選的婦女主任不用,你大隊書記又當婦女主任又當大隊書記。你在違法。你看這個婦女要個避孕套哇、要流產哪、要帶環,還要找你大隊書記,多彆扭哇。」我說「你要那些避孕套干哈呀」?他說我寒磣他,一拳把我打倒,當時我就昏過去了。醒過來我就去了他家,脫了外衣就上他家炕,躺下睡覺。我說:「我不走了,今天就跟你過了,你不是把我丈夫的腿害殘了嗎?我就跟你過了。」他一看確實把我給打傷了,他就報警。派出所來了,警察說:「劉華,走,上醫院給你看病去,你不能在人家待著。」我說我丈夫讓他害殘了,他還把我打了,我就跟他過了,我就不跟我丈夫過了。他們傻了,都過來哄我上醫院去看病。
一天半夜12點,我正睡覺呢,一個電話把我弄醒:「我告訴你劉華,你再告,我把你腦袋拿下來!」是大隊書記的侄子張富強。我馬上打了110,010-110,北京的110。北京轉到了省公安廳。省公安廳的公安開著七八輛警車就去了他家。半夜1點,他家轉圈全是警燈閃,張富強一下子就毛了。警察把門踢開,進門就拽他脖子:「你他媽大半夜去打恐嚇電話,你知道劉華把電話打到哪了?打到北京,北京轉到省公安廳了,我們還活不活了,為你小破事省公安廳都別睡覺!」霹靂吧啦把他揍了一頓。
後來書記又打了我一次,經過瀋陽市法醫鑑定「輕傷」,「輕傷」他就得坐牢啊,但官官相護,派出所所長包庇他,也不追究,就給他一個「警告」完事,還弄個筆誤,說我把大隊書記打了,我還得給大隊書記拿二百塊錢。這事誰能服哇,我被打了,我還要給他錢!我當然要告他!我就上北京告狀。那時我丈夫正在當村長,到北京和我待了一個多月就回去了。(待續)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