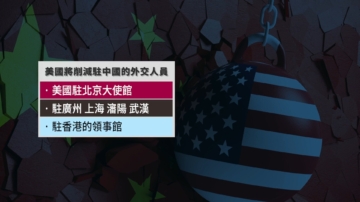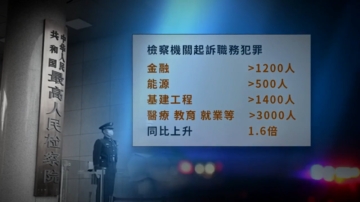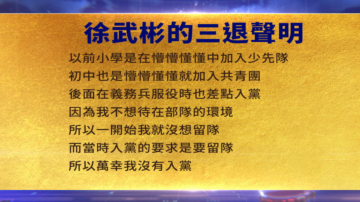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12月22日訊】中共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醜聞,備受輿論關注。12月2日下午,朱軍性騷擾案在北京海淀區法院開庭,但法庭拒絕受害人弦子(網名)公開庭審的申請。12月21日,弦子發表長文公開當年朱軍性騷擾的全部經過,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得到公正的對待。
以下是《弦子:2014年6月9日發生在化妝室的全部經過》全文:
從2018年主動站出來到遞交法院申請,我一直有一個最堅定的訴求:希望可以得到公開審理。
希望公開審理,是因為我相信我的經歷、我的誠實,可以得到公正的對待。
雖然,從2014年到如今,我已經向公安、向法院講述過許多次經過,重複這件事,對我來說本身就是折磨;雖然,無論我如何迴避,被性騷擾的過程依然給我一種性的恥感——在所有人都看過我的當下。我總擔心人們看到我時會想起我在化妝室的狼狽與弱小,性侵受害者的身份,會永遠成為我的標籤。
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想要公開審理,想要將我的痛苦、我的遭遇攤開給所有人看。因為,個人感受必須為正義讓步,我願意公開審理,願意公開全部證據、公開我被朱軍性騷擾的經過,公開所有那些恥辱的細節。
只是,從2018年至今,我們要求公開審理的訴求從未得到過批准,出於對法院、法律的尊重,我恪守諾言,保持沉默。出乎意料的是,近日卻不斷有人對當年案發情況進行斷章取義和惡意歪曲,變成對事實的詆毀、對我的辱罵。
雖然痛苦,但若要求索正義,就必須坦誠,因為時間已經過去六年,記憶難免會有疏漏,但我所回憶、所講述的,都是發生在我身體上的事實。
哪怕我要對所有人,做一次公開的「筆錄」。
1.
2014年6月9日,正在藝術人生欄目實習的我,需要完成導創老師布置的作業:將實習經歷拍成記錄片,老師還強調,我們最好能夠採訪到重要人物,就比如朱軍。
那天,先於我來到臺裡的實習生商同學說要去化妝室找朱軍,因為知道他和朱軍接觸較多,我告訴他我想要採訪朱軍完成作業,商同學讓我和他一起去化妝室,幫我找機會採訪朱軍。
當時,朱軍獨自坐在化妝室,身邊有一把空椅子,商同學坐著與他交流,我則站在一邊等待。但沒想到的是,只在化妝室呆了一分多鐘,商同學就有事要走,我理所當然的打算和他一起離開,但就在我們走到門口時,商同學在門口笑說既然我沒事,可以留下來陪朱軍聊一會兒,說完這句,他就先離開了。
我為什麼會同意留在那間化妝室?因為當著朱軍的面,我沒有合適的拒絕理由、因為我需要採訪他才能完成作業,也因為朱軍是全國最有名的主持人、我們身處工作場合,我根本不覺得這會是一件危險的事。
在此之前,我從未在任何場合和朱軍一對一說過話,交流僅限於在錄製現場和其他人一起向他打招呼,我在實習時還看到過他的妻兒,他對我來說是一個和我父親差不多年紀的長輩。
於是我留在了化妝室,還想找機會採訪他。但在一開始,朱軍就主動向我提問,打過招呼後,他問我是不是老師帶來的實習生,還告訴我他認識老師很多年,在她沒結婚時就見過她的丈夫。
除了聊老師、學校,朱軍還注意到我脖子上掛著一臺索尼的微單相機,那是我為了拍攝找室友借來並隨身攜帶的,因為那時微單還算少見,所以朱軍還讓我把微單取下來給他看,並拿在手裡把玩了一陣,還用這部相機對著鏡子給我和他拍了照片。有人故意在這件事上撒謊,說「筆錄中顯示,弦子還用自己的手機與朱軍對著鏡子合了個影。」明明是朱軍拍攝了照片,筆錄中也是明白如此。利用筆錄不公開,移花接木,惡意製造這些虛假的信息。
一直到這裡,我雖然比較緊張,但因為朱軍隨和鬆弛,甚至算得上親切,所以我還在想接下來可以提出採訪要求。
直到朱軍主動問我是不是想要留在臺裡工作,他可以給幫忙,我才開始覺得奇怪:能留在央視工作非常難,我從沒聽說我的師哥師姐實習時能轉正,更何況我的表現並不突出,他為什麼要幫助我?我坦誠的告訴他我打算大四去考研,並不打算工作。朱軍又開始告訴我他認識那所學校的校長,並且關係相當熟。
談話到這裡,我已經感到不安,為什麼朱軍一直主動對我提供資源與好處?不管留在臺裡還是考研,都是靠自己努力去做的事,尤其是考研要先通過專業課筆試,找校長有什麼意義?我向來不喜這類人情世故,更何況接受朱軍的幫助,我要用什麼去回報呢。
朱軍繼續提到當時央視新樓已經建成,問我去過沒有,說可以帶我去,還說那附近有很多餐廳,可以帶我去。他甚至還提到畢業之後我想要留在北京的話,也可以給我幫忙。我那時雖然只有大三,毫無社會經驗,但總能察覺出他話語中對我們關係的設想是非常越界的,所以一直想要含混過去——如果我表現的對他的提議不屑一顧,那大概率會得罪到他,我只能委婉拒絕:我現在還是大三,想從事電影而不是電視行業,並不需要幫助。
朱軍不理會我一直的否定態度,又說我的臉型像她太太,知道我是南方人後還說南方姑娘比較水靈。他拉著我的手要給我看手相,還告訴我根據手相來看我不應該靠近水——我是武漢人,幾乎就是在長江邊長大,這句話讓我特別詫異且可笑,一直記到了今天。
在朱軍拉住我的手後,我雖然在他說話時把手抽了回來,卻並沒有當場駁斥過他。
可是,在當時,作為一個大三的實習生,我太害怕如果我不禮貌,就會得罪他,如果我得罪朱軍,得罪這位藝術人生的主持人與總製片人,我就會被趕出實習組、失去完成期末作業的機會。在我們系,導創課作為核心課程,掛科有可能影響學位證,我大學的成績一直都很好,四年沒有掛過任何一門課,我根本無法想像我拿不到學位證會怎麼樣。所以即使是朱軍不經過我的同意,拉著我的手要給我看手相,我的第一反應還是我可以忍、我應該忍,為了我的學業,我不能夠得罪他。
而當朱軍開始對我有進一步舉動,開始將手放在我的身體上,並隔著衣服猥褻我時,我則完全整個人都被震驚、恐懼緊緊攥住,陷入了應激狀態,完全不知道怎麼反應。
在朱軍一開始讓我把門關上的時候,我還下意識留了縫隙,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會在化妝室、會在我們第一次談話時直接碰我的身體。
當時只有二十一歲的我,還沒有展開過一段正式的戀愛,更何況是被一個年紀和我父親一樣的男性強迫觸摸身體,甚至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性侵就是被陌生歹徒強暴、在公交地鐵被鹹豬手,我根本不知道女性可能被一個德高望重的名人、在工作的場合觸碰身體。
在那樣的時刻,我的大腦完全是一片空白的,能夠想到的是我要讓他停止,然而我能做的只是緊緊縮在椅子上。當他的手在我身上觸摸時,我用胳膊擋開他的手、當他想要把我從椅子上拽向他時,緊緊的拉住我的椅子,不讓我的身體離開椅子,因為那樣我就會有更多的身體部位可能被他觸摸。
我從未想過會被幾乎陌生的男性觸摸胸部、大腿,巨大的恥感在那時候籠罩著我,我害怕、想哭,但在那個瞬間的我,沒辦法想出任何對策。
為什麼不對抗?可我不敢大聲斥責他,因為我害怕被人聽見、我也不敢反手去打他,因為我害怕他會對我使用暴力。我從沒有和別人打過架,更何況一個比我年長、高大那麼多的男性。
為什麼不逃跑?可我太害怕,我擔心如果朱軍拉住我不讓我離開怎麼辦?我應該掙脫?應該喊出來嗎?可我不敢,我甚至害怕如果動靜太大,我被別人看到朱軍將手放在我的身上,那樣會發生什麼?我會不會被羞辱?這件事會不會被所有人知道?其他工作人員會怎麼看我?一起實習的同學會怎麼看我?如果鬧大了,我們學校的師生又會如何看我?
「被性騷擾並不是受害者的錯」這句話說出來簡單,可對二十一歲的我來說,在那個化妝室被朱軍觸摸時,能感受到的就是巨大的恥辱、想要哭、想要把頭埋進土裡、想要一切都沒發生過。
很多人造謠說,在性騷擾發生的過程中,有快十人、十幾人進入過化妝室,然而這是徹底的造謠——在性騷擾發生的時候,化妝室進來的只有四人:跟隨朱軍多年的、兩位分別姓李、張的製片、助理,和兩位觀眾。
只有這四位,其他都是春秋筆法的造謠,在朱軍斷續實施猥褻行為的期間,沒有其他人進入過化妝室。最後節目嘉賓帶著人來,是我趁機擺脫朱軍的機會,性騷擾的行為都發生在嘉賓進入化妝間之前。
我為什麼不在這兩位製片、助理進入化妝室的時候逃跑?因為即使我只來這裡實習了幾個月,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這兩位中年男性,是整個節目組裡和朱軍關係最緊密的人。
這兩位製片人、助理,要和朱軍一起出差、一起出席活動和飯局、要找朱軍簽合同與報銷單、要傳達完成朱軍分配的工作。我見過他們溝通時的狀態,我知道他們跟朱軍的利益關係是牢牢綁定在一起的。作為節目組總製片的朱軍,可以影響他們在臺裡的工作和發展。
對他們來說,我不過是一個最無足輕重的實習生,朱軍則是他們的領導與利益共同體,如果我當著他們的面說出我正在被性騷擾、如果我當著他們的面指責朱軍,我能得到什麼樣的對待呢?我能想到是,他們可能會包庇朱軍,讓他繼續傷害我。
他們自己進來的兩次時間裡,停留的時間都十分短暫,在那樣短暫的時間裡,性的恥感、對他們的不信任、害怕事情被鬧大我被公開羞辱、害怕失去學業。所以,我不願意讓這兩個中年男人知道朱軍對我的意圖。在他們進來時,我甚至深深的低下頭,想讓頭髮遮住我自己,不讓他們看到我的表情,不給他們造謠中傷我的機會。
我沒有對著朱軍的工作人員呼救,並不意味著我不想反抗、停止朱軍的性騷擾行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已經用了所有我能夠想到的方法讓他停下:我用手推拒他、我試圖和他溝通讓他停止動作。
不一會兒,有兩位觀眾敲門,請朱軍簽名,可我看到朱軍站在門口,我那時太過恐懼慌亂,不敢走上前推開他離開化妝室。這個過程結束的非常快,我還沒做好準備,那扇門就又被合上。在朱軍試圖繼續時,我不得不重新坐回椅子上,因為我需要坐著,坐著身體展開的部分沒有那麼多,他也很難拉扯我。可他的行為還在不斷升級,甚至強吻了我:這件事直到今天都在折磨著我,因為我不願用這麼美好的詞描述他的行為,卻也別無他法。
直到朱軍試圖把手伸進我的裙子時,我已經接近崩潰,渾身都在發抖——朱軍看出了這一點,大概是終究怕我喊出來鬧出來,他停手並沉著臉坐回椅子。那時候我手腳發軟,已經說不出來話了。
我並非不想離開,即使那時候的我已經完全處於應激狀態裡、想要痛哭卻一直在發抖、喉嚨顫抖就好像失聲一樣、滿腦子都是羞恥與畏懼,然而即使到了這樣的情況,我也沒有放棄離開。幸運的是,節目嘉賓帶著很多工作人員走進了化妝室,朱軍站起身和他溝通。直到嘉賓進來和他交談了一會兒,我大腦才漸漸恢復清醒,察覺到這是可以離開的機會,低著頭往門口走——我以為朱軍不會在嘉賓面前制止我,可時至今日,我還記得朱軍看到我要走時說了一聲「你要走啊?」,我愣住了,過了幾秒才用顫抖的聲音說:「我要走。」
我對那句話印象那麼深,是因為我無法相信,即使我表現的那麼痛苦、那麼抗拒,他依然覺得我應該留在那個地方,他如此蔑視我,以為我軟弱且膽小,這種恥辱感直到今天還在折磨著我。
而我之所以只能在嘉賓來的時候離開,是因為我知道相比張、李兩位朱軍下屬,這位嘉賓是節目組的外人,和朱軍沒有利益關係、甚至在演藝界的地位和朱軍平起平坐,朱軍會在意他的看法和對自己的評價。而且嘉賓自己的工作人員,對朱軍來說也是不可控的存在,即使他們不會幫助我,但朱軍在他們面前也要注意舉止,否則總會有傳言流出。
所以,在嘉賓進來之後,雖然我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說出我的遭遇,我還是抓住了這個機會逃了出去。
2.
在之前我就說過,2018年我寫下長文時,原因只是我的一位姐姐公開了自己讀書、工作時被性侵的經歷,在看到姐姐的自述後,我就留言告訴她,我會把我的經歷也寫出來——我希望讓她知道,她的勇氣是有意義的,我會傳遞下去。
那天,我只是想寫下我的經歷,安慰姐姐,也告訴我認識的女生,被傷害不是我們的錯。在寫下那篇記錄時,已經距離報案過去四年,因為我報案從未得到過書面材料,所以我也缺少依據來確認回憶的全部細節,我將那位匆匆一瞥的中年歌唱家嘉賓,誤寫成了閻維文老師,直到去年庭前會議看到筆錄,才確認其實那天進入化妝室,讓我找到機會離開的其實是郁鈞劍老師。
我一直想要為這件事帶給閻維文老師的麻煩公開道歉,因為我在文章中確實記錯了。時隔四年,記憶錯誤。而我當年在派出所的筆錄中說的,就是郁鈞劍老師。在此對閻維文老師造成的困擾表示歉意;對郁鈞劍老師表達遲到六年的感謝——您不知道,您無意中挽救了一個女孩,讓她免於在不知所措中被繼續傷害。
從我被商同學帶進化妝室(18時12分6秒),到我獨自在樓道並神情低落的用紙巾擦嘴(18時57分17秒),這是我在化妝室的全部時間。而這中間,有相當大一部分時間是一開始朱軍和我的溝通交流,並不是性騷擾發生的全部時間。
在性騷擾的過程中,也根本沒有近十人走進化妝室我卻任由性騷擾繼續發生的情況——我已經說出了化妝室的全部經過,我為什麼在李、張二人與觀眾這三次進入化妝室時不逃跑,而是等到嘉賓進入化妝室才找機會離開。
在離開那間化妝室後,我給我的姑姑打了電話,姑姑要我忍下來,我回學校告訴了室友,室友也要我忍下來,她們要我為了學業沉默,於是我甚至在第二天又重新回去實習。
但當回到性騷擾發生的空間、看到節目組的員工、看到帶我去化妝室的實習生、看到那間化妝室時,恐懼與恥辱才終於逐漸變為憤怒。我意識到繼續待在這個空間、繼續實習帶給我的折磨實在太大了,一想到自己還有可能再次陷入那種處境,我就覺得自己寧可死去。
我一個一個的打電話,可無論高中還是大學好友都要我忍氣吞聲,直到我終於找到另一位大學老師,她是第一個告訴我要報警的人,也是在後來陪我報警、保護我讓我學業不至於被打擊報復的人。
3.
在我二十一歲,一個人躲在走廊一次次打電話時,或許那時心裡想的是痛苦與折磨,但總有一點微弱的勇氣,在告訴我這件事不是我的錯,我值得一個正義的對待。這微弱的勇氣支持著我繼續,直到終於有人告訴我應該報警。
2014年6月10日,我人生第一次走進派出所、第一次做筆錄時,我忍住痛苦與恥感,不得不詳細描述在那個化妝室發生的一切,盡力誠實而有尊嚴的保護自己。可我沒有想到,這樣的經歷、這樣的記錄,卻會被曲解成「被摸了四五十分鐘、有近十人進來還不跑」的故事。
我沒有想到,當年那個痛苦又慌張、二十一歲的我,會被那麼多人指責「編色情小說」、「那麼多人來都不跑就是在迎合」、「摸四十分鐘沒有被摸破皮嗎」、「你的臉和身材值得被摸那麼久」、「一男一女那麼長時間怎麼可能只是摸」、「十幾個人進來你不會跑嗎」……
在那些嘲笑聲中,什麼樣的受害者才可以被稱為完美呢?在封閉空間提前預料到性騷擾並錄音錄像?在被侵害的時候激烈搏鬥留下證據?在事發後立即報警公開並尋死覓活?
可對二十一歲的我來說,我沒有預料到化妝室會發生性騷擾所以我沒能錄音錄像、我害怕得罪朱軍會影響學業所以不敢搏鬥、我擔心別人會包庇他的作為所以不敢求助、我知道嘉賓與朱軍不存在利益關係所以逃脫、我太過害怕所以在第一天不敢聲張、我得到鼓勵終於去報警——所有這些過程對於二十一歲的我來說就是自然發生的,我的害怕與勇敢都是我的一部分。
我相信有過同樣感受的女性一定能體會我當時的恐懼。關於封閉空間裡,身體被侵犯的羞恥經歷,被那麼多人施加色情與戲謔的想像,無論我多麼不願意承認這恥感,也要說我確實會被擊潰。我不願去想有多少人將我在那個化妝室的屈辱經歷扭曲成色情小說一樣的意淫段子——女性被性騷擾是色情小說嗎,為什麼我的眼淚會成為其他人的笑料呢?
從14年到如今,6年的時間裡,我對那個封閉空間遭遇的被侵害經歷始終誠實,這就是我保護自己尊嚴的方式,也已經是我竭盡全力所能做到的完美。
我在2014年就已經盡快報案並全力配合了調查,在四年後站出來,從未故意撒謊、隱瞞任何事。我當初的畏懼與勇敢是證據,身體被侮辱的經歷與隨之而來的恥感是證據。即使這意味著我要在所有人面前詳細的回憶我的人格與身體被侵犯的細節,讓我再次因此備受折磨,這痛苦也是我的證據。
以上,是我在六年之後,終於向公眾作出的公開「筆錄」。是發生在我身體上的經歷,是我的痛苦與恥辱。我會在接下來公開更多相關信息,讓大家看到這兩年來我經歷的、我正在經歷的。我對我所說的一切負責。
從始至終,我會用我的軟弱與勇敢,用我的誠實與痛苦,來提出我的問題,來尋找我的答案。
(責任編輯:唐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