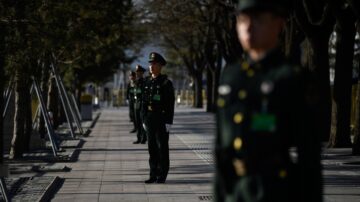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9月6日讯】【编辑语】 谭松,重庆人,生于1955年11月。两岁时其父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分子”,送往重庆长寿湖劳改。在随后的三年大饥荒中,外公因病无钱治疗去世,妹妹饿死,外婆自杀。幸存下来的谭松,下过乡,上过大学,36岁时评为英语副教授,发表过专着、辞典、译着、散文、杂文等300多万字,曾担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中华手工》杂志主编,采访过约400多名各类人士。其中,谭松采访了近百名长寿湖的幸存右派,写成了约50万字的采访录《长寿湖》,收集到珍贵的几百张照片。为此,他曾被当局抓捕关押过。 《1962年,我的外婆》是谭松在2007年的一篇纪实作品,表达了他对外婆的思念和对那个年代的控诉。
《1962年,我的外婆》
又是清明,年近80 的妈妈带着我们来到外婆的坟前。
外婆的坟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山坡上,后面,就是八年抗战时蒋委员长住过的黄山。
妈妈摆上供果,点燃红烛,伫立垂首。
纸钱烧起来,红红的火光,黑黑的墓碑,青烟起处,山风回旋。
泪水,从妈妈眼里滚出来,她又想起那个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在长江边一个叫马鞍山的半山坡上。出门,就是陡斜的石坡,长江,在脚下日日夜夜奔流。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家家户户不准自己做饭,政府不供应煤,甚至连锅都被收缴了,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去吃“集体伙食”。不去,不仅无法生存,而且还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险。
外婆要去的那个公共食堂在山坡下的江边上,距那个着名的“龙门浩月”不远。
外婆是“旧社会”来的女人,小时裹过脚,“三寸金莲”行走起来原本不便,再加上长期饿饭,走路就更显吃力。然而,一日三餐,她必须下到江边,领取二两饭,然后沿着那陡斜的石板山路一步步挪回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下着雨,看见妈支着一根竹竿,挎着个布包,布包里面是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妈妈颤颤巍巍,面黄肌瘦,吃力地往上挪动脚步。我一下子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对我说。
终于,公共食堂的人也看到外婆走不动了,于是他们说:“裴婆婆(我外公姓裴),反正你每天六两粮,我们给你做一个六两的馒头,你一次性领回去,这样每天你就只走一趟。 ”
也只有这样了,去食堂来回下坡上坡,不安全不说,仅运动量大,就不利于对那二两粮的珍惜。
可是,很快发现,这也不是好办法。一个六两的馒头切成三份,每份也只有拳头大,更要紧的是,份量明显不足。
外婆不吭一声,她是传统文化打造的温良恭俭型女人,一辈子谦和恭顺,从没同人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何况,人家还是为她着想呢。
她的三个小孙儿,其中包括食欲极旺的我,每天从幼儿园回来,虽说已吃过晚饭,总渴望再从外婆那儿捞点吃的。外婆不忍面对三双贪渴的眼睛,每天,她都把馒头切下三片,平摊着放在盘子里,用碗盖上,等我们回来。
记得有一次,外婆拿出一个土豆,土豆很小,不便再分,于是外婆叫我们轮流把土豆含在嘴里吮吸,以延长“吃”的美妙过程。姐姐很守规矩地照章执行,吮吸之后吐给了我。我含在嘴里,实在忍不住,一口咬下去。
旁边紧盯着我的弟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那时,六岁的我像一条饥饿的小狼,野性十足地搜寻食物,我把一个六岁儿童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来搜寻外婆可能的收藏。一次,家里来了一个亲戚,外婆竟然冲了一小碗炒面招待他。那个香味直浸润入我骨子。可惜,任凭我痴痴地立在一旁双眼圆睁口水长流,亲戚铁石心肠,一匙接一匙地吃了个精光,连碗都没让我舔一舔。
要是外婆,绝不会这样!
我决心找到外婆秘密藏匿的炒面。
我叫上小我一岁多的弟弟作帮手——帮我搭橙子、扶橙子——我估计炒面藏在高高柜子上那一堆瓶瓶罐罐里。爬上去,逐一查看,没有。我又来到卧室后面那间堆杂物的小黑屋。
在一个角落的架子上,我发现一个方形的冰铁筒。冰铁筒有点沉,里面有东西!我使劲撬开圆形铁盖,探手进去。空空的,只有几块拇指大小的块状物。我掏出一尝,哇,饼干!可惜,实在太小,小得大人们已经把它遗弃。我把几块“拇指”交给弟弟,不甘心地又将手伸进去。
里面有几张纸,掀开纸,下面是半罐面粉状的东西。“炒面”!我大喜,抓起一把送进口里,迫不急待往下咽。
突然,我一阵巨烈咳嗽,哇哇直往外呕,吐得翻肠倒胃。
正美滋滋享受“战利品”的弟弟吓坏了,惊得叫起来。
外婆慌慌张张赶来。 “老天爷,你啷个把石灰吃下去了?!”
“我……我……以为是……是炒面……”
“家里哪有炒面。那一碗?唉呀,那是我花五角钱向隔壁龚婆婆买的呀。”
我一边用外婆给我的水漱口,一边想,大人们为什么要把石灰和饼干放在一起呢?是为了防备我偷吃?
在我的记忆里,不管我做错什么事,外婆从来都没有骂过、更没打过我。我小时十分淘气,常常在外面滚一身泥,或者把衣裤扯烂。外婆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洗补。家里穷,我们几姊妹的衣服都是外婆缝制。记得有一天半夜里醒来,看见外婆爬到桌子上,把针线凑到那盏昏黄的灯前,眯着眼,吃力地试图将线穿过针眼……
我却毫不懂得爱惜外婆夜里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衣服,不懂得孝顺她,关心她、体贴她,甚至有一次,我把她珍藏在一个玻璃瓶里的十几粒糖偷来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外婆只叹了口气,说:“你该分点给姐姐……”
左邻右舍都说,裴婆婆是个好人,是个贤良忠厚的人。
可是,那个年代,好人、正直本分的人生活空间很狭小。妈妈同外婆是同类型的人,善良老实。 “当时我一切都听从政府的安排,不懂得想办法找关系给妈弄点吃的。”多年后,妈妈站在外婆的坟前对我们这样说。
那个年代,家里很艰难。爸爸几年前(1957年)中了“阳谋”,工资被扣掉大半,人也被发配到一个叫长寿湖的地方劳动改造。先是外公因病无钱医治倒下了(1958年),接着是最小的妹妹夭折(1960年),外婆挣扎到1962年,眼见得油灯如豆,朝不保夕。 34岁的妈妈也饿得满面浮肿,脸上一按一个指印。大我一岁的姐姐成天无精打采,已没有出去玩耍的力气。
坡下那家姓张的,外出寻觅一整天,傍晚挑回一担“粮食”——观音土(一种可以撑胀肚子但往往解不出大便的泥土)。然而,“饱饭”没吃两天,人先撑死一个……天地间,像有一只巨大的猛禽,它的翅膀遮天蔽日,扇动处,阴风四起,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外婆身体越来越虚弱,先是一解便就脱肛,直肠鲜鲜红红地垂落在肛门外。外婆呻吟着,用热毛巾摀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后来直肠频频脱落,外婆无法站立,终于卧床不起。上不起医院,请了个私人医生来打针,结果消毒不严,感染了,身子越肿越大,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只得开刀。没想到割开容易,长合艰难,由于极度缺乏营养,那个刀伤一直拒绝愈合,它日日夜夜大张着口,向苍天无声地述说,直到外婆告别人世,它都没有闭合。
那个年代,食物虽然极度匮乏,但“政治”却十分丰盛。妈妈几乎每晚都要参加“政治学习”,还不时要下乡去支援“抗击自然灾害”。通常,都是外婆照料我们。现在,外婆本人需要别人来照料了。她不愿给家人添麻烦,不忍心看到她女儿更加劳累,她觉得自己没用了,是个拖累,便萌生了去意。
公元1962年7月的一天,外婆嗫嗫嚅嚅地说:“我……我想吃……吃一片扣肉。”
“吃一片扣肉(即我们说的烧白)。”这实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渴求,小得就像一片无声飘落的树叶。
可是,妈妈在外婆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前束手无策。
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核武器,要立足打一场核大战——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伟大英明的领袖,考虑的是“超英赶美”的辉煌——那可是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伟业。至于长江边上有一个饥饿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渴求一片扣肉,实在太不值得这个国家和那个领袖关注了。
家里有一张老式木床,木床有一个挂蚊帐用的木架子。 1962年7月28日下午,外婆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木架的一根横杆上,一头系在她脖子上,消无声息地走了。
妈妈下班回来,抱着外婆悬挂的身子,泣不成声。
“她要是再坚持两个月,熬到9月份红苕出来就有救了。”妈妈在坟前对我们说。 “三年大饥荒,她快熬到头了,在快结束时,她走了……我知道妈妈是怕拖累我……她一辈子都为别人着想……”
外婆能坚持到红苕出来吗?她怎么知道大饥荒什么时候结束? (到1962年7 月,肆虐三年的大饥荒在全国各地都基本结束,但四川省仍然严重,这“归功”于极“左”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这是后话。 )妈妈说,外婆死时体重只有50多斤,真真的皮包骨。那张木床,后来我们又用了多年,系绳子的那个横杆,细细的,并不结实,我用手一使劲它就会折断,外婆整个人吊上去它竟然完好无损,可想当时她的生命是何等“轻如鸿毛”。
外婆的丧事我已记不清了,也没有爸爸回来的印象。只记得来奔丧的表姐娣娜姐姐晚上陪着我睡,她对我说:“婆婆是个很好的人。”
还记得那几夜的淡淡的月光,幽幽冷冷,洒在窗台上,一片银灰。
外婆火化后,骨灰埋在屋前一个叫做花园坝的凹台里。那儿,正对着长江,对着江对岸楼房林立的市中区。八年抗战期间,市中区曾是日军狂轰滥炸的地方,在长达五年半的“无区别轰炸”(即不分民房、百姓的轰炸)中,重庆被炸死炸伤3万多人。外婆躲到了涪陵乡下,她靠给别人缝制衣服维持生活,她没有被炸死,也没有饿死,安然无恙地渡过了八年艰难岁月。
可是,在和平年代,在“奔向共产主义幸福天堂”的“康庄大道”上,外婆倒下了。
同她一同倒下的,有多少呢?
前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告诉我,他通过各种资料对比研究,得出的数字是:四川省在三年饥荒年间,至少饿死1000万。
他还说,当时,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认可的数字是800万。
800万也好,1000万也好,在李井泉眼中不过是个数字,他面对这个数字谈笑自若地说了一句“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不提了,“四川出了个李井泉”却让人忍不住有些关切。从突然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1960年9月),活生生地从饥民口中夺食,到动用暴力,把所有不满的人、说出真像的人打入大牢,都是“超英赶美”类的毛式大手笔。在这些大手笔下,卑微如我外婆一样的草民,就只有拿生命祭献了。
1000万,800万,的确不过是数字,但是,我眼前的这一个“1”不是数字,她是我外婆——一个鲜鲜活活的生命,一个一辈子温良贤淑慈善勤俭的生命,一个把最后一口粮食吐给她孙儿的生命。
昏灯下细细的针线、盘子里薄薄的馍片、床架上飘荡的身子……把这个简单的“1”撑得血肉丰盈。即便我也如他人一样得了健忘症,忘掉了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自然灾害”,即使我不再争论1000万还是800万,但是,我会计较这一个“1”,我会年年在这一个真真实实、鲜鲜活活的“1”面前焚香致哀,垂首静思。
山风吹来,松柏摇曳,黑色的墓碑横亘在阴阳两界之间,阻隔了生与死的对话。但我相信,人有一个灵界,它超脱肉体而永存。我伫立在墓前,灵魂向外婆在天之灵跪拜。
青烟袅袅,烛火幽幽,充盈于心底的爱的灵光,穿越阴阳生死的疆界,将外婆紧紧拥抱;那沉寂了45年的迟来的心语,在墓地上空回响——
—— 外婆,我爱您!
于2007年清明
《1962年,我的外婆》
又是清明,年近80 的妈妈带着我们来到外婆的坟前。
外婆的坟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山坡上,后面,就是八年抗战时蒋委员长住过的黄山。
妈妈摆上供果,点燃红烛,伫立垂首。
纸钱烧起来,红红的火光,黑黑的墓碑,青烟起处,山风回旋。
泪水,从妈妈眼里滚出来,她又想起那个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在长江边一个叫马鞍山的半山坡上。出门,就是陡斜的石坡,长江,在脚下日日夜夜奔流。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家家户户不准自己做饭,政府不供应煤,甚至连锅都被收缴了,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去吃“集体伙食”。不去,不仅无法生存,而且还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险。
外婆要去的那个公共食堂在山坡下的江边上,距那个着名的“龙门浩月”不远。
外婆是“旧社会”来的女人,小时裹过脚,“三寸金莲”行走起来原本不便,再加上长期饿饭,走路就更显吃力。然而,一日三餐,她必须下到江边,领取二两饭,然后沿着那陡斜的石板山路一步步挪回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下着雨,看见妈支着一根竹竿,挎着个布包,布包里面是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妈妈颤颤巍巍,面黄肌瘦,吃力地往上挪动脚步。我一下子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对我说。
终于,公共食堂的人也看到外婆走不动了,于是他们说:“裴婆婆(我外公姓裴),反正你每天六两粮,我们给你做一个六两的馒头,你一次性领回去,这样每天你就只走一趟。 ”
也只有这样了,去食堂来回下坡上坡,不安全不说,仅运动量大,就不利于对那二两粮的珍惜。
可是,很快发现,这也不是好办法。一个六两的馒头切成三份,每份也只有拳头大,更要紧的是,份量明显不足。
外婆不吭一声,她是传统文化打造的温良恭俭型女人,一辈子谦和恭顺,从没同人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何况,人家还是为她着想呢。
 谭松外婆胡传芬墓碑怀抱谭松母亲 |
 谭松外婆胡传芬墓碑 |
她的三个小孙儿,其中包括食欲极旺的我,每天从幼儿园回来,虽说已吃过晚饭,总渴望再从外婆那儿捞点吃的。外婆不忍面对三双贪渴的眼睛,每天,她都把馒头切下三片,平摊着放在盘子里,用碗盖上,等我们回来。
记得有一次,外婆拿出一个土豆,土豆很小,不便再分,于是外婆叫我们轮流把土豆含在嘴里吮吸,以延长“吃”的美妙过程。姐姐很守规矩地照章执行,吮吸之后吐给了我。我含在嘴里,实在忍不住,一口咬下去。
旁边紧盯着我的弟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那时,六岁的我像一条饥饿的小狼,野性十足地搜寻食物,我把一个六岁儿童的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来搜寻外婆可能的收藏。一次,家里来了一个亲戚,外婆竟然冲了一小碗炒面招待他。那个香味直浸润入我骨子。可惜,任凭我痴痴地立在一旁双眼圆睁口水长流,亲戚铁石心肠,一匙接一匙地吃了个精光,连碗都没让我舔一舔。
要是外婆,绝不会这样!
我决心找到外婆秘密藏匿的炒面。
我叫上小我一岁多的弟弟作帮手——帮我搭橙子、扶橙子——我估计炒面藏在高高柜子上那一堆瓶瓶罐罐里。爬上去,逐一查看,没有。我又来到卧室后面那间堆杂物的小黑屋。
在一个角落的架子上,我发现一个方形的冰铁筒。冰铁筒有点沉,里面有东西!我使劲撬开圆形铁盖,探手进去。空空的,只有几块拇指大小的块状物。我掏出一尝,哇,饼干!可惜,实在太小,小得大人们已经把它遗弃。我把几块“拇指”交给弟弟,不甘心地又将手伸进去。
里面有几张纸,掀开纸,下面是半罐面粉状的东西。“炒面”!我大喜,抓起一把送进口里,迫不急待往下咽。
突然,我一阵巨烈咳嗽,哇哇直往外呕,吐得翻肠倒胃。
正美滋滋享受“战利品”的弟弟吓坏了,惊得叫起来。
外婆慌慌张张赶来。 “老天爷,你啷个把石灰吃下去了?!”
“我……我……以为是……是炒面……”
“家里哪有炒面。那一碗?唉呀,那是我花五角钱向隔壁龚婆婆买的呀。”
我一边用外婆给我的水漱口,一边想,大人们为什么要把石灰和饼干放在一起呢?是为了防备我偷吃?
在我的记忆里,不管我做错什么事,外婆从来都没有骂过、更没打过我。我小时十分淘气,常常在外面滚一身泥,或者把衣裤扯烂。外婆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洗补。家里穷,我们几姊妹的衣服都是外婆缝制。记得有一天半夜里醒来,看见外婆爬到桌子上,把针线凑到那盏昏黄的灯前,眯着眼,吃力地试图将线穿过针眼……
我却毫不懂得爱惜外婆夜里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衣服,不懂得孝顺她,关心她、体贴她,甚至有一次,我把她珍藏在一个玻璃瓶里的十几粒糖偷来一口气吃了个精光。外婆只叹了口气,说:“你该分点给姐姐……”
左邻右舍都说,裴婆婆是个好人,是个贤良忠厚的人。
可是,那个年代,好人、正直本分的人生活空间很狭小。妈妈同外婆是同类型的人,善良老实。 “当时我一切都听从政府的安排,不懂得想办法找关系给妈弄点吃的。”多年后,妈妈站在外婆的坟前对我们这样说。
那个年代,家里很艰难。爸爸几年前(1957年)中了“阳谋”,工资被扣掉大半,人也被发配到一个叫长寿湖的地方劳动改造。先是外公因病无钱医治倒下了(1958年),接着是最小的妹妹夭折(1960年),外婆挣扎到1962年,眼见得油灯如豆,朝不保夕。 34岁的妈妈也饿得满面浮肿,脸上一按一个指印。大我一岁的姐姐成天无精打采,已没有出去玩耍的力气。
坡下那家姓张的,外出寻觅一整天,傍晚挑回一担“粮食”——观音土(一种可以撑胀肚子但往往解不出大便的泥土)。然而,“饱饭”没吃两天,人先撑死一个……天地间,像有一只巨大的猛禽,它的翅膀遮天蔽日,扇动处,阴风四起,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外婆身体越来越虚弱,先是一解便就脱肛,直肠鲜鲜红红地垂落在肛门外。外婆呻吟着,用热毛巾摀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后来直肠频频脱落,外婆无法站立,终于卧床不起。上不起医院,请了个私人医生来打针,结果消毒不严,感染了,身子越肿越大,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只得开刀。没想到割开容易,长合艰难,由于极度缺乏营养,那个刀伤一直拒绝愈合,它日日夜夜大张着口,向苍天无声地述说,直到外婆告别人世,它都没有闭合。
那个年代,食物虽然极度匮乏,但“政治”却十分丰盛。妈妈几乎每晚都要参加“政治学习”,还不时要下乡去支援“抗击自然灾害”。通常,都是外婆照料我们。现在,外婆本人需要别人来照料了。她不愿给家人添麻烦,不忍心看到她女儿更加劳累,她觉得自己没用了,是个拖累,便萌生了去意。
公元1962年7月的一天,外婆嗫嗫嚅嚅地说:“我……我想吃……吃一片扣肉。”
“吃一片扣肉(即我们说的烧白)。”这实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渴求,小得就像一片无声飘落的树叶。
可是,妈妈在外婆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前束手无策。
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核武器,要立足打一场核大战——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伟大英明的领袖,考虑的是“超英赶美”的辉煌——那可是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伟业。至于长江边上有一个饥饿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渴求一片扣肉,实在太不值得这个国家和那个领袖关注了。
家里有一张老式木床,木床有一个挂蚊帐用的木架子。 1962年7月28日下午,外婆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木架的一根横杆上,一头系在她脖子上,消无声息地走了。
妈妈下班回来,抱着外婆悬挂的身子,泣不成声。
“她要是再坚持两个月,熬到9月份红苕出来就有救了。”妈妈在坟前对我们说。 “三年大饥荒,她快熬到头了,在快结束时,她走了……我知道妈妈是怕拖累我……她一辈子都为别人着想……”
外婆能坚持到红苕出来吗?她怎么知道大饥荒什么时候结束? (到1962年7 月,肆虐三年的大饥荒在全国各地都基本结束,但四川省仍然严重,这“归功”于极“左”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这是后话。 )妈妈说,外婆死时体重只有50多斤,真真的皮包骨。那张木床,后来我们又用了多年,系绳子的那个横杆,细细的,并不结实,我用手一使劲它就会折断,外婆整个人吊上去它竟然完好无损,可想当时她的生命是何等“轻如鸿毛”。
外婆的丧事我已记不清了,也没有爸爸回来的印象。只记得来奔丧的表姐娣娜姐姐晚上陪着我睡,她对我说:“婆婆是个很好的人。”
还记得那几夜的淡淡的月光,幽幽冷冷,洒在窗台上,一片银灰。
外婆火化后,骨灰埋在屋前一个叫做花园坝的凹台里。那儿,正对着长江,对着江对岸楼房林立的市中区。八年抗战期间,市中区曾是日军狂轰滥炸的地方,在长达五年半的“无区别轰炸”(即不分民房、百姓的轰炸)中,重庆被炸死炸伤3万多人。外婆躲到了涪陵乡下,她靠给别人缝制衣服维持生活,她没有被炸死,也没有饿死,安然无恙地渡过了八年艰难岁月。
可是,在和平年代,在“奔向共产主义幸福天堂”的“康庄大道”上,外婆倒下了。
同她一同倒下的,有多少呢?
前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告诉我,他通过各种资料对比研究,得出的数字是:四川省在三年饥荒年间,至少饿死1000万。
他还说,当时,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认可的数字是800万。
800万也好,1000万也好,在李井泉眼中不过是个数字,他面对这个数字谈笑自若地说了一句“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不提了,“四川出了个李井泉”却让人忍不住有些关切。从突然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1960年9月),活生生地从饥民口中夺食,到动用暴力,把所有不满的人、说出真像的人打入大牢,都是“超英赶美”类的毛式大手笔。在这些大手笔下,卑微如我外婆一样的草民,就只有拿生命祭献了。
1000万,800万,的确不过是数字,但是,我眼前的这一个“1”不是数字,她是我外婆——一个鲜鲜活活的生命,一个一辈子温良贤淑慈善勤俭的生命,一个把最后一口粮食吐给她孙儿的生命。
昏灯下细细的针线、盘子里薄薄的馍片、床架上飘荡的身子……把这个简单的“1”撑得血肉丰盈。即便我也如他人一样得了健忘症,忘掉了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自然灾害”,即使我不再争论1000万还是800万,但是,我会计较这一个“1”,我会年年在这一个真真实实、鲜鲜活活的“1”面前焚香致哀,垂首静思。
山风吹来,松柏摇曳,黑色的墓碑横亘在阴阳两界之间,阻隔了生与死的对话。但我相信,人有一个灵界,它超脱肉体而永存。我伫立在墓前,灵魂向外婆在天之灵跪拜。
青烟袅袅,烛火幽幽,充盈于心底的爱的灵光,穿越阴阳生死的疆界,将外婆紧紧拥抱;那沉寂了45年的迟来的心语,在墓地上空回响——
—— 外婆,我爱您!
于2007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