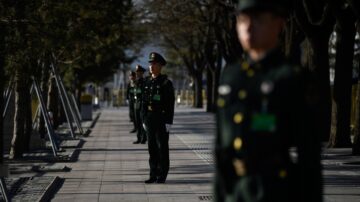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10月5日讯】【编者的话】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边“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者杨显惠历时五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终于完成了《夹边沟记事》,使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夹边沟记事》一本关于四十年前中国饥饿与死亡的真实报告。
《夹边沟记事》连载 走进夹边沟(四)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藉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作者简介】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 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 1975年在甘肃省家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书。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未完待续)

《夹边沟记事》一本关于四十年前中国饥饿与死亡的真实报告。
《夹边沟记事》连载 走进夹边沟(四)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藉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作者简介】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 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 1975年在甘肃省家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书。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