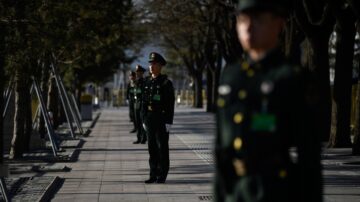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2月28日讯】【献辞】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阮蘅伯,同时献给推翻封建帝制的一代热血青年,以及死于另一个专制暴政下的辛亥志士们。
——作者跪祭

1985年1月我们终于找到了死难者的荒塚,右起第二人为作者。(网路图片)
一
在推翻帝制的决战中,他属驰骋疆场的一代热血青年,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他离开了马背,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荒野……在一片处女地的开拓中,他以智慧与勤奋,凭着一个“死心眼”,塑造了一个开拓者的伟岸形象——挺立在未曾泯灭的历史烽烟中,乱世中……
于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位于重庆南岸花溪河畔冒着热气的一片荒草地上,就在这个青年开拓者的手中,变成了温泉沐浴地,与毗邻的大温泉(南温泉)相呼应,通称小温泉(简称小泉),而且渐渐成了风景名胜区,在花溪十二景中名为“小泉温泳”,以开拓者阮蘅伯(我的父亲)原创的“沂春浴室”、“蘅卢宾馆”及“今是轩”为核心,把花溪河的腹心地带打扮得声情并茂,姿色宜人,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末期,浓缩了一段历史风云,从小舞台走向了大舞台。
缘于“小泉温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民国政府对这块风水宝地也是患上了红眼病的,但,那时的官僚们却不敢也从未起过掠夺之心,诸如以“服从抗战大局”的名义鲸吞嚼食,而是按规矩租用了八年,尽管租用单位——中央政治大学——的校长是蒋中正,但,在本质上及事实上,他仍是我家的房客,换言之,我家乃是蒋委员长的房东。这个租赁关系乃有契约为据,甲乙双方的亲笔签名者,分别是阮蘅伯与蒋中正,毫无苟且;该校在抗战胜利迁回南京前夕,校方则按契约向我父亲办理了全部退还手续。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类契据文书都是盖了“政大”校印和蒋委员长的私人印鉴的,只可惜在后来的改朝换代中被焚毁了(估计在台北档案馆还可能查得到)。但,不可焚毁的却是留在我脑海中的一份珍贵记忆:被推倒的那个党国,在道义和法制方面,乃是后来的这个党国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在拿下江山之前,这个自封“灯塔”的政党,在陪都重庆,在民国首脑聚居的南泉及小泉,对“民主宪政”的呐喊,带头反对一党独裁的调门,比谁都更高吭,更响亮。
二
站在一九四九这条历史断裂带上,面对接踵而来的“镇反”及“清匪反霸”运动,亦即面对天朝伊始的血腥大杀戮,我父亲(阮蘅伯)乃始终毫无惧色,因为他认真研究了并听信了中共“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而且坚信自己的正直和清白可为历朝历代所容纳,因为,他耳闻中共也在口口声声恭维国父孙中山,况且,吾父也一贯自以为他的青春与热血,乃是同辛亥革命的连天烽火拥抱在一起的,无愧国家民族——无论在但懋辛将军麾下,或者在唐式遵将军麾下——其剑锋所指,乃是满清王朝。这有履历及业绩为据:自“四川保路运动”功成圆满之后,未过而立之年的他,即断然拒绝投身军阀混战,亦即毅然放弃了乱世攀升的机会,仅仅凭藉积蓄不多的军晌,立即走向了喀斯特溶岩地貌中的这条小河流,不辞艰辛,终于负债开拓出了风光如画的小温泉。这是他毕生心血创下的命根子,自然更是一大家子的生存源泉。所以,后来面临改朝换代,面对“人民政府”对这桩产业的眼红及口馋,或者威迫利诱,他皆不为所动。因为,他曾经熟读经史,他不相信 “共产”是抢劫。当然,这也是他自已在找死。
重庆“解放”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小泉相继举办了“军政大学”和“革命大学”。这两所“大学”都曾有意购买“沂春”浴室和泳池,但吾父却不识相,拒绝出卖,这当然也同对方的贱价强购有关。稍后,当南局管理局首任局长——就是要求女人们把一切献给党的那个色狼兼贪污犯“韩金牙”——通知吾父把小泉“适当作价”交给南泉“统一管理”时,吾父也是仍然不识时务,因为他仍然相信中共“保护工商业的英明政策”不会改变,并据之作了回绝,最后还敢声言道:
“买卖买卖,两相情愿,我不卖,谁敢抢?除非共产党没政策,没王法!”
“阮蘅伯,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两句对白令我刻骨铭心。韩金牙的确也是言之不假,他第一次叫我们全家落泪的事情果然很快到来了。中共在对“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拉开屠杀序幕之前,也仿效“老区”搞了个所谓的“减租退押”运动(对“铁公鸡”牟国福这种自耕发家而且始终自耕的小地主也无例外),而吾父分得的一点祖业(位于周家沟的十多亩稻田及旱地),则被韩局长左算右算、算得非要拿小泉的家业抵押不可。吾父当然不服。在争辩无效之后,他只好硬着头皮到重庆找遍亲友(包括“起义将领”彭斌将军)借到了两千枚银元,退了“押佃”,总算过了第一道鬼门关。尽管这同强人榨取无异——十多亩田地才值多少钱?一点小土地出租哪会收押金?何况它与我家基本生活来源的关系微之又微——但父亲并不因被变相抢劫而沮丧不己。他坚信,只要地下涌出的温泉不致枯竭,就会替他度过一切难关;何况,他仍然相信中共的工商政策不会开玩笑,甚至认为自己应该属于五星红旗上的一颗星(其实,他真是类同如今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兼优秀的退伍军人)。怀着这份化险为夷的好心情,在自斟自饮中,他不仅续写着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而且还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南泉—小泉规划建设的书面建议。他的性格真像一块有棱有角的花岗岩,顽固而天真。
他的这份天真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在接下来划分成份时,我家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既不属于重点革命对象,也不属于革命营垒——尚可在夹缝中求得一条生路。对此,作为辛亥志士的他,尽管心怀耿介,但同被抓被斗的地主或乡绅相比,也还是算不错的。他的写作仍在继续着;浴室、泳池与宾馆仍在热热闹闹地营运着。
三
或许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抗美援朝”愈发攀升的金钱需要,前朝官僚和地主的“罪名”也就随之火速升级了。被留用的南泉管理局末任局长许敬舆很快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以悭吝与勤劳驰名的“铁公鸡”牟国福也被扣上了“恶霸地主”而被火速敲了“砂罐”……一时间,血流如水并火速变成了“袁大头”——因对“反动官僚”和“恶霸地主”不仅皆须一律杀头,而且惟有如此才可“依法”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可挖地三尺,对于剩下的家眷,皆可扫地出门,任意蹂躏。
我父亲也被升级了,中共首先拿他同“反动官僚”挂了勾,因为他相继任过南泉管理局局长,和万县糖业专卖局局长,不过,其任职时段却在抗战八年之内,属“国共合作”时期,加之为官廉洁,无劣迹可抓,一时还找不到任何藉口敲碎他的“砂罐”并没收他的小泉家业;但是,祖传的那点田地却继续给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当韩金牙代表“党和政府”把“小土地出租”提升为“大地主”后,就接踵给父亲扣上了“官僚大地主”和“恶霸地主”两顶大帽子——绝对够了被“敲”并被“依法”没收全部财产的资格。
但很怪(那年头的怪事也太多),我父亲被抓了,斗了,也关了,但“人民政府”却又对他(对一个“恶霸地主”)表现出了空前绝后的“宽大为怀”,不仅没杀他,而且还很快把他放了并立即逐出了当地——韩金牙主动叫他到外地投靠子女——以致使他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保全了“砂罐”的“官僚大地主”兼“恶霸地主”,同时享有“选举权”。从此(从一九五二年夏天伊始),一位被泼了一身污水的辛亥革命英雄,就只得离乡背井,踏上了茫茫“信访”路,并随身携带着尚未写完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他首先给原“西南军政委员会”首届正、副主委刘伯承和邓小平寄了“申诉材料”,但却如泥牛入海;之后,他赴京找了他的血亲表弟胡子昂(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委、“人大”常委),但仍然无果;最后,他返蓉找到了昔日上司但懋辛将军,经启发说服后,他才对被掠夺的财产有些心灰意冷了,但仍未死心,因为他的性格仍像一块有棱有角的花岗岩,并在嘴边附加了一句口头禅:“既然我是恶霸地主,为啥不敲老子的砂罐?”——其潜台词不挑自明,逻辑坚挺。
四
我在一九五七年被阳谋诱“杀”之后,更难见到父亲了。但是,当父亲获知我同“一点雪”(大黑狗)相依为命时,尤其听到我从死人堆爬出来的那付惨相时,不仅老泪纵横,而且还是倾其所有地向我传来了伟大的父爱,这有不时寄来的一两斤全国粮票和托人带来的一小瓶油煎盐巴为证。他的这些“暗箱操作”无疑同三姐一家子的生存源泉具有直接关系,间或闹得翻脸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虽庶出,但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最爱我,不仅缘于“百姓爱幺儿”。一九六二年,我终于获准返渝探亲时,老爸一开始就提出愿到岷江来同我过日子,受苦也乐意。但这怎么行呢?我认为是他老糊涂了,毕竟己近八旬高龄, 何况我的身份也不能接纳他(就不知两位姐姐为何还要支持他)。被我断然拒绝后,父亲的老脸几乎抽搐起来了。之后,我心中又觉得喘喘不安,老在捉摸着如何给他一些安慰才好。我知道他是渴望残年有靠,与母亲对我的期盼完全不同。所以,我就不必把林玉芳或安丽的像片给他看并重复相同的谎言了。我应当为他另砌一个谎言炉灶才好。于是,我向老爸说,虽然您同我母亲早就结束了封建婚姻关系,而且在离婚书上也明确界定我只对母亲一方才负有瞻养责任,但是,事实上的血缘关系在我心头却是割不断的,您永远是我的父亲。我在五七年以前的表现可以证明这一点,您也认为我是很有孝心的。今后,只要我的命运稍有转机,一定会主动接您上成都,好好侍候您的晚年。我妈也是这个意思, 您知道,她心好,明大义,目前还可自食其力。这次,也是她主动提出要我每月尽可能兑五元钱给您的,叫您买点古巴糖补补身子。我认为您眼前的关键是要静下心来过日子,和衷共济,不要闹。三姐一家子不容易,人人都很惨。等我的情况好了,就好办了,您说呢?
我讲的当然全是真心话,但因难以兑现,也可视为谎言。不过,父亲脸上的愁容却为之舒展多了,而且还在落日馀辉中生出了十分美好的憧憬。为了有幸同我共济一个屋檐下,他还不断地排了长队,凭票购置了碗筷和锅瓢。在人生的边缘上,他仍在编织着一个无比悲怆的梦,包括索回财产的梦……
我同父亲的此次别离(也是永诀)之后,他即在“四清” 和“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赶回了原籍,残喘在南泉建文峰下的一处荒山野谷中,而且仍然携带着他尚未写完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一九六六年,当毛魔用括地三尺的血腥“横扫”拉开“文革” 序幕之初,我父亲就被南泉红卫兵抓去批斗、罚跪、游街、鞭打而终其一生了。时年八旬有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竟会如此煽动子辈孙辈来残害祖辈和父辈者,已足可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即将崩溃了,完全堕落了。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伟大和美丽,我父亲的尸体,一位辛亥志士的尸体,一位国民党人的尸体,一位四川保路运动先驱者的尸体,竟被弃置田野,包括《辛亥革命回忆录》。
我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逃离温江“牛棚”时,到了淑声姑母家才知此事的。我在恸哭中燃起了一腔怒火。如果说,我从温江逃离时还带有不少盲目性的话,那么,从野山传来的这则噩耗则使我的仇恨目标变得明确多了。但是,我并不需要明火执仗的抗争,我首先需要保住自我,先在苦难中作个刑馀的史臣,记下毛魔的罪孽与人间的不幸。倘若未及天明就倒下了,也要设法将我的心路历程和实物资料,尤其是我父亲的死因,留给未来的子孙。
其实,我父亲的死因非常简单,只因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创下了一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容的私人产业,而后者的本性却是屠杀与掠夺——活像狮王张开了吞噬前朝子孙的血盆大口。
五
我已不愿细想父亲惨死在建文峰下的那一刻尤其是那幅情景了,后来听人讲,他被毛魔红卫兵活活折磨致死之后,直至丢坑掩埋之前,乃是未能瞑目的——我觉得,他是在用他死了的怒目和不散的冤魂,向苍天,向大地,写成了一曲辛亥之殇,留下了一笔辛亥之耻。这既是一代人的不幸,更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当年的一代革命青年,翱翔在蜀水巴山的一群雄鹰——邹容、夏之时、唐式遵、但懋辛、阮蘅伯和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他们用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所换得的各自的悲惨结局,共同的命运,乃是留在百年历史烟尘中的最为不幸的一组音符,也是一曲无比悲怆的乱世绝唱。你只要想一想,掂一掂民国元年二十四岁的四川督军夏之时竟在一九五零年被中共“农协会”处死的情景就不难破译并判断谁是新中国了;同样,你只要想一想,掂一掂如今由官、商勾结霸占的“摇钱树”小温泉就不难破译并判断毛的“革命”是个什么东西了。
不过,作为辛亥一代的晚辈,作为阮蘅伯的儿子,我心中最为愧疚和遗憾的还是我不仅没有留下父亲未完的《辛亥革命回忆录》,而且连看也都懒得看一眼(倘若留些记忆在心中该多好)。这自然同当年年幼有关,乱世中,我也根本没有兴趣留意他在写什么;稍稍大一点,站在一九四九历史断裂带上,作为在大陆上相继充当了一个党国末代童子军和另一个党国首批红领巾的我,经“新中国”洗脑后,即小脑瓜中被“划清界线”,“站稳阶级立场”,尤其是被“大义灭亲”之类的血腥观念塞满之后,我更是觉得父亲的那迭手稿(装订得很像一本线装书的东西),乃属不祥之物,不仅对之兴味索然,而且还叫他烧Text Box: 了,更不要去到处“翻案”了。有一次,父亲被我“大义凛然”的“革命态度”气得发火时,冲我怒吼道:
“你是吃错药啦?莫非国父领导的辛亥革命也错啦?!”并附上了他的口头禅:“既然我是恶霸地主,为啥不敲老子的砂罐?”——他充足的理由和雄辩的诘问也委实冲淡了我心中“神圣的党文化”,后来也渐渐记住了他的一些只言片语。如今汇集起来,也可大致勾勒出阮氏家谱和父亲在辛亥前后的人生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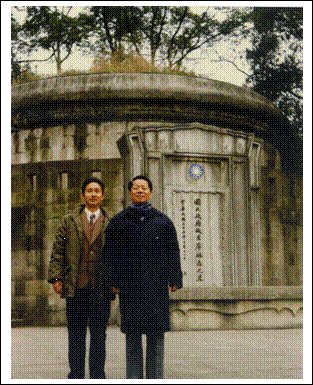
1987年冬同台湾归来收拾父亲骨骸的二哥(阮基绪)合影于林森墓前。(网路图片)
阮氏家族上溯有据的祖先是晋代名士阮籍,祖籍湖北孝感,明末匪首张献忠屠蜀后,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定居于巴县。祖父是前清举人,终身任教于学堂。父亲兄弟四人,排行老大,生于一八八四年,勤奋好学,志向明确,自幼仇恨封建帝制,不顾祖父劝阻,毅然投身反满,相继在但懋辛部、唐式遵部任秘书及秘书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时,年仅二十七岁,由于作战勇敢,文化程度较高,亦即文武双全,在摧毁四川总督府后,被调至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位于成都莲花池)任职;继后又被唐式遵师长召回,俟至将被擢升团级之时,却恳请解甲到小泉,因他不愿参加军阀混战而只是醉心于实业开拓,时年三旬左右,雄心勃勃,才华与抱负如双翼展开,但谁能预卜推翻帝制后的民国创业竟有杀身之祸呢!
呜呼,一代死于中共暴政的辛亥先行者,你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之梦莫非还能久久容忍极权政治的噩梦么?
(原标题: 被弃尸荒山的辛亥老人)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35、36期合刊
——作者跪祭

1985年1月我们终于找到了死难者的荒塚,右起第二人为作者。(网路图片)
一
在推翻帝制的决战中,他属驰骋疆场的一代热血青年,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他离开了马背,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荒野……在一片处女地的开拓中,他以智慧与勤奋,凭着一个“死心眼”,塑造了一个开拓者的伟岸形象——挺立在未曾泯灭的历史烽烟中,乱世中……
于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位于重庆南岸花溪河畔冒着热气的一片荒草地上,就在这个青年开拓者的手中,变成了温泉沐浴地,与毗邻的大温泉(南温泉)相呼应,通称小温泉(简称小泉),而且渐渐成了风景名胜区,在花溪十二景中名为“小泉温泳”,以开拓者阮蘅伯(我的父亲)原创的“沂春浴室”、“蘅卢宾馆”及“今是轩”为核心,把花溪河的腹心地带打扮得声情并茂,姿色宜人,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末期,浓缩了一段历史风云,从小舞台走向了大舞台。
缘于“小泉温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民国政府对这块风水宝地也是患上了红眼病的,但,那时的官僚们却不敢也从未起过掠夺之心,诸如以“服从抗战大局”的名义鲸吞嚼食,而是按规矩租用了八年,尽管租用单位——中央政治大学——的校长是蒋中正,但,在本质上及事实上,他仍是我家的房客,换言之,我家乃是蒋委员长的房东。这个租赁关系乃有契约为据,甲乙双方的亲笔签名者,分别是阮蘅伯与蒋中正,毫无苟且;该校在抗战胜利迁回南京前夕,校方则按契约向我父亲办理了全部退还手续。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类契据文书都是盖了“政大”校印和蒋委员长的私人印鉴的,只可惜在后来的改朝换代中被焚毁了(估计在台北档案馆还可能查得到)。但,不可焚毁的却是留在我脑海中的一份珍贵记忆:被推倒的那个党国,在道义和法制方面,乃是后来的这个党国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在拿下江山之前,这个自封“灯塔”的政党,在陪都重庆,在民国首脑聚居的南泉及小泉,对“民主宪政”的呐喊,带头反对一党独裁的调门,比谁都更高吭,更响亮。
二
站在一九四九这条历史断裂带上,面对接踵而来的“镇反”及“清匪反霸”运动,亦即面对天朝伊始的血腥大杀戮,我父亲(阮蘅伯)乃始终毫无惧色,因为他认真研究了并听信了中共“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而且坚信自己的正直和清白可为历朝历代所容纳,因为,他耳闻中共也在口口声声恭维国父孙中山,况且,吾父也一贯自以为他的青春与热血,乃是同辛亥革命的连天烽火拥抱在一起的,无愧国家民族——无论在但懋辛将军麾下,或者在唐式遵将军麾下——其剑锋所指,乃是满清王朝。这有履历及业绩为据:自“四川保路运动”功成圆满之后,未过而立之年的他,即断然拒绝投身军阀混战,亦即毅然放弃了乱世攀升的机会,仅仅凭藉积蓄不多的军晌,立即走向了喀斯特溶岩地貌中的这条小河流,不辞艰辛,终于负债开拓出了风光如画的小温泉。这是他毕生心血创下的命根子,自然更是一大家子的生存源泉。所以,后来面临改朝换代,面对“人民政府”对这桩产业的眼红及口馋,或者威迫利诱,他皆不为所动。因为,他曾经熟读经史,他不相信 “共产”是抢劫。当然,这也是他自已在找死。
重庆“解放”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小泉相继举办了“军政大学”和“革命大学”。这两所“大学”都曾有意购买“沂春”浴室和泳池,但吾父却不识相,拒绝出卖,这当然也同对方的贱价强购有关。稍后,当南局管理局首任局长——就是要求女人们把一切献给党的那个色狼兼贪污犯“韩金牙”——通知吾父把小泉“适当作价”交给南泉“统一管理”时,吾父也是仍然不识时务,因为他仍然相信中共“保护工商业的英明政策”不会改变,并据之作了回绝,最后还敢声言道:
“买卖买卖,两相情愿,我不卖,谁敢抢?除非共产党没政策,没王法!”
“阮蘅伯,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两句对白令我刻骨铭心。韩金牙的确也是言之不假,他第一次叫我们全家落泪的事情果然很快到来了。中共在对“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拉开屠杀序幕之前,也仿效“老区”搞了个所谓的“减租退押”运动(对“铁公鸡”牟国福这种自耕发家而且始终自耕的小地主也无例外),而吾父分得的一点祖业(位于周家沟的十多亩稻田及旱地),则被韩局长左算右算、算得非要拿小泉的家业抵押不可。吾父当然不服。在争辩无效之后,他只好硬着头皮到重庆找遍亲友(包括“起义将领”彭斌将军)借到了两千枚银元,退了“押佃”,总算过了第一道鬼门关。尽管这同强人榨取无异——十多亩田地才值多少钱?一点小土地出租哪会收押金?何况它与我家基本生活来源的关系微之又微——但父亲并不因被变相抢劫而沮丧不己。他坚信,只要地下涌出的温泉不致枯竭,就会替他度过一切难关;何况,他仍然相信中共的工商政策不会开玩笑,甚至认为自己应该属于五星红旗上的一颗星(其实,他真是类同如今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兼优秀的退伍军人)。怀着这份化险为夷的好心情,在自斟自饮中,他不仅续写着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而且还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南泉—小泉规划建设的书面建议。他的性格真像一块有棱有角的花岗岩,顽固而天真。
他的这份天真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在接下来划分成份时,我家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既不属于重点革命对象,也不属于革命营垒——尚可在夹缝中求得一条生路。对此,作为辛亥志士的他,尽管心怀耿介,但同被抓被斗的地主或乡绅相比,也还是算不错的。他的写作仍在继续着;浴室、泳池与宾馆仍在热热闹闹地营运着。
三
或许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抗美援朝”愈发攀升的金钱需要,前朝官僚和地主的“罪名”也就随之火速升级了。被留用的南泉管理局末任局长许敬舆很快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以悭吝与勤劳驰名的“铁公鸡”牟国福也被扣上了“恶霸地主”而被火速敲了“砂罐”……一时间,血流如水并火速变成了“袁大头”——因对“反动官僚”和“恶霸地主”不仅皆须一律杀头,而且惟有如此才可“依法”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可挖地三尺,对于剩下的家眷,皆可扫地出门,任意蹂躏。
我父亲也被升级了,中共首先拿他同“反动官僚”挂了勾,因为他相继任过南泉管理局局长,和万县糖业专卖局局长,不过,其任职时段却在抗战八年之内,属“国共合作”时期,加之为官廉洁,无劣迹可抓,一时还找不到任何藉口敲碎他的“砂罐”并没收他的小泉家业;但是,祖传的那点田地却继续给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当韩金牙代表“党和政府”把“小土地出租”提升为“大地主”后,就接踵给父亲扣上了“官僚大地主”和“恶霸地主”两顶大帽子——绝对够了被“敲”并被“依法”没收全部财产的资格。
但很怪(那年头的怪事也太多),我父亲被抓了,斗了,也关了,但“人民政府”却又对他(对一个“恶霸地主”)表现出了空前绝后的“宽大为怀”,不仅没杀他,而且还很快把他放了并立即逐出了当地——韩金牙主动叫他到外地投靠子女——以致使他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保全了“砂罐”的“官僚大地主”兼“恶霸地主”,同时享有“选举权”。从此(从一九五二年夏天伊始),一位被泼了一身污水的辛亥革命英雄,就只得离乡背井,踏上了茫茫“信访”路,并随身携带着尚未写完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他首先给原“西南军政委员会”首届正、副主委刘伯承和邓小平寄了“申诉材料”,但却如泥牛入海;之后,他赴京找了他的血亲表弟胡子昂(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委、“人大”常委),但仍然无果;最后,他返蓉找到了昔日上司但懋辛将军,经启发说服后,他才对被掠夺的财产有些心灰意冷了,但仍未死心,因为他的性格仍像一块有棱有角的花岗岩,并在嘴边附加了一句口头禅:“既然我是恶霸地主,为啥不敲老子的砂罐?”——其潜台词不挑自明,逻辑坚挺。
四
我在一九五七年被阳谋诱“杀”之后,更难见到父亲了。但是,当父亲获知我同“一点雪”(大黑狗)相依为命时,尤其听到我从死人堆爬出来的那付惨相时,不仅老泪纵横,而且还是倾其所有地向我传来了伟大的父爱,这有不时寄来的一两斤全国粮票和托人带来的一小瓶油煎盐巴为证。他的这些“暗箱操作”无疑同三姐一家子的生存源泉具有直接关系,间或闹得翻脸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虽庶出,但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最爱我,不仅缘于“百姓爱幺儿”。一九六二年,我终于获准返渝探亲时,老爸一开始就提出愿到岷江来同我过日子,受苦也乐意。但这怎么行呢?我认为是他老糊涂了,毕竟己近八旬高龄, 何况我的身份也不能接纳他(就不知两位姐姐为何还要支持他)。被我断然拒绝后,父亲的老脸几乎抽搐起来了。之后,我心中又觉得喘喘不安,老在捉摸着如何给他一些安慰才好。我知道他是渴望残年有靠,与母亲对我的期盼完全不同。所以,我就不必把林玉芳或安丽的像片给他看并重复相同的谎言了。我应当为他另砌一个谎言炉灶才好。于是,我向老爸说,虽然您同我母亲早就结束了封建婚姻关系,而且在离婚书上也明确界定我只对母亲一方才负有瞻养责任,但是,事实上的血缘关系在我心头却是割不断的,您永远是我的父亲。我在五七年以前的表现可以证明这一点,您也认为我是很有孝心的。今后,只要我的命运稍有转机,一定会主动接您上成都,好好侍候您的晚年。我妈也是这个意思, 您知道,她心好,明大义,目前还可自食其力。这次,也是她主动提出要我每月尽可能兑五元钱给您的,叫您买点古巴糖补补身子。我认为您眼前的关键是要静下心来过日子,和衷共济,不要闹。三姐一家子不容易,人人都很惨。等我的情况好了,就好办了,您说呢?
我讲的当然全是真心话,但因难以兑现,也可视为谎言。不过,父亲脸上的愁容却为之舒展多了,而且还在落日馀辉中生出了十分美好的憧憬。为了有幸同我共济一个屋檐下,他还不断地排了长队,凭票购置了碗筷和锅瓢。在人生的边缘上,他仍在编织着一个无比悲怆的梦,包括索回财产的梦……
我同父亲的此次别离(也是永诀)之后,他即在“四清” 和“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赶回了原籍,残喘在南泉建文峰下的一处荒山野谷中,而且仍然携带着他尚未写完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一九六六年,当毛魔用括地三尺的血腥“横扫”拉开“文革” 序幕之初,我父亲就被南泉红卫兵抓去批斗、罚跪、游街、鞭打而终其一生了。时年八旬有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竟会如此煽动子辈孙辈来残害祖辈和父辈者,已足可昭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即将崩溃了,完全堕落了。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伟大和美丽,我父亲的尸体,一位辛亥志士的尸体,一位国民党人的尸体,一位四川保路运动先驱者的尸体,竟被弃置田野,包括《辛亥革命回忆录》。
我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逃离温江“牛棚”时,到了淑声姑母家才知此事的。我在恸哭中燃起了一腔怒火。如果说,我从温江逃离时还带有不少盲目性的话,那么,从野山传来的这则噩耗则使我的仇恨目标变得明确多了。但是,我并不需要明火执仗的抗争,我首先需要保住自我,先在苦难中作个刑馀的史臣,记下毛魔的罪孽与人间的不幸。倘若未及天明就倒下了,也要设法将我的心路历程和实物资料,尤其是我父亲的死因,留给未来的子孙。
其实,我父亲的死因非常简单,只因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创下了一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容的私人产业,而后者的本性却是屠杀与掠夺——活像狮王张开了吞噬前朝子孙的血盆大口。
五
我已不愿细想父亲惨死在建文峰下的那一刻尤其是那幅情景了,后来听人讲,他被毛魔红卫兵活活折磨致死之后,直至丢坑掩埋之前,乃是未能瞑目的——我觉得,他是在用他死了的怒目和不散的冤魂,向苍天,向大地,写成了一曲辛亥之殇,留下了一笔辛亥之耻。这既是一代人的不幸,更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当年的一代革命青年,翱翔在蜀水巴山的一群雄鹰——邹容、夏之时、唐式遵、但懋辛、阮蘅伯和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他们用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所换得的各自的悲惨结局,共同的命运,乃是留在百年历史烟尘中的最为不幸的一组音符,也是一曲无比悲怆的乱世绝唱。你只要想一想,掂一掂民国元年二十四岁的四川督军夏之时竟在一九五零年被中共“农协会”处死的情景就不难破译并判断谁是新中国了;同样,你只要想一想,掂一掂如今由官、商勾结霸占的“摇钱树”小温泉就不难破译并判断毛的“革命”是个什么东西了。
不过,作为辛亥一代的晚辈,作为阮蘅伯的儿子,我心中最为愧疚和遗憾的还是我不仅没有留下父亲未完的《辛亥革命回忆录》,而且连看也都懒得看一眼(倘若留些记忆在心中该多好)。这自然同当年年幼有关,乱世中,我也根本没有兴趣留意他在写什么;稍稍大一点,站在一九四九历史断裂带上,作为在大陆上相继充当了一个党国末代童子军和另一个党国首批红领巾的我,经“新中国”洗脑后,即小脑瓜中被“划清界线”,“站稳阶级立场”,尤其是被“大义灭亲”之类的血腥观念塞满之后,我更是觉得父亲的那迭手稿(装订得很像一本线装书的东西),乃属不祥之物,不仅对之兴味索然,而且还叫他烧Text Box: 了,更不要去到处“翻案”了。有一次,父亲被我“大义凛然”的“革命态度”气得发火时,冲我怒吼道:
“你是吃错药啦?莫非国父领导的辛亥革命也错啦?!”并附上了他的口头禅:“既然我是恶霸地主,为啥不敲老子的砂罐?”——他充足的理由和雄辩的诘问也委实冲淡了我心中“神圣的党文化”,后来也渐渐记住了他的一些只言片语。如今汇集起来,也可大致勾勒出阮氏家谱和父亲在辛亥前后的人生轮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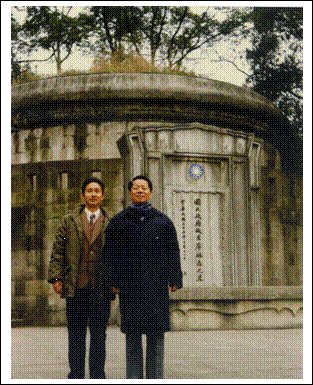
1987年冬同台湾归来收拾父亲骨骸的二哥(阮基绪)合影于林森墓前。(网路图片)
阮氏家族上溯有据的祖先是晋代名士阮籍,祖籍湖北孝感,明末匪首张献忠屠蜀后,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定居于巴县。祖父是前清举人,终身任教于学堂。父亲兄弟四人,排行老大,生于一八八四年,勤奋好学,志向明确,自幼仇恨封建帝制,不顾祖父劝阻,毅然投身反满,相继在但懋辛部、唐式遵部任秘书及秘书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时,年仅二十七岁,由于作战勇敢,文化程度较高,亦即文武双全,在摧毁四川总督府后,被调至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位于成都莲花池)任职;继后又被唐式遵师长召回,俟至将被擢升团级之时,却恳请解甲到小泉,因他不愿参加军阀混战而只是醉心于实业开拓,时年三旬左右,雄心勃勃,才华与抱负如双翼展开,但谁能预卜推翻帝制后的民国创业竟有杀身之祸呢!
呜呼,一代死于中共暴政的辛亥先行者,你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之梦莫非还能久久容忍极权政治的噩梦么?
(原标题: 被弃尸荒山的辛亥老人)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35、36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