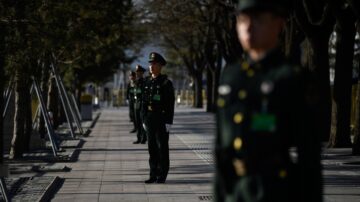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7月25日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因为父亲还不起债而被卖给地主,父亲在除夕夜羞愤自尽,女孩在大年初一从未婚夫身边、从父亲的遗体旁被拖走履约。她在债主家成为一个受尽欺凌的丫头并被强奸,在即将被卖给人贩子的前夜侥幸逃走,跑到山里变成了白毛女。这就是“白毛女喜儿”的故事——它对仇恨的利用和艺术处理,在任何时代都会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愤慨。

2011年在上海城市剧院上演的《白毛女》芭蕾舞剧。(网路图片)
歌剧《白毛女》创作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是中共“革命”文艺史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革命”作品讲究“现实主义”,很多人物和故事都讲求有原型和现实蓝本。《白毛女》的创作者们后来也经常说,这个故事取材于华北的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具体谈到,当年的这个传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直到2011年为了庆祝“中共”窃国九十周年而重排此剧,才有人讲了点细节。
“白毛仙姑”的故事有好多版本,大多没有“革命”内容。有说地主一直无子,喜儿作为三姨太被娶进门后还是生了个女儿,结果母女被一起赶出门;有说一家父子都看上喜儿,打了起来,出了人命,喜儿被嫁祸;还有的说小夫妻打架闹分手,女的一气之下出走……结果都是她逃到深山,几年后头发、皮肤变白,视觉类鬼。当时延安文艺领域的领导人之一周扬却“慧眼识材”,看到了这个故事的潜力,并极力推动再创作。在贺敬之等“革命”诗人的“如椽大笔”之下,这些五花八门的版本统一成了一个阶级矛盾的故事。
这出剧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一个重要成果。作为纪念这个讲话发表70周年的活动的一部分,新版的《白毛女》2012年5月底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上演。主旋律歌手谭晶演喜儿,京剧名花脸孟广禄演杨白劳,话剧影视演员雷恪生演黄世仁。幕后创作者包括了导演胡玫、为张艺谋多部电影作曲的赵季平以及总体艺术指导、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王昆。
在歌剧演出中,不管中外,掌声最多的地方往往是在名唱段之后,但是最新一版《白毛女》,最响亮的两次掌声却是跟着情节走的:一次是喜儿在深山变成白毛女后,在奶奶庙偶遇黄世仁,喜儿尖叫着追打他;还有一次是最后“区长”宣布黄要被法办。虽然从头至尾掌声都不算热烈,但这些掌声仍热反映出,这出戏跟几十年前一样,在激发着观众们支持惩治坏人的心声。
然而这出戏在当年激发出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却是今天的观众所不能想象的,甚至可能是它的创作者们最初也没料到的。
整出悲剧的起点是关于土地的矛盾——杨白劳家欠了地主黄世仁的地租以及利息。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执行的是跟国统区类似的土地政策。它的核心内容是让地主减租减息,使得农民不至于因为年景不好、交不起地租而放弃耕种从而影响抗战。 在此剧最成熟的版本最后一幕中,斗争黄世仁的群众合唱:“为什么你明减暗不减”,说的就是这个。
《白毛女》于1945年4月首演。8月,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旋即开始了为争取农民对中共的支持而进行的“土地改革”。改革内容是从地主和有钱人手中夺取土地和财产,再分给农民。土改的第一步是逻辑建设,让穷人认识到,他们的苦统统可以归因到地主的“剥削”和“为富不仁”。
囿于创作时期的现实,《白毛女》并没有直接否定地租及利息的合理合法性,但以女抵债以及喜儿被欺凌的情节,已经足够对观众进行有效的情感动员。在官方推动下,这个弱女子受欺受辱的故事、这个由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哭诉大作在“解放区”迅速传开,配合了土改的整个过程。《白毛女》所到之处无不激起观众对喜儿一家的同情和对地主的仇恨。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毛女》可谓是生逢其时。主创贺敬之最近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首演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送来贺信,说了三点:“第一:《白毛女》是‘适时的’、生动的‘阶级’教育。第二: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三:黄世仁该枪毙。”
“勇敢”直面创作难题
《白毛女》也有诸多其它艺术形式的改编。比如1950年田华版电影故事片、七十年代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也被拍成了电影)、以及不怎么为大家熟知的李少春、杜近芳版的京剧。而歌剧本身,也一直不断地在修改完善,直到六十年代初,形成了一个艺术水平非常高超的作品。
七十年代末之后,依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几次复排,为缩小篇幅是一方面;为适应时代需要,改动某些细节是另一方面。在最初版本中,黄世仁并没被枪毙,故事结束于喜儿从山里被接回,连批斗会都没开。在中央领导的指导下,喜儿和乡亲们改为开了一场批斗大会,“区长”宣布判处黄世仁死刑,立即执行,然后黄被拖到后台,伴随着群众的欢歌和“毛主席万岁”的呼喊, 后台“当”地一声枪响,地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谭晶版的改编者们,显然是考虑到了当今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把结尾改成了“区长”宣布把黄“交给执法机关依法惩处。”
在这些不断的改编、改动中,对于喜儿被强奸及其后果的处理可谓是一个难点。中国的八十年代之前的“革命”文艺,对于性这个话题一般是回避的。我能够想到的只有郭兰英演唱、讲述雷锋回忆过去的叙事歌曲《八月十五月儿明》,里面一句“妈妈她受凌辱悬梁自尽”,还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常宝唱“我娘却跳涧身亡”一句,暗含她娘被土匪掳走后可能受到性侵的意味。这些都是模糊地点到为止、一笔带过,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提及。性侵带来的屈辱太严重,比丢了命还严重。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芭蕾舞版《白毛女》更是让黄世仁完全没有得逞。
《白毛女》最初的创作者却“勇敢”正视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强奸是一场很重要的戏。从黄世仁几次接近喜儿,到最后他得手把她拖到侧幕或中门下,到事后喜儿独自上场悲鸣而歌,有很大的篇幅,从而使得这一环节成为“揭露地主罪行、从道德上打倒他的非常有力的武器”。
但是在怎样处理强奸的后果?创作者还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抉择。
在最初版本里,喜儿受辱后怀孕,她甚至幻想可以因此嫁给黄世仁。从黄家逃出后,她还在山里生下小孩,并把他养大。田华版的电影中,有喜儿怀孕后仍在推磨,以及在风雨中生下小孩的情节。但是,这带来了一个伦理和政治掺杂的问题。一个“无产阶级”的女儿怀上了地主的孩子,这孩子怎么办呢?是算无产阶级的孩子还是地主的孩子呢?大家还意识到,喜儿怀孕后的幻想也是不妥的,它弱化了纯粹的、天然的阶级仇恨。所以,喜儿作为一个受到性压迫的女性、作为一个母亲所面临的困境统统被删去。不过,在最新一般谭晶主演的《白毛女》歌剧中,又恢复了怀孕的情节,令人很好奇这次的编导们是怎么想的。当然,这孩子后来怎么样,就没交待了。
“大型民族歌剧”
《白毛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艺术成就。这部戏融合了西洋歌剧的框架、中国北方戏曲和民歌的音乐,以及话剧和戏曲的表演方法;配器上以民乐为主,辅以少量西洋乐器加强效果。其中的音乐,不管是甜美亲切的《北风吹》、欢快的《扎红头绳》,还是喷发着仇恨火焰的《恨似高山仇似海》,以及极象西洋歌剧终曲的《我说,我要说!》都非常成功。
这出戏最成熟的制作当属六十年代的郭兰英版。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这一版的视频资料,但是从音频资料中,我仍能感受到它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里面的角色个个过硬,连唱黄母的女中音李波的声音和表演都十分出色。当然,这个版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喜儿的扮演者郭兰英。作为一个民歌演唱者,郭兰英的成就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作为一个山西梆子演员出身的歌剧演员,她的演唱和表演的表现力绝对可以堪比很多世界级戏剧女高音。称她为中国的玛利亚·卡拉斯(Maria Callas)也不过分。
在郭兰英之后,又先后有彭丽媛版、万山红版,到现在的谭晶版,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从万山红版开始,《白毛女》就删掉了内容为喜儿控诉为主的终曲 (Finale)。 这段终曲,有喜儿独唱,有她跟王大婶、张二婶的重唱,有合唱,互相交织,非常好听。但是编导者为了控制长度,把它删掉了。到了谭晶版,没有恢复终曲,却狗尾续貂地加上了专为新版创作的、与原作风格很不搭的序曲和几段合唱。
在歌唱方面,谭晶那金铁霖派的大颤音,并不像是一个北方的农村姑娘。她变成白毛女后穿戴整齐光鲜的白衣白裤白头发,像是要去参加万圣节晚会。她的表演,没什么张力,基本没有进入角色,一直是游离的。孟广禄演杨白劳,一直在注意克服他铜锤花脸瓮声瓮气的头腔共鸣,唱得谨小慎微,只是在情绪强烈的台词中表现稍好些。相比之下,倒是没受过什么歌唱训练的雷恪生和祝延平(饰赵大叔,1983年在电视剧《水浒传》里演武松的那位)更有扯开嗓子就唱的原生态味道。
一位专业学习民族声乐的歌手曾对我说:如果不是民族唱法被认为适于承载主弦律音乐,它可能早已退出主流舞台了。即使是《白毛女》这样的民族声乐的精品,也不能逃脱这个命运。
所以,这个版本,只是一个拼凑的应景之作。我不能想象会有什么国际观众会去看这出戏,我看的那场也确实没什么外国人,但是制作者还是进行了国际化的努力。开幕时,在舞台的大纱屏上打上了巨大的红旗投影,上书中英双语:“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Grand Nationalist Opera:White-haired Girl”。Nationalist 是“民族主义者”的意思。
作者李小龙是戏剧爱好者。
原标题:革命的虚构:歌剧《白毛女》幕后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2011年在上海城市剧院上演的《白毛女》芭蕾舞剧。(网路图片)
歌剧《白毛女》创作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是中共“革命”文艺史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革命”作品讲究“现实主义”,很多人物和故事都讲求有原型和现实蓝本。《白毛女》的创作者们后来也经常说,这个故事取材于华北的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具体谈到,当年的这个传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直到2011年为了庆祝“中共”窃国九十周年而重排此剧,才有人讲了点细节。
“白毛仙姑”的故事有好多版本,大多没有“革命”内容。有说地主一直无子,喜儿作为三姨太被娶进门后还是生了个女儿,结果母女被一起赶出门;有说一家父子都看上喜儿,打了起来,出了人命,喜儿被嫁祸;还有的说小夫妻打架闹分手,女的一气之下出走……结果都是她逃到深山,几年后头发、皮肤变白,视觉类鬼。当时延安文艺领域的领导人之一周扬却“慧眼识材”,看到了这个故事的潜力,并极力推动再创作。在贺敬之等“革命”诗人的“如椽大笔”之下,这些五花八门的版本统一成了一个阶级矛盾的故事。
这出剧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一个重要成果。作为纪念这个讲话发表70周年的活动的一部分,新版的《白毛女》2012年5月底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上演。主旋律歌手谭晶演喜儿,京剧名花脸孟广禄演杨白劳,话剧影视演员雷恪生演黄世仁。幕后创作者包括了导演胡玫、为张艺谋多部电影作曲的赵季平以及总体艺术指导、第一代喜儿的扮演者王昆。
在歌剧演出中,不管中外,掌声最多的地方往往是在名唱段之后,但是最新一版《白毛女》,最响亮的两次掌声却是跟着情节走的:一次是喜儿在深山变成白毛女后,在奶奶庙偶遇黄世仁,喜儿尖叫着追打他;还有一次是最后“区长”宣布黄要被法办。虽然从头至尾掌声都不算热烈,但这些掌声仍热反映出,这出戏跟几十年前一样,在激发着观众们支持惩治坏人的心声。
然而这出戏在当年激发出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却是今天的观众所不能想象的,甚至可能是它的创作者们最初也没料到的。
整出悲剧的起点是关于土地的矛盾——杨白劳家欠了地主黄世仁的地租以及利息。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执行的是跟国统区类似的土地政策。它的核心内容是让地主减租减息,使得农民不至于因为年景不好、交不起地租而放弃耕种从而影响抗战。 在此剧最成熟的版本最后一幕中,斗争黄世仁的群众合唱:“为什么你明减暗不减”,说的就是这个。
《白毛女》于1945年4月首演。8月,日本投降,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旋即开始了为争取农民对中共的支持而进行的“土地改革”。改革内容是从地主和有钱人手中夺取土地和财产,再分给农民。土改的第一步是逻辑建设,让穷人认识到,他们的苦统统可以归因到地主的“剥削”和“为富不仁”。
囿于创作时期的现实,《白毛女》并没有直接否定地租及利息的合理合法性,但以女抵债以及喜儿被欺凌的情节,已经足够对观众进行有效的情感动员。在官方推动下,这个弱女子受欺受辱的故事、这个由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哭诉大作在“解放区”迅速传开,配合了土改的整个过程。《白毛女》所到之处无不激起观众对喜儿一家的同情和对地主的仇恨。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毛女》可谓是生逢其时。主创贺敬之最近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首演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就送来贺信,说了三点:“第一:《白毛女》是‘适时的’、生动的‘阶级’教育。第二: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三:黄世仁该枪毙。”
“勇敢”直面创作难题
《白毛女》也有诸多其它艺术形式的改编。比如1950年田华版电影故事片、七十年代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也被拍成了电影)、以及不怎么为大家熟知的李少春、杜近芳版的京剧。而歌剧本身,也一直不断地在修改完善,直到六十年代初,形成了一个艺术水平非常高超的作品。
七十年代末之后,依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几次复排,为缩小篇幅是一方面;为适应时代需要,改动某些细节是另一方面。在最初版本中,黄世仁并没被枪毙,故事结束于喜儿从山里被接回,连批斗会都没开。在中央领导的指导下,喜儿和乡亲们改为开了一场批斗大会,“区长”宣布判处黄世仁死刑,立即执行,然后黄被拖到后台,伴随着群众的欢歌和“毛主席万岁”的呼喊, 后台“当”地一声枪响,地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谭晶版的改编者们,显然是考虑到了当今建设法治社会的要求,把结尾改成了“区长”宣布把黄“交给执法机关依法惩处。”
在这些不断的改编、改动中,对于喜儿被强奸及其后果的处理可谓是一个难点。中国的八十年代之前的“革命”文艺,对于性这个话题一般是回避的。我能够想到的只有郭兰英演唱、讲述雷锋回忆过去的叙事歌曲《八月十五月儿明》,里面一句“妈妈她受凌辱悬梁自尽”,还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常宝唱“我娘却跳涧身亡”一句,暗含她娘被土匪掳走后可能受到性侵的意味。这些都是模糊地点到为止、一笔带过,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提及。性侵带来的屈辱太严重,比丢了命还严重。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芭蕾舞版《白毛女》更是让黄世仁完全没有得逞。
《白毛女》最初的创作者却“勇敢”正视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强奸是一场很重要的戏。从黄世仁几次接近喜儿,到最后他得手把她拖到侧幕或中门下,到事后喜儿独自上场悲鸣而歌,有很大的篇幅,从而使得这一环节成为“揭露地主罪行、从道德上打倒他的非常有力的武器”。
但是在怎样处理强奸的后果?创作者还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抉择。
在最初版本里,喜儿受辱后怀孕,她甚至幻想可以因此嫁给黄世仁。从黄家逃出后,她还在山里生下小孩,并把他养大。田华版的电影中,有喜儿怀孕后仍在推磨,以及在风雨中生下小孩的情节。但是,这带来了一个伦理和政治掺杂的问题。一个“无产阶级”的女儿怀上了地主的孩子,这孩子怎么办呢?是算无产阶级的孩子还是地主的孩子呢?大家还意识到,喜儿怀孕后的幻想也是不妥的,它弱化了纯粹的、天然的阶级仇恨。所以,喜儿作为一个受到性压迫的女性、作为一个母亲所面临的困境统统被删去。不过,在最新一般谭晶主演的《白毛女》歌剧中,又恢复了怀孕的情节,令人很好奇这次的编导们是怎么想的。当然,这孩子后来怎么样,就没交待了。
“大型民族歌剧”
《白毛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艺术成就。这部戏融合了西洋歌剧的框架、中国北方戏曲和民歌的音乐,以及话剧和戏曲的表演方法;配器上以民乐为主,辅以少量西洋乐器加强效果。其中的音乐,不管是甜美亲切的《北风吹》、欢快的《扎红头绳》,还是喷发着仇恨火焰的《恨似高山仇似海》,以及极象西洋歌剧终曲的《我说,我要说!》都非常成功。
这出戏最成熟的制作当属六十年代的郭兰英版。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这一版的视频资料,但是从音频资料中,我仍能感受到它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里面的角色个个过硬,连唱黄母的女中音李波的声音和表演都十分出色。当然,这个版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喜儿的扮演者郭兰英。作为一个民歌演唱者,郭兰英的成就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作为一个山西梆子演员出身的歌剧演员,她的演唱和表演的表现力绝对可以堪比很多世界级戏剧女高音。称她为中国的玛利亚·卡拉斯(Maria Callas)也不过分。
在郭兰英之后,又先后有彭丽媛版、万山红版,到现在的谭晶版,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从万山红版开始,《白毛女》就删掉了内容为喜儿控诉为主的终曲 (Finale)。 这段终曲,有喜儿独唱,有她跟王大婶、张二婶的重唱,有合唱,互相交织,非常好听。但是编导者为了控制长度,把它删掉了。到了谭晶版,没有恢复终曲,却狗尾续貂地加上了专为新版创作的、与原作风格很不搭的序曲和几段合唱。
在歌唱方面,谭晶那金铁霖派的大颤音,并不像是一个北方的农村姑娘。她变成白毛女后穿戴整齐光鲜的白衣白裤白头发,像是要去参加万圣节晚会。她的表演,没什么张力,基本没有进入角色,一直是游离的。孟广禄演杨白劳,一直在注意克服他铜锤花脸瓮声瓮气的头腔共鸣,唱得谨小慎微,只是在情绪强烈的台词中表现稍好些。相比之下,倒是没受过什么歌唱训练的雷恪生和祝延平(饰赵大叔,1983年在电视剧《水浒传》里演武松的那位)更有扯开嗓子就唱的原生态味道。
一位专业学习民族声乐的歌手曾对我说:如果不是民族唱法被认为适于承载主弦律音乐,它可能早已退出主流舞台了。即使是《白毛女》这样的民族声乐的精品,也不能逃脱这个命运。
所以,这个版本,只是一个拼凑的应景之作。我不能想象会有什么国际观众会去看这出戏,我看的那场也确实没什么外国人,但是制作者还是进行了国际化的努力。开幕时,在舞台的大纱屏上打上了巨大的红旗投影,上书中英双语:“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 Grand Nationalist Opera:White-haired Girl”。Nationalist 是“民族主义者”的意思。
作者李小龙是戏剧爱好者。
原标题:革命的虚构:歌剧《白毛女》幕后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