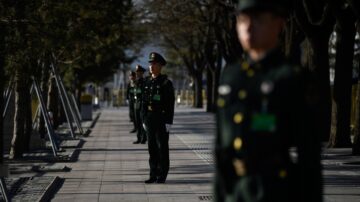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8月26日讯】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是中国一代文豪,于1946年前的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杀。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着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的代表作是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这两部作品现已列入中国初高中语文必读书目,和大学中文专业必读书目。《茶馆》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高中华文文学必修的作品。

中国着名作家老舍 (网路图片)
其中包括三百多万字的小说,四十二部戏剧,约三百首旧体诗等。他的作品多为悲剧,作品的语言以北京方言为主,风格幽默。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馀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1956年到1957年,老舍创作了经典话剧《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元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在休息时交谈 (网路图片)
不堪凌辱 太平湖自尽
尽管老舍一直顺从,但体制却容不下像他这样的传统士大夫和精神贵族。诱惑迫使他在50年代开始参与各项批判整人的政治运动,并且在文革中自己也被迫害致死。
1966年8月23日,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 “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
“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但其家人拒绝他进入家门,要他好好“反省”;而红卫兵组织亦要求他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从家中离开。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当日深夜,中国近代大文豪老舍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死不见尸 血衣残片入葬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老舍)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老舍与家人合影。左起老舍、胡絜青、舒立、舒乙、舒雨、舒济 (网路图片)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文革被扭曲人性 不是“斗”别人就是被别人“斗”
回想老舍15年前所经历的,也就是文革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作为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作家老舍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文化人的清高、文雅、善良和操守。1951年10月,《人民文学》刊登了老舍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这篇关于描述仇恨批斗会的文章,令国内知识界认识感到大为惊讶,有人几乎不相信这会是出自老舍之手,老舍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在北京天坛举行的控诉批斗恶霸大会,他和几百个嘴一起喊“该打!该打!”,他称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他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问题专家林辉曾撰文表示,在经历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后,真正有良知和骨气的知识份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馀的知识份子的脊梁再也无法挺直: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附和中共,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也被摧毁,而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知识份子基本在学术上是无成就可言。
澳洲学院派华人画家赵法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从1949年篡政到今天,一直就把文化当成欺骗民众的手段,用暴力打击敢于说真话的人,用恐怖要挟中国文化界,将中国传统文化拦腰砍断,使得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断层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养天地间正气”的风貌,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朴自然、高雅收敛、清新的优美风格,如今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着名作家老舍 (网路图片)
其中包括三百多万字的小说,四十二部戏剧,约三百首旧体诗等。他的作品多为悲剧,作品的语言以北京方言为主,风格幽默。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馀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1956年到1957年,老舍创作了经典话剧《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元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在休息时交谈 (网路图片)
不堪凌辱 太平湖自尽
尽管老舍一直顺从,但体制却容不下像他这样的传统士大夫和精神贵族。诱惑迫使他在50年代开始参与各项批判整人的政治运动,并且在文革中自己也被迫害致死。
1966年8月23日,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文联,老舍与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惨遭污辱、毒打。血流满面、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 “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
“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但其家人拒绝他进入家门,要他好好“反省”;而红卫兵组织亦要求他24日上午到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从家中离开。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当日深夜,中国近代大文豪老舍自沉于太平湖,年67岁。
死不见尸 血衣残片入葬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老舍)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老舍与家人合影。左起老舍、胡絜青、舒立、舒乙、舒雨、舒济 (网路图片)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文革被扭曲人性 不是“斗”别人就是被别人“斗”
回想老舍15年前所经历的,也就是文革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作为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作家老舍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文化人的清高、文雅、善良和操守。1951年10月,《人民文学》刊登了老舍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这篇关于描述仇恨批斗会的文章,令国内知识界认识感到大为惊讶,有人几乎不相信这会是出自老舍之手,老舍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在北京天坛举行的控诉批斗恶霸大会,他和几百个嘴一起喊“该打!该打!”,他称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他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问题专家林辉曾撰文表示,在经历了反右和十年文革后,真正有良知和骨气的知识份子大多被迫害致死,剩馀的知识份子的脊梁再也无法挺直:或选择沉默,或选择附和中共,人们分辨真伪的健康思维能力也被摧毁,而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知识份子基本在学术上是无成就可言。
澳洲学院派华人画家赵法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从1949年篡政到今天,一直就把文化当成欺骗民众的手段,用暴力打击敢于说真话的人,用恐怖要挟中国文化界,将中国传统文化拦腰砍断,使得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断层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养天地间正气”的风貌,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朴自然、高雅收敛、清新的优美风格,如今几乎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