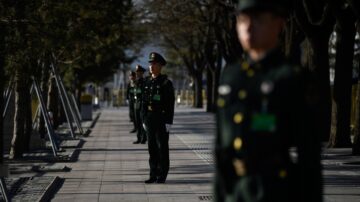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3月20日讯】8月24日——老舍的忌日。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异常普通的日子,对我却早具有了一种浓郁的历史的“罗生门”意味。它时而明晰,时而模糊。有时,我觉得离它越来越近,但瞬间又彷彿觉得它渐行渐远了。我多么希望能成为一个幸运者,可以捕捉到历史的影子。
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来的一场噩梦
我是1993年开始从追踪采访调查老舍之死,切入来研究老舍的。刚开始想法极其简单,就是想找到跟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生前所在单位北京文联遭受红卫兵批斗相关的亲历者、见证人,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记录他们的历史文本叙事,我觉着可能会反映出历史的真相。于是,从1993年开始,历经11年,不断地寻找见证者、当事人,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采访,我的困惑一次又一次增加,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我对于历史的迷惑,又稍稍地变得清晰起来。我经历了一段可以说是对历史的迷途时期,把我领到了混乱之中。我被历史弄迷惑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该相信谁。可以说,我对老舍之死的研究,使我的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老舍之死是一个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文化事件,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是要将它还原,需要藉助于口述史的叙述。而口述史的叙述来自于不同之口,口口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古”字,“古”字怎么写?十口相加为古,就是口太多,口口相传,把别人的口述逐一记下来,这就是产生文字最初时候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可以任人随意打扮吗?你抹一把,我抹一把,历史就五光十色了?可哪个才是真正的历史,从哪个涂彩之中才能追本溯源,贴近那个历史的史实真相呢?不知道。也许正因为此,20世纪爱尔兰伟大作家乔伊斯在他享有天书之誉的《尤利西斯》一书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我十分心仪这句话,他说“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来的一场恶梦。”我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梦,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醒来。不知道大家听完这场讲座,是沦入了梦中,还是能使你从梦中变得清醒一些?人人各异,看待事物、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因而对于人与事的理解也不一样。
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开创者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这本书是引导我从老舍之死的采访追踪向探询口述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切入点。看这本书,我首先直观地感受到口头诗学与口头史学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两者还是兼而有之的。弗里先生在书里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许多民族最早的文学创作样式,几乎都是像《荷马史诗》那样的英雄史诗或神话传说。而且,大多是现代民间口头承传经过长期的累积形成确定的文本创作。
1925年,美国年轻的古希腊文学专家米尔曼·帕里开始对《荷马史诗》产生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的总数约达两万八千诗行的叙述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远非荷马一人所能创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
事实上,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里,关于谁是荷马,他是什么时候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就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主要形成了分辩派与统一派的争端,即“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即有人主张《荷马史诗》是很多人写的,历代累积的,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传说,然后到了荷马这儿,他是一个修订、写定者。还有的人认为,《荷马史诗》就是由荷马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双方各执一词,没有更实证的考证来证明,学术探索步履维艰。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帕里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或思想者一样开始做口述史的田野调查采访。开始是自己,后来跟他的学生一起深入到口述史流传风气很浓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实地的考察,田野作业,发现《荷马史诗》中有相当多的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词”,这些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词”决定了《荷马史诗》既是程式的,又是传统的。同时他发现这种传统的史诗唱法只能是口头的。为了印证这个,他就深入去做田野作业。经过16个月扎实而纵深的田野作业,搜集和记录了总共约达1500种的史诗文本,在掌握了如此丰富的口头史料之后,他宣称:“我相信我将要带回美国去的手稿和口头磁碟的集成,对于研究口头叙事诗歌的生命力和功能而言,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借帕里的话说,从1993年开始我追踪采访调查老舍之死,这11年间所作的口述笔录及录下的几十盘录音带,就其史料价值来说,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昔日的太平湖真的带着老舍之死的记忆永远消失了吗?(网路图片)
我们都是历史“歌手” 时常将它唱成“荷马史诗”
帕里去世以后,他的学生洛德接过他的学术薪火,他后来在1960年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叫《故事的歌手》。这里出现了一个“歌手”的概念,我们记住这个“歌手”,后面我会多次提到。洛德在这本书的开篇引言中就强调,“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荷马是我们的故事的歌手。而且在一个更大的意义上,荷马也代表了从洪荒难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的歌手。我们的这部着作也是关于荷马以外的其他歌手的书。他们中的每一位,即使是最平庸的一位歌手,也和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荷马一样,都属于口头史诗演唱传统的一部分。现代歌手无人可以与荷马并驾齐驱。”
同时,他在对另两位学者就《伊利亚特》之中关于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分类描述所进行的阐述,提出了质疑。他说:“任何一个主题,甚至包括一种分类,都会在时间的推移中显示出其间的变异。故此,不能企望它保存着‘历史的真实’。……在史诗中呈现了事件,但是,相应的年代编排是混乱无序的。时间被缩微到了一支望远镜中。岁月流逝,各个不同时期全都被排列组合到了眼下的表演之中,……口头史诗呈现的只是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
由这儿,我就想到我所调查的老舍之死,以及以前我们印象当中的老舍之死从何而来。它是不是有很多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或者说,老舍之死是不是只是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重新塑造和建构起来的?人们口述的关于老舍之死的那些叙述跟老舍之死真实的历史真相是不是相吻合呢?换言之,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老舍之死,是否也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了许多“特定形容词”编纂而成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
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个给我们的困惑是什么呢?并非它的作者是谁,因为所有向我口述的人,也就是我所采访的这些人,都是有真名实姓的,谁谁谁,什么单位,多大年纪,1966年的时候担任什么职务,等等,全是具体而翔实的,同荷马不一样。困惑来自于史诗本身,并非作者,因为“歌手”都是有名的。而洛德讲到“歌手”作用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对歌手来说,歌就是故事本身,歌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在歌手看来,改变它就意味着讲述了一个不真实的故事,或歪曲了历史。)在歌手的观念中,他专注的稳定性并不包括词语,对他来说,词语从来没有固定过,而且故事的那些非实质性部分也从来没有固定过。他把自己的表演和我们所认为的歌,建构在稳定的叙事框架上,这就是歌手感觉到的歌。”显然,“歌手”感觉到的歌是真实的,他便拿它当真实的再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而一代一代听了“歌手”叙述的歌的“歌手”,又将他所接收到的叙述一代一代往下传,到了我们所能够接收的“歌手”向我们描述历史情形的时候,离那个最初的“歌手”就已经相距甚远了。而最初的“歌手”所传唱的故事,也可能早就已经不是历史原来的本真了。

老舍(1939年)(网路图片)
历史是一只精致的瓷瓶 发生的瞬间就打碎了
对于老舍,我们把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批斗时所发生的事情,简称叫“八二三事件”。当几十位叙述人把历史的记忆凝固在那一天讲述的时候,如果你只面对一个叙述者,你相信他说的是历史真实,便记录下来。然后,与其他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再去作对比,你会发现怎么差得那么远,怎么那么多人会在某一个历史的细节上,说法截然不同。比如,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为什么那天要去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这还算简单的。那天上午,老舍先生是几点到的?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由他的司机用专车接他去的,还是他自己坐的公共汽车?说法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穿着白衬衣、蓝衬衣,还是穿了外套?不一样。中午,老舍先生没有回家,是因为司机罢工不拉他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各说各话。下午,发生红卫兵冲击文联,把许多文化人揪斗,后来押到孔庙去“焚书坑儒”,文联内部到底是谁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到今天这个迷都没有解开。
试想,经历过那一事件的人,在事情过去了三十年以后,当他想到自己可能要为那个事件承担某种个人历史责任的时候,他敢承认是自己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吗?所以,这也就带出了口述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即随着时过境迁,历史的当事人可能调整了心态。可能因为当初自己所处那个历史事件当中的角色和立场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构记忆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重新编排了。换言之,如果说“八二三事件”是一个瓷瓶,在它发生的瞬间就已经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们今天只是在捡拾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碎片而已,并尽可能地将这些碎片还原拼接。但可能再还原成那一个精致的瓷瓶吗?绝对不可能!西方有史学家强调,在历史发生的瞬间,已发生的历史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历史永远不可能和它见证者的口吻相一致。
这样的话,已经过去的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来,尽可能地逼近那个历史真相,还原出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历史所带给我们应有的启迪或启发。如果历史陷入了虚无,我们也没必要读历史,因为没有真实可言,历史就是故事,历史就是小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老舍先生的遗体在太平湖被发现后,是如何打捞的,有三位“歌手”所唱的三个版本,该如何甄别?这对于研究老舍及整个事件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如何被红卫兵揪出来?如何被送到孔庙去批斗挨打?又如何被送回文联?如何在那天晚上被扭送到派出所?一天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的细节,诸多的口述者所说,很难在某一个点上完全统一,支离破碎,都是散在地上的一个个碎片,几乎无法把它拼接起来。如果能找到哪个事情和哪个事情能够相连,或许还容易把它做成一个复原品,但是现在,这片和那片根本就找不着,根本就不相连。因此,这也就造成了制造神话的空间,这是历史产生这种被塑造成神话的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
关于“老舍之死”从认识上,主要是三种说法,“抗争说”、“绝望说”、“脆弱说”。大体上有三类学者。第一种把“老舍之死”理解成是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抗议“文革”,是要舍生取义,与屈原同例。
持“绝望说”者,认为老舍先生一直在挣扎。中共建政以后,老舍先生曾经度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精神状态也很好。但随着50年代初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个接一个,老舍先生感到内心困惑,挣扎,煎熬。虽然在“文革”以前,很多政治运动都没有牵扯到他,但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很多朋友被牵连进去,被批判,被批斗,直到“文革”,灾难找上门来,躲不开了。他绝望,用今天的时髦词叫失去了精神家园,于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持“脆弱说”者认为,老舍先生是因为内心脆弱而经受不起打击而投湖。他们多是经历过中共建政以后一次或两次甚至三次的“老运动员”,经历过一些磨难,所以到“文革”时,他们觉得“文革”的灾难对于自己来说不过是旧伤口上又添了一个新伤而已,可能比以前疼得更厉害点,却可以忍受。他们觉得,老舍先生从中共建政以后,一直是在政治上坐顺风船,一帆风顺,从来没有经受过任何的磕磕绊绊。所以当“文革”的风雨来了以后,一下受不了了,他脆弱的心灵,脆弱的精神根本承受不住这命运的一击,倒下了。
老舍之死就是一场历史的“罗生门”
原来我在某一段时间,也有点倾向于这说或那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老舍之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就像我们很难相信那三个打捞尸体的人哪一个说的是真的一样,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把“老舍之死”的结论下在某一说上。因为“老舍之死”是复杂的,是由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有他自身性格的因素,文本中文学形象的因素,政治因素,等等,都有。
巴金先生在1984年为话剧《老舍之死》剧作写的一篇序中,说过一段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更深一层理解“老舍之死”的很有启迪的话。他说,“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指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确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也不会做出什么结论。”我们看,巴金先生的意思是,既不能简简单单地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他说老舍在抗争的同时,有幻灭,痛苦,疑惑,等等,即有很多种的因素导致了老舍先生的自杀。
我觉得,如果要做一种对比的话,简单地把它和屈原式挂钩,是有点太过直接了,我倒愿意把“老舍之死”跟王国维之死做个比较。如果从文化类型上来说,他们俩可能更有可比性。
第一点,在自杀方式上可以说都与屈原同例,为什么?投的都是水。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老舍1966年8月24日于太平湖投水,享年67岁。两者相隔39年。
第二点,两人死得都很平静,是一种理智性的自杀,而非病态的表现。他们死前都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动,不是说情绪低落、抑郁,流露出一反常态的神情,没有。而且,王国维还留了一封遗书,就是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面还有几句话,但这几句话是很关键的,人们始终探讨。什么叫“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了50岁,就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世变”的世,是世界的世,不是事情的事。这个“世变”是什么?“义务再辱,”“再”,那前面的那个“辱”是什么?留下了困惑,给研究王国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老舍先生自杀前,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虽然后来有很多“歌手”在传唱的时候,说在太平湖上漂了很多碎纸片,纸片上写满了字,人们打捞上那些字,发现是毛xx诗词《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但是,据更多的目击者说,那天湖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你看,不同的“歌手”所演唱的故事内容不一样。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第三,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看法“一直众说纷纭,甚至聚讼不已。”较经典的四个版本是“殉清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说”,还有“殉文化说。”像刚才说老舍之死有三说一样,关于王国维主要有这四说。
第四点,王国维死后,对他的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说法,对老舍之死同样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并由此做出不同的猜测和推论,两者的共同点是“罗生门”的模式。大家有看过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或是黑泽明由此改编成的着名电影《罗生门》的吗?讲一个男人身负刀伤死在竹林中,为了查明这一案件讯问了好几个有关人物,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供诉,而每一种供诉则又都不完全可信。那是因为,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莫不想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从这个细节,来看王国维之死和“老舍之死”,是不是都有这种“罗生门”的意味?
第五,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个“世变”和“再辱”是不是可以用在老舍先生身上?“世变,”“文革”对于老舍来说是不是“世变”?如果对老舍先生来说,“文革”是“再辱”,那在这个“辱”之前有没有“前辱”,“前辱”又是什么?因为在此之前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老舍先生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他可能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至少看到自己有很多朋友卷进去了,他至少可能也会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动,或许他给自己划了一个底线,假如说自己碰上这样的运动,要以死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第六,王国维在民国以后留辫子,这和老舍在中共建政以后依然穿洋装,是不是都暗示着要坚守自己原有的理念?我们知道,民国成立以后王国维留起了小辫子,梳着小辫子的国学大师也成为清华园的一道独特风景。而老舍在中共建政以后,几乎是作家当中唯一一个穿西装的,戴礼帽,拄拐棍,洋派十足。两者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象征意味吗?这都是留给我们思考的。
另外,关于老舍先生选择投水自杀的方式,和他作品当中描述的一些人物最后是以投水作为自己生命的结局,有内在联系吗?还有,老舍先生在自杀之前,走出自己的院落,跟自己的小孙女说了一句话,“来,跟爷爷说再见。”跟哪个剧本一样?《茶馆》。《茶馆》的最后一幕,王掌柜决定要自杀了,他让家人先走。家人往外走的时候,他把小孙女叫住,说:“叫爷爷再看一眼”,儿媳妇又让小孙女“跟爷爷说再见。”这跟老舍先生临死之前是一样的。老舍先生在1957年初写《茶馆》时设定的这个情节,是为自己在九年之后的自杀前从家里出走做谶语吗?再看《茶馆》的最后一幕,那三个老人,围着桌子向空中撒纸钱,这个情节印象都很深,对吧?由这个情节,是不是就生出了有些“歌手”关于太平湖面上漂浮着纸片的传唱?如果我们相信有的话,这个纸片就和《茶馆》的最后一幕,便是艺术的真实跟历史的真实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了。假如是真的,这可是太绝妙的悲剧了!即老舍在《茶馆》当中,营造了一个艺术的悲剧,他自己真实的生命终局,又用死书写了一个史实的悲剧。
关于老舍之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两个小时怎么可能说尽。关于老舍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要投太平湖,都是可以独立成章的题目。总之,有一点,我想用法国作家加缪的话作为结语。加缪说:“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不管对于老舍,对于王国维,自杀都是他们在深思熟虑中默默酝酿的伟大作品。同时也把这个作品的思想意义留给了“无言”的历史,留给了“有声”的后人。历史是“无言”的,我们是“有声”的,但是“无言”的历史无法呈现历史的答案,“有声”的我们就能给历史做定论吗?
最后,我还是带着疑问。所以,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对于历史是有了些清晰的了解呢,还是开始陷入到了一场噩梦当中。
原标题: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此篇原为演讲稿)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8月21日
相关视频:历史回顾 - 老舍的悲哀
历史回顾 - 老舍的悲哀
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来的一场噩梦
我是1993年开始从追踪采访调查老舍之死,切入来研究老舍的。刚开始想法极其简单,就是想找到跟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生前所在单位北京文联遭受红卫兵批斗相关的亲历者、见证人,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记录他们的历史文本叙事,我觉着可能会反映出历史的真相。于是,从1993年开始,历经11年,不断地寻找见证者、当事人,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采访,我的困惑一次又一次增加,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我对于历史的迷惑,又稍稍地变得清晰起来。我经历了一段可以说是对历史的迷途时期,把我领到了混乱之中。我被历史弄迷惑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该相信谁。可以说,我对老舍之死的研究,使我的历史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老舍之死是一个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文化事件,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是要将它还原,需要藉助于口述史的叙述。而口述史的叙述来自于不同之口,口口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古”字,“古”字怎么写?十口相加为古,就是口太多,口口相传,把别人的口述逐一记下来,这就是产生文字最初时候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可以任人随意打扮吗?你抹一把,我抹一把,历史就五光十色了?可哪个才是真正的历史,从哪个涂彩之中才能追本溯源,贴近那个历史的史实真相呢?不知道。也许正因为此,20世纪爱尔兰伟大作家乔伊斯在他享有天书之誉的《尤利西斯》一书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我十分心仪这句话,他说“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来的一场恶梦。”我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梦,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醒来。不知道大家听完这场讲座,是沦入了梦中,还是能使你从梦中变得清醒一些?人人各异,看待事物、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因而对于人与事的理解也不一样。
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开创者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这本书是引导我从老舍之死的采访追踪向探询口述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切入点。看这本书,我首先直观地感受到口头诗学与口头史学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在某种程度上两者还是兼而有之的。弗里先生在书里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许多民族最早的文学创作样式,几乎都是像《荷马史诗》那样的英雄史诗或神话传说。而且,大多是现代民间口头承传经过长期的累积形成确定的文本创作。
1925年,美国年轻的古希腊文学专家米尔曼·帕里开始对《荷马史诗》产生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两部被后人称为伟大史诗的总数约达两万八千诗行的叙述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远非荷马一人所能创作,而肯定是希腊人集体的遗产。
事实上,在荷马时代稍后不久的岁月里,关于谁是荷马,他是什么时候创作出那些我们惯常归功于他的诗作的,就已经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没有留下关于《荷马史诗》创作者的确切记载,后世的学者们只能根据零星的线索,来做各式各样的主观推断。主要形成了分辩派与统一派的争端,即“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两个截然对立的学术派别,即有人主张《荷马史诗》是很多人写的,历代累积的,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传说,然后到了荷马这儿,他是一个修订、写定者。还有的人认为,《荷马史诗》就是由荷马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双方各执一词,没有更实证的考证来证明,学术探索步履维艰。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帕里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或思想者一样开始做口述史的田野调查采访。开始是自己,后来跟他的学生一起深入到口述史流传风气很浓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实地的考察,田野作业,发现《荷马史诗》中有相当多的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词”,这些高度程式化的“特定形容词”决定了《荷马史诗》既是程式的,又是传统的。同时他发现这种传统的史诗唱法只能是口头的。为了印证这个,他就深入去做田野作业。经过16个月扎实而纵深的田野作业,搜集和记录了总共约达1500种的史诗文本,在掌握了如此丰富的口头史料之后,他宣称:“我相信我将要带回美国去的手稿和口头磁碟的集成,对于研究口头叙事诗歌的生命力和功能而言,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借帕里的话说,从1993年开始我追踪采访调查老舍之死,这11年间所作的口述笔录及录下的几十盘录音带,就其史料价值来说,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昔日的太平湖真的带着老舍之死的记忆永远消失了吗?(网路图片)
我们都是历史“歌手” 时常将它唱成“荷马史诗”
帕里去世以后,他的学生洛德接过他的学术薪火,他后来在1960年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叫《故事的歌手》。这里出现了一个“歌手”的概念,我们记住这个“歌手”,后面我会多次提到。洛德在这本书的开篇引言中就强调,“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荷马是我们的故事的歌手。而且在一个更大的意义上,荷马也代表了从洪荒难稽的古代直至今天所有的故事的歌手。我们的这部着作也是关于荷马以外的其他歌手的书。他们中的每一位,即使是最平庸的一位歌手,也和其中最具天才的代表荷马一样,都属于口头史诗演唱传统的一部分。现代歌手无人可以与荷马并驾齐驱。”
同时,他在对另两位学者就《伊利亚特》之中关于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分类描述所进行的阐述,提出了质疑。他说:“任何一个主题,甚至包括一种分类,都会在时间的推移中显示出其间的变异。故此,不能企望它保存着‘历史的真实’。……在史诗中呈现了事件,但是,相应的年代编排是混乱无序的。时间被缩微到了一支望远镜中。岁月流逝,各个不同时期全都被排列组合到了眼下的表演之中,……口头史诗呈现的只是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
由这儿,我就想到我所调查的老舍之死,以及以前我们印象当中的老舍之死从何而来。它是不是有很多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或者说,老舍之死是不是只是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重新塑造和建构起来的?人们口述的关于老舍之死的那些叙述跟老舍之死真实的历史真相是不是相吻合呢?换言之,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老舍之死,是否也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了许多“特定形容词”编纂而成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
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个给我们的困惑是什么呢?并非它的作者是谁,因为所有向我口述的人,也就是我所采访的这些人,都是有真名实姓的,谁谁谁,什么单位,多大年纪,1966年的时候担任什么职务,等等,全是具体而翔实的,同荷马不一样。困惑来自于史诗本身,并非作者,因为“歌手”都是有名的。而洛德讲到“歌手”作用的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对歌手来说,歌就是故事本身,歌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在歌手看来,改变它就意味着讲述了一个不真实的故事,或歪曲了历史。)在歌手的观念中,他专注的稳定性并不包括词语,对他来说,词语从来没有固定过,而且故事的那些非实质性部分也从来没有固定过。他把自己的表演和我们所认为的歌,建构在稳定的叙事框架上,这就是歌手感觉到的歌。”显然,“歌手”感觉到的歌是真实的,他便拿它当真实的再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而一代一代听了“歌手”叙述的歌的“歌手”,又将他所接收到的叙述一代一代往下传,到了我们所能够接收的“歌手”向我们描述历史情形的时候,离那个最初的“歌手”就已经相距甚远了。而最初的“歌手”所传唱的故事,也可能早就已经不是历史原来的本真了。

老舍(1939年)(网路图片)
历史是一只精致的瓷瓶 发生的瞬间就打碎了
对于老舍,我们把他在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批斗时所发生的事情,简称叫“八二三事件”。当几十位叙述人把历史的记忆凝固在那一天讲述的时候,如果你只面对一个叙述者,你相信他说的是历史真实,便记录下来。然后,与其他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再去作对比,你会发现怎么差得那么远,怎么那么多人会在某一个历史的细节上,说法截然不同。比如,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为什么那天要去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这还算简单的。那天上午,老舍先生是几点到的?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由他的司机用专车接他去的,还是他自己坐的公共汽车?说法不一样。老舍先生是穿着白衬衣、蓝衬衣,还是穿了外套?不一样。中午,老舍先生没有回家,是因为司机罢工不拉他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是各说各话。下午,发生红卫兵冲击文联,把许多文化人揪斗,后来押到孔庙去“焚书坑儒”,文联内部到底是谁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到今天这个迷都没有解开。
试想,经历过那一事件的人,在事情过去了三十年以后,当他想到自己可能要为那个事件承担某种个人历史责任的时候,他敢承认是自己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吗?所以,这也就带出了口述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即随着时过境迁,历史的当事人可能调整了心态。可能因为当初自己所处那个历史事件当中的角色和立场的不同,到今天重新建构记忆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重新编排了。换言之,如果说“八二三事件”是一个瓷瓶,在它发生的瞬间就已经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们今天只是在捡拾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碎片而已,并尽可能地将这些碎片还原拼接。但可能再还原成那一个精致的瓷瓶吗?绝对不可能!西方有史学家强调,在历史发生的瞬间,已发生的历史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历史永远不可能和它见证者的口吻相一致。
这样的话,已经过去的历史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来,尽可能地逼近那个历史真相,还原出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历史所带给我们应有的启迪或启发。如果历史陷入了虚无,我们也没必要读历史,因为没有真实可言,历史就是故事,历史就是小说,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老舍先生的遗体在太平湖被发现后,是如何打捞的,有三位“歌手”所唱的三个版本,该如何甄别?这对于研究老舍及整个事件都不是十分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如何被红卫兵揪出来?如何被送到孔庙去批斗挨打?又如何被送回文联?如何在那天晚上被扭送到派出所?一天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的细节,诸多的口述者所说,很难在某一个点上完全统一,支离破碎,都是散在地上的一个个碎片,几乎无法把它拼接起来。如果能找到哪个事情和哪个事情能够相连,或许还容易把它做成一个复原品,但是现在,这片和那片根本就找不着,根本就不相连。因此,这也就造成了制造神话的空间,这是历史产生这种被塑造成神话的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
关于“老舍之死”从认识上,主要是三种说法,“抗争说”、“绝望说”、“脆弱说”。大体上有三类学者。第一种把“老舍之死”理解成是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抗议“文革”,是要舍生取义,与屈原同例。
持“绝望说”者,认为老舍先生一直在挣扎。中共建政以后,老舍先生曾经度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精神状态也很好。但随着50年代初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个接一个,老舍先生感到内心困惑,挣扎,煎熬。虽然在“文革”以前,很多政治运动都没有牵扯到他,但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很多朋友被牵连进去,被批判,被批斗,直到“文革”,灾难找上门来,躲不开了。他绝望,用今天的时髦词叫失去了精神家园,于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持“脆弱说”者认为,老舍先生是因为内心脆弱而经受不起打击而投湖。他们多是经历过中共建政以后一次或两次甚至三次的“老运动员”,经历过一些磨难,所以到“文革”时,他们觉得“文革”的灾难对于自己来说不过是旧伤口上又添了一个新伤而已,可能比以前疼得更厉害点,却可以忍受。他们觉得,老舍先生从中共建政以后,一直是在政治上坐顺风船,一帆风顺,从来没有经受过任何的磕磕绊绊。所以当“文革”的风雨来了以后,一下受不了了,他脆弱的心灵,脆弱的精神根本承受不住这命运的一击,倒下了。
老舍之死就是一场历史的“罗生门”
原来我在某一段时间,也有点倾向于这说或那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老舍之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就像我们很难相信那三个打捞尸体的人哪一个说的是真的一样,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把“老舍之死”的结论下在某一说上。因为“老舍之死”是复杂的,是由复杂的因素导致的,有他自身性格的因素,文本中文学形象的因素,政治因素,等等,都有。
巴金先生在1984年为话剧《老舍之死》剧作写的一篇序中,说过一段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更深一层理解“老舍之死”的很有启迪的话。他说,“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指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确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也不会做出什么结论。”我们看,巴金先生的意思是,既不能简简单单地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他说老舍在抗争的同时,有幻灭,痛苦,疑惑,等等,即有很多种的因素导致了老舍先生的自杀。
我觉得,如果要做一种对比的话,简单地把它和屈原式挂钩,是有点太过直接了,我倒愿意把“老舍之死”跟王国维之死做个比较。如果从文化类型上来说,他们俩可能更有可比性。
第一点,在自杀方式上可以说都与屈原同例,为什么?投的都是水。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终年50岁;老舍1966年8月24日于太平湖投水,享年67岁。两者相隔39年。
第二点,两人死得都很平静,是一种理智性的自杀,而非病态的表现。他们死前都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动,不是说情绪低落、抑郁,流露出一反常态的神情,没有。而且,王国维还留了一封遗书,就是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后面还有几句话,但这几句话是很关键的,人们始终探讨。什么叫“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活了50岁,就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世变”的世,是世界的世,不是事情的事。这个“世变”是什么?“义务再辱,”“再”,那前面的那个“辱”是什么?留下了困惑,给研究王国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老舍先生自杀前,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虽然后来有很多“歌手”在传唱的时候,说在太平湖上漂了很多碎纸片,纸片上写满了字,人们打捞上那些字,发现是毛xx诗词《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但是,据更多的目击者说,那天湖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你看,不同的“歌手”所演唱的故事内容不一样。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第三,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看法“一直众说纷纭,甚至聚讼不已。”较经典的四个版本是“殉清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说”,还有“殉文化说。”像刚才说老舍之死有三说一样,关于王国维主要有这四说。
第四点,王国维死后,对他的死因有各不相同的说法,对老舍之死同样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并由此做出不同的猜测和推论,两者的共同点是“罗生门”的模式。大家有看过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或是黑泽明由此改编成的着名电影《罗生门》的吗?讲一个男人身负刀伤死在竹林中,为了查明这一案件讯问了好几个有关人物,每个人都有各不相同的供诉,而每一种供诉则又都不完全可信。那是因为,每一个相关人物都莫不想为自己的卑鄙做掩饰,为自己的虚荣做辩护。从这个细节,来看王国维之死和“老舍之死”,是不是都有这种“罗生门”的意味?
第五,从王国维留下的遗书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个“世变”和“再辱”是不是可以用在老舍先生身上?“世变,”“文革”对于老舍来说是不是“世变”?如果对老舍先生来说,“文革”是“再辱”,那在这个“辱”之前有没有“前辱”,“前辱”又是什么?因为在此之前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老舍先生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他可能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至少看到自己有很多朋友卷进去了,他至少可能也会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动,或许他给自己划了一个底线,假如说自己碰上这样的运动,要以死抗争,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第六,王国维在民国以后留辫子,这和老舍在中共建政以后依然穿洋装,是不是都暗示着要坚守自己原有的理念?我们知道,民国成立以后王国维留起了小辫子,梳着小辫子的国学大师也成为清华园的一道独特风景。而老舍在中共建政以后,几乎是作家当中唯一一个穿西装的,戴礼帽,拄拐棍,洋派十足。两者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象征意味吗?这都是留给我们思考的。
另外,关于老舍先生选择投水自杀的方式,和他作品当中描述的一些人物最后是以投水作为自己生命的结局,有内在联系吗?还有,老舍先生在自杀之前,走出自己的院落,跟自己的小孙女说了一句话,“来,跟爷爷说再见。”跟哪个剧本一样?《茶馆》。《茶馆》的最后一幕,王掌柜决定要自杀了,他让家人先走。家人往外走的时候,他把小孙女叫住,说:“叫爷爷再看一眼”,儿媳妇又让小孙女“跟爷爷说再见。”这跟老舍先生临死之前是一样的。老舍先生在1957年初写《茶馆》时设定的这个情节,是为自己在九年之后的自杀前从家里出走做谶语吗?再看《茶馆》的最后一幕,那三个老人,围着桌子向空中撒纸钱,这个情节印象都很深,对吧?由这个情节,是不是就生出了有些“歌手”关于太平湖面上漂浮着纸片的传唱?如果我们相信有的话,这个纸片就和《茶馆》的最后一幕,便是艺术的真实跟历史的真实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了。假如是真的,这可是太绝妙的悲剧了!即老舍在《茶馆》当中,营造了一个艺术的悲剧,他自己真实的生命终局,又用死书写了一个史实的悲剧。
关于老舍之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两个小时怎么可能说尽。关于老舍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要投太平湖,都是可以独立成章的题目。总之,有一点,我想用法国作家加缪的话作为结语。加缪说:“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不管对于老舍,对于王国维,自杀都是他们在深思熟虑中默默酝酿的伟大作品。同时也把这个作品的思想意义留给了“无言”的历史,留给了“有声”的后人。历史是“无言”的,我们是“有声”的,但是“无言”的历史无法呈现历史的答案,“有声”的我们就能给历史做定论吗?
最后,我还是带着疑问。所以,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对于历史是有了些清晰的了解呢,还是开始陷入到了一场噩梦当中。
原标题: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此篇原为演讲稿)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8月21日
相关视频:历史回顾 - 老舍的悲哀
历史回顾 - 老舍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