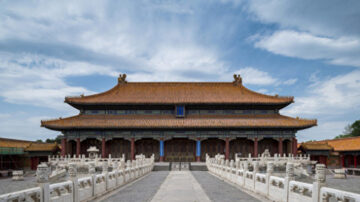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6月2日讯】张大千已经辞世三十年了,他临摹敦煌壁画的壮举,以及不朽的画作,为世人所瞩目。 然而,他奇特的经历和豁达的人生观,更是脍炙人口。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张大千幼时,家贫,曾随母、姊、兄学画,打下了绘画基础。后人重庆求精中学读书,十八岁时,张大千随兄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二十岁时,张大千由日本回国,寓居上海,曾先后拜名书法家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接着因婚姻问题,削发出家,当了一百多天和尚。还俗后,即以其佛门法名“大千”为号,从此全身心致力于书画。

张大千(网路图片)
两个一百天奇特经历
张大千一生入世甚深,“他生来就很特异的,像只猴子似的。”(宣化和尚语),所以我就用较为轻松的笔调映照大师的个性,聊表纪念与敬意。 十岁前就开始习画的你,在十七岁读中学时放学回家的路上突遭绑架,绑匪逼迫你写信以便勒索家人,却惊异于你写得一手好字,不但没伤害你,居然奉你为黑帮顾问,你在虚与委蛇了约一百天后终于重获自由。
二十一岁时,挚爱的青梅竹马兼未婚妻因病往生,从日本兼程到上海的你却因兵荒马乱、道路不靖无法赶回四川老家见她最后一面而伤心欲绝,因此萌生遁世念头,不顾家人反对,准备出家当和尚。但你发现和尚受戒要点戒疤,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太有主见的你跟住持辩论起来:“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流行烧戒。这个花样是梁武帝创造的。当年,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以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在得不到满意答覆之际,你匆忙离开寺庙。向佛之心甚强的你辗转挂单几处,无奈都觉得不是很妥当,在离家乡两千公里流浪的第一百天,到上海火车站北站赴友人之约时被二哥一把抓住,将你一路押回老家。才进家门,老妈大堂一坐,二话不说要你拜了堂娶了妻。
守道义 戒酒戒赌
你常说:“一个画家,应该什么都画。”但有一样东西,你不画——虎。因为二哥张善子画老虎很出色。其实,你也能画虎,但刻意避讳。一次你酒后画的一幅虎图流落出去,不少商人登门出高价请你画虎,你后悔不迭,于是发誓从今以后誓不饮酒,也誓不画虎。果然从此你跟饮酒和画虎绝了缘。
除了戒饮酒和画虎之外,你还戒赌。二十七岁时你学会了打麻将,刚开始是偶一为之,后来越陷越深,有一次被人设下圈套,用家里祖传的无价之宝──王羲之的《曹娥碑帖》抵了赌债。母亲临终之前想看一看这件传家宝,你手足无措,欲哭无泪。幸好你的好友叶恭绰花重金购回这一珍宝归还给你!你后来在为叶恭绰的书画集作序时,把自己年轻时的这件荒唐事公布于众。朋友们劝你不必再自揭短处,你则坚持写进序文,一则让世人知道叶恭绰的高尚品德,二则让世人知道不经一堑不长一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可陷入泥淖。因为此事,你发誓至死不进赌场,也不让家人玩麻将,还严厉告诫子孙:“谁也不准进赌场,进了赌场就不是我张家的人。”

《仿唐人吉祥天女》为张大千临摩了一幅约五尺高的五代时期《吉祥天女像》。(网路图片)
战乱中的临摹与复制
可在家安分没几年,二十八岁的你总觉得有个人生理想需要去实现,所以决定出门游历、充实自我。在此之前的二十六岁,经历丧父之痛,你开始蓄胡,不料一留一辈子,成为你的着名识别标志。
那个军阀割据的时代,没有治安可言,头目间的争斗规模已不是冲动“血拼”,而是实枪“战争”。你可能早上出门上学去,就被路上的阿兵哥强行拉到军队里,当天就换上粗糙的军服准备出发去占领你同学的家乡。
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安然跨越了二、三个大头目与无数个小头目的地盘,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一路欣赏并临摹雄壮的山林美景。那段期间经由你独特的天赋、心灵感受与技法所呈现出的作品,后来大获好评。
当然,除了理想,人还是要填饱肚子。你填饱肚子的方式倒是相当极端——你复制古代知名画家的作品与技法,并藉其名贩卖牟利(你并没觉得理所当然,终你一生都在懊悔这段历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堪),造成这时你的仿古画还比你的创作原画更出名,还瞒过了许多专家的法眼。
比如有一次,中国北方最有名的画家兼收藏家陈半丁,对名画之鉴赏有一言九鼎之威,收藏之富,傲视北方。陈半丁声称新收集一册石涛画页,视为绝妙精品,为此特宴邀艺林名家到家中欣赏。你听说了,虽然未被邀请,为了一睹石涛画册,不请自到。陈半丁拿出宝贝画册,洋洋得意地正想展示,你却突然说:“是这个册子啊!不用看了,我知道。”陈半丁反问:“你知道什啊?”你朗声回答,第一页画的是啥,第二页是啥,包括题款、用印,都一一道来。陈半丁一一核对,丝毫不误,又惊又气。有人以为这本石涛画册曾到过你之手,不料,你竟说:“是我画的!”
曾有位大头目透过专业鉴定师,重金在全国蒐购他心仪画家的作品,后来却陆续发现买来的许多都是A+档仿冒品,一查之下追到生产工厂就是你,于是大头目找了个机会邀请三十来岁的你去他的地盘“吃个便饭”,在那个民主、人权、法治都属于未来式的时代,此行恐怕凶多吉少,而你倒也处之泰然,在简单交代了几时没回来就连络谁谁谁后,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单身赴会去了。没料想这位小你两岁,名叫“张学良”的年轻国府海陆空三军副统帅跟你一见如故,就此结下超过半世纪的友谊。
敦煌壁画金丽辉煌
四十二岁时你立下宏愿要将气势雄伟、结构严谨的敦煌石窟壁画依原尺寸临摹,恢复原作本来面目,于是携家带眷、浩浩荡荡前进敦煌,会携家带眷是因为你估计就当去游历半年,所以有家眷陪伴、顺便游山玩水、培养感情当然是最好。
这真的是个宏愿,别说七十年前地处沙漠中的敦煌是“黄沙旷野,不见茎草”,每天醒来到睡着之间,你都拿着蜡烛在山洞内外爬上爬下、对着壁画临摹画画,希望能将创作者的精神与呈现的神韵透过你的画笔精确地传达给世人。
敦煌夏日中午的气温与入夜后的温差真是“朝穿皮袄午穿纱”,凭藉达成使命般的意志,你乐此不疲,然而最终你心爱的人离你而去。而这趟预计半年的沙漠游历,你一待竟是两年半。此后,你作画有了全新的画风,从宋元明清的儒家风格,一下子回归北魏隋唐佛教艺术的金丽辉煌、庄严殊胜,敦煌时期的作品奠定你一生盛名的基础。
 >
>
张大千在敦煌。(网路图片)
走避红潮辗转漂泊
五十岁那年,中共夺取了政权,于是你离开了祖国,前往佛国子民的国家:印度。从家乡传来消息,中国共产党劫收了你成都的住宅,家人被迫迁至宅旁仆人房室居住。家中所藏古字画以及宋元古纸,价值连城多遭毁坏,你为之唏嘘不已。此外,中共判你“大千有三大罪状:种花一罪也,养猴子二罪也,好吃三罪也,于是议处罚五千单位以赎罪云云。”这些中共横加的迫害,使你馀生坚拒中共。
为了走避红潮,你举家迁往香港继而远走南美,费用来自忍痛出售收藏的两幅珍品: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这一次,你带了黑白猿六只、波斯猫、杂色猫各四只、名犬四头,箱笼论百计,在阿根廷住了一年多,在巴西一住十六年。

这幅张大千的《鱼篮观音》在绘画风格上敢于用重彩重色,用笔极为工整,线条勾勒严谨,流畅细腻,笔笔劲到。可谓大千敦煌归来之后的精品。(网路图片)
见识毕卡索从美好到丑怪
巴西定居期间你已逐渐享誉国际,在巴黎罗浮宫展览之际,会晤西方绘画大师毕卡索,他对你说:“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他再强调一句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
回南美,毕卡索赠给你一幅画,画上只见硕大的一张脸,五官不具人形,胡子剑拔驽张。当人问起怎么选了这样一幅画呢?你赶紧澄清是夫人徐雯波弄出来的一场“误会”。原来是这幅画太丑怪惹得夫人好奇问道:“这张画的是啥子呀?”毕卡索以为你太太对这幅画感兴趣,于是破例题名送画。
一九六二年,你收到了毕卡索为你画的像,有廿七幅之多。你说:“头几张还好,后来越变越难看,越来越怪了。”你看过他年轻时的画,讲究基本功,一点儿也不怪。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毕卡索与张大千夫妇合影于他古堡的花园里。(网路图片)
活跃国际画坛
此后二十年间,你持续在欧洲布鲁塞尔、雅典、马德里、日内瓦等地展出新作,建立国际地位,欧、美、亚等洲际间的画展不断,恰好藉此旅游世界各地。
你的六屏巨幅荷花在纽约展出时被美国《读者文摘》以十四万美金购藏,可见当时国际对你艺术成就的认同,这种认同绝不是自古中国文人一向互相抬举恭维的小圈圈可以比拟的。
七十岁的你再度面临驿马星动,巴西政府为了要建水坝决定征收你位在巴西的家,于是迁居友朋集聚、风光明媚的美国加州,顺便治疗一下你已经健康欠佳的身体,这一住又是七年。
八十岁的你有了传统“落叶归根”的思维,但赤色故土让你却步,在结束周游列国的三十年旅程后,即使对四川的乡愁已接近满溢,你终究选择回到台北,低吟着:“不见巴人做巴语,争教蜀客邻蜀山。垂老不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
此时你的创作力依然旺盛,不断筹办近作展览。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年,正如烟花到达夜空最高点时,喷散出耀眼炫丽的光芒一般,你绘制生平最大、最壮丽的一幅代表作《庐山图》。也像烟火放光之后不久就在夜空归于黯淡沉寂,在回到台北七年之后,你在这个城市长辞此生因缘。
两袖清风
你是一个非常慷慨豪迈的人,就算在不算宽裕的经济状况下,你仍大规模的捐赠敦煌时期的六十二件临摹作品,这些作品二十多年前粗估已价值港币七百万之谱。你的家人也秉持你的遗言,将你珍藏的九十四件古代书画悉数捐出,其价值更是难以估算。你苦心经营、耗费钜资的终点站(在台北市外双溪,占地约五百七十八坪,两层四合院的居屋占二百二十二坪)也同时捐给国家成立纪念馆供后人凭吊。
在该捐的都捐了后,虽然后事备极哀荣,总统特派员慰唁家属,党国要员主持治丧,国内外新闻争相报导,海峡两岸的喧腾瞩目,可谓仅次于元首国丧,但你的身后费用竟然多为故交至友所筹措,两袖清风如此,正映照了当时总统所颁挽额“亮节高风”一语。
正如徐悲鸿所誉的“五百年来第一人”,你这一生的故事真可称之为“传奇”。
原题目:张大千传奇 五百年来一大千 (有删节)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第七十四期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张大千幼时,家贫,曾随母、姊、兄学画,打下了绘画基础。后人重庆求精中学读书,十八岁时,张大千随兄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二十岁时,张大千由日本回国,寓居上海,曾先后拜名书法家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接着因婚姻问题,削发出家,当了一百多天和尚。还俗后,即以其佛门法名“大千”为号,从此全身心致力于书画。

张大千(网路图片)
两个一百天奇特经历
张大千一生入世甚深,“他生来就很特异的,像只猴子似的。”(宣化和尚语),所以我就用较为轻松的笔调映照大师的个性,聊表纪念与敬意。 十岁前就开始习画的你,在十七岁读中学时放学回家的路上突遭绑架,绑匪逼迫你写信以便勒索家人,却惊异于你写得一手好字,不但没伤害你,居然奉你为黑帮顾问,你在虚与委蛇了约一百天后终于重获自由。
二十一岁时,挚爱的青梅竹马兼未婚妻因病往生,从日本兼程到上海的你却因兵荒马乱、道路不靖无法赶回四川老家见她最后一面而伤心欲绝,因此萌生遁世念头,不顾家人反对,准备出家当和尚。但你发现和尚受戒要点戒疤,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太有主见的你跟住持辩论起来:“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流行烧戒。这个花样是梁武帝创造的。当年,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以为,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在得不到满意答覆之际,你匆忙离开寺庙。向佛之心甚强的你辗转挂单几处,无奈都觉得不是很妥当,在离家乡两千公里流浪的第一百天,到上海火车站北站赴友人之约时被二哥一把抓住,将你一路押回老家。才进家门,老妈大堂一坐,二话不说要你拜了堂娶了妻。
守道义 戒酒戒赌
你常说:“一个画家,应该什么都画。”但有一样东西,你不画——虎。因为二哥张善子画老虎很出色。其实,你也能画虎,但刻意避讳。一次你酒后画的一幅虎图流落出去,不少商人登门出高价请你画虎,你后悔不迭,于是发誓从今以后誓不饮酒,也誓不画虎。果然从此你跟饮酒和画虎绝了缘。
除了戒饮酒和画虎之外,你还戒赌。二十七岁时你学会了打麻将,刚开始是偶一为之,后来越陷越深,有一次被人设下圈套,用家里祖传的无价之宝──王羲之的《曹娥碑帖》抵了赌债。母亲临终之前想看一看这件传家宝,你手足无措,欲哭无泪。幸好你的好友叶恭绰花重金购回这一珍宝归还给你!你后来在为叶恭绰的书画集作序时,把自己年轻时的这件荒唐事公布于众。朋友们劝你不必再自揭短处,你则坚持写进序文,一则让世人知道叶恭绰的高尚品德,二则让世人知道不经一堑不长一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可陷入泥淖。因为此事,你发誓至死不进赌场,也不让家人玩麻将,还严厉告诫子孙:“谁也不准进赌场,进了赌场就不是我张家的人。”

《仿唐人吉祥天女》为张大千临摩了一幅约五尺高的五代时期《吉祥天女像》。(网路图片)
战乱中的临摹与复制
可在家安分没几年,二十八岁的你总觉得有个人生理想需要去实现,所以决定出门游历、充实自我。在此之前的二十六岁,经历丧父之痛,你开始蓄胡,不料一留一辈子,成为你的着名识别标志。
那个军阀割据的时代,没有治安可言,头目间的争斗规模已不是冲动“血拼”,而是实枪“战争”。你可能早上出门上学去,就被路上的阿兵哥强行拉到军队里,当天就换上粗糙的军服准备出发去占领你同学的家乡。
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安然跨越了二、三个大头目与无数个小头目的地盘,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一路欣赏并临摹雄壮的山林美景。那段期间经由你独特的天赋、心灵感受与技法所呈现出的作品,后来大获好评。
当然,除了理想,人还是要填饱肚子。你填饱肚子的方式倒是相当极端——你复制古代知名画家的作品与技法,并藉其名贩卖牟利(你并没觉得理所当然,终你一生都在懊悔这段历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堪),造成这时你的仿古画还比你的创作原画更出名,还瞒过了许多专家的法眼。
比如有一次,中国北方最有名的画家兼收藏家陈半丁,对名画之鉴赏有一言九鼎之威,收藏之富,傲视北方。陈半丁声称新收集一册石涛画页,视为绝妙精品,为此特宴邀艺林名家到家中欣赏。你听说了,虽然未被邀请,为了一睹石涛画册,不请自到。陈半丁拿出宝贝画册,洋洋得意地正想展示,你却突然说:“是这个册子啊!不用看了,我知道。”陈半丁反问:“你知道什啊?”你朗声回答,第一页画的是啥,第二页是啥,包括题款、用印,都一一道来。陈半丁一一核对,丝毫不误,又惊又气。有人以为这本石涛画册曾到过你之手,不料,你竟说:“是我画的!”
曾有位大头目透过专业鉴定师,重金在全国蒐购他心仪画家的作品,后来却陆续发现买来的许多都是A+档仿冒品,一查之下追到生产工厂就是你,于是大头目找了个机会邀请三十来岁的你去他的地盘“吃个便饭”,在那个民主、人权、法治都属于未来式的时代,此行恐怕凶多吉少,而你倒也处之泰然,在简单交代了几时没回来就连络谁谁谁后,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单身赴会去了。没料想这位小你两岁,名叫“张学良”的年轻国府海陆空三军副统帅跟你一见如故,就此结下超过半世纪的友谊。
敦煌壁画金丽辉煌
四十二岁时你立下宏愿要将气势雄伟、结构严谨的敦煌石窟壁画依原尺寸临摹,恢复原作本来面目,于是携家带眷、浩浩荡荡前进敦煌,会携家带眷是因为你估计就当去游历半年,所以有家眷陪伴、顺便游山玩水、培养感情当然是最好。
这真的是个宏愿,别说七十年前地处沙漠中的敦煌是“黄沙旷野,不见茎草”,每天醒来到睡着之间,你都拿着蜡烛在山洞内外爬上爬下、对着壁画临摹画画,希望能将创作者的精神与呈现的神韵透过你的画笔精确地传达给世人。
敦煌夏日中午的气温与入夜后的温差真是“朝穿皮袄午穿纱”,凭藉达成使命般的意志,你乐此不疲,然而最终你心爱的人离你而去。而这趟预计半年的沙漠游历,你一待竟是两年半。此后,你作画有了全新的画风,从宋元明清的儒家风格,一下子回归北魏隋唐佛教艺术的金丽辉煌、庄严殊胜,敦煌时期的作品奠定你一生盛名的基础。
 >
>张大千在敦煌。(网路图片)
走避红潮辗转漂泊
五十岁那年,中共夺取了政权,于是你离开了祖国,前往佛国子民的国家:印度。从家乡传来消息,中国共产党劫收了你成都的住宅,家人被迫迁至宅旁仆人房室居住。家中所藏古字画以及宋元古纸,价值连城多遭毁坏,你为之唏嘘不已。此外,中共判你“大千有三大罪状:种花一罪也,养猴子二罪也,好吃三罪也,于是议处罚五千单位以赎罪云云。”这些中共横加的迫害,使你馀生坚拒中共。
为了走避红潮,你举家迁往香港继而远走南美,费用来自忍痛出售收藏的两幅珍品: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这一次,你带了黑白猿六只、波斯猫、杂色猫各四只、名犬四头,箱笼论百计,在阿根廷住了一年多,在巴西一住十六年。

这幅张大千的《鱼篮观音》在绘画风格上敢于用重彩重色,用笔极为工整,线条勾勒严谨,流畅细腻,笔笔劲到。可谓大千敦煌归来之后的精品。(网路图片)
见识毕卡索从美好到丑怪
巴西定居期间你已逐渐享誉国际,在巴黎罗浮宫展览之际,会晤西方绘画大师毕卡索,他对你说:“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他再强调一句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
回南美,毕卡索赠给你一幅画,画上只见硕大的一张脸,五官不具人形,胡子剑拔驽张。当人问起怎么选了这样一幅画呢?你赶紧澄清是夫人徐雯波弄出来的一场“误会”。原来是这幅画太丑怪惹得夫人好奇问道:“这张画的是啥子呀?”毕卡索以为你太太对这幅画感兴趣,于是破例题名送画。
一九六二年,你收到了毕卡索为你画的像,有廿七幅之多。你说:“头几张还好,后来越变越难看,越来越怪了。”你看过他年轻时的画,讲究基本功,一点儿也不怪。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毕卡索与张大千夫妇合影于他古堡的花园里。(网路图片)
活跃国际画坛
此后二十年间,你持续在欧洲布鲁塞尔、雅典、马德里、日内瓦等地展出新作,建立国际地位,欧、美、亚等洲际间的画展不断,恰好藉此旅游世界各地。
你的六屏巨幅荷花在纽约展出时被美国《读者文摘》以十四万美金购藏,可见当时国际对你艺术成就的认同,这种认同绝不是自古中国文人一向互相抬举恭维的小圈圈可以比拟的。
七十岁的你再度面临驿马星动,巴西政府为了要建水坝决定征收你位在巴西的家,于是迁居友朋集聚、风光明媚的美国加州,顺便治疗一下你已经健康欠佳的身体,这一住又是七年。
八十岁的你有了传统“落叶归根”的思维,但赤色故土让你却步,在结束周游列国的三十年旅程后,即使对四川的乡愁已接近满溢,你终究选择回到台北,低吟着:“不见巴人做巴语,争教蜀客邻蜀山。垂老不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
此时你的创作力依然旺盛,不断筹办近作展览。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年,正如烟花到达夜空最高点时,喷散出耀眼炫丽的光芒一般,你绘制生平最大、最壮丽的一幅代表作《庐山图》。也像烟火放光之后不久就在夜空归于黯淡沉寂,在回到台北七年之后,你在这个城市长辞此生因缘。
两袖清风
你是一个非常慷慨豪迈的人,就算在不算宽裕的经济状况下,你仍大规模的捐赠敦煌时期的六十二件临摹作品,这些作品二十多年前粗估已价值港币七百万之谱。你的家人也秉持你的遗言,将你珍藏的九十四件古代书画悉数捐出,其价值更是难以估算。你苦心经营、耗费钜资的终点站(在台北市外双溪,占地约五百七十八坪,两层四合院的居屋占二百二十二坪)也同时捐给国家成立纪念馆供后人凭吊。
在该捐的都捐了后,虽然后事备极哀荣,总统特派员慰唁家属,党国要员主持治丧,国内外新闻争相报导,海峡两岸的喧腾瞩目,可谓仅次于元首国丧,但你的身后费用竟然多为故交至友所筹措,两袖清风如此,正映照了当时总统所颁挽额“亮节高风”一语。
正如徐悲鸿所誉的“五百年来第一人”,你这一生的故事真可称之为“传奇”。
原题目:张大千传奇 五百年来一大千 (有删节)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第七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