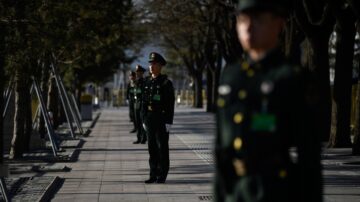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8月6日讯】【导读】战争当然免不了殃及无辜,但仁义之师总是要设法减轻人民的痛苦和牺牲。在国共战争期间及建政后,中共一直宣传共军如何纪律严明,如何得到老百姓支持。但如果我们透过党化历史的表层,走入它的幕后,就会发现这个“解放”的过程并非是一片阳光灿烂。比如极其惨烈(当然是对国军士兵和当地市民而言)的长春围困战。
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长春至此成为被共军及其根据地重重包围的一座孤岛。那时守长春的是郑洞国的10万人马,郑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都是威名赫赫的抗战名将。长春显然是一块硬骨头,四野要想强攻,肯定要付出巨大代价。这样的事,共军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干的,于是就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自然,共军也有本钱这样做。那时四野主力都南下打锦州、沈阳了,围攻长春的共军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队和民兵,但论人数却是长春守军的2、3倍,老郑因此也不敢贸然突围。于是,在长春形成了僵持局面。
围城最关键的是断绝外部的粮食和弹药供应,将敌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6月28日的围城政工会议上,萧劲光、萧华领衔的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萧华在会议上说:“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然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围城之初,由于顾及民心士气及面子,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开长春,但由于城中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要求平民离开长春,老百姓当然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但共军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围困长春满三个月后,9月9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等人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的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引起死亡”。他们还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这是毛在不便明确否决时经常采取的“默否”伎俩——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和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向毛请战,都曾遭遇过这种“默否”。林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下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真正实行,原因可能是毛否决了它。

共军的枪口对着出城的百姓(网络图片)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共军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 8月,段的夫人和儿子因家里断粮,也曾到真空地带(即“卡空”)呆了几天,自然也逃不出去,回来后母子俩很多天精神失常,哭泣无言。后来,儿子对段说,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尸臭难闻,真吓死人。
尽管老百姓不许出城,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却被放出,如有难民回忆:“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呆了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国军持械投诚。携枪逃亡的国军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据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
国军新一军重炮营少尉指导员胡长庚的日记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了佐证。 6月27日,胡记道:“有很多徒步赴沈(阳)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来。听说还有许多老百姓在卡子外面,这面不让进,那面不让走,没有吃的,饿都快饿死了”。 7月1日:“苗太太说她和她母亲、孩子这次走路没走成回来,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横说竖说就是一个不放。你给他们跪下,他们也跪下声言是上面的命令,不敢违背,请原谅!……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饿死他们吗?难道八路军从此就不争取民众了吗?确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7月2日:“从卡子外面回来的退职军人也莫不叫苦连天,称道八路军的‘蜀道难’”。胡也提到“谁有枪就放谁出去”。 7月23日:“今天早晨送于副营长,他是同一个被俘放回的步兵营营长,一个传令兵一块走的,对八路放行的条件是一枝卡宾小自动步枪”。 7月16日的日记,还提到被俘放回的38团刘副团长等人的逃亡。 20日的日记又记载:刘副团长自九台发来电报,逃亡沿途“至为顺利,可勿念”。胡接着感慨:“想不到八路军如此仁义,管接还管送”。何以如此?虽然日记作者未提,但想必刘团副们未不了要提供枪支、望远镜,或者什么军事情报。
国军空投能力本就有限,再加上共军高射炮封锁,城里很快断粮,成了人间地狱。粮价飞涨,高梁米卖到2亿元一斤,豆饼卖到1.5亿元一斤,山货行存的牛皮、驴皮、马皮之类卖到2、3亿元一斤。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人甚至吃起了人肉。段克文提到,有人将小孩诱进屋里,一棒打死,然后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来。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回忆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人,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退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狗已经被人吃光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积极分子想入党,于是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倒地而死。但也有人只是被饿昏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但上哪找这样的米汤呢?国军的粮食也吃完了。国军能够做的,也仅仅是组织收尸队,24小时在马路上捡尸首。一边把尸体往车上扔,一边说“喂狗”。那时狗都吃人,长得膘肥体壮,而人再吃狗。
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门口,路边,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骨头架子。时值盛夏,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绿头蝇,蛆虫也是成片成片的。城外的共军说,最怕刮风,一刮风,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头昏脑涨。
当时的吉林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共方狱中曾交代说,长春饿死约16万人。长春人口本有50万人左右,中共进城时仅剩17万人(段文说仅剩6、7万人,疑为文字错误,其中围城初期由于封锁不严逃亡20万人左右)。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俱”。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认当时饿死12万人(后来尚传道回忆录里提供的也是这个数字)。参加围城的共军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没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段克文也提到,当时城里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心里极度不安,就自杀死了。

尸骨遍地的长春城(网络图片)
而在中共所谓“史诗性战争巨片”《大决战•辽沈战役》在演到长春“和平解放”时旁白道: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长春,这座塞外春城在长达7个月的围困后, “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蘋果掉落下来”(大意)。是的,若从“战争指导艺术”来说,长春之战确实称得上高明——长春曾是伪“满洲国”首都,经过日伪和国民党多年的经营,城防异常坚固,再加上有国民党第一兵团10多万精兵,若强攻,必致共军重大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高超的战争艺术”。后来,长春围困战竟然成了共军加以推广的“长春模式”,粟裕就曾说这一模式后来在“若干城市采用过”。
从古至今,类似的围城战不绝于书。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围困宋国首都河南商丘9个月,致使城内百姓“易子而食,析骨为爨”。公元757年唐将张巡困守睢阳(仍是河南商丘),共吃掉老人妇女小孩两三万人,被台湾杂文家柏杨先生骂作“禽兽”。长春围困战与这两次历史上的商丘围困战也有一个不同之处:长春守方国军对难民放行,而处于主动地位的攻城方共军却出于让这些百姓耗费敌方粮食,和制造大规模饥荒以瓦国军军士气的目的,却不许人们逃难!
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既然今天可以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当作克敌制胜的筹码,那么以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什么样的手段不可以采用呢?如此看来,1948年长春城内的灾难,与一二十年后的“大饥荒”和“文革”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呢?对于这样的历史,我们不想多说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祈愿中华大地,永世不要再遭遇这样的灾难了。
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长春至此成为被共军及其根据地重重包围的一座孤岛。那时守长春的是郑洞国的10万人马,郑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都是威名赫赫的抗战名将。长春显然是一块硬骨头,四野要想强攻,肯定要付出巨大代价。这样的事,共军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干的,于是就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自然,共军也有本钱这样做。那时四野主力都南下打锦州、沈阳了,围攻长春的共军基本上都是地方部队和民兵,但论人数却是长春守军的2、3倍,老郑因此也不敢贸然突围。于是,在长春形成了僵持局面。
围城最关键的是断绝外部的粮食和弹药供应,将敌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6月28日的围城政工会议上,萧劲光、萧华领衔的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萧华在会议上说:“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然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围城之初,由于顾及民心士气及面子,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开长春,但由于城中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要求平民离开长春,老百姓当然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但共军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围困长春满三个月后,9月9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等人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的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引起死亡”。他们还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这是毛在不便明确否决时经常采取的“默否”伎俩——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和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向毛请战,都曾遭遇过这种“默否”。林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下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真正实行,原因可能是毛否决了它。

共军的枪口对着出城的百姓(网络图片)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共军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其他人就再也不敢近前了。 8月,段的夫人和儿子因家里断粮,也曾到真空地带(即“卡空”)呆了几天,自然也逃不出去,回来后母子俩很多天精神失常,哭泣无言。后来,儿子对段说,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尸臭难闻,真吓死人。
尽管老百姓不许出城,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却被放出,如有难民回忆:“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呆了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国军持械投诚。携枪逃亡的国军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据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
国军新一军重炮营少尉指导员胡长庚的日记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了佐证。 6月27日,胡记道:“有很多徒步赴沈(阳)的人走不了又退了回来。听说还有许多老百姓在卡子外面,这面不让进,那面不让走,没有吃的,饿都快饿死了”。 7月1日:“苗太太说她和她母亲、孩子这次走路没走成回来,可受罪可苦啦!八路横说竖说就是一个不放。你给他们跪下,他们也跪下声言是上面的命令,不敢违背,请原谅!……不放走求生路的老百姓,要活活饿死他们吗?难道八路军从此就不争取民众了吗?确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7月2日:“从卡子外面回来的退职军人也莫不叫苦连天,称道八路军的‘蜀道难’”。胡也提到“谁有枪就放谁出去”。 7月23日:“今天早晨送于副营长,他是同一个被俘放回的步兵营营长,一个传令兵一块走的,对八路放行的条件是一枝卡宾小自动步枪”。 7月16日的日记,还提到被俘放回的38团刘副团长等人的逃亡。 20日的日记又记载:刘副团长自九台发来电报,逃亡沿途“至为顺利,可勿念”。胡接着感慨:“想不到八路军如此仁义,管接还管送”。何以如此?虽然日记作者未提,但想必刘团副们未不了要提供枪支、望远镜,或者什么军事情报。
国军空投能力本就有限,再加上共军高射炮封锁,城里很快断粮,成了人间地狱。粮价飞涨,高梁米卖到2亿元一斤,豆饼卖到1.5亿元一斤,山货行存的牛皮、驴皮、马皮之类卖到2、3亿元一斤。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人甚至吃起了人肉。段克文提到,有人将小孩诱进屋里,一棒打死,然后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来。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回忆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人,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退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狗已经被人吃光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积极分子想入党,于是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倒地而死。但也有人只是被饿昏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但上哪找这样的米汤呢?国军的粮食也吃完了。国军能够做的,也仅仅是组织收尸队,24小时在马路上捡尸首。一边把尸体往车上扔,一边说“喂狗”。那时狗都吃人,长得膘肥体壮,而人再吃狗。
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门口,路边,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骨头架子。时值盛夏,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绿头蝇,蛆虫也是成片成片的。城外的共军说,最怕刮风,一刮风,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头昏脑涨。
当时的吉林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共方狱中曾交代说,长春饿死约16万人。长春人口本有50万人左右,中共进城时仅剩17万人(段文说仅剩6、7万人,疑为文字错误,其中围城初期由于封锁不严逃亡20万人左右)。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俱”。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认当时饿死12万人(后来尚传道回忆录里提供的也是这个数字)。参加围城的共军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没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段克文也提到,当时城里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心里极度不安,就自杀死了。

尸骨遍地的长春城(网络图片)
而在中共所谓“史诗性战争巨片”《大决战•辽沈战役》在演到长春“和平解放”时旁白道: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长春,这座塞外春城在长达7个月的围困后, “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蘋果掉落下来”(大意)。是的,若从“战争指导艺术”来说,长春之战确实称得上高明——长春曾是伪“满洲国”首都,经过日伪和国民党多年的经营,城防异常坚固,再加上有国民党第一兵团10多万精兵,若强攻,必致共军重大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高超的战争艺术”。后来,长春围困战竟然成了共军加以推广的“长春模式”,粟裕就曾说这一模式后来在“若干城市采用过”。
从古至今,类似的围城战不绝于书。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围困宋国首都河南商丘9个月,致使城内百姓“易子而食,析骨为爨”。公元757年唐将张巡困守睢阳(仍是河南商丘),共吃掉老人妇女小孩两三万人,被台湾杂文家柏杨先生骂作“禽兽”。长春围困战与这两次历史上的商丘围困战也有一个不同之处:长春守方国军对难民放行,而处于主动地位的攻城方共军却出于让这些百姓耗费敌方粮食,和制造大规模饥荒以瓦国军军士气的目的,却不许人们逃难!
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既然今天可以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当作克敌制胜的筹码,那么以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什么样的手段不可以采用呢?如此看来,1948年长春城内的灾难,与一二十年后的“大饥荒”和“文革”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呢?对于这样的历史,我们不想多说了。只是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祈愿中华大地,永世不要再遭遇这样的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