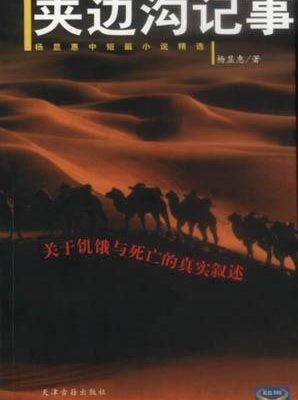夹边沟的酷暑严寒,映照着荒唐的时代、时代的悲凉。
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常常刮来八级大风。夹边沟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三千多名“极右份子”从甘肃各地被放逐至此进行劳动改造。在大跃进的战歌下,右派份子终日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忍饥挨饿,尊严全无。在这里,他们不再是科学家、工程师、博士、编辑。他们,只是一群被压在谷底、感受地狱、与死亡搏斗的蝼蚁。2003年,天津作家杨显惠出版了《夹边沟记事》一书,揭开了当年的恐怖真相。和凤鸣女士的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也提到了夹边沟农场的惨剧。她的丈夫王景超就饿死在那里。
傅作恭,水利专家,在堂兄傅作义的劝说下,从美国归来,报效祖国。为了支援甘肃水利建设,他欣然到兰州工作,结果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年过半百的他每天饥饿难耐,体力不支,于是向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收信后,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回信中对他批评教育。1960年冬季的一天,傅作恭实在饿得不行了,想去抠点猪食充饥,结果倒在了农场场部的猪圈旁,再也没有起来。大雪覆盖了他的身体。
董坚毅,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1952年回到上海,任惠民医院泌尿科主任。1955年,董坚毅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董坚毅被定为右派份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转到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董坚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向组长刘文汉交待如何用衣被和毛毯包裹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去世,年仅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掩埋。七、八天后,董坚毅的妻子顾晓颖千里迢迢又一次从上海前来探望,却被告知丈夫已死。当难友们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时,却发现尸体被抛在荒野,裹尸的毛毯、鸭绒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只剩下紫色的头颅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难友们找来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最后刘文汉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顾晓颖带回上海。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送到夹边沟。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1960年春,沈大文体弱不支,走不动路,却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这位教授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一天夜里,沈大文说,他想吃个糜子面饼饼,室友想方设法为他弄来两个,但是次日清晨,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身体已经冰凉。
“反右运动”是中共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当时,中共使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当人们认真的向党提出意见以后,中共翻脸不认账,将实话实说的人划为“右派份子”。一夜之间,对党忠心耿耿的各界人员降为政治贱民。这些右派按照罪行的轻重被依次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受到前两类处罚的人员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大批右派相继死亡。
《九评共产党》在【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中写:“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在这场运动中,甘肃日报编辑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极右份子,和凤鸣受到牵连,成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二人一同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在十工农场,王景超到了夹边沟。1961年元月上旬,和凤鸣带着积攒多时的牛羊肉、花卷、粮票和钱,辗转到夹边沟农场看望王景超,却得到了他的死讯。
和凤鸣写:“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
“原来,这个世道就是叫人们去饿死的,我的亲人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已饿死了,一切的一切,依然还都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运行。”“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特别是在作为党的喉舌及驯服工具的甘肃日报社,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
她的回忆录记录了当年饿死人的惨状。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们吃掉了。死难者的遗体掩埋得十分草率,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
杨显惠在《夹边沟纪事》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有人说,夹边沟是“右派份子”的“死亡集中营”。近六十年前,数以千计的尸骨,被狂风扫落,葬在荒僻之地,留下一段骇人听闻的惨烈。
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荒唐,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昨天。许多真相,被黄沙掩埋。今日,相似的悲剧,还在上演。尊严被羞辱,生命被虐杀。红色的机器,仍在运转。同胞的冤情凄惨,民族的苦难深重。不应忘却,亟待反思。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常常刮来八级大风。夹边沟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三千多名“极右份子”从甘肃各地被放逐至此进行劳动改造。在大跃进的战歌下,右派份子终日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忍饥挨饿,尊严全无。在这里,他们不再是科学家、工程师、博士、编辑。他们,只是一群被压在谷底、感受地狱、与死亡搏斗的蝼蚁。2003年,天津作家杨显惠出版了《夹边沟记事》一书,揭开了当年的恐怖真相。和凤鸣女士的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也提到了夹边沟农场的惨剧。她的丈夫王景超就饿死在那里。
活活饿死的留美科学家
傅作恭,水利专家,在堂兄傅作义的劝说下,从美国归来,报效祖国。为了支援甘肃水利建设,他欣然到兰州工作,结果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年过半百的他每天饥饿难耐,体力不支,于是向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收信后,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回信中对他批评教育。1960年冬季的一天,傅作恭实在饿得不行了,想去抠点猪食充饥,结果倒在了农场场部的猪圈旁,再也没有起来。大雪覆盖了他的身体。
董坚毅,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1952年回到上海,任惠民医院泌尿科主任。1955年,董坚毅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董坚毅被定为右派份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转到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董坚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向组长刘文汉交待如何用衣被和毛毯包裹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去世,年仅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掩埋。七、八天后,董坚毅的妻子顾晓颖千里迢迢又一次从上海前来探望,却被告知丈夫已死。当难友们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时,却发现尸体被抛在荒野,裹尸的毛毯、鸭绒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只剩下紫色的头颅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难友们找来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最后刘文汉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顾晓颖带回上海。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送到夹边沟。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1960年春,沈大文体弱不支,走不动路,却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这位教授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一天夜里,沈大文说,他想吃个糜子面饼饼,室友想方设法为他弄来两个,但是次日清晨,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身体已经冰凉。
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中共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当时,中共使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当人们认真的向党提出意见以后,中共翻脸不认账,将实话实说的人划为“右派份子”。一夜之间,对党忠心耿耿的各界人员降为政治贱民。这些右派按照罪行的轻重被依次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受到前两类处罚的人员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爆发了全国性的饥荒,大批右派相继死亡。
《九评共产党》在【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中写:“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份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份,就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在这场运动中,甘肃日报编辑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极右份子,和凤鸣受到牵连,成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二人一同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在十工农场,王景超到了夹边沟。1961年元月上旬,和凤鸣带着积攒多时的牛羊肉、花卷、粮票和钱,辗转到夹边沟农场看望王景超,却得到了他的死讯。
和凤鸣写:“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
“原来,这个世道就是叫人们去饿死的,我的亲人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已饿死了,一切的一切,依然还都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运行。”“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特别是在作为党的喉舌及驯服工具的甘肃日报社,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
她的回忆录记录了当年饿死人的惨状。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们吃掉了。死难者的遗体掩埋得十分草率,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
杨显惠在《夹边沟纪事》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有人说,夹边沟是“右派份子”的“死亡集中营”。近六十年前,数以千计的尸骨,被狂风扫落,葬在荒僻之地,留下一段骇人听闻的惨烈。
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荒唐,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昨天。许多真相,被黄沙掩埋。今日,相似的悲剧,还在上演。尊严被羞辱,生命被虐杀。红色的机器,仍在运转。同胞的冤情凄惨,民族的苦难深重。不应忘却,亟待反思。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