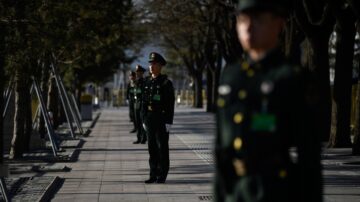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7月22日讯】【导读】画家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17岁的他作为知识青年在江西赣南山区插队落户,1977年借国家恢复高考之际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从而结束了他的知青生涯。2009年1月,他的文集《荒废集》出版。其中收录了略带删减的《幸亏年轻》一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他亲历的70年代的风风雨雨。《荒废集》一书也因这篇文章得名,意指七十年代中,被荒废了的几代人的命运。

1967年,乘客在营口火车站停车时
必须全体下车,跳忠字舞,然后再上车。(网路图片)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而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怀念七十年代。下面是陈丹青先生的《幸亏年轻》全文。
(接上集)
上海弄堂影像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上海要拆除的老房子。(网路图片)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隈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竿,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尼克松访华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力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

周恩来在上海设宴款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用筷子就餐。(网路图片)
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中国新年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36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中国新年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廖廖,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1976年4月,由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网路图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像)。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 ——“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七十年代大事记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泽东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义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北京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网路图片)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泽东死,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拴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 “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颠——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七十年代末的音乐和文艺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滨》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W潮、美国嘻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柯西斯的《计程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伦农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惟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 “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淑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要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整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七十年代被忘却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艾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艾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帐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人文与道德,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溃散,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的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帐滥帐糊涂帐,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大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最为优美的内心体验,是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那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常态时期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日后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剧情,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完)
原标题: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1967年,乘客在营口火车站停车时
必须全体下车,跳忠字舞,然后再上车。(网路图片)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而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怀念七十年代。下面是陈丹青先生的《幸亏年轻》全文。
(接上集)
上海弄堂影像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上海要拆除的老房子。(网路图片)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隈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竿,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尼克松访华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力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

周恩来在上海设宴款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用筷子就餐。(网路图片)
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中国新年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36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中国新年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廖廖,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1976年4月,由广州开往深圳的火车。(网路图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像)。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 ——“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七十年代大事记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泽东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义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北京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网路图片)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泽东死,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拴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 “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颠——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七十年代末的音乐和文艺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滨》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W潮、美国嘻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柯西斯的《计程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伦农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惟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 “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淑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要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整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七十年代被忘却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艾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艾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帐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人文与道德,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溃散,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的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帐滥帐糊涂帐,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大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最为优美的内心体验,是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那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常态时期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日后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剧情,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完)
原标题: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