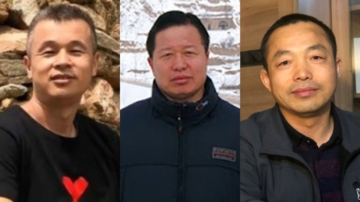在任何一个国家,观察他们的人权状况,评价这个国家、社会中人道价值的高度乃至人伦道德的现状,你最好去了解他们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普遍处境。我绝没有任何夸张的冲动,在中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道处境绝不在地狱以上。物理领域的黑暗是有限的,而人性的黑暗则是一个漫无边际、吞噬一切的黑洞,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监狱罪犯们永远面对的,1949年后只是进入了它的最黑暗时期。
中国历史上一直的是刑民不分,司法、行政合体,而更其可怕的是数千年竟没有生出过“刑事诉讼”这么个人间文明概念。侦、控、审合为一体,数千年的习惯就是,这些权力永远操控在一人之手,成就了人类司法史上最为野蛮、最为恐怖的恶记录,而从无改变冲动。
共产党抢得政权后,像其它所有领域一样,它在所有环节上会认认真真摹仿人类文明共有的形式。与公、检、法对应的侦、控、审,主导刑事诉讼的三大形式环节它一个不少。如果说封建专制时代,悉由地方行政长官一手在明处操控司法的话,共产党却是躲在暗处的黑手。表面上,凡文明制度下的一切形式要件它一样不缺,所谓金玉其表。凡前台施实形式过程的所谓侦、控、审人员,他们就是传统艺人手里的提线木偶,他们背后提线操纵的就是中共的政法委。由于法院是最后的决论环节,所以它干脆在法院设立了一种日常的“提线操作”制度叫“审判委员会”制度(检察院设有党委控制的“检委会”),其成员由党的职务人员组成,他们并不具体审案,而案件的最终判决结论却必须由他们作出。真正具体审案的所谓“审判员”却只能在台前作煞有介事的欺骗性表演。
永忘不了律师资格考前辅导一位讲课老师在课堂上提到的一个事例。讲到烧死三百多个孩子的克拉玛依大火案开庭审理时,法庭设在一楼大庭,新疆政法委领导就坐阵二楼指挥,审判长中途数次休庭上楼汇报、接受具体指令。他说:“你觉得这就是人家的家事,辩护人就是个摆设。”
以我的案子为例,一切基调都由秘密警察头子于泓源定调,台前所有表演都得以定下的基调为剧本进行。从效益及实现目的的成本角度论,共匪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情形较封建专制时代更其的反动外加荒谬。
刑事诉讼的功能及普世价值便是为了保卫人的权利、安全及社会秩序,但很多情形下,中共恐怖组织主导的“刑事诉讼”却是公开地走了向反面。它就是一个冷酷吞噬人权的黑洞,而它本身即成了一个恐怖的犯罪过程。在中国,一个个体人的命运常会被不确定的环节所左右,而这种左右别人命运的力量则永远是确定的,那就是黑帮权力。大部分情形下它们会以台前道具的面孔“决定”行动,但一旦遇到法盲、流氓外加绝不怕羞耻的“领导同志”,表演便不会循着它们寻常的欺骗套路进行。诸如,以常规表演套路,对被告人的批捕及侦控得由“法定”的部门决定,至少在纸面上还是会“依法”云云。
但我曾在海口市中级法院主审的一起贪腐案件中,在检察院阶段阅卷时竟看到一份令人啼笑不适的《起诉意见书》,该起诉书一改以往依据什么什么法律的表演模式,起首直接为:根据吴长猿副省长的指示对被告人进行诉讼。但在后来的中级法院阅卷时则发现又归循了传统表演套路,戴上了“法律”的脸谱。
杨子立先生被构陷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卷中,竟然出现“重要思想”家、曾“在华莱氏面前谈笑风生”的江泽民的要求严惩的亲笔批示。在这种批示下,一切过程均得符合贯彻“严惩”的批示精神进行。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家,案卷里出现“国家领导”的批示,这是会使整个政坛巨震的大丑闻。但这却是一个有着特色的国度,上下一锅糊粥的法盲们,倒置人间的美丑、善恶、荣耻正是他们所以立足的根本。杨子案申诉阶段,我向外界公开了这一不加遮掩的反文明丑闻,邪恶当局安之若泰。但这种上下一桶浆糊的昏乱运作,给无数无声的人民造成了人生的巨大不幸,有的甚至是人生彻底的毁灭。我短暂的诉讼律师生涯,却经历过多起赤裸裸的冤案,铸就了我职业生涯里挥之不去的痛。
乌鲁木齐腾威市场被盗案,就是一起由沙区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个叫孟林富者主办的一起大冤案。我个人与孟只见过两面,未有过一次语言接触,无有个人芥蒂,但他却是我个人记忆生涯里面目最为狰狞的个体之一。孟只是利用了制度的恶,或竟是不自觉地被导入了制度的恶。
中共刑事诉讼程序与文明司法制度下以审判为主的价值运作状态不同,它们是完全以侦查价值为主。由侦查程序提挈着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局面。就是实践中形容它们是公安备料,检察院做饭,法院吃下模式。侦查阶段最恐怖的制度设计是由公安机关先抓人,然后在七天内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这七日内公安就得“拿出”其自行决定抓人合法的证据,而人就在他们手里、不受任何监督,酷刑成了普遍的“取证”方式——直接、方便、快捷而无任何风险。而检察批准逮捕后,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就剩下一种结局——无论如何得“有罪”,否则,公安、检方就算办了错案。名义上,检察院对公安办案过程有法律监督权,但批准逮捕后两家在同一案件上却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那就是被抓的人必须有罪,他们两家才能正确,冷酷的手段就成了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保证。对于冤狱者而言,这个过程生不如死,没有任何人会听他的申辩,而申辩又定会被认为是“不老实交待罪行”。冷血的酷刑,最终必能使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如实交待犯罪事实”。
乌鲁木齐腾威市场原属乌市邮政系统的临街楼产,租与别人而单位收取租金。市场主要销售高档音响及其它电器。案发夜被盗价值十馀万元的电器。我的委托人孙利军,与另外我记不起姓名者三个年轻人当晚在邮政局门卫处值夜,市场是在二楼,邮政单位值班室是一楼,事发当夜,孙他们值班室门口的一副梯子成了盗窃者的工具。因当天夜里有雪,梯子移动痕迹明显,案发后沙区分局刑警中队孟林富主办此案。
孟于第二天勘验完现场后认为当晚邮政局夜值的孙利军等三人有盗窃嫌疑,便抓捕了孙等三人,接下来,孟所有的一切“工作”就是使他们三个人承认盗窃。三个年轻人真所谓祸从天降,地狱般的噩运从被抓的当天夜里开始。孟当天夜里对孙利军实施了骇人听闻的酷刑,就是反覆将人悬空吊起来殴打、使劲捏孙的睪丸,每至生不如死时,孙大叫承认“盗窃”,一放下来就觉得太冤不肯配合“笔录”,经多次野蛮的过程后,孙“承认”了盗窃,并全按孟的口述,作出了与现场勘验情形完全“吻合”的“犯罪交待”。其他两人亦经历了同样生不如死的过程后也被逼“交待了犯罪事实”。孟因这个大案的“迅速破获”而立了功受奖,而孙等三个年轻人则需在监狱里度过每人十几年的囚禁。
中共公安在公、检、法三个环节里是最强势的,有时就是以赤裸裸的威胁来主导整个诉讼程序向着他们已设计好的方向进行。有一个绝对规律是,凡公安侦查人员心知肚明的冤案,他们百分之百地会来“旁听”案件审理,就在现场盯着检方、法院顺着他们的意思进行。该案“庭审”时,孟赫然在“法庭”就坐。警察的滥权只是恐怖的一部分,更其恐怖的是没有独立的审判。
十几年过去了,判决书定罪理由中的一句话使我永不能忘,即:“被告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这里公然地昭示了一切反动司法制度下的一个共有的邪恶规律——即虽然控方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罪,而被告也无法证明自己无罪,因此你就有罪。这种野蛮的定罪价值观使人毛骨悚然。在这个案件里,案发半年后,孟仍不停地补充“新的证据”,法院需要什么证据就补充什么!
孙利军们被迫“认罪”前被实施酷刑的场所对我们辩方,包括三名被告人本人都是个谜。这个案件“审理”中,对于“疑罪从无原则”、“法非证据排除原则”、“不得自证有罪原则”都是公然反动的。我在起草宪法时反覆思考过这个案件中我们需要吸取的记忆及思想,诸如我宪法里特别提到,对拘禁者的监禁,只能在法定的场所或设施中进行。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无底线的私念驱使下的人性的可怖,而更可怕的是可被这种坏人性恣肆利用,并总能予这种坏人性以实质性褒奖的邪恶制度。
我在执业中发现,中共公安侦查制度中竟存在一种被称为“特勤”的机制。这种机制的实际运行,是被我在不同时间里、在不同的法院阅卷时亲眼看到过三回的,证明了它的普遍存在。就是发展一种隐形的侦查人员,是刑事领域设置的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警察。他们甚至原本即是犯罪人员被雇用,有时就是赤裸裸地去培植、蛊惑犯罪,更其邪恶的是有时直接用毒品作道具制造犯罪。“特勤”就生活在普通社会人中间,伺机制造“大案”出来,以换取他们所在单位的立功、受奖或个人士途上的好处。但我印象中这类过程均发生在缉毒案中。
1997年,我被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指定为一起贩卖毒品案的被告人张衣不拉(东乡族)辩护。阅卷中我吃惊地发现卷中夹了些“机密”的材料。这起案件从头至尾就是“我公安特勤人员”经过精心筹划而导演的一起案件。
被告人张子善(张衣不拉的胞哥)多年不见的战友突然来找他,“对人热心,花钱又大方”。这“特勤”在一年的时间里于张子善营造了类亲兄弟般的关系,张子善对其总是大手大脚花钱很羡慕而又好奇,开始问及则必“不肯讲”,追问的多了则“很不情愿”地告诉了张,且发誓赌咒不允许外传。原来这老战友是在贩卖毒品,且告诉张“钱来的很快,非常的保险”,还大方地给张子善买了一辆农用车,然后便数月不见,后来又出现在张子善家,说是又去甘肃东乡县“做了一趟生艺(指贩毒),又赚了不少”,并说只要在甘肃东乡县有熟人便能弄到货(毒品),要能弄回来的话是一本万利,有多少他要多少。而张家兄弟老家正是甘肃东乡县(张是当兵复原后留在新疆的)。记忆中好像还提供了八千元的资金,张家兄弟的贪婪吞噬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张衣不拉的生命。
在这个案件中,我与审判人员进行过交涉,但无济于事。这“特勤人员”显然构成了犯罪,不能因着他有“我方特勤人员”的身份便可以逍遥法外。结果审判人说我脑子有病,说这是“我公安缉毒战线上常用的一种手段”。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再次看到贪欲人性的黑洞。“我方特勤”与其背后的操纵力量,他们精心并耐心地筹划、制造成了这样一起“特大贩毒案”。他们由于“经过一年多艰苦的侦查工作”破获了这起“特大贩毒案”而立了功、领了些奖金,可本案三被告(由于张家兄弟无现钱,他们把东乡县毒品卖主给带到新疆来,欲将八百克毒品卖给“特勤”时被抓)除了张子善被判死缓外,其馀两名被告马尤都斯(货主)和张衣不拉都已被枪决。
恶制度本身就是犯罪的一部分,他们利用了制度之恶,自己制造“大案要案”而“迅速侦破”,而法院成了肯定他们犯罪成绩的制度化工具。所以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思索,于刑事诉讼这方面我考虑的也最多。每个权利或人身保护的具体条款,都会与过去律师工作中的一些痛苦记忆相联系。
如不得在未成年子女面前暴力抓捕他们的父母,便与一个具体案件的野蛮暴行记忆有关。被告人严正在自己的家里被暴力抓捕过程成了其妻权女士尤其是未成年孩子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恶梦。她说几个月后自己还常在梦中被惊醒——因为孩子自那次受到惊吓后经常半夜惊叫、哭嚎。这野蛮制度的罪恶,是我们成年人对孩子们的心灵安全的一种亏欠。在非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得入室拘禁、不得夜晚入室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不得在夜里进行搜查诸条款形成,都与我在1998年严正案中的记忆有关,与孩子受惊吓后的痛苦感情及记忆有着联系。
诸如关于禁止在法定的场所及设施中拘禁的问题,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野蛮囚禁过程中,近八年的囚禁,在“法定”场所关押累计三年,其馀被非法囚禁在共产党私设的牢狱内的时间竟有近五年。国家,成了黑帮犯罪集团任意压迫人民的工具。
在对公民权利确定的起草过程中,另一个于思想感情里最醒目的权利保障内容便是,公民在公共场所被公职人员任意盘查、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对公民人身、随身物品的任意搜查问题,这在中共制下的中国是稀松平常的日常现象。事实上,中共从打家劫舍开始便历来如此,凡有它立足的地方,便会对控制区的人民实行这种野蛮的侮辱性的行径。这是对公民或直接是对人的一项基本自由权利的野蛮侵犯,是对人的人格尊严恣意践踏的活标本。
美国宪政史上也发生过公共场所对公民随身物品搜查的案例,却引发了大规模的辩论,终于还是对人权及宪法价值守护占据了上风,凡未经公民同意,公共场所的任意搜查,即便发现了诸如毒品等犯罪证据,亦不得对该公民进行指控,以保卫人权、保卫宪法原则不可撼动的神圣。社会、国家可以放纵明显的犯罪,但不可以为了一个具体的案件,而撼动国家法治原则的底线。这是未来中国人权及公民权利保护实践所必须持守的价值原则。
附:高智晟《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下载。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中国历史上一直的是刑民不分,司法、行政合体,而更其可怕的是数千年竟没有生出过“刑事诉讼”这么个人间文明概念。侦、控、审合为一体,数千年的习惯就是,这些权力永远操控在一人之手,成就了人类司法史上最为野蛮、最为恐怖的恶记录,而从无改变冲动。
共产党抢得政权后,像其它所有领域一样,它在所有环节上会认认真真摹仿人类文明共有的形式。与公、检、法对应的侦、控、审,主导刑事诉讼的三大形式环节它一个不少。如果说封建专制时代,悉由地方行政长官一手在明处操控司法的话,共产党却是躲在暗处的黑手。表面上,凡文明制度下的一切形式要件它一样不缺,所谓金玉其表。凡前台施实形式过程的所谓侦、控、审人员,他们就是传统艺人手里的提线木偶,他们背后提线操纵的就是中共的政法委。由于法院是最后的决论环节,所以它干脆在法院设立了一种日常的“提线操作”制度叫“审判委员会”制度(检察院设有党委控制的“检委会”),其成员由党的职务人员组成,他们并不具体审案,而案件的最终判决结论却必须由他们作出。真正具体审案的所谓“审判员”却只能在台前作煞有介事的欺骗性表演。
永忘不了律师资格考前辅导一位讲课老师在课堂上提到的一个事例。讲到烧死三百多个孩子的克拉玛依大火案开庭审理时,法庭设在一楼大庭,新疆政法委领导就坐阵二楼指挥,审判长中途数次休庭上楼汇报、接受具体指令。他说:“你觉得这就是人家的家事,辩护人就是个摆设。”
以我的案子为例,一切基调都由秘密警察头子于泓源定调,台前所有表演都得以定下的基调为剧本进行。从效益及实现目的的成本角度论,共匪体制下的司法运作情形较封建专制时代更其的反动外加荒谬。
刑事诉讼的功能及普世价值便是为了保卫人的权利、安全及社会秩序,但很多情形下,中共恐怖组织主导的“刑事诉讼”却是公开地走了向反面。它就是一个冷酷吞噬人权的黑洞,而它本身即成了一个恐怖的犯罪过程。在中国,一个个体人的命运常会被不确定的环节所左右,而这种左右别人命运的力量则永远是确定的,那就是黑帮权力。大部分情形下它们会以台前道具的面孔“决定”行动,但一旦遇到法盲、流氓外加绝不怕羞耻的“领导同志”,表演便不会循着它们寻常的欺骗套路进行。诸如,以常规表演套路,对被告人的批捕及侦控得由“法定”的部门决定,至少在纸面上还是会“依法”云云。
但我曾在海口市中级法院主审的一起贪腐案件中,在检察院阶段阅卷时竟看到一份令人啼笑不适的《起诉意见书》,该起诉书一改以往依据什么什么法律的表演模式,起首直接为:根据吴长猿副省长的指示对被告人进行诉讼。但在后来的中级法院阅卷时则发现又归循了传统表演套路,戴上了“法律”的脸谱。
杨子立先生被构陷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卷中,竟然出现“重要思想”家、曾“在华莱氏面前谈笑风生”的江泽民的要求严惩的亲笔批示。在这种批示下,一切过程均得符合贯彻“严惩”的批示精神进行。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家,案卷里出现“国家领导”的批示,这是会使整个政坛巨震的大丑闻。但这却是一个有着特色的国度,上下一锅糊粥的法盲们,倒置人间的美丑、善恶、荣耻正是他们所以立足的根本。杨子案申诉阶段,我向外界公开了这一不加遮掩的反文明丑闻,邪恶当局安之若泰。但这种上下一桶浆糊的昏乱运作,给无数无声的人民造成了人生的巨大不幸,有的甚至是人生彻底的毁灭。我短暂的诉讼律师生涯,却经历过多起赤裸裸的冤案,铸就了我职业生涯里挥之不去的痛。
乌鲁木齐腾威市场被盗案,就是一起由沙区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个叫孟林富者主办的一起大冤案。我个人与孟只见过两面,未有过一次语言接触,无有个人芥蒂,但他却是我个人记忆生涯里面目最为狰狞的个体之一。孟只是利用了制度的恶,或竟是不自觉地被导入了制度的恶。
中共刑事诉讼程序与文明司法制度下以审判为主的价值运作状态不同,它们是完全以侦查价值为主。由侦查程序提挈着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局面。就是实践中形容它们是公安备料,检察院做饭,法院吃下模式。侦查阶段最恐怖的制度设计是由公安机关先抓人,然后在七天内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这七日内公安就得“拿出”其自行决定抓人合法的证据,而人就在他们手里、不受任何监督,酷刑成了普遍的“取证”方式——直接、方便、快捷而无任何风险。而检察批准逮捕后,被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就剩下一种结局——无论如何得“有罪”,否则,公安、检方就算办了错案。名义上,检察院对公安办案过程有法律监督权,但批准逮捕后两家在同一案件上却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那就是被抓的人必须有罪,他们两家才能正确,冷酷的手段就成了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保证。对于冤狱者而言,这个过程生不如死,没有任何人会听他的申辩,而申辩又定会被认为是“不老实交待罪行”。冷血的酷刑,最终必能使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如实交待犯罪事实”。
乌鲁木齐腾威市场原属乌市邮政系统的临街楼产,租与别人而单位收取租金。市场主要销售高档音响及其它电器。案发夜被盗价值十馀万元的电器。我的委托人孙利军,与另外我记不起姓名者三个年轻人当晚在邮政局门卫处值夜,市场是在二楼,邮政单位值班室是一楼,事发当夜,孙他们值班室门口的一副梯子成了盗窃者的工具。因当天夜里有雪,梯子移动痕迹明显,案发后沙区分局刑警中队孟林富主办此案。
孟于第二天勘验完现场后认为当晚邮政局夜值的孙利军等三人有盗窃嫌疑,便抓捕了孙等三人,接下来,孟所有的一切“工作”就是使他们三个人承认盗窃。三个年轻人真所谓祸从天降,地狱般的噩运从被抓的当天夜里开始。孟当天夜里对孙利军实施了骇人听闻的酷刑,就是反覆将人悬空吊起来殴打、使劲捏孙的睪丸,每至生不如死时,孙大叫承认“盗窃”,一放下来就觉得太冤不肯配合“笔录”,经多次野蛮的过程后,孙“承认”了盗窃,并全按孟的口述,作出了与现场勘验情形完全“吻合”的“犯罪交待”。其他两人亦经历了同样生不如死的过程后也被逼“交待了犯罪事实”。孟因这个大案的“迅速破获”而立了功受奖,而孙等三个年轻人则需在监狱里度过每人十几年的囚禁。
中共公安在公、检、法三个环节里是最强势的,有时就是以赤裸裸的威胁来主导整个诉讼程序向着他们已设计好的方向进行。有一个绝对规律是,凡公安侦查人员心知肚明的冤案,他们百分之百地会来“旁听”案件审理,就在现场盯着检方、法院顺着他们的意思进行。该案“庭审”时,孟赫然在“法庭”就坐。警察的滥权只是恐怖的一部分,更其恐怖的是没有独立的审判。
十几年过去了,判决书定罪理由中的一句话使我永不能忘,即:“被告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这里公然地昭示了一切反动司法制度下的一个共有的邪恶规律——即虽然控方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罪,而被告也无法证明自己无罪,因此你就有罪。这种野蛮的定罪价值观使人毛骨悚然。在这个案件里,案发半年后,孟仍不停地补充“新的证据”,法院需要什么证据就补充什么!
孙利军们被迫“认罪”前被实施酷刑的场所对我们辩方,包括三名被告人本人都是个谜。这个案件“审理”中,对于“疑罪从无原则”、“法非证据排除原则”、“不得自证有罪原则”都是公然反动的。我在起草宪法时反覆思考过这个案件中我们需要吸取的记忆及思想,诸如我宪法里特别提到,对拘禁者的监禁,只能在法定的场所或设施中进行。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无底线的私念驱使下的人性的可怖,而更可怕的是可被这种坏人性恣肆利用,并总能予这种坏人性以实质性褒奖的邪恶制度。
我在执业中发现,中共公安侦查制度中竟存在一种被称为“特勤”的机制。这种机制的实际运行,是被我在不同时间里、在不同的法院阅卷时亲眼看到过三回的,证明了它的普遍存在。就是发展一种隐形的侦查人员,是刑事领域设置的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警察。他们甚至原本即是犯罪人员被雇用,有时就是赤裸裸地去培植、蛊惑犯罪,更其邪恶的是有时直接用毒品作道具制造犯罪。“特勤”就生活在普通社会人中间,伺机制造“大案”出来,以换取他们所在单位的立功、受奖或个人士途上的好处。但我印象中这类过程均发生在缉毒案中。
1997年,我被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指定为一起贩卖毒品案的被告人张衣不拉(东乡族)辩护。阅卷中我吃惊地发现卷中夹了些“机密”的材料。这起案件从头至尾就是“我公安特勤人员”经过精心筹划而导演的一起案件。
被告人张子善(张衣不拉的胞哥)多年不见的战友突然来找他,“对人热心,花钱又大方”。这“特勤”在一年的时间里于张子善营造了类亲兄弟般的关系,张子善对其总是大手大脚花钱很羡慕而又好奇,开始问及则必“不肯讲”,追问的多了则“很不情愿”地告诉了张,且发誓赌咒不允许外传。原来这老战友是在贩卖毒品,且告诉张“钱来的很快,非常的保险”,还大方地给张子善买了一辆农用车,然后便数月不见,后来又出现在张子善家,说是又去甘肃东乡县“做了一趟生艺(指贩毒),又赚了不少”,并说只要在甘肃东乡县有熟人便能弄到货(毒品),要能弄回来的话是一本万利,有多少他要多少。而张家兄弟老家正是甘肃东乡县(张是当兵复原后留在新疆的)。记忆中好像还提供了八千元的资金,张家兄弟的贪婪吞噬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张衣不拉的生命。
在这个案件中,我与审判人员进行过交涉,但无济于事。这“特勤人员”显然构成了犯罪,不能因着他有“我方特勤人员”的身份便可以逍遥法外。结果审判人说我脑子有病,说这是“我公安缉毒战线上常用的一种手段”。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再次看到贪欲人性的黑洞。“我方特勤”与其背后的操纵力量,他们精心并耐心地筹划、制造成了这样一起“特大贩毒案”。他们由于“经过一年多艰苦的侦查工作”破获了这起“特大贩毒案”而立了功、领了些奖金,可本案三被告(由于张家兄弟无现钱,他们把东乡县毒品卖主给带到新疆来,欲将八百克毒品卖给“特勤”时被抓)除了张子善被判死缓外,其馀两名被告马尤都斯(货主)和张衣不拉都已被枪决。
恶制度本身就是犯罪的一部分,他们利用了制度之恶,自己制造“大案要案”而“迅速侦破”,而法院成了肯定他们犯罪成绩的制度化工具。所以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思索,于刑事诉讼这方面我考虑的也最多。每个权利或人身保护的具体条款,都会与过去律师工作中的一些痛苦记忆相联系。
如不得在未成年子女面前暴力抓捕他们的父母,便与一个具体案件的野蛮暴行记忆有关。被告人严正在自己的家里被暴力抓捕过程成了其妻权女士尤其是未成年孩子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恶梦。她说几个月后自己还常在梦中被惊醒——因为孩子自那次受到惊吓后经常半夜惊叫、哭嚎。这野蛮制度的罪恶,是我们成年人对孩子们的心灵安全的一种亏欠。在非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得入室拘禁、不得夜晚入室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不得在夜里进行搜查诸条款形成,都与我在1998年严正案中的记忆有关,与孩子受惊吓后的痛苦感情及记忆有着联系。
诸如关于禁止在法定的场所及设施中拘禁的问题,我自己亲身经历的野蛮囚禁过程中,近八年的囚禁,在“法定”场所关押累计三年,其馀被非法囚禁在共产党私设的牢狱内的时间竟有近五年。国家,成了黑帮犯罪集团任意压迫人民的工具。
在对公民权利确定的起草过程中,另一个于思想感情里最醒目的权利保障内容便是,公民在公共场所被公职人员任意盘查、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对公民人身、随身物品的任意搜查问题,这在中共制下的中国是稀松平常的日常现象。事实上,中共从打家劫舍开始便历来如此,凡有它立足的地方,便会对控制区的人民实行这种野蛮的侮辱性的行径。这是对公民或直接是对人的一项基本自由权利的野蛮侵犯,是对人的人格尊严恣意践踏的活标本。
美国宪政史上也发生过公共场所对公民随身物品搜查的案例,却引发了大规模的辩论,终于还是对人权及宪法价值守护占据了上风,凡未经公民同意,公共场所的任意搜查,即便发现了诸如毒品等犯罪证据,亦不得对该公民进行指控,以保卫人权、保卫宪法原则不可撼动的神圣。社会、国家可以放纵明显的犯罪,但不可以为了一个具体的案件,而撼动国家法治原则的底线。这是未来中国人权及公民权利保护实践所必须持守的价值原则。
附:高智晟《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下载。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