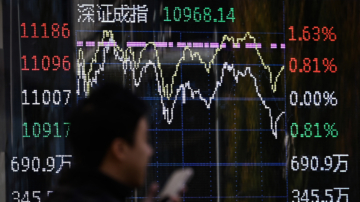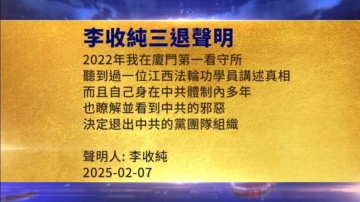【新唐人2019年05月03日訊】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在當今中國是否還有新聞自由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既簡單也不簡單。簡單的是,幾乎每天都有中共政府打壓媒體,或是企業、媒體本身自我審查的消息傳出來。不簡單的是,中國的媒體環境紛繁複雜,要有一定深度地回答這個問題還需要下番功夫。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家傲通過審視中國調查報導的興盛和衰亡的過程,從一個側面為中國的新聞自由現狀加上註解。
不到十年前,青島人紀許光還是紅極一時的中國調查記者。他2001年入職廣州羊城晚報報業集團,邁入了他的記者生涯。此後十幾年間,他先後在《民營經濟報》、《新快報》、《南方都市報》等媒體工作。他2006年涉足社會新聞,此後做了八年調查記者。
2012年,一篇名為《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的性愛視頻》的文章在網上傳開。正是紀許光在微博上實名舉報了這位中共重慶官員包養二奶的情況,並以不雅視頻截圖為證。為此,舉報人紀許光還上了央視新聞,描述他事後採訪雷政富的情節。
「雷政富表現得非常著急,當然他那個時候還是在矢口否認的,但是這都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沒有關係。也就是說,他有權對這個東西提出自己的意見。」
事件迅速發酵。此事曝光後不到三天,雷政富就被免職並立案調查。當年有人評價說,紀許光創造了中國網絡反腐史上的最快紀錄,號稱「63小時秒殺一個正廳級幹部」。
名記坐不住了
可就是這樣一位曾經風生水起的媒體人,卻越發感到力不從心。為了確保自身和家人的安全,紀許光於2014年攜妻兒移民美國。今天看來,他覺得中國調查新聞已經徹底迷失了方向。
「過去是屍橫遍野,未來是一片迷茫,走一步看一步吧。現在中國的這個情況,大家不要再談什麼新聞理想了。」
中國媒體環境正在惡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近日,致力於保護記者免受迫害、推進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國際組織公布了2019年新聞自由指數。中國較去年又下跌了一位,在180個國家中位居倒數第四,不及越南和古巴。
2018年4月25日,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祕書長克裡斯托弗·德魯爾(Christophe Deloire)在巴黎展示「2018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報告稱,中共越來越趨近於當代版本的極權主義,外國記者越來越難在中國開展工作。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了多位前中國調查記者,了解這個行業的當前形勢。雖然他們目前都沒有繼續全職從事調查報導,但一些記者仍在撰寫調查類報導。
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的輿論審查環境漸趨嚴峻,調查報導的選材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出於安全原因,部分受訪人表示不便透露真實身分,本台使用化名替代。
調查報導一向被認為是新聞業中投入最多、風險最高的「硬骨頭」。在中共官媒看來,調查報導是一個西方詞彙,他們更喜歡把這樣的文章稱作「深度報導」,也就是業內俗稱的「剝洋蔥」。
喪鐘為誰而鳴?
紀許光認為,中國調查新聞的空間已經幾近枯竭了。現在是苟延殘喘的階段,沒有什麼所謂的政治氧氣可言了。如果說中共不想讓你活的話,誰都活不了,這就是中國媒體的悲哀。
2014年,廣電總局在換發記者證時,首次要求所有中國記者參加全國統一考試,以便他們「更有意識地保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2016年,習近平在京召開輿論座談會時更是提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作為黨政宣傳陣地,這些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
黨媒「人民網」近日發布了一則首席調查記者的招聘啟事。其職位要求的第一點便是中共黨員,並要堅定「四個意識」、樹牢「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而記者的專業素質卻位居其次。
談到中國媒體的裡程碑事件,近年來引發國內外最大轟動的風波可能就是《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了。2013年1月3日,這家曾被外媒形容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報紙」的新年獻詞,在出版前被強行修改,而原本呼籲憲政的內容變成了對執政者的讚歌。
第二天,曾在這裡工作的50多名新聞人聯合發表公開信,要求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引咎辭職,而《南方週末》員工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還在其總部大樓外一度發生對峙。
「都說媒體是一個沒落的行業,我覺得的確是的。目前,國內很多還在媒體的人會不斷地給媒體唱讚歌,唱好調查報導,但實際上,中國大陸的媒體真的很不幸。可以說在2013年後,它已經面目全非了。」
瀕臨滅絕的物種
如果說不少媒體人感到中國調查新聞正在發生質變,那麼學界證明了它也在經歷空前的量變。
中山大學教授張志安2017年發布的《新媒體環境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顯示,調查新聞行業發生了嚴重的人才流失。經過雙重核實,他核定中國僅剩175名調查記者。與2011年首次調查結果相比,人數幾乎被腰斬。中國廣電總局數據顯示,國內持證記者人數在2017年超過了22.8萬人。這意味著每1300位中國記者中,平均只有一位是調查記者。
他還表示,調查新聞行業近年來承受了多重壓力。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媒的興起削弱了傳統媒體的文化權威,導致調查新聞面臨著社會影響力衰落的考驗。由於發行量下滑,這些傳統媒體的廣告費較往年大幅下降。為了節約成本,一些都市報裁減甚至撤銷了調查新聞部門(業內普遍稱之為「深度報導部」)。
另一方面,隨著黨政宣傳報導力度的增強,媒體主管部門及各級政府為了維穩,對敏感社會問題加強了行政管控,進一步壓縮了報導空間。
我還能報導什麼?
現中國某一線雜誌記者趙蕾2016年曾在《新京報》調查組實習過幾個月,此後她還在報社的突發組和深度人物組工作過,直到上個月跳槽。回顧在《新京報》的三年,趙蕾坦言,單位的報導尺度明顯縮水。
「我記得2016年年底前,其實報社的尺度是很大的。那個時候,北京很多負面的調查報導,比如說哪裡採礦死了人,大家還是可以報導的。但是2017年之後,就不太樂觀了。然後2018年,報導限制就更明顯了。」
她舉例說,繼2017年#MeToo(「我也是」)反性侵運動在美國好萊塢爆發後,中國「米兔」運動仍方興未艾。但當《新京報》前一陣兒想就此做些剖析時,她們就接到了主管部門的通知。
「我們就只是碰了一下,然後只要碰了,禁令就會來得非常快,後來我們就乾脆不碰了。所以米兔運動我們報導得非常少。」
趙蕾表示,她當年在調查組實習時組內的六七位全職記者目前都已離職,而接替他們的基本都是「90後」。她說,老一輩調查記者普遍都有自己的成名作,也相對更受人尊重。在中國調查新聞的黃金時代,他們留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作品。
懷念最好的時代
業界普遍認為,廣州《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峰2003年發表的《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一文,標誌著中國調查報導步入了黃金時代。這篇報導記載了在廣州工作的外來務工青年孫志剛因為沒有「暫住證」,被送至收容站後遭毆打身亡的事件。此事引發了中國社會對收容遣送制度的熱烈討論,並最終促成當局廢除這項制度。
此後幾年,中國調查新聞漸入巔峰。期間,多位記者因報導重大社會事件,他們的名字也與這些作品一道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烙印。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包括2005年《河南商報》記者范友峰發表的《一案兩凶,誰是真凶》,重啟塵封十多年的聶樹斌案,顯示他並不是本案真凶。
2008年,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發表《甘肅十四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的文章,完成了一起特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首次曝光;2010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發表《山西疫苗亂象調查》,揭露了當地的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
當中,王克勤由於長期從事調查報導,發表了無數引發社會強烈反響、推動政策法規變革的文章,被業界稱為「中國揭黑記者第一人」。即便已身經百戰,他還是沒能逃脫行業的變遷。2012年底,隨著他後來任職的《經濟觀察報》調查新聞部被解散,他淡出了新聞圈。作為大愛清塵公益基金發起人,他近年來致力於推動中國數百萬塵肺病農民的救助工作。
本台記者聯繫到了王克勤,但他表示,自己離開老本行已有多年,不便置評。
「我離開本行的時間很久了,也不便說什麼了。」
不光是他,很多前些年聲名大噪的調查記者也已告別了本職工作。就拿上面的例子來說,揭發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簡光洲在2012年8月離職。那一年,他在微博中說:「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目前,簡光洲在上海一家公關公司做總經理兼合伙人。
而對聶樹斌案提出質疑的范友峰也在報導發表後被辭職,而這起冤案最終在2016年得到平反。范友峰於2008年淡出新聞一線,從事廣告經營,目前擔任《新華每日電訊》副總經理。
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樓?
現居美國的前調查記者紀許光對中國調查新聞曾經的輝煌不屑一顧。他坦言,直到多年以後,他才漸漸意識到,這些調查記者其實都是中國政府的棋子,他們的生與死終究由不得自己。
「中國媒體從來就沒有什麼所謂的政治博弈的空間。共產黨之所以讓它活著,是因為黨內有一股力量需要它。當不需要它的時候、當黨的聲音要趨於一致的時候,不管你是誰,全都得死。」
說到觸碰當局紅線的新聞人,前調查記者劉虎或許就是一個例子。2013年,時任廣州《新快報》記者劉虎因實名舉報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涉嫌瀆職犯罪,被北京警方在其重慶家中以「造謠」罪名刑事拘留,直到近一年後才得以取保候審。
43歲的劉虎可謂是見證了中國調查新聞的大起大落。他2004年入職《重慶晨報》做機動記者,2008年來到《成都商報》作全國性報導。出獄後不久,他就與武漢《長江商報》簽約,繼續他的本職工作,並在此期間寫下了貴州茅台虛假廣告的調查報導。但就在這家報社因報導一系列敏感事件被勒令整頓後,劉虎於2015年離開紙媒,成為了自由媒體人。
劉虎的記者十年與這個行業一同沉浮,打磨了他犀利的觀點。他對本台記者表示,雖然中國調查新聞的下坡路看似也與市場動盪有關,但這到頭來還是政治環境的產物。
「市場形勢也是政治因素引起的。中國的輿論管制導致媒體不能報導一些事情。這導致了在市場化的媒體環境中,就沒有多少可看的東西,這造成了讀者的流失和訂閱量的下降,降低了對廣告主的吸引力。這樣的話,媒體的收入下降,很多媒體不得不縮減版面,有的直接就停刊了。」
人都需要好好生活
此外,一些年輕記者對調查新聞還存在一個心結,那就是薪水太低。北京某都市報前調查記者陳曉(化名)對本台表示,她們承受的壓力可以用一句俗話來概括:「女的當男的使,男的當牲口使。」
她表示,即便如此,很多都市報調查記者的基本工資都很低,而她們主要靠拿稿費過活。但由於調查報導通常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她感覺付出和收穫之間的反差太大。
「我原來的同事和現在(在調查組工作)的同事做調查新聞,其實心裡面並沒有想著要賺錢,我們都還是希望能做出一些東西、起到一些作用。但如果做的時間特別長,而經濟方面一直都趕不上你的付出的話,可能心裡也會有一些落差吧。」
前《新京報》調查組實習生趙蕾表示,據她從幾位業內人士了解到的情況,一篇四五千字的普通調查報導的稿費大概在6000到8000元不等,而特別出色的報導的稿費最高可能也不過一兩萬元。
陳曉說,自從她2015年底入職到去年調入報社的另一個部門,此前與她一同工作的調查記者都已離開了原崗位,他們中有的做起了企業公關,有的回老家投靠了當地媒體,有的和她一樣,進了報社的其他部門。她說,很多資歷豐富的調查記者如今都另謀高就了,而這其中不乏現實原因。
「有些人做了小領導,然後又去做公關,賺錢去了。有些人自主創業,做個自媒體,可能有更好的發展,然後就不會堅持做調查新聞了。調查新聞確實很苦很累,很耗時間。有時候你調查一件事,可能跟蹤好久都沒能作出報導。」
尋求心靈救贖
在與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的短信交流中,前調查記者紀許光坦言,移民美國五年來,他漸漸意識到自己不該再延續以往的「自我審查」了。但與此同時,作為調查記者,他理應身處最黑暗的新聞一線,而他現在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這也是他決定潛心學佛的重要原因。
「我的職業讓我看到了社會太多太多的陰暗面和人性之惡。但是佛教又被稱為圓教,它能夠給我們帶來心靈上的良好慰藉。」
紀許光痛斥中國如今的政治風向,他還留下了這樣一句話:「那個當今皇上,掉頭飆車!千古罪人!!」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文馨)